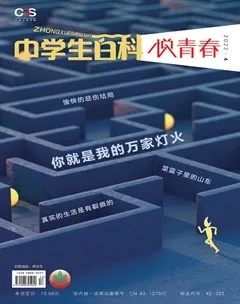愉快的悲伤结局
爱丽丝

下午三点的公交车像一个寒酸的储蓄罐,零星的乘客塞在绿色的铁皮罐子里,发出刺耳的声响。龙美伊坐在临窗的位置上,在奶油一般黏稠的阳光中昏昏欲睡,忽然听到一声训斥:“宠物不让上公交车。”
“可是,”少年的声音青涩,仿佛雨后的某种草本植物,“点点不是宠物,它是我的导盲犬。”
“那也不让上车,万一咬到人怎么办?”司机是个有脾气的中年男人,说话时语速极快,几乎水泼不进,“再说了,导盲犬哪有你这种杂色的?”
的确,导盲犬一般由金毛或者拉布拉多训练而来,或黄或白,毛色纯净。相比之下,少年脚边的狗明显不合格,一张极似金毛的脸上多了几块灰斑,压在脸上,仿佛古时候的黥面之刑。
龙美伊下意识摸了一下自己的脸,好像有火在烧。正是这份灼痛感迫使她站出来,像一個人质一般,颤抖地向外界发出了自己的求救信号:“公共交通工具允许工作犬乘坐,所以,你不该赶他下车。”
五分钟后,笨重的公交车再次启动,龙美伊和少年一起站在陈旧的公交站台前,被浓郁的汽车尾气呛了一脸。龙美伊揉了揉发红的鼻尖,忽然看到导盲犬将头搁在少年的脚背上,一双黑葡萄般的眼睛湿漉漉的,发出细微的呜咽声。

“没关系,你做得很好了,那不是你的错……”少年半蹲在地上,抚摸着狗,与它说话。他语气温和,神色镇静,却因为眼神没有焦点,呈现出一种目空一切的傲慢。身体的孱弱与灵魂的高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几乎令人心悸。
下一刻,龙美伊几乎是不受控制地与少年搭话:“你要去哪里?我可以陪你过去。”
少年似乎辨认出这个声音之前帮助过自己,脸上少了两分警惕之色,小心说道:“那样不会太麻烦你吗?”
“没关系,反正我现在没什么事,”龙美伊假装忘记了自己应该去补习的事情,热情地做了自我介绍,“对了,我叫龙美伊。”
“你好,我是秦慕。”
秦慕让龙美伊带自己去了一家私人电影院。说是私人影院,其实只是老式居民楼里的一个小房间,里面铺设了廉价的红色化纤材质地毯,架了一台投影仪,隔三岔五播放一些老电影。这一次,他们来得有些迟了,逼仄的房间里已经坐了六七个观众。龙美伊拉着秦慕在角落坐下,安静地听。
没错,是听。在屏幕的侧面,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拿着麦克风,温和地为观众描述电影中的画面:光影、色彩、角色神态变化……那些话语是细碎的光子,在黑暗中奔涌、堆积,最后洒满一地,仿佛温暖的琥珀糖。
“你以为,就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既没有灵魂,也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有一颗心!”这段台词透着丰饶的热气,烫得龙美伊不自觉后缩了一下,心底涌出了巨大的悲哀。
“如果我脸上没有斑点的话,”那些阴暗的念头在胸口彼此纠缠、啃噬,留下一个又一个空洞,“如果我可以长得更漂亮的话,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像电影里的女主角一样,说出这种明亮滚烫的誓词呢?”
秦慕喜欢“看”电影,尤其是老电影,哪怕是在失明后,依然愿意为一部老电影摸索着出门。
因此,在那家私人电影院被取缔后,龙美伊就恶补了为盲人讲电影的技巧,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为秦慕的“电影讲解员”。天气好的周末,他们会约在秦慕家附近的小公园碰面,一人带笔记本电脑,一人带笔记,点点则穿着导盲犬的工作服,在长廊下追逐飞远的落花。天空蓝得格外高远,而少年少女仰望天空的眼睛,比天空更蓝。
“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当这句电影台词响起时,龙美伊想,自己应该和秦慕一起翻过那座山,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路上,当暴雨降临时,龙美伊几乎是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去秦慕家避雨。那是一间普通的二居室,面积狭小,却因为家具很少,显得十分空旷。门窗边角都被用柔软材料做成的护角包裹着。
秦慕给龙美伊倒了一杯热水。绿色的塑料杯子,杯身上的米老鼠图案磨损得微微发白,呈现一种与苦难格格不入的稚嫩。
“杯子很可爱。”
“这是我妈妈买的,”秦慕的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情绪,“自从我出事之后,她把家里所有的餐具都换成了塑料的。”
这是他第一次提及自己的家人。一个爱子如命的中年妇女,在儿子因意外而致盲后,便立刻换掉了家中所有可能会令他受伤的东西,生怕有一丝疏忽。然而,同样是这份浓烈的爱意,让她难以面对秦慕的残缺,宁可用繁重的工作来麻痹自己,也不愿回到家中,注视一双失焦的眼睛。

至亲至疏。龙美伊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一个漂亮如仙子的女人,会为女儿受到嘲笑而脱下高跟鞋与人打架,却始终无法接受女儿的平庸长相,觉得那是一个需要被修正的错误。可是,为什么呢?明明自己的缺陷并没有给这个世界造成任何伤害啊。
龙美伊想不通这个问题,也不愿意去想。她能做的,是和一个看不见自己缺陷的人做朋友,用他人的苦难来掩盖自己的痛苦。
电脑屏幕中,主角们的旅程仍然在继续,惊险刺激,跌宕起伏。可是啊,那只是一种规律之内的恢宏壮阔,而真正的人生不是这样的,它更加失控,让人难以找到自己的来处与归途。
雨不知何时停了。龙美伊起身告辞的时候,看到门后藏了许多课本和试卷,乱糟糟地压成一团,翘起的边角像一瓣瓣柔软的花。
“秦慕,你有想过回到学校吗?”“什么?”
“如果你想的话,” 龙美伊忽然有了勇气,“也许我可以帮你。”
点点并不是真的导盲犬,在和秦慕第一次见面时,龙美伊便怀疑过这一点,原因是它太跳脱了,不仅会被路边的声响吸引注意力,还会对她手上的食物垂涎三尺——不管哪一点,都和资料上介绍的经过严格训练的导盲犬相差甚远。
这个疑惑,一直到她在网上看到了和点点同款的导盲犬工作服后,才有了答案。可是她在面对秦慕时,依然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知道,人是需要遮掩的,就像她用刘海来遮掩脸上的雀斑那样,秦慕需要用一条假的导盲犬来假装自己正在失明后的世界里积极求生。
可是,谎言并不会因为重复而变成真实,在自我欺骗的背后,依然是难堪的现实,如蛆附骨,如影随形。
市里唯一的特殊教育学校建在郊区。要去那里的话,秦慕就必须穿过三条马路,爬上一条蜿蜒的山坡,穿过长长的河堤,最后站在一块生锈的、巴掌大小的公交牌下,等半个小时来一趟的公交车。
龙美伊按照网上看来的知识,笨拙地教秦慕如何辨认盲道:凹凸不平的暗黄色砖块,直条代表直行,点状代表转弯。它们拼接在一起,像一条浑浊的河流,裹挟着两条年轻的生命,奔向遥远的未知之境。
小城市里的盲道建设不规范,常常有消防栓、电线杆、窨井盖一类的障碍物拦在路中间。有好几次,秦慕都被“突如其来”的障碍物绊倒在地,手中的盲杖飞出,落下,仿佛一道暗色的鸦影,发出不祥的声响。
“再坚持一下吧,”龙美伊帮秦慕包扎伤口的时候,总会说这种徒劳而重复的话,“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而秦慕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唯有殷红的血珠自伤口滚落而下,宣告一场身体输掉的战争:屡败屡战是一种美德,可是屡战屡败呢?是耻辱。
“够了吧。”在龙美伊再次絮叨“坚持就是胜利”时,秦慕终于给出了言语上的回应,措辞冰冷,语音却细弱,反差之大,几乎让人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你说什么?”
“我说,”秦慕的声音又细又颤,仿佛是暴雨降临前摇摇欲坠的蛛丝,“已经这么久了,你该玩够了吧。”

“我是为你好!”龙美伊气得脸颊通红,“你的眼睛看不见,要是再不比普通人多吃点苦,难道要一直靠一只假的导盲犬来自欺欺人吗……”
然而下一秒,她的满腔的热血便因为对方的一句话而冻结成冰。
秦慕说:“龙美伊,我早就在学校见过你。”
在失明之前,秦慕一直和龙美伊在同一所中学读书,只是不同班。他第一次注意到龙美伊,是在一节体育课上。那时,女生进行体能测试,跑800米的时候,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儿向前冲,只有她因为忙着抬手压住刘海而落到了队伍末尾,并因此被老师大声呵斥,要求重跑。
一遍,两遍,三遍……很快,龙美伊的刘海被汗浸透,不必刻意用手去压,也会紧紧地贴在额头上。而她似乎对这一切无知无觉,依然死死地压着刘海,抬起的胳膊微微僵直发胀,仿佛死后依然盘踞在珠宝堆上的恶龙。
操场边,完成体测的同学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对场上的少女指指点点,“她干吗一直捂着刘海啊?”
“因为她脸上有很多斑,丑得要命。”
“我初中和她一个学校,那时候学校不允许女生留刘海,为此,她妈妈还来大闹了一场,说学校不尊重孩子的隐私。”
“哈哈,这也太搞笑了吧……”
在这些流言蜚语中,秦慕不自觉地记住了主角的名字——龙美伊。因此,当他在公交车站受到龙美伊的帮助时,心底闪过一瞬的吃惊:在他的印象中,龙美伊自闭得几乎要抱蚌而居,根本不会主动对陌生人伸出援手。
“说到底,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和我做朋友呢?”秦慕几乎笑出了眼泪,“难道不是因为我看不见你的脸吗?”
“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
在书上看到这段话时,龙美伊已经与秦慕断了近半年的联系。在这半年时间里,她虽然有过懊悔一类的情绪,但是从来没有真切地察觉到自己做错了什么。直到这一刻,似有闪电划破浓厚的夜色,头脑忽然一片清明。
“我做了一件多么卑劣的事情啊。”龙美伊想。明明自己一直在享受秦慕的残疾,却因为可笑的自尊心,故意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俯视他,用近乎虐待的方式来告诉他,你必须依赖我而生。可是,人无完人,我们都一样残缺不堪,所以才需要交友,来让自己感到完整。
直到书页濡湿,龙美伊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竟然哭了起来。她哽咽着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秦慕,我现在可以来见你吗?”
“我想见你。”
“求求你,让我来见你。”
无论拨打多少次,电话那端永远是忙音——自从那次决裂后,秦慕便拉黑了她。最后,龙美伊丢开手机,抓起了椅背上的外套,在母亲的惊呼声中,跌跌撞撞地冲出了门。
“不接電话也没关系,”龙美伊想,“我可以去他家找他……我本就该亲自向他道歉。”
她跑得那样快,那样急,厚重的刘海先被汗水濡湿,又被风吹干,最后轻飘飘地扬起来,仿佛一尾墨色的鸦羽。然而,当她气喘吁吁地赶到秦慕家门口时,开门的却不是她心心念念的少年,而是他的母亲:“小慕今天不在家。”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不知怎么地,龙美伊忽然有些心慌,“我可以等他。”
“他今天不会回来了,”女人说话的声音很轻,仿佛声音稍大一些,就会惊醒某种苦难,“他生病了。”
“他在哪个医院?我想去看他。”
长久的沉默。就在龙美伊以为对方不会回答自己时,一个词突然快速地溜进了耳朵:“六院。”
六院是当地唯一一所精神病医院。
这一天,龙美伊听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故事里,盲少年在某个夜晚忽然独自出门,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走,走了多久,抑或是摔了多少次……女人只知道当自己找到他时,他正站在高阔的河堤上,满身是伤,却仿佛丝毫感觉不到痛苦一般,对着河面发呆。在那里,湿润的水汽自河堤深处涌起,团聚,飘散,最后落在少年的脸颊,像一个冰冷的吻。
“小慕,你一个人瞎跑什么?还不快跟我回家!”找人找了一晚上的女人又急又气,粗暴地拽住了少年的手,随即遭遇了对方自眼盲以来最为歇斯底里的一场大哭:“就因为我看不见,我就无法被人们平等地看待吗?”
“明明我一个人爬上了这座河堤啊!”这是秦慕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之后,崩溃的秦慕便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不再与任何人交流。为此,女人劝过,骂过,最后只能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鸵鸟综合征”,即因为无法接受自己的残疾而选择了逃避现实,建议住院治疗。
女人的嘴一张一合,龙美伊看着她,恍惚间,以为看见了自己的母亲。自从她进入青春期后,母亲便一直张罗着要带她去医院做祛斑手术,为此与她爆发了多次争吵。最激烈的一次,龙美伊砸碎了家里所有的镜子,最后在粼粼的碎片中泣不成声——似乎人人都默许,长有斑点的脸是一种残缺,注定要低人一等。可是,凭什么呢?
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啊。
同样,秦慕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根本不需要逃避。
龙美伊去医院看望秦慕。
正是初秋时节,阳光中荡漾着桂花甜腻的香气,秦慕穿着宽大的蓝白条纹病号服,独自坐在沙发与墙壁形成的逼仄空间中,微垂着头,仿佛没有悲喜的人偶。可是龙美伊知道,那些伤害仍然存在,它们仿若杯弓蛇影,在脏腑中时时翻搅,令人不得安息。
之前,龙美伊问过秦慕的主治医师,知道秦慕对外界仍有着一些感知,只是不敢亦不愿做出回应。对于他而言,世界仿佛一出荒诞戏剧,他可以看见戏中人的喜怒哀乐,但他选择了无动于衷。
龙美伊知道自己该如何撕破这层“幕布”。
“从记事起,我的脸上就一直有雀斑,它们就像是商品的条形码,与我的人生牢牢绑定。”龙美伊半跪在秦慕身边,厚重的刘海覆在额头上,像是半副假面,遮掩了她所有的情绪,“其实一开始,我并不讨厌自己脸上的斑点,即便旁人觉得碍眼,可是我依然觉得,它们只不过是斑点而已。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将它们藏起来的想法呢?”
初中的一个晚自习,班上的男生闲来无事,开始评选班上最丑的人。龙美伊听见他们喊出一个又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心生慌乱,便连忙趴到桌子上,假装睡觉,却不想真的睡着了。醒来时,早已放学,教室里空荡荡的,只余下她一人。龙美伊迷迷糊糊地抬头,在黑板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下面是满满的“正”字,以及一个滑稽的、嘲讽的猪头。
后来,这件事被好事者传到龙美伊的母亲耳朵里。她“杀”到了学校,当着众多老师学生的面,拎着高跟鞋与人打架。一片混乱中,龙美伊被人推倒在台阶上,点点鲜血自膝盖滴落,恍如花坛里色泽猩红的美人蕉。

“从那天起,我便知道,人有时候就是要为自己没有做错的事付出代價的。”
这份代价是母亲的失态,是膝盖上的伤口,是额头上厚重如乌云的刘海,是恨不能从人群里消失的忧郁。人对强加于己身的“代价”多少会有一些不甘心,是以,无论母亲如何劝说,龙美伊都不肯去祛斑,不肯像母亲口中的其他女孩子那样,干净清爽地活下去。
“我觉得,如果我祛除了脸上的斑点,祛除了我与生俱来的一部分,那么,我就是在对那些人投降妥协。”
说话间,龙美伊从背包里掏出了一把银色剪刀,然后郑重地将柄端塞到秦慕手里。“我一开始的确是因为你看不见我的脸而与你交往,可是到后来,这种心态逐渐改变,我愿意和你做朋友,是因为在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一个明明愤怒却只能躲起来的灵魂。”
就像龙美伊不在乎自己脸上的斑点一样,真正让秦慕心灰意冷的并不是残疾本身,而是在眼盲后,来自他人的自以为是的、看待异类的目光。
少女牵动少年的手,让银色的刀刃如一扇燕尾,钳住了自己额前的刘海。龙美伊说:“可是,躲避比投降更为卑劣,它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自己最厌恶的那种人。”“咔嚓”一声,乌色的碎发飘落空中,仿若一场沉冤的飞雪。“孤身一人与世俗规则相对抗,是一场壮烈的悲剧。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做到自我坦率就是一种胜利。”
她用力地抓着他的手,让他的掌心贴在自己赤裸的额头上。那里有新冒出来的几颗青春痘,温软得仿佛一团少年心事。她说:“这是我们能够达成的、最愉快的悲伤结局!”
泪眼蒙眬中,龙美伊感到秦慕覆在额头的手掌轻微地弹动了一下,紧接着,她听到了此生里最响亮的抽泣声。她知道,那是少年的梦,醒了。

- 中学生百科·悦青春的其它文章
- 记忆同样可以唤来声音
- 屋外的声音
- 医生为什么穿“绿大褂”
- 不刷牙的科莫多龙
- 袁氏悲剧
- 为鳕鱼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