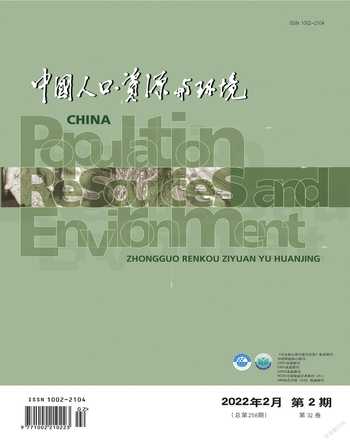论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逻辑进路与制度展开
李华琪
摘要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强调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功能,有助于完善环境风险规制体系、顺应司法救济逻辑顺位并回应社会公众预防环境风险之需求。当前,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偏离司法裁判逻辑、忽视预防性责任主体、受限于损害救济范畴等局限性问题,致使诉讼预防性功能彰显不足。现代社会下的行政机关承担着环境风险规制任务,但风险的科学不確定性必然会使行政权遭遇风险规制难题,美国货运协会案表明对环境风险行政责任的寻求不仅具备必要性,也具备可行性。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当转向以公法责任为基础的公法诉讼类型,强化法定义务主体的风险预防责任,涵盖环境资源利用行为与环境风险行政规制行为。从逻辑进路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当坚持尊重环境风险行政判断的基本立场,确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地位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递补地位,并在诉讼过程中纳入包含环境健康要素在内的风险考量,明确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确立多元主体诉权融合。就具体制度而言:一是在坚持公法诉讼性质定位基础上,作出具备公法属性的立法思路设计,包括立法模式、风险范围及程序规则;二是通过拓宽案件线索来源、诉前程序的类型化、明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及完善风险认定体系这四个方面构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以发挥其环境风险治理监督功能;三是通过细化风险认定标准、引入不同方式的诉前程序、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及增加司法听证程序来重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现诉讼预防性措施的优化适用。
关键词 环境风险;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风险行政;公法诉讼
中图分类号 D91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22)02-0096-11 DOI:10.12062/cpre.20210811
风险社会的来临给行政权构成了新的挑战,为了适应风险社会下行政权的变化,法院在公共利益的问题上开始转变态度并表达了更多的关注,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便是现代风险社会下司法权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和第八条明确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可以针对“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之情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确立对环境的保护方式从救济扩大到预防,通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发挥预防性功能。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对2015年司法解释予以更新修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其中仍然通过第一条和第八条的确立进一步强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预防性功能。然而,基于司法权的谦抑性特征,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中国并未得到深入探索和发展,收效甚微。即便司法实践中已有预防环境风险的典型案例,但从受案范围、诉讼程序、预防效果等方面来看,预防性功能体现并不充分,如法院支持社会组织诉讼请求后通常仅是针对个体行为采取具备暂时性约束效力的措施,重大环境风险是否得到防控这一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无法达到“源头防控”的效果。因此,如何借助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挥环境风险预防功能值得进一步思考。
现有研究已经意识到当前中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事后救济性特征无法满足风险预防需求[1],有学者试图探讨并纠正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对重大环境风险的司法认定路径[2],更有学者提出建立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3]及在环境领域中探索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4]等方法路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只是现有研究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位、构造和价值目标等主要问题分析并不充分,即使有探讨诉讼性质和定位问题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对民事公益诉讼或行政公益诉讼其中一类,未能系统性看待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文章将首先分析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与价值,继而对现有制度安排和司法实践进行问题分析,以公法责任作为出发点讨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开展的逻辑前提,继而厘清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监督立场、诉讼模式、价值目标及要素考量,最后从制度层面构建和落实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
1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与价值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相对于救济性环境公益诉讼所提出的概念,其作为贯彻落实风险预防原则的途径之一,能够从源头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呈现出完善环境风险治理体系、顺应司法救济逻辑顺位及回应公众预防环境风险需求的价值功能。
1.1 概念与特征的提炼
近年来,由损害预防原则向风险预防原则转向,已然成为中国环境法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向[5]。面对环境风险的出现,人们试图从司法层面寻求环境风险规制途径,由此,蕴含风险预防理念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运而生。
认识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仍然要从风险预防原则入手。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解前提是存在“风险”。为了准确认识风险,理论界引用危险和剩余风险的概念以区别和界定风险。目前,中国已有环境法律所确立的损害预防原则实际就是适用于“在可预见一段时间内,在持续性过程中,某一个事实状态经证实具有充分的盖然性将导致损害的发生”[6]的危险情形,剩余风险是立法者经过价值判断与权衡后,通过放弃对该部分法益的保护而享受所带来的未来收益的结果[7]。而风险是介于危险和剩余风险之间,损害发生的程度较低,但无法像剩余风险一样完全排除,又未达到危险发生的高度盖然性程度,且一旦发生将不可逆转的情形。这实际上是从法益损害的预期程度所作出的一个区分,换句话说,只要预期到必然存在某种可能发生的危害,可能危及生命权、健康权、环境利益等重大法益就有讨论采取预防措施的必要。有学者基于这种危害预期提出,最重要的是对“最糟糕情景”的预期,有必要将其作为危害预期的上限[8]。所谓“最糟糕情景”是指“能够激发公众感情的显著事件的最糟糕情景本身就能够影响公众的想法和行为,对于其发生概率的大小并不重要”[9]。同时,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必然具备科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指向预期的危害不必然发生,并且基于现有知识经验无法完全推导和证明危害发生的程度与范围。但为了对这种不确定性风险予以规制,则应当允许规制主体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对其展开度量。考虑到不确定性的来源十分广泛,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对度量的结果产生较大的差异,这就需要对度量工具的选择与运用是否恰当进行判断和调整,以确保这种对不确定性的认识达到更为精准的程度。基于此,风险预防措施是风险预防原则实施的主要方式。相比较实际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风险社会中的因果关系最多只能通过概率的方式加以描述和认定,而有效的预防措施则是通过阻断危害发生的因果关系以防止重大风险发生和扩大。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蕴含着风险预防原则的理念,属于司法层面的预防措施,“以预防生态损害为核心目标的环境公益诉讼,是环境公益诉讼的理想形态”[10],其主要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以考察风险规制主体在当前知识与经验限度内作出的风险规制判断是否合理,从而决定是否采取能够避免不可逆转损害发生的预防措施。
1.2 诉讼负载的价值意蕴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属于环境公益诉讼之预防性功能的具体体现,是完善环境风险治理体系的一种新路径,不仅符合司法救济的逻辑顺位要求,还能从一定程度上对公众预防环境风险的需求加以回应。
其一,完善环境风险规制体系。在环境法产生之初,各国均以“污染者負担”原则为基础建构秩序型环境治理体系,对风险的预防仅限定在重大紧急情形范围。风险社会的挑战使得秩序型环境治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且环境保护步伐不可能因科学不确定性而有所延缓,甚至要求现代社会必须超越已有科技水平对未来的环境政策加以规划与决定。其中,对环境风险治理的正当性控制是保障环境风险规制有效性的途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实施,可以对产生重大环境风险的行为加以监督,补强环境风险规制效果,且能避免环境风险规制手段异化为吞噬社会自由空间和侵害公民环境权利的方式,能够有效应对风险社会下环境治理体系所面临的挑战。
其二,顺应司法救济的逻辑顺位。所谓生态利益是“生态系统对人类非物质性需求所满足的利益”[11],只是通过经济手段补偿环境利益损失的方式并不能阻止生态功能与生态系统遭受实质损害,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损害的不可逆性。基于此,生态环境损害的难以填补或无法填补决定了生态环境损害预防的前置性和先决性,而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将重心从“损害结果”转向“损害行为”,关注损害行为本身所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进而采取司法裁判下的预防措施防范未发生环境损害的系列风险。从这个角度而言,环境公益诉讼不仅应当具备司法救济功能,还应当具备相应的预防功能,且预防措施应当是环境公益诉讼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第一顺位选择,因为只有当预防无效时,再对损害结果予以司法救济,符合环境司法救济的逻辑顺位。
其三,回应公众预防环境风险需求。环境风险的存在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造成社会恐慌。这是因为环境风险所造成的后果很可能直接对置身于受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范围内的人体产生不可逆的危害。在此期间,这种对人体的危害具有一定潜伏性,当危害积累超过人体所能承受的标准值时,就会出现无法救济的损害结果,从早些年中国发生的厦门PX项目事件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都反映了社会公众预防风险的现实需求。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环境风险预防的途径之一,通过推动行政机关加强环境风险治理,能够降低社会公众遭遇环境风险的概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公众预防环境风险需求的一种回应。
2 中国现行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之局限
近些年,中国出现了不少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案例,如2015年中石油云南炼油案、2017年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2018年回龙山水电站建设案、2019年安徽八公山风景名胜区生态破坏案、2020年刚刚判决的五小叶槭案等。但现行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仍面临着偏离司法裁判逻辑、忽视预防性责任主体、受限于损害救济范畴等局限性问题,预防性功能彰显不足。
2.1 偏离司法裁判逻辑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确立,中国便遵循着传统诉讼模式构造了“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之二元格局。从规范来看,已形成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的主体制度,且行政机关借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介入到环境公益维护范畴。从实践来看,检察机关成为公益诉讼的主要推动者,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近几年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占比从2015年的28.3%跃升至2019年的92.8%[12],逐步呈现出“国家化”[13]趋势。具体表现为:在内部层面,通过不同机关之间建立联络员机制、定期信息交换机制、先期预警机制、案件移送抄报机制等等[14]。在外部层面,各主体之间进入到协同发展阶段,通过搭建协作平台以开展环境公益诉讼,譬如通过签署各类规范性文件,建立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联席会议制度、探索座谈会检察建议送达模式,甚至协同社会组织召开座谈会等等,从而提高环境公益诉讼程序的运行效率。这种“通过政府权威与运动型动员机制调动资源,致使政府或职能部门作出高度敏锐的反应和互动的高度关联型治理模式”[15]在实施初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多数企业违法行为和违法行政行为或不作为通过诉讼程序得以矫正或履行,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环境保护目标实现的效率,但其仍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其一,主体作用空间被压缩。当“环境公益诉讼”逐步朝着“检察公益诉讼”方向发展时,意味着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的主要推动者,加之政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的行使,势必压缩了社会组织或其他主体提起诉讼的作用空间,留待社会组织或其他主体的可诉事项被层层剪除,这种负载着环境民主价值的社会监督机制将会被削弱;其二,案件受案范围受到限制。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强调对可能造成重大环境风险的行为加以规制,结合检察机关“履行职责发现违法行为”的线索来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成为其主要战场,一般存在着明显的违法行为或损害结果是案件诉讼的主要缘由,在以“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实际损害”为诉讼前提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挥空间更小;其三,诉讼策略侧重在主观面向的利益权衡。检察机关通过协作与行政机关开展诉讼,同时又承担着“执法诉讼”的监督职能,基于检察机关与行政系统这种高度关联的状态,再借由公益诉讼途径加强对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这种程度的“执法诉讼”所具备的监督与矫正功能更多是主观面向的利益权衡,而非客观面向的法秩序目标,无法开拓出应有的法治治理空间。
结合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特征与价值意蕴,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高度关联型”治理模式会随着案件积累逐步转向消极,而诉讼请求、诉讼衔接、构成要件等判断标准问题都得不到充分论证,导致司法裁判中立性相对不足,裁判说理匮乏。也正是在这样的模式下,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将会随着治理成本的日趋攀升而逐渐式微,势必会抑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预防功能之发挥。 2.2 忽视预防性责任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纳入“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将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确立在民事诉讼框架下。风险预防的主旨不是消除非常可能出现的损害事件,或者是事后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害,而是专注于危害的主要根源,通过公共机构的规制行为来干预危险源,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最终使得损害得以避免[16]。从政治学意义来讲,政府是国家为实现表达公共利益的法律,设置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双重职能的组织,对环境的利用和保护,政府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通过对已有案例的分析,行政机关作为预防性责任主体的地位并未得以体现,换言之,对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环境风险产生并未纳入到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反而成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进行司法认定的判断标准。“重大风险”是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要素,但中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其作出内涵界定,且实践案例中对“重大风险”的认定以行政机关的决定为依据。如在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之初,行为的行政违法性成为原被告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焦点问题,尤其是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诉讼的重要支撑证据。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就明确行政合法不代表不存在环境侵权之证明主张。即便如此,在证明存在重大风险时,司法实践仍以被告行为的行政违法性作为起诉依据,似乎存在着行政违法必然环境侵权的证明逻辑。在云南绿孔雀案中,自然之友认为被告新平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水电站建设项目环评报告存在实体和程序问题,将淹没绿孔雀的主要栖息地,很可能导致孔雀灭绝。该案作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在一审程序取得阶段性胜利,只是该案同样围绕着被告行为行政违法性的问题所展开。同时,司法实践对“重大风险”的判断以行政决定为依赖。在云南炼油案中,昆明中院和云南高院直接以“被告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已取得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复同意”为由认定被告一系列行为不存在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仔细来看,法院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结果认定,并未对其行为进行实质性的风险评估和说明,这就导致行政机关间接地成为了案件是否存在“重大风险”的认定主体,这种理应由法院作为决定性认定主体的情形,却因其对行政管理结果的依赖出现认定主体错位。如果法院一味地以行政监管结果来认定是否存在“重大风险”,从深层次思考,甚至有违于“审判权由法院独立行使”的宪法安排[17]。由此可见,在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作为预防性责任主体并未被纳入到诉讼范畴。
2.3 受限于损害救济范畴
就中国而言,置身于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框架的环境公益诉讼,其聚焦点始终在于损害救济,即关注实际损害结果,这种审查视野的局限性直接决定了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功能实现之不足。
一方面,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实体法方面主要依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关于侵权责任法功能存在着单一功能说[18]、双重功能说[19]、多重功能说[20]三种主张,其中多重功能说认为侵权责任法具有补偿功能、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尽管三种主张存在较大分歧,但对侵权责任法具有“补偿功能”达成了共识。事实上,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体系主要围绕侵权责任法的填补损害功能展开,也有人将其理解为“救济”功能。这种补偿功能强调的是以损害结果为重心。在侵权法的矫正正义传统[21]下,侵权责任通常以损害赔偿责任为主,侵权行为的司法认定必须以实际损害为要件,体现的是一种结果责任。这就使得置身于民事诉讼框架下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逐步呈现出私法化趋势,致使近年来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案例几乎以损害结果为诉讼要件,即主要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造成实际损害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种以民事责任为基础的诉讼制度与预防性责任的内涵并不相契合,现有司法实践探索并未取得较好结果。究其原因,正是在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作用下,环境公益诉讼以侵权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为基础,注重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填补,甚至提出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以资金补偿救济环境公共利益,致使法院在对“重大风险”的认定标准仍局限于民事责任的逻辑,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开展困难。
另一方面,中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旨在监督环境行政机关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也许能从一定程度上实现“预防性责任”,但看中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检察机关需要满足“履行诉前检察建议程序和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这两点方能提起诉讼,事实上环境损害结果已然发生。而关系到环境公共利益的规范性文件这类抽象行政行为最初阶段就游离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审查视野范围之外,一旦行政机关制定某项规范性文件,其他部门纷纷依据该决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此时,再通过行政公益訴讼进行审查可能已经无法逆转生态环境损害的产生。由此可见,中国行政公益诉讼仍然无法逃离以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损害结果为诉讼构成要件,同样未能成为“预防性责任”实现的诉讼制度。
3 公法责任: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开展前提
基于当前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所面临的局限,公法责任能够为化解这一制度困境提供方向指引。环境风险预防的目的在于从源头降低各项环境资源利用行为产生的环境风险,以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和维护环境质量,其目的决定了其属于公法责任。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当转向以公法责任为基础的公法诉讼,强化法定义务主体的风险预防责任,涵盖环境资源利用行为与环境风险行政规制行为。
3.1 环境风险行政规制难题
随着“夜警国家”向“福利国家”发展,再到“风险社会”的模式转变,行政机关的职能从“以推动和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转为兼顾社会风险的控制、社会稳定的维护、非经济性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22],行政规制的范围呈不断扩大趋势,尤其是环境风险。环境法上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三类:一类是损害已经发生,却囿于科学认知局限而无法确认源头,如臭氧层空洞问题;一类是科学上存在较大争议且短期内无法准确判断,如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另一类是无法通过经验判断的新型事物,如含有未知毒性的化学物质等。这几类环境风险显然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潜在威胁,传统秩序法上的行政规制手段无法再依据经验法则加以应对,不得不转变为积极的风险预防。
从中国环境立法来看,主要通过各种措施预防和规制环境风险,包括命令与控制、经济激励、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制度。尤其是在2018年通过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确立了“风险”概念,授予行政机关在土壤污染防控标准制定、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实施等方面的主导权,明确了风险管控基本原则。但即便是通过事先确定的规范对行政权力予以规范先定,由于风险的科学不确定性特征,行政权在风险规制方面仍不可避免存在着规制困难的局面。其一,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原则的紧张。行政法治理念中,行政活动的合法性是由形式合法性提供的,行政机关的任务在于执行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所确立的事项而,面对风险社会所包含的不确定性概念引发了行政机关举证责任问题,即遵循法治要求,行政机关应待科学揭示因果关系或危害实际潜在可能变成现实才能采取措施,但这也就失去了对风险防范的程度。其二,风险规制行为本身便很可能成为风险的来源。实际上的风险一种来自私人活动,另一种则是权力被滥用而侵犯公共利益的风险,若是对后一种风险限制过多,很可能导致第一种风险的溢流,反之,若对第一种风险进行控制而授予规制者过多的权限,可能导致第二种风险的失控,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这类灾难性后果。其三,民主基础与科技基础的双重缺失使得行政规制的正当性受到极大挑战。环境风险的识别是一个技术认定与价值判断的综合考量,需要公众参与保证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反映,又要确保行政机关的实体决策和监管过程符合科学技术要求,任何一项要素的缺失都可能导致行政决策出现错误,要么会过多地限制人们行动自由,要么未能有效防止危险发生,出现规制过度或规制不足的情形。3.2 风险行政责任的寻求
面临着环境风险行政规制的困难,允许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裁量空间成为一种解决思路,在风险规制中多数是以裁量行政方式出现,因而,要如何保证其裁量空间不至于过宽或违背规范要求便是一个重要命题,而公法上的司法审查能够在规范行政权行使发挥作用,即允许相应主体依据预防环境法律制度,对风险规制行为提起带有预防措施的诉讼。American Trucking Ass’ns,Inc.V. EPA(美国货运协会案)就是一个典型范例。
美国货运协会案的焦点在于美国《清洁空气法》要求美国环保署颁行并定期更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因为环保署在1997年制定了一项更严格的标准,美国货运协会请求法院对修订后的标准是否是对《清洁空气法》的合理解释实施司法审查,案件经过四审最终认定环保署在标准修订中对其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具备合理性。那么,这引申出一个关键问题:法院应当如何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裁量权以确保其达到合理的标准。考虑到行政机关比立法机关拥有更多制定相关标准所需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技术等,由其制定规范裁量权行使的标准可能更高效,哥伦比亚巡回上诉法院在审理时,便选择了将该标准发回行政机关由其进行“自我设限”的方式重新解释,显然,要求行政机关制定自己应当遵守的裁量标准存在着公信力问题,同时,法院并不具备要求行政机关制定新规则的制度创设能力。因此,最高院否定了上诉法院的这一判决,并要求其通过司法裁量的方式承担起制约行政裁量的责任,试图将这种风险规制与民主需求相协调,最后通过确保裁量为“可理解的原则”引导来确定行政行为的负责任性[23]。该案所反映出来的思路是,风险规制是一项多要素的综合权衡,往往是高度情景化,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规制者与多数企业、个体一样在论证决定合理性时并不要求有很高的确定性,如果要求行政机关能够揭示不确定性的占比较高时,实际上是在要求行政机关确定“可接受风险水平”这一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也正是风险社会下普遍性所存在的问题。最高院否决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说明,在风险规制时代,要想对风险行政的审查达到一个有效且平衡的状态,首先就应当对风险规制任务所处理的风险事项具有符合实际的理解,这种实际理解是科学技术无法帮助行政机关确定一个准确的阈值界限,行政机关在综合权衡风险后果严重性大小及风险发生概率基础上确定一个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应当属于合理。
由此可见,司法权随着实践需求在法律适用方面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风险社会下的法院通过对风险行政责任的寻求,要求行政机关在程序和实体上尽可能考虑维护公共利益,但又不逾越行政权替代其作出决策,从而发挥法律监督和法律适用的专长,达到监督风险行政的目的。
3.3 引入“公法诉讼”的契合性
随着中国环境法体系逐渐完备,众多造成重大环境风险的行为均被纳入到行政法规制范畴,因而,“公法诉讼”性质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亟须确立。相比较侵权诉讼框架下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公法诉讼”性质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更能够实现环境风险预防的功能。
从受案范围来看,“公法诉讼”性质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能够涵盖环境风险所涉诸行为,包括环境资源利用行为与环境风险行政规制行为。因为环境风险的源头不应仅限于环境资源利用行为人的行为,虽然一般利用行为会是产生环境风险的直接来源,但这类行为以行政行为的实施或许可为前提要件,甚至本身就可能具备产生重大风险的情形。从行政行为来看,具体可以将行政过程划分为“标准阶段、行为阶段、执行阶段、救济阶段”[24]。在前述的几个阶段中,均可以通过诉讼对行政行为予以风险治理监督,至于救济阶段,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同样能够发挥预防功能,如2016年中国第一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针对环保局多次违法颁发试生产许可证使污染企业合法化的行为提起的诉讼[25]。该案审理后,原国家环保部发布了停止颁发试生产许可证的第29号公告,要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再进行建设项目试生产审批。由此可见,当一个行为是行政机关为实现环境公共利益所作出的,其应当属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审查范畴,并应从不同程度进行审查确保该行为实施不存在环境风险规制不当情形。
然而,公法诉讼的运行并不意味着对私主体行为进行监督的绝对排除。事实上,行政执法在公益救济层面所存在的内在缺陷正是中国公益诉讼兴起的根源,因而逐步发展出具有“代位执法”诉讼功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类诉讼在实体上依照公法裁判,通常以违反环境法强制性规定作为诉讼启动前提,并围绕着环境法律义务的履行予以裁判,客观上指向主体数量具备不特定多数性、客体具备非排他性和利益客体的共享性的环境公益,反映出其作為公法诉讼的特殊属性与独特规律[26]。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必然需要这类代为执法诉讼参与监督,不过环境风险本身发生的概率低就决定了通过该渠道提起的诉讼并不多,一旦提起意味着环境风险存在的情形从行政阶段就未得到有效规制,此时借由具有“代位执法”诉讼功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将各方利益聚焦,为个案提供相应的预防措施,相比较侵权诉讼框架下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其更能依据环境法律规范对环境风险实施预防和监督,从而弥补环境风险规制之不足。
4 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逻辑进路
随着风险社会下的行政权功能变迁,司法权也应当随之灵活变动。定位于公法诉讼性质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当选择清晰的逻辑进路,在监督立场上应当明确与行政权的关系,在诉讼模式上应厘清针对不同行为的诉讼监督地位,在要素考量上应关注到人体健康、利益衡量方法及多元主体诉权等问题。
4.1 监督立场:尊重环境风险行政判断
环境风险规制过程中行政机关始终是关键的一环,即便是公法诉讼的干预,行政机关同样应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基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在对环境风险所涉行为加以监督时应首要尊重环境风险行政的基本判断。
基于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无法通过事前立法进行命令与控制,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概括授权的方式赋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裁量权[27]。如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条就授权生态环境部门或相应政府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力争达到科学合理,将风险水平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不仅是行政裁量,还涉及行政判断,相比较行政裁量,行政判断更多地适用于涉及预测性、专业性等行政风险决策,发挥着价值判断和将价值概念具体化的作用[28]。概言之,当存在不确定性法律概念时,而现行法律制度和标准亦无法规制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时,行政机关在风险评估结果基础上采取临时规制措施,此时则应当尊重其行政判断结果。若是相应主体提起诉讼,则作为“公法诉讼”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之行使,应当以风险行政规制的有效性为目标,具备法定性、程序性和必要性。首先,法定性意味着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在法律层面得到具体明确的规定,不仅是法律允许起诉的条款,还包括原告资格、适用范围、起诉条件、责任方式、判决执行等制度实施问题作出法律规定,从而厘清对环境公共利益的判断和界定、司法权干预的范围与程度及公共决策中行政权的主导性等重大问题。其次,程序性意味着对重大环境风险规制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实质是对环境法的一种“执行”。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涉及公共责任的创制与承担,需要运用公法确认所涉及的风险利益及责任,只是这类“执行”并不是替代行政机关作出预测和判断,而是对其是否作出合理准确的政策判断加以监督,避免将这类公法责任落入私法规则中,导致对具体环境风险的认识错误与规制混乱。最后,必要性则强调环境风险行政规制的监督程序应当具备现实必要性。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项规定,法院有权裁定停止执行可能产生重大环境损害风险的行政行为,但这类预防性措施应当充分考虑预防环境风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影响,必要时对预防性措施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尽可能契合比例原则。同时,法院应当及时跟踪评估和认定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旦重大环境风险情形消失后,应允许行政机关申请撤销或法院主动撤销预防性措施,确保行政机关充分履行风险规制义务。
总之,当行政机关能够通过现有行政权行使实现预防生态环境损害的目标时,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则不应当被启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机关虽然依法能够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但该诉讼主要在损害事后救济领域发挥作用,并不具备预防功能,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并不冲突。
4.2 诉讼模式:行主民辅
基于风险来源的主体不同,可将“公法诉讼”性质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界分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前者旨在监督环境风险行政规制行为,对可能存在重大環境风险的行为经法定主体提起后予以审查,后者是依据环境法律规定,由法定主体提起并要求消除重大环境风险的诉讼。结合环境风险规制的行政主导性特征,应当确立“行主民辅”的诉讼模式。
行政机关在环境风险规制过程中可能受主观因素影响存在着规制错误或规制不足的问题,此时通过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能够对这部分规制影响因素加以排除,以确保环境风险行政规制行为的正确性,可以说,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最接近环境风险源头的形式。基于此,检察机关应对行政机关加以监督,这里采取的标准为行为标准而非结果标准,即只要行政机关穷尽了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法律赋予的各种行政手段,即使未能有效制止环境违法行为或有效消除环境风险,也不应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29]。
不仅如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其正当性与必要性,应坚持在风险预防过程中的有效递补地位。这种递补性地位体现在:一方面,环境风险规制后仍然存在重大风险的情形。环境风险来源广泛,即便立法为环境风险预防作出系列规定,但行政机关受到国家政策、执法资源、监管力量等多要素引导,必然存在环境风险预防的空白之处。例如,新冠疫情的出现促使人们意识到食用野生动物的巨大风险,《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订成为了环境风险的预防热点,但仍然存在着许多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可能会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情形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更谈不上行政机关的监管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监督程序履行后尚未消解的重大环境风险情形。任何主体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必然经过决策、建设、实施等系列阶段,可分阶段进行考量。例如,大型工程项目未依法组织环境影响评价直接开工建设,而继续建设必然导致地方物种灭绝或环境资源破坏的情形,应当及时予以制止。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对项目施工建设的重大损害结果发生可能性予以客观评估,即便在这个过程中建设单位取得行政许可,若建设项目的重大风险并未得到实质性消除,诉讼监督仍然需要继续。据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辅助性地位在于通过检察机关或社会组织行使预防环境风险的补充性诉权,关注行政执法或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尚未消解重大环境风险的情形,对可能造成重大环境风险的行为进行科学论证,可以理解为运用民法手段实现风险预防的公法责任,属于责任性质与责任实现手段不同的表现形式。
4.3 价值判断与要素考量
风险社会的出现要求行政机关从危险防止转向风险预防,因而,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之实现应采取行政与民事并重的诉讼构造。这就要求诉讼开展需要确立其独特的诉讼价值判断,同时在符合既有法律的规范性要求下,合理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并确定多元主体诉权融合。
一是强调包含人体健康在内的环境风险判断。环境法律已经为防范环境风险确立了比较细密的监管执法事项,重点在于保护公众免受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损害或威胁,但显然专注于这一层面的环境风险无法满足环境保护需求。例如,人们猎捕、交易、运输、食用野生动物引致病菌被扩散蔓延,使得环境健康问题新增为环境风险的又一表现形式。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应将对环境风险的判断延伸至公众健康要素,事实上,现行环境风险防范制度中多数缺乏健康影响评价和技术导则,直接导致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难以充分考虑公众健康因素,因而,有必要强调包含人体健康在内的环境风险判断。
二是合理运用利益衡量方法。风险预防领域中,利益衡量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无法通过成本—收益方法准确分析,这需要风险规制主体融入一定的价值考量,从而在利益衡量中寻求到一种平衡,即引入风险交流制度[30]。例如,招商引资的发展项目有着科学技术证明可以避免重大环境风险的产生,并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同时,作为环境风险后果承担者的社会公众坚决反对引进该项目,那么,决策者应当对一系列的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再决策。在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法官在环境损害结果发生的概率性和程度性进行客观评估基础上,对是否采取预防措施及采取何种预防措施同样要作出利益衡量,应当寻求擅长成本收益分析的行政专家的意见,并听取社会公众作为利害相关人的看法,采取预防性措施对国家环境风险预防义务作出一定的补强,促使诉讼朝着可预测性作用的方向转变。
三是确立多元主体诉权融合。要构建预防性诉讼制度,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实现多元主体的诉权融合。在当前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背景下,针对可能存在重大环境风险的情形,社会组织能够提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但不包括可能产生重大环境风险的行政行为,同时,检察机关虽能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但却局限于损害救济已经发生的情形。尤其是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空间扩张的情形下,社会组织的参与空间被不断压缩,而社会组织背后所含括的公民精神和社会共治的潜力巨大,应充分考虑社会组织在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因而,就同一对象进行保护的共同目标决定了检察机关与社会组织的诉权应融合实施,依照诉权启动时间的客观标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与社会组织的積极性。
5 中国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展开
为强化诉讼预防功能且坚守诉讼定位,制度展开应结合其公法诉讼性质确立具备公法属性的立法思路,并围绕起诉条件、诉前程序、举证责任及风险认定等方面构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实现对风险行政责任的寻求,在现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基础上对审理标准、诉前程序、举证责任及听证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与补充。
5.1“公法诉讼”的立法思路
明确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公法性质定位,确立其与其他公法机制的本质同一性,按照“依法实施、分类发展、执法有限、司法补充”的原则进行制度安排,是制度完善的根本方向。那么,制度开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立法。
首先,明确公法属性的立法选择。公法诉讼严格依法实施,然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条款,即便有《民事诉讼法》为制度实施提供法律依据,但整体而言诉讼实施仍受限于侵权诉讼的逻辑框架,在诉讼基本原理和制度内容方面都存在着与侵权诉讼的重合之处,致使司法实践开展均是以侵权规则为参照,不利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展开。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环境法律中先行建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例如,正在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地法》等单行法中增加诉讼条款,在可能存在重大环境风险的领域先行探索,若是能够制定专门的公益诉讼法,那么可在专门法律中对该诉讼制度加以具体确定。
其次,扭转诉讼规制风险的方向。司法解释中的“重大风险”所强调的是发生概率高且引发的损害后果严重的“风险”,并未将风险中“科学不确定性”这一特征囊括进去,其实质仍然是对危险的界定而非是对风险的考量。从公法诉讼性质定位看,应当将危险与风险加以区分开来,主要转向蕴含科学不确定性特征的环境风险,且这类风险可以为人们所认知并认定为十分重要,即并非所有被认知为“重大”的风险都应当纳入到风险规制范畴。换言之,不利后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另一面是获得各种收益之可能性,包括物质利益或更高层次的价值目标如自由等[31]。反之,为了利益或价值追求就具备了选择的可能性,这必定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零风险是不可能实现的。基于法律对人们行为的调整功能,那么,进入诉讼监督范围内的风险从概念上应被理解为与人的决定和行动相关。
最后,整合不同类型的诉讼程序规则。定位于公法诉讼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实则囊括了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和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事实上,产生环境风险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连续性,例如一项重大工程的实施从审批、许可、建设等环节都面临着风险后果的可能性,这种行为的连续性决定了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和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在案由、目的、功能等方面可能出现重叠,应当合并开展审理,即便不能合并也应当建立衔接机制,立法应从诉讼请求、责任形式、审判程序、公众参与等方面做出详细的规定,实现公法机制的法定性特征。
5.2 建立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由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指向公法责任,首先要确立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纳入对行政机关之环境风险预防义务的考量。在制度构建上,应当围绕着案件来源、诉前程序、证明责任及风险认定这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拓宽诉讼案件线索来源。因预防诉讼不以损害结果为要件,诉讼主体在损害结果尚未出现时获取线索的难度较大,应通过多方协作予以补足。一方面,加强与社会组织的线索沟通。从已有的预防案例来看,社会组织对地方环境保护有着较高地警惕意识,并具备挖掘案件线索的专业能力,可以通过构建检察机关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机制来增加线索的掌握可能性。另一方面,强调行政机关与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义务。立法已经明确规定各类主体应当公开环境信息的具体义务,以确保公众及时收悉相关的环境信息。诉讼主体可以通过公开后的环境信息以掌握具体环境资源利用行为的数量、方式、浓度等各要素,从而获得案件线索和证据。
其次,诉前程序的类型化。在中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框架下,诉前程序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履行已经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仅2019年1月至11月期间,行政机关对检察建议的回复整改率达97.65%,但其并未对产生重大环境风险的行为予以适用。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应分阶段进行:在标准阶段可采取“异议型”建议,如相关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与法律相抵触的情形,可以由检察机关提出异议;在行为阶段可采取“提示型”建议,如行政行为即将实施和开展,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相关建议,告知其行为实施危害性;在执行阶段可采取“中止型”建议,可以请求行政机关暂停采取措施;在救济阶段则采取“纠正型”建议,即要求行政机关作为或不作为,避免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该检察建议的履行并不具备强制性。
再次,明确证明责任分配规则。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定位于风险防范,这使其本身包含着缺乏充足科学证据的特点。在针对行政行为提起的预防性诉讼中,应综合适用“谁主张、谁举证”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32]。
以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为例,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由检察机关承担环境损害风险存在的事实证明责任,并确定重大环境损害风险与所诉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行政机关应当就其行为不存在重大风险加以举证。倘若案件进入到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可以由法院适用纠问式调查原则,依职权调查案件,而不局限到双方举证内容。在举证责任确定的前提下,结合检察建议的督促情形来看,其所掌握的证明材料准确全面,应要求检察机关采取完整证明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在提起诉讼时,应当把握其诉讼论证逻辑,要求其首先应论证行政违法性所在,从行政机关的行为与义务之间是否符合比例原则进行评价,之后推演违法行政行为或不作为将造成的环境公益损害程度,避免沦陷到损害风险与利益救济的传统论证思路。
最后,完善风险认定体系。环境风险认定体系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审查采取过程性审查认定标准,即法院不仅要审查行政行为的程序性缺陷,还要深入审查行政机关的决策过程是否充分严格考量可能存在的影响。过程性审查并不像实质性审查那样,要求法院自己判断以取代行政机关的决定,而是审查行政机关在决定过程中是否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种环境风险因素,即“通过强调对行政决定作出的过程加以审查,确保其符合最低限度的合理性标准”[33]。这样既能够避免法院介入行政权合理行使过程中,又能够从更深层次确保行政决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5.3 重构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结合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递补性地位来看,现行诉讼制度仍面临着环境风险预防的滞后性,应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包括风险认定、诉前程序、证明责任及司法听证等,确保案件审理能够契合对重大环境风险的预防要求。
首先,细化环境风险认定标准。前述案例分析可知,行政违法性并非意味着重大环境风险必然存在,应当摒弃这一思想,转向对环境风险的技术判断。法院在审查环境利用行为是否会造成重大环境风险时,应当结合中国环境科学标准具体展开。例如,对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行为予以考察是否符合特定环境质量标准或环境基准,对可能造成重大生态破坏的行为则考察是否满足包含最低安全需求限度、最低可恢复限度、最低可容忍限度三个方面的生态保护红线[34],由此,将重大环境风险直接与环境利用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明晰,对“重大风险”后果严重性及发生可能性的阈值予以具体化确定。
其次,引入禁止令和和解协议的诉前程序。就禁止令而言,美国司法实践中普遍采取禁止令的方式以阻止某项行为的实施或继续开展,继而由法院综合判断情形,对案件胜诉可能性、不可弥补的损害、双方及公共利益等进行考量,以确保采取该项禁止令能够避免环境风险的进一步扩大。如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v. Hill(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法院认为有必要通过发布一个禁止修建巨大规模的大坝的禁止令,以保护濒危灭绝的鱼,通过禁止或要求被告作出一定行为,从而实现其预防目的。就和解协议而言,和解协议是建立在当事人主义理念之上的一种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基于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一个具体的环境风险预防方案或计划,借由协议来推动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在项目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都更关注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由法院对协议内容是否合法、对公共利益有无损害进行判断进而做出认定。这样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累,又利于矛盾化解和协议执行[35]。
再次,完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针对企业或其他主体行为提起的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中,采取“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作为前提条件,由原告提供初步的证明证据,证明重大环境风险的损害结果与相关损害行为之间的部分因果关系,即原告能够证明部分关联事实,便可推定其余部分事实也同样存在。基于被告与风险源头的关联性,继而将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并由被告证明其行为不会产生不可逆转的严重损害后果。同时,考虑到重大环境风险可能存在多种原因要素,当被告承担反证证明责任时,无须对重大风险因果关系的全部待证事实一一举证,应当允许其将经验准则和间接事实作为前提要件,通过三段论证明方式,推定主要事实是否存在。若被告无法对其造成的损害进行反证证明,则因果关系推定存在而应承担相应责任。
最后,增加司法听证程序。环境风险预防更多是一个利益衡量的决策过程,风险交流制度的存在有着现实必要性,不仅是在行政决策阶段,在诉讼阶段同样应当确立。其中涉及的科学技术问题需要以专家专业知识为支撑,同时也需要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判断。而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启动意味着重大环境风险经过系列程序论证存在现实可能性和影响广泛性,在诉讼过程中有必要引入司法听证程序,将本案诉讼主体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纳入到诉讼过程中,听取相关主体或受影响环境周边当事人的意见,为法官在环境风险认定及裁判中提供更多地事实考量和理由依据。
参考文献
[1]唐瑭.风险社会下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阐释及实现路径:基于预防性司法救济的视角[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7(3):29-37.
[2]于文轩,牟桐.论环境民事诉讼中“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J].法律适用,2019(14):25-32.
[3]王春业.论检察机关提起“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J].浙江社会科学,2018(11):51-58,157.
[4]吴良志.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确立与规则建构[J].江汉学术,2021,40(1):15-23.
[5]于文轩.生态文明语境下风险预防原则的变迁与适用[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59(5):104-111,221.
[6]张旭东.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规则思考[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4):164-172.
[7]王旭.论国家在宪法上的风险预防义务[J].法商研究,2019,36(5):112-125.
[8]苏宇.风险预防原则的结构化阐释[J].法学研究,2021,43(1):35-53.
[9]杨小敏,戚建刚.风险最糟糕情景认知模式及行政法制之改革[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30(2):83-94.
[10]吴凯杰.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J].理论与改革,2017(3):146-161.
[11]邓禾,韩卫平.法学利益谱系中生态利益的识别与定位[J].法学评论,2013,31(5):109-115.
[1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19)[R].2020.
[13]陈杭平,周晗隽.公益诉讼“国家化”的反思[J].北方法学,2019,13(6):70-79.
[14]刘艺.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检察公益诉讼[J].中国法学,2020(2):149-167.
[15]梁鸿飞.预防型行政公益诉讼:迈向“过程性规制”的行政法律监督[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4(4):85-94.
[16]乌尔里希·普罗伊斯.风险预防作为国家任务:安全的认知前提[M]//刘刚,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53.
[17]张洋,毋爱斌.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重大风险”的司法认定[J].中国环境管理,2020,12(2):138-144.
[18]许传玺.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J].政法論坛,2002,20(1):34-49.
[19]潘同龙,程开源.侵权行为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24.
[20]杨立新.侵权法论[M].3版.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40.
[21]王竹.侵权责任分担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数人分担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9.
[22]王明远.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方向: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理论的分析[J].中国法学,2016(1):49-68.
[23]FISHER E. Risk regu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searching for‘in‑telligibleprinciples’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J].Environmental law review,2001,3(2):139-147.
[24]江利红.行政过程的阶段性法律构造分析:从行政过程论的视角出发[J].政治与法律,2013(1):140-154.
[25]刘艺.构建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机制[J].法学研究,2018,40(3):39-50.
[26]巩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性质定位省思[J].法学研究,2019,41(3):127-147.
[27]张宝.从危害防止到风险预防:环境治理的风险转身与制度调适[J].法学论坛,2020,35(1):22-30.
[28]尹建国.行政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释义[J].法学论坛,2009,24(1):59-65.
[29]吴凯杰.论预防性检察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定位[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1):30-44.
[30]金自宁.风险中的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89.
[31]巴鲁克·费斯科霍夫.人类可接受风险[M].王红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4.
[32]林仪明.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立法难题与司法应对[J].东方法学,2018(2):151-160.
[33]刘东亮.涉及科学不确定性之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美国法上的“严格检视”之审查与行政决策过程的合理化的借鉴[J].政治与法律,2016(3):125-139.
[34]曹明德.生态红线责任制度探析:以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为视角[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6):71-78.
[35]赵秀举.论民事和解协议的纠纷解决机制[J].现代法学,2017,39(1):132-144.
Logic and system development of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LI Huaqi
(School of Law,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China)
Abstract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mphasizes the prevention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system, conform to the logical order of judicial relief and respond to the public ’s demand for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At present,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is faced with some limitations such as deviating from the logic of judicial judgment, ignoring the subject of preventive responsibility, and being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damage relief, which results in insufficient performance of the preventive function of litigation. In the modern society, administrative or‑gans undertake the task of environmental risk regulation, but the scientific uncertainty of risks will inevitably make administrative pow ‑ er encounter difficulties, the case of 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s shows that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feasible to seek admin ‑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China should turn to public law liti‑gation based on public law liability, strengthen the risk prevent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subject of legal obligations, and cover environ‑ mental resource utilizatio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al risk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behavior. Logically, when settling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basic posi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 administrative judgment should be respected, the supervi‑sion status of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 available preventative position of civil environ ? 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risks such as environmental health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est measurement method should be define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 litigation rights should be realized. As far as the specific system is concerned, firstly, on the basis of insisting on the litigation nature of public law, the legislative ideas with the na‑ture of public law should be designed, including the legislative mode, risk scope, and procedural rules. Secondly, the preventive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four aspects: broadening the sources of case clues, classi‑fying the pre-litigation procedures, clarifying the distribution rules of the burden of proof, and improving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system, so as to give play to its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function. Thirdly, the preventativ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 ‑terest litigation should be reconstructed by refining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introducing different ways of pre-litigation proce‑dures, improving the distribution rules of burden of proof, and increasing judicial hearing procedures, so as to realize the optimal appli‑ cation of litigation preventive measure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risk administration; public law litigation
(责任编辑:王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