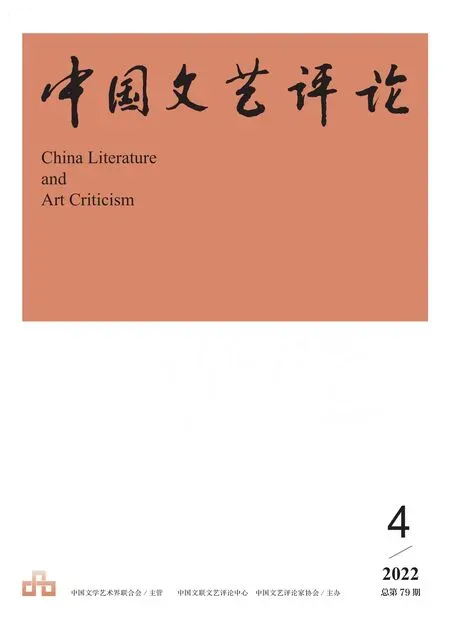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的成熟道路
——兼以《人世间》为个案
■ 王一川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相通点和结合点
假如以上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简括有一定合理性,那么,从理解文艺问题的角度看,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以下相通点:一是都主张无神论,反对宗教和迷信对人类的欺骗或麻痹,从而反对把文艺源泉归结为上帝或其他神秘原因;二是都标举人学,注重人在世界上的主体性,都主张文艺来自人的社会生活;三是重实践或实行,主张知与行的统一,反对空谈或玄想,要求文艺注重社会生活刻画、重视社会生活效果;四是讲究事物矛盾和转化的辩证法,强调事物是运动和变化及转化的,注重文艺的对立面及其辩证转化;五是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要求文艺符合“美”或“文心”。
当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毕竟存在相异点,例如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中国传统智慧则信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循环往复运动,尤其是主体(人)不过是客体(天)的一部分;前者要通过集体的社会实践去改造世界,而后者更强调以主体心性去调整与世界的关系。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而中国文化传统则需要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适应现代中国国情的变化。
有鉴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上述相通点和相异点,如果确实需要在它们之间找到相结合的文艺道路,中国式现实主义无疑是一个突出的范例。
二、现实主义文艺与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
从以上的简略列举可见,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观的主要精神在于,突出文艺的个性、真实性、典型性、生动历史性、倾向隐蔽性,主张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结合,要求文艺帮助人们从中更好地领略社会历史的规律性。
三、现代中国文艺中的现实主义
四、跨文化涵濡与心性现实主义范式
如前所述,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很多,这里还是集中为以心性智慧为代表的倚靠个体心性修为去化解人生问题的思维方式,如仁厚、仁义、中和、和合、友善、慈悲、知行合一等,还可以简约为王阳明倡导的“心功”。对这种中国智慧,尽管可以就其中的儒家式仁义之心、道家式天地之心和佛家式即心是佛等内部差异作细致辨析,但它们在注重心性修为的作用上无疑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式心性智慧通过漫长时期的相互浸润、化合等跨文化涵濡过程,才逐渐找到一条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文艺道路,并在《人世间》等作品中将这种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美学范式推向成熟。
五、当代中国文艺场中的《人世间》

图1 电视剧《人世间》海报
先看这种文艺场在小说生产过程中的特定作用。综合有关材料可知,这部小说由作家梁晓声于2010年起构思、2013年初动笔、2017年9月完成初稿并试发行,2018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字数约115万字。需要看到,参与推动其创作的作用力远不止作家一人:(1)当作家还在酝酿小说构思时,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就亲自介入约稿和催化;(2)当这个暂名《共乐区的儿女们》的长篇小说项目还处于写作状态而尚未完稿时,就被该社凭其立项计划书而入选中国作家协会2017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计划;(3)该选题还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4)中国青年出版社在该小说尚未交稿时就不顾内部反对以特殊政策提前支付作家10万元预付稿酬并预签出版协议,以防中途被其他出版机构拦截;(5)小说在出版后于2019年8月获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简称“茅奖”),并在终评时得票高居第一,可见其在文学界受欢迎和嘉许的程度。
对文学(小说)与电视剧之间的近乎全民参与的艺术公赏局面的形成及其原因,当然需要专门总结,但可以简要指出的是,文学为电视剧改编奠定坚实的故事、人物及其思想题旨基础,而电视剧擅长把它们改造成为普通公众乐意接受和喜爱的影像系统;文学可以受到文化人群体欢迎,电视剧可以扩展到巨量普通受众中;当电视观众受到震动而愿意回头捧读小说时,小说确实可以提供电视剧所没有的文心底蕴去抚慰。
在理解当代中国文艺场的作用时,需要追究的是,为什么《人世间》能够受到小说出版界、文学行业协会及其评奖机构、国家图书出版立项机构、电视剧行业龙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诸多顶级文化艺术机构的如此高度一致的欢迎、推荐、好评和嘉许,好像他们一直在等待它出现似的?这就需要看到,从这部小说动笔的2013年年初到根据其改编的电视剧播映的2022年年初,适逢中国进入“新时代”刚十年。这十年中国社会形成了由多方面合力构成的特定的当代中国文艺场,这个场特有的语境和氛围给予《人世间》顺利萌芽、巨量生产和传播以及近乎全民参与的艺术公赏以充足的文艺生产机制和美学动力结构等培育条件。要理解这个当代中国文艺场,涉及的因素多且复杂,但想必其中有六种要素必不可少。
二是行业优投。无论是小说出版方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是电视剧联合出品方阅文集团、腾讯影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机构,以及向小说颁授“茅奖”的中国作家协会等,都对该项目予以优先和优质投入,这也可以视为上述国家导向的高效落实。假如把它们都视为当代文艺生产行业机构的主干的话,那么这些行业机构是让作品顺利萌芽、生产和传播的基本动力部门。没有这些文艺生产动力部门的实际运行,《人世间》要想如此顺利地生产、以及生产后要想产生现在这般的社会效果,都是不可能的。其间如果出现一些闪失,都会不仅导致其社会效果打折扣,而且就连出版或播出也可能成为问题。电视剧改编时如果结尾还是像小说原著那样让作家周蓉的作品描述成为弟弟周秉昆的未来指引,以及在周秉义去世后让其妻郝冬梅改嫁“红二代”远走国外定居,想必观众都不会买账。而中央电视台如果没有安排在春节期间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效果也不会如现在这样好。这些显然都属于行业机构实行优投的结果。
三是民生体验。这是文艺家们进行文艺创作时依赖的对于社会生活、人民生活或人间活剧这“唯一源泉”的深切体验。作家没有仅仅凭借国家的有关号召就去生硬地写“人民”,而是对于所描写的社会生活素材有着长期而深厚的个人体验的浸润,尤其是他从小就熟悉周志刚式的家庭,能够把自己的个人和家庭生活投影分别浸润到周志刚、李素华、周秉义、周蓉和周秉昆等主要人物身上。可以说,这部小说由于写的是作家自己所亲历和想象的那个家庭和它的时代,因而就是从他的个体生命之树上仿佛自己长出来的花朵和果实。而在电视剧改编时,故事发生地从哈尔滨被移植到长春,也是由于导演本人就是长春人,熟悉其地缘环境,能够精心营造出“江辽省吉春市同乐区光字片街道”这个特定的城市平民生活场所,透过它而让观众洞悉整个中国社会“人世间”的风云变幻。可以说,没有这样丰厚而真切的当代东北民生体验,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小说和电视剧《人世间》。
五是艺术创意。这是文艺家(包括小说家、剧作家、导演、制片人和演员等)对待文艺作品从媒介、语言、形式到形象和意蕴等的全方位的创造性发现、构思和加工环节,其结果是富于独特艺术个性的文艺作品的完成。上述所有四种要素的力量都只有转化成为具体的艺术创意,才能直接孵化出优质文艺作品来。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作家、编剧、导演和演员四方面作用所形成的美学合力:作家的文学创意为该作品的人世间故事及其感人魅力的生成提供了独具个性的原创性、丰厚的意义沃土以及可以持续开垦的广阔空间;剧作家的编剧创意由于其本人谙熟大众艺术的美学逻辑和各类观众的群体心理指向,而善于将改编引向符合电视观众共同预期的方向;导演熟悉以吉林为代表的东北地缘生活、民风民俗和普通人形象塑造,可以综合出一部集中映现东北地缘生活风貌的作品;所选主要演员几乎都是行业中的优秀人才和敬业者,可以确保编导的艺术创意在故事叙述和人物形象塑造上都一一夯实。
六是全媒鼓应。这是当前全媒体或融媒体时代由各种相关媒体(包括传统媒体、新兴媒体、自媒体等)组成的给予文艺作品传播以影响力的媒介环境的统称。这是一个历来容易被忽略但在当代已变得必不可少和十分要紧的环节:从小说出版到电视剧播映的几年间,特别是在电视剧从播出前夕到播映期间,相关的多种媒体如报纸、杂志、互联网平台、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都共同参与和助推了该作品的传播,从而为其生产和传播营造出有利的媒介环境。有的知名短视频平台就不断为此造势,观众一旦在手机上关注过它一次,之后就随时随地能自动、优先和似乎特别贴心地接收到它源源不断的相关信息,包括从电视剧中及时摘录出来加以反复品味的那些警句或格言式对白。这些相关信息的有备而来、持续传输和与观众的贴心互动,表明相关行业机构在该剧和该小说的持续宣发和营销上投入之巨大和持久。不仅在该剧首次播映时有多种媒体参与集体营造声势,而且就是在第二次开播时,多种媒体仍然在进行与之相关的进一步鼓动和呼应,以期持续扩大该剧的受众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这种后续的宣发和营销其实本身也是文艺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可以循环往复的文艺再生产过程。
上述六要素(不止于此)的合力,形成了《人世间》从小说到电视剧的孕育、生产和传播的优质机制、动力结构和总体氛围。假如没有这些要素的综合的催化、询唤或促进作用,《人世间》在现在问世并且产生如此强劲的传播效应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可以说,《人世间》正是当代中国文艺场的创造物。这有力地说明,当代文艺力作以及杰作的生产离不开当代中国文艺场的特殊作用力。
六、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的特征
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及其产物——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能够在《人世间》中趋于成熟的原因,也应从当代中国文艺场的特殊作用中去探寻:假如在此前更早的文艺场中,例如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文艺场中,这种成熟还缺乏可能性,因为那时的国家导向里还不可能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等相关指导思想,从而那时的文艺生产行业机构也还不可能产生出对《人世间》之类作品以超常规订货和优惠投拍等强烈意向。只是在当前这种文艺场中,当现实主义与以心性智慧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借助《人世间》这个产品而发生跨文化涵濡时,现实主义文艺必有的客观性、典型性和批判性等特征同以“心功”为代表的中国式心性智慧相结合,才能发生奇妙的化合反应。这里可以依托小说和电视剧及其相互比较,初步指出《人世间》所呈现的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的几方面特征。
第一,在再现现实的目的上,真善交融。这就是不单独追求现实再现的纯客观性或真实性,而是让个体的仁善之心去浸润真实,以仁润真。《人世间》确实能够不加掩饰地暴露周家生活的苦难性:父亲周志刚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八级技工的优秀代表,却到头来妻子李素华神经错乱、长子周秉义不替他生孙子、女儿周蓉与人私奔和只顾自己、小儿子周秉昆总是不争气;周秉义这样的好官却被人举报且身患胃癌;周秉昆一生命运坎坷: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仇人”骆士宾又来纠缠;好不容易开心于养子周楠考上清华再转美国留学时,不料周楠在美国遇枪击身亡,随后他与骆士宾发生言语冲突和肢体冲突,失手致骆士宾死亡,被判入狱近十年;周秉昆之妻郑娟年轻时遭骆士宾强暴生下长子周楠,而且后来因周楠被骆士宾诱惑和鼓动与周蓉之女冯玥恋爱,不得不痛心地向众人揭开心底隐痛,可谓雪上加霜,唯一的弟弟光明眼瞎;周秉昆入狱留郑娟一人孤苦地支撑全家。对于这家好人却没得好报而一再遭遇苦难的原因,作品没有硬性给出一个准确答案,而是让人物自己的活法去证明:周志刚临终前对自己一生和子女们都表示满意,周秉义坚持按照父亲和岳父母的教导和希望全力做有作为的好官,周蓉后来有着自我批评和转变,周秉昆以“觉得苦吗,自己嚼嚼咽了”之类口头禅要求自己,郑娟则以仁厚和慈悲之心对待苦难。凭借这些宽厚、正义、反思、坚韧、慈悲等自觉的个体心性修为,周家人才能顺利渡过一道道难关而迎来心灵的安顿。小说和电视剧都注意以个体心性修为去过滤和规范单纯的客观性冲动:既无一坏到底的坏人,也无完美无缺的完人(周秉义心中也曾对俄罗斯姑娘产生好感),好人中有不足(例如曹德宝和乔春燕夫妇无端举报周秉义),坏人中也有可同情或可宽恕处(对骆士宾的无理性和贪婪也可以理解)。个人如此,整个当代现实世界也一样。对于周秉义这位在小说和电视剧中都具有引领地位的灵魂人物,电视剧在他去世后没有遵循其遗愿让其妻郝冬梅改嫁“红二代”并移居海外安度余生,显然是尝试安抚对周秉义的刚正务实风范依依不舍的电视观众的公共情绪,体现仁善之心对过于无情的真实性或客观性冲动的缓冲和节制作用。
第三,在再现现实的根源上,地缘化育和时势造人。正像“地灵人杰”“钟灵毓秀”“南橘北枳”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等习惯语所揭示的那样,中国传统历来信奉水土养人或地缘化育的作用,注重展示特定地域的地缘内生力。地缘内生力是特定地理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独特人类生命力,对人物性格的生成和演变有着特殊构型作用。同样的人,因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等不同会发生人格变异,显出不同的地缘特征。电视剧虽然把小说中的哈尔滨地缘场景转换为吉春市“光字片”,但都注意深挖和凸显东北地缘内生力的潜移默化的形塑作用,建构起从“文革”末期到改革开放时代江辽省吉春市同乐区光字片街道的底层市井形象。同时,时代变迁所造就的新时势,更会给予人的性格及其命运以新的影响以及形塑,所以说时势造人。体现在电视剧中,就是让骆士宾、水自流、彭心生等在深圳创业成功的第一批东北籍商人携带改革开放时代新风气去与老工业基地传统发生激荡作用,并且让原来在小说里简略的他们转而在剧中占据更显眼的位置。周秉义去往深圳面见昔日兵团战友姚立松,骆士宾更是在深圳经商成功,周家第三代冯玥也到深圳就业,他们都受到南方及“下海”的时代风气影响。这里的东北地缘化育景观以及时势造人景观,让观众能像欣赏《温州一家人》《圣天门口》《平凡的世界》《情满四合院》《大江大河》《装台》《山海情》等分别带有华东、华中、西北和北京等地缘特征的电视剧那样,欣赏到东北独特的地缘家族及其人物风貌。如果说,周志刚、周秉昆、郑娟、乔春燕等人物都烙上了典型的东北地缘烙印,那么,周秉义、周蓉、骆士宾、冯玥等人物则呈现出中国进入流动型社会以来人口频频流动所带来的地缘化育和时势造人相交融的奇观,因为这些人物身上已经显示了东北地缘文化自身的独特特征及其在新时代发生演变的新印记。

图2 电视剧《人世间》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四,在再现现实的态度上,褒贬皆有。这就不是单纯的冷峻批评,也不是简单的肯定和赞扬,而是始终携带富于情感态度的批评、批判和有着保留的肯定、赞扬,使得批判中有赞扬、赞扬中有批判或批评,褒贬皆有、批赞共存。对于几乎完美的模范人物周秉义也有批评:在周志刚晕倒后,周秉义和周蓉从外地赶回家,一致责怪周秉昆没能照顾好父亲。前者怪他没及时联系郝冬梅,后者直接对他发脾气:“你咋整的啊,我告诉你,爸有事我跟你没完啊。”幸好父亲本人出来替小儿子说了公道话:“爸爸啊,是你们仨人的爸,不是秉昆一个人的。你不能因为弟弟一直守在爹妈身边,出了什么事就都怪他呀。”这样的描写显然既表扬了周秉昆的孝顺,又对周秉义和周蓉兄妹俩作了含蓄批评。电视剧更突出周秉昆作为底层平民在全剧的根基地位和感召作用,这种改动让人不禁想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在改编时突出孙少安而弱化孙少平,同样都是在大众文艺中弱化读书人或文化人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全剧最后的话还是由周秉昆的“想想就美”四个字来作结,以及留下主题歌《人世间》作余音——“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世间的苦啊,爱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甜啊,走多远都记得回家/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这样的余音产生出点题效应。
当然,小说和电视剧对最值得赞扬的第一主人公周秉昆,也包含不留情面的批评。他不该时常产生迷信心态,更不该莽撞地与骆士宾两次打架,从而给家庭带来几乎致命的打击和灾难:第一次是由于郑娟派周楠道歉才免于牢狱之灾,第二次则是周楠亡故后与骆士宾打架时致对方身亡。不过打架致对方身亡之事也有特殊缘故:电视剧第44集叙述周秉昆在首都国际机场送走郑娟后见到骆士宾,后者埋怨前者没有早点把楠楠交给自己去美国培养所以出了事,前者反过来指责后者太自私,关键是后者不仅蛮横地说楠楠和郑娟都是自己的人,而且竟敢无耻地侮辱说郑娟是没文化的和自己玩剩的女人,说着还狗急跳墙地用双手猛烈推搡前者,彻底激怒了前者,两人激烈厮打,直到骆士宾摔倒后脑勺撞在石墩上昏死。这里显然都让观众既寄予同情和理解,也同时带有遗憾和隐性责备。
而在对待周蓉雅奇孤傲的性格时,电视剧的批判性更强烈。在讲述周蓉不顾郑娟感受,去动员她同意冯玥和周楠恋爱时,周蓉轻飘飘地责备说:“为了那些不知道过去多少年的陈年旧事,耽误孩子们的一生,值不值?”这话显然太自私,丝毫不顾及郑娟的隐痛,其理由竟然是“我一直觉得你是女人中的女人,心里面没有自己,只要家好,家人好,孩子好,亲人好,不像我那么自私、那么任性”。郑娟坚持辩解说:“孩子们的一生是一生,我们的一生就不是一生了?”这里透过周蓉的孤傲自私表现,弱化她作为作家或文化人在小说里原有的终极代言人高位,包括不再沿用她的小说新作《我们这代儿女》中第476页的格言警句式语言作为全剧关键话语,也就是没有采纳小说中蔡晓光电话指导周秉昆阅读并给予权威性开导的原来构思。在这个特别显眼的关键点上,电视剧显然不想让作家或文化人“自我感觉良好”。
同时,电视剧也没有结束在周秉昆请求妻弟萤心和尚保佑的话语中,似要弱化小说中多次流露的这类迷信;而是变成了周秉义遗书对于周蓉和周秉昆姐弟俩未来人生的启示,从而突出周秉义这一刚正有为人物在全剧的引领地位。当小说不无道理和顺理成章地让作家周蓉的作品在全剧结尾产生画龙点睛般导向作用时,电视剧宁愿改让周秉义和周秉昆分别承担“顶天”和“立地”的特殊作用,而把周蓉适当地降低为游动于“天”与“地”之间的居中者或中介者角色,可谓各有各的处理法。
七、结语
对于《人世间》在小说原著和电视剧改编之间的异同,完全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需要看到,这两者从不同方面合力共推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在过去多年探索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巨量公众的公共认同而走向成熟。这确实是需要认真总结的当代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的一条经验。当文学的心性现实主义探索走在各文艺门类美学探索的前沿、但又主要局限在文化人群体里时,电视剧的心性现实主义探索将其推广到更广泛的各阶层群体中,由这两者在不同维度上的共同努力的合力衍生出强劲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借助于近乎全民公赏的公共认同而得以成熟。数量巨大、代表性广泛的公众群体的公共认同,无疑是一部当代好作品的可传世品质的重要基础和醒目标识,无论它究竟属于哪个文艺门类。相信《人世间》这部作品及其推向成熟的中国式心性现实主义范式,会对当前和今后各文艺门类叙事类文艺创作起到有力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