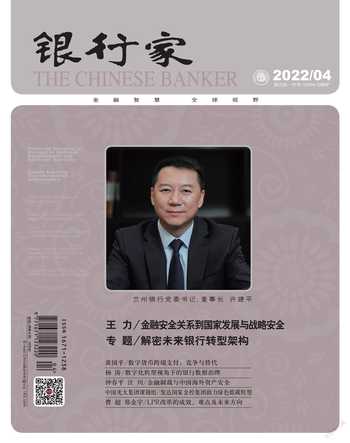信托受益人的诉权问题反思
柏高原 汤杰

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民事实体权益的权利,而受益人的诉权是受益人实体权利在程序法上是“映射”。英美法下,如受托人在信托财产管理运用中与第三人缔结合同,在合同履行中存有争议的,受益人一般情形下不享有针对第三人的诉权,仅在受托人违反信托等特殊情况时才允许受益人向第三人提起诉讼,即“信托衍生诉讼”。本文所讨论的案件是一例典型的资管纠纷案,原告/上诉人为一家农商行(委托人/受益人),被告一为一家股份制银行(资管中的受托人),被告二为一家券商(该券商系受前述资管受托人所托,通过资产管理业务对资金进行投资、运用,不妨称之为“再受托人”或“第三人”)。允许受益人将再受托人列为被告,既虚化了受托人的受托义务,又混同了“委托”与“信托”,有所不妥。英美法下受益人仅在特定情形下方享有对第三人的诉权,与股权衍生诉权类似,值得国内借鉴。
案涉资产管理业务概况
临西农商行和恒丰银行间存在合同关系,双方签署了《委托定向投资业务合作总协议》,并在协议签署后由临西农商行向恒丰银行发出《投资指令》。根据《投资指令》,恒丰银行与中信证券签订《资管合同》,由恒丰银行作为该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方,以资金作为委托财产由中信证券通过与奥创公司、河沈电缆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向河沈电缆提供融资和租赁服务(见图1)。
一审法院认定:“恒丰银行和中信证券仅根据约定提供必要的事务协助或者服务,不承担主动管理职责,并收取相关通道费用或管理费用。因此,案涉信托资产管理应认定为通道业务。”同时认定:“三方之间签订的相关协议不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故对临西农商行与恒丰银行、中信证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应当依据案涉信托文件的约定加以确定。”
信托关系下诉权的“射程”
一審、二审中,中信证券均提出其不是适格的被告。笔者推断,考虑到一审并未判定其承担任何责任,中信证券并未提出上诉。一审法院对于中信证券的被告地位是这样论述的:“虽然临西农商行与中信证券并未直接订立信托协议,但在双方与恒丰银行分别订立的相关协议中,均可明悉临西农商行系案涉信托资金的实际出资人,中信证券系定向投资资产管理计划的受托人及管理人。临西农商行与中信证券对彼此的存在及在案涉信托关系中的地位均是明悉的。中信证券系案涉通道业务的一方当事人,临西农商行向其提起诉讼并无不当,中信证券关于其与临西农商行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法律关系,其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无论从实体法的角度还是程序法的角度,一审判决的部分说理有可商榷之处。临西农商行作为委托人,“越过”恒丰银行这一受托人,将中信证券作为被告,这一做法与委托贷款中被告确定规则有些“相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答复意见规定委托人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和对受托人的被告地位加以明确,从而对委托人权利加以保护。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件中,也可见相关案例。上诉人北京长富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武汉中森华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森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巨云、陈少夏、湖北徐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北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祥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建中森建设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合同纠纷案一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124号。该委托贷款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三方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建立了委托贷款合同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因借款人明知委托贷款系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发放的事实,《委托贷款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借款人,委托人可以自己名义直接向借款人主张权利。基于这一法理,有关合同直接约束本人和第三人的规定,在《民法典》中也依然延续。受托人基于委托关系与第三方建立合同关系,且第三人对前一环节的代理关系知晓的,委托人向第三人提请诉讼,与实体法与程序法均无不合。
委托本应区别于信托,信托关系下,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对财产进行管理和运用,而委托则不同。在认定构成信托关系的情况下,却又允许委托人“越过”受托人对第三人提出诉讼,一审这一判决与信托的法理相悖。
受益人向第三人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
英美法下的受托人大部分并不具备投资专长,信托财产的投资管理通常由外部投资顾问完成。因此,信托财产投资争议是信托受益人、受托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如外部投资顾问对信托财产投资管理亏损负有责任时,受托人有义务向外部顾问主张赔偿。值得注意的是,受益人通常无权“越位”直接向外部投资顾问主张权利,即并无诉因(cause of action),除非符合受益人“衍生诉讼(derivative claim)”的条件。受益人的诉讼策略通常可以有两种选择:申请更换当前的受托人,并主张当前受托人承担违反信托的责任;或者将当前受托人和外部投资顾问作为共同被告,启动衍生诉讼。
通常而言,信托受益人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就信托财产提起诉讼。但由于信托关系的特殊性,为了保护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英美法的判例中也形成了一种例外的规则,允许受益人在特殊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就信托财产提起衍生诉讼。比如在一个案例(Vandepitte v. Preferred Accident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1933] 1 AC 70 〔PC〕)中,确立了“范德佩特程序(Vandepitte Procedure)”,即受益人可以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前提条件:信托受托人拒绝履行信托义务,受益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衍生诉讼,但前提是受托人需加入诉讼程序或是在法庭出席。此后,在另一个案例(Hayim v. Citibank NA [1987] 1 AC 730 〔PC〕)中,审判委员会在审判的过程中重点论证原告(受益人)是否有权在特殊情况下提起衍生诉讼。该案中,大法官(Templeman)论及:“当受托人违反信托、或者涉及利益和义务冲突或者在其他特殊情况下,受益人可以代替受托人起诉第三人。但是,受益人被允许提起衍生诉讼并不会比受托人以适当的方式履行其相关职责更具有优势。”委员会进一步提到,受益人无权对第三人提起诉讼,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受托人未能履行其对受益人负有的保护信托财产或保护受益人在信托财产中的利益的义务。该案中,法官遵循了“范德佩特程序”,但同时对于“特殊情况”的范围做了更加详细的叙述,使得这一程序更具可操作性。
再看临西农商行一案。临西农商行与恒丰银行的资管业务合同关系,应界定为信托法律关系,临西农商行为委托人兼受益人,恒丰银行为受托人。受托人依照资产管理合同所约定的方式进行投资运作,将财产委托中信证券设立另一资产管理计划,该“另一资管计划”的性质也应界定为信托关系,委托人及受益人为恒丰银行,受托人为信证券。前后两项资产管理业务均属信托关系,但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均不相同。在后一资产管理业务中,中信证券应对其委托人/受益人负有法律和合同义务,临西农商行与中信证券间并无合同关系。允许临西农商行“越位”向中信证券主张权利,于实体法及程序法均有不妥。更为适当的做法是,如临西农商行认为恒丰银行违反信托合同,应向恒丰银行主张违反信托合同的责任;如中信证券在受托管理运用财产中违反了合同,恒丰银行负有向中信证券主张权利的义务,否则,恒丰银行应对其受益人承担责任。至于临西农商行能否越过受托人恒丰银行,直接向第三人中信证券主张权利,至少在现行法下答案是否定的。未来如果修订《信托法》,可以借鉴英美法下“范德佩特程序”的做法,允许受益人在特定情况下向第三人直接主张权利。
受益人向第三人提起诉讼的做法,英美法下称为“衍生诉讼”。这种做法与公司法下股东衍生诉讼有相似之处。在一个案例(Roberts v Gill & Co & Anor [2010] UKSC 22)中,法官也对受益人衍生诉讼与股东衍生诉訟作了类比。《公司法》下,股东与公司为独立的主体,分别享有权利、拥有财产。但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侵害,特别是受到有控制权的股东、母公司、董事和管理人员等侵害而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时,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个人有权以公司的名义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股东衍生诉讼本质上是一种代位诉讼,其代位的前提是作为诉权实质意义的享有者——公司不行使其诉权。信托法律关系下,受托人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在信托财产受到侵害时,受托人拥有诉权以保护信托财产,在特殊情况下(如受托人未能履行义务),受益人享有诉权。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受益人享有诉权,但并不意味着受益人是信托财产的拥有者。这在一部经典信托法著作(Lewin on Trusts 〔20th Ed., Vol. 2〕) 中也有论及:“受益人拥有代表信托财产或更准确地说代表受托人起诉的‘对人权(rights in personal)’。”可以认为,受益人所拥有的诉权,是代表信托财产或代表受托人,英美法下这种权利依然是“对人权”,而非“对世权(rights in rem)”。
临西农商行一案的延展
我国在引入信托制度时,产生了“普通法一物二权”的普遍观念,这实际上是对英美法系信托制度的误读。英美法系信托法中的权利建立在财产权体系之上,与源自罗马法的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权利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英美法系的信托关系中的受益人权利不宜简单对应我国《民法》中的“物权”,“一物二权”更无从谈起,因此也不存在与《物权法》的冲突。英美法系财产法强调所有权的分割性,但分割的并非实物,而是实物上的“抽象权利束”,组成完整所有权的“一束权利”之上可能有多个所有人。这些所有人的权利之间存在一定的界限,并且会动态调整。在英美法中,财产权可以在时间、功能等多维度上被分割,这种分割的理念成就了现代信托制度。因此,简单地将英美法信托中的财产权“estate”对应大陆法下的所有权,会导致不必要的困惑。
早期的英国法庭只承认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的法定所有权(legal title),然而,由于衡平法院(Court of Equity)在某些情况下会承认受益人为实际所有人(actual owner),这种所有权只能在衡平法院得到强制执行,故称为衡平法所有权(equitable ownership)。不幸的是,法定所有权和衡平法所有权这两个术语的使用被混淆,给人以“信托财产是双重所有权和冲突所有权”的印象。
实际上,英美法下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非没有争议,但采取了比较务实的做法。一位英国学者(Maitland)没有将信托下的受益权视为所有权,而是仅将其作为针对受托人或从受托人处取得信托财产者的“对人权”。另一位学者(John Austin)则持不同观点,他区分了“对世权”和“对人权”,将受益人在信托下的权利视为所有权。虽然理论界争执不下,但立法采取了较为务实的观点,即出于某些特殊目的或在特定情形下,“受益权”应被视为所有权。情形一:当国家试图对受益权征税时;情形二:当受益人试图根据一个典型案例(Saunders v. Vautier)中的规则终止信托时;情形三:当受益人试图追查受托人滥用的信托财产时。在以上情形下,受益人被视同取得了信托财产所有权。如果只涉及受益人和受托人之间的问题,如当涉及受托人对信托的管理争议时,受益人对受托人只有对人权。
在传统二分法下,信托受益权的限制的确难以定位,或许这也是信托受益权性质一直存在争议的原因之一。但传统的“物权债权二分法”近年来也受到了挑战——物权与债权相互交融,二者的界限日益模糊。例如,《公司法》下的股权,既非物权亦非债权,却在我国被普遍继受和运用。既然有例可援,为何因循守旧?因此,“物权债权二分法”不应构成我国继受信托的障碍。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会有更多的“权利/权益”需要借鉴、移植和创设,这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予以接纳。
(作者单位: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南开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杨生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