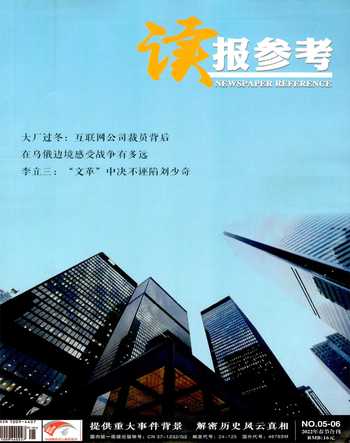勇气、传奇与信仰:老英雄赵引群的太原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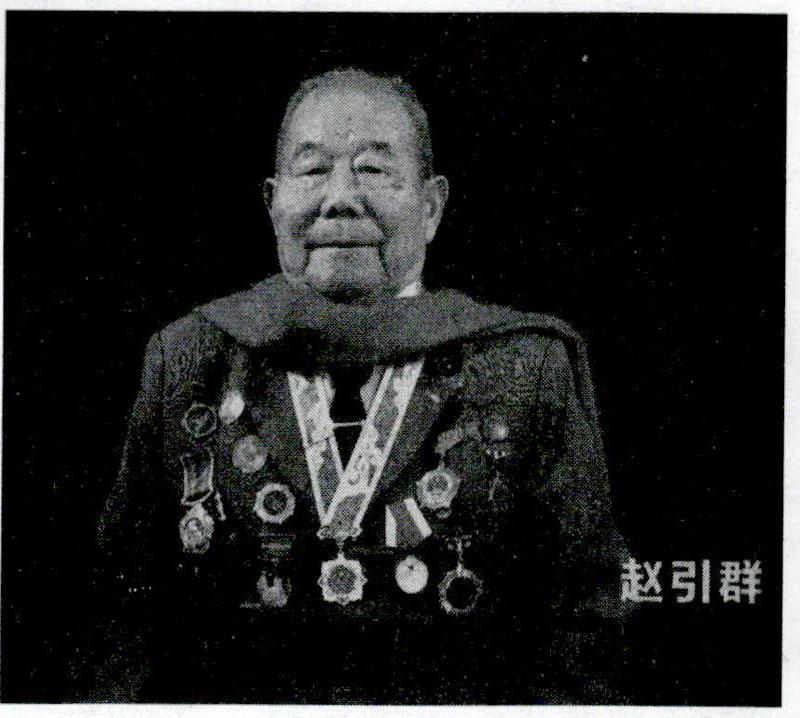
太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6个多月,伤亡4.5万人,是解放战争中历时最长、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现年91岁高龄的青岛军休干部赵引群,正是当年亲历太原战役的老兵之一。虽然时隔70余年,但是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老人依然记忆犹新。
主动去嗅毒气的人
“我记得是1948年11月前后,打太原战役的时候,我们攻下了淖马阵地。站在这个阵地,就把太原城看清楚了,所以,敌人一心要夺回来,我们就在这儿守,白天晚上地守。淖马阵地,哎呀,敌人不知道打了有十几次……”
老人的记忆非常清晰。淖马阵地是东山的“四大要塞”之一,它比太原城高出300米,由10余个子阵地组成。1948年10月27日我军攻占淖马主阵地后,一连两天,敌军以4000余人的兵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连续反扑19次,均被我军击退。此后,敌人的反扑依然连绵不绝,直至11月12日,历时半个月时间,淖马阵地方被我军完全占领。在反攻淖马阵地的过程中,阎锡山不仅动用了被他视为“精銳部队”的投降日军,还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毒气弹。
“我中毒了三次。”赵引群说,“阎锡山的毒气弹可多了,经常用。他的毒气有两种,一种是催泪气,眼睛马上就睁不开了,疼、肿,眼泪鼻涕很快就流下来;另一种是窒息气,气味不大,但是能把人熏倒。防毒的办法就是赶快用布蘸水捂在鼻子嘴上,没有水的时候就先拿手捂着,然后赶紧接尿,尿也是水,能起作用。”
“但是我不捂嘴,防毒是我的工作,我每天看风向。”赵老的乡音很重,怕别人听不懂,一边回忆,一边还不停打手势作辅助说明,“风向西刮的时候,敌人不会打毒气弹,不然会刮到他们自己那里去。但是风向我们这边刮,我就小心了。窒息气有一点点味道,炸弹一爆炸,我就使劲闻,闻到味道就大喊:‘防毒!敌人放毒啦!我一喊,吸进去的毒气多,就容易晕,一般最多喊三声,我就倒了。”
“不过不要紧,一般中毒3天,自己就醒了,不用住院,但脑子还是会受损失。我倒了没关系,战友听见我喊,一边捂着嘴,一边赶紧打电话。这样,后面第二梯队很快就能冲上来。不然前面的人迷糊了,没有人顶替,敌人上来阵地就没了。”
赵引群的叙述令人动容。面对敌人的毒气,他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躲避或保护自己,而是主动去嗅!他所说的“不要紧”,其实是中毒过深昏迷后,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三天三夜,而且这个过程,他在短短半个月内居然主动重复了三次!
据战后被俘的日军辅佐官城野宏交代:“我们违反国际法而施放了毒气弹,仅在牛驼寨,就毒害了1600余名解放军战士。”由此可见,毒气毒性之烈。普通人闻到刺鼻气味,本能就会躲避,如果知道是毒气,更会躲得远远的。然而,赵引群为了保护阵地,为了保护战友,一次又一次地主动去嗅毒气,一次又一次地警告战友防范,一次又一次地挺身而出直面死亡。这种勇气,常人无法想象。
抢救了多少名伤员,连自己也记不清楚
赵引群是一名军医,然而,他当军医的过程却颇具传奇色彩。
“我刚到部队时,当的不是医生,是小卫生员。为什么后来当医生了呢?因为我跟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大夫学止血、学包扎。我对他客气,人家不管怎么样也是大夫,你得尊重人家。我早上给他打洗脸水,吃饭的时候给他打开水,地脏了我就整个扫。不尊重人家,人家也不教你呀!大夫就主动教我怎么止大血管出血,我也学得快、学得好,结果后来起大作用了。”
“打太原时,有一个班长负伤,就喊我。我跑过去一看,大血管断了,血往外直滋。我就拿出血管钳子,嗵!一夹。”说到这里,赵老伸出两个手指,干脆利落地作了个往下夹的手势,“这个血管钳子还是我自己拿钱买的,因为按规定,卫生员没有止血钳子,就只有镊子。大夫教我以后,我会止血了,但我也不好去领止血钳,就是领人家也不给你,‘你一个卫生员,你要止血钳子?我就自己买了一个。”
“班长喊我,我跑过去一夹,拉着扎血管的线扎住,消毒后给他包扎,挂‘一危伤员,就是挂着那个红的、绿的、白的、黑的布条条区分,优先往后运去抢救。”90多岁的老人一边说,两手一边灵巧迅捷地作出扎血管的动作。从他那极其娴熟的手法可以看出,当年在战场上,他抢救了多少伤员的生命。在后来的采访中得知,赵引群在朝鲜战场上,曾创下了一天抢救70多名伤员的纪录。
“后来那个班长送到了和平医院,就是白求恩那个和平医院。一个主任给他换药,就问他,哎,谁给你止的血?班长说是个小卫生员。主任说,不对,是不是你流血过多迷糊了?班长说,我没有昏迷,一受伤我就叫卫生员,他就来了。本来血滋滋地,他一弄,血就不滋了,不淌血了。”
“主任还是不相信,可班长坚持说他没记错。最后,主任告诉班长,这个卫生员的止血办法,现在很多大夫都不会用。你碰见这个卫生员,算你命大,这是个有本事的卫生员,你的命就是这个卫生员救的,再晚一分钟,你的命就没了。你要好好回去感谢这个卫生员。”
“那个班长伤好了就四处找我,我们部队已经跑到大西北,解放西安、宝鸡、武功……他就找不到我了。后来重新分配,他分配到华北,打听到我们部队是五五七团。结果刚打听到消息,我们部队又到甘肃去打兰州外围,接着去打宁夏战役,后来又去青海打西宁战役,到四川解放成都、西康,打土匪打得很好,消灭了好几万。那时候,他官当大了,在西康打听,我又到贵州黔东南剿匪去了。那里的国民党投降了,又叛变,拉到山上跟我们打游击,副支队以上的土匪头子我们消灭了62个,土匪打了4.8万人。再后来,他当师长了,又找我,我又到朝鲜战场去了。到朝鲜,他还找,又找到我部队了,居然又改海军了。我到海军,他就不了解了……”
一连串的战役名称,耄耋之年的赵老如数家珍。恐怕只有非常熟悉解放战争史和抗美援朝史的专家才能数清楚,老人的前半生究竟参与了多少场战斗,经历了多少次的生死考验。然而,即便搞清楚了这些,恐怕也没有人能知道,赵引群在战场上曾经抢救了多少名伤员——就连赵老自己也记不清楚。
梦回吹角连营
然而,赵引群的事迹还远不只于此。作为军医,赵引群还时常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亲手毙敌。
“解放太原的时候,城外到处都是敌人的工事,我们就偷偷挖坑道,换班挖,斜着往下挖,挖的时候还要避开壕沟和碉堡,挖着挖着,就挖进敌人那里去了。到总攻太原的时候,我们把地道盖子捅开,捅开以后,部队就呼呼呼冲上去,冲到敌人阵地上了。”
“我冲到洞口,听见指挥员叫‘号目吹冲锋号。连里面是司号员,营里面的叫‘号目。号目这样半跪着吹号,刚吹了一下,就叫子弹打中了。我冲上去一看,唉,都打到心脏了,救也没用,接着我也冲上阵地了。”
“刚出地道,我也分不清方向,到处都是枪炮声,我就一个劲往太原城的方向冲,冲得很快。到阵地上,我看见一个中校,其实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什么中校,后来在俘虏那儿才知道的。当时我就听见他在那儿打电话,喊:‘顶住!顶住!你退下来,我枪毙你!我一看是个官,我也不管你是什么官,拿支手榴弹,他在那打电话,我朝他那儿一打,嗨!就把他打倒了。”
说到此处,92岁的老英雄站起身,左手指着后脑勺的部位,右手握空拳摆出攥手榴弹的样子,做了个狠狠打的动作。
老人的眼睛闪着光芒。那一刻,仿佛他又回到了70多年前的战场上,仿佛他的身躯又恢复到年轻时的英姿飒爽。一个身背急救包的少年身影,在枪、炮、血、火肆虐的世界里纵横驰骋,俯身救人,抬手毙敌,脚下的大地在爆炸中震颤,炮弹在他头顶呼啸,机枪在他耳旁嘶吼,浓烟在他四周弥漫,火焰在他身边燃烧,热血在他周身沸腾,唯有信仰,在他心中不动如山。
“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老人缓缓坐下,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他讲到太原战役的黄土坡战斗,包括团参谋长在内的干部、战士全部牺牲,全连只剩一个炊事班坚守阵地,毙敌数千。战场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他所在连队冲上阵地支援时,鞋子瞬间被血泥染红浸透。
他讲到自己在朝鲜两次受伤,在鬼门关上昏迷数日才被抢救过来,可是伤愈后,立刻再次奔赴朝鲜战场。
他讲到因为自己喜欢治病救人,解放后不愿当部门領导,甘愿去一个小门诊部,当了个营职的医生。
他讲到当年救的那位班长,后来当了将军,来青岛继续找他,却因为在团职以上干部名单中没找到他,最终失之交臂。
他讲到自己在战场入党,面对用一根残木横架起来的红旗,说出了自己信仰一生并为之奉献一生的誓言。
他讲到去世的战友,这位乐观豁达的老人,勤奋好学的小卫生员,勇猛坚毅的少年,不计名利的军医,舍己为人的英雄,无数次遭遇生死关头都没有流露过丝毫畏惧的坚强战士,潸然落泪。
——也许,正是这么多闪光点的合集,才铸就了共产党人的品质。
“我是建国前的党员,我在党组织的这一生,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现在活着,这么好的待遇、这么大的荣誉,我感激党,感激我们党中央。我现在身体不好,也是90多岁的人了,没有几天活头了,但是我还是永远跟着党、永远拥护党,我就是死也得跟着共产党,这是我的信仰啊!”
(供稿单位:青岛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