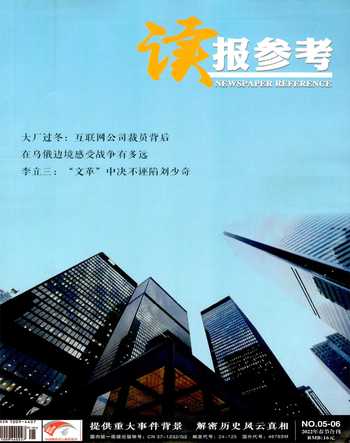天圆地方,渗透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人在观察宇宙万物运作中,归纳出阴阳之道,天圆地方也逃不出这样一种辨证的框架,至今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一
所谓方圆,不一定只是直观的方形与圆形。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它们更像是一种概念,其内涵具有无穷的丰富性与相对性。一般来说,方具有静态、规则、原则性等特点,而圆则有动态、整体、圆满、灵活性等特点。方是具象,像农田一样方方正正,是可以感触之物,观物若仅停留于方,就会滞于形述,必須由方入圆;圆是天道,虚廓飘渺,天的精神是超越具象的,是万物深层所蕴含的流转不息的生命之流。《孟子·离娄上》里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方圆,一方面代表了过去人对万事万物的归纳,另一方面要和人伦产生联系。这也直接体现在我们的造词里,譬如“方”是规整,“圆”更多是应变,两者合一就是“智圆行方”,这也是中国人处世的基本哲学。
在东方人的哲学里,方圆与阴阳、虚实一样,都必须相辅相成,方能不变应万变,或者以万变应万变。有方无圆则拘泥,有圆无方则不立。可以说,方圆理论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渗透进古人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
在中国古代,天地形态往往被概括为天圆地方,它表现在符号和图像上往往用圆和方作为宇宙模式的象征。
古代建筑,一方面要考虑人居的实用性,另一方面就是以天地伦常作为设计的准则。典型如古代礼制中的明堂建筑,从外观上就是象征天圆地方的,汉代李尤《明堂铭》云:“布政之室,上圆下方。体则天地,在国正阳。窗达四设,流水洋洋。顺节行化,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进贤良。秋厉武人,冬谨关梁。”《淮南子·主术训》载:“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
圆是观念,方是实际,这些空间意识演变到明清两代更加融合绘画艺术,形成园林美学。中国园林是综合艺术的殿堂,方与圆的景别布置是园林空间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园艺与方圆互相依存、互渗互融,譬如隔景的门普遍要做成圆形或扇形,因为圆形能让园景形成一种若虚若幻的画面,而叠石则多数给人方正的印象,因为它们是构成园景的基础元素,而且也寓意着主人的品性。我们去苏州观察那些古典园林,就会理解古人是如何以方圆让天然地形变拙为巧的,建筑结构或方形或圆形,有些顺势建造,有些则化直为曲,让方圆彼此呼应。最终,园林造景就和回环的玉璧一样,看起来层次感很强,如同天上铺叠的云层。方圆形态结合人文意境,让原本的小建筑因与广阔无垠的文人精神世界接壤,而被赋予了品之不俗的人文况味。小世界,纳方圆,建筑空间的深刻含义之大,远远超出了它的建筑尺寸。
三
方圆哲学对中国古代艺术的渗透,书法的例子同样典型。
很多人说中国人的汉字是方块字,这个说法更多是针对印刷体而言,而在传统书写中,汉字结构总体是外圆内方的。线条的方向与长度变化,是古人在造字过程中处理空间造型的基本形式。从书法的角度看,同一个字因左右两个边线在方向上的变化,从而使各自形态具有趋于圆与方、向与背、开与闭的视觉变化。同样,线的长短也可以使空间产生差异,两个字因左部的竖画与右部上下两个横画在长度上的变化,使字型具有了趋于连与断、离与合的视觉趋向。书法艺术讲求在不平衡中的平衡,让线条在变化中体现其流动的节奏韵律,汉字外圆内方的特征,与书法艺术的这一审美追求是相契合的。比如,方笔斩截爽利,给人以内柔外刚、精神外露之感;而圆笔圆劲饱满,给人以外柔内刚、气质含蓄之感。汉字的内方产生总体的一种平衡与和谐,而外圆能够形成流动不滞、无穷变化的艺术效果,也保证了书写的结构能够不断地走向开放,使得书写过程更加契合文人性情里不拘的自由。
以北宋黄庭坚的书法为例,其结体内紧外松,每个字几乎都有笔画向四面伸展,内方外圆产生了强烈气势,最终形成非常强烈的动感。乍一看来,东倒西歪,但又字字稳当,章法和谐。内方保证了书法艺术不至于走向无所依凭的、没有骨架的境地,就像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在《笔髓论·契妙》里说:“如水在方圆,岂由乎水?且笔妙喻水,方圆喻字,所视则同,远近则异。”可以说,中国人的书法是一个以中心点为圆心而构成的圆,进而形成由一点而发散的具有无穷变化的意象性符号。如同方与圆构成万物存在的方式与品格,汉字也不例外。
(摘自《文汇报》利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