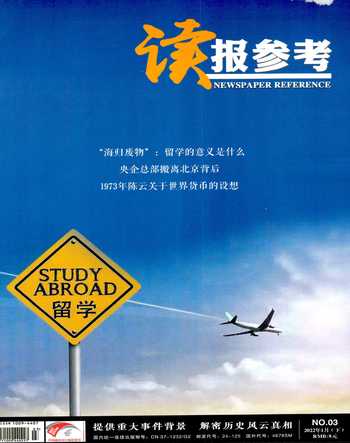韩仕梅:一个写诗农妇的“觉醒”
2021年,作为一个写诗的农妇、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韩仕梅被采访了20多次。1月,她的故事首次被媒体报道。后来,她的家成了“新闻现场”,她被拍进纪录片,写进大学生的毕业作品里。她的诗被发表在《新工人文学》杂志上。“我已不再沉睡,海浪将我拥起。”这是她写的诗《觉醒》中的一句,“觉醒”也正在她身上发生着。
一
2021年11月25日,韩仕梅受联合国妇女署邀请来到北京,在“与她并肩,携手同行”男性参与圆桌论坛上演讲。和她坐在一起的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荷兰驻华大使、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她穿着一件暗红色外套登台,台下的人西装革履。去之前,她对儿子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官,怕去了哆嗦。”在台下候场,韩仕梅无心听别人发言,把耳朵上的翻译机拽了。而真站到了台上,她反而不紧张了。她边念,边扫视观众,看见几十个观众认真听着,最后,工作人员对她竖起大拇指,两个外国人对她点头微笑。她觉得自己讲得比之前排练的每一次都好。
在演讲里,她活过的这半个世纪重新浮现。她自幼家庭贫困,初二时因为交不起18元一年的学费辍学,开始务农。22岁,她被母亲嫁给大她5岁的丈夫,兩人毫无感情基础。娘家收了3000元彩礼,盖了新房子。而结婚后,她发现那3000元钱是婆家借来的,她又要还债,“自己把自己买了回来”。丈夫几乎从不做家务,还曾沉迷赌博。她生育了一双儿女,怀女儿时腿上没力气,只能一条腿跪在地里干活儿。2020年春天,韩仕梅开始在网上写诗,以此排解心里的“郁结”。她说,看着那些网友留言,她感觉“情感被接住了,这是我从没体会过的感觉”。她曾形容和丈夫的相处:“和树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苦。和墙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痛。”
这一年,韩仕梅发现自己变快乐了。虽然她还是会偷偷哭,但次数变少了。她看到2020年发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照片里,都没有笑容,而2021年的照片,“露出灿烂的微笑”。因为去参加联合国的演讲活动要请假,韩仕梅和干活的工厂起了冲突,最后她丢掉了工作。但她还挺高兴,“你们来了,我可以给你们做饭了”。
如果撕掉新闻赋予她的标签“田埂上的诗人”,离她本人更近一些,会发现,比起“诗人”,韩仕梅更像一个渴望幸福的普通女人。她有一定的语言天赋,但她的生活离文学很远。2021年,她没有读完一本书。别人寄来很多书,她只偶尔翻翻。“看多了,我都心里发急。”从北京回来后一个月,她想要翻书看看,发现眼镜找不着了。
诗歌是她苦闷生活的一个出口。她曾说如果能上大学,她想做老师,同时可以写诗。如果能上大学,“有本事,有才华,有才能,我可以把弟弟姐姐嫂子们都带富裕。他们对我都挺好。让儿子女儿过得开心快乐”。她的痛苦是具体的,她想上大学,和一个互相体贴的人结婚,过得幸福,不受苦。
二
韩仕梅让很多年轻人想到自己上一辈的女性,那些被迫辍了学、嫁错了人,为家庭操劳了半辈子,没出过远门的普通女人。年轻律师庄金龙愿意为她免费打离婚官司,因为觉得她和自己的母亲很像。有网友说:“看到她,就像看到我的妈妈……她们被绑在那个家庭里,被绑在老公身边,后来又把自己绑在孩子身边。”
韩仕梅的一位诗友,一位生活在河北的农妇,在接受了几次媒体采访后,把自己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作品都设置成私密,还改了名。12月,她拒绝了一位记者的采访并说:“此后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只想平平淡淡生活。”“从昨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心里很矛盾,现在我想通了,余生平淡为好。”“一个50岁的农民,相夫教子,脚踏实地地过日子比啥都强。”她没有解释心里的“矛盾”是什么,只是客气地说着:“谢谢你看得起阿姨!”韩仕梅说,自己的村子里,没有人和她是一样的,“有的也不快乐,但她们还会守住,她们思想比较守旧,受传统观念束缚,但是我不想被这个东西再压迫着了”。
这一年,因为怕韩仕梅“跑了”,丈夫王中明在改变。他开始做早饭,洗衣服。但也看她更紧。在韩仕梅说要离婚的时候,他没有发怒,只是沉默地抽烟,说:“这不是说笑吗?前面多苦的日子都过了,现在的日子不比别人的差。”韩仕梅则说:“好过了才离呢。”在媒体以往的采访中,面对离婚这件事,丈夫重复说着:“农村人都理解这个事,农村的不容易。”韩仕梅也知道,“农村离个婚挺难的”。
12月7日,她在朋友圈转发了自己半年前的一条动态。其中她写道:“我也想像玫瑰一样绽放/可惜已枯萎在那条小河上/我也想像清晨的朝阳/纵上苍穹,光芒万丈/每天都过着重复的日子/田埂、工厂,洗衣做饭,收拾屋子。”
韩仕梅想要的不过是幸福。在成为新闻人物这一年,她想得更多了,也“回不去了”。她知道眼前或许会有陷阱,但她曾说:“那我也不后悔,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有人骗我,我至少为了自己的幸福努力过。”
(摘自《中国青年报》郭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