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实践形式研究的可能性
□吕微

内容(质料)和形式,是五四学者经常使用的一对概念。本文中,笔者依据“质料”和“形式”以及“理论(实证)”和“实践”这些对立的范畴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分析五四民间文学草创时代的学术实践。
胡适在比较自己与周作人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时说过,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指明了新文学运动的内容,而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则是举起了新文学形式革命的大旗。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简单说来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学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
胡适所谓“工具”就是“形式”的意思。胡适说:“我最初提出的‘八事’,和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都是顾到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不曾把内容和形式分开……但我们在国外讨论的结果,早已使我认清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对于胡适来说,白话文只是新文学这一“作战”的工具形式,而且,胡适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新文学运动不仅是学术的认识而更是一场“作战”,即新文化的实践。因此,在谈到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时,胡适指出: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说来极平常,却是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他要用这一个观念来排斥中国一切‘非人的文学’”。
在胡适这里,学问给出的形式概念“白话”和内容命题“人的文学”也就是实践(作战)的形式和内容,对于胡适来说,学术和实践是不分的,胡适《白话文学史》的“白话”就是用于认识的学术概念。但胡适倾向于认为,对于新文学运动来说,白话形式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原因在于,旧的古文形式固然也可以表达“人的文学”内容,也只能是少数人所掌握的文学形式,古文形式不能为多数人所掌握,所以文学要成为多数人表达“人的文学”内容即主体的文学实践形式,就必须诉诸白话,白话形式反而成为制约民众主体的文学实践的“瓶颈”,相对于文学内容来说,白话形式更能直接说明民众的主体地位。后来,胡适的这一思想为郑振铎所继承,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主要讲的就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中心的俗文学的各种体裁形式(“型式”)——“文体”,以为民众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证明。1950 年代,郑振铎的学术思想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这并非指鹿为马,只是误解了郑振铎,郑振铎的形式恰恰是关于民众主体性的存在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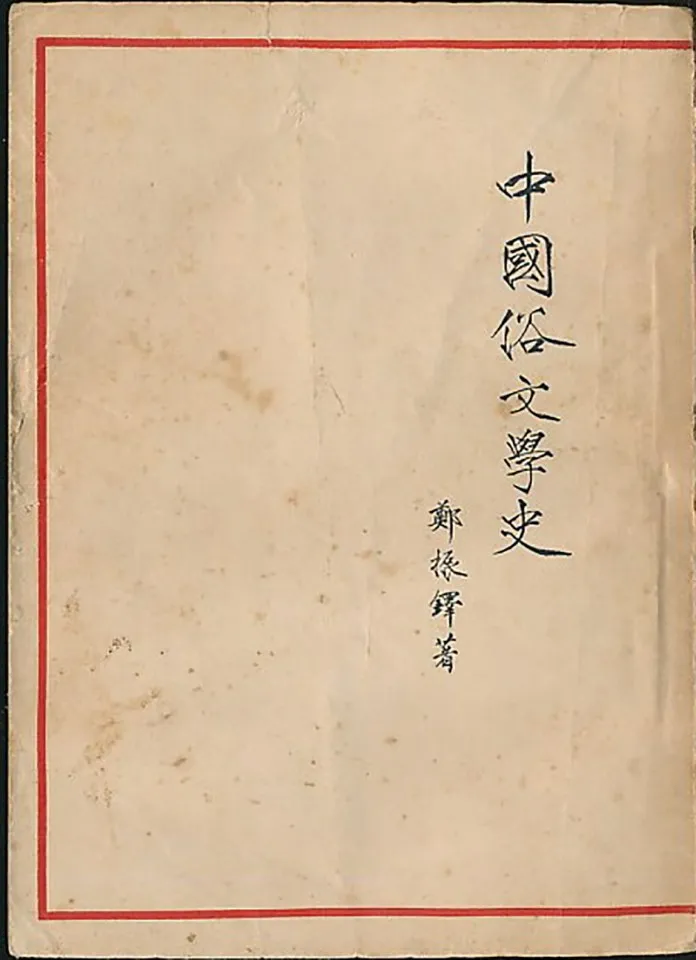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 年出版,作家出版社1953年根据初版纸型重印
胡适认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是关于文学内容的命题,当然是不错的,“人的文学”与“活(白话)的文学”构成新文学实践的内容与形式的两极,而且对于胡适来说,对文学现象的理论认识与他所主张的文学实践是分不开的。但是,胡适所主张的白话形式,对于新文学的实践来说还只是一种外在的实践形式,就像黑格尔所说的书籍的印刷形式相对于书本内在的论理、叙事和抒情形式来说是外在形式一样。比较而言,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内容的主张,不仅仅是单纯内容的,看似平实、平常,但从纯粹实践的立场看却并不那么简单,其内容设定本身就是有形式的,即实践的形式,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内容命题是“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内”的内容,即由实践形式所给出的实践内容。那么,何谓文学实践的内在形式呢?
周作人主张,“人的文学”之所谓“人”有两重意思:第一,从动物进化的;第二,从动物进化的,前者重点在“动物”二字,后者重点在“进化”。根据这一主张,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命题包括一系列对立的范畴:外面的——内面的;肉体的——灵魂的;兽性的——神性的;本能的——理性的;利己的——利他的;个人的——人类的;实在的——理想的。总之,周作人主张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的文学”。即人的感性的一面和理性的一面都要照顾到的文学,但“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而人的道德之本却在于“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这个“全然出于自由意志”在康德看来就是人的道德实践的完全摒弃感性(动物本能)依赖的纯粹理性的实践形式。所以对周作人来说,虽然他也承认人的动物性存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对人的道德性的存在设定更具有本质的意义。
康德把人的实践形式分为两种:一般理性的实践形式,以理性为手段(工具)而服务于感性目的的实践形式;纯粹理性的实践形式,以理性为手段的同时也以理性自身为目的,即绝对独立于感性目的而由理性自己给出纯粹理性目的(质料)“绝对的善”的客体对象的实践形式。相对于胡适、郑振铎所说的文学实践的白话形式(语言形式)和俗文学形式(文体),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的主张就在文学实践的外在形式之外,更深刻地提供了实践精神的内在形式——纯粹实践理性的绝对自由形式,“人的文学”就是由这种形式所直接给出的实践内容——道德的即善的文学实践的质料对象,恰如黑格尔所言,由实践的自由形式所直接给出的自由的实践内容。
“人的文学”固然是文学的内容(质料),但却不是由白话形式所给出的,周作人始终强调,“人的文学”或者说“平民的文学”的精神性就在于全然是由人的纯粹理性的道德实践的自由形式所给出的“先天所与的客体”。所以周作人不同意仅仅用文学外在的语体形式或文体形式——古文、白话或雅文学、俗文学来划分文学的“精神的区别”,他说,“文学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区别”,意思是说,文学的外在形式不是文学的内在形式,文学的精神区别是由文学的内在形式即文学实践的自由(或不自由的)形式所规定的。在周作人看来,真正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其实是一种由文学的自由实践形式先天给出或设定的文学的理想内容或理想的文学内容,因此,“人的文学”或“平民的文学”作为一种先天可能性,是无论其在经验中是否已经存在甚至从来都不存在也都可能存在的“应该”(就像桌子床、本子书作为纯粹形式概念与作为实物而实质地存在的桌子床、本子书了无干系一样)。周作人的想法显然与胡适在历史中发现白话文学的经验思路不可同日而语,胡适总是希望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现白话文学最早的经验源头,以作为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合理性的经验证明,但是对于周作人来说,“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并不需要一个历史或现实的经验证明,尽管周作人也讲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对于周作人来说,“人的文学”就好像康德所说的是由人自身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发生形式所给出或设定的纯粹先天的文学理想或文学信仰。
如果非要让周作人举出什么新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来源”,那只能让周作人“觉得为难”,勉强举例就只好举明末的公安、竟陵两个文学派别了。但周作人又会马上强调,他与这两派的意见“根本上也不尽同,因为我所说的是文学(精神)上的主义或态度,他们所说的多是文体的问题”。公安派的主张可以用一句话代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看似与周作人关于“人的文学”的主张相似甚至相同,其实相去甚远。公安派的“性灵说”不尽是关于文体形式的主张,“性灵”与人的感性、感觉不能说没有丝毫关联。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的理想尽管也兼顾了人的感性欲求,即同时兼顾了人的“动物”的一面和人的“进化”的一面,但周作人把人的精神“进化”的一面先于人的“动物”欲望的一面予以安置,其“全然出于自由意志”的文学实践的自由形式就更接近康德所说的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发生(决定)形式。汪晖写道:“事实上,像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仍然相当完备地表述了古典的‘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良有以也。
站在人的主观自由意志的态度而不是客观自然规律的立场审视中国文学的历史,即使周作人在中国历史上发现了与五四新文学精神相通的文学实践,那么这也只是“巧合”,但这同时也就是说,前者不是后者的“起源”,而是二者源于同一的自由的必然性。
站在古典人道主义的立场,周氏兄弟对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严酷的道德理性主义一直持有极严厉的批判态度,以为宋明理学的道德规定是非人性的,这从他们兄弟二人对“二十四孝”故事的极度反感即可领略,但这并不说明至少不说明周作人的文学理想不是道德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五四”的民间文学先驱者关于人的实践精神的“主义和态度”与宋明理学——心学对于人的道德实践的至高要求其实有着难以割舍的隐秘联系。
如果说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现代学术难以区分自身的经验认识功能和精神实践功能,胡适本人甚至有意混淆这两种功能;那么在周作人那里,五四民间文学运动的经验认识功能和精神实践功能之间的区分意识却是非常清楚,我们不妨再重温一遍据说是根据周作人的思想起草的《〈民俗〉周刊发刊词》: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对于周作人来说,民间文学的学术性(理性的理论运用)和文学性(理性的实践运用)是两个相辅相成的目的和概念,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的目的和概念是对民间文学的经验现象的感性直观和理性认识,但是作为文学的民间文学则是通过“当来的”(应该)尽管至今一直“隐藏着”的“民族的诗”所给出的先验理想的理智直观和理性实践。周作人关于民间文学本质的存在设定或存在信仰,不像胡适那样来自文学进化的历史规律,尽管周作人也说过“人的文学”是“从动物进化的”结果,但周作人关于民间文学的道德内容的存在设定却不是从历史经验中发展而来,而是出于人的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实践形式在逻辑上先于现实经验条件而可能(“隐藏”着历史和“当来”的理想)的自由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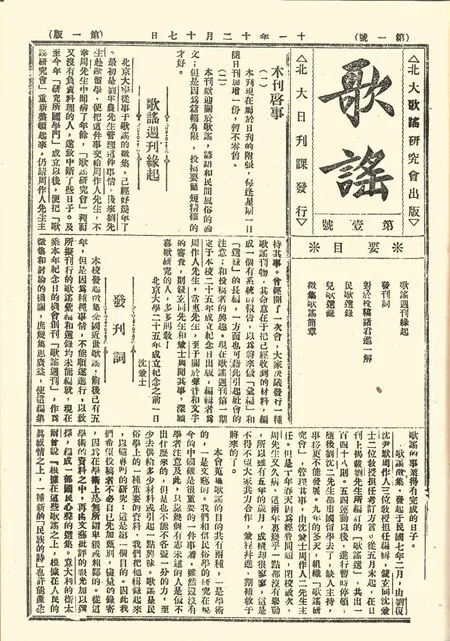
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发刊词”。《歌谣》(合订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 年影印
这样,在胡适那里,在感性直观的经验现象的意义上,白话文学就是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也就是白话文学,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为白话文学往往就是民间文学外在的语言形式,尽管这并不具有经验的普遍性,民间文学也可以采纳古文的形式。而对于周作人来说,经验的民间文学与“人的文学”的理想之间同样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周作人在一个更深刻的立场上讨论了民间文学的“人的文学”标准,这就是从民间文学的实践形式出发所给出的先天标准,民间文学只有在符合了人的纯粹理性意志的自由实践形式所给出的先天标准,才能够自诩是属于“隐藏”和“当来”的“人的文学”。
周作人通过“人的文学”的命题给民间文学树立了一个绝对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周作人承认,历史上的多数民间文学的作品内容都入不了“人的文学”的范围,周作人写道:“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而且这不是周作人一个人的想法,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家除了胡适、周作人,还有顾颉刚、郑振铎大都持有上述立场。那么,民间文学是否只有理论研究的意义而没有实践研究的价值,这是摆在五四民间文学家面前的一个纯粹的同时也是现实的理论问题,当然也是实践问题。而从这个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现实性出发,也许我们对周作人关于民间文学作为学术和作为文学的划分能有一种语境化的同情理解。
也就是说,除了纯粹学理的理由,笔者认为,在周作人那里,对学科目的、功能的划分还有一个特别现实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胡适无需考虑的。因为对于胡适来说,不仅民间文学与白话文学的重叠可以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据,更因为胡适仅仅关注文学外在语体和文体形式而不大关注文学内在的道德内容(尽管胡适强调自己并非不关注内容),当然更没有考虑过文学的内在形式,于是胡适也就不必考虑文学的学术性与文学的实践性这样的问题。而周作人更关注文学的道德内容并以此为路径,追问到文学实践的自由形式,以及文学实践的自由形式所给出的纯粹先天的实践客体——文学内容的质料对象,于是,在民间文学的叙事内容难以卒读的情况下,周作人主张将民间文学的学术认识与文学实践分而治之就是非常现实的考虑,这样,在对民间文学进行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学术研究的时候,至少可以把非道德的民间文学作品纳入研究的对象范围。
在纯粹求真而不是求善的学术目的下,将民间文学的“糟粕”即落后的内容纳入学术研究的对象范围,我想,是那个时代的学者所能够想象的将民间文学引进大雅之堂的最佳方案了。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家们在防止其他学科对本学科研究非道德的民间文学现象的指责时往往抬出科学研究做挡箭牌,在价值无涉、道德中立的学术研究的角度下,人们就没有理由阻止你研究民间文学,顾颉刚反问道:你要批判封建残余,你总得先科学地认识封建残余吧?当然这其实是一个“弱理由”,因为这是一个先行后退然后侧面迂回,而不是正面进取的“强纲领”。
将民间文学的主体实践作为客体现象纳入科学理性的理论认识的经验领域进行研究,是那个时代提升民众在社会上、文化上的存在地位的尽管是权宜的也是有效的办法,用胡适的话说,将民间文学现象纳入科学学术的对象范围是那个时代的先进分子“供给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几个根本见解”之一。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胡适、周作人一干先驱者为现代中国所提供的那“几个根本见解”,民众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至少在康德的“理论”意义上至今仍是无法想象的,但也正是因为仅仅在科学认识的理论意义上将民众的生活实践纳入经验——实证研究的理论研究而不是实践研究的视野,民众的主体性地位在当下中国仍然是一个多多少少停留在学者的客位他观理论中而不是已经成为民众的主位自观实践的问题,“让”民众能够通过学者学术的实践研究而在社会生活的文化实践中真正成为自由-理性的主体仍然是今天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需要解决的五四遗留。
学术从来不是价值无涉、道德中立的纯粹理论——经验的实证认识,即使是最纯粹的理论-经验的实证认识也具有实践的功能,无论你情愿不情愿,无论你意识不意识,你的纯粹学术都具有实践关切的效果,你的纯粹学术必然会现实地进入社会关怀的文化实践、政治实践并讲述一个自身就是实践关切或实践关怀的故事,尽管这个实践关切或关怀的故事是通过你的学术以理论——经验的实证认识的方式所讲述的。
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纯粹的学术研究必须自觉地把民间文学不是仅仅作为学术认识的理论研究、经验研究的客体对象,而是也要同时把民间文学视为民众主体的文化实践、生活实践,并通过对实践质料的研究回溯到对实践形式的研究。只有回溯到民间文学实践形式的研究,回溯到民间文学实践主体——民众的自由实践的形式意志,民众在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才不仅仅得到理论认识的经验性、偶然性质料的“弱证明”,而是得到实践认识的先天性、必然性自由实践形式的“强论证”,即康德所说的“先天的证明”。
一旦民间文学研究回溯到民众主体的文学实践的自由形式,现实的民间文学作品是否拥有道德的内容就不再是民众主体性地位的最终保证(1950 至1960 年代的学者们在民间文学中发现的“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精神”,该内容“保证”也仍然是质料性的因而仅具偶然性),于是,即使我们在现实的民间文学中不曾发现一例符合道德标准的作品内容,我们也不会据此就否认民间文学的实践主体对于自身道德的存在设定。周作人、顾颉刚、郑振铎对民间文学作品内容的道德失望可以因之而得到补正了。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古希腊人的那个古典命题,事物、事件、事情的本质不在于其质料而在于其形式,不仅认识的客体——存在物是如此,就是实践的主体——存在者亦是如此。主体的一般理性实践所给出的质料对象并不足以充分说明主体实践的自由本质,因为,主体实践经常要受制于自身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感性经验(比如欲望本能的内部感觉),但这并不说明主体根本就不具有道德实践的可能性,笔者已经引康德的“强论证”指出,道德实践并不因为不曾有现实性就因而不具有可能性。如果说,五四时代的民间文学先驱者们在民间文学作品的经验内容中发现了民众的主体性(尽管民众的主体性也经常被民间文学自身的内容所否定),那么五四先驱者给后来者留下的遗嘱就是:在民间文学的纯粹理性的实践形式中重新发现民众主体的自由存在。
这就是五四先驱者留给后来者的问题,即:民间文学是认识的客体还是主体的实践?先驱者们或者将这两个问题合二为一,如胡适,或者把这两个问题分而治之,如周作人。但是,都没能为后来者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学术之路,于是作为后来者的民间文学家们,或者用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政治的、文化的社会实践,或者把学术研究完全隔离于社会实践,学术研究如何能够在坚持学术的纯粹实践研究的同时亦与社会实践保持相关性,即无用之大用。这就需要我们把过去的视被研究的理论——经验认识的客体现象向主体实践的研究视野转换。在经过视野转换的情况下,作为主体实践的民间文学的自由形式及其实践法则而不是作为经验认识的客体对象就会呈现出来,当然这一学术转换的大方向早就经由我们的先驱者所指明,这就是周作人曾提出的民间文学的“全然出于自由意志”的实践形式。
在此我想特别提及的人是郑振铎,郑振铎的学术思想表面上是直接继承的胡适,他与胡适一样把民间文学的文体形式而不是文学内容视为下层民众的文化表达的主体证明,比周作人更甚的是,郑振铎认为俗文学的内容往往“不堪入目”,但是,如果俗文学的内容无法为俗文学——民间文学的价值做辩护,那么就只剩下俗文学——民间文学的文体形式了。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1938 年)几乎全书都是关于俗文学文体形式的论述,郑振铎就是通过对俗文学-民间文学文体形式的肯定而肯定了民众主体的文化创造力量,进而肯定了俗文学——民间文学的价值,也就是下层民众的存在价值。所以,尽管《中国俗文学史》被讥为一部资料大全,其实并不乏理论贡献,其贡献就在于尽管郑振铎接受的是胡适的文体论思路,所回答的却是周作人的民间文学——俗文学的价值论问题,进而民众的主体存在论问题。以下是郑振铎对俗文学的分类:
可以看到,郑振铎对俗文学的分类是中西古今大合璧,一级标题大体上以西方文学理论所规定的诗歌、小说、戏剧为依归,增加了他自己“杜撰”的“讲唱文学”的名目(这一“杜撰”具有作为概念性认识的理论化含量)。在一级分类下面比如“讲唱文学”之下的二级标题中,多列举俗文学体裁的本土命名,而这些本土命名都是民众自己对文学体裁的实践命名,在不同的实践体裁之间并不具有像“诗歌”“小说”“戏剧”和“讲唱文学”那样的“文体”概念的理论区分意义。但是对此,郑振铎似乎没有什么自觉意识,因为他坚持胡适的认识论思路,把俗文学体裁的实践形式的命名顺手拉来作为认识文学现象的概念形式,而没有意识到文学研究的认识形式——概念与民众对自身的文学实践形式的“实践的命名”之间的错位。
然而,尽管郑振铎没有关于俗文学的认识研究与实践研究相区分的意识,他企图将其前辈胡适与周作人乃至“五四”民间文学运动遗留的实践问题及其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尝试在一部《中国俗文学史》中一举解决,但也因此使其内在的矛盾以更尖锐的形式凸现出来,为我们今天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学术史和思想史资源,这就是:在民间文学体裁的实践形式中,蕴含着民众作为文化实践主体的自由形式意志。
据此,郑振铎通过划分俗文学与雅文学体裁的理论与概念形式,以确立民众的主体地位的企图和尝试虽然失败了——这是因为他始终把民间文学的文体形式“体裁”视为文学内容的表现形式亦即认识文学现象的概念形式,所以他对俗文学的体裁形式作为民众主体性证明的论证是没有实践研究的理论力量的——但是,也正是由于郑振铎的理论失败,为后来者转换对俗文学-民间文学体裁的理论解释为实践理解开启了新的思想维度:不是外在性的“文体”理论——概念形式,而是内在性的实践——理念形式——纯粹理性精神的自由发生形式——俗文学——民间文学的“体裁”中,蕴含着郑振铎们所希望发现的民众主体性的“强证明”。
这就是五四给我们留下的思想和学术遗产。对于五四留下的这份思想-学术遗产,我们不曾很好地消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没能够在胡适、周作人、郑振铎的立场上再前进一步,反而把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倒退为单纯的理论——经验的科学实证研究,而放弃了周作人所提示的民间文学的实践研究的可能性前景,特别是他提出的“全然出于自由意志”的民间文学的精神发生形式即自由实践形式的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可能性。
回顾三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历程,我们沿着五四先驱者所开辟的道路重新又走了一遍长征路,我们又经历了一遍对民间文学的质料性经验研究模式、纯粹形式化的经验研究模式,以及质料性的实践(生活)研究模式。现在,纯粹形式性的实践研究模式正在被提上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的议事日程。笔者相信,民间文学的纯粹实践的形式研究经过自我批判的理性检验已具备了初步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奠基于五四先驱者的深刻思想,更奠基于现代中国文化实践与学术研究的尖锐而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将民间文学的实践本质充分展现出来,能够见识及此真是中国学者的幸运!但这幸运却是以我们民族文化的现代经历为惨痛代价的,如果我们不能从我们的文化问题中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民族在近百年中因文化精神挫折所换来的教训就将彻底地付诸东流。
①在黑格尔使用中,“质料”和“内容”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两者间的区别,即在于质料虽说本身并非没有形式,但它的存在却表明了与形式不相干,反之,内容所以成为内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内。”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279 页,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2版。
②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载《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第244 页,中华书局1993 年,以下凡引该书仅注页码。
③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载《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44 页。
④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载《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58 页。
⑤“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2 页,商务印书馆1938 年,作家出版社1953 年重印。
⑥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278—279 页,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2 版。
⑦周作人《人的文学》,载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第13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以下凡引该书仅注页码。
⑧《人的文学》,载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第14 页。
⑨《实践理性批判》,第2 页,第63 页。
⑩《平民的文学》,载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第3 页。
⑪《平民的文学》,载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第4 页。
⑫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1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⑫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2 页。
⑭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23 页。
⑮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运动》,载《汪晖自选集》,第320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周作人原话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见周作人《人的文学》,载《艺术与生活》,第11 页。
⑯《人的文学》,载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第16 页;《二十四孝图》,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232 页以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
⑰“他(指周作人)对儒学经典的说教,尤其是对孝悌纲常的观念的批判,从不手软;但对于文学艺术等其他方面,他却显得比一般民间文学家保守得多。他认为,从总体上看,正统文化中大多僵死、错误的东西应该摒弃,但仍不乏正面的、积极的和有价值的成分。这种提法与他发表于1918 年的那篇《人的文学》著名论文中的人道主义文学主张密切相关,他是一直把自己的启蒙文学思想贯彻始终的。这种文学思想与儒学核心——仁学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洪长泰《到民间去——1928~1937 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第275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年。
⑱《〈歌谣〉周刊发刊词》,载《周作人民俗学论集》,第98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99 年。
⑲ 如何判断民间文学符合“全然出于自由意志”的“人的文学”的法则标准?根据康德的方法,判断的形式应该是这样的:“从大前提(道德原则)中的一般性的东西出发,经过包含在小前提里面的、把(作为善或恶的)可能的行为归属于那一般的东西之下的活动,继而进到结论,也就是主观的意志决定(对于实践上可能的善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准则的关切)。”《实践理性批判》,第98 页。
⑳《人的文学》,载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第13 页。
㉑ 参见顾潮、顾洪《顾颉刚与民俗学研究》,摘自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年,收入《顾颉刚民俗学论集》,第454 页以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年;以及吕微《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载《民间文化论坛》2004 年第4 期。
㉒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载《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41 页。
㉓《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432 页。
㉔ 俗文学的“第四个特质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她未经过学士大夫们的手触动,所以还保持其鲜妍的色彩,但也因为这,所以还是未经雕斫的东西,相当的粗鄙俗气。有的地方写得很深刻,但有的地方便不免粗糙,甚至不堪入目。……许多民间的习惯与传统的观念,往往是极顽强地粘附于其中,任怎样也洗刮不掉。所以,有的时候,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表示民众的保守性些。”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5—6 页。
㉕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6—13 页。
㉖“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