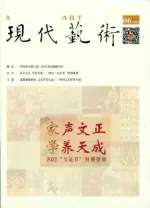语言是存在的家

《巴中民间语言》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对巴中民间语言进行了论述,言及了语言的神奇与魅力,论及了川东北方言与川西方言的异同,以及《巴中民间语言表现形式》,最有意思的是,里面还附有《巴山情歌里的方言词》,其中内含50首情歌。后面的《最巴中100句民間方言词》《最巴中100句民间俗语》《最巴中100句巴中歇后语》让人既忍俊不禁,又倍感亲切。下编为《巴中民间语言集成》,通过巴中民间的方言词、民间俗语、民谚、歇后语、谜语、顺口溜,完全可以体验到巴中民间语言的风貌和特色。
一
今年上半年刚收到阳云先生所著的《巴中风尚志》 《巴中山水志》两部新书,两部“大书”各30万言,我还在消化之中,他又发来了他与其夫人陈俊合著的《巴中民间语言》的定稿,并嘱我作序。
这三部厚重新著,是阳云、陈俊伉俪给故乡的献礼,体现了他们的文化情怀,我虽浅陋,倒也乐于从命。
多年来,夫妻二人笔耕不辍。他们对巴中的书写,可谓不遗余力。两人的文字都不是简单地辑纳,而是付出了自己的精力和才华,有自己的视角和看法。两人都是巴中文化的书写者,也是研究者和宣传者;既有对山川大地、民俗风情的歌唱,也有对人文和历史的梳理和解读。由此可见,夫妻两人对巴中这片土地都“爱得深沉”。他们所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巴中的人和事,都是巴中的历史文化、山川河流、草木动物。他们对家乡的热爱,从字里行间,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我就在想,一个人对故乡要有多么深沉的爱,才会倾注一生来做这件事?
我十七岁当兵入伍,在北方生活了二十二年,说句实在话,乡音还是有所改,自己听不出来,老家的人一听便知。我曾经想写故乡,但就是因为少年离家,对故乡了解不多,感受不深,所以提笔生怯。
阳云和陈俊传递给我的,无疑是“故乡消息”,无疑是一个纸上故乡。他们所书写的山水、历史、文化,是我所熟悉的,但又了解不深,大多流于传说。他们的文字,无论是对历史的书写,对山川河流的描摹,还是对笔下人物故事的叙述,都变得可信,使我对故乡的认识,有了“信任”的依凭。他们所写的山水风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都在呈现殊异之美,但会永存;而有些已存之数千年的东西——比如方言、风尚,却正在消失。这些都是值得书写和记录的,也有人在做,但很少有人像他们那么认真、彻底和扎实。
二
作家一生都在与语言战斗,想着怎么用语言尽可能准确地描绘这个世界,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是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对语言自然充满无限的敬意。
1880年11月,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3个月,他在给普希金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阿克萨科夫的信中写道:“我承认,作为朋友我向您承认,我有意明年出版《文人报》后,经常跪着久久祈祷上帝,愿上帝赐我一颗纯洁的心灵,赐给我纯正完美的语言,无邪无欲的语言,不惹众怒的语言。”
他已写完《卡拉马佐夫兄弟》,五十九岁了还在祈祷,“我经常痛苦地发现,我连二十分之一想表达,甚至也许能够表达的东西,都没有表达出来。拯救我的,是锲而不舍的希望,但愿上帝总有一天赐予我力量和灵感,让我更完整的表达,总之,让我全部表述我的心迹和想象。”
所以说,即使再伟大的作家,也不会认为自己找到并驾驭了语言。因此语言是神秘的。它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有自己的色彩、个性和样貌,同样的词句,不同的人说出来,会有不同的意味和韵致,相同的词句,不同的人写出的文章各有文采。除非录音重放,人间没有一段相同的话,除非抄袭,天下没有一篇相同的文章。给一堆同样的词语,有人能用它写出人间华章,有人却只能写出酸腐之文,即使一个人,因人生的阶段不同,用相同词句写出的文章也会不一样。
语言如人的基因,代表了他的出身、生活地域、家乡的地理位置,乃至人生境况、境界、学识,一个人的品质也多在其言谈中表现。
少小离家,乡音无改。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话都是倍感亲切的,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忘记自己的家乡话,就像一个人不能忘记自己的父母兄弟、故乡亲情一样。它是人之本,会像血液一样供养我们的生命,伴随我们一生。
文学其实是一种方言的呈现。方言按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是一方之言。就世界范围来说,每一个语种——英语、俄语、法语、德语、乌尔都语等都是一种方言,当然,汉语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而每一种语言又可细分为东西南北腔,山南海北调。
在文学创作中,方言自古就有运用。《诗经》中的《风》相对于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王畿”而言,就带有民歌色彩,是周的十五个诸侯国的土风民谣,传唱者也是多用各地方言歌唱的民间歌手,被视为《诗经》中最具文学精华的部分,故排在《雅》《颂》之前,后人将其与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并称“风骚”。在没有“普通话”之前,作家的作品也是用广义的“方言”创作的,《金瓶梅》用了大量山东方言,《西游记》中则有淮安土语,《儒林外史》用了安徽全椒话,《红楼梦》则使用了南京和北京两地的方言;而李劼人先生《死水微澜》对成都方言的娴熟运用,使其成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成熟的标志”。《尤利西斯》被著名翻译家肖乾先生叹为“天书”。乔伊斯就运用了拉丁语、古英语、中世纪英语、方言俚语和洋泾浜语,他将语码转换作为叙事策略,以用来显示人物身份,表现语言优越感,以改善人际关系和谈话气氛。到后来,文学正是在“普通话”的影响下,造成了“同质化”,失去了文学的鲜活度和多彩性,以致韩少功先生用方言写出《马桥词典》时,它带给人的,竟然是“先锋小说”的印象了。
阳云对此也有认识,他在该书中说:“早在宋代,释惠洪在《冷斋诗话》的文学评论中,就谈到了方言俗语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
他进而论及:“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其原因首先是方言自身的独特魅力,方言作为中国多元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表现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方言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它承载和记录着这方土地上的历史和原住居民的情感,充分体现了民间语言的凝练、生动和富于表现力。”
三
方言是一个族群的标志性特征,所以才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之说。
民间语言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闪烁着内涵丰富的文化光芒,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学等多种学问都包含其中。认知、考察、研究一个地方的文化,当从这个地方的语言说起。而民间语言以方言土语为承载,包含多种表达形式,如俗语、谚语、歇后语、谚语、顺口溜等。
阳云、陈俊伉俪对巴中民间语言的研究已有时日,陈俊多年前就曾赠送给我一部她著的《巴中方言土语》。阳云也有多篇论及巴中方言的文章——如《散谈巴山歇后语》《乡骂》《说话带把子》《川北人的方言普通话》等。两人都对民间语言形式进行过分析,探究过其特点,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巴中民间语言》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对巴中民间语言进行了论述,言及了语言的神奇与魅力,论及了川东北方言与川西方言的异同,以及《巴中民间语言表现形式》,最有意思的是,里面还附有《巴山情歌里的方言词》,其中内含50首情歌。后面的《最巴中100句民间方言词》《最巴中100句民间俗语》《最巴中100句巴中歇后语》让人既忍俊不禁,又倍感亲切。下编为《巴中民间语言集成》,通过巴中民间的方言词、民间俗语、民谚、歇后语、谜语、顺口溜,完全可以体验到巴中民间语言的风貌和特色。
可以说,《巴中民间语言》既是一部川东北民间语言辞典,也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入探究川东北民间语言的集大成之作。
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说过:“从一个国家的格言和谚语里,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才智和精神面貌。”那么,也可以这么说,从巴中的民间语言里,也可以看出巴中甚至川东北地区的才智和精神面貌。
民间语言最能体现一个地区对文化的认同,从而体现出一个地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但据媒体报道,2020年,全国的普通话普及率已达80.72%。就消除语言交际障碍,提升社會交际效能,负载知识和机遇而言,这无疑是好事;但随着普通话的普及,方言自然面临消失的危机。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如何保住民间语言这个“家”,已经作为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而阳云、陈俊伉俪合著的《巴中民间语言》,就是为了保留民间语言这个“家”做出的努力。因此,这部书在这个时候完成,无疑更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
卢一萍
巴中南江籍作家,曾任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副主任。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山》,小说集《银绳般的雪》《天堂湾》,长篇非虚构《八千湘女上天山》《祭奠阿里》《扶贫志》,随笔集《世界屋脊之书》等。曾获解放军文艺大奖、上海文学奖、天山文艺奖、四川文学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白山》被评为“亚洲周刊十大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