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芯片”被卡

小小一颗种子,正在成为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的焦点。
事实上,虽然种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却被忽视。
“从农业生产链条来看,过去重生产、轻育种的现象比较普遍。从利益链条分割来看,育种产业投入大、回收周期长、风险较高、收益不明确。因此,无论是种植户还是农业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短平快的生产环节,长此以往,产业高度集中于生产链条,种业却有所忽略。”东北农业大学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王刚毅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种业与粮食安全密不可分,是农业生产链条的初始源头和核心环节。
毫无疑问的是,重视种业已经刻不容缓。问题在于,种业“翻身仗”该怎么打?
种子被“卡”在哪里
种子进出口数据最为直接,也最有说服力。据中国种子协会官网公布的进出口数据,仅2021年1月1日至3月10日,种子进口记录共1493条,出口记录仅有9条。
据不完全统计,进口种子的作物包括蕹菜、胡萝卜、南瓜、甜瓜、西瓜、玉米、番茄、大葱、菜椒、黄瓜、莴苣、苦瓜、辣椒、青花菜、西葫芦、菠菜、空心菜、甜菜、茄子等至少数十种。用途主要是对外制种,试验、转让销售等。出口种子作物为稻和玉米,用途主要是大田生产。
从全年数据来看,2020年中国对外进口种子记录达10873条,出口种子记录为755条。出口与进口相比,所占比例不到十分之一。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曾在全国两会期间透露,种子在“有没有、保生存”这个问题上,立足国内是能够满足的。比如,水稻、小麦两种最基本的口粮,就完全用的是自主选育品种。
同时,在“好不好、高质量”方面存在差距。比如,玉米、大豆单产水平还比较低,不到世界先进水平的60%。蔬菜里的甜椒、耐储番茄等种子,从国外进口还比较多。
一位在黑龙江经营数十年种子的经销商向记者提到,小麦、水稻种子基本都是国产,蔬菜有一些就是进口的。进口种子价格一般比国内种子贵10倍左右,个别品种贵20倍左右,但品質好产量高。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所长杨天育表示,就小麦、水稻等大作物,以及我国特色小杂粮等作物来说,“卡脖子”是不存在的,“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是不成问题的”。
杨天育说,玉米和蔬菜,尤其是一些高品质蔬菜,国外种子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如果说是‘卡脖子,那应该是卡在这一部分。”
需指出的是,进口种子种类数量与作物播种面积无必然联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民院士曾提到,国内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水稻、小麦两种口粮作物品种已完全自给。
来自黑龙江桦南县的农民技术员孙斌,同时也是一家农业开发企业的负责人。在他看来,被“卡脖子”的作物主要是一些蔬菜、水果、大豆等,甚至还有一些畜禽。其中蔬菜最为明显。
北京一家饲料企业负责人表示,据其了解,猪、牛、羊等牲畜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卡脖子”的风险。
原始创新技术和理论不足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甚至可以说“种地”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天赋”,为什么却存在“卡脖子”的隐忧?其背后原因有哪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柴岩分析称,一是在研究方面,国外的研究投入、研究经费、研究力量比国内更为集中。国内的育种研究是分散到全国各单位。二是在技术攻关方面,攻关目标不够精准,而且力量较为分散,没有统一地联合作战,未能形成强大的科研合力。三是相关部门支持力度不够,政策没有连续性,有时候投入经费多,有时候投入少。
种子“卡脖子”背后还有许多深层次原因。柴岩提到,在农业科研领域,育种是基础性研究,几十年也未必能培育出惊天动地的品种。但如果科研人员能在知名期刊上发表一些文章,不仅可以很快评职称,而且还可以为所在学校或科研单位带来巨大效益。
柴岩还特别提到,对国内的种质资源缺乏保护也是重要原因。过去外国种业公司可以比较容易地收集国内的种质资源。种子“卡脖子”背后还有许多深层次原因。柴岩提到,在农业科研领域,育种是基础性研究,几十年也未必能培育出惊天动地的品种。但如果科研人员能在知名期刊上发表一些文章,不仅可以很快评职称,而且还可以为所在学校或科研单位带来巨大效益。
柴岩认为,对科研如何评价其实是有一种导向功能。所以许多专家更愿意去做高深的研究,去争相发表研究论文,而不能沉下心来搞育种研究。
此外,在国家层面,种子法还不够完善,许多作物品种尤其是杂粮,未能受到有效保护。比如绿豆、小豆、豌豆,大麦、燕麦等。有的甚至未能被审定、登记。
说起种子被“卡脖子”,大豆常被外界视为标志性作物。资料显示,多年来国内大豆产量为1500万吨左右,即使近两年增加了种植面积,但总产量仍不足2000万吨。
2020年国内大豆累计进口达10032.7万吨,首次突破1亿吨。据此前报道,国内大豆亩产平均约130公斤,与国外有较大差距。大豆依赖进口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
柴岩认为,大豆大规模进口并不是被“卡脖子”的原因。进口是市场行为,有需求就需要进口。但育种研究不能放弃,不仅是大豆、玉米以及杂粮作物,“甚至所有农作物的育种研究都应该得到重视”。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刘永忠研究育种多年。他也提到,大豆本起源于中国,而中国对大豆研究也有先天优势,但相关研究做得远远不够。
刘永忠解释称,种业是一个全流程的产业,至少涉及种源、鉴定、评价、扩增、改良、创新应用六个方面。前五个都是关键,而且也是创新应用的前提,前面做不好,后面创新也无法真正应用到农业实践中。
他提到,比如种源问题,要善于利用起源中心的种质资源。玉米起源于南美,就需要从南美引进资源进行研究。相反,大豆起源于中国,但国内对大豆的研究,并未充分利用起源地的优势。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孙连军表示,种子被“卡脖子”原因主要是原始创新性技术和理论不足。
他提到,以美国为代表的种业发达国家已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创新体系,企业投入研发动力足,投入资金大。而国内种业创新目前是以科研院所为主体,产、学、研链条结合存在一些薄弱节点。
守住种业基地“国家队”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曾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要建设好国家农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三大种质资源库,这是搞好种业创新的物质基础。同时也要抓好国家现代种业基地建设,目前已经形成了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基地。下一步,要继续提升基地建设水平,高质量打造国家南繁硅谷等种业基地,为农作物育种提供基础保障。
“杂交水稻的成功,一半功劳应该归功于南繁。”这里的南繁就是指海南国家级种业基地,号称中国种业“硅谷”。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种业基地并不仅是传统农业园区,更在努力成为高科技,集资源收集、繁殖保存、种质创新与供种分发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功能区。
为什么种业基地都分布在南方?据王刚毅解释,这主要因为气候原因。北方一年一季,种完这一季,收获之后再测量数据、收集数据再来这个周期很长,一年只能出一次试验。
“例如大豆,咱们国家的大豆种植主要是东北,但是大豆种质资源大多分布在云南、四川、重庆、贵州,这些基地就是做种质资源开发和保护的中心。可以把这些基地看作农业生产的缩影,实际生产的链条分工是怎样,在这个基地中就是怎样运转的。”
近几年,多地也在为南繁单位租地进行补贴。以四川省为例,2020年8月,根据《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规划(2015—2025年)》对于新增南繁科研用地,以省为单位“统一规划、统一拿地、统一建设、统一运行、统一管理”的要求,以及《南繁新增科研用地租地补贴方案》,2020年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四川省南繁单位在海南南繁科研用地租地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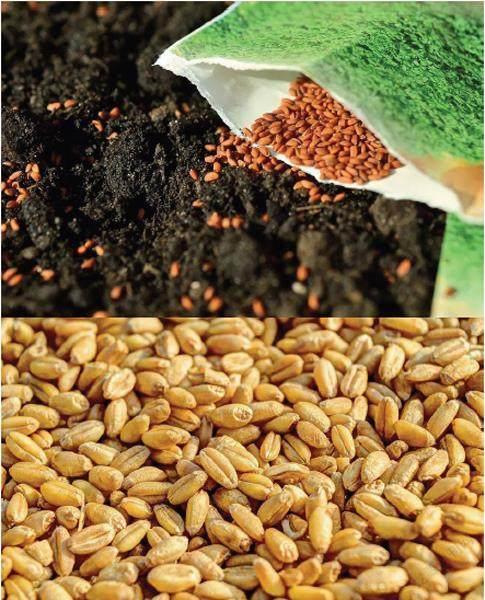
把種子交还给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国家级种业基地仍以教学科研用途为主,较少看到企业租地育种。当前,企业育种研发主要集中在自己的试验基地内部,整体规模较小。
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折射出企业在种子研发领域的“缺位”。长期以来,我国种业公司存在“小而散”的问题,企业研发投入受限,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企业数量有限。从经营规模上看,我国农作物种业企业前十强仅占国内市场15.8%的份额。
农业生产链条的重要发端,企业为何长期“淡出视野”?王刚毅认为,一个原因是种业天然具有周期长、回报慢的特性。此外,由于知识产权缺失导致的无序竞争,长期以来国家对种业企业的规制较为严厉。相比之下,国家更倾向于让公办公立的主体如高校和研究机构来承担种业创新工作,这也导致了企业研发投入越发不足,竞争力被削弱。
他进一步指出,虽然高校和种业企业接触十分频繁,但实际合作效果并不理想,二者并未实现良性互动。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高校与企业的需求出现错配。
“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主要目的是取得学术成果,往往对市场需求不熟悉、不了解,甚至没兴趣。而企业追求的是直接能转化成生产力,满足市场需求。纯学术转换成实际生产力,中间上线周期太长,短期很难见效,企业也等不及。”
也正因此,种业领域的分工关系亟待理顺。在王刚毅看来,事关国家安全战略的种质资源库开发、建设和维护,以及企业在市场上不能得到回报或短期之内很难见到成效的,应由科研院所和高校主导。对于其他商业化的领域,则应保证充分的市场化竞争程度,这也是保证种业创新生命力的基本前提。
“本质上还是需要制度机制的创新,让种业的市场化、法治化程度更高。剩下的就与其他的农业环节一样,把创新主体交给企业,把种子还给市场。”王刚毅说。
◎ 来源|综合南方农村报、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