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陀罗
齐剑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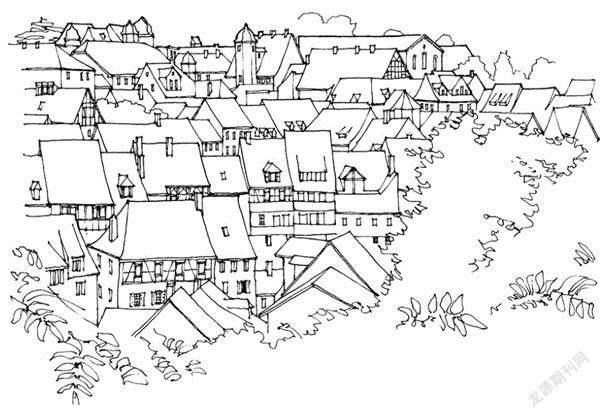
秋婶外出买菜时,在小区的绿地里看到了一株曼陀罗,她停下了脚步,俯身观察。不错,这就是一株曼陀罗,手掌大小的带刺的叶子,喇叭状的白色花朵。曼陀罗是学名,在秋婶的家乡,管这种植物叫作臭麻棵。秋婶的家乡在河北的东南方向,这里的人们喜欢将青枝绿叶的植物叫作某某棵,比如,苍耳叫苍子棵,青蒿叫蒿子棵,泽漆叫作害眼棵。秋婶自小就经常给猪羊拔青草,田野里的野菜都叫得出名字。她最怕的就是遇上曼陀罗,无意间砍断碰折,它就会发出强烈的臭味,这种臭味和厕所的臭味截然不同,是一种令人头疼欲呕、浑身难受的味道。传说曼陀罗能让人麻醉,秋婶故意将它喂给家里的山羊,年老狡猾的山羊决计不吃,有一只小山羊上当了,吃了几片曼陀罗的叶子,很快就四肢发麻,别的小羊上蹿下跳,它咩咩怪叫着,挪不动脚步,四蹄打战。
秋婶不敢过多逗留,急匆匆地拎着菜上楼。进到家里,女儿叶子正陪着外孙雷雷在沙发上玩积木,看到秋婶便埋怨,妈,怎么才回来啊?铁峰十二点下班,鱼还能炖熟吗?秋婶笑了笑,说,我马上就做,来得及。秋婶赶紧走进厨房,戴上围裙,取出一把干香菇泡水发着,这边就动手拾掇鱼。鲤鱼是她在菜市场亲手挑的活鱼,眼看着人家杀掉,刮了鱼鳞。秋婶嫌别人宰杀得不够干净,将鱼腹残留的内膜都择掉,鱼身也要再刮一遍,以免还有残存的鱼鳞。鲤鱼拾掇完了,清洗多遍,改刀,撒上盐。秋婶在老家的时候,做鱼都是过油炸一炸,放锅里抛上盐和葱花、姜片,炖熟了味道就挺好。但是来到这座大城市,照顾怀孕的叶子,在叶子的要求下,跟电视直播学着做。第一次炖鱼,叶子喝了一口就吐掉了,抱怨秋婶要改掉老家的饮食习惯,不能吃那么咸,吃咸了会使人血压升高。再一次炖鱼,秋婶几乎没放盐,按照电视指导用牛奶炖鱼,结果大受好评。女婿铁峰也不住夸赞,说秋婶比外边大酒店做得不差。秋婶美滋滋的,但那锅鱼汤却没喝几口,她觉得寡淡,喝不下去。液化气灶上小火炖着鱼,秋婶紧张地忙碌着,还要炒两道菜,香菇油菜,青红椒炒肉,顺便凉拌一根黄瓜。大小四口人,需要做四道菜。大城市里生活就是讲究,顿顿饭都要有炒菜,不像村里面,不愿意炒菜,捞块咸菜疙瘩,切成薄片,就能下饭。
将饭菜都摆上餐桌,秋婶忙得一脑袋汗。叶子带着雷雷坐下,铁峰也回家了。秋婶到卫生间擦了把汗,洗了洗手,她喘匀乎了气儿,回到餐厅坐下。叶子说,妈,我得赶紧吃饭,主管发微信要去公司加班。秋婶说,那好,你赶快吃你的饭,雷雷和家里的事儿都别管了。叶子在一家私企工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铁峰希望叶子换一家公司,好腾出时间精力照顾雷雷。但是这家私企的工资和待遇还不错,叶子迟迟没有选择跳槽。叶子和铁峰很快地吃完了饭。铁峰说,叶子,我送你去上班。又朝秋婶客气地说,家里就辛苦你了,妈。秋婶笑笑,说,自家人,还客气个啥,你们都走吧!叶子麻利地换了衣服,和铁峰下楼。秋婶望着满桌子的菜,苦笑着摇头。两个炒菜吃了一些,凉拌黄瓜没动,家常炖鲤鱼,两人只是喝了两勺汤。她和雷雷就是把肚皮吃破了,也吃不完这些菜。秋婶又盛了碗米饭,铆足了劲儿,想把俩炒菜都吃掉。雷雷喜欢吃鱼,指着大碗说,吃鱼,吃鱼。秋婶放下饭碗,夹起鱼肉,把刺儿仔细剔掉,再放到雷雷的碗里。雷雷很爱吃饭,他长得很快,身上还肉乎乎的。秋婶打心眼里喜欢这孩子,她亲眼看着孩子出生、长大、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现在呢,会叫姥姥,会说一般的对话了。雷雷的每一点成长都让秋婶欣喜不已。
秋婶到这里来看孩子,心里是有牵挂的,她牵挂着老伴秋叔。秋婶原本没有工作,在家侍弄几亩田地。秋叔在乡镇税务所上班,总是骑着自行车下乡收税,过午才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后来秋叔调到了县城,在县城买了房子,秋婶也跟着进城了,秋叔给她找了个打扫卫生的活儿,闺女叶子也转到县城来读书。时间过得很快,叶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就在北京找了工作。秋婶来给女儿伺候月子,又照看孩子,秋叔在家成了孤家寡人。有时候秋叔也会来北京待几天,家里住的是三居室,这里却是个七十多平方米的两室,秋叔住着嫌憋闷,出门转转,也遇不到熟悉的人,他在家和朋友同事三天两头聚会喝酒,根本不愿意到这里来。遇上叶子放假了,秋婶才能坐火车回老家,邻居郑嫂说她这是享受天伦之乐。秋婶苦笑着自嘲,说,什么天伦之乐啊,就是当老妈子。秋叔批评她,以后当人不要这么说,不就辛苦这两年嘛,等雷雷入了托就好了。秋婶神情忧郁,说,不知道我能不能扛过这几年。秋叔恼火地说,瞎说,再累还比得过在村里干活累?
雷雷四岁了,很快就可以入托了。秋婶暗暗高兴,她解放的日子就快来了。郑嫂她们天天打麻将、跳广场舞,秋婶不喜欢打麻将,准备去学广场舞,一大群上了年纪的熟人们,跳啊笑啊,既愉悦心情,又锻炼身体。伺候雷雷吃完了饭,送他到客厅看电视,秋婶急忙把碗里的饭扒到嘴里,又是一阵忙碌,才将厨房拾掇利索。她坐到沙发上,长出了一口气。雷雷最喜欢看《爆笑虫子》,秋婶也喜欢看,她看着看着,就酣然入梦了。在梦里,她背着草筐,闯进了一大片曼陀罗丛,左冲右突,摆脱不了围困,她大叫着,滚一边儿去,臭麻子,我最讨厌你了!挥舞镰刀,痛下杀手,曼陀罗被砍得枝叶横飞、骨断筋折。就在秋婶感觉痛快之时,却听到了碎裂声和尖叫声。秋婶睁开眼睛,发现雷雷摔倒在地,号啕大哭,手上鲜血淋漓。秋婶大惊,发现她手边茶几上的一只茶杯被打碎了,地上洒着水渍和玻璃碎片。秋婶明白,是自己睡梦当中打飞了茶杯,导致雷雷受了伤。雷雷的手腕被玻璃割破,鲜血不停地朝外冒。秋婶慌忙撕下一条沙发巾,缠到伤口上,鲜血慢慢将沙发巾染红了。雷雷不满意地说:“姥姥坏,姥姥打雷雷。”秋婶尴尬地道歉:“雷雷,对不起,姥姥刚才睡着了。”雷雷还是不满意地说:“姥姥打雷雷。”秋婶说:“雷雷,姥姥不是故意打你的。”她将碎玻璃小心地扫干净,用墩布将血迹擦干净,又将雷雷的外衣衫脱下来,连同几个沙发垫都丢进洗衣机,洗干净甩干,拎到阳台上晾晒。
晚上,秋婶在厨房忙着,有点忐忑不安。女婿铁峰回家了,发现了雷雷的伤势,问:“雷雷,怎么了?”雷雷回答:“姥姥打雷雷。”铁峰说:“雷雷,别瞎说!”秋婶急忙走出厨房解释:“铁峰啊,我不是故意的。”铁峰抱住雷雷,心疼地观察着,说:“妈,没事儿,看孩子哪有不磕着碰着的,可是,这么处理伤口怕会感染。”防盗门打开了,叶子进来一眼就看到雷雷的伤,惊慌地问:“雷雷,怎么了?”雷雷的嘴巴快,说:“姥姥打雷雷。”叶子看看秋婶,脸色铁青地说:“妈,你怎么能打小孩子呢,看看还受了伤。”秋婶讷讷地说:“我不是故意的。”铁峰说:“雷雷的傷口需要重新处理,咱们到街道拐角的门诊去吧。”叶子皱着眉头说:“嗯,划伤了动脉可就不得了了。”两个人抱着雷雷出去。秋婶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句:“你们快回来啊,饭已经做好了。”
秋婶把天然气灶关闭了,颓然地坐到餐桌旁,胡思乱想着,雷雷这个孩子,见到爸妈就告状,什么姥姥打雷雷,姥姥真舍得打他吗?秋婶觉得冤得慌,琢磨着怎么跟叶子和铁峰解释。神思恍惚之间,听到客厅传来声音,叶子带着雷雷回来了。秋婶急忙又打着了炉灶,将炒了一半的菜继续炒熟。将饭菜准备好了,秋婶朝客厅里叫:“都来吃饭了!”
这顿饭吃得没滋没味,秋婶留神看看雷雷的手腕,布条被除掉了,换了雪白的纱布,缠得严严实实。秋婶问:“大夫说什么了,没什么事儿吧?”叶子阴阳怪气地说:“没什么事儿,大夫说再割深一点,这只手怕是废了。”秋婶脑袋有点大,苦笑说:“有这么严重吗?不要听大夫忽悠。”铁峰认真地说:“妈,大夫不是忽悠,以后你可要留神一点儿。”秋婶笑了笑说:“好的,我以后拿他当小祖宗供着。”秋婶没留神蹦出这么一句话,说完了非常后悔。叶子和铁峰都很尴尬,被噎得说不出话。秋婶急忙补充说:“我以后会留神的。”
这件事以后,秋婶和女儿女婿之间产生了隔阂,觉得雷雷不那么可亲了。这么点儿的孩子会告状,一天十几小时伺候,还是和爸妈最亲近。秋婶处处小心地照顾雷雷,唯恐再出什么差池,她做饭却是越来越心不在焉。淘完米装进电饭锅,却忘记了按下按钮;切好了肉片,炒熟了菜,肉片还搁在案板上未动;再就是煮汤的时候,总觉得没有放盐,放了一勺盐,再放一勺,汤齁得难以下咽。叶子问:“妈,你是不是有点小脑萎缩啊?”秋婶说:“也许吧。”铁峰要带秋婶去医院检查,秋婶坚决不去,说:“我哪都不疼,哪都不痒,我以后多留心点就行了。”
雷雷终于入托,中午在学校里吃饭,早晚由铁峰开车接送。秋婶的压力陡然减轻,外出买菜,可以和楼下的老太太们闲聊几句,心情愉快了很多。一天晚饭后,大家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叶子问雷雷:“雷雷,今儿在学校学的什么啊?”雷雷举起手说:“老师让观察手掌,说我们有五根指头。”雷雷手腕的伤痊愈了,留下一道淡淡的疤痕。叶子笑着抓过雷雷的手掌:“雷雷,老师没教你们数数啊?”雷雷摇头说:“没有。”叶子掰着雷雷的手指说:“很快会教你数数的,来,一二三四五——”雷雷跟着叶子数了数,忽然想起什么,问:“妈妈,你说什么是脑残?”叶子说:“脑残啊,就是人傻,脑子不好使。”雷雷说:“我明白了,姥姥是脑残!”铁峰急忙训斥:“瞎说什么,姥姥不是脑残。”雷雷又说:“那为什么姥姥总是办糊涂事啊?”叶子说:“姥姥岁数大了,有点糊涂,但不是脑残。”秋婶窘得脸通红,讪讪地说:“雷雷,姥姥是脑残,你说得不错。”
过了中秋,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夜间敞着窗户,房间内会很冷。秋婶睡前就不再淋浴,洗洗脸、洗洗脚就上床了。叶子和铁峰还是每天晚上都要洗澡。叶子提醒秋婶:“妈,你隔一天洗一次澡吧。”秋婶摇头说:“天凉了,不出汗了,没必要洗澡了。”秋婶在老家也算是干净利索的人,来到大城市里,就和女儿不合拍了。几天后吃晚饭,女婿进了厨房就问:“有一股味道,怪怪的。”叶子朝秋婶身上瞄了一眼,没有说话。雷雷说:“姥姥臭臭!”秋婶窘得脸红脖子粗,说:“吃完饭我就去洗澡。”叶子说:“妈,从村里带来的毛病,还是要改掉啊。”秋婶心里嘀咕,我哪里是村里的,在县城也待了十几年呢,还是苦笑着说:“好的,闺女,我改。”
叶子突然干哕起来,跑进洗手间呕吐,铁峰赶去捶背,秋婶也端了杯凉白开,让叶子漱口,歉意地说:“瞧瞧,都是让我闹的。”铁峰笑了笑,说:“妈,不关你事儿。”叶子不好意思地说:“妈,我可能又怀孕了,闻到蒜味儿就想吐。”秋婶做的一道菜就是蒜蓉娃娃菜,原本叶子很喜欢吃的。秋婶搔了搔头,问:“现在放开二胎了,这个孩子,你们要不要呢?”铁峰说:“我们还没商量好。”
当天夜里,秋婶突然失眠了,叶子又怀了二胎,秋婶感觉到了压力,胡思乱想、翻来覆去,临近黎明才入睡。梦里,秋婶又闯进了一片曼陀罗地,她想摆脱这些野草的纠缠,但是曼陀罗丛无边无际,累得虚脱都没能走出去。叶子在叫,妈,你还在睡觉吗?秋婶惊慌地爬起来,发现天已大亮,叶子站在门口,诧异地望着她。秋婶每天都醒得很早,起床后准备早餐,从未耽搁,今天却起晚了。秋婶慌忙穿衣,尴尬地说,我睡过了头,马上给你们做饭。叶子淡淡地说,不用了,等你做熟了,上班就迟到了,我们马上出发了。秋婶歉意地说,让你们饿着肚子不合适啊。叶子说,没事儿,同事大多不吃早餐。秋婶说,给雷雷拿点饼干吧。
女儿、女婿和雷雷都走掉了,秋婶又是轻松,又是空虚,仄歪在沙发上想,一个人在家,早餐还做不做呢?这时,肚子很不争气地咕噜起来。秋婶知道自己消化功能很好,人上了岁数,能吃能喝是好汉。她走进厨房煮了一碗面,一边吃着,一边想起秋叔来了。昨天出去买菜,听楼下人们议论,有个老太外出看孩子,老头自个儿在家,夜里犯了心脏病,过了两三天才被邻居发现,人已经死翘翘了。秋婶放下筷子,赶紧去给秋叔打电话。电话半晌也没接通,秋婶心跳加快了,她想,不能这么巧合吧,老头子也会死在家里没人知晓?又打了两次,电话接通了。秋叔在那边问,什么事儿啊?秋婶说,我还以为你犯心脏病了呢?秋叔不满意地说,我身体好着呢,昨天刚做了体检,什么毛病没有。秋婶说,你还是在意一点儿,把酒戒了吧。秋叔说,你在北京,管得了老家的事儿?我喝了酒说没喝你也不知道。秋婶说,你喝了酒,我隔着电话就能闻到你的酒气。秋叔笑了,说,你这么能耐,你闻闻我嘴巴里有没有酒气?秋婶说,别瞎扯了,我这是提醒你要注意身体。秋叔不耐烦地说,行了,没别的事儿,挂了,女人就是麻烦。秋婶突然说,我想回老家。秋叔说,你回老家了,雷雷谁照应呢?秋婶说,雷雷上幼儿园了,不需要我了。秋叔说,那你和叶子商量,他们让你回来,你就回来。秋婶又回到厨房,看看剩下的面条,犹豫了一下,端起倒进了垃圾桶。
叶子听到秋婶要回老家的想法,沉吟了一下,说,好的,妈,你回家歇歇吧,在这里待得很累了。秋婶吞吞吐吐地问,叶子,这个二胎要不要?叶子说,铁峰和他爸妈商议了,想要。秋婶说,这个二胎,我怕不能给你帮忙了,我身体最近不大好。叶子笑了,说,妈,这个你不要牵挂了,现在家政服务业很发达,我们会雇一个保姆。秋婶歉意地说,叶子,不是你妈偷懒,是你妈有点力不从心。叶子说,妈,看你这话说的,咱們娘儿俩谁和谁啊,你伺候我和雷雷付出这么多,我和铁峰都记着呢。秋婶忙说,叶子,伺候你们是我应该的,我回家待一段儿,可以再回来。叶子笑,妈,你回家吧,别操心我们了,多陪陪我爸。
秋婶回家了,她是坐普通火车回家的,叶子想让她坐高铁,她执意不肯,因为高铁站到她们家,还有五十分钟的车程,必须得打出租车,坐普通火车呢,能直达她们的县城,只是到站稍晚一点。秋婶出了车站,已经过了夜间十二点,她溜溜达达,十分钟之后,就走进了自家小区。秋婶心里还嘀咕着,没提前打电话,不知死老头子回家没有。秋婶抬头望了望自家的窗口,发现没有亮着灯光。秋婶愤愤地想,这个老头子,怕是还在外边喝酒呢,一天就是喝酒喝酒,早晚喝死拉倒。秋婶从背包里摸出钥匙,顺着楼梯拾级而上。
秋婶打开了防盗门,将客厅的灯打开,屋内果然和她想的一样,乱七八糟,一片狼藉。秋婶放下背包,立即动手收拾,一边低声地咒骂着,这个秋叔啊,就是一头猪。她刚刚拾掇了几分钟,卧室内走出一个浓妆艳抹、头发蓬乱的女人,朝着秋婶展颜一笑,说,你回来了?秋婶愣住了,等那女人摘下衣架上的包,挎到肩上走出去了,才回过味儿来。她冲进卧室,嚷着,秋叔,你个杀千刀的!秋叔伸着四肢,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发出了一阵强似一阵的鼾声。秋婶朝秋叔胸脯乱拍乱打,你个杀千刀的,还有脸睡觉!秋叔迷迷糊糊地醒来,瞥了一眼秋婶说,你回来了。翻过身想继续睡觉。秋婶抱住秋叔的腿使劲儿拉拽,嚷,你还有脸睡觉!秋叔的火被挑上来,随便地踹了一脚,把秋婶踹倒在地。秋婶放声大哭,一边数落,你这个杀千刀啊,我不在家,你就找小三啊!秋叔坐起来看看秋婶,搞明白是老伴儿从北京回来了,慌忙穿上裤头,过去搀扶秋婶,说,老伴儿啊,我没找小三,你误会了。秋婶恼怒地将秋叔的胳膊推开,骂着,你以为我眼瞎啊?刚才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秋叔尴尬地解释,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秋叔将秋婶搀扶起来,坐到椅子上。秋婶质问着,不是找小三儿,是怎么回事?秋叔尴尬地说,嗨,男人嘛,需要发泄嘛。秋婶觉得湿腻腻的,站起来一瞅,椅子上扔着一只用过的避孕套。秋婶指着秋叔骂,你真恶心,你不是人!她跑进了洗手间,反复地用肥皂洗手。秋叔垂头丧气,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坐在沙发上抽烟。
早晨,秋婶还躺在床上,就听到秋叔起来洗漱,她想起來给秋叔做饭,坐起来又赌气躺下。秋叔推门外出,过了半晌回来,走进秋婶的房间,嬉皮笑脸地说,老伴儿啊,给你买肉夹馍来了,快出来吃吧!秋婶没好气地说,不吃!秋叔摸摸秋婶的额头,说,你没发烧,身体好好的,走吧,咱们一块去吃早餐吧。秋婶恼火地说,说不吃就不吃,看到你就生气,你滚!秋叔笑嘻嘻地将秋婶拽起来,架出了房间,说,咱们老夫老妻的,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啊,吃饭!秋婶没吃肉夹馍,喝了几口稀饭,郑重地说,你以后还找不找小姐?秋叔抓过秋婶的手抚摸着,说,老婆,我保证再也不找小姐了,就找你一个人!秋婶将秋叔的手甩开,呸了一声,道,你别找我,恶心!
吃完了饭,秋婶翻出秋叔的脏衣服,又把床单窗帘都卸下来,轰隆轰隆地开动了洗衣机。秋叔企图帮忙,在秋婶身边转来转去。秋婶骂着,滚,碍手碍脚的。秋叔嘿嘿一笑,说,你嫌我碍事,我出去转转,找他们下下象棋。说完就开溜了。秋婶卖力地干活,排解心里的烦躁,衣服床单洗完晾到阳台上,又将各房间仔细擦洗了遍,又打开冰箱,将里面腐烂过期的都丢掉,清洗一遍,这才下楼外出购物。
秋婶胡思乱想着,走出了小区,走进了附近的菜市场。她买了肉蛋蔬菜,拎着大包小包地转回家,刚走上小广场,就听到有人叫她。秋婶回头一看,原来是夏大婶。夏大婶又白又胖,额头微微出汗,两手也拎着蔬菜鱼肉,笑着说,看背影像你,什么时候回家的啊?夏大婶的男人老夏和秋叔是同事,比秋叔小两岁。他们原来住在税务局家属院时是邻居,门紧挨着门,关系不错,搬到现在的小区后,不做邻居了,还是常见面。秋婶急忙说,夏嫂啊,我昨天回来的,你这多半年挺好的吧?夏大婶说,我啊,没病没灾,吃得饱睡得着,挺好的,你的气色不太好,是不是看孩子累的啊?秋婶急忙掩饰,说,不累不累,俺家的外孙入托了,我很轻松!夏大婶点头,嗯,孩子入托就轻松了,这次回家能待多久啊?秋婶说,我不想回去了,孩子大了,不需要我看了。夏大婶笑着说,对啊,你这算是解放了,回家好好地享受自己的生活吧。对了,晚上你可以到广场上来,我教给你跳广场舞!秋婶说,行,晚上我来看看。
中午秋婶烙的韭菜肉馅饸子,秋叔吃得痛快淋漓,连连夸赞。秋婶也不拿正眼看秋叔。秋叔说,你去给咱闺女看孩子,我可就惨了,成了一个老光棍啊,衣服自己洗,吃喝自己做,一个人吃饭没劲儿,能不找老朋友喝两盅吗?秋叔的几句话说进了秋婶心里,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嘛,两口子就要做个伴儿。秋婶说,叶子又怀孕了,她们想要这个孩子。秋叔一怔,说,要了二胎啊,你还得去伺候啊?你这个老妈子还要当,我这个老光棍还要打啊?秋婶白了秋叔一眼,说,胡扯什么呢!叶子说了,不让我管了,他们雇保姆看孩子。秋叔咋了咋舌头,说,大城市雇保姆,工资可是高得很呢。秋婶说,反正我不能再去了,再去我非得病了不可。秋叔打量着秋婶,说,你脸色是不太好,明天我带你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秋婶叹口气,道,我不用检查,我身体没病,就是心里不大好。秋叔突然笑起来,说,老婆,我知道,你最需要的是我的爱!秋婶气得差点鼻子歪了,骂着,你就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晚上,秋婶如约到广场上来找夏大婶。热闹的广场舞火爆进行着,夏大婶站在最前排领舞,动作优美,驾轻就熟。夏大婶看到了她,大声招呼,秋嫂啊,你站到后排跟着学吧!秋婶勉强笑了笑,摇头说,我不会跳,我来看看就行。夏大婶自顾自地跳舞,顾不上再和秋婶说话。跳舞的队伍约有两三百号人,缓慢地朝前面行进着,队尾的人都是初学乍练,动作僵硬,跟不上节奏。秋婶没去看孩子的时候,也天天泡在广场舞的人堆里,听到音乐身上就跟打了鸡血一样,跳一大晚上也不觉累。几年过去了,舞蹈风格变化了很多,秋婶也找不到感觉了,干脆就不想下场活动。
秋婶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溜到了广场的一侧,在灯影里寻到一条长椅,坐了下来。她感觉对什么都失去了热情、什么都没意思。忽然之间,她嗅到一股熟悉的臭味儿,警惕地站了起来,朝身边的灌木丛望去,果不其然,在成片的女贞丛中,她发现了一株曼陀罗,手掌大小的带刺的叶子,白色的喇叭状的花,还有核桃大小的果实。这些枝叶花果统统散发着强烈的气味儿,让秋婶一阵一阵地晕眩。秋婶忽然明白,曼陀罗之所以这么臭,就是不愿意有人接近它,它已经习惯了田野上的风吹雨淋,移植到别的环境就会格格不入,再回到田野上,也会不适应了。
责任编辑/董晓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