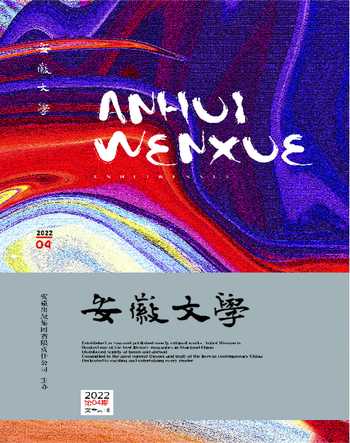无盐日子也有味(外一篇)
王张应
盐是重要物资,入列国家专管与储备。人过日子不能缺盐,它能给平淡的日子增添美味。但盐在人不知不觉间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烦恼,甚至重大危害。醒悟之后,对盐的摄入,人皆慎之又慎。在我家里,因为盐的食用有分歧,老派同少派之间,没少发生龃龉,乃至某种不见硝烟的战争。
最早的战争,发生在十多年前。那时,老派还不老,少派真的很年少,小荷才露尖尖角。可就是那么小的“尖尖角”,她已经锋芒毕露了。在她认定的道理上,常常寸步不让。少派以为她有科学根据,少吃盐是出于对老派的关心和爱护,有时竟心安理得采取老派难以接受的“极端”的方式表达。
忘不掉某年春天,因为盐的问题,在餐桌上爆发的一场战争。那年春节前,老派的老派,少派的老老派,她老人家在乡下老家费了许多劲,腌制了不少腊肉,春节后让我带回县城。晴日里,挂在院中树枝上晾晒。金黄的腊肉,在明艳的阳光下晒得滴油。人一走进院子,便能闻到腊肉香。老派很是喜欢那种感觉,那可是富足啊,早些年人人向往的境界。
这还只是生腊肉的香气,烧熟的腊肉比它还香十倍。将腊肉切成薄片,伙大蒜一起炒,蒜叶的青,蒜秆的白,腊肉的黄,三种颜色绝佳搭配,香气更是诱人。视觉、嗅觉饱餐之后,大蒜炒腊肉被一对筷子兄弟齐心协力忙忙碌碌地送入口中,那滋味美得差点让人吞下自己的舌条。
美食上桌,本是一件开心事,应该出现一家人围桌而坐、大快朵颐、其乐融融的愉快场面。老派忙乎半天,端着饭碗走出厨房,在饭桌边坐下,三番五次喊少派过来吃饭。岂料少派一到场,见到色香味特别诱人的大蒜炒腊肉竟皱眉头。她夹取一小段白而软的大蒜秆半信半疑地送到嘴里,稍微嚼动几下便说,嗯,这个还挺香,就是太咸了。少派说咸,老派才意识到咸。大蒜伙腊肉,它的一份重要职责是将腊肉身上的盐吸收一部分过来,使得腊肉的咸味略微淡化一些。吃大蒜都咸,可想而知,腊肉有多咸。老派爱吃腊肉,却不知咸。
饭桌上,见老派的筷子并不嫌弃那碗“咸货”,筷子头时不时在盘中“青”“白”“黄”中选择“黄”。少派面带愠色说,那东西,你们还是少吃,要吃就吃点大蒜吧。说完,她用筷子在碗里翻拣分类,一类是她准许的“青”“白”二色,一类是被她禁止的“黄”。老派毕竟是老派,总得以老派自居。未将少派的话当回事,筷子兄弟一次又一次触碰她划定的“禁区”,少派便不乐意了。到底是年少气盛,少派呼啦一下起身,端起菜碗,将一大碗“青”“白”“黄”全倒进垃圾桶,片甲不留。
简直暴殄天物,这还了得!老派向来惜福惜物,自然容不得少派如此大逆不道。老派一氣之下手臂高高扬起,眼看着一个重重的耳刮子就要落到少派稚嫩的脸上,老派中另一人当即伸手阻拦。一场即将发生在肢体间的严酷战争被遏止,随即转变成目光间的严厉战争。少派却根本不吃老派的那一套,一推饭碗,离开饭桌,扬长而去。
从那以后,老派有所反省,理解了少派的苦心。虽然少派的做法不妥,忤逆而且强硬,但出发点是好的。她是为老派着想,希望老派活得健康长久。老派也便多了些自律,尽量少碰那些诱人的腊味。日常烧菜时往锅里撒泼白色细末,手也尽量稳重把持,少哆嗦两下,让小勺里雪白的晶体微末留下一半,回归它的来处——小瓷盅。
老派的“妥协”,换来屋檐底下一方小小世界的暂时和平。一时间,岁月静好,时光平淡。少派中学毕业离家上大学,背起行囊,远走他乡,住集体宿舍,吃学生大食堂。俩老派结伴而行,千里相送,校园挥别,双双抹泪而归。刚入学那段时间,少派每次打电话回来,总是跟老派诉苦,唉,学校食堂里的饭菜真难吃,还是家里的饭菜好吃,出门在外才明白什么是妈妈菜的味道。一到寒暑假,少派立即离校,如小鸟归巢,迫不及待,回到老派身边。老派心疼少派在外吃了苦,回到家里便犒劳少派,每天变着花样给少派做好吃的。少派狼吞虎咽,吃得笑靥如花。她似乎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凡是好吃的“好”或说美味的“美”,当中总有盐的重大贡献。
仅仅几年时间,少派不在身边,老派便放松紧惕。不记得从某日开始,老派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口服降压药。这事儿让少派严重关切,她甚至一度很是紧张。少派厉言批评老派不听她的话,多年以前她就告诉老派不能多吃盐。现在好了,自作自受吧,不听话的恶果找上门来了。少派立即恢复先前少女时代的做法,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坚决不让老派沾染“咸货”。当然,少派以身作则,不让老派吃的,她自己也不吃。在那个不大的空间里,不见“咸货”的踪影,不闻“咸货”的气息。
不吃“咸货”,还不是少派对老派最严厉的要求。在与降压药结缘之后,老派已自觉对“咸货”敬而远之。即便如此,少派仍嫌不够。因盐而起的龃龉,在少派为人母之后,尤为剧烈。少派的少派在一家人的千呼万唤中姗姗到来,随即老派便更显老成,跟着少派升了一级。原先的少派不再是真正的少派,她只能算是“中间派”,或曰“两面派”:在老派面前,她还是少派;在幼小的少派面前,她陡然变成了老派。时光的力量真是太强大了,它足以改变一切,由少到老,仅在人的不经意间。
战争重新开始,祸根还是盐重。真是难为了那个亦少亦老的“中间派”,既要张开翅膀护着真正的少派,又要菽水承欢,孝敬老派。自从有了那个小小的少派,“中间派”对盐更加警惕。她要求老派尽量少碰盐,最好不碰。对于小小的少派,则完全禁止碰盐。
小小的少派到来,给老派带来许多欢欣,却也让老派多受些累。累都不怕,就怕埋怨。一句随口而出的埋怨,往往引发一场战争——后来的战争,仅限于语言或目光。所有的埋怨,皆因盐而起。可怜小小的少派,她无力主宰自己的饮食,“中间派”或者老派喂她什么她就吃什么,好吃就多吃几口,不好吃就少吃几口。有时她也抗议,喂给她的食物,她使劲摇头,紧闭嘴唇拒绝接受;甚至,被人送进口的食物,咀嚼再三之后,她又悄悄吐出来。那些东西怎么可能好吃呢?那个小小的人儿,都两岁了,竟然还没吃过一粒盐,尚不知道人间烟火可以调制多姿多彩的滋味。老派俩人时常愤愤然,为那小小的人儿抱不平。在小区门外的广场上,有许多跳舞遛娃的人,老派咨询过其他带孙娃儿的老派,人家的娃儿几个月大就跟大人一样有滋有味地进食。老派似乎发现,人家的娃儿都格外精神,长得也特别壮实。那可能是盐的作用吧,盐能给人增加劲力。老派有体验,人不吃盐,就会四肢无力。
吾家“中间派”烧给小小少派吃的菜从不放盐,就连给她做菜的锅碗瓢盆,包括菜刀和切菜板,都要接受严格审查,看一看它们在历史上有没有接触盐。如有不纯洁的历史,则被排除在外,不得提起使用。所以,吾家灶台上备有两套锅碗瓢盆,一套是吃过盐的,一套是未吃过盐的。给那個小小的少派做饭菜,当然是使用那套未曾吃过盐的家伙。吃过盐的锅碗瓢盆,肯定有咸味。清洗之后,它还能释放多少盐分?我不大相信。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既有少派的明确指示要求,那就照章落实吧,免得多费口舌闹不愉快。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不留神就将两套家伙弄串了。在老派看来,弄串了那些家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中间派”)小时候一直跟着大人一起吃咸盐,不也很好吗?哪来那么多的讲究。老派更多时候还是依赖老经验,相信“照猪养”,简单,好养,娃儿更结实。而“中间派”则迷信“照书养”,书上怎么说,她就怎么做,严格落实科学配方。所以,一发现灶台上的家伙弄串了,可能在不该给小小的少派碰盐的时候给她碰上了一丝一毫的盐,“中间派”自然不能接受,她便大呼小叫,以警示老派以后小心。
老派后来发现,“中间派”的讲究虽然苛刻似乎也有些道理。盐这东西,的确能调味,变平淡为神奇,给人许多美好的享受,但它真的不能多吃。吃多了,危害的严重程度,人都想象不到。
明白这个道理,是因为看过一篇文章。有人说,现在通过体检发现那么多人患有淋巴结节,可能与食盐中的碘有关。而且,据说食盐中的碘添加并无明确依据。人不能缺碘,缺碘的人就可能出现重大缺点,脖颈肿得粗粗大大很是难看。可碘的摄入过多也不是好事,它对人身体有许多看不见的危害。
此后,老派的吃食又有进一步改变,不仅不吃“咸货”,很多时候烧菜干脆不放盐,保持原汁原味。为防止清淡寡味,买菜的时候便做选择,专买那些本身有味儿的菜蔬。比如西红柿和茼蒿就常买,它们自带美味,一个酸甜,一个清香。淡炒西红柿或茼蒿的口感很好,完全避免了无盐的尴尬。
偶尔无盐,日子也有滋味。
红芋娘子
从前,一到谷雨,乡人便忙着去地里秧红芋娘子。
拣一块稍微肥沃的菜地,刨开,松土,整平,然后回家打开地窖,叫醒在温暖湿润的地下酣睡了半年之久的红芋娘子。那些被人从梦中掠走的红芋娘子,睡眼惺忪,满脸通红。离开幽暗的地窖,被转移到另外一块更加温暖潮湿的土地里。躺在新的眠床,它们却很难继续安心酣睡。暮春的阳光一层层叠加在土地上,厚实的光热给土壤里的所有生命注入强大活力。动物或植物,都不甘心被埋没在土层里,它们小心翼翼地伸出触角,缓缓穿透土层,试探着在地面上露出怯生生的小脸,见一见越来越火热的天空和日头。
红芋娘子被人秧到阳光下的薄土层里,一星期后便有绿色芽头冒出地面。接下来,芽头逐渐伸展,舒松开来,形成叶片,且开始以藤蔓的形式,在地面上匍匐,向远处探进。地面上的绿色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先是一条条,继而一块块,随后便是满目,覆盖了地面。这时候,红芋娘子基本上完成使命。地面上,那一根根健壮的藤蔓,便是红芋娘子作为母亲的骄傲,是它生命的延续。
说到这里,是否还需要解释一下?红芋就是红薯或山芋,红芋娘子是指用于作种的红芋。吾乡人很少叫它红薯或山芋,这两个名词似乎有些书面化,乡人可能羞于出口。红薯和山芋,两个名字并在一起,连头带尾简称红芋,似乎也有道理。当然,吾乡人叫它红芋,两个名字的合并简称只是巧合,理由好像不在这里。这种耕种目的在于收获根茎的作物,本质上是一种芋头,它的皮肤是红色的,所以叫红芋。我还记得当年在家乡吃过两种红芋,都是红皮的,但内瓤不同。一种内瓤生鲜状态呈乳白色,烧熟后便变成黄色。另一种内瓤生鲜状态呈淡黄色,熟了就变成橘红色,叫红心红芋。两种红芋内瓤颜色不同,味道也有异,前者口感粉面,后者柔软甘甜。那年头,我爱吃的是后者,红心红芋。可能是它不太喜欢吾乡的气候土壤吧,在那块土地上产量不高。红心红芋在吾乡种植量小,或许乡人觉得种它不划算,种一点尝尝而已。
当年人家给农作物留种,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将长得最健壮、最俊美的果实选出来,养到它们完全成熟,小心翼翼收获好、储存好,希望来年它们能给人带来好收成。留作红芋种子也是这样。头年秋天,乡人从地里挖红芋时,便一直留心出土的每一枚红芋,看哪一枚红芋可作种子。边挖边选,选出块头大、品相好的红芋,轻拿轻放,谨防碰破红芋的表皮,装进专门的筐子里。
留种的红芋必在地窖里越冬,身盖一层厚厚的潮湿沙土,给它保温又保湿。刚出窖的红芋种子,细皮嫩肉,肤色红润,模样儿十分周正美观。作为种子,在次年春夏之交被埋进土里,它的使命是发出新芽,长出很多长长的藤蔓,为栽插新一季红芋提供优质秧苗。乡人将每根红芋藤剪成若干段,每段上至少有一片叶子。藤蔓的切面都是斜剪出来的,不是圆形,是椭圆形。斜面的端头,自然尖锐,便于插进土壤。同时,因为切成斜面,藤蔓与土壤的接触面增大,藤蔓在土里易于吸收养分尽快生出根系。
地面上的藤蔓一根一根被剪除,作为秧苗一截一截地插进红芋地,埋在地里的红芋娘子就会被翻挖出来,再次在太阳底下亮相。完成使命后的红芋娘子,那形象让人看见难免伤心。从土里挖出来的红芋娘子,跟当初埋进土壤的红芋娘子,真有天壤之别。原先的细腻、娇嫩与红润,消失得无影无踪。出土的红芋娘子浑身皴裂,龇牙咧嘴,模样臃肿。如果说入土时的红芋娘子是十八岁的俊美姑娘,那么完成任务出土后的红芋娘子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婆婆。它身体内的激情与活力,全给了地面上那些葱茏茂盛的藤蔓——从红芋娘子身上分蘖出来的新生命。
完成使命的红芋娘子,耗尽它一生从阳光和土地中吸收来的汁水,它便不再具备作为食粮的属性功能。人们不愿意再吃它,但我还是吃过,是在食物短缺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中期。它跟普通红芋不是一个味儿,丝毫没有普通红芋的粉面与甘甜,入口寡淡,嚼无劲道,食之如饮白水。
少年时代,我曾纳闷,明明是红芋种子,乡人却叫它红芋娘子。后来,我似乎明白过来。在吾乡,“红芋种子”是用来骂人的话语。比如,谁家孩子顽皮,在太阳底下暴晒,父母看见,可能会以心疼的口气骂那孩子:“你晒红芋种子啊!”骂语当中饱含父母对孩子的关心与疼爱,生怕晒坏熊孩子,让那个漂漂亮亮的宝贝儿成为红芋种子一样的丑八怪。
几十年后,细细品味“红芋娘子”这称呼,仿佛感受到字词间有一股浓浓的敬意,恰如世人对母亲的敬重。自己的母亲,旁人的母亲,天下所有的母亲,那些满面沧桑的妇人。不再年轻美貌让人艳羡,却在人前得到真诚的敬重。
“红芋娘子”,不可小觑的方言俚语,凝聚一方水土养育出独有的人文精神。
责任编辑 黄月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