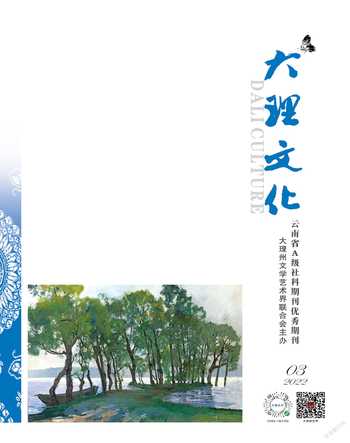苍山
李木


1
我们出现在了月亮坪。“月亮坪”,在一个垭口的木牌上,用木炭写就,字迹歪歪扭扭。我们还要往下,去往山谷里。富生家在那里。福东曾经来过富生家,他努力推开十多年前的记忆之门,记忆中有山,有牧羊的富生的母亲,有厚到膝盖的雪,还有因饥寒而颤抖的双腿。有时,记忆呈现出了容易消淡的一面。我们也意识到一些记忆不会轻易消淡,就像富生在我们记忆中的样子。
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富生,他坐在长长的羊槽上等着我们,他的羊群围拢着他。黑色的羊,黑色的牛,黑色的马,黑色的树木。遇见富生后,我们将与太多的黑色相遇,我们还将遇见黑色的湖水,黑色的岩石,以及有关黑色诗意的幻想,但那些黑色并没有给人冰凉感,反而因为富生、因为世界本身而有了丝丝入扣的暖意。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依然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富生。富生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方面的原因回到了老君山,以放牧为生。木头栅栏里的洋芋花开得绚丽,白色和紫色两种色彩交杂,洋芋旁边种植的是中草药,狗吠鸡鸣,一派热闹的样子。
富生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而我们几个人的孩子都还很小。我们一眼看到了,时间与生活在富生身上留下的痕迹。在古木林立的山里绕了一小圈,熟悉的红豆杉(不是很多),还有其他熟悉的植物(很多)。我们朝着一个空啤酒瓶扔石头,扔了一个又一个,我打不中,福东没能打中,财仁打中了一个,富生试扔了几个,不中,富生的不中定有因由,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到来。回到富生家。杀羊,羊皮被整张剥落,内里的血丝在滴落,富生那时并没有参与其中,只是帮他的几个兄弟磨了一下刀,用水冲了一下刀。他的几个兄弟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把羊解剖完成,他们拿起羊胆看了一下后,丢进盆里,在他们看来有羊胆就很好,富生说偶尔运气差会碰到没有羊胆的羊。羊皮被剥落的过程,我们多少感觉有点点残忍,剥落的羊皮内侧上凝结的血滴一直凝结着,就那样慢慢干结。
夜间,月亮周围有着一些红晕。那时,那个世界的命名,与真正的月亮有了联系。当月亮隐去,又一次看到了群星璀璨的夜空。随着星辰慢慢多起来,我们的话也开始多了起来。十多年不见的富生依然温文尔雅,依然沉默寡语。我们谈到了过去,谈到了十多年以前。富生的兄弟,要离开月亮坪,去往另外一个住处,那个异地搬迁点,那个叫“索玛小镇”的地方,他与富生一样温文尔雅,只是话要多一些。富生的兄弟离开后,富生说起了他弟一岁多的女儿夭折了,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我们由于沉浸于再次见到富生的喜悦中,他弟也一定强压着内心的伤感,我们竟忽略了他弟那很难消释的痛苦。富生说了之后,我们重返他弟在时的场。他弟的低声诉说中,是有着那种一直压制着的悲伤,多少人又能轻易从失去孩子的苦痛中挣脱出来。只是在滋滋燃烧的火塘边,我们真是把一些东西忽略了。我们几个人围坐在火塘边,烟雾缭绕,因为富生的侄姑娘而沉默了一会。那时,我们的内心很痛。那时,酒又开始起作用了。从不喝酒的富生也喝了一小点。夜已经很深,我们的酒杯不断被满上,我们是要好好喝点,我们是要好好地谈谈,我们这些习惯沉默之人,累积了太多要说的话。
羊群出笼。富生有一百多只羊。那时,我们还在酣睡。早早就赶着羊群出去的是富生的母亲。富生的父亲早逝,富生家有五个兄弟姐妹,她的压力可想而知。她一定在富生父亲去世时,夹着烟蒂沉默了很长时间。富生的母亲给我们的感觉是很少说话,一直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看到富生的母亲,我便想到了老祖(老祖在很长时间里,或者一直是我在内心里形成的标尺。老祖的那种善良与隐忍,在富生的母亲这里又以另外的样子在表达着)。她的沉默,并不是语言的原因。富生的母亲会讲白族话,反而是富生的几个孩子不会讲白族话,只会讲彝语和汉话。只是在我们面前,她一直很沉默,与我们不绝的言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富生的不抽烟与她的抽烟。富生兄弟的相对滔滔不绝与她的沉默寡语。老人的沉默里,有着很大的原因是生活很长时间的重压。而现在,老人已经相对轻松了。
富生在离家有些远的镇上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他要给孩子们做饭、辅导作业,每到富生去陪孩子们时,生活的重担又再次轉移到了家里的女人身上,老人又开始放牧的生活。富生的母亲与我在苍山中遇到的很多老人一样。在与那些老人不断相遇交谈之后,我真成了容易被感动的人。细细思量,才意识到那些人并不是为了打动我,也不是为了打动自己,只是因为生活如此,他们必须如此。他们的表情,他们的皱纹,他们的语言,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与世界之间的那种关系,都在以一种很奇妙的方式击打着我。有时,一些巨大的悲伤会侵袭着我;有时,又是一些巨大的感动朝我袭来。
富生的母亲,依然在那里一根接着一根抽烟,我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她抽烟的娴熟动作上,而是放在了她抽烟时的若有所思上(那不知道是在什么样情形下所形成的,可能是在她的丈夫离世之后,也可能是在富生高中毕业之后不能继续上学之时,还可能是自己一岁多的孙女夭折之时,我们能理解一个老人的沉默,其实富生的母亲年纪还不大,还不到六十,不到六十又怎么能是老人呢,只是她身上呈现出了很强烈的老年人特征)。
那时,我已经回到苍山下,与友人北雁说起了富生的母亲,说起了很多老人,讲得可谓如泣如诉,内心复杂。我们都在强调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来的很多品质。在富生家那一夜,夜色中繁星闪耀,我再次看到了满天繁星。繁星出现之前是月亮的影子,我们不再添柴,用火钳拨弄着火塘,火塘慢慢冷了下来。我再次走到木质的建筑外,那时天空中就是繁星密布。我跟财仁说好长时间看不到这样的繁星了,至少在苍山下的那座城里,已经见不到。财仁在那一刻反驳了我,反驳说在那座城中,他依然多次见到了繁星。他的反驳,把我好不容易营造的氛围转瞬打破,但因为酒的原因,那种营造的美好氛围很快又回来了。那是属于内心的夜晚,那样的感觉很奇妙,我以为那样的夜晚将是稀缺的。但在苍山中,我还是多次遇见了那样的夜,并沉醉其中,内心里住着一些星辰,那是花甸与土地上空的星辰纷纷就着酒坠落心底,在内心形成的璀璨,一直无法消散,直到夜尽,直到天明。那样的夜,会让一些忧伤褪色,同样也会让一些忧伤加重。有那么一刻,我们大家都忧伤起来,我们说不清楚为了什么,那就为了那个于当时的我们而言真正稀缺的夜。43B78BA8-2F64-4E05-9FEB-677A1870E016
富生曾要离开这个村落,想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在这里,就只有他们一家人。后来他没能通过读书改变什么回来后,又多出了一家,当他弟弟长大了后,又多了一户。我们能理解为何现在的富生为了孩子,要在很远的学校附近租房子。富生的爱情也在这里,富生的婚姻也在这里。富生并没有真正离开过这个现在只剩一户人家的村落,他的弟弟经常离开村落去往一些大城市打工,他让自己的媳妇也跟着弟弟一家外出打工了几年,而他自己就一直是牧人,一个高中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远离的牧人。富生的兄弟说自己的酒喝得差不多了,就要给我们唱一首歌,但他的酒一直没有喝够,我曾想象过他的兄弟会用他们自己民族的语言,在有些阴冷的村落里唱出一群人的忧伤。其实我们能肯定的是,如果他真唱了,那绝不会是忧伤,一定是一首欢乐的歌。
自然,汩汩流淌的溪流,繁星,生命的漫长路途,那些依恋与徘徊,那些爱与无奈(富生身上的无奈感,似乎是少了些,但其实那只是我们一开始的感觉,当富生说起让他们去往集中安置的小区,内心还是有些复杂,那意味着他们将离开月亮坪。他说幸好还可以在山上放牧)。
黑色笔记本
在苍山中的那个村落里,所有的灯火早早就熄灭了,人们早早就躺到床上,大家都在静静等待着亡灵的回来。苍山中的那条河流在厚厚的夜幕中,响声清越,还有点点冰冷,落入河中的星辰也感觉到了那种透心的刺骨。白天,苍山中的那个村落里,一场丧事刚刚办完,一些人沉浸于悲痛中还未能缓过来。暗夜,夜是忧伤的,忧伤的心亦无法真正入睡。人们的讲述中,亡灵会踏着冰冷的月光回来,月光很淡,只有亡灵才能看清淡淡的月光照出来的路。人们把亡灵生前最重要的物摆放在了坟墓前面,一根拐杖,一个烟斗……夜晚倏然而逝。人们都说那个夜里,亡灵是回来了,人们听到了他在门口抽了几口烟,然后磕了几下烟斗,然后就进来了,亡灵要轻轻碰触一下亲人,但亲人不能动。亡灵忘记了烟斗。人们还看到了磕烟斗时留在门口的灰。那都是亡灵回来的痕迹。亡灵的亲人,把烟斗展现给大家,就为了证实亡灵曾经回来过。人们说,在尸骨被安葬的那晚,所有的亡灵都会在那个晚上回来,那时,无论是狂风骤雨,还是冰冻湿滑,那些年老逝去的亡灵,有了重返青春的力气,他们留在夜间的脚印,与常人无异。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人们说起一些年老的亡灵时,都肯定地说他们听到了亡灵走路时喘气的声音,还信誓旦旦地说起看到了亡灵停步歇歇气时令人悲伤和怜惜的身影。我参加了其中一次葬礼,那一晚,我猛喝了几杯酒,然后早早就躺了下来,冰冷与恐惧让我很长时间不能入睡。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入睡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是翌日,人们开始纷纷说起亡灵回来的事情,所有人都面露肯定的神色。我也丝毫没有怀疑,毕竟在我的记忆中,在人们多次说起之后,我的潜意识里已经对此深信不疑,即便在众人的异口同声中,一些可疑的东西依然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即便时间继续往前,人们对于亡灵的认识依然是这样,至少在苍山下那些村落里是这样。我离开了那个村落,人们依然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亡灵回来的情景,这次亡灵忘在家里的是拐杖,那个支撑着生命度过了众多严寒冬日的拐杖。我回头看了一眼,是看到了那根被时间擦亮的拐杖。信与不信,似乎有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离开了那个村落。河流的声响在白日人们喧闹的讲述中,变得小了很多。我远离了人群,我沿着河流走了很长的路,才真正从那个村落里走了出来。在我一个人时,在与那些喧闹的人群有了一些距离后,河流的声音开始大了起来,河流变得真实起来,我俯下身子,像牛饮水一样长长地喝了一口冰凉刺骨的河水。
2
从富生家出来,富生要带我们去往山顶。我们将面对着的就是纯粹的山,即便他的母亲、他的兄弟,还有那个早夭的孩子,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天然的石头不可思议地堆积在了山顶,从山顶往下有很长一段距离,都是石头。我们踩着那些一块又一块天然的石头往山顶爬着。那些石头堆积的世界里,偶尔会有着一些低矮的杜鹃,而比较多的是雪茶,一种白色的细小植物,一些人在那些石缝中找寻着那种植物,我采擷了一点放入口中,细嚼,微苦,然后慢慢回甘。富生叫我们轻轻地吸口气,雪茶的味道开始在口腔里游走,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了它在游走,过喉,抵心。如果不是富生说起那种植物,并在说的同时把那种植物放入口中,我们很有可能就会把那种白色的植物忽略。那种植物太容易被人忽略了,形似花瓣,如雪,贴着地面生长。那时,我的注意力都被那些堆积的石头吸引。那些石头,不像是在山的另外一面那样,我们能看得到它们生长的模样,石崖挨着石崖,而我们所在的这一面,只是石块的堆积,它们就像被什么人搬来那里胡乱堆积起来一样,或者就像是山顶上有着一个巨大的用石头建起的房子,突然轰然倒塌,从山顶往下滚落。我们在上面攀爬时,并不用担心那些石块会滚动。那里,我们看到了很多枯死的杜鹃(我又一次想到了关于白骨的比喻),那种悚然感在雾气中弥散,我努力把那些石头想成一些尸骨,却做不到。植物和石头之间依然还是有些区别,只是在那个世界里,它们成了一体,以各自生命的形态成为一体。那些石块就像在那个山坡上那样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骨骼拥有了一部分石头。
我们听到了水流在喧响,但看不见水流。那些满溪谷堆积的石头,把溪流覆盖。我们沿着石头往上,石头消失,湿地出现,闪现眼前的是一小滩水,那是溪流的源头。那真是一条刚刚出生的溪流,那些石头的堆积,似乎就是给年幼的溪流一个保护的外壳。我们只能用听到的声音来想象一条溪流,声音的大与小,声音的缓与急,都在暗示着一条溪流的成长,它可能如那些石头堆积出来的影子,它也可能不是那些石头堆积的模样。站在那条溪流的源头往上看,如果没有山顶萦绕的雾气,就能看到近在眼前的山顶,已经很近,只有几十米了,山有多高,似乎水也可以有多高。福东说自己心里满意的高度就是那条溪流的高度,他就在那里等我们,他太喜欢那条看不见的溪流了(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那时,我们沿着那条石头河往下,就会看到溪流的样子,那时的溪流早已不是石头下面年幼的样子了。在那里,溪流的年纪似乎是用石头堆积的长度在计算的。一条溪流,一些覆盖着溪流的石头,组成了一个可以让我们无限想象的世界。43B78BA8-2F64-4E05-9FEB-677A1870E016
老君山在制造一些想象,同样也是在唤醒一些想象。我们坐在那些石头上,溪流就在我们下面流淌着,我们听着那些年幼的声音,闭上眼睛一会,把溪流边正在败落的花暂时忘却,不然溪流与花之间的那种对比,不自然就会出现,就会让你无端想到生命的出生与凋落。在一个纯粹的自然世界中,生命感依然突显,那是生命的诸多形态,那时回到我们的生命状态,一些让人羞愧的东西就会出现。我们猛然在石头的夹缝里看到了溪流的影子,用手捧起就喝,冰凉,甜美。富生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很幸运,能在那些夹缝处喝到水,而在冬季,溪流依然在,你真正只是听到了一条溪流在流淌,却看不到真正的溪流。
石块,溪流,低矮的植物。它们都在同一个世界里。那时,它们就在老君山中。它们是一样的。它们又必然是不一样的。还有原始的森林,还有水潭。那时,雾气哗哗地在山顶奔跑,世界变得很迷蒙,我们在山顶上能感觉到蒙蒙雾气的那种力度,击打着人的力度。一些湖水开始从消散的雾气中显出来。许多的湖水,就在山的相对低处。山上的湖水。那时,就剩下我们三个。牦牛在山口迎着风啃食着草还啃食着那些潮湿的云雾。富生朝那个山顶指着,一些色彩在那里轻微地动了动,他说那就是牦牛,我朝他指的方向望去,财仁朝他指的方向望去,财仁点头,我也点头,其实我有意扶了扶眼镜,依然看不清楚。牦牛就这样成为了山的一种色彩。那里低矮的杜鹃正在败落。色彩慢慢往下移动,落入湖水中。众多的湖水。传说中有九十九个龙潭。在我们目力所及处,就有好几个,它们像极了那些干净的眼睛,像极了那些干净的泪水波动。湖水中有鱼吗?富生说他没见过。富生对于那些龙潭太熟悉了,我们相信他。那时,我们在其中一个湖水中,看到了许多大蝌蚪,还有一只不大的蟾蜍,似乎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再看不到其他生命,那是海拔四千左右的湖泊。湖水清澈透明,山的影子进入其中,石头的影子进入其中。当那些湖水在雾气中清晰可辨后,财仁再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要朝能见到的最远的那个湖泊跑去,我们只能跑,那时时间已晚,我们还要返回到富生家,我们还要返回到福东家,福东还在那条被石头覆盖的溪流边等着我们。
那是后话了,那时我们已经回到山下,福东说在那条溪流边冰冷的风不停撕扯着他的脸庞,很冷。我们真朝黑龙潭跑去。那时,朝黑龙潭跑去的人就我们三个。我们在那些低矮的灌木丛中穿行。我们的鞋子一不小心就陷入湿地。去往那个黑色的湖水,要穿过那片黑色的树林。我们在那片树林里待了很长时间。青苔很厚。青苔在地上堆积着,生长着,与我们平时见到的青苔完全不同。青苔还往树上爬着,树胡子在树林里垂挂着。绿色的青苔与白色的树胡子。我找了一棵粗壮的古木,靠了一会,地上是厚厚的湿润的青苔。空气里飘荡着各种植物混杂的气息,一些菌类腐烂的气息,一些绿色充盈的气息。湖水近在眼前(有那么一会它消失了,我们只听到了一些鸟鸣,富生模仿起鸟鸣,富生内心里一直装着一只鸟,富生的内心里是应该住着一只鸟,一开始,我们都没发现是富生在模仿鸟的叫声。当我们猛然意识到是富生发出的叫声时,多少有些诧异,特别是我。我们都知道是可以模仿的,但富生发出的声音已经分明不是模仿那般简单。我也想模仿,但感觉口干嘴涩,不知道怎么发声。富生才是真正生活在那座山的人,他熟悉山上的很多生命,他不会在山林中迷失方向)。话不多的富生走在我们前面。湖水在山林中显露出来。湖水的声音,那时只有流入湖水的溪流在哗哗淌着,在湖的这一边都能听到那种哗哗的声音,而在山林中时,那样大的声音竟消失了。湖水边,有着野猪出现过的迹象。湖水边会不会出现熊?那个湖中应该是有一些鱼。我们希望那么幽深那么寂静的湖里能有鱼。因吃了一些杜鹃花,而轻微中毒如醉的鱼,吃了鱼而醉了的熊。这些在人们的讲述中曾经出现。那时,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湖水本身,我们就在湖边的石头上坐了一会,很短的一会,毕竟时间已经很晚,然后返回,返回到最为现实的世界之中。我们再次过山林,再次在那些厚厚的青苔上停留了一会。有那么一会,我对那种寂静竟有些不适应,甚而心有所恐。自然的安静,人影的消失,那是会让你既希望能一直在,又不敢真正把自己长时间放置其中的寂静。里面夹杂的矛盾,你无法进行评判。你唯一能评判的是那次的行走,充满了不可信的虚幻与真实。
黑色笔记本
那时,在苍山下的那个村落里,正举行着一场祭祀活动。祭祀活动中,人们要宰杀一头牛,祭师把酒倒在牛的槽里,要让牛饮酒,要让牛同意才能宰杀它。那个村落里的所有人都坚信,喝了祭酒的牛,如果不同意自己被宰杀的话,会变得较平日更为躁动,那场祭祀需要的是一头安静的牛,一头平静地面对死亡的牛。其中一个已经喝酒醉了的人说,牛与人一样,多少人在喝了酒还能变得那般平静。我出现在悖论与诡辩之中。我关心的是那头牛,我多少希望那头行将被宰杀的牛会突然躁狂起来,然后冲出人群,消失在苍山中,从此它只是成了关于苍山的讲述的一部分。只是我的希望与眼前的真实之间没有交互的影子。你继续喝了一口酒,然后努力安静地看着那头牛的动静。让你有些失望了,那头牛,并没有躁动,而是在酒的作用下,变得更为安静。人们早就会料到如此,他们已经面对了太多类似的牛,他们对此都已经有些麻木了。生命的麻木感,需要一些东西来刺激和唤醒。这样的情景,有点虚幻,有点不可信,但在我真正出现在那里后,又變得无比真实,酒的作用反而是让自己变得更为清醒。也因为酒,我讲述的近乎就是一场梦,也很可能就是一场梦。牛安静地反刍着,面对那么多的人,它不为所动,它早已习惯了很多人。所有的人都开始喧闹起来。牛只是很短时间内被人注意关心,突然间人们都忽略了牛,忽略了祭祀中最重要的牛。牛的主人,可能已经混入喧闹的人群,也可能去了别处。我没有去问牛的主人是谁。那时,我抬头,看到了苍山上浓雾团聚,山顶可能正在下雪。我猛然意识到这天是大雪。我在黑色笔记本上记录下:大雪日,苍山下,宰牛,饮酒,苍山上,一场雪正在落下,生命暂时的冬天。
3
从月亮坪出来,我看到了那对父子。我再一次看到了那对父子。那对几乎没有任何交流的父子。我不知道自己见到的是否就是同一对父子。我又希望在苍山中有着很多那样的父子。毕竟一个人面对着苍山,总归还是会孤寂的。我曾目睹着其中一对父子在一些墙体上作画,创作之时他们沉默不语。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沉默。我就在沉默中安静地看着他们日复一日地作画。即便双方就那样沉默不语,但那样的沉默不语与一个人的沉默不语是不同的。43B78BA8-2F64-4E05-9FEB-677A1870E016
在苍山中,当作为纯粹自然的苍山暂时被人们忽略时,人便成了主角。在一些时间里,苍山会隐去,而那些人会突显出来。我与各种各样卑微如蝼蚁之人相遇,他们身上有着星星点点的光,他们在重塑着一种筋骨,我想搜集的便是那些星星点点的,很容易就会消散的光。那时,我就是某种屈光的生命,想希望用那些生命之光来照亮内心的某种幽暗。那时,蛾子正扑向燃烧着的松脂。那时,我便是蛾子一样的生命。那时,我又想到了我们的魂是透明的蜘蛛(我生活的那个白族村落,会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去往庙宇,为那些失魂落魄的人找魂魄,找到的魂魄往往就是一种很微小的透明如蜘蛛的生命),我们的一些魂会不会也是一些蛾子?松脂是用来照明的,燃烧的火塘边,只有我和几个老人,那时瑟瑟的冷风扑打着窗户,那时我们都在屈向光,屈向火塘的温暖。就是在那个夜晚,一些老人的精神之光对我产生的那种影响便开始了。
我多次出现在苍山中一些偏僻的村落里,与一些老人在火塘边聊天,那时火塘上面的灯光往往是昏黄的,但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并没有感到有多么疲乏,我们谈论的话题很宽,在我们看来,我们所关注的既有些狭隘,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狭隘。一些老人,不再是衰退的生命,而是善良、坚韧的延续。就像不断出现的老祖,就像在周城遇见的织布的老人、制香的老人、扎染的老人,就像制作银器的老人、烧陶的老人,就像是富生的母亲、福东的母亲、财仁的母亲、仲华的母亲、我的岳母、我的母亲,就像是姑爹的父亲……这些人我熟悉,我们经常在一起说起他们,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在他们身边,但他们都在以很特殊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世界,并影响着我们。那些身上所显现的是生命的坚韧,他们朴实木讷,他们只会说白族话,他们除了自己生活的那个村落外,很少远走,他们不曾去过城市。我真受到影响了吗?我身上的一些鄙俗,依然如铁锈般嵌入肉身与灵魂。
那对父子出现了。那时,客车在苍山中颠簸前行,客车风尘仆仆的,一群人风尘仆仆的,焦虑的应该只有我,我扑闪不定的目光到处游移,我擦了擦客车玻璃上厚厚的一层灰,露出来一小块,但那样一小块在那时已经足够,那小块上面并没有任何的眼睛。我望向了窗外。窗外是生长稀疏的草木,一些牛马在山坡的草甸上朝我们张望,我竟然还看到了一只麂子(许多人也看到了,它在啃食着青草的间隙里,也朝我们望了一眼,然后继续吃草。当车子转了个弯,又可以看到那只麂子刚刚出现的地方,麂子早已消失不见,就像之前的从容只是一种伪装的镇定)。那对父子搭车上来,没有座位,只能靠着车门,人群拥挤,热汗淋漓。他们就那样安静地站着,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对话,他们没有注意到在拥挤的空间里烦躁的我正在注视着他们。
那对父子是为庙宇塑像和画墙画的人。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塑的像还不是真正的神,只能是神的形。他们所在进行的同样是很纯粹的艺术创作。那对父子出现在了苍山中的许多个村落,以及许多个苍山的子山上,苍山中的每个村落都有着自己的神灵,每个子山都有自己的庙宇。庙宇和村落之间的联系,要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至少是有一些人出现在庙宇中时,才可以捕捉到那种隐秘的联系。而当他们父子二人出现时,庙宇成了个体,被分割开的,那时庙宇与那对父子间构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联系,一种极为特别的构图。他们重塑一些泥像,重画一些画,一些并不是光怪陆离的画,有那么一会,我又希望看到的画是超现实的、是变形的、是色彩斑斓华丽的。他们还做的就是对一些塑像与墙画进行修补,他们就像在一个又一个废墟上重建一个世界,把那些倾倒的东西重新树立起来。他们说自己的创作,只与艺术有关,更多与信仰无关,只是有些特殊而已。
这对父子是否就是原来我曾见到的那对?那是在很久以前了,同样的情景,他们也同样在半路搭车,汇入拥挤的客车之中。客车中的人群异常疲惫,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他们就像许多在苍山中到处游荡的人一样(他們父子也可以算是游荡的人)。父子,这样的关系往往很微妙。那时,那对父子保持沉默,还暗暗透出一种隐忍的东西。眼前的这对父子,我能从他们背负的东西上肯定他们便是多年前我所见到的那对父子。那对父子,以不同的步调、不同的希冀,进入一个村寨,或者是山中暂时没人的庙宇。那对父子,无意间见到一些破损的塑像时,也会去修补一下,对一些残损的画也会进行修补。我们往往会去感叹那些墙体上的绘画,那些源自民间的、源自在大地上近乎流浪的艺人,他们默默地呈现着技艺的精湛,以及思想世界的某种丰腴。
黑色笔记本
黑色笔记本中,有一些生命,有一些东西,具有着那种冲破凝固黑色的质地。那些与黑色不一样的东西,它们的出现似乎被黑色笔记本的惯性所阻挠着,类似一些生命生长时会遇到的阻力与难度。那时,黑色笔记本的黑色只是笔记本本身。三只老虎出现,与苍山中悬挂在树枝上成串的蝴蝶出现时是一样的,黑色笔记本翻开,那些空白处是三只老虎的脚印,是那些蝴蝶羽翅的缤纷。三只老虎从苍山中走了下来。苍山,可能是我现在面对的真实的苍山,也可能是另外的山。苍山,那时成了一座有着形容和象征意味的山。当我出现在真正的苍山下的那个村落,那个叫鹤阳还是什么的村落时,人们竟惊人地提到了三只老虎。而在这之前,三只老虎首先出现在那个会议室,三只老虎在没有任何自然气息的会议室被人们讲述着。那些老人,跟我说三只老虎就是从那里下来的,他们指了指那里,那是在树木不是很茂密的地方,三只老虎结伴而行实在是太醒目了。三只老虎从苍山中的那条溪流中渡河。溪流在冬日色调的作用下,更加清澈,溪流在冬日里依然是丰盈的。那条溪流,让我想到了苍山中的一条溪流。鹤阳村往上。灵泉溪。溪流丰沛。疏浚河流的几个人(只可惜,他们只顾着疏浚溪流,而不跟我说任何有关那条溪流的种种)。水中的废铁(隐喻一般的存在)。河流成为空间(宫殿,抑或陋室)之内的声音,河流成为教堂上彩绘壁画的一部分,河流从本主庙前流过。坐在露在溪流外的一小堆沙石上,看河流流淌,主要是听,听那些不断撞击着胸膜的流水的声音,还夹杂在流水声中的鸟鸣。一些鸟飞过,遮挡着阳光照入溪流,阳光被切割成鸟的碎影落入水中,又从水中振翅,朝灵泉溪的源头飞去。那里再不能往上了,一些人脱了鞋子渡过溪流。三只老虎进入了溪流。有人出现在了那里,就像我一样出现在了那里。三只老虎,似乎并不饥饿,它们也无意去伤害眼前那个无辜的人,它们对视了一下,它们甚至根本看都不看那个人,三只老虎继续往前,而那个未被伤害的人吓得晕了过去,醒来便疯了。它们将出现在另外一条大河。那是苍山中的那些溪流所会汇入(也可能不会汇入)的一条大河中,那条叫“澜沧江”的大河。三只老虎,讲述的人说,其实不只是三只老虎,而是很多老虎,它们浩浩荡荡地从苍山中离开。曾经它们让自己斑斓的色泽,把苍山的草木染得更加斑斓,它们还在暗夜中释放出炫目又感伤的色彩。三只老虎,在被讲述出来时,我是被迷住了。讲述的人在提到老虎时,那三只老虎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我离开了讲述的人群,我逃离了他们的记忆,我出现在了他们所指的溪流边,脱掉了鞋子,过河,从河的那边又走了回来,那时我便是其中一只老虎,我试着感受着那三只老虎渡河时的内心,但感觉不到,感觉到的是空,是河流的冰冷,是河流的清澈。三只老虎还将从冻结的冰层上跌跌撞撞地走过。三只老虎被那些在苍山中行走着的艺人画在了某个庙宇之上。抽象的老虎,属于印象主义的老虎,只是色彩的,又只是忧伤的色彩。只是不能肯定的是那变形而忧伤的三只老虎,就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三只老虎。是那对父子跟我说起的,我们无意间说到了它们。我以为是那对父子画的。但那对父子坚决地摇了摇头,他们同样惊讶于那些栩栩如生的老虎。那个苍老的父亲这样说完后,他们继续在那里画着。我看了一会,他们正画着一条我熟悉又不熟悉的河流。我能肯定的是,那无疑就是苍山中的一条河流。那条河流同样是印象主义的。我离开那对父子,远远地看着他们,那时苍山、苍山中的庙宇、庙宇旁流淌的河流,那对父子汇入庙宇的红中,成为一幅印象主义的画,或者是我所认为的印象主义的画。我竟然产生了错觉,那对父子还画下了时间,一块变形的钟表,正在融化的钟表,有点像达利的时间与钟表。当我再次望向他们时,那块我以为的钟表没有出现,却出现了一只老虎的身影,真出现了一只老虎,它正把自己的头探向河边,饮水。然后又出现了一只幼虎,试探着朝那只大老虎与那条河流走去,同样饮水。在转瞬间的色彩变化中,那对父子不见了。43B78BA8-2F64-4E05-9FEB-677A1870E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