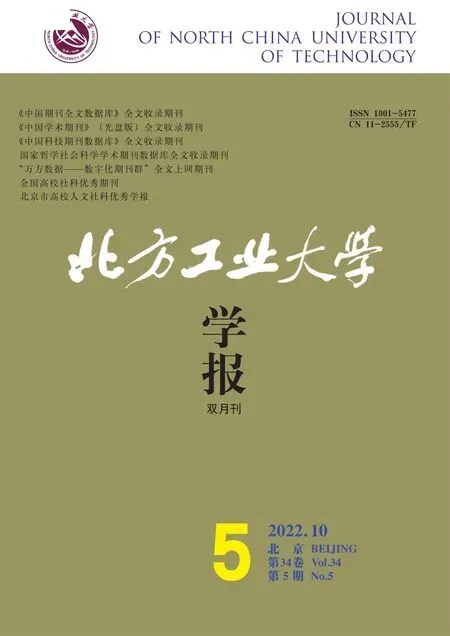秦代《春秋》经传之学存续考略*
刘 伟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73165,曲阜)
对于秦代的《春秋》经传之学,学者往往语焉不详,在已出版的《春秋》学史著作中也罕有论述。沈玉成、刘宁所撰《春秋左传学史稿》为国内同类著作中较早系统研究者,然其所述始于西汉刘歆,没有提及秦代《春秋》学。[1]赵伯雄先生在《春秋学史》中说:“秦始皇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几乎禁止了一切学术活动……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竞相讲学论道的风气不复存在。 ……假如秦的统治照这样再维持个五六十年,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文化传统就将大部灭绝。”[2]其书阐述《春秋》学史也从先秦直接越过秦代而至两汉。 然秦祚虽短,国策虽严,战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余脉尚存,对这一时期经学的面貌,实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 以下试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整理与解读,对秦代《春秋》经传之学的基本情况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稍微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1 秦代经学并未中断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总的来说,秦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所推行的各项制度,都是以战国时期的秦国制度为基础的,并体现出浓厚的法家影响。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李斯的一段话,非常清晰地展现出秦朝统一后国家统治政策与治国思想的变化。 李斯认为“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3]亦即战国时期列国并立战乱频仍、百家争鸣的情况,在秦刚统一之初,对诸子百家的政策并没有马上调整,博士的设置、私学的延续都是明证。[4]
而随着以皇帝制度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各项制度的完善,局面也发生了变化。 “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认为国家应该改变思想文化领域的政策,“以吏为师”,焚毁“诗、书、百家语”,只保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5]在这一方针指导之下,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家文献均遭到严重破坏,《春秋》经传当然也未能躲过此劫。 但正如郑樵《秦不绝儒学论》所言,“陈胜起山东,二世召博士三十余人问故,皆用《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 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6]历代有不少学者也曾指出这一点。 王子今先生也曾以稷下学为例进行深入讨论,认为“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极端的文化专制的举措并没有宣布稷下学的终结。因‘不中用'导致的冷落和迫害,并未能摧毁稷下学继承者的文化自信,他们仍顽强坚持自己的学术风格。”[7]田君先生也曾指出:“作为秦朝官学代表的博士,职掌官方所藏儒学典籍以及诸子百家语的研习、整理与教授,尤其在秦朝制度建设方面,儒学有着广泛的影响。 秦始皇焚书并没有阻断儒家经典流传,在这一传承过程中,秦代儒学还呈现出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8]可以看出,尽管儒家学说及其经典文献在秦朝命运多舛,但可以肯定的是,儒家思想对秦朝政权和社会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儒家经典的传承也没有完全断绝,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士人也以自己的方式顽强生存下来。 因此,在秦代的文化荒漠之中,仍然可以看到一抹抹绿色。 对此,当代学人李景明先生认为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简单认识:“从空间范围看,经学活动遍及朝野;从时间跨度看,贯串秦朝始终;从经学家看,居处不同,学派各异,或专一经,或通六艺;从经典看,六经都有人研习传授;从经学作用看,经学成为统治思想体系构成因素、议政工具,干预了秦政治与现实生活。”[9]就《春秋》经传来说,战国以来已经非常成熟的传承方式和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学人也给后人留下了来日复兴的火种。
概而言之,尽管出现过“焚书坑儒”这样的事件,并推行“以吏为师”等相关举措,秦代的国家政策并没有完全阻断儒家经学。 《春秋》经传之学在这一时期的延续,既源自战国以降学术传承的历史惯性,也有赖于儒家后学与孔门后裔的文化自觉,以下试分别论之。
2 秦代诸儒与《春秋》经传之存续
由于秦祚短暂,这一时期的《春秋》经传之学,实际上以能延续不绝为最大成果。 秦代熟稔《春秋》经传并能将其保存、运用和传播者,能留下姓名事迹的甚少,其中对后世贡献最大者当是张苍。 作为荀子晚年的入门弟子,张苍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才进入生命中最具活力的阶段。 《史记·张丞相列传》云:“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 好书律历。 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 有罪,亡归。”裴骃《集解》引如淳曰:“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 秦以上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 或曰四方文书。”司马贞《索隐》亦谓:“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 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周柱下史。 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 方书者,如淳以为方板,谓小事书之于方也,或曰主四方文书也。 姚氏以为下云‘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主郡上计',则‘方'为四方文书是也。”[10]而《史记》老子本传云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11]由御史、柱下史、守藏室之史的职掌来看,三者确实非常接近,历代学者也赞同柱下史即御史之说,然董平玉女史认为老子之“守藏室之史”与张苍之“柱下史”职责存在差异,两者当是前后相继的关系,是周秦之间官制衍变的结果,[12]其说也可参考。 张苍担任掌管图书文献的御史一职,显然与其学识渊博密切相关,至于是不是有其同门学兄李斯的作用,则难以考证。 张苍掌管的图书不在焚烧之列,而本人又长于《春秋》经传,故《左传》《国语》等书在秦时得以保存当不是问题。
秦时长于《春秋》经传之学的儒生,还有名浮丘伯者。 《汉书·楚元王传》载:“楚元王交,字游,髙祖同父少弟也。 好书,多材艺。 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 伯者,孙卿门人也。 及秦焚书,各别去。”[13]浮丘伯,楚人,曾与李斯一起在荀子门下求学,但二人志趣差别极大,《盐铁论·毁学》篇载桑弘羊之言曰:“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切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丘子不免于瓮牖蒿庐,如潦岁之蛙,口非不众也,卒死于沟壑而已。”又载文学之言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 包丘子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14]对于桑弘羊和贤良文学都提到的“包丘子”,陈立《公羊义疏》卷九云:“秦有儒生浮丘伯,见《汉书·楚元王传》。 而《盐铁论》作‘包丘子',盖古音通也。 按‘浮'‘包'古韵同部,故从‘孚'从‘包'字,经多相通。”[15]《四库全书考证》卷二十亦云:“古浮、包字同。 《公羊传》‘盟于包来',《左氏》作‘浮来'。浮丘伯见《汉·楚元王传》,而《盐铁论》作‘包丘子',是浮丘公与上所引苞丘先生同为一人也。”[16]则浮丘伯、包丘子、苞丘先生是同一人,历代均无异议。 从《盐铁论》所载可知,李斯虽然问学于荀子,但志在仕途,故辞荀子而入秦,一度位极人臣,然终未能善终;而浮丘伯则安贫乐道,讲学收徒,继承荀子之学,并得以善终,且影响及于汉代。 上引《汉书·楚元王传》提到浮丘伯是《鲁诗》一系的重要传承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五“诗序二卷”曾概述其师承系统云:“盖子夏五传至孙卿,孙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苌,是毛诗距孙卿再传。 申培师浮邱伯,浮邱伯师孙卿,是鲁诗距孙卿亦再传。 故二家之《序》大同小异,其为孙卿以来递相授受者可知。”[17]由此可见,荀子在《春秋》经传与《诗经》学的传承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只此二者,皮锡瑞还指出大小戴《礼》与《易》等经的传承也离不开荀子,“是荀子能传《易》《诗》《礼》《乐》《春秋》,汉初传其学者极盛。”因此其“传经之功甚巨”。[18]荀子是儒家学说与儒家经典传承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特别是放在战国末期、秦亡汉兴的大背景之下来看的话,荀子的地位与贡献尤其显得重要。 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荀子,汉代以后的经学会是什么面貌实在难以想象。 基于此,后世学者纠结于其学派归属就显得没有意义了。
在经学史上,浮丘伯除了是《诗经》的重要传承人之外,对《春秋》经传之学的传承也是贡献卓著。 上引皮锡瑞之文已经提到《儒林传》有“瑕丘江公受《榖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之说,而申公正是浮丘伯的学生,可见《榖梁传》也是由荀子通过浮丘伯传入汉代的。 对此传承关系,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卷四曾提出怀疑:“《疏》称荀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 申传江见《儒林传》,申受于荀尚不足信。 《楚元王传》:‘少时与申公等受《诗》浮丘伯。'伯,荀卿门人。 申于《诗》为再传,何独于《春秋》而亲受业乎? 且申至武帝初年八十余,计其生当在秦初并天下日,荀卒已久。 疏凡此等俱讹谬不胜辩,聊发愤一道,以为举隅云尔。”[19]阎若璩提出的疑问在于,若据孔疏的说法,《诗经》的传承是荀子经浮丘伯至申公,而《春秋》经传的传承则是申公“亲受业”于荀子,但荀子去世时申公还未出生,故孔疏所称“荀卿传鲁人申公”之说“讹谬不胜辩”。 杨士勋《榖梁疏》也说《榖梁传》传自子夏,后榖梁氏传于孙卿,孙卿传申公,申公传江公。 孔、杨二疏所说荀子传《榖梁传》于申公,中间当遗漏了浮丘伯这一环节。
阎若璩之疑问是针对孔疏而发,而若将上引各种资料综合分析,便可知孔、杨二疏之失。 在《榖梁传》传承中,荀子肯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浮丘伯无疑也有贡献。 吴涛先生根据汉初陆贾、贾谊等人著作引用《榖梁传》以及《榖梁传》自身引书的情况推测《榖梁传》出于荀子之门,又根据浮丘伯本人治学风格推测《榖梁传》作者很可能就是浮丘伯。[20]其说虽难称定论,但肯定荀子、浮丘伯在《榖梁传》传承中的作用,这是没有问题的。 荀子博通诸经,又不拘于一家、一经之学,其门徒如李斯、韩非、张苍、浮丘伯等等都体现了这一风格,对秦汉以后经学发展居功甚伟。
3 孔鲋与《春秋》经传之传承
在秦代《春秋》经传传承序列中,孔鲋也是不得不提的人物。 关于其本人的生平经历,《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21]《孔丛子·独治》说:“子鱼,名鲋,陈人或谓之子鲋,或称孔甲。”[22]孔鲋为孔子八世孙,其父孔慎(顺)曾任魏国相。 《史记·儒林列传》又云:“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 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23]秦始皇焚书后,孔鲋“隐居嵩阳,授弟子常百余人”。[24]陈胜首倡反秦,孔鲋受邀为博士,后死于军中。 孔鲋其人的治学经历、言行事迹,主要保存在《孔丛子》一书中。 尽管学界对《孔丛子》的真伪与编纂时代尚有争议,但其中所载孔鲋之史料大体可信。 《孔丛子·独治》篇载其治学经历,云其“生于战国之世,长于兵戎之间,然独乐先王之道,讲习不倦”。 在他看来,“今天下将扰扰焉,终必有所定。”基于此种考虑,“吾修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 且吾不才,无军旅之任,徒能保其祖业,优游以卒岁者也”。[25]
孔鲋之学以家族相传为主,金朝时衍圣公孔元措所撰《孔氏祖庭广记》卷一《世次》说“子鱼好习经史,该通六艺,秦始皇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召为鲁国文通君,拜为少傅。”[26]若此说可信,则孔鲋在秦始皇时期已经应召出仕。 那么,上引《孔丛子》所说孔鲋“独乐先王之道,讲习不倦”,以“能保其祖业,优游以卒岁”为人生理想,当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后。 但陈胜举兵反秦时,孔鲋没能拒绝陈胜的邀请,在陈余的劝说下出任博士,《孔丛子·独治》载此事云:“陈王郊迎而执其手,议世务。 子鱼以霸王之业劝之。 王悦其言,遂尊以博士,为太师,咨度焉。”[27]据《孔丛子》所言,孔鲋担任陈胜博士期间,曾多次与陈胜谈论治国之道,深得陈胜赏识。 只是局势变化太快,孔鲋未能幸免于难,殊为憾事。 对于他改变治学收徒之志、转而辅佐陈胜以致死于战乱之事,《史记·儒林列传》曾评价说:“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28]其论可谓一语中的。 孔鲋对秦朝焚书黜儒政策非常不满,故选择投奔陈胜,希望儒学再兴,也显示出作为孔门传人的责任感。 除此之外,对于秦始皇的焚书举措,孔鲋还曾采取藏书的方式保存了部分儒家经典文献,《孔丛子·独治》篇载其事云:
陈余谓子鱼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子鱼曰:“吾不为有用之学。 知吾者、惟友。 秦非吾友,吾何危哉? 然顾有可惧者,必或求天下之书焚之,书不出则有祸。 吾将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29]
据《秦始皇本纪》,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毁民间所藏经史诸子之书,但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冒险藏匿,孔鲋就是一个例子。 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卷一《世次》也说“鲋知秦将灭,藏其《家语》《论语》《尚书》《孝经》等,安于祖堂旧壁中。”[30]至于有哪些经典藏于壁中,历来说法不一,《汉书·艺文志》提到“《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可见数量颇多。[31]这与孔鲋的身份也相符合。
孔鲋藏书除了《尚书》《礼记》《论语》《孝经》之外,有没有《春秋》经传? 《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均未明说,唯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五上叙云“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32]笔者以为,孔氏家人世代相传之书,《诗》《书》《礼》《乐》《易》《春秋》皆应在内,孔鲋自幼所学,也当以六艺为主。 《孔丛子·论书》篇云:“夫不读《诗》《书》《易》《春秋》,则不知圣人之心,又无以别尧舜之禅、汤武之伐也。”[33]以理推之,其藏书也当涵盖六艺之学。
孔鲋自云其曾读过《春秋》,除上引《论书》篇之言外,《孔丛子·公孙龙》篇也有一个很好的例证:
平原君曰:“至精之说,可得闻乎?”答曰:“其说皆取之经传,不敢以意。 《春秋》记六鶂退飞。覩之则六,察之则鶂。 鶂犹马也,六犹白也。 覩之则见其白,察之则知其马。 色以名别,内由外显。 谓之白马,名实当矣。[34]
孔鲋所说《春秋》六鶂退飞之事,载僖公十六年《春秋》经:“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 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35]孔鲋引此与公孙龙之白马非马说进行辩论,足见其学养之深。 除了《春秋》经文外,在《孔丛子》中也能看到运用《左传》《公羊传》的痕迹。 如《记义》篇载子贡之言说:“昔孙文子以卫侯哭之不哀,知其将为乱,不敢舍其重器而行。 尽置诸戚,而善晋大夫二十人,或称其知。”[36]据《左传》,孙文子即卫卿孙林父,因得罪于卫殇公而以其封地叛晋。 《左传·成公十四年》说卫定公死时之事云:“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尽置诸戚,而甚善晋大夫。”[37]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孔丛子》所述来自《左传》。 再如《记问》篇载“西狩获麟”事云:
叔孙氏之车卒曰:“子锄商樵于野而获兽焉。众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有麕而肉角,岂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 吾将观焉。”遂往,谓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视之,果信。 言偃问曰:“飞者宗凤,走者宗麟,为其难致也。 敢问今见其谁应之?”子曰:“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祥。 今周宗将灭,天下无主,孰为来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 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38]
“西狩获麟”之事,初见于哀公十四年之《春秋》经。 《左传》释此事说:“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 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39]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左传》述此事较为简略,其中“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的说法与《记问》中“子锄商樵于野而获兽焉”一句相似。 《记问》接下来的说法则与《公羊传》比较接近:“麟者,仁兽也。 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 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40]《公羊传》至迟在战国中期便已经出现,早期之传承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为主要形式,到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赵伯雄先生言之甚详,[41]此处不赘。 《记问》关于麟兽“有麇而肉角”的形象描述,以及孔子见此而哭泣并感叹“吾道穷矣”的描述,都与《公羊传》有明显的引述关系。 由此可见,《记问》篇关于“西狩获麟”的言论,当是综合采用了《左传》和《公羊传》的叙述,而以《公羊传》为主阐发己意。
除了利用《左传》《公羊传》之外,《孔丛子》也曾引用《国语》中的事例,而《国语》本身便与《左传》密切相关,其传承与流布也是早期《春秋》学的组成部分。 《孔丛子·记义》载鲁大夫公父文伯死后,有两妾欲陪葬,其母坚决反对,并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孔子,天下之贤人也,不用于鲁,退而去。 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随。 今死而内人从死者二人焉。 若此于长者薄,于妇人厚也。”[42]《国语·鲁语下》述其母之言曰:“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 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 二三妇之辱共先者祀,请无瘠色,无洵涕,无搯膺,无忧容,有降服,无加服。 从礼而静,是昭吾子也。”孔子听说此事后,对公父文伯之母给予高度评价:“公父氏之妇智也夫! 欲明其子之令德。”[43]《孔丛子》与《国语》尽管具体言辞有所不同,但有相承关系还是非常明确的。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孔丛子》书中不仅有引用《国语》的例子,还出现了最早对《国语》史事的评论分析。 《孔丛子·答问》篇云:
陈王涉读《国语》,言申生事,顾博士曰:“始余信圣贤之道,乃今知其不诚也。 先生以为何如?”答曰:“王何谓哉?”王曰:“晋献惑乱听谗,而书又载骊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 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 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 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辞,将欲成其说以诬愚俗也。 故使予并疑于圣人也。”博士曰:“不然也。 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 举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以无讳示后世。 善以为式,恶以为戒。 废而不记,史失其官。 故凡若晋侯骊姬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 若夫设教之言,驱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 今此皆书实事,累累若贯珠,可无疑矣。”王曰:“先生真圣人之后也。 今幸得闻命,寡人无过焉。”[44]
如果《孔丛子》的基本内容确定形成于孔鲋时期,则这段记载是目前所见文献典籍中“《国语》”书名的最早记录。 陈胜在战争时期还能读《国语》,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国语》为兴衰成败提供鉴戒的功能。 陈胜所读之申生故事,见《晋语一》。 陈胜读《国语》所载晋献公宠幸骊姬而迫使太子申生自杀、改立太子之事,见书中有“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之语,认为夫妻夜话这样的隐私,外人无从得知,应该是“好事者为之辞,将欲成其说以诬愚俗也”,由此出发,陈胜认为所谓典籍所载“圣人”“圣贤之道”不可尽信。孔鲋则从史官职责和史书编纂角度进行了解释,认为“今此皆书实事,累累若贯珠,可无疑矣”,并打消了陈胜的疑虑。 可以看出,《孔丛子》这段解说已经不仅仅运用《国语》所载史事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了,而是以“优施教骊姬夜半而泣谓公”这一记载出发,探讨了周代的史官设置与职能,以及史书的教化和鉴戒作用。 可以认为,《孔丛子》此论是有据可查的《国语》学史的开端。
4 余论
秦代的文化政策造成大量先秦典籍散佚不存,很多知识精英湮没无闻。 受这一大环境制约,战国时期非常活跃的儒家经学与诸子之学此时基本处于隐忍或蛰伏状态,但知识精英们传承文化之心未泯,遇到稍微合适一点的土壤,孕育已久的种子便会破土萌发,鲁壁藏书之举便寄托着他们不灭的希望。 而孔鲋放弃隐居山林,以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以博士之职为其宣讲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本是满怀期待,然时局变换,不久便身死军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顷刻之间便被倾盆之水浇灭。 即便如此,直到楚汉战争之时,仍有不少儒生坚守理想,“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45]他们所等待的,只是一个机会。 斗转星移之间,刘邦建立了西汉帝国,天下重归一统。 尽管刘邦不好儒家,但毕竟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于是“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46]困境迷茫之中的百家之学迎来了转机。儒家学说尽管没能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但形势已经大有改观,“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 就连刘邦本人也意识到叔孙通所言“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之理,用其制礼,然后“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47]在此背景之下,汉初的经学得以恢复与发展。
在战国末年经秦至汉初的《春秋》学存续过程中,张苍无疑是继荀子之后最重要的传承人之一。 据前文所引《史记·张丞相列传》所述,张苍在秦时曾任柱下史,掌管“图书计籍”,后有罪亡归。 到刘项反秦战争时,张苍跟随刘邦入武关。刘邦称帝建汉后,张苍被封为北平侯,又曾任计相、淮南王相、御史大夫等职,是西汉初期的朝廷重臣。[48]张苍学识渊博,于儒家经典、黄老之术、天文历算等皆有成就。 对于张苍在《左传》学方面的贡献,可以大略包括两方面。 一是献书,《说文解字》卷十五上叙云:“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49]刘师培《左氏学行于西汉考》一文以为:“此西汉秘府有《春秋》古经及《左传》之始,盖在高帝之时。 故高祖之诏引其文,叔孙通之伦并才其说以制礼,下迨文帝诏书、武帝制令、哀帝封册,咸述其文。 汉廷有司,亦持以议礼。 此即张苍所献之书,亦即刘歆所谓‘《左氏春秋》,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者'也。 及成帝之世,陈发秘藏,以考学官所传经,欲立三传博士,胥君安以《左传》不祖圣人相驳,然成封孔子后,仍推迹古文,以《左氏》相明。 此均歆、莽以前《左氏》 行于汉廷之征也。”[50]汉高祖、叔孙通等人言论中所引《左传》之文,刘师培也有说明,可以参考。 二是著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历数孟子、荀子、公孙固和韩非之后有一句简单的描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51]《汉书·艺文志》有《张氏微》十篇,列于《春秋》家,有学者认为即张苍的作品。 又有《张苍》十六篇,列在道家类,当即司马迁所谓“历谱五德”之作,实际也与《春秋》经传有密切关系。
与张苍有学术渊源的贾谊,是汉初治《春秋》经传之学的另一代表人物。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言“苍传洛阳贾谊”,[52]后世学者基本认同此说。 然《史记》本传说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 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又说:“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文帝召以为博士。”[53]《汉书》本传沿袭《史记》,都没提到贾谊师事张苍,而是曾在吴廷尉(吴公)门下,且其入仕途也是得到吴廷尉的提携与引荐。 又,赵伯雄先生曾指出,张苍和贾谊二人在汉为水德或土德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倘张苍与贾谊真有师生之谊,似乎主张不应如此相左。”[54]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汉书·儒林传》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 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55]未把张苍和贾谊列为师承关系,而是并列叙述。 《史记》本传又云:“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56]则吴公之学传自李斯,而李斯与张苍同出于荀子之门,可见贾谊之师承虽然不是直接来自张苍,其学术渊源仍出荀子。《汉书·儒林传》 又云贾谊“为《左氏传》 训故”,[57]则是《左传》学史上较早的训释之作,可惜其著不存,无法见其详情。
简而言之,战国到秦朝时期的经学传授,主要存在两条线索。 一条是儒家各派之师承授受,如《七录》《经典释文·叙录》所载《左传》传承系统。 另一条则是孔子与历代孔氏之家学传承,由孔子始经子思乃至于孔鲋,对于儒家经典文献的保存以及经学的传承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春秋》经传之学,其源肇于孔子,在战国时期出现了分化,但各派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共同开发”先辈们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成为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各家皆可利用的思想资源。 秦代的《春秋》经传之学虽然受到文化政策的极大影响,但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张苍、浮丘伯、孔鲋等人均为传承与传播《春秋》经传之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代秦而立的汉代经学复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