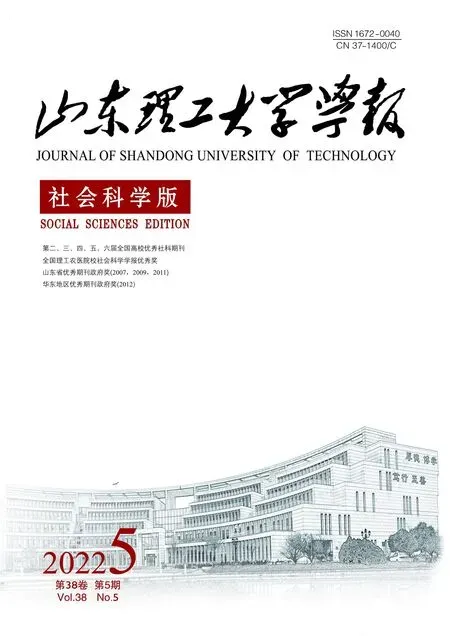“蒲学”献疑:张笃庆规劝过蒲松龄吗?
张 宇 声
长期以来,在“蒲学”界,凡涉及蒲松龄与其挚友张笃庆的关系时,有一种相沿已久的说法:张笃庆与蒲松龄的文学观念不合,对蒲创作《聊斋志异》不甚赞成,曾作诗加以“规劝”。此说几成定论,影响甚大,屡屡为人引述,同时也写进了文学史。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八编“清代文学”之第四章《聊斋志异》,即说:
蒲松龄自谓“喜人谈鬼”“雅爱搜神”。其挚友张笃庆康熙三年(1664)有《和留仙韵》,诗云:“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后来,张笃庆写给蒲松龄的诗中屡有“聊斋且莫竞谈空”“谈鬼说空计尚违”一类的句子,表明他这里引用张华故事,说“涪水神刀不可求”,也是寓规劝之意,意思是说“神怪之事”既虚幻不实,写来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也表明蒲松龄从青年时期便热衷记述奇闻异事、写作狐鬼故事了[1]。
文学史这一编的主编是袁世硕先生,《聊斋志异》这一章的撰稿也是袁先生。其实,追溯“规劝”一说的源头,也应该是出自袁先生所著《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一书的《蒲松龄与张笃庆》一文[2]。学术界陈陈相因的“规劝”之说,大多是从袁先生的这篇文章沿袭而来。因此,重新考察这一问题,不得不回到袁先生这篇文章。质疑这种“规劝”说,也就自然地有与袁先生商榷的意味。受袁先生影响而形成的诸家之论,为免枝赘,此文不作引述。
应该说,重新考索蒲松龄与张笃庆两人的交往,现在并无多少新材料可以使用,仍然是以蒲、张二人的诗歌往来为主。在此说明一点或有必要,引起我对蒲、张交往诗歌加以注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团队近三年在整理明清时期淄博的文献,其中就有张笃庆的《昆仑山房集》,而我承担这部集子的审稿任务,借以通读张笃庆的全部作品。阅读过程中,对其写给蒲松龄的诗歌格外注意,而且是带着先前由袁先生文章而形成的“规劝”之说作为理解前提来阅读的。在阅读过程中逐渐地产生疑问,感觉不是那么回事,才觉得有进一步仔细阅读、全面把握、深入思考的必要。这样重新考察的结果就是,所谓张笃庆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不理解,并从而进行“规劝”之说,似乎是靠不住的。
我们就首先看张笃庆作于康熙三年(1664)的几首诗歌。这一年蒲、张二人诗歌往来颇多,很能透露两人心迹。袁先生也很重视这一年两人的诗歌往来,作了很多分析。在分析这些诗歌之前,需要先了解这一年两人的行迹。
康熙三年,蒲松龄25岁,据路大荒《蒲松龄年谱》记载:“是年先生读书于李希梅家,时同课者先生甥赵晋石金人,作《醒轩日课序》。”[3]读书于李希梅家,见《醒轩日课序》的记载,而此序则非写于本年。
张笃庆本年23岁,其《厚斋自著年谱》记载:“春二月,余病牙痈几殆,五阅月始愈。”“春间,予患牙痈危甚,参戎岳玉野为调治,五阅月而平复”[4]。是本年张笃庆患牙病数月,其状甚痛苦。
张笃庆本年作《答蒲柳泉来韵》一诗:
迩来将遁世,闭户绝交知。君自神仙客,吾岂帝者师。(自注:来诗谬以子房相况)惊人怀谢朓,流水识钟期。不厌狂夫态,披襟共吟诗。
袁先生分析此诗首联谓:“首联显然表明,他们此时正由于科举失意,有点心灰意懒,甚至不好意思出门。”该说法虽有道理,但也不必尽然,还有另一种解释。蒲松龄的初应及再应乡试时间尚存争议,而张笃庆是于顺治十七年和康熙二年两应乡试而都铩羽的。即使作此诗之前一年两人应乡试不第,但两人都时值青年,正在积极地读书求进,一两次乡试落第未必就会如此情绪低落,以至有“遁世”“闭户”之想。结合本年张笃庆的处境,首联所说,是因为五个多月的患病,闭门在家,不得与朋友来往。此联不宜作过分引申,似乎不存在“心灰意懒”“不好意思出门”的潜在心境的表达。
“君自神仙客”的颔联,是袁先生重点分析的诗句。“吾岂帝王师”一句,有张笃庆的自注,可知蒲松龄来诗中以汉张良喻张笃庆,正如袁先生所精当分析的,是“勉励他努力进取,将来必能建功立业之意”。至于上句的分析,袁先生颇费斟酌,推测说:“蒲松龄并非黄冠羽士,也没有要出世的打算,不仅年轻时代,直到老年也没有。张笃庆何以称蒲松龄自是‘神仙客’呢?可能的解释,恐怕只能是蒲松龄好谈神仙怪异之事,如他后来在《聊斋自志》中所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我并不完全同意袁先生的推测,认为与诗意不算贴切。此两句可能与两人名字相关,此点王光福已先我提出,极有见地,惜未稍加分析[5]。众所周知,蒲氏字留仙,字中有一个“仙”字,故张可以“神仙客”称之。还可更进一步考虑的是,即蒲氏名与字的联系问题。蒲松龄何以字留仙,来源何处?有何关联?此事未见国内学术界有人论及。此事萦绕于心多年,尚不得真解。我现在的看法是,蒲氏名与字的联系也在汉张良这里。张良封留侯,是为“留”之出处。张良成就功业后,从赤松子游,追慕神仙,是为“仙”之出处,而赤松子又契合“松”字。“龄”字则为其辈分,其兄弟即名“柏龄、鹤龄”,蒲氏也常常自称单名为“松”,而从不单称“龄”字。与蒲松龄同时的无锡著名诗人秦松龄,亦字留仙,二人同名同字,显然同一出处,都是与汉张良有关①此文写成后,方读到有文章介绍新加坡《振南日报》1915年12月16日刊无方撰《蒲松龄与秦留仙》一文,谓蒲、秦二人同名同字,“均从留侯赤松之典,取义无疑”。具体参见李奎、吴美龄《新马汉文报刊所载〈聊斋志异〉相关资料辑补续》,载《蒲松龄研究》2018年第4期,84-89页。。这一联张笃庆借蒲氏来诗中以同姓张良借喻自己,也顺带地用蒲氏的字来加以回应,一典双关,实为巧妙。以同姓古人指代对方,这是明代以来诗人作诗习用的方法,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一书中曾专门论及,蒲、张二人都是沾染此种风气者。如此来理解,这一联的寓意似乎不必深求,“神仙客”一词未必是指蒲氏“好谈神仙怪异之事”,也谈不上两人在爱好、趣味上有什么不同。至于诗歌最后四句,颈联以“谢朓”代指蒲氏诗才,以“钟期”喻两人知己,末联照应开头,写自己虽然因病“闭户”,但读蒲氏来诗,依然狂态复萌,兴致盎然地吟诗作答。全诗首尾照应,浑然一体,语意完整。诗歌反映了两人的友谊与共同的诗歌爱好,尚看不出与《聊斋志异》的写作有何关联,也看不出两人在个人爱好上有何差异。
张笃庆作于同年的七律《赠蒲柳泉》二首,一向不受人们重视,袁先生也未加引述。其二之颔联颇值得注意,即“买得黄金铸少伯,朅来紫玉饰干将”。上句“少伯”指越国范蠡,字少伯,助越王勾践灭吴,飘然归去。越王思之,以黄金铸其像置于身侧,事见《吴越春秋》。但此处用典,我颇疑是指唐诗人王昌龄。王也字少伯。“黄金”借用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第八首:“论诗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只是将黄金所铸者移为以“七言长城”著称的王昌龄。如此移改,除了作诗对仗的因素外,或有“龄”字与蒲氏名字相关联的原因。下句“紫玉”出自《搜神记》的“吴王夫差小女”一节,“干将”出自同书之《干将莫邪》篇,一句两典,均出自以志怪著称、且为蒲氏所有意效仿的《搜神记》一书,或非偶然。“朅来”有“何来”之义。两句大意是指蒲氏本来崇拜王昌龄,有作诗之才;何为效仿《搜神记》作记载“紫玉”“干将”的志怪之事。这两句诗倒是隐约透露了蒲氏的志怪情趣,甚至还有据此证明蒲氏此际有可能已开始创作《聊斋志异》。但诗意在称道,对蒲氏毫无不理解、不满意的意思,更无“规劝”之意。
袁先生最看重的、并得出不赞成乃至“规劝”之类结论的诗,是这一年张笃庆写的《和留仙韵》二首,主要是第二首,诗云:
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刘。一时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
这里应先说明一个问题,“应刘”一词,袁先生文中作“应侯”,查中科院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所藏张笃庆《昆仑山房集》,均为“应刘”,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袁先生抄录之误,但后来学者引述此诗,均沿袭此误作“应侯”。“应侯”不通,“应刘”出自曹丕的《与吴质书》,指建安诗人应瑒与刘桢。另外,关于“涪水神刀”一典,已有刘洪强考出为三国时铸剑师蒲元之典,与《博物志》之“多记神怪事”不应混为一事[6]。其实,蒲松龄有《呈树百》一首七律,末联为“我有涪洼刀百炼,欲从河海斩长鲸”,也是用蒲元之典,赵蔚芝先生《聊斋诗集笺注》早已注出这一典故[7]。至此,关于前两句的解释焕然改观,与一直以来的理解大相径庭。这两句又是用同姓古人作比的例子,上句张华指张笃庆自己,下句“涪水神刀”一典用蒲元代指蒲松龄。上句写自己是能著书的风流之人,下句写蒲氏是擅长著述的“神刀”之手。此句“不可求”三字,也要正确理解,不可草草放过,有些解说不得要领,未中肯綮。此三字一要结合上句自注:“多记神怪事”,二是要上下句结合起来理解。两句意谓:我也似晋张华那样,有写《博物志》“多记神怪之事”的能力,但要像蒲氏淬炼“神刀”一样的技艺则不可能达到,“不可求”者,找不到这样的才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地也。如不这样上下句合起来理解,自注之“多记神怪事”没有着落,上句之“本风流”之“本”字也无着落。这样,袁先生所说:“张笃庆这里用张华事,而且‘涪水神刀不可求’句‘不可求’三字,显然含有一定的贬意,至少是不赞成。”又说:“联系前面《答蒲柳泉来韵》‘君自神仙客’句,可以认为是指蒲松龄喜欢谈鬼说狐,意在表示他是不赞成蒲松龄把精力用在这种虚幻不实、荒诞不经的东西上。”我们的理解与解释就完全与之不同,这两句不但没有“贬意”或“不赞成”,反而是极力推崇,自惭不如,对蒲氏写作“神怪”之举更是毫无“规劝”之意。应该说,袁先生得出张笃庆“不赞成”《聊斋志异》写作、并进而得出“规劝”之结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这两句诗的理解与解释上。我们作出新的解释,如能成立,则“规劝”之说的立论基础就拆掉了一半。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袁先生根据此诗这两句和《答蒲柳泉来韵》“君自神仙客”一句,得出一个推断说:“张笃庆这两首诗颇值得重视,它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蒲松龄从二十多岁时起就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刘洪强在发掘出关于“涪水神刀”的资料后,认为此诗不能用于证明蒲氏此时已开始创作《聊斋志异》。我的看法是:“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两句,再结合上文提到的“朅来紫玉饰干将”一句,的确可以证明袁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张笃庆知道此时蒲氏已经开始创作《聊斋志异》,而且对蒲氏“记神怪之事”的才能很是推崇,在《聊斋志异》创作的初期即极为首肯。
这首诗的颔联“君自黄初追正始,我从邺下识应刘”两句也需要重新作一些解释。袁先生认为这两句:“这意思是你蒲留仙以黄初、正始为宗,我是师法建安七子的。”王光福则以为此两句为钱钟书所称之“丫叉句法”,即本联上句承接首联的下句,下句承接首联的上句。而我则认为这两句是互文,表述两人共同的诗歌追求,即你我都学习汉魏诗歌,具体地说就是学习“建安七子”。这两句的“黄初”“正始”与“邺下”“应刘”,几乎同义,无大差别,这里面看不出如袁先生所说的“两人在举业之外的文学志趣之不同”。考察张笃庆全集不难看出,他的诗学观念是推崇“明七子”,特别是“后七子”的首领人物李攀龙,他不时地写诗致敬李攀龙,这种学习建安文学的观念与“明七子”“古诗学汉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前面说将“司空博物”“涪水神刀”的理解厘正以后,“规劝”说的立论基础就拆掉了一半。但还有另一半,就是“说鬼谈空”,这涉及张笃庆写给蒲松龄的另外几首诗。
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张笃庆有《寄留仙希梅诸同人》一首,诗云:“清明时节杏花风,有客南来类转蓬。驽马自惭过冀北,神鱼终羡奋天东。故人诗酒迟经岁,海国文章赖数公。此后还期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诗末两句最容易让人发挥,袁先生即云:“所谓‘努力’,就是要努力研讨时艺,争取乡试中试。下句显然是劝蒲松龄不要再写《聊斋志异》了,用‘谈空’二字,比起说‘涪水神刀不可求’,就更明显地是极言其无意义。”但理解或有不尽然者。其一,“聊斋”是蒲松龄的斋号,是否等同于《聊斋志异》一书?若是斋号,即指蒲松龄本人。其二,“谈空”是用典,本指魏晋清谈,也指佛教义理探讨,是否等同于写作《聊斋志异》?唐诗中用“谈空”者,如李端《慈恩寺怀旧》之“篮舆来问道,玉柄解谈空”,如孟浩然《游明禅师西山兰若》之“谈空对樵叟,授法与山精”,都是指清谈义理,并无著述之意。故“谈空”不能等同于写作《聊斋志异》,更无指责其虚幻不实之意或“极言其无意义”。写此诗时,张笃庆正入国子监读书,预备参加顺天秋闱,对科举抱有极大之信心,他通过此诗鼓励大家一起“努力”,目标正如袁先生所说“争取乡试中试”。且诗题中尚有李尧臣及“诸同人”,即郢中诗社的诸社友,如此情况下,就不会单挑出蒲松龄来,劝说其著书无益。
相同的情形还有写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寄蒲留仙二首》,主要是第二首,诗云:
谈鬼谈空计尚违,惊人遥念谢玄晖。老来更觉文章贱,贫病方知雅道非。同学故人萧屑甚,一时遗老姓名稀。床头吏部今何在,痛哭西州掩泪归。
“谈鬼谈空”一词,袁先生引文倒置为“谈空谈鬼”,此问题不大。省图藏《昆仑山房集》十六卷本作“说鬼谈空”,文字差别也不大,但究以“说鬼”为好。“说鬼”也是用典,典出《搜神记》卷十六:阮瞻持无鬼论,有客人与之争辩,为阮瞻所屈,情急之下,遂化鬼恐吓。此事也见于《晋书·阮瞻传》。这一典故张笃庆在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题聊斋志异卷后》三首其一中也用过:“常笑阮家无鬼论,愁云飒飒起悲风。”这一典故也可用苏轼“姑妄言之”的说鬼来解释,即《聊斋自志》中所谓的“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这里的“说鬼谈空”就可以说是指《聊斋志异》的写作。上一诗的“谈空”单用与此处的与“说鬼谈空”连用似乎不同。盖上诗是写给“诸同人”的,此首是单独寄赠蒲氏的。上诗“谈空”词意宽泛些,难以坐实;此处“说鬼”词意具体,可以指认。再加《题聊斋志异卷后》一句的佐证,可以认定“说鬼”即指《聊斋志异》的写作。但“计尚违”是何义?此处的“计”不是指写作《聊斋志异》的行为,而是指一生谋求考试中举的打算。张笃庆另有《寄柳泉希梅六首》组诗其四云:“非是甘丘壑,青云计未成。”“计尚违”之计,就是“青云计”之计,是谋科举进身之计,“计尚违”即是谋身之计未能实现,是叹惜时命不佳,科举无成。“说鬼谈空”与“计尚违”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能理解成因为“说鬼谈空”而导致“计尚违”;而恰恰是转折关系,是叹惜有“说鬼谈空”之才华,却造化弄人,而偏偏“计尚违”。这诗正如袁先生所说:“前四句是同病相怜,抒写两人共同的怀才不遇的牢骚,见得其心情也是凄苦的。”但袁先生转而又说:“然而,首言‘谈空谈鬼计尚违’,意思是蒲松龄耽于写狐鬼故事,是失策的事情,这不是和三、四的牢骚语不相协调了吗?”将“计尚违”理解成著书《聊斋志异》的“失策”,并不符合诗的原意。大概袁先生时时有“规劝”之意存于心中,故作此曲解,因而感觉诗意不顺。其实,正因为一生科举之“计尚违”,才有“文章贱”“雅道非”之“牢骚”,才有“心情凄苦”,诗意通畅,其间又何尝“不相协调”呢?
关于这首诗,也附带说两点。一是“惊人遥念谢玄晖”一句,与前引《答蒲柳泉来韵》一诗的“惊人怀谢朓”一句完全相同,都是以谢朓喻蒲氏,典故出自唐冯贽撰《云仙杂记》:“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用此典借以表达对蒲氏诗才之佩服和两人倾心相交之情感。二是关于“床头吏部”,袁先生解释:“是用高适《醉后赠张九旭》诗‘床头一壶酒,再能几回眠’句意,借指蒲松龄馆东毕际有。”其实“床头吏部”的典故出自《晋书·毕卓传》,卓“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8]1381。此典亦见《世说新语·任诞篇》刘孝标注引《晋中兴书》。可见用同姓古人借指时人,是张笃庆常用的手法。
依然是说“说鬼谈空”,接下来要解说的一首诗或许较难以辩解,即张笃庆写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岁暮怀人诗》组诗中怀念蒲松龄的那首:
传经十载笑齐伧,短发萧萧意气横。八斗雄才曹子建,三升清酒管公明。谈空误入《夷坚志》,说鬼时参《猛虎行》。咫尺聊斋人不见,蹉跎老大负平生。
这首诗写出了对蒲松龄老大不遇的叹惜与伤感,充满真挚的同情,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作者本人的切身感受,可谓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张、蒲二人的遭际真是太相似了,都是长期坐馆,所谓“传经十载”,都是屡试不第,被人讥为“齐伧”(齐地之鄙夫),都可以说是“蹉跎老大负平生”。“八斗雄才”一联,虽然是称道蒲氏,但也可以说同时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意气纵横。袁先生称这首诗“情真意切”,是极为精微的体会。但对后两联的解释,袁先生却说:“然而,后四句仍然是对蒲松龄作《聊斋志异》表示不以为然。虽然他也看出蒲松龄‘说鬼’有揭露苛政等方面的内容、意义,但用了‘误入’二字,就把蒲松龄‘蹉跎老大’,归因于‘谈空’‘说鬼’,作《聊斋志异》了。”这里我们不禁又发出“何所见而云然”的疑问。我们不能割裂“谈空”一联的完整意思,单独解说“误入”一词。全联的意思大概是:本来是作说理的文字,却成了《夷坚志》志怪的写法;而说鬼的故事中,却结合了古乐府《猛虎行》的诗意。这样理解,又何尝有指责,又何尝有贬义,完全是褒扬、称道的语气,怎么能得出对创作《聊斋志异》“不以为然”的意思呢?怎么会产生“说鬼谈空”与“蹉跎老大”之间有因果关系的理解呢?这里也要说明两点,一是提到《夷坚志》,可能是受到了蒲松龄早年所作《感愤》诗中“新闻总入《夷坚志》”一句的影响。二是《猛虎行》是乐府诗题,乐府歌辞尚在,且有后来陆机、李白等人的拟作。这里的引诗我特意加了书名号,以见对仗工整。袁先生引诗未加书名号,且在释意中有“揭露苛政”的说法,大概是将其理解成“苛政猛于虎”之意,这也是一个小疏漏。另外,写作此诗时,张笃庆已53岁,蒲松龄是55岁,《聊斋志异》早已结集,高珩与唐梦赉早已作序,此时还对创作《聊斋志异》表示“不以为然”,这也是不合情理的事情。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简单地看看张笃庆写的《题聊斋志异卷后》三首诗,袁先生考证这三首诗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这是完全正确的。诗其一中间两联为:“五夜燃犀探秘箓,十年纵博借神丛。董狐岂无人伦鉴,干宝真传造化工。”称赞《聊斋志异》一书如温峤燃犀,烛照鬼神,十余年的倾情创作,广搜博览,从秘籍中探取,如有神力借助。这种书真如干宝《搜神记》,不只是笔传造化;真可称为“鬼董狐”,而且借鬼神故事,表达“人伦鉴”,富有教育意义。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评价。其三颈联为:“琅嬛洞里传千载,嵩岳云中迸九华。”这也是称赞《聊斋志异》如道教福地琅嬛洞的秘籍,足以流传千载;如道教圣地嵩岳山中迸发的神奇之花,直可光耀一世。这都是无以复加的赞誉之笔。相信张笃庆的这种赞美是发自内心,并非只是虚与应付之语。袁先生虽然承认这些诗是“赞扬其有功于人伦,文笔足千秋”,但又表示“常笑阮家无鬼论,愁云飒飒起北风”之类诗句,是指《聊斋志异》写得太虚,是表示“心里并不赞同”。“阮家无鬼”典故前边已讲,这两句的意思是:看《聊斋志异》,感觉阮瞻的无鬼之论有点可笑了,书中的鬼怪故事读起来简直有“愁云飒飒”“悲风萧萧”之感。这是称道《聊斋》文字的感染力之大,能引人入胜,令人身临其境,这里何尝有“虚实”之问题?岂能读出“并不赞同”之意?更有甚者,袁先生特意抓住第二首末联,说:“诗中还是流露出了两句颇有点煞风景的话:‘君自闲人堪说鬼,季龙鸥鸟日相依。’这不就是说写这类鬼狐故事,只有闲散的人才能做,非闲散的人就无法、也不屑为之了吗?看来,他还是把诗才看作文学正宗。”感觉袁先生抓住“闲人”一词,引申过重。其实“闲人”也可以解作恬淡之人,有闲情逸趣之人,并非纯指闲散或闲来无事。特别是“季龙鸥鸟”一典用得颇为深曲,值得疏通。“鸥鸟”一典本出《列子》,多指不存机心,但张笃庆此处用典非出《列子》,乃出《晋书·佛图澄传》,见《晋书》十六卷“艺术类”。“季龙”是十六国后赵皇帝石虎的字,石虎父子奉天竺僧人佛图澄为国师,尊为“大和尚”。“支道林在京师,闻澄与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龙为海鸥鸟也。’”《晋书》记佛图澄“能役使鬼神”,本卷末之赞语又称佛图澄:“澄乃驱役鬼神,并通幽洞冥,垂文阐教,谅见珍于道艺,非取贵于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8]2487,2485,2504张笃庆用此典,是将蒲松龄比喻为佛图澄一样的人物,能“役使鬼神”,并“垂文阐教”的。如此再反观“闲人”一词,也有得一新解之可能。佛图澄是佛门人物,又是后赵国师,而蒲氏则是乡野人物,与佛图澄相比,自是“闲人”。此说或许迂曲,不知当否,说出以求教于方家。如此理解,这两句就毫无讥讽之意,更无“煞风景”之感。总结张笃庆三首题辞,全为称道之词,不存任何话外之音,几乎可以断言。关于张笃庆推崇《聊斋志异》,还可以补充一个不常为人引用的例证,即《次蒲柳泉来韵》一诗之第三联:“洗耳怜余归隐暮,回头愧尔著书多。”诗写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这“回头愧尔著书多”,不就是指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写作吗?不正是由衷表示钦佩吗?是相形之下觉得自己比不上蒲氏而感到惭愧。我们似乎不应怀疑古人“修辞立诚”之心,将这些看作应付之语、客套之话而不加以认真对待。以张笃庆与蒲松龄这种挚友关系,在交往酬赠的诗歌中暗存讥讽,皮里阳秋,是不符合古人交友之道的,当为宅心仁厚的张笃庆所不取。
总之,我们将张笃庆写给蒲松龄、并与写作《聊斋志异》有关的一些诗歌重新作了疏解,做出了很多与袁先生不同的解释,意在说明从中全然看不到张笃庆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有不理解、不支持,并加以“规劝”之意。如果所解不谬,蒲学界长期以来流传的、几乎成为定论的“规劝”之说应该终止,文学史上的这一结论应该得以修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还古人张笃庆一个公道。
最后说明一下,袁先生是我的大学本科授业老师,也是学界公认的大师,我无意悖逆师教,也无意挑战权威,不存“蚍蜉撼树”之狂妄,只作无愧于心之表达。是耶非耶,愿聆批评;知我罪我,一并担承。西谚“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句,或可成为我的遮羞之布与挡箭之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