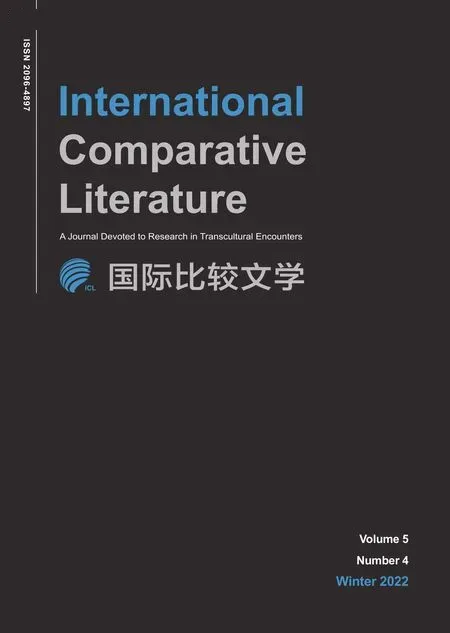在民族国家、文学与学术之间:比较文学史回溯及反思*#
姚孟泽 南开大学
引言
重视历史是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优良传统。自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兴起以来,几乎每一部教材中都有专门的学术史章节,而且还出现了多种专门的学术史著作,共同建立起了一种相对稳固的历史叙事。概括起来,这一叙事以“学派”和相应方法的更迭为内在线索,记载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欧洲萌芽、法国确立、美国发展到中国繁荣的过程,具有体系严明、逻辑清晰、板块完整和易于教学的特点。由于这种学术史格外强调“学科”的身份,并且也主要是在“学科”内部进行历史叙述,因此可以被称为“学科史”。可以说,学科史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概论”中最“基本”的知识。然而,也正是因为其“基本概论”的身份,学科史研究在近十年来陷入了停滞状态。的确,经过40年的累积,尤其是在已有几部学科“通史”之后,“基本概论”已基本无需再论,即便再论,也不可能成为“前沿问题”。在既有的模式之下,继续开拓的空间不大,能够做的看起来也主要是填充细节和续写新时段,似乎很难再做出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价值的成果。
实际上,这种学科史模式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既有的学科史叙事十分简略,很多教材和专著中的学科史内容存在大量简单重复和转引转述的现象。尽管学界对于学科史上关键节点、代表性学者及其代表性言论早已烂熟于胸,但对除此之外更多的学术观念与实践了解并不多;其次,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信息作为依据和语境,学界对以上内容的理解难免有误读或误会;再次,这种学科史往往有意无意地割裂了学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也导致了对真实历史的忽视或误读;最后,或许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学科”本身是一种在学术史上迟来的建构之物,因此以“学科”为框架来框定学术史就带有浓重的理念先行和目的论的色彩。挪用王国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一语来说,这种简明整齐的学科史成为了只在课堂和考试真空中存活的“可爱而不可信”的知识——它固然易于讲解和考察,但与真实的研究实践日益疏远,更无法为学科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作为更大的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比较文学所依傍的文学观念和学术意识处于不断的互动和变化之中,作为实践者的学者也并非生活在“学科”之中的人,而是具有多样的文化经验和政治意识的“社会人”。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线性的学科现象史,而是将实际的学术观念与实践归置到大历史中去综合理解的“超学科”的学术史,是更加关注细节和深度(而非体系与理论)的问题史,以及更加关注知识背后之社会动因及知识之社会影响的知识社会史。当然,这远非一篇论文力所能及之事。本文的目的,是在上述思路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放置到不断变幻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学术语境之中,以比较文学与民族国家、文学和学术这三种要素持续的协商互动为入口,为理解比较文学学术史提供更为开放和有效的描述方式,以利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一、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学的双重发现:18-19世纪文学比较意识的萌发
若要讲述比较文学学术史,不必回到古希腊对古代东方文化的吸收,或者是古代中国对印度佛经的翻译,而是需要回到那个“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被发现的历史时刻。这是因为,人们有意识地进行文学比较,是从普遍意识到不同的民族文学存在价值开始的。今人已经习惯把“民族文学”当成是自古有之的天然之物,而且是“世界文学”的前提和基础。但从观念史的角度看,这恐怕只是现代人以今视昔所导致的视差效应之一。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用拉丁文写成的文学就是普世的文学(universal litera‐ture);对于17-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法语文学成了新的普世文学。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1939)中提到,在17-18世纪的德意志,上层人士普遍认为德语是僵硬笨拙的,以至于说法语被当成“有教养”的标志,甚至就连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又称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1740-1786年在位)都认为,德语是“半开化的语言”,深受德意志下层百姓所喜爱的莎士比亚戏剧是野蛮低下的,只有法语和法语文学才是高尚的典范。1(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8~13 页。[Norbert Elias,Wenming de jincheng:wenming de shehui fasheng he xinli fasheng de yanjiu(The Civilizing Process:Sociogenetic and Psychogenetic Investigations),trans.WANG Peili and YUAN Zhiying,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3,8-13.]这里有两个关键点需要稍加解释。第一点,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也就是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等带有艺术特性和可供审美的作品)相比,当时西方主要语言所谓的文学含义要宽泛得多,还包括学术研究、历史、神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文本,以及关于文本的学术研究和知识。2关于西方“文学”含义的演变,可以参看(美)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中的相关讨论。见《辨异:续〈批评的诸种概念〉》,刘象愚、杨德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37 页。[René Wellek,“Bijiaowenxue de mingcheng yu shizhi”(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Bianyi:xu piping de zhuzhong gainian(Discriminations: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trans.LIU Xiangyu and YANG Deyou,Shanghai:Shangha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2015,7-37.]第二点,腓特烈大帝对德语的贬低和焦虑表明,一种民族意识和不同民族间的比较意识正在萌发——这在比较文学学术史上非常关键。
腓特烈大帝在此将我们带向了比较意识萌发的历史时刻,也就是18-19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前后。在18世纪的法国文学之外,英语文学和德语文学实际上都逐渐发展起来了,而且正在逐渐被本国之外的知识阶层看到。例如,在1726-1729年,伏尔泰(Voltaire)流亡英国时,观察到英国与法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的巨大差异,写作了一系列关于英国政治、宗教、哲学和艺术的文章,并于1733年以英文、1734年以法文分别结集为《英国通信》和《哲学通信》出版,使法国人第一次系统接触到了英国社会和文学文化,对法国启蒙运动影响巨大。另外,在腓特烈大帝时期的德意志地区,也出现了诸如康德、莱辛、歌德和席勒等文化巨匠。其中,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在法国引发了“维特热”。与此同时,在德语中,一个崭新的概念出现了,那就是民族/国家文学(Nationalliteratur)。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中谈论这一概念的起源时说:“Nationalliteratur(国家文学)的概念从1770年代开始在德国发展出来。[……]‘一个国家’拥有‘一种文学’,这种意涵标示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发展,也许也标示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3(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71页。[Raymond Williams,Guanjianci:wenhua yu shehui de cihui(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trans.LIU Jianji,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5,271.]
这里所说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主要就是民族国家的生成、民族意识的发展和不同民族文化界限的显影。“民族”和“民族国家”作为今天国际社会(国际,interna‐tional,也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的基本单位,已经主宰了我们认识现实和历史的方式。但仍需明确的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并不主要是按照民族来认识自身和区分彼此的。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在其《历史的运用与滥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2008)中说道:“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出现得非常晚。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欧洲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英国人(也不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或威尔士人)、法国人或德国人,而习惯认为自己属于某个特定家庭、宗族、地区、宗教或行会。有时他们会以他们的领主来划分自己的身份界限,无论标准是当地的男爵还是君主。后来,当他们开始称自己为德国人或法国人时,他们不仅认为这个身份是一种政治差异,更看重其文化上对不同民族的区分。”4(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孙唯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08~109 页。[Margaret MacMillan,Lishi de yunyong yu lanyong(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trans.SUN Weihan,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21,108-9.]正是在这种“文化区分”的意义上,普遍的民族间文学比较意识开始萌发,关于不同民族文学的讨论在欧洲大量出现。
例如,在德国,施莱格尔兄弟和莱辛等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了不同民族(如英、法)和文化(如古希腊、古罗马和现代法国)文学的比较。在法国,最为著名的就是斯达尔夫人(Germaine de Staël)的代表作《论文学》(De la littérature,1800)和《论德国》(De l'Allemagne,1810/1813)。例如,在《论文学》中,斯达尔夫人关注不同民族文学的特色,对自古希腊以来的各种文学进行了对比,并探讨了差异背后的地理、文化、种族和时代精神等方面的成因,对后来法国比较文学的出现产生了影响。5(法)斯达尔夫人:《论文学》,徐继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Germaine de Staël,Lun wenxue(On Literature),trans.XU Jizeng,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6.]她还特别强调了语言文化作为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也曾经出现在德国学者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772)之中。赫尔德通过论证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内在关系,强调了各个民族文化和文学的特色,以及诸如神话、传说、民歌和民族史诗等文学样式的独特价值。6(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Johann Gottfried Herder,Lun yuyan de qiyuan (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trans.YAO Xiaoping,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9.]不过,尽管斯达尔夫人和赫尔德都强调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和民族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初步的文学比较,但双方的意图有根本性的差异:在斯达尔夫人那里,比较意识被用来消解法国文学的普世性和优越性,而在赫尔德那里,比较意识最终将导向对自身民族优越性的肯定。
赫尔德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然而,在赫尔德身后,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类似的呼喊最终朝着更加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了。前面说过,在18世纪,法语和法语文学被德国上层社会视为典范。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德国知识分子对于大革命和催生大革命的启蒙思想主要持欢迎态度。然而,随着大革命而来的拿破仑战争改变了一切。美籍德裔历史学家格奥尔格·G.伊戈尔斯(Georg G.Iggers)指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导致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崛起,具体表现为:(1)启蒙运动对于普遍适用的道德与政治价值的信仰被完全打碎:“德国受过教育者的观点都同意一切价值和权利都是有历史和民族根源的,外国制度不能被移植到德国土壤中”;(2)民族概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在“1812-1813年冬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德国历史学家——引者注)对战争的充满诗意的界定中,德意志祖国将被发现是在那些‘每一个法国人被称作敌人,而每一个德意志人被叫作朋友的地方’”;(3)国家占有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地位:“赫尔德在1784年写道:‘无法理解人是为了国家而形成的。’……1792年洪堡(德国历史学家——引者注)以非常类似的语言指出国家权力有局限性……但是到1813年,他开始把‘民族、人民和国家’相等同”。7(美)格奥尔格·G.伊戈尔斯:《德国的历史观:从赫尔德到当代历史思想的民族传统》,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7~49 页。[Georg G.Iggers,Deguo de lishiguan:cong heerde dao dangdai lishisixiang de minzu chuantong(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trans.PENG Gang and GU Hang,Nanjing:Yilin Press,2014,47-49.]
在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潮中,一种新的学术实践——民族语文学(national philology)——出现了。美国学者苏源熙(Haun Saussy)曾回顾这一段历史道:“自1800年起,语文学的各类学科风靡欧洲,使人们能够阅读各种语言写成的文本……人们细细研究……史诗的神话和历史渊源,并且探询对把这些史诗作为自己民族起源和文化‘遗产’的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格林兄弟的《德意志语法》(The Deutsche Grammatik)和《德意志神话》(Deutsche Mythologie)创造了一种‘德国性’作为文化遗产,这种德国性不是通过政治手段达成的。以法德为轴线的民族敌对状态尤其严重,这样的民族敌对状态使得学者成为英雄。”8(美)苏源熙:《新鲜噩梦缝制的精致僵尸:关于文化基因、蜂房和自私的基因》,陈琦等译,见苏源熙编:《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0 页。[Haun Saussy,“Xinxian emeng fengzhi de jingzhi jiangshi:guanyu wenhuajiyin,fengfang he zisi de jiyin”(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trans.CHEN Qi et al,in Quanqiuhua shidai de bijiaowenxue(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ed.Haun Sauss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9-10.]这些学术实践,推动了后来德国式的比较文学主题学和民俗学的发展。也就是说,在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民族危机中,明确民族界限和凸显民族独特性的文化政治需求,成为了德国的文学比较意识发展的动机之一。然而,当民族独特性被过分强调时,比较文学也就无法展开了。到了20世纪上半叶,德国民族主义愈发朝着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蜕变,需要跨国研究的比较文学不仅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还成为被国家高度规范的知识禁区。9Oliver Lubrich,“Comparative Literature—In,From and Beyond Germany,”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3,no.1(2006):49.
总而言之,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前后,在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学兴起的同时,文学比较意识随着新的民族界限的凸显而萌芽了。此时,尽管比较文学尚未成为一种学术实践,但作为比较文学之源头的语文学已经发展起来,为下一阶段比较文学的兴起定下了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学术基调。
二、跨越国界的文学史:19-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比较文学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Van Tieghem)说过:“人们说十九世纪是历史的世纪,这是再确切也没有了。”10(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7页。[Paul Van Tieghem,Bijiaowenxue lun(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trans.DAI Wangshu,Changchun:Jilin Publishing Group Co.,Ltd.,2009,7.]之所以会如此,是由于民族意识的发展不仅催生了民族文学,而且还催生了民族史学,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到的那样,“历史写作的时尚在19世纪上半叶风行欧洲。几乎不曾见过这么多人以坐在家中撰写大部头历史的方式,来理解他们的世界。”1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6 页。[Eric Hobsbawm,Geming de Niandai: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trans.WANG Zhanghui,et al.,Nanjing: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9,386.]需要注意的是,在19世纪民族语文学的意义上,民族史学和民族文学本身是融为一体的——对民族史的充分研究就等同于对民族文学(也就是一个民族所有的文本材料)的研究。反过来看,对民族文学的研究主要采取“文学史”研究的路径。塞萨尔·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等认为:“在过去的150年里,文学史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主要路径——这是德国浪漫主义的遗产,也是这种浪漫主义被民族国家概念的兴起所裹挟的结果。”12César Domínguez,Haun Saussy,and Darío Villanueva,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Abingdon &New York:Routledge,2015),3.
在民族意识的驱动和民族国家的建构需求之外,历史学取得自身的地位还需要依靠“科学”的权威保障。德国历史学家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指出:“在19世纪,历史书写的彻底民族化是同历史学科的职业化同步发展的。这种趋势产生的历史学家是整个欧洲民族建构的捍卫者,因为他们可以是有关民族过去的权威。在欧洲的历史编纂学中,历史主义的崛起是一种引导手段,它让‘科学的’威信进入历史书写这门学科,并使其实践者扮演了解释过去的特殊角色,进而使后者得以通过科学,掌握理解当下、预测未来的钥匙。”13(德)斯特凡·贝格尔:《民族历史的权力:19-20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书写》,《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斯特凡·贝格尔主编,孟钟捷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6 页。[Stefan Berger,“Minzu lishi de quanli:19-20 shiji ouzhou de minzu lishi shuxie”(The Power of National Pasts:Writing National History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Europe),in Shuxie minzu:yizhong quanqiu shijiao(Writing the Nation:A Global Perspective),ed.Stefan Berger,trans.MENG Zhongjie,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18,86.]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科学”虽然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但并非指“自然科学”,而是指一种求真和实证的专业化研究,它与建立在想象、感觉和个性基础上的艺术相对立,主要建立在大量“客观”证据和对证据进行可验证的阐释之上。在19 至20世纪之交执法国文学史研究之牛耳的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说过:“我们希望,在以某一学说或某一宗教的名义来评定博叙埃和伏尔泰以前,人们应该尽力认识他们,专心地收集尽可能多的真实可靠的知识,尽可能找出最大量的经过验证的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理想是描绘出无论天主教徒和反教权主义者都无法否认的一个博叙埃和一个伏尔泰,为他们提供一个他们也都承认是真实的形象,至于加上什么带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那就随他们的便了。”14(法)居斯塔夫·朗松:《文学史方法》,见《朗松文论选》,徐继增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 页。[Gustave Lanson,“Wenxueshi fangfa”(The Method of Literary History),in Langsong wenlun xuan(Selected Essays of Gustave Lanson),trans.XU Jizeng,Tianjin: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2009,3.]朗松对“真实可靠”和“验证”的强调,以及对中立客观知识的信心,鲜明地传达了他对于作为“科学”的“文学史”的理解。
这种科学化的历史学和文学史学,是19-20世纪上半叶法国比较文学诞生的学术母体。从19世纪20年代末开始,维尔曼(Abel François Villemain)、安培(Jean-Jacques Ampère)和沙勒(Philarète Euphémon Chasles,1789-1873)等学者先后开设了超出法国范围的文学讲座和课程,培育了比较文学的早期形态。在他们的教学中,法国文学与其他文学的影响关系,被放置到了历史考察和科学分析的核心位置上。例如,在“外国文学比较”(“The Comparison of Foreign Literature”,1835)课程中,沙勒将比较的目的设定为认识不同的民族精神、文明特征和创造能力等方面的历史,强调通过对大量的和确证的细节来研究“国家之间的行动和互动”,“过去的思想和行动对未来的影响”,并对作家在“伟大的思想巨链”中的位置和作用进行“化学分析”。15Philarète Chasles,“Foreign Literature Compared,”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The Early Years,an Anthology of Essays,ed.Hans-Joachim Schulz(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3),35-36.
这些课程和讲座还只是带有偶然性特征的比较文学雏形。到了19世纪末,法国的一些大学里开始设立固定的比较文学教席,先后由约瑟夫·戴克斯特(Joseph Texte)、路易-保尔·贝茨(Louis-Paul Betz)、费尔南德·巴登斯贝格(Fernand Baldensperger)、梵·第根、让-马利·伽列(Jean-Marie Carre)和玛-法·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等执掌,从制度上确立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存在。除了教席之外,还有专业的出版物标志着法国比较文学的确立和发展:1900年,由贝茨主编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书目(相当于比较文学领域的文献目录索引——在没有计算机和数据库的时代,这样的书目是专业研究的必备工具)(Bibliographi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出版;1902年,巴登斯贝格在贝茨书目的基础上出版了第二部书目;1921年,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创刊;1931年,第一部比较文学理论著作、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出版。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几位学者因师生传承关系而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学术观念和集团色彩,而且他们主要在巴黎的几所大学任职,因此被后来的一些美国学者称为巴黎学派或法国学派。
法国学派的观念,在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达。梵·第根对比较文学的概括是:“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的。”16(法)梵·第根:《比较文学论》,第4~5页。[Paul Van Tieghem,Bijiaowenxue lun(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4-5.]把这段话和前文所引朗松的那段话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梵·第根的比较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从属关系。梵·第根也是从这种从属关系来解释比较文学的——在本书的导言中,梵·第根用一种“诱敌深入”的方式引出比较文学:他从读者随意的阅读开始,讲到最初“享乐”的阅读,讲到欣赏与批评的阅读,进而讲到对一本书的文学史兴趣。在他看来,文学史研究是阅读的最高阶段,包括研究一部著作的“本原”(即前驱、源流和所受影响等)、“创世纪”(即从灵感萌发到出版的过程)、“内容”“艺术”和“际遇”(即读者接受、批评好恶和它对后来作品的影响等)。其中,关于“本原”和“际遇”的研究,也就是关于作家作品所受和所施影响的研究,“是超出所研究的原书本文以外的,它们单独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研究了”;而当这种研究超出法国文学的界限时,就走到了比较文学的领域。17同上,第1~10页。[Ibid.,1-10.]也就是说,在梵·第根看来:(1)比较文学要以事实为基础,是作为文学研究最高阶段的文学史研究的分支;(2)比较文学是对跨国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是对民族/国别文学史的延伸和补充。这也就意味着,此时的比较文学,尚且只是人文学术和文学研究中的边缘领域。
“二战”之后,梵·第根的这种比较文学观念开始遭到广泛的批判。这些批判的声音影响深远,以至于严重限制了后来人对法国学派的认知。但实际上,哪怕是批评法国学派“对‘事实’的要求已经不幸过时了”18Henry Remak,“Comparative Literature: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Method and Perspective,ed.Newton P.Stallknecht and Horst Frenz(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1),4.的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Henry H.H.Remak)也说过:“幸运的是:法国人在实践上远没有在理论上那样地胆怯和教条主义。对于法国和接受法国训练的学者来说,比较文学是各种比较研究中占分量最大的领域。”19Ibid.,5-6.的确如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这一点。首先,法国比较文学不只是有巴登斯贝格等传统上被标签为“法国学派”的学者,还有更多样化的实践。例如,在20世纪早期得到广泛翻译的洛里哀(Frédéric Loliée)的《比较文学史》(Histoire des littératures comparées des origines au XXe siècle,1903),是一部从各国文学互相关联和总体的视野所撰写的欧洲文学简史。又如,和梵·第根同为巴登斯贝格助手的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的《欧洲思想的危机》(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1680-1715,1935)和《十八世纪欧洲思想:从孟德斯鸠到莱辛》(La Pensée européenne au XVIIIe siècle,de Montesquieu à Lessing,1946)等著作,则是欧洲思想史的典范著作。其次,即便是巴登斯贝格和梵·第根等人的实际研究,也并不符合所谓“法国学派”的刻板理论或形象。巴登斯贝格的《歌德在法国》(Goethe en France:Étud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1904)是对歌德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史的研究,但其研究的出发点和旨归,都落在了如何理解歌德艺术和个性、进而如何在关系和对照中理解法德两种“民族精神”之上。梵·第根自身所从事的研究,与其说是他《比较文学论》中所规定的“比较文学”,不如说是“总体文学”。例如,他的《文艺复兴以来的欧美文学史》(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Europe et de l'Amérique,de la Renais‐sance à nos jours,1946),就是建立在文学关系之上的总体文学研究之典范。由于他在这部作品中并未完全着眼于事实关系的研究,还被美国学者维尔纳·弗里德里希(Wer‐ner Friederich)指责为“仅仅指出了不同文学体裁发展过程中迷人的相似(fascinating par‐allelisms),并未真正地着眼于持续的影响和接受(give and take),以及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引人深思的关联。”20Werner P.Friederich and David H.Marlone,Out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From Dante Alighieri To Eugene O'Neill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4),i.
可见,《比较文学论》等著作中的“理论”表述,严重地妨碍了人们对“法国学派”本身的认识。如果着眼于法国比较文学的具体实践,可以看到,所谓“比较文学”,实际上即指超出单一民族国家界限的文学史研究,而且可以被分为两个方面:(1)法国和其他国家(通常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的文学关系研究;(2)欧洲文学史研究(总体文学研究)。不过,历史地看,此时比较文学还只是一种法国的地方性学术,其学科定位较为边缘,学科界限较为明确固定,研究范围较为狭隘,研究方法和范式也缺乏足够的普适性。这是此一时期比较文学的特征,也是其最核心的缺陷之所在。
三、超越国家的西方文学学术共同体:20世纪中叶的美国比较文学
美国的比较文学课程最初设立于19-20世纪之交。但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美国比较文学都处于边缘和追随的地位,甚至在“二战”中和法国比较文学一道陷入沉寂。但在“二战”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比较文学在美国就成为了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美国也取代法国成为比较文学的中心。这一历史现象,使得学界经常将美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看作是对于法国比较文学的一次革命或断裂式的进化。然而,这种看法是经不起史料验证的。在1965年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学科报告(列文报告,The Levin Report)中,哈里·列文(Harry Levin)强调:“我们之所以能够从战后以来一步步发展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美国的文化多元主义,特别是对欧洲人和欧洲观念的接受能力。”21(美)哈里·列文:《列文报告——专业标准报告》,王柏华译,伯恩海默编:《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 页。[Harry Levin,“Liewen baogao:Zhuanye biaozhun baogao”(The Levin Report,1965:Report 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trans.WANG Bohua,in Duoyuan wenhua shidai de bijiao wenxue(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ed.Charles Bernheimer,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27.]这段话包含两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方面,美国比较文学界同法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其学者构成的多元化和非集团性,这也就决定着,所谓的“美国学派”,并不是像“法国学派”那样建立在相对一致的方法和观念基础上的方法论集团,而是一个松散多样的学者群。另一方面,美国比较文学与法国以及欧陆比较文学的联系,远比我们通常所认知的要多:美国比较文学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对法国比较文学的继承;甚至可以说,美国学派,首先建立在法国学派的美国化之上。
这种法国学派的美国化,非常典型地体现在被称为“美国比较文学的哥伦布”(le Christophe Colomb du comparatisme américain)22David H.Malone,“Introduction,” in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Other Addresses,ed.William J.DeSua,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0,xiii.的维尔纳·弗里德里希身上。1905年,弗里德里希出生于瑞士图恩,在瑞士伯尔尼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进行过学习。大学毕业后,弗里德里希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先后获得了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北卡罗莱纳大学(以下简称“北卡大学”)教授德语文学和比较文学,并以此为基地积极推动了美国比较文学的重生与发展。他之所以被称为“哥伦布”,主要是由于其在美欧两个大陆之间的接引角色,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美国比较文学的巨大贡献。弗里德里希在法国学习期间,与巴登斯贝格、让-马利·伽列和梵·第根等比较文学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成为了巴登斯贝格实际上的助手。同时,在学术观念上,他最为推崇巴登斯贝格的观念与实践,并称法国比较文学为“几乎完美的比较文学方案”23Werner P.Friederich,“The Cas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1915-1955) 31,no.2(1945):214.,希望以此为基础推动美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主导了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也就是比较文学史上著名的1958年教堂山会议——的召开,并使之成为了同时带有鲜明的弗里德里希个人烙印和战后美国印记的大会:首先,会议的主题被定为“美欧文学关系”,也就是弗里德里希个人最为关注的领域,以及传统法国比较文学范式的延伸;其次,凭借着自己的资历和声望,弗里德里希力邀约260 位学者参会,其中约有60 位来自美国之外,使得教堂山会议成为“二战”以后美国的第一场国际性的人文学术会议。由于1955年第一届大会的主题和参会人员都主要局限于欧洲内部,教堂山会议也成为了比较文学历史上第一场西方意义上的国际会议。24Diane R.Leonard,“Werner Paul Friederich:‘Christopher Columbus of American Comparatism’,”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7,no.2-3(2010):186-87.这场会议正式标志着美国成为了西方比较文学的中心,同时也标志着比较文学从一种法国的地方性学术领域发展成为了整个西方的学术共同体。
不过,也正是在这场会议上,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发表了引发广泛争议的报告——《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这篇报告往往被解读为“美国学派”的宣言,也就是在提倡一种不同于“法国学派”的另一种比较文学方法。然而,这种认识是不符合韦勒克本意的。韦勒克当然是不认可传统法国比较文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建立另外一种对立的和特殊的比较文学。他认为,“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只有一个研究对象:文学。”25René Wellek,“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284.也就是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被视为一种统一的研究对象,而不应该被划入“比较文学”和“非比较文学”之中。他进而提出:“除非将文学作为一种与人类其他活动和产品相区别的对象,文学研究不会在方法上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的问题,也就是美学的中心问题,以及艺术与文学的本质问题。”26Ibid.,293.所谓研究“文学性”问题,实际上就是对文本进行审美批评。韦勒克指出:“真正的文学学术关注价值和质量,而非呆板的事实。因此,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之间不应有区隔。”27Ibid.,291.也就是说,韦勒克想要的比较文学,并非是一种(不同于法国比较文学的)特殊的比较文学,而是建立在文学性和审美批评基础上的文学研究。事实上,很多学者也是如此来认识韦勒克及类似学者的主张的。例如,艾田伯(René Etiemble)在其《比较文学的危机》(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1966)一文中用“历史和批评”(histori‐cism and criticism)来区分两个“学派”。28René Etiemble,The Cri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trans.Herbert Weisinger and Georges Joyaux(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6),35.雷马克在《十字路口的比较文学:诊断、治疗与预后》(“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Diagnosis,Therapy,and Prognosis”,1960)一文中也指出:“比较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学术中的一部分,必然会受到大环境中已经持续了一两代人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激烈论争的影响。”29Henry H.H.Remak,“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Diagnosis,Therapy,and Prognosis,”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vol.9,ed.Werner P.Friederich and Horst Frenz(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0),1.
弗里德里希和韦勒克,代表了美国比较文学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坚持法国比较文学传统,一种是试图新建一种以文学性为核心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我们不能以此就确定,美国比较文学就是弗里德里希或韦勒克所主张的那样。朗松在讨论文学史方法时曾经提醒道:“我们通常总有个幻想,总把极端的事实当作最有代表性的事实。实际上,既然这些事实是极端的,那就是异乎寻常的,它们只是事态的强烈程度的某一极限,或是极大值的代表。”30(法)居斯塔夫·朗松:《文学史方法》,第26 页。[Gustave Lanson,“Wenxueshi fangfa”(The Method of Literary History),26.]这一提醒在学术史研究中同样适用。在弗里德里希与韦勒克这二者之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和多样化的观念与实践。德裔美籍学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就曾指出,美国比较文学家的观点覆盖了从索邦大学式(弗里德里希)到克罗齐式(韦勒克)的广阔光谱,因而无法被归约为单一的理论主张。31Ulrich Weisstein,“Influences and Parallels:The Place and Function of Analog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Teilnahme und Spiegelung:Festschrift für Horst Rüdiger,ed.Beda Allemann and Erwin Koppen(Berlin and 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1975),594.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律内尔(Pierre Brunel)等在《何谓比较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1983)也说过,美国比较文学的“出色特点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32(法)皮埃尔·布律内尔、(法)克洛德·皮叔瓦、(法)安德烈-米歇尔·卢梭:《何谓比较文学》,黄慧珍、王道南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5 页。[Pierre Brunel,Claude Pichois and André Rousseaux.He wei bijiaowenxue(What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trans.HUANG Huizhen and WANG Daonan,Shanghai: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1991,15.]这种多样性,也体现在亨利·雷马克著名的比较文学定义上。在《比较文学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 Literature,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1961)一文中,雷马克提出,比较文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超出一国限制的文学的研究”,二是“对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33Henry H.H.Remak,“Comparative Literature: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3.尽管雷马克的这个描述性定义并不准确,也受到如韦勒克和韦斯坦因等美国学者的批评,但它——以及那些美国学者并不同意它这一事实——的确反映出了美国比较文学远较法国比较文学多样这一事实。34实际上,法国学者并不否定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关系的研究。例如,文学史家朗松就有《文学与科学》的论文(见《朗松文论选》)[See Langsong wenlun xuan(Selected Essays of Gustave Lanson)]。反过来,美国学者也未必同意这种研究。韦斯坦因就说过,“这种观点[即雷马克主张文学与其他学科相比较的观点]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并且,由于无论是法国还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都不同意,它在我们学科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unique)的。”(See Ulrich Weisstein,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Survey and Introduction,trans.Riggan William and Ulrich Weisstein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3],27.)此外,韦勒克也曾经批评道:“雷马克先生却不得不作出某些人为的、站不住脚的区别,例如,研究霍桑与加尔文教的关系被称作‘比较文学’,而研究霍桑关于犯罪和赎罪的观念责备称作‘美国文学’,这类区别显然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雷马克的这一提法似乎是为一个实用的目的设计的,那就是,在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把某一论文的题目贴上‘比较文学’的标签,可以抵挡那些认为自己的学术领域受到侵犯的同事们的抱怨和攻击。但是作为一个定义,它却经不起仔细推敲。”(见勒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第23 页。[Wellek,René Wellek,“Bijiaowenxue de mingcheng yu shizhi”(The Name and Na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23.])
这种多样性,正是美国比较文学对法国比较文学的真正推动和发展。哈利·列文曾经将比较文学从法国到美国的发展概括为两个方面:(1)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大:法国比较文学主要关注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德文学关系,美国比较文学将时间延伸到更早和更近的时代,将空间延伸到西方与斯拉夫文学、乃至远东文学的文学关系上。(2)对“文学关系”的理解得到了更新:法国式的文学关系主要建立在影响关系之上,而美国比较文学将对文学形式、运动和价值也纳入考量之中。35Harry Levin,“The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vol.1,ed.Werner P.Friederich and Horst Frenz(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2),44.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以为,此一时期的美国学界将比较文学推进到了无远弗届的地位。虽然如列文所言,远东文学和文学形式等问题也被纳入研究的范围,但历史地看,当前整个美国比较文学的重心仍然是西方世界内部的文学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弗里德里希和韦勒克的比较文学观念南辕北辙,但他们在对比较文学在维护西方共同体的政治意义上却不谋而合。弗里德里希在解释西方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性时说:“年轻一代所需要的,是对所有西方文明的文化统一性、以及对我们伟大文学传统之间持续的和硕果累累的影响和接受关系的坚定认识。”36Werner P.Friederich,“Our Common Purpose,”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vol.4,ed.Werner P.Friederich and Horst Frenz(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55),58.与之类似,韦勒克从文学审美和价值教育的角度提出,比较文学“不仅有益于学生的审美和智识教育,而且也有益于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并至少是间接地培养他们对西方传统和作为公民以及人类的价值的意识。”37René Wellek,“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Gener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 2.3(1948):218.他们都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建设西方文学学术共同体的时代,而比较文学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比较文学在继承法国式的跨国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上,依托二战之后反思民族主义和重视文学价值的知识氛围,发展成为超越国家、但又主要局限在西方世界的文学研究,成为一种西方文学学术的共同体。
四、全球在地化与理论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国家与超文学的人文学术实践
1996年,在参与编辑《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逾三十年之后,亨利·雷马克以“创伤与胜利”(“Traumas and Triumphs:the Yearbook,1952-1990”)为题回忆这部重要出版物的历史。文章结尾,雷马克写到了《年鉴》 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的变化:新一代的学者开始承担编辑工作,新的理念和问题被引入到年鉴的内容里,但编辑之间却再难达成共识,以至于只好由不同的编辑各自决定每一本年鉴的主题。38Henry H.H.Remak,“Traumas and Triumphs:The Yearbook,1952-1990,” in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vol.44,ed.Gilbert D.Chaiti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7),134.
雷马克观察到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文学学术史一次大转向的表征。20世纪70年代,随着“越战”结束和反战运动、平权运动、少数族裔文化兴起和“冷战”边界松动等一系列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美国高等院校展开了对原有的知识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同时,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全球联系增强的背景下,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方法不断涌现,尤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和全球意识使得人们意识到一切文学和一切事物之间都存在可查的联系,因而原有的西方界限之内的比较文学显得愈发尴尬。使这种尴尬加倍的是,当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都开始声称其全球维度时,“全球”和“世界”的含义也被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以至于远远超过了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能够处理的范围。因此,比较文学以文学(无论是文学关系还是文学性)为阵地的研究实践是否能够满足时代要求,就不只是这个学科所面临的挑战,而且关乎其背后“西方文学学术共同体”是否还能维系的大问题。在此背景中,就学术实践的层面来看,比较文学呈现出两方面的发展趋势——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和理论化(theorization)。
首先是全球在地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在地化”(localization),似乎是含义相反的概念,但在比较文学的实践中,二者又是互相纠缠和互相强化的。这是因为,比较文学的全球化,本身即是在对全球不同地方和不同主体的文学及其所属的社会现实进行认知的基础上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地方”,并不等同于民族国家,而是在对作为现代性制度的民族国家和对全球/民族国家二元结构进行拆解的基础上发现的更为多样的现实区域。所谓的全球在地化,要求学者在文学研究中不仅要探索文学的世界地图,重新理解作为“全球”的“世界”,而且也要关注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如此,许多原先被排除在“文学”制度之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议题被重新发现了,例如族裔、性别、阶级、媒介和区域,等等。这并不是说,这些议题之前不存在;相反,它们一直深刻地支配着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和文化实践。但在原有的“西方”和“文学”制度的影响下,人们所讨论的文学,主要是由西方白人男性精英主导的文学;它通过伪装成普遍性的文学,遮蔽了更多样的文学实践和文学所属的社会现实。在《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中,萨义德指出了文学批评领域中“文人的背叛”: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躲避在“古典作品、人文教育的美德和文学可贵的愉悦”“文学理论”和“文本性”的背后进行专门化的智力劳作,“对于一切这些事物生发于其中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世界表现出沉默(也许是无能为力)。”39(美)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页。[Edward W.Said,Shijie,wenben,pipingjia(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trans.LI Zixiu,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House,2009,3.]与此相反,萨义德主张更加重视作为文本之生发地的“世界”的“世俗批评”:“文本是现世性的(texts are worldly),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事件,而且即便是在文本似乎否认这一点时,仍然是它们在其中被发现并得到释义的社会世态(social world)、人类生活和历史各阶段的一部分。”40同上,第7页。[Ibid.,7.]
与这种极具现实指向性的全球在地化相伴的趋势,就是高度的理论化。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由来已久,尤其是对于“二战”之后的美国比较文学来说,对文学理论的思考就是比较文学的起点之一——美国比较文学的第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就是韦勒克和沃伦(Austin Warren)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1949)。这是因为,对文学的理论思考,本身就需要超越不同文学的界限,在比较和关系中进行抽象的归纳。因此,有些国家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都没有作为学科建制的比较文学,却同样有实际的比较文学实践,而这些实践主要就是以理论的方式展开的,例如前苏联的文艺学。而且,韦勒克-沃伦式的和苏联文艺学式的文学理论还有极重要的相通之处,即它们都是建立在唯一真理观(所谓“原理”)基础上的文学理论,因此不止是一种理论化的学术实践,更重要的是对更广泛的学术实践的规范。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是一元的,犹如艺术和人性是一元的一样。只有运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文学史才有前途。”41(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5~46 页。[René Wellek and Austin Warren,Wenxue lilun(Theory of Literature),trans.LIU Xiangyu(Nanjing: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5),45-46.]基于这种“一元”理念,两位作者将文学理论解释为“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42同上,第32页。[Ibid.,45-46.]
与这种作为原理和规范的文学理论完全相反,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理论是唯一真理观破碎的产物。美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者吉拉德·格拉夫(Gerald Graff)曾指出:“所谓‘理论’,就是当作为共同体之实践基础的根本逻辑不再被认可之时、当之前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事物成为争论(并且这种争论往往不会得到最终解决)对象时迸发而出的东西。”43Gerald Graff,“Why Theory?” in Left Politics and the Literary Profession,ed.Lennard J.Davis and M.Bella Mirabell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23.18世纪文学研究专家大卫·里希特(David Richter)也曾以自身经历来说明这种理论的“迸发”,提到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从教时,“理论”往往是指历史中的理论,例如古典时代的诗学,然而与此同时,“一场最终将使批判(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成为文学专业之轴心的革命已经开始了。……在欧洲大陆,思想的动荡和冲撞已经在数十年前开始,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当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解构主义、拉康的心理学、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现象学和接受理论蜂拥而至时,我们这些居于边缘的人(我们只能磕磕巴巴地读法文和德文,俄文则一窍不通)才体验到理论的爆炸。”44David Richter,“Preface,” in The Critical Tradition,ed.David Richter(Boston and New York:Bedford/St.Martin’s,2007),v.里希特提到的这些理论大多来自于欧陆,它们本身往往是哲学思考,但在美国主要进入到文学研究领域内;当然,理论所冲击的当然不只是比较文学,还包括各种国别文学领域。然而,此时的比较文学却成为了理论的中心,正如苏珊·巴斯奈特所看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新一代雄心勃勃的研究转向了文学理论、女性研究、符号学、电影和媒体研究、文化研究,将这些领域看作是更激进的选择对象。他们放弃了比较文学,将之视为自由派人文主义史前时代的恐龙。”45(英)苏珊·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查明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 页。[Susan Bassnett,Bijiaowenxue piping daolun(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trans.ZHA Mingjia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5,6.]
尽管此时的理论仍关注所谓“文学研究的本质”,但它们不再是对韦勒克-沃伦式的原理的探寻,而恰恰是对原理和唯一真理观的质疑和批判。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理论并不作为谈论文学的诸种方式之一种而出现,而是对其他各种形式的批评分析采取一种批判姿态。它尤其倾向于怀疑这些批评分析所说的大部分都是在回避问题。”46(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Terry Eagleton,Ershi shiji wenxue lilu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trans.WU Xiaoming,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8,4.]因而此时的理论往往具有强烈的解构、多元主义和非本质主义倾向,其具体论述虽然和文学关系密切,并且主要是一种学院派的话语实践,但其旨归往往超出文学论述和学院体制,表现出鲜明的现实和政治介入色彩,尤其是与弱势群体/阶层和少数族裔的身份政治结合起来。里希特曾指出,当理论兴起之时,“许多体系都使妇女和少数群体表达和她/他们迫切的社会需求成为可能,使她/他们得以为争取更多自由和权力的需求寻求一种理论的表征。”47David Richter,“Preface,” v.
由于全球在地化和理论化的发展,在学科形态层面,新的比较文学呈现出后国家与超文学的特点。其中,所谓“后国家”并非是说作为制度的国家已经消失,而是说尽管它依然存在并对人文学术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其在人文学术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前文说过,在这一历史时期,民族国家和全球/民族国家二元结构都遭到了学理上的拆解,在文学研究层面,“国家”已经不再被视为天然的单位或研究工具,而是被视为待拷问的问题。这与前两个阶段对于民族国家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前两个阶段,无论是跨越国家还是超越国界,本身都是建立在承认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单位的基础上进行的。此外,在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地理范围也大大超越了“西方”的界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学术实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兴起,一时间成为引领风尚的热门学科,其中的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还发展出了别具特色的比较文学知识体系。
所谓的“超文学”,是指新的比较文学突破了传统的文学研究形态(即作家研究和文本研究),呈现出多中心和多重心的研究局面。在研究对象上,新的比较文学将范围扩展到对媒介、族裔、性别和文化等互有重叠的对象上。与此相应,具体的研究者也未必来自于文学研究领域,更未必以“比较文学学者”来标签彼此。即便是在比较文学“学科”之内,学者身份也都变得愈发多元和难以辨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比较文学就不是“文学”的——在具体的实践中,这些研究虽然未必会涉足文学作品,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学研究的意味。乔纳森·卡勒在《理论中的文学》(“The Literary in Theory”,2000)一文中指出,虽然文学和文学性在理论讨论和更多研究中未必居于中心位置,但这些研究实际上都呈现出文学化的特征:文学对个体、他者、情感、悖论、含混、陌生化和复杂性的重视和呈现,极大地启发了各种各样的研究,而这些研究也从文学文本中不断地吸收灵感,获得行动的方向;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充分吸收了文学研究的概念、方法、思路和阐释模式,如此一来,“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的各种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的”。48(美)乔纳森·卡勒:《理论中的文学》,见《理论中的文学》,徐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5页。[Jonathan Culler,“Lilun zhong de wenxue”(The Literary in Theory),in Lilun zhong de wenxue(The Literary in Theory),trans.XU Liang,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9,35.]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文学已经变得无法辨认了,但反过来,比较文学也终于变成了韦勒克所呼吁过的文学研究本身,尽管是以他未必期待和认可的方式罢了。换句话说,从名义上看,“比较文学”因为已经普泛化而不再重要,但从实质上看,比较文学取得了历史的胜利,成为一种复数的人文学术实践。
结语
美国古典学家扬∙齐奥科斯基(Jan M.Ziolkowski)曾在讨论比较文学史时说:“是什么造就了比较学者?不是学位,而是能力和视野。这些能力和视野会不可避免地依时而变,同时也会根据我们对文学和阐释的理解而变,甚至,比较文学的名义也会由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发展而变化。”49Jan M.Ziolkowski,“Incomparable:the Destin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Globalization or Not,” The Global South 1,no.2(2007):44.的确,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知识探寻,它的形态会因时、因地、因势而不停变化。因此,对比较文学实践、理论和方法的思考,不可离开对比较文学学术史的认知;而对学术史的思考,更不可离开对学术背后的大历史的认知。比较文学的萌芽生发自18-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学双重发现的历史过程中,此后,随着不同时空中的学者对于“民族国家”“文学”和“学术”这三要素的不同理解,比较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形态差异。在19-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通过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和确认历史学与文学史的“科学”地位,比较文学在文学关系史基础上呈现出跨国界和历史学研究的特征。到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通过继承和突破文学关系和文学史学,比较文学从一种地方性和边缘性的学术领域转型成为西方的文学学术共同体,呈现出超越国家和文学中心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全球地方化和理论化的发展,比较文学成为一种后国家和超文学的复数的人文学术实践。从民族国家、文学与学术这三要素来描述比较文学的历史脉络,既能清晰地看到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界人文学术的多元形态,也能深入体认不同的比较文学实践与大历史的动态关联,从而为更好地理解比较文学的历史与未来打开通路。如此,当面对“什么是比较文学”等“大问题”、或者是“某位学者的比较文学观念为何”的“小问题”时,我们或许可以首先反问道:对于具体的研究主体来说,“民族国家”、“文学”和“学术”,都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