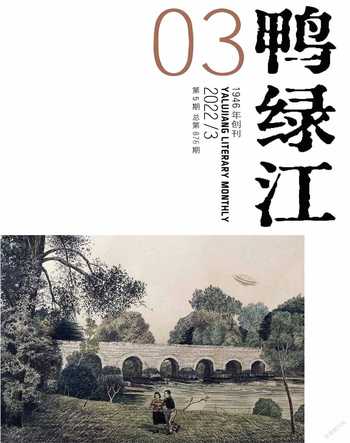当代性、地方性与文本意义
何言宏 李犁
何言宏:在当代中国,辽宁的女性诗歌创作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到今天,一直都很有活力。这些女诗人均处北国,同为女性,诗歌创作上不无共性,同时,个体主体性的多样化建构又使她们各具特色,体现了人文主义最核心的方面。
辽宁的女诗人,无论是在诗歌观念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普遍具有女性主体的个体自觉。这种具有主体性的个体自我表现在辽宁女性诗歌创作的许多方面。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诗歌一样,辽宁女性诗歌同样深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特别是美国自白派诗歌的影响,女性主体的个体表达经常会采取身体书写的策略。在最为属己的身体书写之外,辽宁女性诗歌个体主体性的建构还表现在诗人们对孤独体验的深切表达。也正是这样的表达,塑造和呈现出了她们各自不同的个体主体形象。当然,女性主体的多样性建构,除了表现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在个体主体的内部也表现出丰富复杂的多样性。
实际上,辽宁女性诗歌有关爱的话语结构中,并不只有“爱情”话语。女诗人们爱的话语还包括对亲人、民众、自然、乡土的爱——甚至有着宗教意义上的爱——对于她们爱的话语的整体考察,应该是另外一个很有意义的关于情感主义的课题。特别是她们对包括母亲在内的其他女性(如女性历史人物和底层女性)的爱、在母性的意义上对孩子的爱、契合生态女性主义的对自然万物的爱,都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人文学术价值。但是,作为一个同时具有地域性的女性诗歌群体,辽宁女性诗歌的地方性书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辽宁地处东北。英国学者彼得·戴维森在谈到北方的观念时,曾经一再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北方”“每一个个体心中都有专属于他自己的极北之地,真正的、纯净的北方”。无论是在自然地理还是在人文地理的意义上,辽宁地处北纬40 度和山海关以北,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世界的地理空间中都属北方。因此,辽宁女性诗歌对东北的书写,实际上同时也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北方书写,戴维森所讨论的由地形、历史和文学想象交织而成的“北方的观念”,同样存在于辽宁女性诗歌中。对作为家乡的北方的地理、自然和历史文化的关切与热爱,是她们诗作中的共同主题。在此意义上,她们对北方的爱,正是她们爱的话语结构的重要内容。由于不同于男性的“环境感知和环境价值判断”,她们对北方的“恋地情结”很自然地意味着她们女性主体的丰厚、拓展和延伸。
北方是她們的家乡,她们对北方的故乡之情无可置疑。她们的精神性格中,宿命般地存在着北方气息。在辽宁女性诗群对北国的爱与认同中,以辽宁为中心为重点的北方的历史文化是很重要的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极有意义地构成了她们“北方的观念”中的“文化北国”。
在辽宁的女性诗歌中,雪和大地是非常典型的基本母题,特别是大地,在她们的笔下,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地理自然的属性,而包蕴着非常深刻的生命启示与精神内容。
李犁:如果编一本权威公正的《中国精英女子诗选》,一下子有十多位甚至二十位女诗人入选的省份,非辽宁莫属。
辽宁女诗人的写作中,作品更多介于关怀人间冷暖与关注个人内心之间。具体来说就是这些女诗人那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率真让她们更加灵敏地感受到自然万物所透露的信息和命运。像游丝迎接风的吹拂,一点点的波动都能在她们的心里引起翻天覆地的战栗甚至折断。表面看是触景生情,实际并不是简单的触景生情。因为那些情早就在她们的心里堆积、鼓胀,偶遇的景物仅仅是捅破和勾出了这些情。这些涌动的感情逼迫她们俯瞰世界,找到能点燃自己的人和物。所以我暂且称之为外瞰,即从里向外探试和寻觅。外面的景物是她们内心的喻体,或者说是互为喻体。在这种对望和互相印证中,诗人解开了束缚自己的绳索,放出了休眠甚至囚禁的自己。
从文本上讲,这种俯世精神在这些诗人身上稀释,稀释成一个诗人的素质和品质。也就是说,诗人已经把对具体的人与事的关怀,转变成对天空大地万物的体恤,转变成一种普遍常态下的写作态度。需要指出的是,俯世是这些诗人的姿势,也是精神内核。在写作方式上,她们又努力出新,保持着文本的前卫性,所以这些诗人与其他写作风格也有着交叉,胸襟一张开就是广阔的现实写作,写作的视角一闭合就又跑回内心,写出的诗歌又成了另一种风格,成为探索生命体验和神秘体验的内视诗人。
诗歌文本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技术的更新和革命。诗歌就是修辞学。诗贵出新,诗歌也厌旧恋新,最优秀的诗歌永远是河流最前面的那部分。所以诗人要有勇气去探索,去颠覆并创造新的技术,以保证诗歌的鲜活性和先锋性。辽宁的女诗人是深悟此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