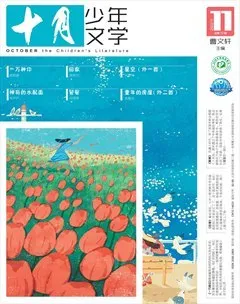“双层结构”的平衡统一
2022-04-12 00:00:00李学斌
十月·少年文学 2022年11期

首先,就文体属性而言,童话的核心特征是幻想性和隐喻性。其中,幻想性是童话的文体依据,隐喻性是童话的审美效应。而童话就是将现实生活逻辑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按照内心愿望或幻想逻辑,用散文形式写成的故事。此时,幻想逻辑、心理逻辑与现实逻辑之间或错位衔接,或同规超越就成为童话叙事发生的根源。这其中就包括将动植物“人格化”的拟人体童话。拟人体童话借动物、植物演绎童年事、人间事,其动物、植物形象既非大自然生物学范畴中的动植物,也非社会学或童年学意义上的成人、儿童,而是动植物与人的合二为一。
此时,对完整的动植物形象而言,生物性与人性(儿童性)缺一不可。否则,这些动植物形象就是无根、少魂的。
举凡世界经典拟人体童话,我们会发现,其动植物形象往往都是“双层结构”:人性(儿童性)为表,生物性为里。正因为此,童话中,小狗小猫、小花小草才有言行、心理;也因为此,那些小狗小猫、小花小草才是小狗小猫、小花小草,而不是其他。足见,拟人体童话中:生物性是现实根源、想象基础;人性(儿童性)是思维方向和意义建构。而衔接并融通二者的是幻想或想象。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拟人体童话创作的要领就是依托物性特点,而寻求“生物性”与“人性”(儿童性)的平衡和统一。譬如,《田鼠阿佛》中的“阿佛”既是勤勉的小老鼠,也是温情的“诗人”;《爱心树》中的“树”既是枝繁叶茂的大树,也是无私奉献的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