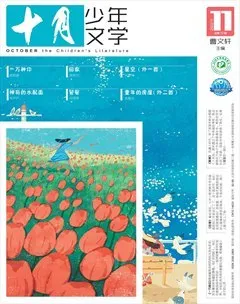小说盲盒中的时代洞察
常新港写了四十年儿童文学,专注城市儿童生活也有将近二十年。拿到这部书稿之前,我在想,他还会写出什么?—在文艺创作中,有时候经验和疲惫是双生花。我知道他口袋里还有得是好东西,他手插口袋,掂量着时机把它们展示给我们看。但这些好东西里有多少是“新”东西,我是心存怀疑的。但当我读完整部作品,不得不叹服于一个“老”作家接纳和吐露新东西的能力。
《谁在撸猫?!》一篇中,学校开启了线上教学。线上学习也要遵守上课纪律—不能吃零食、打瞌睡、随意走动……每天都有一个值班家长在线上监督同学们的学习纪律。这可难坏了有猫有狗的舒西西,他管得住自己,管不住猫和狗呀!上课的时候,小狗凡鸟枕在他的拖鞋上,小猫嬴猪跳到他的腿上。不巧的是,这天线上值班的正好是同班好友菲菲的妈妈。一堂关于线上课纪律的家庭战争一触即发……
《猜猜那是谁?》中,班里的同学们都在关注一个短视频账号。那个博主戴着一个孙悟空面具,让人猜不出她是谁。但她讲的都是班里发生的事,所以她一定就在他们中间。大家对她好奇,因为她神秘;大家喜欢她,因为她敢说他们不敢说的真话……
《伴飞》中,菲菲的大鸟风筝在天空中交到了两个好朋友—麻雀和黑白相间的无名鸟。它们组成了一场关于春天的盛会。然而一架嗡嗡作响的无人机的到来驱散了风筝的朋友们……
这些故事的取材都有十足的当下性,在短短的篇幅中有起有落,最后熟辣地停在一个充满哲思、引人深思的地方,有点儿城市寓言的味道。科技的变革、生活的变化会在孩子眼中折射出什么,在孩子心里留下什么,是不能回避也值得关注的话题。这部作品再一次拉近了儿童文学与此时此刻的距离。
小说题目叫《一万种你》,它当然无法讲述一万个孩子的故事,而是讲了三十二个取材各异的故事。读过之后我发现,这些故事虽有勾连但是每一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如果我们不追求从头至尾的阅读仪式,打乱顺序,从中随意抽取篇章阅读,也丝毫不影响理解。于是我想到了一个阅读游戏—抽盲盒式阅读。三十二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盲盒,每一个盲盒里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孩子生活中的一个瞬间。就像我们打开一个玩偶盲盒,里面的玩偶以特定的服饰和姿势定格在一瞬间。不限定抽取故事的顺序的话,会出现上万种组合的阅读路径。选择不同的阅读顺序,相当于选择了靠近这群主人公的不同的路。如果我们先抽到《挖坑》这个盲盒,会看到一个有点儿叛逆有点儿“坏”的舒西西,会给爸爸挖语言的坑;如果我们打开《嬴猪和凡鸟》盲盒就会率先认识舒西西家的小猫和小狗;当我们打开《猜猜那是谁?》,又会看到舒西西善良和成熟的一面—他认出了“孙悟空”是谁,却选择保守这个秘密……如果反过来呢?我们对主人公的印象会不会不一样?每一次遇到舒西西,我对他的印象都会改变一点儿,他的形象都更丰满一点儿。但即便读完整部作品,我也没能认识全部的舒西西,因为还有很多作者没讲的故事。在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很难凭借一两个瞬间对人对事下结论。抽盲盒式的阅读仿佛一场社会学实验,让我们看看自己的认知是先入为主还是理性客观。
除此之外,作品很吸引我的还有弥漫全篇的淡淡的孤独感。陈果果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孩子,寂寞得像个透明人。就连芳芳老师都是在一次叫了他的名字没人回应的时候,才想起来他已经转学了;吕威的奶奶整天整天地坐着,爸爸给奶奶雇了个保姆,主要是陪奶奶说话,可奶奶不爱和保姆说话,她更喜欢和那个只会说三句话的电子娃娃说话;舒西西想起以前排队买书换棉花糖的书店,却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串串香店,他“站在那里,左看右看,待了很久……”读着这些段落,我也被薄薄的落寞笼罩。不过没关系,人在孤独的时候容易思考,人在思考的时候也容易孤独,那些寂静的时刻是成长的时刻。
三十二个故事不长,却拼组成了无数形状,我看到了一万种孩子,一万种思考,一万种关于文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