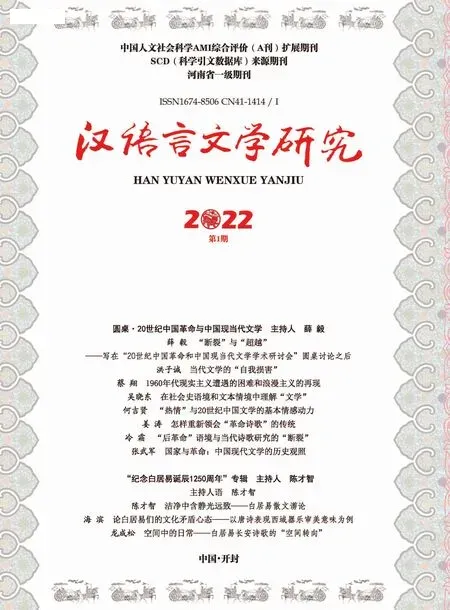空间中的日常
龙成松
摘 要:白居易诗中对于自己在长安生活、工作、社交、娱乐的空间有详细的记录和描述,被学者作为唐代长安研究的重要“诗料”。白居易对于长安空间的特殊感知和记忆,与他在长安辗转的寓居经历和波折的仕宦经历有关,也与他对于相关地理空间知识的习得和积极整理密切相关。中唐时期地理学、舆图学的新发展,引起了白居易及同时代诗人的关注,并对他们的诗文创作中空间表现技巧产生了实质的影响,其中一种典型的形式就是“空间耦合”结构。中唐时期以长安为背景的诗歌、传奇等文学体裁,成为长安空间知识生产的重要助推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唐文学的“空间转向”。后世学者对于长安空间的“复原”研究,对中唐诗歌、小说的引用,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唐文学这一空间特质。
关键词:白居易;长安;空间;里坊
长安是唐代的都城,也是帝国文艺舞台的中心,难计其数的诗人曾宦游或定居长安,留下了众多的诗篇。可以说,长安是唐诗锦绣万花筒最显眼的地理空间标识之一。正因为唐诗与长安之间密切的关系,清代学者开创了援诗为证探索唐长安宫室、里坊、街曲、景观的方法,产生了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这样的名著。徐松在其书的序言中提及:
古之为学者,左图右史,图必与史相因也。余嗜读《旧唐书》及唐人小说,每于言宫苑曲折、里巷歧错,取《长安志》证之,往往得其舛误,而东都盖阙如也。……校书之暇,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之《长安图》,作《唐两京城坊考》,以为吟咏唐贤篇什之助。①
徐松对于长安文学空间研究的开创之功,朱玉麒先生已有很好的概括②。徐松是从“唐人小说”视点展开自己的唐长安空间想象,事实上他在论证的时候引用的更多是诗歌。《唐两京城坊考》中引用唐诗达150余首(次)。有意思的是,在徐松引用唐诗中最多的就是白居易,达40余首(次),远超出同时代和其他时段诗人。这与白居易诗歌中详细的长安里坊街曲空间地理信息有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呼吁:“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③这一想法在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年谱》中已经部分实现。沿着他们的道路,国内外学者对于白居易诗歌中长安景观、地理空间的“诗史互证”取得丰富的成果。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对白居易与长安空间的分类和复原,在有关研究中最有代表性④。然而白居易在长安的行迹,尤其是在更微观的街坊曲巷空间活动,仍有待进一步开拓。本文拟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梳理。
妹尾达彦将白居易诗歌中的城市景观分为五类:居住地、友人家、名胜和寺观、宫殿和官厅、郊外的友人家或名胜地。其中比较稳定的是他的住所、工作空间和友人家,本文重点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白居易长安住宅的诗歌呈现
白居易诗歌中近乎实录的长安里坊、街曲及景观信息,与他在长安长期的生活经历有关。白居易先世曾寓居长安,两岁时其祖父白鍠即卒于此。根据新出墓志的记载,白居易家族的一些支系在长安也有祖业①。成年以后,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正月来到长安参加高郢主试的进士科,登第后返回洛阳省亲,贞元十八年(802)又入京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次年登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开始长安定居生活。白居易在长安的居住地多次更迁,徐松说:“按白居易始居常乐,次居宣平,又次居昭国,又次居新昌。”②这是其大概,但有讹误。王拾遗、朱金城等先生曾撰文对白居易长安住宅有过详细的梳理。③下面结合白居易诗作一个概述。
(一)从常乐坊到永崇坊
白居易在长安居所可考的第一站是常乐里,假居关播私第之东亭。常乐坊东边靠近外郭城墙,白居易居所正在东边,所以郭外鸡犬之声相闻,白诗中有记载。但白居易在此居住的时间也不长,校书郎的工作比较闲散,所以第二年春他曾游洛阳、徐州,并举家迁徙到下邽金氏村。王拾遗先生认为元和元年(806)三月,白居易校书郎任期满后失去俸钱收入,只得退掉常乐里房子,而与元稹、周谅等人住到永崇里的华阳观,准备迎接制科考试。朱金城先生则认为贞元二十一年(805)白居易重返长安时已寓居永崇里之华阳观。揆诸白居易的行迹,朱先生之说为洽。其《春中与卢四周谅华阳观同居》诗云:“杏坛住僻虽宜病,芸阁官微不救贫。”④作于永崇里期间,尚为校书郎,其中也透露出他换房子的原因——校书郎俸禄太低,无法开支此前关相家的“大房子”的房租。永崇坊近城南,人口较此前的常乐坊为稀,所以白居易《永崇里观居》诗说:“永崇里巷静,华阳观院幽。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⑤其中还有旅馆,诗人元结、皮日休朝京师时曾寓居其中,这可以作为白居易选择此地寓居的参照。华阳观寓居生活,是白居易人生中一个新起点,《策林序》中详细记载观中读书事,很多朋友也是在这时结交的。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制科登第授盩厔县尉,结束华阳观寓居生活。元和九年(814)《重到华阳观旧居》追忆道:“忆昔初年三十二,当时秋思已难堪。若为重入华阳院,病鬓愁心四十三。”⑥感慨颇深。
(二)靖恭坊到新昌坊
白居易虽然离开长安到盩厔为官,但仍频繁往返两地。这期间他在长安的居所也有一些线索。比如元和二年(807)春,他曾与杨汝士家人屡有交游,就是暂住于靖恭里杨家,有《宿杨家》诗。同年秋,他自盩厔调入长安充进士考官,试毕帖集贤校理;十二月又召入翰林学士。这二者都是实职,自然需要白居易在长安有住所。从他与杨家交往的情况看,应该都是暂住那里。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迎娶杨汝士妹妹,同年四月他迁左拾遗官,依旧翰林学士。这一时期他的诗文中出现新昌坊住所的信息,如《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云:“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闲。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暂开。”⑦所叙为在翰林学士时事。王拾遗先生认为,白居易这次入住新昌坊是因为结婚的缘故,也是租的房子。白居易此期间还有《松斋自题》《早朝贺雪寄陈山人》等诗。据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自注,白居易在新昌坊一直住到元和五年(810)春,元稹当年被貶谪江陵时,他曾在新昌坊北送别。
从元和二年到元和五年,这是白居易成年后在长安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新昌坊则是他长安活动空间最持久的地方,其后买宅于此或许也与此有关。
(三)从宣平坊到昭国坊
据《襄州别驾府君事状》,白居易母陈夫人元和六年(811)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此前,白居易曾上书援引姜公辅求京兆判司奉亲之例,求京兆之官以养母。徐松据此认为宣平坊宅是“陈夫人就养于居易之第”①。王拾遗先生认为,白居易迁居宣平坊可能是在元和五年,当年五月白居易改官京兆户曹参军,俸禄较高,并引用《初除户曹喜而言志》为证。但奇怪的是,白居易诗中从未提及自己在宣平坊事,这与他入住其他宅第时不同。白居易宣平坊第的出现,起因是在长安工作需要有固定住所,迫切的原因是他结婚需要新房,终极的原因则是要奉养母亲。这些因素叠加起来看,宣平坊宅第只能是租赁而非购置。另外,也不能排除白居易寓居宣平坊亲朋家的可能。白居易诗文中唯一一次提及宣平坊,是在《过刘三十二故宅》诗中,朱金城先生编于永贞元年(805)。白母卒后,他们一家丁忧退居下邽金氏村,至元和九年(814)冬再次返京时又赁居昭国坊,据此也可以看出宣平坊居所的特殊性。
白居易在下邽金氏村一直待到元和九年冬才重返长安,出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次回京,他是赁居昭国坊王家的宅院。在《朝归书寄元八》中说:“归来昭国里,人卧马歇鞍。……柿树绿阴合,王家庭院宽。”②昭国坊地近城南,紧临曲江,坊中人少,其《昭国闲居》诗中描述了这一情形。有时白居易下班后,还能到城南一游,《朝回游城南》诗记之。
与前几次在长安的居住经历相似,白居易一家在昭国坊待的时间前后不足一年。元和十年(815)八月,白居易外贬江州就离开了。
(四)重回新昌坊
元和十五年(820)夏白居易召回长安拜司门员外郎,至冬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这段时间白居易住在何处,朱金城先生认为不可考,或者借住在亲友处,或者另有住宅,其诗文中缺乏记载。至长庆元年(821)二月,白居易始购置新昌里宅第。这段经历详细见于其诗,其中《卜居》说得十分动情: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③
白居易贞元十六年到长安应试,至十九年(803)授官在常乐里暂寄关播家的房屋,至长庆元年才购置的自己的宅第,前后正好二十年。这与韩愈《示儿》中“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相似。这也印证此前在诸坊的宅第都是寓居或赁居。究其原因就是一个“贫”字,在《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中也有剖白。因为储蓄不多,所以他买这套房子比较小,虽然说是“新居”,其实是“二手房”,《旧房》《题新昌所居》等诗也有相关记录。但白居易对这套宅第情感十分深沉,所以相关的诗歌也最多。他购置了宅第后,给友元宗简寄诗说“莫羡升平元八宅,自思买用几多钱”④,无奈中带着戏谑之意。他在新昌旧居上面也倾注了相当多心血,《竹窗》《庭松》等诗中三致意焉。
然而白居易与长安的缘分就是充满戏剧性,他这次在新昌坊只住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长庆二年(822)七月他外刺杭州,又一次启程离开。大和元年(827)四月他重回长安(是年底又奉使洛阳至次年春才回),至大和三年(829)二月分司东都,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新昌坊。此后他就再没有回来过,新昌坊宅一度空置。大和四年(830)白居易在洛阳有《闻崔十八宿予新昌弊宅时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一宵偶同两兴暗合因而成咏聊以写怀》,说明当时宅第还在。新昌宅最终的下落如何,前人有争议。大和九年(835)白居易在《诏授同州刺史病不赴任因咏所怀》诗中说:“白发来无限,青山去有期。野心惟怕闹,家口莫愁饥。卖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资。”①王拾遗先生认为白居易并没有卖掉新昌坊宅第,只是想想而已;朱金城先生则认为白居易是卖了房子。日本学者埋田重夫认为,大和九年前后一系列原因促成了白居易卖掉新昌宅:该宅长期无人居住;购入洛阳履道坊宅第,对于东都分司的心理倾斜;爱弟白行简与好友元稹相继去世;嫡子“崔儿”夭折,白居易“或望子孙传”的希望被摧毁;大和九年女儿阿罗结婚,白居易完成父亲的职责。②其说不可易。可以补充的是,白居易晚年对于宅第的热情大大减退,多见于诗,如《吾土》《吾庐》《达哉乐天行》等,这与他晚年深受佛教思想影响有关。
关于白居易长安住宅有一个问题有待辨析。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在“永宁坊”下著录白敏中宅,并引用李商隐《白居易墓志》为证说:“盖白公有杨凭旧宅,敏中所居即乐天第也。”③按李商隐原文作:“其曾祖弟,今右仆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复宪宗所欲得开七关,城守四州,以集巨伐。仲冬南至,备宰相仪物,擎跪斋栗,给事寡嫂。永宁里中有兄弟家,指向健慕,以信公知人。”④按照文意,永宁里当为白敏中宅,而奉养嫂夫人白居易妻。并没有说永宁里为白居易宅。疑徐松误解了“永宁里中有兄弟家”一语。另外,永宁里确有杨凭宅,白居易曾得杨凭洛阳履道坊旧宅,疑徐松又涉此而误以为白居易得杨凭永宁里旧宅。但白居易夫人在白敏中永宁里奉养无疑,也算白居易和长安最后的一段缘分。
综上所述,白居易长安住宅,可考者就至少辗转经历七处之多。从屡次租房到最后买房,与其经济条件有关,也与其个人“动荡”的为官经历有关。事实上,这并不是白居易一个人如此,唐代多数的官僚都有这样的情况。不同之处在于,白居易用自己的诗歌详细地记载了自己每一处居址,甚至居住环境的细节,这是唐代绝无仅有的案例,所以我们才能“复原”他在长安的大致生活空间。
二、白居易长安工作空间的诗歌呈现
从贞元十九年到大和三年(829),白居易在长安断断续续的生活与他的为官经历密切相关。白居易诗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每一段为官经历的情况(如除官时间、俸禄等等),还记录了他工作部门的地理、空间和交通信息,可以大致勾勒出他在長安政治生活的基本空间。
(一)秘书省、贡院、左春坊
贞元十九年春,白居易书判拔萃登第,授官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在西京皇城内,承天门街西,第五横街之北。承天门街东西宽百步,南接皇城之朱雀门,两边种有槐树,俗称“槐衙”。大和元年三月十七日白居易为秘书监,再次进入秘书省工作。所以他对于秘书省的工作情况有较多的记录。为秘书郎时候,正寓居于常乐里关播私第之东亭。白居易有诗叙述当时的工作状态是“典校在秘书、三旬两入省”。校书郎正九品上,定员八人,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是比较清闲的工作,也是唐代士人释褐官的良选。白诗中所叙,正是其当时工作的基本状态。再为秘书监时,工作性质和心态已完全不同,在《初授秘监拜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所怀》等诗中有记录。白居易诗中对于秘书省的具体位置和空间信息也有一些记录。如《秘省后厅》中提及秘书省有后厅,种植有槐花、梧桐等树,为秘书监办公处。此后厅,即虞世南为秘书监时,编纂《北堂书钞》处,白居易诗可以互证。
元和元年白居易校书郎罢官,同年又参加才識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授盩厔县尉。元和二年(807)秋,入京充进士考官,这是白居易在长安的第二次为官经历。白居易充进士考官,当供职于尚书省礼部贡院。据《唐摭言》卷一五“杂记”:“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南院放榜。”注:“南院乃礼部主事受领文书于此,凡板样及诸色条流,多于此列之。”①所谓“都省”,及尚书都省,为尚书省的总官署,又称为都司、都台或都堂。都堂居中央,即进士考试之地,此宋代“殿试”之前身。但白居易时代,贡院实际在尚书南的礼部南院。据《长安志》,其位置在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五横街之北。元和二年进士试律诗题为《贡院楼北新栽小松》,当年及第的白行简、李正封、钱众仲、吴武陵诗皆存,是一个极具位置标记的题目。不知此题是否为白居易所出。
元和九年冬,白居易从下邽征回,官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他又一次进入皇城官署上班,他当时家在昭国,办公地在延喜门内东宫官署区的左春坊。两地距离颇远。所以《初授赞善大夫早朝,寄李二十助教》诗说“远坊早起常侵鼓,瘦马行迟苦费鞭。”左赞善大夫为太子左春坊属官,掌传令、讽过失、赞礼仪、教授诸郡王等职,也是一个闲职。所以他诗中说“官闲居处僻”“青宫官冷静”云云。
(二)集贤院与翰林院
白居易在贡院主持完考试之后,就进入集贤院为集贤校理。十一月四日,由集贤院赴银台候旨,五日召入为翰林学士。这两个工作地都是中央文馆。集贤院是唐代中书省下的文馆,其位置在大明宫中书省西原命妇院,院西为南北通街,南出昭庆门,北出光顺门。出光顺门往北,西面就是翰林学士院,西出为右银台门。白居易从集贤院赴翰林选候旨,即走这条路线。白居易对于集贤殿的位置和空间有过不少的描述。大和二年白居易《和刘郎中学士题集贤阁》中说:
朱阁青山高庳齐,与君才子作诗题。傍闻大内笙歌近,下视诸司屋舍低。万卷图书天禄上,一条风景月华西。欲知丞相优贤意,百步新廊不蹋泥。②
这里道出了集贤殿的几个信息:一是刘禹锡善于书法,集贤阁请他题字,可见一斑;二是集贤阁楼颇高;三是集贤阁在月华门西;四是集贤殿与宰相办公的中书省政事堂有百步走廊相连接。这都是非常细微的信息。
白居易在翰林学士职上待的时间较长,从元和二年十一月到元和六年六月。其间虽然他在元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除左拾遗,元和五年五月五日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但真正的工作地点其实都是在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作为皇帝近侍,其工作地点往往“随驾”所在。白居易诗中有多篇与翰林院的位置、空间和交通有关,其中《早朝贺雪寄陈山人》颇有代表性③。此诗作于元和五年,白居易时居新昌坊。诗中基本上“还原”了从新昌坊到翰林院的上班路线。“银台门”为上班地翰林院所在,“新昌里”为白居易住所。“上堤”,是指走在沙堤上。唐代长安街道都是泥路,但宰相家不同,“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④。“子城东街”为皇城之东的南北官道,道路较宽,是官员进入大明宫上朝的主要路线。宰相上朝的“沙堤”虽然是权威的象征,但内参官僚也能使用,白居易就是如此。⑤“十里向北”是新昌坊往东至朱雀门东第三街,一直北行至于大明宫前横街;“待漏五门”是指建福门外百官待漏院等候入朝;“候对三殿”指在麟德殿朝会。
翰林院中的景观在白居易诗中也有涉及。如《惜牡丹花》二首,其一自注“翰林院北厅花下作”⑥。据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北厅院内有古槐、松、药树、柿子、牡丹等花木。白诗可以互证。翰林学士作为皇帝近侍,随时备顾问之需,所以常需要在院中值守。白居易有《冬夜与钱员外同直禁中》《和钱员外禁中夙兴见示》《夏日独值寄萧侍御》《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等诗,都是在翰林院中值日时事。
(三)尚书省与中书省
元和十年八月白居易贬江州司马,元和十五年夏由忠州刺史召回拜司门员外郎。司门员外郎为刑部属官,从六品上,其办公地在皇城内,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省内有都堂,分左右各司,兵部、刑部、工部在西,右司统之。白居易在司门员外郎期间住在何处不详,朱金城先生认为可能是寓居朋友家。据他作于司门员外郎时的《早朝思退居》《曲江亭晚望》等中所见上班早起及靠近曲江等信息看,他应该住在靠近城南的地方。
大和二年二月十九日,白居易由秘书监除刑部侍郎,再次来到刑部,直到大和三年三月末罢官。这一段时间他住在新昌坊,其《喜与韦左丞同入南省因叙旧以赠之》诗云:“差肩北省惭非据,接武南宫幸再容。跛鳖虽迟骐骥疾,何妨中路亦相逢。”①韦左丞为韦弘景,元和四年(809)入翰林学士,与白居易同列,所谓“差肩北省”(“北省”就是中书、门下省,翰林学士属之)也;大和二年韦拜尚书省左丞,又与白居易同在尚书省,所谓“接武南宫”也。韦弘景为韦嗣立孙,其宅第不详。但他们同在尚书省为官,所以路上相逢亦属于必然。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白居易由司门员外郎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实职为“知制诰”,负责草外制(“知制诰”的翰林院学士草内制),办公地点在中书省(“西掖”)的舍人院,与中书舍人一样②。长庆元年春,他购置了新昌里宅第。十月十九日又转中书舍人,同样在中书省。这段时期,他在长安工作和生活空间大致就这两地之间,有很多诗歌涉及中书省环境和上班路线,其中《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朝入阁因示十二韵》诗颇有代表性③。元和十五年白居易授主客郎中知制诰,白行简授左拾遗,兄弟同属“近职”,同住新昌坊。行简的上班地点在门下省,乐天在中书省。兄弟二人很早就起床,从新昌坊往西进入子城东街的“沙堤”,北上到大明宫建福门外待漏院。禁门开启后,入宫至下马桥步行,然后行简随门下侍郎,乐天跟随中书侍郎,依两省朝班入含元殿朝会,结束后各自回到官署工作。层次非常清楚。
白居易在中书省期间与同僚颇多唱和,诗中常涉及中书省周边空间标记信息。如《吴七郎中山人待制班中偶赠绝句》:“金马东门只日开,汉庭待诏重仙才。第三松树非华表,那得辽东鹤下来。”④中书省北有待制院,因宣政门外有松树,所以唐代诗人常称道之。
三、白居易长安朋友圈空间的诗歌呈现
白居易在长安生活期间,结交的朋友、同僚很多,其诗中记录相当多与他有“同坊之谊”或“邻坊之谊”甚至“隔坊之谊”的人⑤,这也是我们复原白居易“空间中的日常”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因为涉及的人众多,下面我们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对他们的交游空间进行分析。
白居易的长安朋友,不少是在贞元十八年(802)前后订交的,其中元稹无疑是其朋友圈的中心。不同于白居易,元稹先世已占籍长安,在靖安里有祖宅,自其六代祖元岩至元稹时已传七代,这在唐代是罕见的例子。元稹早年的生活主要是在长安度过。贞元十九年,元、白同时登第,同授秘书省校书郎,但二人關联诗歌尚少。元和元年二人同居永崇坊华阳观累月,专攻制科,唱和逐渐增多,且往往能空间上互证。元和五年白居易作《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回顾二人的交情,提及不少长安地点:慈恩、皇子陂、唐昌、崇敬、曲江池,为长安著名的游览景点;三省、九逵、东垣、乌府、赤墀,为二人长安工作地;兴善、靖安、北村古柏、南宅辛夷,则元稹住所及周围环境。这些记载可与元稹自述互补,而且还要详细和完整。比如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自注:“开元观古松五株、靖安宅牡丹数本,皆曩时游行之地。”⑥元稹贞元中一度在近城南的道德坊开元观闲居读书,而白诗提及开元观中古柏,当与乐天同游。另外,白居易《和元九悼往》《见元九悼亡诗因以此寄》提及元稹宅中牡丹花,《洪州逢熊孺登》诗还提及靖安院里辛夷。
靖安坊及周边是唐代著名的“诗人聚落”,元稹同坊就有武元衡、韩愈、刘伯刍、李宗闵、张籍等。元和十三年(816),白居易在江州有《梦与李七、庾三十三同访元九》诗:“同过靖安里,下马寻元九。元九正独坐,见我笑开口。还指西院花,仍开北亭酒。”①李七为李宗闵,庾三十三(据前人考作“二”)为庾敬休。元、白、李、庾等人是一个交情颇深的朋友圈,元稹《台中鞫狱忆开元观旧事呈损之兼赠周兄四十韵》中也提及:“忆在开元观,食柏练玉颜。……李生隔墙住,隔墙如隔山。怪我久不识,先来问骄顽。十过乃一往,遂成相往还。……因言辛庾辈,亦愿放羸孱。既回数子顾,展转相连攀。……还招辛庾李,静处杯巡环。”②可见当时李、庾等人也住在道德坊周围,并有“邻坊之谊”。《唐两京城坊考》中李宗闵、庾敬休分别有宅在靖安、昭国坊,应该都是后来的事。白居易追忆当年诸人交游,时空有时也存在折叠情况,但总体上为写实。
以白居易先后住过的几个坊为中心,一坊之中、隔坊之外,形成了多个白居易长安朋友圈。白居易在诗中用类似“点名”的方式对朋友的住所进行了记录,如元八升平新居、靖恭杨家、修行里张家宅、韦令公旧池、裴相公兴化小池、周皓大夫光福宅等。妹尾达彦注意到白居易往来的友人,“更为集中在白居易居住地的近邻诸坊,这也就告诉了我们当时官员日常骑马所能交游的范围”③。
同坊之谊者,如常乐坊同坊之友有李顾言,疑白居易贞元末寓居此坊时认识。元和九年秋白居易在下邽时有《村中留李三顾言宿》诗回忆当时在金明门分别,元和十年李顾言卒,白居易有《哭李三》,则是从昭国坊到常乐坊吊唁。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失收李顾言条。新昌坊同坊之友则有窦易直,白氏有《惜牡丹花》其二自注“新昌窦给事宅南亭花下作”④。还有李谅,元和十年从长安贬谪江州途中《独树浦雨夜寄李六郎中》诗称“忽忆两家同里巷,何曾一处不追随”⑤。还有张彻兄弟等人,在《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中提及:“张贾弟兄同里巷,乘闲数数来相访。”⑥
白居易邻坊、隔坊之谊尤其多。如贞元末白居易在长安,与宣平坊的刘敦质(刘太白)有交往,其《过刘三十二故宅》有记录。宣平坊与白居易寓居的常乐坊和永崇坊都是隔街。白居易住昭国坊时,邻坊修行坊李建为其密友,二人约贞元十九年已订交,在《秋日怀杓直》诗中他追忆:“忆与李舍人,曲江相近住。常云遇清景,必约同幽趣。若不访我来,还须觅君去。开眉笑相见,把手期何处。西寺老胡僧,南园乱松树。携持小酒榼,吟咏新诗句。同出复同归,从朝直至暮。”⑦邻坊之谊可谓缱绻。长庆元年李建卒,白居易有吊唁之作《晚归有感》。昭国坊另一位邻坊友人是张山人,其《送张山人归嵩阳》诗记之。
白居易对于“卜邻”同坊的情结在元宗简身上用得最深。元和十年白居易有《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诗:
平生心迹最相亲,欲隐墙东不为身。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每因暂出犹思伴,岂得安居不择邻。何独终身数相见,子孙长作隔墙人。⑧
元宗简宅在升平坊,当时白居易寓居街西南的昭国坊,有买房和元八为邻的打算。此前元和四年他住在新昌坊,也称“时方与元八卜邻”。但直到元宗简时候,他也未做成同坊邻居,所以有“水竹卜邻竟不成”之叹。
同坊、隔坊之谊不仅停留在一般友情,还上升为其他各种更密切的关系,如白居易、萧昕、高郢。萧昕是高郢的座主(宝应二年及第),高郢是白居易的座主(贞元十六及第),白居易有《与诸同年贺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得群字韵》诗所描述的就是这个情况。而“巧合”的是,萧昕宅在永崇坊,高郢宅在其北的永宁坊,白居易在罢校书郎后也在永崇坊华阳观寓居。这种由座主门生关系联系起来的同坊、邻坊之谊,表明了长安人物空间关系的复杂性。又如白居易与靖恭杨家的关系,因为留宿而联姻,因为联姻又转变为邻坊关系,空间因素与婚姻相叠加。如果仅仅凭借《唐两京城坊考》,我们只能看到单一的空间点,而如果将白居易的诗歌及其交游网络放到长安空间中,则会发现各种因素影响交错的特殊形态。
白居易出游访友有固定路线,这也是他对长安空间感知和书写的重要部分。《闲出》诗说:“兀兀出门何处去,新昌街晚树阴斜。马蹄知意缘行熟,不向杨家即庾家。”①杨家为靖恭坊杨汝士一家,庾家或为昭国坊庾敬休家。以白居易工作和居住的地点为起点,以各个朋友的居住地为终点,我们勾画出白居易在长安访友的大致路线图。远一点的如张籍,住在街西延康坊。“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②这时他住在昭国坊,往延康坊访张籍,最近的路线也要经过八坊。《酬张十八访宿见赠》中也提及张籍远从延康里来访。
又如白居易在《和答诗序》中提及元和五年元稹贬江陵,“诏下日,会予下内直归,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遇于街衢中。自永寿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马上语别。”③《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怅然感怀因以此寄》诗也说:“永寿寺中语,新昌坊北分。归来数行泪,悲事不悲君。”④当时元稹住在靖安坊,永寿寺在其北的永乐坊。元稹被贬的诏令就是从翰林院发出,白居易还为其辩护。所以他从翰林院值日回来绕道去送别元稹,而此时元稹已经出门,他们永寿寺横街相遇,一起在寺中短暂留别,然后一起往白居易家新昌坊方向走,到坊北元稹再往东,至朱雀街东第五街北上,至春明门出城。徐松认为:“白居易下直,每自朱雀街经靖安里之北,集中有《靖安北街赠李二十》诗是也。”⑤朱金城先生也引用其说,疑误。白居易《靖安北街赠李二十》诗作于元和十年,与元稹无关,诗中说“榆荚抛钱柳展眉”是四五月间,当时元稹已经外贬通州司马。白居易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住在昭国坊;李绅为国子助教,工作地点在务本坊,其住所不详(李绅在新昌坊有宅,但应该是后来才购置)。诗中又说“两人并马语行迟”,是上班同路。靖安坊在昭国坊西北邻,白居易出门后折转即可到。靖安坊北街在延兴门、延平门东西大街上,往西至朱雀门大街,一直北行进入皇城,这就是他的上班路线。李绅要同路,应该也在昭国邻近。诗又云:“还似往年安福寺,共君私试却回时。”安福寺在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皇城西之第一街颁政坊之北,安福门外。疑李绅曾寓居安福寺,这里是回忆元和中他们同时登第的时候,白居易绕道送他, 这也是一次相对较远的路线。
白居易诗中对于友人住所的特殊的地理空间和景观也如数家珍。如元宗简升平坊新居中的看花屋、累土山、高亭、松树等景观;周皓光福宅新亭子中的草木(红药、绿筠),珍奇(猕猴、鹦鹉),家妓及音乐;裴度兴化池亭的小船等等。这也是长安诗歌的重要主题。
四、白居易诗与中唐文学的“空间转向”
“空间”作为文学史的重要量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亟待挖掘的主题。虽然文学地理、地域文学、交通与文学等领域已经有较多成熟的研究案例,但仍然是比较粗放的线条。在唐代文学家中,作品能详细编年、系地者寥寥可数,而能具体而微到日常空间,则中唐是一变。对于日常空间近乎纪实的刻画是中唐文学的特质之一,在长安和洛阳题材诗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个显见的例子就是长安空间词汇的扩大。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基础上修筑,整个唐代其格局虽然颇有改动,但里坊街曲布局和命名大体保持了一致。然而在唐代不同时期的诗歌中,长安里坊街曲的出现记录却并不一致。还以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为例,其中引用63位诗人152首(处),初唐仅4人4首,盛唐13人21首,中唐则有22人90首,晚唐也有24人37首。这侧面说明以两京宫殿、里坊、街曲等具体信息入诗,中唐是一个转折点。川合康三先生曾以盛、中唐诗中终南山的变容为例讨论过“风景与认知”的关系,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从自然中选择什么,如何再建构,文化、时代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此根据所属文化圈的不同,人们‘能看到’的是各不相同的风景。”①妹尾达彦先生也从唐宋转型(他称为“9世纪的转型”)这一个非常广阔的社会背景考察了中唐文学城市空间的形态,除了白居易外,他还关注了韩愈和《李娃传》等个案②。
就白居易而言,他的长安主题诗歌与长安城市空间之间的紧密联系确实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妹尾达彦认为:“自从初次进入长安城以来,对于白居易而言,长安的街头、居民、宫殿、树木和第宅都充满着催发诗歌创作欲望的魅力。”③他在讨论白居易诗歌与长安和洛阳的关系时候还提出了一个命题:“文学中的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在限定的固有空间和时期,通过与作者间的强烈的相关性为媒介体现了出来,这一点颇耐人寻味。”④他说这一想法是受到本雅明的启发。本雅明曾翻译波德莱尔诗歌,他发现9世纪巴黎的城市空间与波德莱尔的诗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以描写巴黎的城市社会志来进行诗歌分析。而妹尾达彦则认为,通过对白居易两京为对象的诗歌进行分类,可以再现白居易的城市景观。他在论文后附录了《白居易诗歌中出现的长安地点》和《白居易诗歌中出现的洛阳地点》等图,以及《白居易两京居住表》,就是想要完成其“再现”唐两京景观的尝试。他的研究给后来者做了非常详实的铺底。但是因为他关注的点过多,其展开的背景也太大,所以未能在白居易长安诗歌的空间问题上进一步深入探讨。
白居易长安诗歌的“微观空间”或者“日常空间”,特点鲜明,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白居易在诗题、正文、诗注中巨细无遗地记录他在长安居住、工作、友朋、游观空间信息,这事实上就是另一种“诗史”。我们根据他的诗歌,可以“还原”唐长安城宫殿、官署、街坊、寺观等空间的布局、走向,甚至其中的景观、陈设等等。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长安志》以下各种地志,长安城的地理空间就需要用白居易等诗人的诗来复原。
白居易长安相关诗歌中强烈的空间感、位置感、距离感和路线感,与白居易本人内在“空间感知”能力有关,也与他对于地理知识(地志、舆图)的习得有关。现代生理學、心理学研究对于空间感知能力的机制及其形成过程充满了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不同人对于空间的感知能力是有差异的。正如我们身边生活在同一个街区的人,有的能准确描述不同楼宇的位置、路线和距离,有的则可能被称为“路痴”。同样生活在长安的唐代诗人,并不都像白居易一样能“脑补”长安各种景观的位置、路线。当然,“空间感知”能力也与后天习得的空间知识和信息密切相关。白居易在长安生活近十五年,他的住所和工作地都经历了大范围的挪移,这是他接触更多空间信息的契机。而另外一个空间信息则来源于纸上,尤其是地志和舆图。这有白居易诗文的内证和其他外证。白居易《题洛中第宅》说:“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唯展宅图看。”①这里提到了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当时城中宅第有“宅图”。白居易另外一首诗《闲行》中也说:“专掌图书无过地,遍寻山水自由身。”②虽然是对担任秘书监一职的回应,但也证明他对于“图书”的关注。白居易此前曾为秘书校书郎、集贤校理,都与“图书”整理有关。白居易诗歌的结构和叙述,也颇有舆图视角的特征,或者说 “图景式”色彩,如长安研究者经常引用的《登观音台望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③这种俯视视角,颇有我们看当代卫星地图的感觉。
从外证来看,白居易所处的时代是中古地理学或者说地理知识突破性的时代,以《元和郡县图志》为代表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具有集大成的意义。此外,贾耽《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在制图学及中外交通上也是重要的突破。白居易的为官经历也需要他有地理知识的支撑。元和十五年,他从忠州召回拜司门员外郎,“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④,这自然需要相应的知识和图籍,白居易诗中对于各种关、门、津、渡的熟悉应该也与此有关。白居易曾编纂过一部类书《六帖》,其中收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其卷二十三“水田门”中内容与敦煌写卷《水部式》有渊源关系,后者包含了唐代两京沟渠、斗堰、桥梁等各种信息,一些能在白居易诗中找到对应。
当然,具有很强的空间感知能力、同时有很丰富的地理空间知识,要在诗歌中呈现出来,需要有这种叙述的意识,还需要相当的文学技巧。美国华裔学者王敖对于中唐地理学的发展与文学的关系有最新的研究,他也注意到了元白唱和诗中的空间地理同步现象。⑤空间并置和比较在元白诗歌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并且内化为二人的一种观念——通过“计程”,推算二人空间的离合。白居易长安空间诗歌的叙述中也有类似空间并置,我们可以称之为“空间耦合”关系,这是一种空间自觉意识投射到文学文本中的结果。妹尾达彦先生敏锐地注意到:“白居易的诗歌用对偶句的方式把两京对照性的特征作了机械性的描写。”⑥王敖则将元白诗歌中地理比较称为一种“双联”形式,即将地理信息相对仗的独特技巧。通过对仗、意象并置、叙述视角、结构形式来呈现“空间耦合”情形,也是白居易长安诗歌空间表现的重要形式,如《闻崔十八宿予新昌弊宅时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一宵偶同两兴暗合因而成咏聊以写怀》:
陋巷掩弊庐,高居敞华屋。新昌七株松,依仁万茎竹。松前月台白,竹下风池绿。君向我斋眠,我在君亭宿。平生有微尚,彼此多幽独。何必本主人,两心聊自足。⑦
“一宵偶同、两兴暗合”这并非巧合,而是刻意的安排。白居易对这种人物的空间并置有非常清楚的認知,并且在诗歌书写中有意进行关合,这首诗尤具代表性:前八句都是并置,后四句是合写。这种空间意识对于白居易诗歌的内在肌理显然已经产生了实质的影响。进而言之,白居易对于空间的自觉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心理(动机、灵感)和创作过程(构思、布局)。白居易的一些长律诗,就局部采用了两个空间或者多个空间耦合的结构方式,如《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