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坐过的台阶
2022-04-11 04:58陈年喜
视野 2022年6期
/陈年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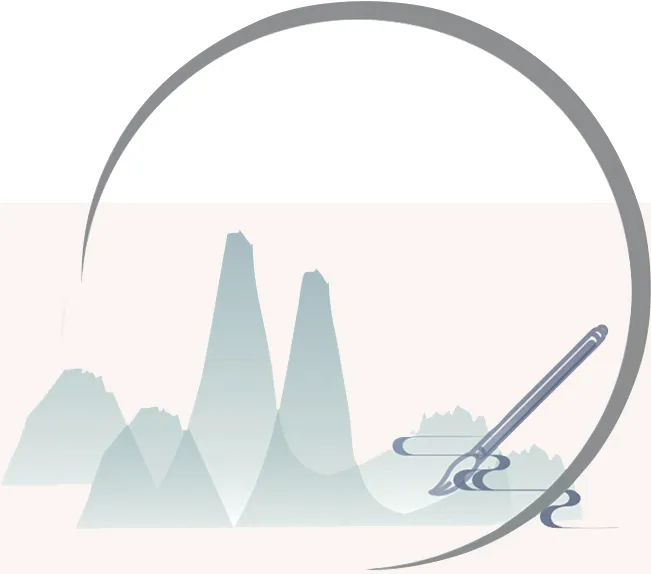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写作,我也没有答案。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会突然失声笑起来;或者夜深人静时,会突然用被子裹住头,泪流满面。
记得有一年,与一群人颠沛到黄河三门峡一个叫槐扒的黄土峡谷段,彼时初春无雨,源头雪山未化,黄河裸露出一节节嶙峋的河床。
这些流水和时间坐过的台阶,向远方铺排。它们经历了什么,见证了什么,又似乎一无经历和见证。
我们坐过流水,又被流水坐过。彼此留痕又彼此忘却。
逝水流长,追赶春天的人一身霜白。春风与朔风互为永恒,欢欣与悲伤互为永恒,生与死互为永恒。人在无数永恒之物间穿行,倏忽而过。
一地霜白,愿白霜超越本身,愿霜色如华,照彻行色匆匆的人。
猜你喜欢
娃娃乐园·综合智能(2021年12期)2022-01-18
翠苑(2019年4期)2019-11-11
创新作文(1-2年级)(2018年11期)2018-04-24
发明与创新(2017年42期)2017-12-04
大众科技(2015年12期)2015-11-24
学习月刊(2015年16期)2015-07-09
发明与创新(2015年33期)2015-02-27
学生天地·小学低年级版(2014年10期)2015-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