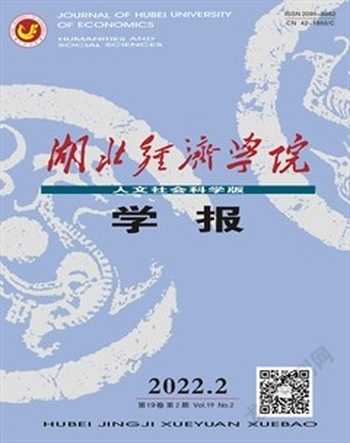网络共同犯罪中意思联络的重构
缑开心
摘要:意思联络作为共同故意的特殊构成要件要素,在互联网犯罪中难以按照传统理论加以认定。我国实定法对意思联络已作出明确规定,在互联网犯罪的场合下也仍应坚持意思联络这一共同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呼应网络犯罪这一特殊场合,对意思联络应作符合时代要求的解读,对缓和说也应当作出肯定和拥簇。在意思表达形式上加入符号语言等新型沟通表意方式,故意的程度选择未必故意即可达到意思联络的缓和认定。对于处罚范围有可能扩展的风险,应通过个罪的考察加以限定。
关键词:共同犯罪;犯罪故意;意思联络;未必故意
一、意思联络的必要性
(一)实务中的挑战
案例一:2016年6月,被害人张某通过中介人员冯某和当时身为吴中家天下的物业经理被告人王雷租赁了吴中家天下新三期17栋地下库房存放红酒及茶叶等。此后,被告人王雷对他人包括对被告人刘昊自称库房内的酒类等物品为其个人所有:并曾取走库房内的红酒三箱,经鉴定,被盗物品价值共计人民币2160元。2017年7月7日被告人刘昊在与被告人王雷的往来中,要求被告人王雷按约定给付其红酒,王雷微信回复可以给其拿钥匙,在被告人刘吴表示钥匙拿得晚就撬开库房自己拿,王雷回复“0K”微信表情,于是被告人刘昊撬锁并搬走红酒七十箱左右和茶叶五盒。经鉴定,部分被盗物品价值人民币101160元。2017年7月末被告人刘昊在未经被告人王雷及被害人张某允许的情况下私自盗走10箱红酒。经鉴定,被盗物品价值共计人民币6900元。本案案发时王雷并无权限管理吴中家天下地下库房的租赁①。
案例二:2018年12月上旬至20日期间,被告人孙飞、单大伟为非法牟利,组织工作人员、招揽赌客以麻将牌玩斗牛的形式,在苏州市姑苏区白塔东路棋牌室以及大光明影城7楼棋牌室进行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自2018年12月10日至2018年12月20日,该赌场共抽头渔利人民币153000元。经查,2018年12月10日至案发,在该赌场负责抽取庄风款的华某共向单大伟等人发放代表抽头渔利金额的微信表情274个,合计金额人民币14800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孙飞、单大伟、孙孝进开设赌场,情节严重,均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告人孙飞辩称:赌场未经营时华某发的微信表情头像不应认定为收取庄风款的依据。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均未对华某的行为提出异议②。
(二)学理上的反思
网络进入中国20多年来,信息产业加速增长,网络犯罪也呈现出与之匹配的发展态势,其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链条性、合作性、产业化特征,在此过程中,网络犯罪逐步形成定型化,暴力犯罪案件数量持续下降,传统违法犯罪向网上蔓延。网络犯罪占犯罪总数近三分之一,可以说已经成为第一大类的犯罪类型。互联网使得各个国家、地区的人们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实现沟通交流,信息的获取和交换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因此,网络犯罪较之传统共同犯罪凸显出极强的跨区域性,这一点在犯罪地的认定上尤为突出②。同时,网络犯罪具有无现场性及高收益性的特征。
我国《刑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传统理论将这一条款拆分为三部分,即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共同行为三部分。在“共同故意”这一条件要素下,又特别要求共同犯罪参与人需存在意思联络。然而,网络环境下符号语言等新型沟通表意方式的出现,为意思联络的认定也创造了新的障碍。传统共同犯罪中,犯罪团伙多为空间内的紧密联合体,表征出联系紧密的合伙状态,就犯罪的共谋和决意也鲜少有新形势下的变异表达出现,转换到新型互联网共同犯罪中,意思联络的外在载体已然出现变革。作为共同故意的特殊构成要素的“意思联络”,无论是放弃这一要素直接认定成立共犯,还是缺乏这一要素就不成立共犯,然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何种程度的意思联络就可以达成共同故意这一条件。说到底,理论的认定终归需要回到法条的射程之内。因此,在互联网背景下,如何在维持刑法第25条共同犯罪对共同故意的需求前提下,对意思联络做何种缓和的解读。也即:当意思联络现出何种样态就可以认定犯罪参与人达成共识具有共同故意,是本文阐释的重点。
二、互联网环境下的共同犯罪
普遍认为,网络犯罪具有异地性、无现场性及高收益性的特征。网络犯罪所处的网络空间具有显著的技术性与虚拟性,利用网络技术实施网络犯罪呈高度增长态势,日益促使网络空间成为新型的犯罪场域,并开始向现实社会延伸,对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与冲击不断扩大。网络空间的普及化与技术本身自然形成的虚拟性提供了更便捷、更低廉的准入条件,网络空间的社会关系化迹象日益明显利用網络实施的犯罪行为需要技术性的支持,还需要有人实施具体的前期骗取受害人的信任及后期提取、转移赃款乃至分赃等犯罪行为。因此网络犯罪更多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阿。
本文将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做区分抽离,将两者短暂划分为两个存在空间,以此对共同犯罪中的意思联络这一要件做对比分析。现实空间内自然人表现出唯一生命体性,表露为行为人受物理空间的限制,要达到某一行为目的必须以自身身体为行为媒介。具体而言:共同犯罪的行为人若想使其团伙成员获知共同犯罪的实行计划,或是在犯罪沟通中达到畅通的效果,必然要经历物理空间的转移,从而达到双方意会的目的。而互联网空间内受P和D及其网络平台的影响,自然人呈现出多平台存在的特征。申言之,一个自然人个体可以拥有多个网络平台账户,在互联网平台的扩散下,多个社交账户即可看待成为自然体的分裂者,表露出现实空间内不曾表露的多种个性。这一个性特征有可能完全违背个人性格,也有可能无限贴近“本我”,暴露出在现实法治社会下被压抑的一面口。前述特质本无特殊性,一旦自然人借由互联网进行共同犯罪时,现实条件下自然人分散性的问题会呈现出多种有别于传统共同犯罪的区别。其一,现实空间内行为人就故意内容等沟通时,时间、空间上的差距在互联网平台上被消融,自然人集中在网络平台内,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犯意表达可以通过留言的形式被其余行为人获知,因此意思联络也可畅通无阻。其二,在国家管控尚未形成密网的当下,行为人借由互联网隐秘身份的特征也会给侦查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有必要对互联网空间和现实空间内的意思联络作比较分析,以探寻网络共同犯罪中意思联络的重构出路。
(一)联系:双重空间下意思联络要件的同一性归纳我国学界关于意思联络和共同故意的关系通说认为,意思联络是共同故意内容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主观的认识要素。我国《刑法》第25条中规定的共同故意,其“共同”则意指犯罪参与人要有意思的互通有无。因此不难得出结论:意思联络是共同故意的形成前提。如果在共同故意的讨论框架内否定意思联络,后果则为否定共同故意。因此,如若讨论共同故意犯罪,则必然需要意思联络的存在。此点无论是现实空间亲手共同犯罪还是猎由互联网平台的共同犯罪都不能回避的中心点。
1.意思联络的表达样态
从意思联络的表达样态分析,意思联络应当具有明确的传达性,也即意思联络的参与人应当就意思联络本身达成故意,从而表现出明示的意思联络。前述提到,我国实定法的范畴内并无片面共犯的立身之地,因而默示的意思联络也不应当成为共同故意犯罪的主观要素,唯有明示的、明确的意思联络,具有外向型、内含意义,可被传递、获知的意思联络才应当是共同犯罪中的意思联络。
2.意思联络的行为样态
从意思联络的行为样态分析,意思联络的达成需要经历发出、传递、接收、反馈、合意五个部分。传统的共同犯罪构造中,诸犯罪参与人以其语言沟通为意思联络传递,双方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完成上述五步骤,更因其共同故意盖已达成,事后追究时也很容易定性。以致鲜少有人按图索骥判定是否具有共同故意。而在网络犯罪中,这五个步骤的特征因其交流的互动化表现出更明显的特质。例如,在曹帅、张成祥等诈骗案中:曹帅等人通过互联网组织开办了视频聊天室,向网络用户虚假宣传该聊天室能提供裸聊等色情服务,吸引网络用户登录该聊天室并注册会员,后该聊天室又以享受色情服务需要提高会员级别、提供主播安全保证金、提供退款和建立、恢复数据档案押金等虚假事由,骗取该聊天室网络用户充某人民币3063191.6元③。本案中,曹帅以互联网手段向符某发出租用其视频网站的请求,此请求经腾讯QQ平台传递,符某回复,回复消息回馈至曹帅等人的QQ账号上,并以第一部分500元人民币达成租用符某假设的程序从事网络色情诈骗一事达成合意。因其有网络社交平台的沟通留痕,上述五个步骤可一对一对应验证。概言之,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互联网空间,意思联络的合意仅存在步骤清晰明了抑或笼统完成的微小区别,但整体而言都需要联络双方就意思表示发出直至达成合意的五个步骤,达到最低程度的共同故意的要求。
(二)区分:双重空间下意思联络特征的差异化对照网络空间内诸多特征使得共同犯罪中的共同故意也出现内容不充分、表达方式不明朗的特征。相较于以往共同故意辨析明确的特征,寄生于网络平台的共同犯罪在共同故意的表现方式上呈现于弱化趋势,打破了以往共同故意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存在基础和共识。共同故意内化于意思联络,因而这种模糊性、隐秘性、不确定性在意思联络这一要件上表现更为突出。互联网犯罪发展至今呈现出其特定的犯罪形态表示,从个罪偏向来看互联网犯罪多分布在诈骗罪、网络赌博犯罪等罪中,从犯罪参与形态来看互联网犯罪几乎倾倒性偏向共同犯罪。尤其是借由网络平台制作线上赌场案件,近年来频频发生,而此类案件的难点多集中在共同故意的认定上,也即意思联络不能通过传统书证、物证分析认定。在一项有关共同故意的证据认定中,有数据表明:意思联络的合意可经由微信聊天记录、相册照片、暗号语言符号等达成。前述传统刑法界域内的意思联络认定方式面对信息化的新型犯罪显得捉襟见肘,而这种尴尬的局面正是由意思联络的嬗变所引起。易言之,在人员众多、物理空间分散的网络共同犯罪中,意思联络传递者不再表现出明显的易判定性,而是通过网络平台内各个网站的D昵称表达。同样,意思联络这一表达形态也脱离了原有的点对点、近距离表达,演变为点对面、远距离超越时空的沟通。可以说,意思联络作为共同故意认定的一个特殊构成要件要素,在网络时代的影响下,已经产生了本质的改变。分述如下:
1.时空特征对比
其一,互联网传播的一大特征即借由社交平台的传递,表意反馈不再是需要等待的复杂过程。在互联网条件下,行为人一方发出信息,另一方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但只要共处一个社交平台,就可以无视地理空间上的差异,及时收到前行为人发出的指令。与其相反,现实物理空间内的共同犯罪多数为团伙作案,普遍具有共同生活的特点,当行为人需要共谋犯罪意图及过程时,犯罪共同参与人表露出面对面沟通交流的趋势。受制于这一表象,当传统共同犯罪的参与人不再同处于一个内部空间时,犯罪意思的沟通则受阻于物理空间上的障碍。
其二,互联网联络的社交性也决定了“群发”这一功能具有现实空间不可对比的替代性。当一个犯罪计划需要被更多的人了解意图时,网络共犯常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建立群聊,以达到一对多的传讯目的。例如前述曹帅、张成祥等诈骗案中,对被害人应作如何行为指令、被害人前期不信任时应如何沟通等,这一切由曹帅、张成祥管理的群聊控制,及時与其手下“小弟”沟通,操控其言行,从而顺利达到使受害人心甘情愿相信骗局交付财产的目的。反观传统诈骗案,犯罪团伙的指令指挥呈现出“层层下达”的趋势,为金字塔机构,这就导致一旦被害人怀疑犯罪行为对接人的言语诱骗时,上层头目不能及时操控整个骗局。因此,分析新型网络诈骗案件及传统诈骗案,不难得出网络诈骗因其意思联络优势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概言之,互联网空间条件下的意思表示因其即时性、广泛性的特点突破了现实空间物理上的限制。
2.身份特征对比
尽管2017年10月公布的规定,要求平台受国家监管,需要用户实名认证身份信息④。互联网终端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始终隐藏在各个平台的D之下,当用户不想表露昵称背后的真实信息时,网友无法通过合法的技术手段获得其真实身份。并且,仍有一部分网站对于实名认证的审查多处存在漏洞,导致盗用、冒用、过期身份信息等假认证过审。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合法匿名”的规则之下,互联网犯罪的各个参与人免受被“队友出卖”的威胁,从而加大了犯罪活动空间。如前例曹帅、张成祥等诈骗案中,曹帅购买的软件程序开发者“老K”与行为人沟通时仅使用此代号,因其隐匿在D背后,“现有证据不能确定符某就是老K”,使其仍逍遥法外。并且,匿名性的存在还导致犯罪参与中间人对整个犯罪流程仅了解自身负责的一部分,对上下游的犯罪参与人仅了解他们的网络信息,而在现实中毫无交集。这种对接也加大了链条式犯罪上下游破案的难度。如继续忽视这种匿名性带来的意思联络,那么带来的后果有可能是共犯关系在这类网络犯罪中却消失殆尽了。可以说,网络环境下犯罪参与的行为人借助平台D匿名性的特点突破了现实空间真实性交往的限制。
3.符号语言与文体语言对比
传播方式的丰富致使面对面的肢体语言、口头表达不再成为意思联络的唯一选择方式。网络共同犯罪中的行为人除文义表达之外,拥有了更多表意的语言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自互联网出现才开始拥有除肢体语言和口头表达之外的表意行为。需要纠正的一个误区是:网络共同犯罪的出现仅仅是更加凸显了非自然语言的沟通方式及现象。在传统典型的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参与人之间的意思联络也未必都是以口头语言或肢体语言表达出来的,德国刑法学者普珀教授指出,在共同犯罪场合,存在“可推断的犯行约定”。6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犯意表示可能并不通过清晰、明了的语言或是肢体动作完成,而是选用其他的符号语言完成沟通一致的犯罪合意。这种低层次的犯罪合意延伸到网络环境下,演变成了外表更具模糊性、表意靠心领神会及提前约定好的符号语言完成。
例如在祝志祥、邓洪伟、彭奋等组织卖淫案中⑤,犯罪行为人供述:“其每次卖淫之后都会给他发一个笑脸的表情,代表卖淫一次”“祝志祥让其加了邓洪伟的微信,让其每做一个客人就发一个笑脸的表情给邓洪伟,是对账用的”。卖淫女借由社交网络向祝其祥发送微笑表情时,就已经完成了“卖淫一次”的信息传达。又如潘益军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中,“被告人潘益军多次在得知公安机关接警后,即通过微信发送表情包的形式向郎某通风报信,帮助开设赌场的犯罪分子郎某等人逃避处罚”。而放哨的人发送特定表情包时,开设赌场的郎某就获得了“警察马上要来的”信息传递⑥。如将此案换置在传统卖淫案件环境中,记录卖淫次数需要账本计数:放哨消息需要电话或短信层层传递,甚至通风报信一次只能完成点对点的报讯,而借由网络平台做联合平台,放哨人可以瞬间达成点对面的消息汇报。因此,以符号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意思沟通方式是当下互联网共同犯罪的故意推定的一大壁垒。
三、网络环境下意思联络程度和方式的重构
网络环境背景下互联网语言与传统表意语言的对比表征出信息社会交流形态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对意思交互的载体和途径产生了新的影响。如前所述,一方面互联网的群聊、群发功能使得意思联络不再局限于点对点的现实交接状态,另一方面自然人借由互联网隐匿在社交平台昵称之后,链条式上下游犯罪中的行为人可能对彼此的身份互不知晓。这种匿名网状交流的方式既影響了意思联络的程度,又影响了意思联络的方式5。传统的犯罪共同说要求行为人之间的共同故意完全一致,意思联络的状态必须完全一样;部分犯罪共同说也要求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内部有重合的部分,即意思联络须得有同样的地方;后期客观主义立场的行为共同说尽管并不要求数人必须具有共同实现犯罪的意思联络,但也要就实施行为具有意思联络2。在最低限度下的意思联络里,也要求以个人联系为基础建立意思联络。而这种二人联系,通常以点对点联系以及同一空间为纽带。但互联网社交平台以及诸多网站的建立,使得这种交互性对现代人的交流沟通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互联网亚文化的流变使得网络空间内的表情包语言、网络热门流行语成为网络上人尽皆知的意会语言符号。也因此造就了以互联网为平台,实施共同犯罪的犯罪参与人之间的意思联络的方式程度展现出了极大的改变。
为了使基于互联网条件演变的新型网络共同犯罪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考虑互联网特殊性以及维持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的共同故意这一共犯构成要件要素的基础上,应当对意思联络作出新的理解,使其满足共同故意的需要,从而划定网络共同犯罪的边界。
(一)意思联络程度的缓和:故意层级的选择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了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传统理论将共同拆解为共同行为和共同故意,分别归入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中。这就要求,行为人不仅需要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而是和犯罪同伙一起实施。再者行为人还需要和犯罪团伙就整个犯罪计划实施共谋。我国刑法学者高铭暄教授指出:“共同犯罪人认识到自己和他人相互配合共同实施犯罪”,就是承认犯罪参与人需要共同性,且这种共同性需要被认知。在这种解读程度上,共同性中包含的共同行为和共同故意应在同一位阶内被探讨,也就是客观上的行为共同性和主观上共同的意思联络具有同等性。外在的行为共同可以通过犯罪参与人的实行行为进行判定,主观上的意思联络虽然包含心理性共识,但这种心理性共识是以各方的共同认知而存在,因此也是心理认识的外在客观化表达。对意思联络的缓和也就意味着对于故意层级的再解读,在双客观要素的共同性需求下,使用要素叠加的思辨方式对意思联络程度的选取更具有说服性。
德国刑法将故意分为三个等级,即:蓄意(第一级直接故意,Absicht?)、直接故意(第二级直接故意direkterVorsatzoder-dOLusdirectus)、间接故意(bedingterVorsatzoderdOLusdirectus),在以上三个等级的划分中,一级故意通常含有目的性的寓意,行为人追求构成要件情状的实现,并且希望通过他的举止能引发这种实现,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行为人具有第一级的故意,即有目的地加以追求的事件是行为人行为的主要结果。
二级故意通常是指“确定性认识的故意”作为故意的形式。如果行为人认为实现该构成要件情状是它所采取的举止的必然结果,那么,他便具有了第二级的故意。在这个意义上,第二级的故意通常和我国刑法理论中的“明知”一词的含义非常接近,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存在质疑的点在于:明知的认识结果都包括哪些要素,是指行为人必须认识到结果是危害社会的,还是只要认识到结果,而该结果被普遍评价为危害社会的即可。当下我国通说认为:明知作为符合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了作为判断基础或者判断资料的事实,原则上就应当认定行为人认识到了符合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即行为人具备了明知所要求达到的条件2259,第三级别的故意(也称间接故意)通常被理解为“有条件的故意”,与一级二级故意相比,三级故意在认识因素上并没有确信,而只是以为结果发生有具体的可能性。简言之,间接故意并不要求以目标为导向的欲望(wOLlen)。
因此,为了达到意思联络缓和的目的,在互联网共同犯罪的场景下,考虑意思联络是否存在时,应当将最低限度设为二级故意,也就是说,如果蓄意这一特征无法判断时,至少应当包含直接故意,也就是明知。但显然还是存在问题:如果仅仅以这种揣测对方心理展开行动,同时这种瞬时间完成不清晰的沟通就能认定双方就某一实行行为达成共识,是否有极度扩张处罚范围的嫌疑。于是需要考虑以下问题:在何种场合下行为人之间具有二级故意的意思联络即可,在何种场合下还需要一级故意的意思联络才行。这便是选择哪种符号语言与故意层级匹配的问题。
(二)意思联络方式的缓和:符号语言的选择
在人与人的沟通过程当中,人们可以根据对方的面部表情、语速、声音、语调以及手势动作判断其所处的心理状态。通常这种沟通方式被划分为三种:口头沟通、书面沟通以及非语言沟通阿。在网络成为主要沟通桥梁的当下,书面沟通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表情包等符号语言作为一种图像化的非语言的视觉交流符号,在更短的时间内呈现出丰富的含义,交流者可以直接进入到对方的情感世界中获知对方给予的信息。因此,在网络社交中表情符号被非常广泛地运用。
符号语言的传播过程通常由“编码”和“解码”两部分构成。传播人在未展开传播时对想传递的某种信息作出解码,然后依照特定的文化语境,将表达含义融入表情,最后采用特殊的形式对社群内的人展开传播。进一步,在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网络共同犯罪中,符号语言因上述这种特性也被赋予了作为意思联络媒介的这一功能。表现在曹帅、张成祥等诈骗案中,即:曹帅等人需要一个不易被侦查的暗号完成卖淫次数的统计,对此需求进行解码,继而对“完成卖淫一次并获得收入”这一信息按照卖淫窝点的约定俗成进行编码,将此信息融合在“微笑”表情中,然后对它进行传播使用。当整个卖淫团伙对“发送微笑表情就表示卖淫一次”这一特殊信息均已了解后,卖淫女给曹帅等人发送微笑表情,曹帅即可获知卖淫女成功卖淫一次的信息。
多元感官化的视觉传达成为网络社交的一大特征,无论是基于平常交互而采用的表情包、emoji⑧还是在特定社群中流传的暗号,都成为网络社交背景下无法回避的一种特殊语言。当这种特殊语言被犯罪分子拿来做规避侦查风险的道具时,应当对以符号语言作为意思联络媒介作出相应的规制。由此,对于网络社交背景下的互动群态,宜将符号语言分为两类进行不同的探讨。即:无约定的符号语言和有约定的符号语言。
1.无约定的符号语言
通常为了使某目的在传播中拥有最大化的传播范围,人们更偏向于用视觉修辞的方式来对传播媒介加工。一方面使以文字语言或图像语言作为媒介达到视觉效果或进行视觉上的理解认知,另一方面是在图像的基础上辅以语言文字等m。例如在微信社交中,发送“呲牙笑”表情,接收者瞬间就可以意会对方给予的善意和传递的情绪。这种不需要特别加以注解、社会普遍能理解的语言符号即为本文所指无约定的符号语言。
无约定的符号语言的范围涵盖了以一般人标准作为判断依据的情况,无需特别约定,就可以解码该符号指代的含义。这里通过一起民事纠纷佐以阐释:承租方租赁期满后,面对出租方多次提醒、提出加租意愿时,既不表示继续承租,也不表示搬离涉案房产,只是回复了一个“太阳”的微信moji表情。这个表情符号在出租方看来即为对加租的认可,而承租方提出了反对意见,因此对出租房提出诉讼⑨。该案件二审法官经审理,支持了出租方的诉求,判定应当認定承租方同意按照加租后的标准继续承租。这也说明,判决书支持了这种无约定的符号语言作为表意的有效性、传递简单意思的准确性。
2.有约定的符号语言
有约定的符号语言一般产生在特定社群的环境中。无论是基于网络环境而聚集在一起的社群还是某固定物理空间聚居地的社群,因其长期交往的特质,从而产生了因风俗而依存的某些话术。而这种解码和编码就是对特定内容指代的约定。因其符号内涵常常不为外人所明知的特性,这种约定之后存在特殊含义的符号语言更加明显活跃于犯罪活动中。如在杨昱衡、张宇危险驾驶一案中”。该飙车团伙均默认“今晚炸街”的意思就是轰油门、轰排气,“炸隧道”是隧道内急加油的意思。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炸街、炸隧道含有爆破的意思,而这个符号表情并不能令一般人联想到飙车行为,因此只有在特定的团伙中,才会产生这种独特的解码和编码行为。当一个符号语言表露出不具有它被大众所了解的特质时,不能直接认为该符号无意义,仅当无人定义、无社群情况下,个人独做这种编码的情况下,才能认为这种符号语言没有约定,不能有效传递其行为人的意思和意志。
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当符号语言被约定含有某种特定意思的时候,并不意味这种约定存在唯一性和独占性的特征。不同社群对于同一符号可能存在不同的解读,因此有约定的符号语言之特定含义通常仅对社群内的人产生预先设定的效力。
四、对网络共同犯罪的具体演证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了共同犯罪,剖析其构成要件可以明确共同故意的必要性,意思联络应当为共同故意构成不可或缺的一项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在寻求片面共犯理论作为解决无意思联络或默示意思联络困境的出路未果后,当认定我国共犯的构成仍需犯罪参与人的意思联络,此为认定共犯构成的基础点。前述提出,意思联络作为一项主观构成要件要素是共同故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当各个犯罪参与人之间被证明具有意思联络时,就可以推定其具有共同故意。而当犯罪行为人以互联网为平台实施共同犯罪行为时,意思联络的方式和程度的显性特征大多已消解在互联网发展变迁的特性中,通常不容易被侦查到。
当典型的共同犯罪演变成为互联网犯罪时,在维持我国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故意的条件下,对意思联络的缓和理解可以如下作出新的公式解读,这样更有利于细致地划定互联网共同犯罪关系的边界。
(一)两个判定公式的提出
1.第一级直接故意+无约定的符号语言=存在意思联络。当犯罪参与行为人为临时起意纠结而成的犯罪团伙或并非存在一定规章制度、层级分明的犯罪团伙时,其内部沟通如采取社会一般人也能理解的符号语言做意思传递的媒介,在这基础上,如犯罪嫌疑人实行行为时具有带目的性的故意,即前文论述的一级故意,即可认定该犯罪行为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即,第一级直接故意+无约定的符号语言=存在意思联络。
将行为人的主观行为目的限定在第一级直接故意这一层级,即行为人须有明显的、包含目的性倾向的故意,在这基础上,如果行为人之间表意传递的媒介为无约定的符号语言,就可以认定行为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继而认定行为人具有共同故意。在犯意明显表示的意思联络案件中,需要行为人达到蓄意的故意程度才可以。
2.第二级直接故意+有约定的符号语言=存在直接故意。当犯罪参与行为人并非临时起意,而是长久厮混在一起的固定犯罪团伙或者虽然为松散的团伙关系,但领头人就某暗号代指何种行为做了规定,在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参与的行为人只要知道暗号、符号代指何种情况,并依然实施被分配的实行行为,就可以认定实施行为的犯罪参与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即,第二级直接故意+有约定的符号语言=存在直接故意。
当行为人之间存在或可能存在社群关系,同时基于这种群落关系对某些符号语言的特殊解读,当犯罪参与的行为人对其他行为人的表意存在明知的认知程度即可判定二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在犯罪参与人为同社群成员,存在约定、犯罪参与人可以毫无障碍读懂对方隐晦词语下表达的真实目的的犯意表示及接收的情况下,行为人只需要具有明知的故意即可认定存在具有意思联络的共同故意。
值得注意的是,两项公式内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和不可替代性。当各个行为人之间已经就犯罪方式、手段、目的等达成决议,并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约定好某符号语言为某含义时,犯罪参与人的故意需达到明知及其以上。换言之,第二项公式中第二级直接故意为最低要求,如行为人具有强烈目的的犯罪蓄意时,可替代本项公式中对故意的要求。即有约定的符号语言为前置必要条件,故意的层级为可替代条件。
通常情况下,即使犯罪行为人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完成团伙之间的犯罪共谋,其共同故意并不理所当然藏匿于暗号或表情符号下,也未必具有上述疑难点,无法认定。本文所指需借助符号语言及故意层级认定意思联络是否存在的方式仅限定于传统表述中无法证实的一小部分共同犯罪案件。仅当各个犯罪参与人借由互联网做意思联络的媒介,双方以网络符号语言做意思传递的工具,并借此完成犯罪或隐匿罪证或组织望风等犯罪行为时,且在此类案件中,意思联络的推定无法按照固有的证据存在形态认定。上述情况为本文公式的嵌套规制。申言之,下述两项公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仅当前述类型案件存在的情况下,对意思联络的采纳应以此为认定法则。
(二)案例的效力证成
案例一中,刘昊和王雷二人显然并未就吴昊偷拿红酒茶叶一事进行充分的共谋,二人仅以微信为联络媒介,王雷最后给刘昊的回复也仅仅发送了一个微信表情。“OK表情包”是否可以认定为二人达成共识,这一点给盗窃合意的意思联络造成了举证的困难。分析本案可得知:首先,王雷一开始就在无权管理的条件下盗窃了三箱红酒。其次,刘昊要求王雷交付红酒时,王雷表示只能给其钥匙。于是刘昊告知王雷:如果王雷钥匙拿得晚,就撬开库房自己拿,王雷回复“OK表情”。在这一连串行为中,刘吴和王雷就盗窃行为一事的犯意联络于微信上完成了前述合意的五个步骤,在最后一步合意的反馈阶段,王雷采用了微信ok表情作为应允的表示。按照社会一般人标准,这种被大众广为赞同的符号标志就成为王雷和刘昊达成意思联络的媒介。因此,只要王雷在发出这个表情时认识到:“我发送的0k表情具有同意的意思,而这个表情无需提前约定,就可以被随机接收到这个表情的人获知我信息传递的内涵。”同样,刘吴在收到这个k表情时认识到:“王雷并没有就发送表情作出提前约定,因此0k表情意思就是他对我发出消息的认可。”再次,无论是王雷或是刘昊,在动手拿红酒和茶叶时,二人均知道这些东西归他人所有,但仍然行事。因此不难得出结论:王雷并刘昊二人就盜窃红酒一行为之故意为第一级蓄意的直接故意,同时,二人在沟通是使用了无约定的符号语言作为意思表达传播的媒介,从而达成意思联络的合意。故可认定二人为盗窃罪的共犯。
案例二中,根据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规定,孙飞、孙孝和单大伟之间就组织工作人员、开设赌场、谋取不正当利益一事上存在合意,此三人构成共同正犯毫无疑问。华某作为该赌场负责抽取庄风款并统计抽头渔利金额的帮助人员,却未受到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调查,这显然存在疑点。华某在该组织及其下设赌场内,并非组织外围人员,其工作行为涉及抽取款项、统计款项收人、向单某汇报抽头金额等行为,同时华某就约定好的何种表情符号为多少数额一事存在应然的认知,应当认定华某于该赌场能正当运转、并完成非法盈利数额统计一事上存在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华某理应被作为同案犯对待。华某可能存在疑问的地方正是能否以其发送的代表抽头的微信表情作为其有单大伟等人具有犯罪意思联络的证据。根据上述论证,华某作为一开始就参与在赌场内的知情人员,显然对单大伟及其同伙从事赌博一事明知存在故意,而其遵循团伙约定,以约定好的微信表情作为非法盈利次数的标记,正是前文所述,特定的社群内部以约定好特定的符号语言作为意思联络的媒介,映射在本案中,华某以该特定微信表情与孙飞、单大伟等人存在意思联络,而其对孙飞、单大伟等人从事的非法经营活动又存在明知的故意,因此应当认定华某为本案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人之一,宜以开设赌场罪的帮助犯对其定罪量刑,而非使其成为法外漏网之鱼。
五、结语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我国共犯理论的通说,该刑法条文可拆解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共同犯罪三部分。因此传统刑法理论模型下,行为之间应当存在,也必须存在就犯罪为中心的意思联络,如此方可符合刑法条文规定的共同犯罪满足的条件。当下我国互联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网络犯罪通常由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然而网络共犯通常借由互联网及时广泛、匿名以符号语言的便捷,给侦查和审查阶段中是否存在意思联络就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本文对意思联络方式和程度的缓和从四个方面入手作出新的理解。第一,意思联络的程度的缓和可以分为第一级直接故意和第二级直接故意的认定,即含有目的性的蓄意和明知这两方面。第二,意思联络方式的缓和可以分为无约定的符号语言和有约定的符号语言这两方面。以上述四方面为基础,提出两项证明存在意思联络的公式。其中,公式一为固定公式,具有不可替代性,行为人就犯罪故意至少应当达到明知的程度,而此处的符号语言是作为传统犯罪合意的网络变异体呈现;公式二中第二级直接故意具有被替代性,明知是这个层级故意的最低要求。当行为人同时具有约定好的符号语言以及明显目的的犯罪故意时,是本项公式的理想化模型。当行为人无法判定是否具有蓄意故意时,可以退而求其次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明知的故意。因前置条件已设定为须有约定的符号语言,因此故意的层级应为明知及其以上。基于前述各项要点以及上述两个公式的提出,应当能使基于互联网条件演变的新型网络共同犯罪中的意思联络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注释:
①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2018)吉0105刑初202号刑事判决书。
②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8刑初602号刑事判决书。
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苏0612刑初290号刑事判决书。
④国家网信办公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规定:落实实名制要求、配合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数据支持。
⑤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0110刑初508号刑事判决书。
⑥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2017)浙0723刑初426号刑事判决书。
⑦Absicht一词通常含有“目的”的含义,因此第一级直接故意通常含有于目的性故意的意思。參见[德]耶塞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⑧Emoji由1998年日本设计师栗田穰崇所设计,原为日文词汇,是一种由图形和文字组合的表情符号。我们常用的微信表情如哭笑、龇牙笑等均为emoji表情。
⑨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6民初9304号民事判决书。
①2020年1月27日17时5分许,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被告人杨昱衡在“跑山小分队”微信群发出“要不约一波炸街?”,邀约他人一起飙车,被告人张宇在当日17时55分许回复“晚点出来蹦”、“我去拿前途”,被告人杨昱衡随即回复“蹦蹦蹦”。随后被告人杨昱衡驾驶经改装的鄂A×xxxx黑色大众高尔夫GTI轿车(悬挂临时牌照)、被告人张宇驾驶临牌灰色前途K50轿车,伙同肖某2、王某、喻某1各自驾驶车辆从本市和谐大道出发超速行驶,被告人杨昱衡、张宇在湖团山隧道行驶时为追求刺激,相互追逐竞驶,随意变道、超速并行,超过限定时速100%以上。参见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0)鄂0192刑初415号刑事判决书。
参考文献:
[1]王华伟.我国网络犯罪立法的体系性评价与反思.法学杂志,2019,(10):129.
[2]张金璇新形势下网络共同犯罪的现状与防治[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2019(12:113.
[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7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64-166.
[4]王牧新犯罪学(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217
[5]孙道萃.网络共同犯罪的多元挑战与有组织应对[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3):147.
[6]白海娟.论共同犯罪理论的网络异化[J]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4):21.
[7)]陈绚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62.
[8]韩卓瑞.论《刑法》第25条中的共同故意.吉林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9]王志刚,高嘉品.链条型网络犯罪中的“共同故意”证明[J]法律适用,2020,(15):111-112.
[10]米铁男.共犯理论在计算机网络犯罪中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案[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0):55.
[11]Puppe,Der gemeinsameTatplan der Mitt?ter,ZIS2007,234,238.引自:吕翰岳.互联网犯罪中的意思联络法学评论,2017,(2):156.
[12]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
[13][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著,蔡桂生,译.刑法总论教科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9-142
[14]陈磊.类型学的犯罪故意概念之提倡:对德国刑法学故意学说争议的反思[J].法律科学,2014,(5):191.
[15][美]斯蒂芬·P·罗宾斯著,慕云五,尚玉帆译.管人的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106.
[16][英]斯图亚特·霍尔,孟登迎译.文化研究:两种范式[J]文化研究,2013,(2):305-308.
[17]魏然.网络表情符号的视觉修辞分析[J].东南传播,2016,(10):10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