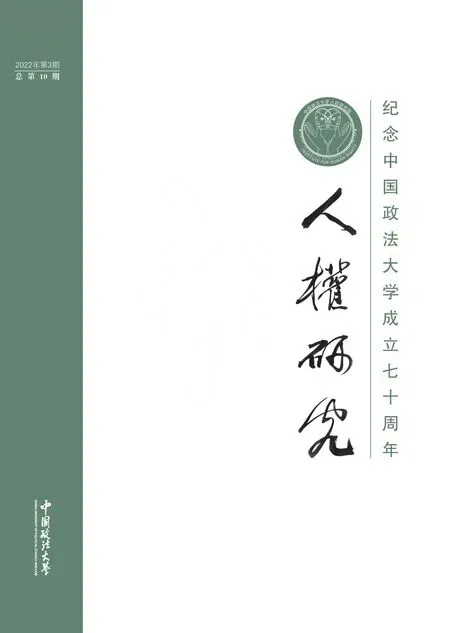从信息权利到信息人权:法理证成与分层建构
李 蕾
一、引言
《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之后,诞生了多种新型“信息权利”。人权学者们试图将其纳入“新兴人权”的范畴。“新兴权利”“新型权利”“新兴人权”均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但是它们能够描述信息权利在不同阶段的特征。在最初阶段,信息(数据)权利表现为个体的主张,此时权利停留在“应然”层面,尚未被国家基本法律所确认(“新兴权利”阶段1参见谢晖:《论新兴权利的一般理论》,载《法学论坛》2022年第1期,第42—45页。)。随后这些主张会进化为司法诉讼请求,当事人试图通过裁判让国家认同这些权利,例如国内被遗忘权第一案1该案的原告是自然人任某某,他认为以前供职的公司名声较差,要求网络公司删除自己与该公司相关联的信息,但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中并没有支持任某某的诉讼请求。这说明“被遗忘权”在获得法律确立之前已经在个人司法诉求中出现,只是这个诉求未获法院支持。参见任某某诉北京市百度网讯科技公司侵犯名誉权、姓名权、一般人格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人脸识别第一案2在该案中,杭州野生动物园违法采集游客郭某的信息。人脸信息属于高度隐私的生物信息,在商用领域要严格进行限制,终审法院最终要求动物园方删除游客脸部、指纹等生物识别信息。这说明即使尚无人脸识别的相关立法,但基于人格隐私以及信息采集的正当性、必要性原则,法院承认了个人对高度敏感生物信息的自我决定权。参见郭某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浙01民终10940号。、大数据杀熟第一案3该案不仅关乎个人隐私信息采集权限,还涉及“算法歧视”。一审原告胡某是某旅游平台应用程序的贵宾客户,但未享受高级别优惠,反而相较一般用户需要支付更高房价。终审法院判决该旅游平台退还原告差价,支付三倍赔偿金,并要求该旅游平台更改服务协议与隐私政策。参见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诉胡某侵权责任纠纷上诉案,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浙06民终3129号。等(新兴权利的司法证成阶段4参见王方玉:《新兴权利司法证成的三阶要件:实质论据、形式依据与技术方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第113—129页。)。信息权利的成型阶段是国家通过制定法对其进行保护(“新型权利”5参见谢晖:《论新型权利的基础理念》,载《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第7—8页。阶段)。当信息权利进化到成熟阶段,人权学者希望其成为一种“新兴人权”。
信息权利的客体、结构较之传统权利有较大更新,它们在社会实践中呈现出“新”的样态和“新”的现象6参见姚建宗:《新兴权利论纲》,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第5页。。信息权利的出现引起了人权实践和理论上的挑战与争鸣。其一,虽然权利与人权在正当性论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信息权利还未上升为信息人权,需要通过法理证成范式或人权哲学理论证明信息权利的人权属性。其二,部分信息权利与传统人权的衔接路径需要进一步确认,信息权利与传统人权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平行、互补还是兼容式同步更新,需要权衡与选择。其三,信息权利上升为人权,应当回答信息权利在人权代际体系之中的地位问题,即信息权利属于第几代人权,并且需以多维度视角辨析信息人权内部的多重利益博弈与道德属性。
二、从信息权利到信息人权的法理证成
(一)信息权利还未上升为信息人权
在众多人权学术文献中,学者对“权利”与“人权”的系统区分并不多见。本文认为信息权利与信息人权的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起源不同。信息权利的确立来自信息传播惯例、商业交易习惯,以及个人、组织、市场、公共领域的信息诉求。探索信息人权起源除了考虑上述情况,还需要结合人权法哲学的逻辑证成范式、人的普遍属性、人权的道德属性等内容进行研究。第二,表现形态不同。信息权利最原始的形态不是权利,而是合法利益与诉求,或是约定。这些形态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并且呈现碎片化的、不稳定的、表述模糊化的特征。信息立法出现之后,信息权利形态随之出现,它们分散于区域立法(欧盟相关立法)和国家内的公法、私法、经济法之中,有的甚至不以“权利”的字眼出现。信息人权一旦成立,其常态化的表现形式是纲领性的原则或规则,并应较多出现在人权宣言、人权公约、各国宪法总纲之中,具备整体性、基础性的特征。它必须比信息权利更加稳定、完整度更高,其确立过程之中要防止无效、碎片化人权类型的扩张。第三,效力等级不同。信息人权在等级、效力、科学性、风险预测能力上应当高于并优位于信息权利,它是判断各类信息权利合理性、正当性的评价标准。
(二)信息人权成立的法理证成范式
虽然信息(数据)人权被学者誉为“新兴人权”,人权学界也有人提出“新兴人权”这个概念1参见伍科霖:《新兴人权困境及其辨证》,载《人权》2020年第2期,第143页。,但信息人权还停留在专家、民众希望其获得人权认可的一种宣告阶段。信息权利作为新兴权利被提出并成为一种新型权利被国家立法所保护,最后上升为信息人权,需要严谨的法理证成过程。人权的法理证成范式是人权学说最核心的理论。所谓人权的法理证成范式是指对一项新的人权进行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证明的一系列科学方法论和定律,这些方法论和定律中蕴含着人权成立的基本精神、公理、法则与价值,以及一项新人权诞生的历史渊源与社会基础。
人权证成范式可以从法学理论方法论上进行分类。曾有学者总结过人权的两种推定模式(当时对人权进行论证使用的是“推定”一词):“经验式”与“先验式”。2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151页。后来有学者将“推定”变更为“论证”,并将人权的论证增加到三种范式:“超验论”“经验论”“先验论”。3参见周刚志:《论人权论证的三种范式》,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65页。还有学者将人权证成范式归纳为“自然法范式”“功利主义范式”“尊严范式”“关系范式”“尊重范式”。4参见管华:《人权证成范式批判》,载《人权》2016年第1期,第16—31页。此外,总结各类人权研究文献,可以根据权利的起源将人权范式总结为“历史范式”“习俗范式”,还可以按照价值目标对人权论证范式进行分类,如“理性”“共识”“自由”“平等”“需求”等论证范式。本文选择了几种主流人权证成范式作为信息人权成立的理论根基。每一种人权论证范式对信息人权的法理证成来说都有优势与局限。
首先,在人权证成范式的演进历史中,“自然法范式”是较为经典的法理论证范式。 “自然法范式”通过“先验论”“超验论”两种认识论实现。自然法认同先验的普遍正义。德国学者康德就认为自然权利以先验的纯粹理性原则为依据。5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9页。“超验论”集中体现在中世纪的自然法中,它以神学、神意为根基,主张人由上帝所创造,所有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超验视角下的人的本质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无论超验还是先验视角下的人权历史实践,人的平等均是以区分族群与等级为前提的。在近代,超验、先验论证均受到了文化相对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冲击。由远古时代的甲骨文、结绳记事、烽火传信就可以确定“信息”是人类的自然属性,理应存在一系列自然法确立人类信息交流的规则。由于自然法的黄金时代与信息时代相隔甚远,自然法自身的规则过于形而上且宽泛缥缈,这也使传统自然法论证范式的局限性凸显出来。
其次,在人权的论证过程中,“功利主义范式”曾经也被作为人权评判的标准之一。功利主义发现了人的欲求、愿望,认为权利围绕实在法展开,弱化了人权的道德根基,从社会总体考量计算快乐值,忽视个体的选择与自由权利。由于人离不开信息之上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克服功利主义的局限,从利益法学的思路间接证明一项新的人权的诞生。利益法学以德国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黑克(Philipp Heck)为代表,它与功利主义的“大多数人最大幸福”有所不同,它强调不同主体之间、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均衡与博弈。利益法学实践性较强,它并不致力于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而是帮助法官在既定的法律秩序内实现公认的理想。1参见[德]菲利普·黑克:《利益法学》,博广宇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页。信息之上往往存在多个主体的多重利益,例如隐私、知情、自决、通信、名誉、信用、交易、使用等。信息权利的构建立足于这些利益之上,并均衡各类利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虽然人权也是主体利益的体现,但是人权更注重主体最根本、最基础的利益,例如人格、安全、公平等。
再次,信息人权论证离不开“经验论”视角下的人性研究。在这种视角下,确认一项人权依赖于人类的具体生活体验与认知。经验论下的人权见证了人类不同族群对自我进行审视的演进历程。但是经验式人权论证的局限在于,它基于人群共同的经历、体验、同情心、共情观念而产生新的人权意识,而不同地区文化思潮的差异会导致相互冲突的人权观念产生,从而影响人权的历史构成。个人主义、种族主义、集体主义,都是影响人权构成的价值观念。信息权利是一个受时代技术力量决定的权利,使其上升为信息人权较难通过超验、先验方式进行论证,更适合通过经验范式进行论证,通过经验观察和历史回溯,我们将会获得人类信息活动的历史规律。虽然各国在信息确权的类型与信息利益保护模式上会有差异,但相对于宗教、文化、习俗、政治而言,人类的信息科技发展水平在全球各区域的趋同性较强。究其根本,人类不断增长的信息诉求在全世界依然是类似的。
此外,信息人权的论证需要一个坚实的道德根基,如果说经验论或利益法学人权范式满足了人类世俗生活世界的需求,那么“道德式”的人权证成范式回应了人从世俗式生存到至善幸福生活的哲学追问,也回应了人权的价值目的,这也是基于启蒙运动力量的推动。人权范畴每一步的更新都是人类“道德”与“善”的升级。道德式人权论证范式也会陷入困境。宗教、文化价值、个体选择差异造成世界道德秩序处于混沌甚至矛盾状态,这些观念同时影响着各国人权价值观念与人权结构体系。“善”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有差别。人权的道德论证范式应缩小全球道德分歧与差异,寻求信息技术世界的道德公约数。例如,中国的儒学强调“人本”“仁”“爱”,欧洲国家强调“博爱”,美国的麦金泰尔(Alasdair C. MacIntyre)、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等学者强调“美德”。虽然涉及的概念不同,但是我们本质上要辨析信息权利中“善”的品格,并将信息人权进行类型分析、属性分层研究,阐释不同新型信息人权对“善”的生活、“好”的生活、“幸福”生活的实现程度。
(三)“信息人”假说助推信息人权诞生
人的属性是一个关于“人究竟是什么”的终极追问。它是一项新型人权诞生的最根本的理由与重要推动力。人权重视人的普遍属性,对人的特别化、个性化的“利益”“需求”权衡是次要的。从上文的阐释中我们发现,新兴权利与新兴人权在法理论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人权的法理证成过程之中,除了上文提及的人权证成范式,还应当对人的普遍属性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这种论证较常规性的人权法理论证更为抽象、独特。
人性是人权内核,学者在人性论证的历程中分别使用过“经济人”1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从交换、分工的视角对经济人理性、利己的行为进行过描述。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经济人”假说揭示了国民经济的普通规律,为构建严谨的经济学体系提供了理论前提。人权中的经济权利其实也符合“经济人”逐利特征。国家在保障经济权利时必然同时考虑私人利益、权利成本、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问题。、“社会人”2“社会人”假设与“自然人”相对应,它是管理学、经济学上的一个转型学说,马克思也曾经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页。“社会人”假设从结构主义视角强调人在社会群体中的角色与地位,“社会人”追求尊重、友情、社会角色。人权的变革也经历过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过程,人权理论可根据“社会人”假设构建劳动权、工作权、结社权、弱者权利体系。、“政治人”3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指出,“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文化人”等人性设定,这些非人权学者的人性假说对人权理论具有启发作用,人权学者可以借由这些假说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维度构建立体的人权理论体系。人性的重新界定有助于为信息权利成为人权提供更充分的证成理由。人的属性、定义一直在变化之中。自然科学、法学一直孜孜不倦地研究“物质人”“精神人”,却没有发现符号世界、信息世界中的人。信息也是人的自然属性之一,这种属性通常易被生命科学、医学所忽视。人类诞生之初就具有信息属性,人类通过DNA遗传密码传宗接代,人类是地球上最多使用手势、文字、符号传递信息的动物,属于强信息交流生物。普通动物虽然也运用信息进行繁衍(DNA复制)和生存(警报、标记、气味),但是普通动物属于弱信息处理生物,它们不能将生活的历史、记忆、智慧记录下来。这些有别于普通动物的信息能力将人推向了万物之灵的地位。
“信息人”4在我国,“信息人”假说的较早提出者是著名理论信息学者李宗荣教授,法学界龚向和教授也提出了“信息人”观念。参见李宗荣等:《信息心理学:背景、精要及应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页;龚向和:《人的“数字属性”及其法律保障》,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71—81页。、“数据人”、“符号人”是继各类人学研究之后诞生的假说。20世纪60年代的认知科学家将人与计算机进行类比,认为人是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系统,人的生活是一系列符号信息处理过程,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将人归纳为“符号的动物”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人在世界留下的信息让人具有独特的品质、独特的个性。人在失去生命之后,信息能够让人以另一种形态(信息态)继续延续生命。
“信息人”具有以下四方面含义。
第一,人体是一个信息处理系统,大脑是信息中央处理器,眼、耳、鼻、舌、触觉是外界信息感应器。人的一生都在不停运转处理信息,信息是人存在的非物质化延伸,人留在世界的所有信息共同汇聚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人”。这些信息既包括个人的历史、经历、兴趣、宗教信仰等,也包括个人为世界创造的智慧,例如,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文学、艺术、科学创造等。
第二,“信息人”最终的呈现形式是具体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信息人”是人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信息人”的载体就是具有独特体系和结构的符号、数据、影像等,这些是他人认识一个人的途径。
第三,信息是人获得价值与意义的工具,信息赋予人以生命不朽的意义。“信息人”是人格尊严的具体化,人拥有一种新的自我抉择能力,人能够通过信息进行一种自我评价,或对他者进行评价。
第四,符号、信息对世界的改造是巨大的,“信息人”的出现使现代人得以与人类祖先进行沟通,对先贤的智慧进行传承。“信息人”是对人的本质的提炼与概括。1参见张雨声:《论“信息人”》,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109—112页。“信息人”是非物质的人,是后天的人,是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人,是对人性尊严的一种巩固,从这个层面上看,信息权利具有深厚的人性根基。对“信息人”的保护体现在人性意义上的平等,同时也是对人“体面生活”的维护。人权自始至终以人为依托,它最终保护的是人的尊严、人的诉求,而保护个人信息最终保护的也依然是人的尊严。关于人与信息的意义与关系的论证能够推动并促成信息权利上升成为信息人权。
“信息人”假说有助于推动人权从单一保护“物质人”转向同时保护“物质人”和“信息人”。信息侵权案件的不断增长说明“信息人”是脆弱的,因为信息容易被篡改、被删除、被违法者所利用,并最终伤害“物质人”。信息人权为“信息人”的安全保驾护航,保护“信息人”在“赛博空间”的安全与存续。“信息人”的存在,使人类无惧生命的衰亡,虚拟生命可以通过信息继续延续。理想的信息人权能够保护不受生命时间限制的“信息人”。
三、信息权利与人权的衔接
(一)信息权利是否属于“第四代人权”
通过上文多重法理证成范式,信息权利上升为人权已具备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根基,但是信息权利上升为人权之后,其归属于第几代人权却存在争议。自从法国学者卡雷尔·瓦萨克(Karel Vasak)将人权划归到不同的历史类型之中并把人权的历史类型分为三代以来,人权的代际划分理论已经深入人心。这三代人权在属性、内容上是一种递进关系:从消极人权上升为积极人权,从个体人权上升到集体人权。其实人权发展到第三代时已经具有较强的憧憬性、连带性2参见[法]卡雷尔·瓦萨克:《人权的不同类型》,张丽萍等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2—477页。,人权义务主体也在朝多元化发展。
当代学者都在找寻“第四代人权”的范围。人权学者在界定“第四代人权”类型时,意见并不统一。很多学者提出过不同类型的“第四代人权”观:徐显明教授在2006年提出“和谐权”为“第四代人权”1参见徐显明:《和谐权:第四代人权》,载《人权》2006年第2期,第30—32页。;莫纪宏教授提出“生态权”为“第四代人权”2参见莫纪宏:《生物安全法催生第四代人权观》,载《瞭望》2020年第9期,转引自中国法学网,http://iolaw.cssn.cn/zxzp/202002/t20200227_5093730.shtml。;张永和32018年7月18日,“改革开放与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研讨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张永和教授在“改革开放与中国人权理论创新”分议题讨论中,以《论第四代人权》为题发言,认为享有“美好生活”是第四代人权诉求。、范进学教授均认为享有“美好生活权”是“第四代人权”诉求4参见范进学:《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下的美好生活权论》,载《法学》2021年第5期,第7页。;马长山教授提出,“数字人权”是开启“第四代人权”的代表5参见马长山:《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16页。。
另有学者指出,信息权利即使成为人权,它也不是“第四代人权”。这种对新兴人权泛化的批判之声有其根据。例如,刘志强教授认为,数据、信息权利均尚不具备新一代人权的基本要素,也不足以构成人权的代际革新。6参见刘志强:《论“数字人权”不构成第四代人权》,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20—34页。本文认为,人权的代际革新强调人权主体与社会在特殊时期的关系,强调具体的人权主张具有新目的和新价值,强调人权制度设计上的创新性与特殊性,更强调该人权在历史形成中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特征。第一代人权是调整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第二代人权对抗的是资本世界的不平等;第三代人权的使命是共同体的发展与和平。信息人权的价值使命为:自由、秩序、平等、人格尊严、信息自决、信息财富自主、信息资源共享,这些价值分别包含在了这三代人权之中,并没有形成跨越。
代际人权观念的设置并非完美无缺,它促使人们总是追寻更新的人权类型。如果我们忽视对旧代人权体系、理论进行完善和补充,新代人权诞生将对旧代人权形成一定的冲击。7See Spasimir Domaradzki, Margaryta Khvostova & David Pupovac, Karel Vasak’s Generations of Rights and the Contemporary Human Rights Discourse, 20 Human Rights Review 423, 423-443 (2019).新型权利是个体新的主张、诉求、利益形成的权利,如果其上升为人权,并成为人权代际发展中的新生代人权,就应当论证这些权利在人权历史洪流之中的独特属性。信息、数据等权利是人类发展到高级信息化阶段的诉求。这些诉求的终极目标其实依然围绕传统的基础性人权展开,依然服务于传统的基础性人权,例如自由权、人格权、平等权、财产权等。由于终极目标没有超越基础性人权的范围,所以这些权利依然停留在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人权的范畴之内。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诞生以前,信息、数据权利具有义务主体不明确的特征;当权利的义务主体明确之后,它们与传统三代基础性人权已经可以进行衔接。新型的信息权利,如信息自决权、知情权、复制权、删除权(被遗忘权)、携带权等,都是具有人格、社会、经济属性的权利,本文认为这些信息权利即使上升为信息人权,依然可以将它们归属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人权交叉重叠的范畴之内。信息自由属于第一代人权所保护的对象;具有人格意义的信息利益被第二代人权中的人格权所保护,较为复杂的是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权利,它们大部分也属于第二代人权;信息资源的集体分享与共建可以将其纳入第三代人权范畴。
在世界范围内,目前还无法达成以公约为形式的国际通行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但已有学者建议,应当根据相关主题制定一项国际示范法。这显然也不容易实现,因为目前各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还未形成统一的国际共识。1See Robert Walters, Leon Trakman & Bruno Zeller, Data Protection Law: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sia-Pacifi c and European Approaches,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2019, p. 432.本文认为信息人权应当被国际公约认可,为了防止新型人权类型出现冗余化和过度膨胀的情形,可以暂时不将“信息人权”四个字作为独立的新类型人权名词。传统人权可以对信息权利进行吸收、合并,使信息权利被传统人权所兼容。现存的人权公约在与新型信息权利可重叠、可兼容的范围内,与新型信息权利进行同步更新,信息权利与传统国际人权体系完全可以实现相互促进、协调互补发展。
(二)多元、立体的权利辅助人权体系的更新
权利结构的更新,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权体系的更新。传统人权体系的局限性体现在框架较为陈旧,核心概念的界定滞后于时代发展速度。信息技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程度有较大差异,这些技术差异导致立法制度中信息权利的名称、结构、属性变化多端。在信息社会早期,“个人信息权利”这个名称并没有出现,但是已经出现了以信息利益、信息行为为客体并对其进行规范、保护的立法。当时的信息权利并未显露其纯粹的权利特征,而是附着于其他类型的规则之中,如知识产权法对智慧信息的保护、网络法对网络操作信息的保护、竞争法对商业机密信息的保护等。早期的立法偏重对整体网络信息秩序的维护,是典型的公共空间、社会本位的立法模式,这些立法对个体的局部信息利益进行了保护,但是并未对信息之上的所有个人信息诉求进行保护。直到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这种立法模式的弊端不断显现,个人信息权利才被逐渐关注,并作为一个新兴概念逐渐被学术界所认同,个人信息也才逐渐独立成为权利的客体。各国分别采取了不同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模式,欧盟立法为信息权利区域立法提供了新基准。我国《民法典》《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为个体增添了更多、更新的信息利益诉求,但是这些信息利益无法通过权利主体单一、利益诉求单一的一元权利模式体现出来。
我们将信息权利多元、立体的这种特殊属性描述为“权利束”2参见闫立冬:《以“权利束”视角探究数据权利》,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2期,第60页。,也有学者将其描述为“权利块”3参见许可:《数据权利:范式统合与规范分殊》,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第90页。。“权利束”(a bundle of rights)理论描述了财产权的各项分支权利,它将多种法律关系进行拆解,最后再捆绑在一起。“权利束”理论运用比较广泛,土地权、知识产权、水权等权利都是以多种“权利束”的结构存在的,都属于财产权的分支权利,它们结构分散,权利所指向的客体类型较多,不能与抽象人权形成完整的兼容。经典人权的结构相对单一,复杂的权利结构体系都尚未纳入基本人权的研究体系之中。信息“权利束”的特征在于:在同一个信息之上,公共权力、私人权利等不同属性的权利或权力可以同时并存,例如阅览权、删除权、征信权、公共管理权同时并存,所有权与他人使用权并存。以“权利束”状态存在的信息权利意味着个人、企业、国家都可以进行信息的使用、开采、参与。现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信息权利具体表述为“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第四章),只是列举了部分信息权利,并非完全列举。随着信息的不断开发,“权利束”中权利的数量必将持续增加。如果说“权利束”理论较为平面化,架构感较弱,那么“权利块”(Right as Modularity)理论能够弥补其不足。民法学者对数据“权利块”理论进行了设计,既强调整体设计又强调个别设计,权利模块可以自我调节并发展。“数据权利可分解为服务公共利益目的的‘公共数据(Public Data)权利模块’和以私主体利益为依归的‘私人数据(Private Data)权利模块’。”1同上注,第93页。各个模块之间可以重新按比例进行交叠、排列组合、按需匹配。无论是“权利束”理论还是“权利块”理论均表明信息权利相较于普通的、单一的财产权具有更加多元、立体的结构层次。
多维、立体的信息权利结构能够辅助解决处于创设阶段的“信息人权”与制定法相衔接的难题,突破了传统人权权利主体不立体、义务主体不多变、人权内容清单化的固定模式。传统人权同时可以兼容属性相同的“权利束”或“权利块”,例如,“自由权”不应再局限于其创立时的含义,它既可以是意志自由、表达自由,也可以是个人对信息的控制自由;人格权可以兼容信息隐私权益、名誉权益等;平等权可以兼容信息知情权等;财产权可以兼容信息交易行为中产生的经济利益等。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民法典》中的权利架设为信息人权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法律基石。学者们已经花费了较多时间探索信息权利的类型与司法实践范式,除了通过传统人权兼并新型权利模式之外,此时“信息人权”还应当发挥统筹全局的功能,既能回应如何均衡分配信息“权利束”“权利块”的问题,也能使个人信息之上的多元利益达到一种均衡,促进信息人权发挥其道德层面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层面的作用。
(三)非权利条款间接巩固了人权
并非所有类型的信息权利都以清单列举的方式呈现,也并非所有的人权都以文字形式载明于法律条文之中。权利或人权精神可以隐藏在强制性规则之中,有些强制性义务与责任也是对某种特定人权的保护。新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除了强调个体的权利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强调信息义务主体具体的信息行为方式。权利或人权本身蕴涵着一定的强制性义务,剥离义务的权利或人权是不存在的。国家法律通过强行性规则体系保障个人的基本信息权利不被任意克减。
不同立法体系对信息义务主体的称呼有较大差异,例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亦有译为“《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其称为“数据控制者”,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其称为“信息处理者”。权利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对义务主体的进一步束缚,每增加一项数据或信息权利,特定主体的义务就会相应增加。由于数据或信息权利的类型较多,其对应的义务履行方式、权利救济手段在成本与经济效率上存在较大差异:与人格有关的信息权利注重侵权预防,删除权、自决权、知情权重视信息主体信息自决的效率,实现自动化决策、算法的公平与透明既要考虑决策优势又要顾及其监督成本。总之,越是依赖信息技术的权利,其义务履行成本相对越高。但另一方面,成熟的信息技术其实可以将一般性义务主体的负担降低,由技术来承担法律规则中的义务。1使用信息技术代替人承担义务,在实践中已经较为常见,例如网络平台通过设置隐私算法将用户敏感信息自动隐藏,这里的隐私保护义务无需让普通人来承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规则不仅调整人的行为,也调整着信息运算方式和程序发展的方向。
不是所有的强制性义务都与权利、人权的具体主体一一对应。有的义务与公共秩序有关,有的义务与国家强制管理有关,而最终,国家维护秩序与管理所产生的红利会回馈给个体。这是一种通过公共权力间接巩固个体权利或人权的手段。例如各国设置对动物、植物的强制性保护义务,并不意味着动物拥有权利或人权的主体资格。国家的强制保护最终会形成一种自然物种生态秩序红利。为了维护社会的健康卫生秩序,在流行病调查环节中,个人也有提供健康状态、高风险地区行踪的义务。在个人信息跨境领域,信息流通的方式与国内不同,国家要求信息处理者通过安全评估或经过安全认证或签订符合标准的合同,这是为了国家整体安全利益诉求而确定的强制性义务。这些强制性条款虽然不能直接保护具体的个人权利或人权,却能间接地对个体人权的实现形成一个制度化的平台,更有益于人权的实践。并非只有以“权利”体现的方式才能实现国家对个体人权的关怀,社会整体道德风尚的提高以及公共法律的强行性条款也是人权实践道路之中的必备要件。
个体的大部分信息福利源自于国家公法、经济法、社会法制度的构建,因此构建一个新的信息人权,其重心不仅仅寄托于个人信息权利之上,还需要相关制度的共同支撑。《民法典》是率先保护自然人信息利益的法律,但是《民法典》作为纯粹的私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必须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形成一种平行、互补的关系。而《个人信息保护法》也不是以“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法”命名的法律,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享有的权利是通过分散的“权利束”与信息处理者的“义务束”实现的。不过《个人信息保护法》所保障的利益具有功能主义特征,这些功能间接巩固了个体的人权主张。综上,优秀的信息类立法应平衡公法、私法、经济法三重领域:既强调个人在信息传播、处理之中的利益诉求,同时为信息处理者设置义务清单;既为国家监督、管理设置合法权限,也要为自由竞争的信息市场提供良好的交易规则,发挥信息的财富效能,进而提升全民的信息福利。
四、信息之上的利益博弈与人权分层
在信息权利到信息人权的逻辑证成过程中,我们要避免无效人权数量膨胀的情形。随着新兴权利的不断合法化,人权的数量与种类也急剧增加。国内外人权专家不断通过扩充人权内容以获得成就感,人权话语成为像“变戏法”一样不断膨胀的1参见黄金荣:《人权膨胀趋势下的人权概念重构——一种国际人权法的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26页。乌托邦式的语言,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这样的膨胀过程,因为单薄的人权话语、人权宣告并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即使人人享有相同名字的人权,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个体所获得的具体利益并不均衡。当然,新兴人权数量的膨胀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权的真正价值不断贬值,即多方主体从不同角度提出新的不同主张时,各方主体的利益都会受到挤压、排斥(具体表现形式如信息表达自由对个体人格的抑制,信息使用、开发自由对信息安全的冲击等),从而导致特定人权价值遭遇贬损。因此,我们需要研究的不仅仅是提出一种新的人权,更重要的是需要辨析信息之上各方利益与诉求的关系。
在同一个信息、数据之上存在多方主体利益的博弈。第一,自然人拥有人格、安全利益。第二,为了自由市场的秩序,市场经济主体需要获取个体的征信利益。第三,商事主体需要对信息进行剩余价值的再次发掘,探索更多的利润空间。在市场规则运行过程中,商事主体与市场监督部门还要集体探讨如何应对信息垄断,如何治理资本滥权对信息无序控制的难题。第四,国家为了公共安全、公共健康等利益,以及出于治理公共空间秩序的考量,需要获得特定信息的采集、管理、监督权限。在上述所有类型的利益之中,有些利益可以转化为法定的权利,并上升为人权;有些利益可以转换为约定的权利。个人人格、安全的利益属于核心人权的范畴;基于交换与约定的利益属于在人权框架之下的民商自治领域;国家通过授权获得信息的采集、处理与监管权限,并通过信息公共权力服务于公民,其达到的效果可以体现为人权的促进和实现。
人权分层理论借用了社会学的“社会分层”论,不同类型的人权获取方式具有较大差异,不同个体获得的人权份额也是不同的。分层论可以使学者熟悉每类人权的具体特征以及它们在人权谱系之中的地位,同时也能回应人权泛化、膨胀所带来的困境。从信息权利到信息人权的过程中,不同的视角下人权的分层是不同的。“三代人权”理论其实是依据人权的形成时间顺序和人权的目的价值进行的分类,但是“三代人权”理论并没有回应信息时代所产生的新的信息权益与冲突。下文将论证各种信息利益与人权的关系,并对信息人权进行一个科学的分层建构。
(一)信息之上的人格利益与人权
信息之上的人格利益是直接能够上升为人权的利益,是人应当享有的人权诉求,因此保护个体人格信息属于人权范畴。信息之上的传统人格利益包括隐私、荣誉、名誉、姓名等,信息是承载人格的工具,人格是构成“信息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权利在传统人权体系中缺位是由于传统人格权内涵中没有电子信息技术的痕迹。知情、自决、查阅、复制、更正、删除(被遗忘权)逐渐成为发达信息社会中信息主体的新兴行为主张,如果将它们纳入人格的范畴,则突破了传统人格的定义和内涵,它们并非传统人格权系统内的产物,也不是《世界人权宣言》第6条2《世界人权宣言》第6条:“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中“人格”的内涵。
人权理论中的人格内涵忽视了人格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信息、数据等,含有人格的信息让人格可以显现、外化。个人信息是符号化、影像化、可视化后的人格,个人信息之上承载着较多的人格尊严。国内民法学者利用“一般人格权”扩充了具体人格权的内涵,可供人权理论作为参考、借鉴。我国学者杨立新教授在一般人格权之上又提出抽象人格权概念,并认为抽象人格权保护“意志人格”1参见杨立新、刘召成:《抽象人格权与人格权体系之构建》,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81—97页。,意志决定了人作为主体的地位。人对信息的自我决定、自我选择均构成了“意志人格”,知情、查阅、复制、更正、删除都是人的意志选择的体现。人有权利自由选择以何种信息、何种方式呈现自己的人格。
2020年《民法典》突破了传统民法体例的局限性,创设了人格权编,填补了人格权在立法保护体系之中的空缺。人格权编虽然事实上兼容了大部分个人信息权益,但并没有直接注明“信息权”三个字,毕竟一项新型权利的创立需要国家创设一系列救济制度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民法典》将信息权利转化为一种信息利益进行保护,并运用具体人格权对信息之上的人格利益进行规范。《个人信息保护法》与《民法典》二者平行且互补,同时也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两部立法其实是将具体人格权、抽象人格权与自由权进行了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信息行为、利益的界定更为详尽,它既对信息处理者的行为进行了限制,也授予了信息主体在信息处理中的权利,该法第四章赋予个人拥有在信息处理中的权利,这些具体权利包括知情、决定、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
目前,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建立了不同模式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个人信息权利高速发展的历程说明国家立法、区域立法在时间上远远领先于联合国框架下的信息类人权规则。虽然我们尚未将这些信息权利称为人权,但其实基础人权体系中的“人格权”可以涵盖大部分以人格信息为载体的新型信息权利。人格权与新型信息权既有重叠又有平行。我们可以重新界定并拓展人格及人格权的内涵,并将人格信息利益包容在经典人权的框架之内。人格权与其他信息权益相比,是位阶较高的人权,当个体信息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首要保护的是信息之上的人格利益。当信息人格利益被保护之后,可以创设其他类型的信息人权进行补充保护。
(二)信息财产利益与人权
本文所论证的个人信息的财产利益分为两种:第一种指自然人通过自我信息获取的经济利益。这种信息经济利益属于一种人格信息财产,这些经济利益可以通过信息主体直接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名称类信息获得,也称为“人格商业化利用权”2我国《民法典》采取了人格“一元”保护模式,同时保护了个人的人格与经济利益。。美国立法中的“公开权”就是通过人格信息获得商业价值的权利。通过个人信息获得的财产利益兼具精神人格与经济利益属性3其实,兼具人格与经济属性的权利还有知识产权,《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知识产权划归至文化权利之中。。第二种信息财产利益指合法的信息处理者使用智力或体力劳动对海量个人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可视化设计而获取的报酬。如信息平台对个人信息进行脱敏、“清洗”之后设计的大数据分析系统可供科研机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人购买并使用。两种基于个人信息所产生的财产利益均可以认定为“新型”私有财产类型,其“新”体现为财产的非物质化、虚拟化特征较强。虽然现行财产权理论承认个人信息财产利益的合法有效性,但难以对其进行归类、定性。
两种信息财产利益已经逐步获得私有财产权的合法认同,现在需要追问其作为私有财产权在人权体系之中的地位。虽然私有财产权已被纳入《世界人权宣言》,但是私有财产权的人权地位曾经被质疑过。有学者认为私有财产权的公平属性较弱1See Briana Creeley, Private Property Is Antithetical to Human Rights, American University’s Undergraduate Policy Magazine (26 October 2021), https://www.theworldmind.org/home/2021/10/26/private-property-is-antithetical-to-human-rights.,公有财产的公平属性较强,例如德国保罗·蒂德曼教授(Paul Tiedemann)提出,私有财产权其实是一项“伪人权”2See Paul Tiedeman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p. 313-317.。不同阵营学者对私有财产权的人权属性持有不同意见3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当年起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未能就是否列入与财产有关的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美国提议将《世界人权宣言》的案文纳入其中,但智利、埃及、印度、黎巴嫩、菲律宾、波兰、乌拉圭等国代表都表示反对。 See Harvey M. Jacobs, Private Property and Human Rights: A Mismatch in the 21st Century?, 2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S85, S91-S92 (2013).,这种分歧可追溯至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当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市场经济与私有财产理念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私有财产权与其他基础型人权相比的确存有较大差异:
首先,私有财产权主体不是静态地、被动地享有财产权。财产的多与寡基于个人的努力、机遇而生成。以个人通过自我信息获取财产利益为例,信息主体必须通过自身的社会地位、财富基础(继承)、劳动力才能获得信息之上的财产利益。洛克(John Locke)将私有财产权产生途径归纳为“劳动”4[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页。,然而其他基础型人权(如生命权、人格权、健康权等)无需具备“劳动”或其他要素。
其次,私有财产权的全面平等价值较弱。它只能保护部分的平等价值,即平等保护个人对已经合法获取的财产的所有、占有的自由支配地位。因此私有财产权不像生命权、健康权那样具有对人保护的绝对性、普遍性、全面性、平等性。不同主体拥有的私有产权类型是不同的。如果某类权利所产生的利益在不同主体间未获得均衡分布,也会导致私有财产权所保护的平等价值与其他基础型人权所主张的平等价值关怀之间存在差异。
最后,生命权、人格权、健康权等对于每一个人的人格尊重与关怀都是等值的,这些生命、人格尊重与关怀也是不能随意克减的。私有财产权所能发挥的具体经济效能在不同个体身上是不等值的,当一个人是无产者时,财产权就是那个人享有、但未充分实现的人权,“多产者”更能发挥财产权的优势。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不是恒定的,信息财产权并不保障每一个信息主体必然获得经济价值,不能保障信息财产之上财产利益的多寡,也不能确保财产利益的平均分配。
独立的私有财产权不能回应“财产分布失衡”的难题,即不解决个体基于运气、时代、政策、国情、出生、地域等原因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问题。个人信息之上的财产利益也会受到财产权属性的局限,汪习根教授所论证的“发展权”理论或许可以回应人类发展起点不平等的问题。“发展权以人类生产能力的日益提升为现实基础。”1汪习根:《法治社会的基本人权——发展权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发展权鼓励多元主体对个人信息进行经济价值的提取,并将人类技术生产力进行不断提升,服务全人类。发展权能够弥补产权私有化的不足和缺陷,消除个体、集体因历史、环境困境导致的资源鸿沟。在发展权的引导下,我们努力追求每个主体不因出生、地域等因素都能达到一种公正的个人信息财产利用水平。
本文认为,即使私有财产权具有特殊属性,各类信息之上产生的合法财产利益也应当被人权所保护,否则信息产业世界的自由竞争规则将失去方向,繁荣的信息经济市场将会黯淡无光。国内学者对信息财产利益所进行的合法性论证并不能回应道德性难题。合法并不代表完全合乎人权本意。立法滞后、监管漏洞、市场失灵、垄断均可能在合法的情势下出现。人权之中的信息财产权应重点考虑政府通过信息财产利益再分配方式为公民提供基础的公共信息资源保障2公共信息资源包括个人、组织、社会因生产或发展需要而获取的信息,包括灾害预警与防护信息、就业信息、市场风险信息等。公共信息资源可以基于信息公共利益进行设置,具有公共福利性质。。这种再分配模式也是全体人民追求美好、繁荣与幸福生活的实现路径之一。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信息财产利益的特殊性,同时也应当探索公共权力如何防止个人信息财产利益的异化:首先,信息所产生的财产利益是人在社会化之后的诉求。个人信息之上的财富属于稀缺资源。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也会出现失真或呈现随机性,即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具有浮动性、动态性、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会使信息主体间的不平等加剧。其次,如果信息主体间信息财产价值不平等加剧或异化,我们就得思考国家公权力的干涉模式。国家为了保障社会整体财富的均衡与平等可能会对无限膨胀的高财富人群进行财产流动的限制,例如对外汇进行管制。理论上任何人权是不允许被随意限制的,但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弱者的基础需求会采取一系列政策。为了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目标与精神,国家将对高获利数据、信息的收益者采取累进税收政策。个人信息的财产获益者也将会受国家其他财富政策的影响和限制。国家为了促进人权整体目标的实现,还要鼓励公共脱敏信息资源的免费共享,合理设置信息收益的再分配,实现信息财富的平等分配。
(三)信息公共利益与人权
信息是资源、是宝藏,它不仅属于个人所专有,特定的信息还属于公共所有。信息具有可无限复制的属性,无数个体可以同时分享信息之上的公共利益。成熟的人权理论应当能够协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当个人信息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全体公民整体福利时,个人可以让渡部分信息利益,以实现公共管理、群体福利的目标。疫情期间的流行病学调查就是典型的例子,此时的信息利益属于整个社会的公民共同享有,公民共享之信息利益并不是通过私权利调整方式实现的,信息人权可以弥补实体法信息权利体系的缺漏,不拘泥于私法与公法的边界,并通过国家公共信息管理与监督权力实现以信息为手段的公共利益。
个人信息产生的公共利益分为如下两种。
第一,实名信息产生的公共利益。基于公共利益、社会秩序的需要,部分实名信息需要进行公开。人格信息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在特殊的情境下,为了公共秩序,在言论表达与新闻报道中个人的部分人格信息可能会被公开。这些信息被公开都是基于社会秩序、公共知情权等公共目的,例如刑事犯罪立案与判决信息的公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公共新闻的发布等。实名信息的公开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压缩特定私人信息权利的空间。公共言论自由、信息传播自由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的被遗忘权就存在一定抑制,导致被遗忘权在很多领域都会遭遇限制1See Sabine Jacques & Felix Hempel,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UK: A Fragile Balance?, in Franz Werro e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mergent Right’s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in Europe, the Americas, and Asia,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p. 207.。例如个人在科学研究、历史研究、统计研究中对个人实名信息的引用也会使被遗忘权受到限制,在司法辩护中提出法律主张也会限制被遗忘权。虽然将人格信息公开所产生的公共利益并不一定能够促进个体人权的实现,却能够促进社会整体人权价值的实现,尤其是公众的知情权与安全权所代表的社会整体秩序的人权价值。
第二,匿名信息产生的公共利益,或称为个人信息在褪去了人格属性之后所产生的利益,不属于私权调整范围,本文将它归类至公共物品范畴,其中包括无法识别身份、不涉密、脱敏的信息(例如人口普查数据、房屋买卖数据、疫情感染人数等)。匿名信息作为公共物品在信息空间中流动时就已经剥离了人格意义,脱离了具体的人对其的所有权属性。人人可以从这些信息中获益。公共利益不属于私人基本权利的范畴,它有益于整体国家福祉,并增进人权。匿名信息被特定人再次开发(例如大数据分析、数据计算)之后将会产生财产利益,附着在这些信息之上的劳动,以及这些再次被开发后的信息所产生的财产利益属于私人权利或人权保护的范畴。传统人权观念认为,人权的实现方式就是个体拥有一项项具体的权利,需要通过宪法、民法等国内立法将权利一一列举出来。其实如前文所述,并非只有“权利”条款才能实现人权,公法框架所调整的强制性信息规则也能够对个体人权进行保障。在福利国家、服务型国家理念下,人权的实现越来越依赖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规则。
(四)信息契约权利与人权
信息契约权利基于信息主体与信息使用者的选择、合意、约定而产生,既是权利也是利益。它区别于人权,同时也受制于人权。信息契约权利与人权的差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存在的前提不同。人权的存在不以国家立法、私人主体的约定为前提;信息契约中的权利与义务是随着信息契约成立而被创设,契约消失则权利消亡。即使没有合同与契约,人权依然存在。
第二,属性不同。人权具有道德性、自然法属性,其权利主体是每一个人;契约、合同中的权利由契约双方相互授权而来,是建立在个体的偏好、利益之上的,其权利主体是特定的。契约行为是一种私人自治行为,既享有国家为私人创造的自由空间,同时也受制于国家强行性规则的约束。
第三,稳定性不同。人权是稳定的、有历史连续性的;信息契约权利内容的任意性较人权更大,它们是以个体互惠互利、共赢为前提的。信息契约中的权利条款不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宗旨与依据。
虽然信息契约权利与人权有差异,但是信息契约之中的权利与义务依然不能越过人权的边界。信息契约行为包括信息授权行为(信息主体有偿或无偿授权信息控制者对信息进行采集、处理、利用的行为)与信息交易行为(信息控制者与信息购买者的信息交易行为)。信息的授权与交易行为均受制于人格权、公平权、财产权等权利规范的约束。
在信息契约中,脱敏信息交易契约是一种新的契约类型:交易的买方与卖方都不能主张其完全拥有对脱敏信息的所有权,只能主张信息之上的“用益权”。这类信息契约是一种“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买方可以主张占有、使用权,卖方可以在这些信息之上主张信息加工报酬权利。信息加工报酬基于合约约定,或由自由市场机制调节自动生成价格。由于脱敏信息已经失去其人格属性,该信息财产利益并不基于人格产生,因此原始信息主体不能直接主张这些再次被开发的信息之上所产生的财产利益。
基于信息契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理论上已经属于广义私有财产权的范畴。人权可以通过私有财产权理论保护主体基于契约获得合法财产权的地位,保护信息契约双方法律地位的公平,防止特定主体对信息资源的垄断。虽然传统的人权理论与信息经济、信息金融、信息交易相隔甚远,但现在“工商业与人权”理论逐渐兴起,其在阐释信息财产的定价标准、交易合规上依然有很多探索空间。人权理论和体系并不是万能药方,其在精确调整社会、经济、市场中公民个性化的信息利益诉求时容易彰显不足。这也说明人权理论在信息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河之中需要持续拓展,人权学者要对信息市场经济规律、信息行业惯例进行深入研究。我们要继续发挥人权理论的优势,使其可以判断并指引信息契约的公平性,为新型的信息交易方式提供指南,并为信息市场规则的创设设置最终红线与标准。
(五)利益均衡与道德视角下的人权分层
我们可以通过“利益均衡”“道德品格”视角对设想中的“信息人权”理论体系进行分类、分层。从前文论述所知,信息之上的利益可以分为人格利益(人格尊严、人格安全)、财产利益(人格财产利益、信息加工财产利益)、契约利益(授权、交易)和公共利益(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和征信系统、公共福利、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等)。每种利益为社会提供的目的价值也较为不同。这些利益可以同时重叠并存于个人信息之上,也可以在不同时间交叉出现。我们要根据具体现象分析这些利益背后的核心与本质,并以均衡视角来平衡这些利益。在个人信息去人格化之前,人格利益是基础性利益,其他私权利主体需以尊重人格尊严为前提;但个人信息去人格化之后,其产生的财产利益分配模式是依据惯例、约定、市场规律确定的。与私权利主体的利益有所不同,信息公共利益较为特殊,其运行模式也较为独特。信息公共利益能够使个人在一个高效率的环境中获得信息福利,它必须通过公共权力进行规范。信息公共利益来源于个人被强制让渡的那部分信息利益。强制让渡行为必须在基本人格与财产利益、契约公平得到完整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公共权力基于公共利益理由对个人进行信息的获取必须遵循最小、必要、合比例等原则,且这些信息公共利益不能仅停留在“国家”“公共”层面,它们最终必须公正地回馈给个人。
以道德与善的角度来看,每种信息权益所附着的道德品格会有种类之分。“道德”不同于“利益”,“利益”与“善”的关系较为疏离。因此,以道德视角来看信息人权的分层,会有部分相似结论,也会有部分不同结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善”有多种类型:身体的善(健康、强壮、健美等),灵魂的善(勇敢、节制、公正等),外在的善(财富、友爱等)。1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页。高级的善是幸福。不同性质的信息权利都是个体追求更高级的善的不同手段,不同人权所体现的善的品格也是不同的,人权以身体与灵魂的善为基础,核心信息人权是涉及个体人格尊严的“灵魂之善”。所谓外在的善(信息类财富等),最终是为了成就灵魂之善。亚里士多德强调公共善的地位,提倡公民拥有高贵品德;我国儒家文化强调“仁”“爱”“天下为公”。信息人权需要发挥人的至善、至美的品格。崇高“善”的人权表现形式有基于个人信息之上的公共福利、慈善贡献,它们是个人与公共善的融合。
五、结语
这是一个新型信息权利的时代,个人信息权利是一系列新型权利结合而成的“权利束”或“权利块”。结构多元、保护模式多样化是个人信息权利的特征,其显著的创新属性助推了传统人权体系的更新。
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第一,运用法理方法论证了信息权利成为信息人权的理论前提,弥补了信息权利在人权论证上的缺位。第二,将新型、新兴信息权利与经典人权进行有机衔接。大部分信息权利其实都可以被自由权、人格权、财产权等经典人权所兼容,将二者进行有机衔接有效发挥了传统人权的实质作用,防止无效人权类型的继续扩充。第三,辨析了信息人权内部与外部各类信息利益的定位与博弈问题,并对各类信息利益进行分级、分层研究,例如信息之上的财产利益、信息之上的公共利益及公共福利、信息之上的市场经济发展利益等。第四,将部分信息权利归类于信息契约私人自治的范畴,并以整体人权标准框架作为其自治界限的评判依据,为信息契约中的权利设置了原则与公平方案。第五,辨析不同类型的信息利益在人权体系中的差异与分层,并从自然法、科学技术、市场规律、道德、利益均衡等多种范式层面将信息人权理论系统化。
我们需要在信息人权领域构建一个成熟、完备且科学化的理论体系。新兴信息权利、新兴人权的研究还在继续,已经生效的个人信息权利立法并没有穷尽所有信息主体的主张。本文也尚未构想出一个完整的信息人权理论体系,新一代人权理论还有更多拓展的空间。信息权利仅能覆盖信息主体的局部利益需求;理想的信息人权,其理论架构与体系应当比信息权利的体系更加科学,并能填补信息权利中的制度性漏洞。在接下来的时代里,学者们将继续探索信息与技术的各类命题,并通过信息人权理论回应全体人类共同面临的信息主权、信息鸿沟、信息公平、信息福利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