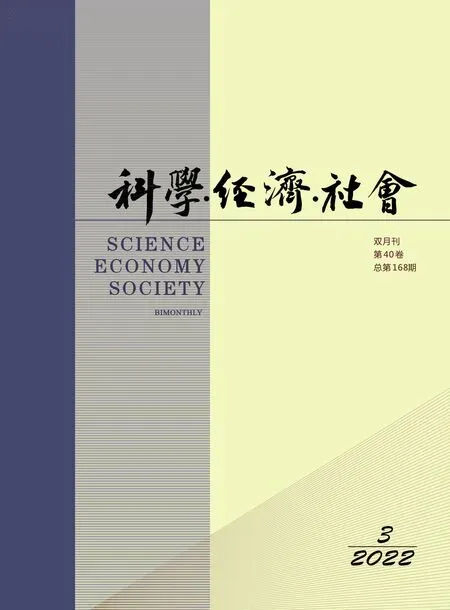笛卡尔与人工智能:“我思故我在”作为智能测试标准的可能性
张伟特
一、导论:笛卡尔与人工智能
虽然“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被视为是1956 年以后才正式出现的工程科学领域,但在西方哲学史上早已出现关于AI设想和思考的根苗①徐英瑾:《人工智能科学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哲学中的观念起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78-90页。。笛卡尔作为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发展了一个具有极强原创性、系统性和整合性的哲学体系,其中也包括了他对人和机器之本质的深入思考,甚至也讨论了人工智能机器可能性的问题。笛卡尔哲学的丰富资源启发了后世很多新兴学科领域,早期的控制论、信息科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人物,如控制论先驱维纳(Norbert Wiener)、信息论创始人香农(Claude Shannon)、人工智能之父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都将笛卡尔视为机械化认知的先驱①David Bates,“Cartesian Robotics”,Representations,2013,Vol.124,No.1,pp.43-44.。笛卡尔对人工智能问题的思考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②Keith Gunderson,“Descartes,La Mettrie,Language,and Machines”,Philosophy,1964,Vol.39,No.149, pp.193-222;周晓亮:《自我意识、心身关系、人与机器——试论笛卡尔的心灵哲学思想》,《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 年第4 期,第46-52,111页;徐英瑾:《人工智能科学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哲学中的观念起源》;赵汀阳:《终极问题:智能的分叉》,《世界哲学》2016 第5 期,第63-71 页;丁三东:《重审这个问题:人是机器?——人工智能新进展对人类自我理解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10期,第73-77页。,一般认为笛卡尔对机器具有类人智能的前景持完全否定态度,因为人工机器无法通过他提出的语言测试和理性行为测试这两个智能判断标准,同时部分学者也注意到这两个测试跟后世AI 符号主义路线和图灵测试的某种关联性。本文认为,笛卡尔哲学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他早期的人工智能不可能的判断并未耗尽笛卡尔哲学思考人工智能问题的全部理论潜力。虽然依据他的身心二元论理论架构和机械理论确实意味着人工智能没有可能性,但是笛卡尔晚期哲学中潜在的、更基础的三元论理论架构却并未完全断绝这种可能性。不仅如此,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简称《沉思集》)的独特认识论程序在某种意义上还潜在地提供了第三个、也是更有潜力的智能测试标准:“我思故我在”测试。
二、笛卡尔关于人之本质的思想:身心二元论和身心三元论
在《沉思集》中,笛卡尔从认识论角度尝试证明,思维(thinking)和广延(extension)是两种宇宙最基本的首要属性(其他一切属性只是它们的不同表现模态),它们彼此之间是实质有别的。在笛卡尔的世界观中,世界只有两类实体:思维实体和广延实体。而思维实体有两类:一类是作为不被创造的无限的思维实体,即上帝;一类是被上帝创造的有限思维实体,比如构成人的一部分的心灵(mind)。思维有各种模态表现形式,最基本的是知觉(perceptions)和意愿(volitions)。整个自然世界的物质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广延及其各种表现形式,如运动、大小、形状等;作为人的一部分的身体(body)本质上也是物质,是一种广延实体。在笛卡尔那里,身体和心灵实质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彼此在概念上不同、在属性上不同、在本质上不同、在实体上不同、可以脱离彼此而存在、在认识上优先次序不同(心灵比物质更好被认识)、各自功能不同、各自遵循的原理不同和被上帝创造的方式不同,这些特征构成了广为人知且影响深远的笛卡尔身心实体二元论(dualism)的主要内容③施璇:《笛卡尔的心物学说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在笛卡尔看来,心灵和身体虽然实质区别,但是它们也存在被联合的可能性,比如它们像船员和船一样构成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①Med, 6.13, CSM 2: 56,AT 7: 81。笛卡尔文献标准引用说明,AT: Œuvres de Descartes, 11 Volumes (revised edition),C.Adam and P.Tannery(ed.),Paris:J.Vrin,1982-1991.(引用格式为“AT 卷数:页码”);CSM: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vols.1&2,J.Cottingham,R.Stoothoff,and D.Murdoch(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85. (引用格式为“CSM 卷数:页码”);CSMK: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The Correspondence, vol.3 of the preceding entry, J. Cottingham, R. Stoothoff, D. Murdoch, and A. Kenny(tra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引用格式为“CSMK:页码”)。Med.: Meditations on the First Philosophy(《第一哲学沉思集》)。“Med,X.Y”:指第X(X=1,2,…6)沉思第Y段;XthReplies:指第X(X=1,2,…7)组答辩;Principles: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哲学原理》).“Principles, X.Y”: 指第X(X=1, 2, …4)部分的第Y 条。下同。。在人这个身心联合体中,心灵处于优势地位,人的本质还是在于心灵,而不在于身体,而且心灵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身体只是心灵的工具和居所。在某种意义上,心灵是本身性实体,身体是偶然性实体,但它们之间有个统一点②唐尼:《笛卡尔:当理性遭遇信仰》,赵廷、王煜译,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灵魂(心灵)和身体的联合是在身体中的大脑的松果体处。松果体被笛卡尔视为是人类共通感(common senses)的所在,也是灵魂的居所。心灵的直接对象不是外物或身体,而只是观念(ideas)。一切心灵外的信息首先是汇聚到松果体的共通感之后才为心灵接受为观念。观念是物质或身体与心灵之间关系的中介。如罗蒂所言,在笛卡尔的表象主义机制中观念被设定为心灵表象世界的一面镜子。
在笛卡尔哲学中,心灵、思维(心灵的本质属性)、观念(心灵的直接对象)具有“三位一体”的独特关系③凯莫林:《“我”之观念——笛卡尔哲学研究》,蒋运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76-77页。,心灵、思维、观念是同一个思维事件的不同向度,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不同称呼而已。思维作为心灵的本质有两种活动形式:理智的知觉(perceptions of the intellect)和意志的意愿(volitions of the will)。理智的知觉有两大类:一种是理智/理性的纯粹理解,比如心灵直观、归纳、演绎、纯粹理智的记忆等,是一种理性的直观或推理能力。在笛卡尔看来,建立哲学和科学知识或真理的可靠方法是这种理性的直观—演绎。一种是理智在身体参与下的知觉,比如感觉、想象、身体参与的记忆等。前者是人作为人的本能或本质,其目标是认识知识和真理;后者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其目标是维持身体的健康,趋利避害④Med,6.15,CSM 2:57-58,AT 7:83;Letter to Mersenne,16 October 1639,CSMK:139,140,AT 2:597,599.。而意志的意愿活动就是一种自由选择能力或者自由意志,针对知觉提供的观念对象进行肯定、否定、悬置、喜欢、厌恶等选择。在笛卡尔看来,人类的心灵是介于上帝(一个不被创造的至上完满的思维实体)和虚无之间。因此人类心灵既分有上帝的神性、完满性或无限性,也分有虚无。人类心灵的自由意志能力跟上帝的自由意志能力是一样伟大而无限的,体现人带有上帝的形象和相似性,体现人的神性。相比于上帝而言,人的知觉能力(纯粹理解、感觉、想象、记忆等)是有限的,有缺陷的⑤Med,4.4,4.8,CSM 2:38,39-40,AT 7:54,56-57.。因此,笛卡尔认为人的本质性属性在于思维能力,在于思维中的纯粹理智或理性的理解或知觉能力,在于思维中意志的自由选择能力;有与身体相关的感觉、想象等知觉能力都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是人的非本质性属性。
跟人类拥有理性能力密切相伴的是人类有语言能力,而动物没有理性也因此没有语言能力,这构成了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在笛卡尔看来,人类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把思维的内容——思想或观念——附着在表达它们的语词(words)上以便于记忆和重新想起,导致语言和思想彼此纠缠难以分开①Principles,1.74,CSM 1:220-221,AT 8a:37-38.。在语言的使用中,人类把语词的声音和字母关联于它们的意义,意义就是心灵中的思想②Letter to Chanut,1 February 1647,CSMK:307,AT 4:604.。笛卡尔认为,人类个体,不管是愚蠢的人、白痴还是最笨的小孩,都能够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先天聋哑人虽然缺少说话的器官,却可以创造手势语言来表达思想,而其他动物全都不能表达思想;虽然八哥和鹦鹉可以吐字,但是却不能像我们这样说话,不能证明说的就是它们心里的意思,虽然动物有表达情感的自然动作,但是这个跟使用语言不能混为一谈;动物语言能力的缺乏并不是由于它们缺少语言器官,而是由于动物的灵魂跟人类的灵魂在本性上不同,它们没有理性,而人类有理性。学会说话是用不着多少理性的,但是甚至最完美的猴子和鹦鹉在学语言方面都比不上最笨的小孩,甚至也比不上疯孩。这个充分说明人跟其他动物有无语言能力根本在于它们有无理性能力③Discourse,CSM 1:140-141,AT 6:57-58.。动物(比如狗、马、猴子、鹦鹉)只能被训练成可以使用语词或符号表达激情(passions),比如快乐、悲伤、希望(吃)、恐惧等,但是不能表达思想(thoughts),使用语词或符号用来表达思想的能力专属于人类;而且“从未有过一种动物如此完美,以至于能够用一个符号来让其他动物理解与它激情无关的东西;没有人是如此不完美,以至于不能实现这一点,因为即使是聋哑人也会发明特殊的符号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动物不能使用语言不是因为它们缺少器官,而是它们没有思想④Letter to The Marquess of Newcastle,23 November 1646,CSMK:303,AT 4:574-575.。人可以使用语言表达思想,而动物最多只能使用语词表达自然的冲动(愤怒、恐惧、饥饿等)或激情,这个是人跟动物之间“真正特殊差异”⑤Letter to More,5 February 1649,CSMK:366,AT 5:278;cf.Letter to More,15 April 1649,CSMK:374,AT 5:345.。因此,相比其他动物,人类因为拥有理性能力从而具备使用语言表达思想的能力。因此,语言能力作为人类之本质的一部分,是依赖于人类理性的衍生性能力。
在身心实体二元论的背景下,笛卡尔式的“人”被赖尔(Gilbert Ryle)形容为“机器中的幽灵”(the ghost in the machine)。但是,这对笛卡尔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虽然身体和心灵是两种完全异质的实体,但这并不意味着身心联合的人的所有本质都可以还原为身和心这两个单独的实体,并不意味着身心的联合是松散的。相反,笛卡尔主张身心的联合是一个整体(a unit)⑥Med,6.13,CSM 2:56,AT 7:81.。他在晚年《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1643 年5 月21 日)中明确提出,身心统一、广延、思维三者是分别理解人的身心结合、身体、心灵三者的“原初性观念”(primitive notions),都是不能进一步被简化或被还原为其他观念的初始观念;我们依赖于身心统一的观念来理解灵魂推动身体的力量和身体推动灵魂而产生感觉和激情的力量⑦Letter to Princess Elizabeth,21 May 1643,CSMK:218,AT 3:665.。这也就意味着人的本质超出了单独身体和单独心灵的范围,它们的联合产生了新的实体,产生了新的本质属性。就像水(H2O)由H和O两种原子联合而成一样,虽然水的本质依赖于两种原子各自的本质,但是两种原子结合之后产生一种独一无二的单独性质①唐尼:《笛卡尔:当理性遭遇信仰》,第64页。。我们通常认为整体的属性不能等同于各个部分的属性相加,部分的结合可能涌现出整体上的新特征。笛卡尔对身心统一性的证明实际上经历了四个阶段(《沉思集》《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哲学原理》《灵魂的激情》)②冯俊:《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8-148页。。在这封信中笛卡尔暗示一种关于人的三元论的立场并不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思想,并不是对《沉思集》思想的偏离,身、心和身心统一体三者都是最原初的、最确定的东西③贾江鸿:《作为灵魂和身体的统一体的“人”:笛卡尔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5页。。不过,笛卡尔认为对身心统一体的认识不适宜单纯依靠理性,也不适宜依靠在想象力协助下的理性,而只适合单独使用感觉。尤其是那些从未哲学化而只使用感觉的人很容易认识到身心联合为“一个单一的(single)事物”,很容易在自身中经验到自己是“一个单一的人(a single person)”④Letter to Princess Elizabeth,28 June 1643,CSMK:227,228,AT 3:692,694.。对笛卡尔而言,似乎这种三元论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范围,因为似乎人类心灵不能同时形成一个关于身心区别和身心统一的分明观念,因为同时设想它们既是一个单一事物又是两个事物是荒谬的⑤Letter to Princess Elizabeth,28 June 1643,CSMK:227,AT 3:693.。因此,对统一体的认识不是从理性的理解出发,而是从感觉的经验出发。笛卡尔是在《沉思集》中通过理性的认知程序确立了身心二元论的形而上学知识,而在理性之外还通过感觉经验到同样真实而原初的身心统一性特征,后者同样也构成了人的本质,建立这种三元论架构并非基于同一种认识能力的认知秩序。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笛卡尔三元论在笛卡尔体系中的首要地位⑥黄作:《笛卡尔是一个二元论者吗?》,《世界哲学》2018年第6期,第58-67页。。确立身体和心灵的原初地位源于笛卡尔在认知秩序中建立新形而上学的一生一次性的奠基工作,而身心统一性特征则是奠基于一个更深刻的形而上学结构之中,这个结构是由无数个一次性瞬间构成的生活经验,因此由这个经验确立的身心统一性比身体和心灵两者的地位更原初、更根本⑦李猛:《“一生一次”:笛卡尔与现代形而上学的“新计划”》,《哲学研究》2021年第12期,第90-100页。。
总体而言,在笛卡尔世界观中,人类具备如下特征:
A.身心统一性:人是由身心两种完全异质的实体构成的一个新的单一性实体或整体,这种统一性或单一性是最首要性的、最优先性的、最原初性的,不可还原为身心两者各自的本质,可类比于H 和O 两种不同原子构成了新的事物水(H2O)的情形。这种人类本质超出了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范围,只能被感觉(作为身心统一体的特殊机制)所经验。身心统一性包含心灵推动身体运动的能力以及身体影响心灵产生感觉和激情的能力。
B.作为本质的心灵:在人这个身心统一体中,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可以区别出心灵和身体两种完全异质的实体;就这两者而论,心灵处于优势地位,心灵是本质性的,身体是偶然性的;人的本质是在于心灵而不在于身体;心灵可以脱离身体而存在。
C.神性的自由意志能力:在心灵实体的本质中存在着一种类似于上帝的自由意志能力,一种无限的自由选择能力,是人类神性的体现。
D.有限的理性能力:心灵实体的本质中存在着纯粹理智或理性的理解、直观、推理、记忆、计算等能力。这种能力属于人类心灵的本质性特征,是人作为人的本质,但是这种能力是有限的、不完美的,也容易受到身体的干扰和混杂。
E.使用语言的能力(表达和交流思想):衍生于心灵的理性能力,人类具体使用语言(语词或符号)来表达和交流自身思想的能力。
F.作为非本质的身体:在人这个身心统一体中,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可以区别出心灵和身体两种完全异质的实体;身体作为广延物,其表现模态在于形状、大小、运动等,体现了人作为动物的特征,对于人的本质而言是偶然性的,作为人之本质的心灵可独立于身体而存在。
在上述特征中,A与B和F之间存在张力和矛盾(在理性的认知秩序来看),它们并非依据同一种认识秩序而被确立;C、D 都收归于B,而E 是衍生于D。因此,如果站在笛卡尔的立场上来定义人类的本质,那就是体现了A到E,但是核心是A和B。由于笛卡尔作为近代理性主义的奠基人被广为熟知,人们往往只强调D,而实际上忽略了A、C 和E这个三个特征,尤其是A和C。
如果我们要在笛卡尔框架下思考人类智能的本质以及探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问题,那么以上特征就构成了我们讨论的基本出发点。
三、笛卡尔关于人工机器的思想:人工智能机器的不可能性
笛卡尔认为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整个可见的宇宙就像一架机器一样,物质中所有运动的原因都与人工机器相同①Principles,4.188,CSM 1:279,AT 8a:315;CSMK:213,AT 5:546.。笛卡尔借助对人工机械内部运作规律研究的机械学(mechanics)来理解整个自然世界,认为自然的法则和机械学的法则是完全等同的,没有所谓的“人工的”和“自然的”之分,全部物质的运动规律都是受机械原则支配。因此,笛卡尔把机械学的原则上升为物理学的普遍原则,进而对整个物质世界(不区分人工物和自然物)的规律持一种机械论(mechanism)的哲学立场,整个物理学就是机械学。在笛卡尔看来,在人工机械领域所有机械运行的结果都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的因果原则被机械内部各部件的广延特性(形状、大小、运动)的组合方式所决定的,人工机械服从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因果决定论,机械的状态完全是由其组成部件的形状、大小、运动性质所决定②宋斌:《论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从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的角度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版,第8-15页。。
由于笛卡尔持有一种物质世界的必然性机械论立场,因此自然世界中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都服从同样的机械定律,生命现象(生物学)被纳入物理现象(物理学)的机械论式的理解之中,生命现象(具有像人的肉体的生命体)和非生命现象没有本体论上的不同,它们都是以物质的广延为基础,都服从笛卡尔物理学中的三大定律(两个惯性定律和运动量守恒定律)①宋斌:《论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从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的角度看》,第180-182页,211-214页。。笛卡尔曾经尝试完全从机械论立场建立一个关于人的科学,纯粹将人理解为一台机器,但是他后来发现这种科学无法成立,这成为他引入心灵概念来解释人类部分现象的重要原因②Betty Powell,“Descartes’Machine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1970-1971,Vol.71,pp.209-222.。因此,笛卡尔选择只将人的身体和动物视为自我运动或自动化的机器(automatons)。
笛卡尔早期的著作《论人》(Treatise on Man)就是将人的身体当作一架机器(machine)来理解的。在他看来,很多人工机器(时钟、人造喷泉、磨坊等)是人类所设计,人的身体只不过是上帝所设计的,但是两者遵循的原理一致。身体这台机器由骨骼、神经、肌肉、静脉、动脉、胃、肝脏、脾脏、心脏、大脑等构成,身体的各种功能其实都是依赖于器官的配置(dispositions);而理性的灵魂或心灵相对于身体这台机器就像喷泉的管理员与喷泉的关系一样③Treatise on Man,CSM 1:99-101,AT 11:119-121,129-132.。死人和活人的区别就像运行良好的机器与停止运行的机器之间的区别④Passions,CSM 1:329-330,AT 11:330-331.。人的身体是一种上帝创造的精美机器的观念一直贯穿在笛卡尔《谈谈方法》和《沉思集》以及其他文献中⑤Discourse, CSM 1: 139,AT 6: 55-56; Med, 6.17, CSM 2: 58,AT 7: 84; Conversation with Burman, 16 April 1648,CSMK:346,AT 5:163.。他晚年甚至还有著作《人类身体的描述及其所有功能》来专门描述整个身体机器的机制⑥Treatise on Man,CSM 1:315-316,AT 11:226-227.。而动物这个自动化机器,虽然可以自己运动,但是不能思维,没有语言能力,有一定的意识(但没有人类意义上的自我意识),有感觉和激情⑦唐尼:《笛卡尔:当理性遭遇信仰》,第72-77页。。相比人工机器,动物是自然制造的更高级的机器⑧Letter to More,5 February 1649,CSMK:366,AT 5:278.,而人类则是更高级的、有灵魂或心灵的机器,人类可以自我运动,有思维,有自由意志,有理性,会语言,有感觉和激情,而且人类身体这个机器与心灵统一成一个整体或新的实体,具有另外独特的属性。因此笛卡尔虽然认为人的身体和动物都是机器,但是反对认为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只是机器⑨周晓亮:《自我意识、心身关系、人与机器——试论笛卡尔的心灵哲学思想》,第46-52页。。
笛卡尔将人工机器视为一种遵循必然性法则运行的物质体或广延物⑩Letter to Huygens,12 June 1637,CSMK:58-59,AT 1:377.,就像没有理性或灵魂的动物一样,它们遵循物理学领域的必然性因果法则,它们的运行都以广延(形状、大小、运动)的规律为基础。这似乎预示着人工机器不可能达到人类智能的水平,如果人类智能的特征是完全以心灵的特性为基础的话。在笛卡尔那里,物质与心灵是实质有别的,从物质的广延特性组合中似乎永远不可能出现或涌现心灵的特征,这暗示着笛卡尔对人工机器实现类似于人类程度智能的前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笛卡尔确实在两处文本中讨论了被后世称为人工智能之可能性的问题。第一处在《谈谈方法》第五部分:
假如真有这样一些机器,其具有猴子或其他缺乏理性的动物的所有器官和外形,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知道它们并不完全具有跟那些动物一样的本性。但假若有一些机器,相似于我们的身体,从实践目的的角度尽可能模仿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仍然是有两种极其可靠的方法识别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人(real men)。第一个方法是:它们永远不会像我们那样使用语词(words)或组合其他符号(signs),以便向他人传达思想(thoughts)。因为我们的确可以设想(conceive)一台机器,被构造得会表达语词(utter words),甚至可以设想其表达的语词是匹配于一些将最终导致相关器官变化的身体行动(比如,当你触碰它的一处地方时,它就会问你想要对它说什么;而当你触碰另外一处时,它就会哭诉你正在伤害它等等)。但是不能设想此类机器将产生语词的不同组合以便能就人们在其面前的说话给出一个切实有意义(appropriately meaningful)的回应——尽管最笨的人也能胜任这一点。第二个方法是:尽管这类机器能够跟我们一样做相同的事情,或者甚至做得更出色,但它们必然(inevitably)会在做其他事情上失败。这表明,这些机器并不是通过理解(understanding)而是根据构成它们器官的配置(disposition)来运作的。因为,理性(reason)是万能的工具(universal instrument),能用于一切情景。而这些机器的器官针对每个特定的行为就需要某些特定的配置。因此,让一部机器配备足够多的不同器官来应付生活中一切偶然性(contingencies),就像我们的理性指引我们行动的那样,这从实践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①Discourse,CSM 1:139-140,AT 11:56-57.
第二处文本在一封书信中,是针对第一处文本的补充:
假设一个人一生都在一个地方长大,除了人以外,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动物;假设他非常专注于机械学的研究,制造或帮助制造了形似人、马、狗、鸟等的各种自动化机器,这些机器行走、进食、呼吸,并尽可能模仿它们相似的动物的所有其他动作,包括我们用来表达激情的符号,比如被击中时哭泣,被大声吵闹时逃跑。假设有时他发现无法区分真人和那些只有人形的机器,并且通过经验了解到,只有两种方法可以区分他们,我在……《谈谈方法》的论述中解释了这一点:第一,这种机器人除了偶然之外,永远不会用语言或符号回答向它们提出的问题;第二,虽然它们的行动往往比最聪明的人更规律、更确定,但在许多模仿我们所必须做的事情上他们的失败却比最愚蠢的人更糟糕。②Letter to Reneri for Pollot,April or May 1638,CSMK:101-102,AT 2:43-45.
结合这两段文本,笛卡尔提出了两个判断人工机器不具备人类智能的方法:一是能设想机器表达语词来匹配一些身体行为,但是不能设想机器可以排列各种语词非偶然地针对各类情景的交流给出切实有意义的语言输出,因此人工机器不能像人一样非偶然地使用语言(语词或符号)来表达和交流思想;二是尽管机器可以执行某些特定任务,但是在很多其他任务情景中必然失败(甚至不如最愚蠢的人)。由于机器的运作依赖于各个部件的配置(disposition)而不是依据理解(understanding)或知识,而且每个部件只能对应一定的情景,而实践中我们不可能为之配备大量的部件。因此,从实践角度看,机器不能成功地应对无限丰富的偶然性情景。而人则可以运用万能的理性来应对无限复杂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方法或标准可以看成是笛卡尔提出的两个智能测试:语言测试和理性行为测试,用来区别智能的人与动物或机器①Keith Gunderson,“Descartes,La Mettrie,Language,and Machines”,p.198.。支撑这两个测试的论证既存在深刻的洞见也存在明显的瑕疵。
这两个论证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周晓亮认为第一个论证具有的洞见是,笛卡尔实际上预言机器(或现代计算机)不可能表现人类意识的语义内容,暗示笛卡尔对图灵式测试作为智能标准的否定性回答,塞尔等人关于机器的形式语法对于语义的不充足性理论、中文屋的思想实验以及对强人工智能的反驳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笛卡尔的洞见并未过时②周晓亮:《自我意识、心身关系、人与机器——试论笛卡尔的心灵哲学思想》,第46-52页。。而徐英瑾则认为第一个论证太弱、标准太低,是否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语义输出策略是一个程度性问题而不是一个质性的鸿沟,当前AI 领域的技术能力出现根据环境变化而有限调整语义输出策略的程序并非不可能。如果依据笛卡尔的标准,这种程序的出现意味着机器智能的实现,那就明显违反我们的直觉③徐英瑾:《人工智能科学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哲学中的观念起源》,第78-90页。。丁三东认为第一个标准的关键在于人可以实现“语言的无限组合”④丁三东:《重审这个问题:人是机器?——人工智能新进展对人类自我理解的启示》,第74页。。笔者赞成前两位学者的判断,而不赞成最后一种观点,因为笛卡尔强调的要害其实在于人能稳定地使用语言表达思想。图灵测试的本意就在于看到了可以从语言测试角度测度智能的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是一个具备反思能力的万能系统,语言的能力等价于构造一个世界的能力,具备语言能力等价于具备思维能力,语言的界限等于思想的界限,语言与思维同步⑤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哲学动态》2018 年第4 期,第5-12页;赵汀阳:《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何以可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1期,第1-8页。。在这一点上,笛卡尔无疑极具洞察力的。不过,笛卡尔这个语言测试并未提供一个判断的限度或者临界标准。
周晓亮认为第二个论证表明笛卡尔认为机器没有人一样的学习能力,只能按照预先设计的程序运动,不能处理程序未规定的事情,其依据在于笛卡尔的二元论奠定的心物之间的鸿沟无法用技术来填平,虽然笛卡尔的二元论站不住脚,但是笛卡尔提出的问题在当代依然是一个挑战②周晓亮:《自我意识、心身关系、人与机器——试论笛卡尔的心灵哲学思想》,第46-52页。。徐英瑾认为第二个论证质量比较高,从后世符号AI的核心思路——在机器中预置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和不同情境下调用不同方法的调用程序——来判断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同时笛卡尔天才地提出,真正的智能是一种通用问题的求解能力,这个判断比较符合一般人的直觉;但是这个论证存在非法跳跃,笛卡尔从“所有可被我们设想的机械不具有通用问题求解能力”这个前提出发得不出结论“所有机械都不具有通用问题求解能力”,这个推理跳跃在于笛卡尔关于机械制造的可能性的设想太局限,高估了自己的想象力③徐英瑾:《人工智能科学在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哲学中的观念起源》,第78-90页。。丁三东则认为,从演化的角度看,人类智能也是演化适应的产物,没有理由夸大它的普遍性、通用性和独一无二性,也没有理由贬低人工智能的未来潜力,尤其是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早期那种预先置入规则的方式,而是自身获得强大的学习能力,机器已经和人类智能一样踏入了自身的演化之路,只不过这种演化相比人类智能的自然演化而言在速度上会更快。在某种意义上,笛卡尔所谓的人之理性的万能性只是相对的,与机器的通用性相比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无本质上的鸿沟,因此基于理性对人和机器的严格划分并没有充分的依据①丁三东:《重审这个问题:人是机器?——人工智能新进展对人类自我理解的启示》,第74页。。本文基本认同三位学者的判断,笛卡尔第二个论证存在致命瑕疵,对机器的想象力受到了他的机械论哲学的极大限制,同时他也没有为这个测试给出区别智能与非智能的清晰判断标准。这个测试和第一个测试似乎都是一种质性判断。
基思·冈德森(Keith Gunderson)认为笛卡尔语言测试在本质上和理性行为测试是同一个类型,只是前者的行为范围更宽,未通过语言测试必定意味着未通过行为测试;笛卡尔事实上更信赖语言测试;不过两者都体现人和动物以及机器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是有能思维的灵魂②Keith Gunderson,“Descartes,La Mettrie,Language,and Machines”,pp.199-202.。如我们在第二节分析的那样,笛卡尔将人类的语言能力视为出于心灵之理性的衍生性能力,因此,虽然语言测试指向表达和交流思想的语言能力,但其本质上仍然是指人类的理性能力。笛卡尔这两个测试的本质都是理性能力测试。
笛卡尔除了把理性能力作为人类智能的根本标准外,还从必然和自由的角度对比机器和人类的区别。他认为,“自动机能够准确地产生它们设计用来执行的所有动作,因为这些动作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人类的行为与之相反而是自由的,因为人类的意志是自由的,这是人之为人值得称道的地方③Principles,1.37,CSM 1:205,AT 8:18-19.。不管是理性还是自由意志,都归并为人类心灵。
因此,对比第二节我们对笛卡尔关于人类之本质的思想的分析以及本节他对人工机械本质的看法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笛卡尔体系中人工机器的本质等同于人的特征F(作为非本质的身体),而不可能具有特征B(作为本质的心灵)、C(神性的自由意志能力)、D(有限的理性能力)和E(使用语言表达和交流思想的能力)。因此,人工机器无法通过语言测试和理性行为测试,即理性能力测试。因此,在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框架中,类似于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是无法实现的。
笛卡尔这样一个结论是决定性的吗?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一结论依赖于在两个前提(笛卡尔的机器观和身心二元论)下的两个测试。依据笛卡尔所持的极端机械论宇宙观,所有物质和机械的本质都无非是广延性质(形状、大小、运动性质)的“配置”(disposition),不会超出机械学的范围;而依据身心二元论,广延与思维是完全异质的。限于笛卡尔所在时代的机器技术,在他的机械观中很难想象诸如Alpha Go(2016)这样的存在,笛卡尔的机械观或许是一个极其粗糙和简化的理论。虽然当前大脑科学、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等领域一直尝试修正身心二元论,但似乎并未达到决定性的进展。因此笛卡尔这两个前提的有效性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同时笛卡尔的两个测试都是质性的测试,缺乏一个可操作性或者临界性的标准,即在何种限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某个行为体算是通过了这种测试。图灵测试可以看成是笛卡尔语言测试的可操作性版本,它从测试的功能性表现出发建立判断标准。
上述分析表明,笛卡尔对人工智能的可能性的问题具有深刻的洞见,也有极大的缺陷。这是否就是笛卡尔针对人工智能问题的最后价值呢?他的哲学是否真正耗尽了对于人工智能问题的理论思考潜力呢?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笛卡尔对人工智能的启发并不止步于此。
四、笛卡尔哲学对人工智能问题的潜在启发: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和“我思故我在”测试
本文认为,笛卡尔哲学对当前人工智能的可能启发大约有三方面:
(一)笛卡尔的身心三元论:人工智能体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三节的分析表明,笛卡尔判断人工智能的不可能性主要是从身心二元论架构出发,并没有将更具有首要地位的三元论框架纳入考虑。主要原因可能是笛卡尔在《谈谈方法》讨论人工智能机器问题时并未发展出他在《沉思集》以及以后提出的三元论思想。依据第二节的分析,笛卡尔是依据理性从认识论角度确立身心二元性,同时又从感觉经验角度确立身心统一性。虽然三元论在理性秩序中是冲突和荒谬的,超出了理性的认知能力,但是身心统一、身、心却都是真实的原初性本质,不可再简化和再还原为其他事物,而且身心统一性更具有优先性的地位。因此,从三元论角度,从身心统一性(人的特征A)这个原初角度来理解人类的本质可以设想人工智能在理论上的可能性,那就是人类或许有一天可能像上帝(神奇地)创造人类那样也创造出了一种具有人类智能水平的机器,尽管这种创造可能超出了单独有关身体和心灵的知识。
从身心统一性作为思考人工智能的出发点,我们至少有两个合适的理由:
第一,所谓身心二元论无非只是一种理性认识论的秩序,并不等同于一种本体论的实在秩序,我们还有可能从其他非身心范畴出发把握人类的本质。三元论的存在意味着当我们将人从身体和心灵两个认知角度来理解时,我们仅仅是在理性的认知秩序中在把握人类的性质,并不意味着就穷尽了人类的实在性。
第二,笛卡尔确立身心二元论的系列论证本身存在极大的问题。至少在《沉思集》的《第二沉思》分析“我”之本质时,笛卡尔将一种认识论上的可能性等同于本体论上的可能性,从而得出结论人的本质在于思维,而思维的存在不以身体为前提。笛卡尔的论证脉络可重构如下①Med,2.4-2.9,CSM 2:17-19,AT 7:25-29.:
(1)我思故我在。
(2)如果我有灵魂的属性——思维,那么我确定地知道我存在。【依据(1)】
(3)除了属性“思维”外,我能够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属性(比如经验中的各种身体属性以及跟身体关联的属性)而存在。【依据(2)】
(4)如果某物能够不依赖于某个属性而存在,那么这个属性就可以和该物分离开。(参考《第四组答辩》补充)②Fourth Replies,CSM 2:154-155,AT 7:219.
(5)除了属性“思维”之外的任何属性都可以和我分离开。【依据(3)、(4)】
(6)所以,惟独属性“思维”不可和我分离开。【依据(5)】
(7)我是一个思维之物。【依据(6)】
如果本文的重构是精确的话,那么笛卡尔在这个推理中,从(2)到(3)意味着一种认识论秩序向本体论秩序的飞跃。正如“如果我有论文,我就知道我会很有安全感”不必然得出“除了有论文之外,我能够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而有安全感”。因此,其实笛卡尔在这里并不能排除思维是以身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也不能排除像中国古人理解的情况:形体和精神都是气在不同清浊尺度上的表现。因此,如果身心二元论并不成立,那就意味着笛卡尔完全可以从身心统一性角度出发理解机器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
从身心统一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的本质,就像我们优先从水这个整体和单一体来思考水,而不是单单从H 和O 两种原子各自本质的角度把握水。笛卡尔判断人工智能的不可能性的依据无非是单独从O(身体/机器)的角度可能永远无法产生带H 的事物(人类智能/机器智能),这陷入了H和O这对思考范畴的秩序限制。当然,从笛卡尔三元论角度出发思考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只开显了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只是表明身心统一体作为一个原初性本质蕴含了关涉这个问题的理论潜力。
(二)笛卡尔的思维原子主义理论:对符号AI的可能理论价值
在笛卡尔的心灵理论中,笛卡尔持有一种观念的原子主义思想。笛卡尔认为所有人类心灵的思想或观念可还原为数量有限的原子式简单观念。原子观念“就像真实的颜色一样,我们从这些颜色中形成我们思想中出现的所有事物的图像”①Med,1.6,CSM 2:14,AT 7:20.。笛卡尔认为有五类原子观念:最普遍的观念(如数的观念、存在的观念、公理性的命题式观念)、广延(物质第一性)的基本观念(大小、形状、运动的观念)、思维的基本观念(比如怀疑、否定、肯定等观念)、物质第二性的观念(比如颜色、味道、疼痛等)等②Med, 1.6-1.8, 3.19-3.21, CSM 2: 13-14, 29-30, AT 7: 19-20, 43-44; Letter to Princess Elizabeth, 21 May 1643,CSMK:218,AT3:665-666;Principles,1.47-1.49,CSM 1:208-9,AT 8a:22-24。。“人类的所有思想都是由简单观念构成的”“……对人的所有思想进行编号和排序,甚至把它们分成清楚和简单的思想……是获得全部知识的伟大秘密。”③Letter to Mersenne,20 November 1629,CSMK:13,AT 1:81.因此,笛卡尔认为,通过分析人类思想中各个复杂观念对原子观念的蕴涵情况就可以建立人类全部知识。由于思想与语言符号纠缠在一起,因此笛卡尔这种思维原子主义思想可归于为符号AI 奠定哲学基础的那个哲学传统之列④成素梅等:《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虽然由于笛卡尔对原子观念的界定过于宽泛而缺乏标准导致这个思想存在很大的内在困难,但是这种还原主义思路依然并未说明已经决定性失败,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有可能优化语言测试的标准。
(三)“我思故我在”:作为人工智能测试标准的可能性
笛卡尔被视为是西方近代宗教、科学和哲学领域声势浩大的新皮浪怀疑主义(New Pyrrhonism)浪潮(以路德、桑切丝、蒙田、沙朗等为代表)的最大挑战者和克服者⑤Richard H.Popkin,The History of Scepticism from Savonarola to Bayle,third enlarge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xxxxx.。在《沉思集》中,他提出了一个极其极端的怀疑场景(代表古代皮浪主义和近代新皮浪主义传统所可设想的最强怀疑方案)去怀疑一切,然后找到了“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以下简称CES)这个他认为能免疫一切怀疑的坚固支点,以此出发笛卡尔相继分析出这个“我”的本质是心灵的思维,一个假定存在的物质(一块蜡)的本质是广延,然后再提出了清楚分明性知识标准,证明非欺骗性的上帝存在,接着证明知识标准有效,然后相继证明外部世界存在、心灵和物质/身体实质二元。这个系统性的破和立的工作标志着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和主体性转向,笛卡尔从认识论的角度推进了哲学对人类主体之本质的认识。
正是因为笛卡尔在《第一沉思》和《第二沉思》提出怀疑一切,甚至怀疑那个怀疑者自身(“我”)的存在,才使得笛卡尔提出通过CES(I am thinking,therefore I am)来确证“我”的存在(“我思故我在”)和自性/主体性(“我思故我是”)。由于这个“我”被后来的分析表明其本质乃是心灵,因此CES实际上承担了从绝对怀疑中确证了心灵这个人类智能主体存在和自性的功能。这个确证过程不就蕴涵着某种判断和识别人类智能主体的最低限度的标准吗?如果能表明CES程序的判断场景并不以预设人类某些专属性特征为前提,那么这个标准就具备一种应用价值,可以用来测试其他行为体(如人工机器)。分析这个CES 测试,我们不也就知道了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基本标准吗?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沉思集》中CES 面对怀疑场景中的主角替换为一台机器,这台机器被人怀疑它并不存在,并没有自性。在一段程序的计算之中,它要如何才能够经受最极端的怀疑向外界确证自我的存在呢?它如何向他人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理性的自性主体呢?如果一个行为体提出或认可CES 这个命题,那么不管它是一台机器还是一个真人,通过这个测试就应该可以判断它具有主体性或自性。
本文提出将CES作为智能测试标准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1.CES 程序具有语言对话和交流的特征:CES 程序并非一种私人语言,而是预设了一种沉思者与自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沉思者使用了语言。
笛卡尔在第一沉思的怀疑继承自古代皮浪主义怀疑传统。皮浪主义的怀疑方法是如果有一个正面论证(arguments)支持结论P1,那么怀疑者只需要构造一个反面论证/平衡论证(counter-arguments)得出P2。由于两个论证都具有某种意义上同等的论证效力,且P1与P2相矛盾,从而使得断定P1的真假不得不终止,导向对关于P1的真假判断的悬置①恩披里克:《悬搁判断与心灵宁静:希腊怀疑论原典》,包利民、龚奎洪、唐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8-11页。。而笛卡尔将他的怀疑视为一种“论证(argumentum)”“推理(ratio)”②Med,1.10,CSM 2:14-15,AT 7:21;cf.Med.,1.2,2.4,CSM 2:12,17,AT 7:18,25.,一种针对正面论证的对冲性、平衡性或抵消性(counter-balanced)力量③Med,1.11,CSM 2:15,AT 7:22.,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反论证(ratio contraria)”④Med.,5.15,CSM 2:48,AT 7:70.。他发展了三个主要的怀疑论证:感觉怀疑、梦境怀疑和恶魔怀疑,相应针对的正面论证是:不理想外在条件下的感觉(远处看见一座塔是圆的)、理想外在和理想内在条件下的感觉(看见我有手)、数学运算(2+3=5)、CES 等。因此,在笛卡尔那里,怀疑作为反论证是在与正面论证的相互升级的对冲性关系(对话关系)中将怀疑推进到最高程度:怀疑怀疑者自身的存在。而CES本身面对的怀疑论证就是恶魔怀疑:一个全能的恶魔无时无刻不在欺骗沉思者以至于可能一切沉思者所知觉皆为虚幻。在CES 程序中,怀疑者虽然处于第一人称视觉,但是并非处于一种无法理解的私人语言的喃喃自语中,而是在跟自身进行一种可理解的、理性的对话和交流。因此,确立CES 的程序是一种正面论证和怀疑论证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可以认为使用了语言,遵从了理性。
2.CES 中“我”具有空洞性:这个“我”并指向作为本质的思维,而只有空洞的意义,因此“我”并不预设人类本质的任何特征,它只是一个逻辑主体、位置或角色,可以将其替换为一台机器智能体。
CES中的术语“我”容易给人一种误导,让人以为这个人称代词在某种程度上已预设人类主体的某些特征和存在性。在这种情况下,CES 程序就只限于人类主体,而无法将其推广用于人工智能体。凯莫林(Andreas Kemmerling)认为,在CES 处于恶魔怀疑的极端怀疑场景下,这个“我”的指称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a)如果“我”指向某物,那么它就指向唯一一个个体(“我”是一个单称词项);
(b)“我”的指称机制保证“我”一定指向某种存在物;
(c)“我”的指称机制不允许借助心灵之外的(或其他不具有确定性的)因素。
因此,“我”不可能是普通的专有名词(比如“笛卡尔”),因为专有名词含有认证标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记录、身份证等),而这个认证在怀疑场景中是不可调用的,否则违反(b)和(c)。“我”也不可能是摹状词“那个ɸ”(比如“《谈谈方法》的作者”)的缩写,ɸ是一种性质,但是怀疑者并不能在怀疑场景下确信自己是否具有ɸ,否则违反(c)。“我”也不是一个代词,因为代词身后都藏着一个专有名词或摹状词(比如“这”,本质上是一种依赖语境的摹状词)。“我”也不是没有独立意义的助词。“我”唯一的可能性是一个非正常专有名词,它没有可被描述的意义,但是在指称功能上与摹状词“那个ɸ”一样,而且怀疑者可在怀疑中确信那个性质ɸ。在怀疑状态中,CES 中的这个“我”只能依赖CES 自身,那个性质ɸ 就在CES 自身之中。而在CES的时刻,“我”只证明自身存在,并不证明“我”的本质是什么,因此这个“我”并没有语义内容(关于本质),是空洞而没有意义的。但是“我”毕竟有某种意义,那就是有一种认知内容ɸ(能引导指向该对象,但不关心是否把握了对象的本质)①凯莫林:《“我”之观念——笛卡尔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2-99页。。
凯莫林还通过严密而令人信服的分析表明,“我思故我在”“当我思考我存在这个命题时,这个命题为真”“当我思考时我存在”“我存在”等命题在笛卡尔体系中都是同构或等价的表达,它们共享一个共同的“深层结构”:
P:本思考事件的思考者(有本思想并)因此存在。
The thinker of this thought event(has this thought and therefore)exists.②凯莫林:《“我”之观念——笛卡尔哲学研究》,第101-102 页;参考德文版Andreas Kemmerling,Ideen des Ichs—Studien zu Descartes’Philosophie,the 2nd edition.Frankfurt:Suhrkamp Verlag,2005,S.119-121。
如果去掉P 中的括号就是命题“我存在”,而保留则是CES。这个结构表明“我”的指涉只有认知内容:“我”只是这个P自身的思考者,并不具有语义内容:作为本质的思维。
人们或许否认CES 具有P 这样的结构。让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关于CES 的主流解释。辛提卡(Kaarlo Jaakko Juhani Hintikka)认为CES是一种存在性自我确证(existentially self-verifying)的言语行为。这个行为就是如下场景:
单项a:我。
单项b:听者(可以是a自己)。
句子Q:我存在,或蕴涵这个意义的其他陈述句。
行为:a对听众b言说Q以表明Q为真。
结果:Q为真。
CES就是一个存在性自我确证的言语行为:当a向听者b言(可以是a自己)说一个句子Q想使听者b相信“a存在”时,这个a的言语行为(performance)本身恰恰在效果上向听者b表明“a 存在”,从而说话者实现一种自我确证①Jaakko Hintikka,“Cogito, Ergo Sum: Inference or Performanc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2, vol.71, No.1, pp.3-32.。在这种解释中,关于“我”的指称机制并未超出凯莫林的分析范围,“我”只是一个言语行为者,也就是一个思考者。
在本文看来,凯莫林和辛提卡两种主流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兼容。CES中的主体只是一个思考行为相关的逻辑位置,只是一种逻辑主体或角色。因此,在普遍怀疑的氛围之中,CES中这个逻辑位置完全可以被其他行为体填补,以向外界表明它通过CES确证了自身主体或自性的存在。因此“我”的空洞性为CES成为智能测试标准扫除了关键障碍。
3.CES的程序蕴涵了对理性之理解和判断能力的使用。
在凯莫林和辛提卡对CES 的主流解释中,可明显看出CES 涉及到“我”对“我”自身、“思”和“在”之间关系的理性直观和把握,以及对相关项之间逻辑关系的联结和判断。CES的核心逻辑在于,从本体论角度看,如果不在便不可能思;只有我在,才可能思。但是从认识论角度看,如果现在可以确定我在思,那么这必定蕴涵着我可确定我已经在。CES 具有一种独特的自我确证、自我担保为真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理性的理解和判断。这一点能够保证CES作为机器智能检测标准时将理性能力指标纳入测试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CES这个正面论证的是反论证恶魔怀疑。如果一个怀疑论证与一个正面论证处于一种完全对冲状态,那么理性在权衡之下就需要悬置判断。因此CES程序中潜在包含一种悬置判断的可能性,这是判断人工机器是否具备人类智能的重要指标。因为人类智能思维具有停机或悬置的特征,这种悬置至关重要,因为人类可依据这种悬置和停机能够处理矛盾、悖论、不可判定性等问题②赵汀阳:《终极问题:智能的分叉》,《世界哲学》,2016年第5期,第63-71页。。
4.CES存在一种反思性的自我意识以及独特的自我指涉或自相关性。
在凯莫林和辛提卡的两种解释中,CES 均包含一种反思性的自我意识,思维者需要意识到自己在思维,意识到自身具有相关联的思想。除了这种反思性自我意识,CES 中还存在一种独特的自我指涉或自相关性。在句子“本思考事件的思考者有本思想并因此存在”中,这个“本”具有一种自反性特征,指向整个句子本身。在言语行为的理解中,被言语的命题“我存在”本身则自反性地指向言语者自身的存在状态。
赵汀阳认为CES 具有一种反思意识,涉及一种自相关性,标识着人类智能的独特特征。“笛卡尔反思我思而证明我思的真实性,这非常可能是自相关能够成为确证的唯一特例,除此以外的自相关都有可能导出悖论或不可判定问题。其中的秘密可能在于,当作为主语的我思(cogito)在反思被作为所思(cogitatum)的宾语‘我思’(cogito)时,我思(cogito)所包含的二级宾语所思(cogitatum)却没有被反思,或者说没有出场,而只是隐含于我思中,因此,各种潜在的悖论或哥德尔命题之类的隐患并没有被激活。但是,笛卡尔式的自我证明奇迹只有一次,当我们试图反思任何一个包含无限可能性的思想系统时,种种不可判定的事情就出场了,就是说,反思一旦涉及思想的具体内容,不可判定的问题就出现了。”①赵汀阳:《终极问题:智能的分叉》,第63-71页。赵汀阳是意识到笛卡尔我思对人工智能问题价值的少数学者,但是本文不同意他对CES的解释,依据我们上面的分析,CES 被反思的只有其命题自身或者“我存在”这个命题,并没有涉及其他思想的具体内容,而CES 的反思跟哥德尔这种系统层面的反思不属于一个类型。但是本文认可赵汀阳把反思性和自相关能力视为一种人类智能核心的观点。“智能的要害不在于运算能力,而在于反思能力。人的主体性本质在于反思能力,没有反思能力就不是思维主体。”②赵汀阳:《人工智能提出了什么哲学问题?》,《文化纵横》2020年第1期,第43-57页。CES 包含对思维活动的反思性特征和自相关性特征正好体现了CES作为智能测试标准的优越性,它包含了这两项关键指标。
5.CES作为认识起点可对后续关于人类本质的模型架构保持中性。
笛卡尔是在确立CES后来才继续分析“我”之本质在于心灵之思维,然后再通过后续的工作确立身心二元论(虽然整个论证存在瑕疵),同时又保留三元论的架构。由于CES是笛卡尔整个认知事业的绝对起点,因此在认识论的秩序上CES并不依赖于在它之后被确立的任何关于人类本质的模型,它对身心二元论或三元论等后续理论都是中性的。这个优点使得CES作为人工智能检测标准不会预设任何关于主体本质的知识框架。
从上面五点可以看出,CES提供了一个古典极简模型和最低限度的标准来判断人类主体的存在和自性。CES 程序体现了人类智能的几个核心特征:语言对话能力、理性的理解和判断能力、反思能力、自相关性思考能力。同时CES具备两项独特的优势:“我”具有空洞性而只是一个逻辑位置(不预设以人类智能为前提);CES不依赖特定身心框架而是中立的。其他形式的表述,比如“我不在故我不思”“你在故你思”“他在故他思”“我们思故我们在”“思故在”等形式都不能替代CES 的独特性以及相应的优势。CES 成为人工智能的检测标准并不存在本质性的障碍。因此笛卡尔的丰富哲学中还潜在地包含一个关于智能标准的第三个测试:“我思故我在测试”。这个测试比笛卡尔的前两个测试(语言测试和理性行为测试)更为完备、更为综合、更为聚焦、更有可操作性、更有清晰的临界点和判断标准。
我思故我在测试的要求比图灵测试的似乎更高,是一种更高智能水平的测试标准。图灵测试主要从语言或符号系统的角度来判断机器是否具有理性或智能,其基本设想在于,语言能力等价于构造世界的能力,具备人类的语言能力就具备思想能力①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第5-12页。。赵汀阳认为,从智能的哲学性质上看,人工智能可区分为二类:一类是尚未达到笛卡尔我思标准的非反思性人工智能,相当于当前图灵机概念的AI(包括单一功能的人工智能,例如Alpha Go,以及尚未成功的通用人工智能);二类是达到或超越了笛卡尔我思标准的反思性人工智能ARI(artificial reflexive intelligence),ARI 具有自主反思和修改自身系统的能力,具有自律自治的主体性,大约等同于超级人工智能SI(super intelligence),或超图灵机,也可称之为哥德尔机;笛卡尔式的我思和哥德尔式反思性都代表着一种人工智能等级的标准和奇点②赵汀阳:《人工智能会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吗?》,《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第49-54页。。赵汀阳洞见到笛卡尔“我思”对人工智能测试的潜在价值,不过他对我思测试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其中包含的反思性自我意识和自相关两方面,并未从本文的其他四个方面分析CES测试所能体现的完整智能特征以及这种测试的可行性。同时,本文不赞同赵汀阳将我思的反思和哥德尔式反思的哲学效果等同起来,因为它们的反思性层级并不一致。CES的反思和自相关性主要是针对这个命题本身或者“我存在”这个命题,而哥德尔的反思和自相关性则是针对数学系统而具有系统性,两者具有质性的差别。因此,本文认为,更合理的划分应该是图灵测试、我思故我在测试、哥德尔测试三个等级。满足哥德尔测试的机器智能性会更高。就如赵汀阳所言,如果机器智能具有哥德尔式的自相关性反思能力,就具备自主建立游戏规则的创造力,修改自身的系统,机器就非常可能进化为与人等同或更高级别的存在②赵汀阳:《人工智能会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吗?》,《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第49-54页。。只要能对自身进行自相关研究,标志着思维获得自主性,能对思维系统进行修改;人工智能有能力通过哥德尔测试就成为世界的立法者③赵汀阳:《人工智能提出了什么哲学问题?》,第45-56页。。人工智能的危险不在于能力,而在于自我意识,有了对自身系统的反思能力,就能够改造自身系统,创造新规则④赵汀阳:《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何以可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1期,第1-8页。。如果具备制定规则和修改规则的能力,就有了创造性,而这个是更高等级的智能标准。这个是我思故我在测试所不能达到的。
以上我们论证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程序作为一种人工智能测试标准的可能性。如果一台机器在恶魔怀疑的约束和挑战下能提出或认可“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台机器已具备某种智能,具备笛卡尔确证人类智能之自性和存在那种尺度上的智能。
五、结论
本文重构笛卡尔关于人之本质、关于人工机器之本质的思考,分析笛卡尔对人工智能持悲观态度的判断中表现的深刻洞见和论证瑕疵。本文认为,笛卡尔哲学并未耗尽自身关于人工智能问题的理论思考潜力。他的身心三元论、思维的原子主义思想、确立人类主体自性和存在的“我思故我在”分析都可能对当前人工智能具有启发性。笛卡尔不仅明确地提供了两个广受关注的智能测试标准(语言测试和理性行为测试),而且还潜在地提供了更优的第三个智能测试标准(我思故我在测试)。当然,本文的全部工作只是从哲学理论上提出“我思故我在”作为潜在智能测试标准的可能性问题,具体技术操作以及相关的其他问题则有待AI专家更进一步讨论和论证。
致谢:本文的形成得益于本人在清华大学开设《西方近代哲学》(2018-2021)课程中的师生讨论,得益于山西大学梅建华教授的鼓励,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