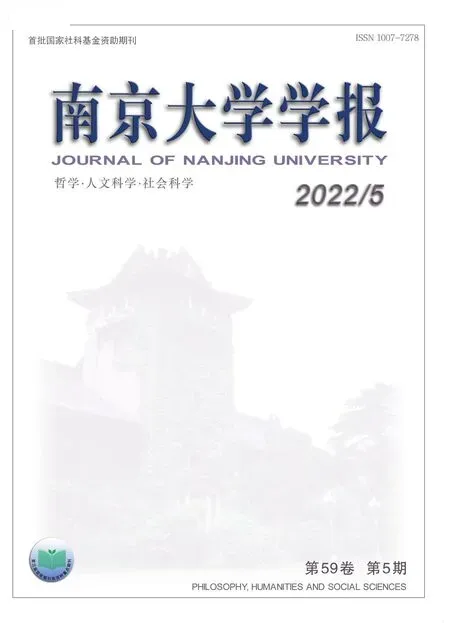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
——《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生存论
张志伟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存在与时间》之所以难以理解有很多方面的原因,而此在与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是此在,但此在指的并不就是“人”。人不过是诸存在物中的一种存在物(1)《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将“das Seiende”译作“存在者”或“在者”,实际上也可以译作“存在物”。按照惯例,我们往往把人称为“者”,把单纯的物称为“物”,然而当海德格尔说人是诸在者中的一种在者时,与人是诸存在物中的一种存在物,基本上是一回事。考虑到与中译本引文的一致,本文在存在者和存在物之间交替使用,其意相同,特此说明。,人作为此在则说的是它为存在所规定,具有“去存在”(zu sein,to be)的性质,因而是一种能够存在论地存在的特殊存在物,海德格尔称之为“此在”(Dasein),取“存在”(Sein)在“此”(da)存在出来之义。所以,人最源始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不是族类式的,也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存论的。于是问题就集中于此在的特殊身份上:此在是诸存在物中的一种存在物,不过又是能够“去存在”的存在物,因而“这个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之有所作为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4页。,海德格尔称之为“向来我属性”(Jemeinigkeit),而这里的“我”并没有主体、自我、灵魂等意思,“向来我属性”比这些都更“源始”(3)“源始的”(ursprülich)并非时间上在先的“原始的”,而是根源的、源泉的、基础的意思。,此在并非由“类”所规定,也非与世界绝缘的主体,而是作为个体而生存的存在物。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不是形而上学之思想的对象,而是在此在的生存活动中显现的,解答存在问题须从此在的日常生存活动入手,因而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乃是一切存在论之所以可能的基础,此即“基础存在论”。
因此,此在具有“双重身份”,它是诸存在物中的一种存在物,同时又是能够“去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此在对它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它对存在的领会决定着它的存在,而它的存在则影响着存在的显现。我把这种“双重身份”称为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意在体现这种双重身份的“重叠”所造成的复杂性。或许“之间”并不是合适的表述,很容易被看作是两个东西“之间”,所以我为“之间”打上了引号,这里的“之间”并非在两个东西之间,而就是这个“之间”本身:此在是存在物,也是去存在的存在物,它与它的存在乃为“一体”。就此而论,此在与存在具有某种相互需要的复杂关系:此在因存在而存在,存在因此在而显现;当此在仅仅把自己当作存在物的时候,它的存在便遮蔽了存在,然而即便是此在对它的存在的遮蔽,其存在也具有“去存在”的性质,甚至可以说,唯有此在能够以遮蔽自己的存在的方式存在。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通过此在对自己的存在的遮蔽而展露出此在之存在的存在论(生存论)机制,从而探寻让此在不再以遮蔽存在而是以让存在显现的方式而存在的途径。所以,当海德格尔区分此在之存在的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之时,这并不意味着此在的存在“原本”是本真的,后来“堕落”为非本真的(沉沦),而是说,无论本真状态还是非本真状态都是此在“去存在”的可能性,因而在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的“背后”是此在的“能在”(Seinkönnen),“生存着的此在包含有向来我属性,那是本真状态与非本真状态之所以可能的条件”(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80页。。
“之间”(Zwischen)是《存在与时间》中的一个概念,但不是重要的概念,我用“之间”来体现此在之为此在这一能够去存在的存在物的复杂处境。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活动的生存论分析的目的是让此在自己“道说”出自身的存在,然而此在的特殊身份恰恰阻碍了存在的显现,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此在自始就已经“沉沦”,它从来就没有本真地生存过。那么,为什么能够“去存在”的此在千方百计地逃避自己的能在?如何让此在从沉沦之迷梦中醒来?这可以看作是《存在与时间》已完成的部分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形而上学试图通过抽象思维把存在当作思想的对象,由此来超越个体性和有限性,通达普遍性和无限性,虽然路走错了,但是可以理解的;而海德格尔试图以具有“向来我属性”的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此在来解答存在问题,似乎不可理解:个体的此在其存在难道不是个别的存在吗?如何由一个个体存在物来解答所有存在物的存在?这亦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此在的“优先地位”
黑格尔之后,形而上学衰落,不过在诸多批判形而上学的哲学流派之中,海德格尔与众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问题是哲学的真正开端。哲学起源于希腊。思想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因而哲学深受希腊语(印欧语系)的影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存在”(Being)成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系词“是”(to be)构成了印欧语系的基本语法结构,由苏格拉底概括为“是什么”(what is)的问题则构成了希腊哲学(科学)的基本问题。如果把我们面前的自然万物都看作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描述(S是P),那么世界就是由所有可能的描述所构成的整体;当希腊人追问生灭变化着的自然万物中究竟什么是不变的,“存在”便脱颖而出:所有的描述“S是P”中的“S”和“P”都是生灭变化的,唯一不变的是维系着所有的“S”和“P”的“是”,由此而出现的现在分词“Being”,我们通常译作“存在”,便成为哲学要追问的东西。巴门尼德第一个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强调存在是“一”,是不动不变的,但是难以返回去解释生灭变化多种多样的事物(现象)。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是什么”问题出发,形成了作为事物之本质共相的“理念”,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区分了科学与哲学的工作:科学分门别类地描述存在物,哲学则为所有存在物的存在“分类”。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存在是一套范畴体系,即为所有不同类的存在物之统一的存在提供最普遍的解释的逻辑结构。由此,以存在作为思想的对象,以一套范畴体系规定存在的结构,就构成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黑格尔之后,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对形而上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不过英美分析哲学强调的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伪问题,而海德格尔则试图把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在他看来,问题是有意义的,只是形而上学的解答方式错了,形而上学追问存在问题的方式从一开始就误入了歧途。
王庆节教授曾经在一次讲座中强调《存在与时间》第二节“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的重要意义,笔者深以为然。海德格尔把问题的结构分为三个方面:“问之所问”(Gefragtes),“被问及的东西”(Befragtes)和“问之何所以问”(Erfragtes)(5)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9页以下诸页。,这看起来有些故弄玄虚,实际上大有深意。我们要追问的问题是“存在”,一说到存在总是指某一存在者的存在,不过存在问题只能从能够存在论地存在的此在入手,因而存在问题不再是诸存在物的存在,而是此在自己的存在,这意味着存在问题的事先引导乃是此在对自己的存在的“领会”(Verstand)。存在对于此在成为问题“之前”,此在已经存在着,总已经对自己的存在有所领会,而此在对存在的领会则主导着此在的生存活动。“我们不知道‘存在’说的是什么,然而当我们问道‘存在’是什么时,我们已经栖身在对‘是’(‘在’)的某种领悟之中了,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确定这个‘是’意味着什么。”(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9-10页。
存在问题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此:虽然一切存在物因存在而在,但一说到存在总是存在物的存在,唯有当某一个存在物能够追问自己的存在的时候,存在问题才算是一个有效的问题,而只有人这种存在物(即能够去存在的此在)可以对自己的存在发问,所以是解答存在问题的入手之处。一方面,在存在问题上,我们不是对存在于我们“之外”的存在物发问,而是对自己的存在发问,这意味着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在问题的问法上就误入了歧途,它实际上把存在当作存在物来追问了:我们作为主体“站在”存在对面,存在则超越一切存在物而成为我们思想的对象。然而另一方面,存在总是存在物的存在,离开了存在物我们无法“触及”存在。由于我们与自己的存在原为“一体”,在存在成为理论问题之前,我们就栖身在对存在的领会之中了,我们怎么领会自己的存在,我们就怎么存在,我们的存在也就怎么“展开”,因而唯有通过对我们自己“最本己的存在”的追问才能回答存在的意义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回溯到“前科学”“前理论”“前理性”……的维度或境域,不是对存在进行“理性直观”“理论分析”或“逻辑推理”,而是通过此在于其日常生活中与存在浑然一体的生存活动崭露存在。此前所有的存在论都没有深入到这个维度,所以都是无根的,唯有通过关于此在的生存活动的生存论分析才能为存在论奠基。
因此,在存在问题上此在无论如何都具有“优先地位”:此在“这个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此在在它的存在中总以某种方式、某种明确性对自身有所领会”,“它的存在是随着它的存在并通过它的存在而对它本身开展出来的。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的规定。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在存在论层次上存在”(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8页。。然而,此在的这一优先地位并不意味着它天然地就处在让存在显现的状态之中,恰恰相反,此在一向在逃避自己的存在,从而遮蔽了存在。这不仅构成了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根源,也构成了《存在与时间》之所以难以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此在与其存在之间的“张力”
《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包括导论和第一部的前两篇。导论概述存在问题,第一篇是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说明此在为什么自始就已沉沦,第二篇《此在与时间性》,说明如何让此在从沉沦迷梦中醒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与时间》自始至终缠绕于此在与其存在的复杂关系之中。
因为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所以此在是追问存在问题须首先追问的存在物,然而了解了这一点并没有使问题变得简单,反而更加复杂了,问题恰恰出在此在的“优先地位”上。《存在与时间》导论中有两段话揭示了此在与其存在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确实,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不仅是切近的,甚或还是最切近的——我们自己甚至一向就是此在。虽然如此,或恰恰因为如此,此在在存在论上又是最远的。(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3页。
因为这个存在者层次上的“切近”就等于存在论上的“最远”:存在虽然总是存在者的存在,追问存在问题必须落实在此在这一特殊的存在者上,但是执着于存在者也正是此在遗忘存在的根源。
所以,此在特有的存在建构(如果把它领会为属于此在的‘范畴’结构)对此在始终蔽而不露,其根据恰恰就是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在存在者层次上离它自己“最近”,在存在论上最远,但在前存在论上却并不陌生。(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4页。
此在乃是诸存在者中的一种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而存在如此地“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以致此在仅仅把自己当作存在者,因而“在存在论上最远”,但是此在之为此在毕竟是“去存在”的存在者,即便是仅仅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也是如此,故而“在前存在论上却并不陌生”。
形而上学把存在当作思想的对象,貌似以人为认识主体,把存在当作与我们相对而立的认识对象,从而把存在对象化为存在者,所以形而上学始终与存在失之交臂。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不在此在“之外”,存在在此就是此在的存在,即一向为形而上学不屑一顾的日常生活中的生存活动。结果,“正因为平均状态构成了这种存在者在存在者层次上的首先的情况,所以它过去和现在都在对此在的解说中一再被跳过去了。这种存在者层次上最近的和最熟知的东西,在存在论上却是最远的和最不为人知的东西,而就其存在论意义而言又是不断被漏看的东西”(1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6页。。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把此在这种居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最近”“最远”但又并不“陌生”的相互缠绕、难解难分的复杂状况揭示得淋漓尽致。
因此,形而上学以范畴体系的方式提供关于存在者的存在的逻辑结构,实际上不过是关于存在者的抽象而形成的本质规定,由此而形成的只是关于物的规定,根本无法触及存在。就此而论,在海德格尔这里,“zu sein”(to be)不是系词,而是动词,他要呈现的不是一个由普遍的共相构成的、为现象界提供逻辑结构的“本质世界”,而是此在的“生活世界”,即“存在”(Sein)于“此在”(Dasein)源始的“生存活动”(da)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所以真正构成存在论基础的不是规定存在者的范畴,而是能够呈现此在活生生的生存活动的生存论规定。鉴于这个此在的源始世界实际上是“忘在”的“常人世界”,形而上学在此有其根源,所以海德格尔致力于揭示此在沉沦中的生存论机制,谋求能够让此在摆脱沉沦状态从而本真地在世的可能性。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当此在自己存在从而立足自身而在世时,此在就是本真的(本己的);当此在不是自己存在,而是仅仅把自己看作存在者从而立足于“他人—常人”而在世时,此在就是“非本真的”(非本己的)。问题是,既然此在“本性”上是“向来我属”地“去存在”的存在者,它为什么不是作为自己而是作为“他人—常人”而存在?此在作为存在者被抛地在世,“被抛状态”(Geworfenheit)意味着此在是不自由的,然而被抛之处却是可能性的境域,当此在畏惧无依无靠的可能性境域而选择沉溺于被抛状态,消散于操劳之在者,混迹于芸芸众生时,不恰当地说,此在实乃不自由地“陷入”了自由,却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这意味着无论本真还是非本真,都是此在“去存在”的可能性,不过此在的“首选”却是非本真地生存。在一切存在者中,唯独此在既是存在者同时也是“去存在”的存在者,于是此在便集对于存在的遮蔽和显现于其一身。正是因为此在之“去存在”的方式乃是存在的显现,它可以显现自身,也可以不显现自身而把自己显现为别的东西,例如以“他人—常人”的方式而在世。
那么,此在为什么作为“去存在”的存在者却始终在逃避自己的“去存在”?海德格尔通过最极端的情绪——“畏”(Angst)——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此在是“去存在”的存在者,自己去存在就必须由其自己去筹划并且为之承担责任,相反,按照“他人—常人”的方式生存在世则使此在油然而生起某种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一切都在最佳安排之中、一切都有人负责的“家园感”。而当此在自己去存在时则会感受到存在的负担,有负担便会有情绪,所以情绪是此在之生存的最源始的呈现,恰恰在情绪中我意识到了“我在”,而真正能够让此在直面自己的存在的情绪就是“畏”。畏之有所畏却不知道畏的是什么,因而畏启示着“无”。畏之无把此在带到了它自己的存在即可能性面前,此在作为向来我属的个体存在者并没有任何存在者可以依靠,常人其实查无此人,从无此人,因而在畏所启示的境域中,诸神隐退,万物消融,一切都沉陷了,唯此在孤零零地面对自己的存在,从而让此在意识到“我存在,且不得不存在”乃至“我存在,且不得不能在”。由此可见,存在对此在来说并非赏心悦目的理想对象,而犹如空无所有的深渊。这就是此在是去存在的存在者却自始就在逃避自己的存在的根本原因。
海德格尔试图惊醒世人的是,此在逃无可逃,逃来逃去,还是在自身之中,它所依赖的“常人”查无此人,实际上不过是此在自己。所以,海德格尔把此在的沉沦称为“从自身脱落到自身”,这意味着此在从一开始就是把自己当作常人而“自欺”地生存在世的。此在生来就在沉沦的常人世界之中,并非先是本真的,后来堕落而沉沦。“本真的自己存在并不依栖于主体从常人那里解脱出来的那样一种例外情况;常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上的东西,本真的自己存在是常人的一种生存变式。”(1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87页。既然此在自始就已经沉沦,而其沉沦亦源于其“去存在”的本性,那么如何让此在从沉沦之迷梦中醒来?
三、向死而在
此在之沉沦是此在“从自身脱落到自身”,惊醒此在的沉沦迷梦也就是让它“从自身回到自身”。海德格尔试图以“畏”这一最极端的情绪将此在迫回到自身而自觉其能在,但此在恰恰逃避能在而不敢去畏。能够迫使此在去畏的是直面死亡,这就是海德格尔为什么要让此在“提前到死中去”“向死而在”,而其中的关键就是从生存论上把死亡解释为一种特殊的可能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通常的死亡观即非本真的沉沦的死亡观,把死亡看作是“存在到头”:活着是存在,死亡是不存在,因而死亡是发生在生存“之外”的事,可以与生存毫不相干;而海德格尔生存论的死亡观则把死亡看作是“向终结存在”,由此而把死亡解释为一种生存论的特殊现象。在他看来,死亡并不是发生在人生之外的事件,而是人从一出生就不得不承担下来的最确定也是最极端的“可能性”。人生终有一死,这是人从一出生就注定了的结果,但是对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死当下还没有“来”,所以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可能性”。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所有的可能性都可能实现而为现实性,死亡这种可能性却不可能这样“实现”,恰恰相反,死亡乃是使一切可能性不再可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死亡就好像“嵌入”了我们的人生之中,我不能摆脱,他人也不能代替,所以死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上述这两个方面表明死亡具有“去存在”(可能性)和“向来我属性”(本己性),而这正是此在的生存论性质:
每一此在向来都必须自己接受自己的死。只要死亡“存在”,它依其本质就向来是我自己的死亡。死确乎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存在之可能性:在死亡中,关键完完全全就是向来是自己的此在的存在。死显现出:死亡在存在论上是由向来我属性与生存组建起来的。(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34页。
由此,死亡作为一种独特的生存论现象所体现的不是不存在,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当此在“先行于自身”“去存在”时,死从始至终“悬临于此”。如果我们把死亡看作是“终结”,那么此在的生存始终“向终结而在”,即“向死而在”。如果我们把死亡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可能性,那么可以说此在之“向终结而在”即“向可能性而在”。于是:
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此在在这种可能性中完完全全以它的在世为本旨。此在的死亡是不再能此在的可能性。当此在作为这种可能性悬临于它自身之前时,它就被充分地指引向它最本己的能在了。在如此悬临自身之际,此在之中对其他此在的一切关联解除了。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同时就是最极端的可能性。此在这种能在逾越不过死亡这种可能性。死亡是完完全全的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于是死亡绽露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1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47页。
直面死亡,就像在畏的情绪中直面空无一样,此在直面的是自己之纯然可能性的能在。死是此在一旦生存就不得不承担的可能性,而且是不可推卸的可能性。因而在其所有的存在可能性中,死亡是最本己的可能性,向死而在即向最本己的可能性存在,这就为此在开展出它最本己的能在来:此在在此清楚地看到,它在这一别具一格的可能性中保持其为脱离了常人的,即是说,死这种存在可能性的不可替代性使此在对常人的依赖变得毫无意义,从而迫使它回到自己的能在中,也正因为如此,此在意识到自己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沉沦”于常人的。因此,“把向死亡存在标识为向着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也就是向着此在本身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可能性的存在”。在向死亡存在中,“这种可能性就必须不被减弱地作为可能性得到领会,作为可能性成形,并坚持把它作为可能性来对待”(1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60、361页。。因而能够让此在摆脱对存在者状态的执着,非得“置之死地而后生”,故而死亡作为一种别具一格的生存论现象,乃是与可能性之境域、“先行于自身”之“能在”,即与此在的“去存在”,联系在一起的,直面死亡也就是直面可能性的人生,即直面自己的存在。海德格尔将死亡与存在相提并论,的确独出心裁,别具一格。
海德格尔死亡观的核心即从生存论的角度把死亡看作是一种可能性,此乃此在如何能够本真地存在的关键,并且也是我们由此而思考存在问题的焦点:作为“向来我属性”而去存在的个体化的此在如何能够展露出所有存在者的存在?
四、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
在某种意义上,从海德格尔哲学的角度看,哲学的所有问题,形而上学的所有问题,甚至人生在世的所有问题,都源自此在与存在的复杂关系。如前所述,存在与此在有一种奇特的相互需要的关系:一方面所有存在物(包括人在内)皆因存在而存在,另一方面存在必须通过某一存在者而显现,人作为此在就是能够显现存在的存在者,或者说是被存在“选中”显现其自身的存在者。既然此在是存在者,它从存在者出发把自己看作是存在者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就此而论,它不会把自己看错。然而,因为此在是能够去存在的存在者,如果它仅仅把自己看作像自然万物那样的存在者,它肯定会陷入迷途,实际上也只有此在才有可能如此“误入歧途”:“只有这样一种存在者才具有这种除根的存在可能性,除根不构成此在的不存在,它倒构成了此在的最日常最顽固的‘实在’”(1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40页。,形而上学之“忘在”应该在此有其根源。但是无论如何,此在之“去存在”乃是“先行于自身”,“先行”的并非规定其存在的本质,而是指向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去存在”意味着此在始终面临着犹如深渊的不确定的可能性境域,因而它无时无刻不在“操心”(Sorge)之中。它之非本真地沉沦于世是如此,自欺有“常人”作为依靠也是如此,能够提前到死中去,向死而在,亦是如此。
看上去存在与此在之间的关系类似基督教之上帝“道成肉身”或黑格尔哲学之绝对“化身为人”,然而从根本上看二者是不同的。存在既不是超越的上帝之道,也不是潜在的绝对,类似先在的本质通过人来“实现”,存在相当于“无”。按照海德格尔后期的说法,存在以呈现为存在者的方式让此在思存在,然而此在满目都是存在者,存在却无迹可寻。所以此在之艰难就在于,作为一个能够去存在的存在者,它要作为一个存在者而呈现存在,可是只要它有所行动,就已经是存在的存在者化了,所以真正的难题就是,此在如何能够作为一种存在者而显现存在?此在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它很容易而且实际上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处在两者之间,即存在与存在者这两者之间,形而上学一向也是这样看的;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此在并不在两个东西之间,只有存在者存在着,存在并不“存在”,它必须通过此在而存在,所以此在源始地就是这个“之间”本身,《存在与时间》的一切努力,就是让此在成为这个“之间”。
那么,作为存在者的此在如何能够成为这个“之间”?
此在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却并非自然而然地就是“之间”。此在作为存在者而被抛入世,与众(在者)不同的是,它是能够去存在的存在者,“此在”(Dasein)的“da”就是存在在此存在出来的“境域”,因而此在之被抛实乃被抛入了“去存在”的可能性之中。既然是存在者,此在就要像其他存在者一样要现实化自身,海德格尔称之为“实际性”(Faktizität),其区别于一般存在物的“事实性”(Tatsächlichkeit),指的是此在特有的现实化。对此在来说,实际性这一现实化不是一次性成型就此凝固不变了,此在始终在现实化之中,而且并非某个东西或实体的现实化,所以重要的不是此在现实化而成为“什么”,而是始终保持自身为“去存在”。由此我们将面临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此在是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去存在”的存在者,这意味着此在总是一个个体存在者,那么一个个体存在者对自己的存在的显现,如何能够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
形而上学也把人看作存在于存在与存在物“之间”,只不过这个“之间”是两个东西的“之间”。存在作为思想的对象,是人试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超越一切存在物而意欲通达的最高的存在者,这意味着人要从存在物这一边“超越”到存在那一边。哲学家们殚精竭虑、千方百计谋求的是如何从思想上呈现无限永恒的存在,然而如何超越横在存在与存在物之间的鸿沟,以有限存在者之思而把握无限永恒之存在,实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不是思想的对象,而是在此在这种能够去存在的存在者的生存活动中显现出来的,此在的“超越”就体现于它的“去存在”之中。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此在的生存活动就是存在的显现?唯当此在投身于可能性的境域,它自己就是可能性本身,从而始终保持自身为“去存在”的状态,即成为“之间”。因而,此在的存在如何能够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可能性”之中。
海德格尔不再按照认识论的思路或者理论的态度来解答存在问题,而是从生存论出发,通过对人这种始终处在“去存在”的存在者的生存活动的生存论分析,来揭示存在是如何通过此在而显现出来的。一方面,海德格尔揭示了形而上学忽略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仅仅把存在者的普遍共相视为存在,这实际上把存在对象化为了存在者。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把存在与存在者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因为存在问题毕竟只能通过某种存在者来回答,这意味着必须有一种存在者能够“克服”这一差异,这就是此在——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者。由于此在具有“去存在”的性质,所以是存在在此存在出来的境域。然而,此在是能够去存在的存在者,但也毕竟是存在者,当存在通过此在而显现的时候,难道就不是存在的存在者化吗?如果存在是作为此在的存在而实存的,我们如何能够以这种方式解答存在问题?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试图通过思想来超越有限性而通达存在,这的确有其问题,但是通过个体化的此在来通达所有存在者的存在,难道就是可行的吗?就此而论,海德格尔面对的是一个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有限之人,或者有死之人,如何通达存在?这里的关键是,存在通过此在的生存活动而显现,存在的显现不是显现为“什么”,而是“显现”,或者说要通过显现为什么而成为显现本身。此在是有死的,人之有死,盖棺论定,总是概括总结他都做出了什么丰功伟绩,然而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所以人之一生总有“尚未”而残缺不全,总是未完成的。倘若仅仅关注于此,我们见到的就只是存在者状态,当然见不到存在。然而,如果存在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存在便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此在之所以能够承担让存在显现的重任就在于此——此在本身就是可能性。此在不可能也没必要实现存在的所有可能性,只要它是可能性,足矣。
显然,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这个“之间”是很难描述的,因为任何描述所描述的总是存在者,存在是不可描述的。我们可以试着用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来理解这个“之间”。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向”,此在不再是海德格尔解答存在问题的“立足点”,他从致力于让此在来显现其存在,转向了不显现的存在本身。相对于“Dasein”,海德格尔更多地使用“Da-sein”,即不是强调此在乃是“在之于此”中的“此”(da),而是强调“此之于在”中的“在”(Sein),或者说,唯有当人进入到这个“此”,它才是此在。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此”理解为“之间”。的确,当存在向人“本质性地现身”(wesen)之际,存在者存在,而存在“悬缺”。存在不是存在物,如果我们把存在物叫作存在,那么存在本身就“不存在”,存在相当于“无”。然而这里的“无”并非没有,存在其实在呈现存在物之际已然在此,只不过是以“无”的方式在此。所以海德格尔在《尼采》中说:
人即使在惟一地根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认识存在时也已经与存在相对待,就此而言,人就在与存在打交道。人置身于存在本身与人的关联中,因为人之为人是要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打交道的。由于存在把自己托庇于无蔽状态中——而且只有这样它(Es)才是存在——,存在本身就与它的到达场所(作为其悬缺的寓所)一道发生出来了。这个所在(Wo)作为隐蔽之所的此(das Da der Bleibe)属于存在本身,“是”(ist)存在本身,因此被叫作此之在(Da-sein)。(16)海德格尔:《尼采》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89页。
存在以悬缺的方式呈现出存在物而隐匿了自身,显现与遮蔽是一同发生的。人只有成为“Da-sein”,进入显—隐“之间”,才能“思”存在。
在《存在与时间》中,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是此在,而在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中,在“显隐之间”“在与不在之间”,也可以说在“有无之间”的,是“存有”(Seyn)(17)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页注。“Seyn”(存有)是“Sein”(存在)的古式写法,大抵与“本有”(Ereignis)有同等的意义,海德格尔以此来思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和存在历史。,人投身于存有即投身于“之间”。海德格尔在《尼采》中做了一个比喻:如果我们把存在与存在者比喻为一条河的两岸,那个既不是存在者也不属于存在的东西能够作为河流在存在者与存在之间流动吗?(18)海德格尔:《尼采》下卷,第878页。或许《哲学论稿》可以看作是一种答案。“存有”作为“之间”乃是这河流,人必须投身于存有而成为“之间”才能进入此—在。不过,此—在投身于存有的这条“河流”没有“两岸”而只有一岸——存在者,所以存在对此在来说乃是“深渊”(Abgrund)。存有是“原始—基础”(Ur-grund),不过这个“原始—基础”相当于“无—基础”(Un-grund),所以是“深渊”(Abgrund)或“离—基深渊”(Ab-grund)。由此来看《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即是在存在与存在者“之间”,不过不是在两个东西之间,这个“之间”只有一边是“实在的”,另一边是深不可测的深渊。就此而论,《存在与时间》基于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而以此在之时间性结构作为思在的先验境域,《哲学论稿》则意在“消除”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而“此—在”的“之间”克服分离并不是由于它在存有与存在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而是由于它把存有与存在者同时转变入了它们的“同时性”(Gleichzeitigkeit)之中。(19)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第502-503、406、263页。
海德格尔是形而上学的批判者,但是他接过了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可以视之为试图解答存在问题的最后一次努力。存在之为形而上学乃是崇高的理想对象,而在海德格尔这里却是此在避之不及逃无可逃的深渊。人成为“此—在”即投身于“之间”,相当于跃入“离—基”深渊之中,去测度和经受住“离—基”深渊本身。(20)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第406页。
然而,有没有人愿意追随海德格尔,冒险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