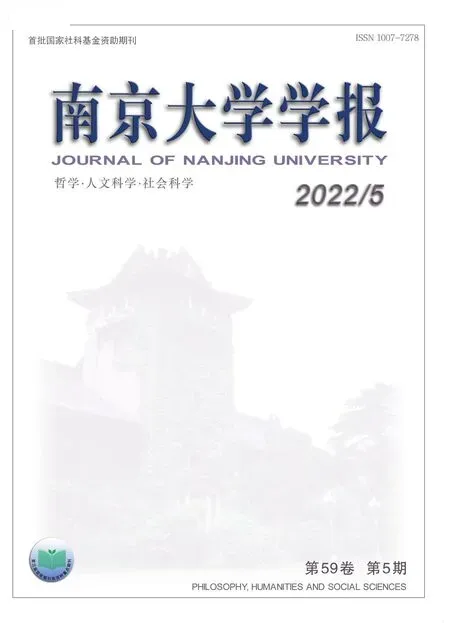清代城乡对抗中的水利之争与文化之争
——以无锡显应桥冲突为例
罗晓翔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南京 210023)
无锡老城西门外运河与梁溪交汇处有一河心小岛,明清时称“太保墩”,现为西水墩公园。连接公园与河对岸的石桥名“显应桥”,外观并不起眼,桥洞下绘制的“显应义举”壁画却讲述了一段清代地方传奇。壁画中的主人公为开原乡约正支凤。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无锡遇旱,为引水灌田,支凤率领西乡农民将显应桥下石坝扒开。城里士绅大为不满,因之上告,支凤被逮下狱。一年后道光帝即位,大赦天下,支凤才被释放。
与学界以往较多关注的乡村争水案不同,显应桥事件并非村民内部的水权纠纷,而是城乡间的对抗。雍正年间,城里士绅为改造风水、重振科举而筑坝桥下,由此引发的城乡矛盾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嘉庆二十四年的开坝事件只是一次集中爆发。由于冲突双方存在明显的身份落差,城乡水利纠纷之上又叠加了阶级对抗内涵。这不仅给乡民“以弱敌强”的行为增添了英雄色彩,也令“恃强凌弱”的城绅遭受道义谴责,一场舆论与道德战随之而起。
令人惊讶的是,文化战场上的主导权一直把握在乡民手中,城绅反而成为“失语”一方。显应桥冲突在晚清各类官私史料中难见记载,却依靠民间说唱文学——宝卷——广为流传。(1)《中国宝卷总目》中收录有29部以此为主题的宝卷,抄录时间从清道光至民国时期,地域分布十分广泛。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332-333页。宝卷故事不仅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更因其通俗性、大众性而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因内容敏感,直至民国时期,民间艺人在无锡城内说唱《显应桥》时仍常遭士绅驱逐殴打(2)《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苏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2年,第228页。,但这并不能改变城绅在舆论阵地上的劣势。随着时间推移,支凤这位乡村小人物非但未被历史遗忘,反而变得家喻户晓,甚至以“一介农氓,敌满城巨室”的传奇事迹成为无锡历史上“十二奇人”之一。(3)华重协:《梁溪十二奇人小传序》,张瑞初:《西神遗事》,南京图书馆藏2010年尤永基复印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苏省戏剧团于1954年将新编锡剧《显应桥》搬上舞台。“显应义举”故事就此定格,民间叙事最终形塑了地方记忆。
可以说,显应桥冲突呈现的不仅是城乡水利纠纷,更是城市与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心理层面的全面对抗。通过这一个案,笔者试揭示清代江南城乡关系中常被忽略的面向:从生存策略到价值取向,从空间分离到心理隔膜,从资源争夺到阶级对立,从权力比拼到舆论大战,乡村与城市愈行愈远,紧张感不断加剧。这与传统认识中以耕读文化、宗族纽带及双向空间流动维系的前近代“城乡一体”格局大相径庭。
当然,城乡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反映,清代江南的赋税压力、钱粮清查、科举传统、城乡流动、租佃矛盾以及官绅民关系,才是推动城乡格局变迁的决定因素。就此而言,显应桥冲突既有其偶然性与特殊性,也体现出历史之必然。这不仅启发我们重新思考明清江南地域社会“指导者”与“秩序原则”的传统话题(4)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中国史研究会‘地域社会—地域社会与指导者’”主题报告》,《“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60页。,亦有助于从长时段理解江南社会的近代转型模式。
一、开衅:改桥为坝
嘉庆二十四年的显应桥冲突,缘于西乡民众要求开坝引水,抗旱救苗。显应桥下为何有坝?士绅又为何禁止乡民开坝?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追溯之前,有必要对显应桥的地理位置及无锡水文环境略做说明。
明清时期,无锡县境内水道以运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运河以东之水多辗转入江阴、常熟二县,运河以西各支则多归太湖。在西部水网中,梁溪又是联系太湖、运河与内河的主脉,发挥着调节蓄泄的作用。如内河水浅位低,太湖水可经梁溪、运河而下,汇入西北乡芙蓉圩等处灌溉民田。当内河水涨位高之时,则可由运河、梁溪泄往太湖。
梁溪与运河交汇于无锡县城西门外的环城河,太保墩即当二水之冲。该墩在明代曾为无锡乡宦秦金所有。(5)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一)》卷2,《无锡文库》第1辑第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25页。秦金,字国声,号凤山,明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有“两京五部尚书,九转三朝太保”之称,谥“端敏”。其城内西水关旁宅院称“尚书第”,惠山别墅“凤谷行窝”即寄畅园前身。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秦金进太子太保,墩名由此而来。太保墩与县城一水相隔,墩东之水可经西水关进入无锡城内之束带河,显应桥则位于墩西。该桥始建时间不可考。万历二年(1574年)《无锡县志》中未载此桥,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因传显应桥有碍县令功名将其拆毁(6)华希闵:《请改显应桥为梁溪堤呈》,《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754页。,建桥当在这近百年间。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重修显应桥,筑坝则发生在雍正八年至九年(1730—1731年)间。看似寻常的一件小事,却开启了城乡间的长期争端。
改桥为坝由无锡士绅发起倡议,其中一位关键人物为华希闵。华希闵,字豫原,号剑光,无锡望族华氏后裔。先世华麟祥在明代由生员入监,后经商发迹,“以赀雄于乡,再传而中落,至曾祖而荡然矣”。鼎革后,华希闵祖父以研田为生,祖母辛勤持家,华家“始有负郭百余亩”,并由南塘徙居无锡城内图南里。华希闵之父华汝珍生于城中,幼攻举业,“三试棘闱不中,遂不复试,以事亲治生为重”。尽管身份不高,但华汝珍积极投身地方事务,凡邑中善泽会、育婴会、棉衣会皆竭力襄赞,又捐赀瘗漏泽园遗骸,并参与康熙十八、十九年(1679、1680年)煮赈,乡人“感激不衰”。(7)华希闵:《先考邑庠生履祺府君述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7册,第734-735页。
到了华希闵这一代,华家在举业上依然留有缺憾。华希闵为诸生30余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中举时已年近五十,授安徽泾县训导。但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华氏在无锡的知名度不断提高,“邑中有大利害,非先生莫决,大吏咸致书通问”(8)顾栋高:《皇清钦赐知县升衔前诏征博学鸿儒泾县学博庚子科举人剑光华公墓志铭》,《无锡文库》第3辑第5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494页。。乾隆朝无锡、金匮两部县志均由华希闵主撰。
据华希闵称,改桥为坝之事“都人士有同心,特莫肯先发”。雍正八年,无锡县令江日容迁泰州知州,“濒行,绅士饮饯河干,谂之席上,退复具词以告,始得允行”(9)华希闵:《新筑西郊堤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7册,第693页。。所谓“具词以告”,乃指华希闵向县令正式提交《请改显应桥为梁溪堤呈》。
在公呈中,华氏首先驳斥了建桥有碍邑令功名之说,随后指出该桥关系地方科名甚重,“毁桥而脱会榜四科,桥建而人文复盛”(10)华希闵:《请改显应桥为梁溪堤呈》,《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7册,第754页。。但从风水上说,西门外水道中黄埠墩为天关,太保墩为地轴(11)时人认为“黄埠墩为天关,太保墩为地轴”。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一)》卷2,《无锡文库》第1辑第5册,第224-225页。,河水流经太保墩时“稍嫌径直,绝少纡回,地轴不关,形家所忌”。为此邑绅提出:“若将显应桥堵塞,俾水道从太保墩左转入湖。估费不过数金,回流不越数武,而水势湾环,风气完聚,不特人才挺出,抑且物产丰盈,士庆亨嘉,民歌富有,为益不小。”(12)华希闵:《请改显应桥为梁溪堤呈》,《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7册,第754页。县令江日容在离任前批准了这一请求。雍正九年春“即桥垒石为堤,实瓦砾于其左右”。华希闵欣然感慨道:“如形家之说果信,吾知邑之人文加盛于前,必有立德立功、继往哲、泽生民,以为桑梓光者。”(13)华希闵:《新筑西郊堤记》,《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7册,第693页。
明清之际,江南为科举文化重地,地方望族多由科举起家,无锡亦不例外。明代无锡即有“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的科场佳话。清顺治四年(1647年)、六年(1649年)两科会试,中试均高达11人。顺治九年(1652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间更创造了“六科四鼎甲”的辉煌。(14)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38页。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关心科名原为士绅阶层之本能,但笔者认为,雍正年间无锡士绅竭力推动显应桥“风水改造”,还应置于钱粮清查这一时代背景下理解。
江南素称重赋之区,钱粮积欠亦多。为缓解地方官征税压力,雍正初于苏、松、常三府大规模升州析县,无锡亦析置金匮,二县同城而治。但“分县没有解决钱粮拖欠的老问题”(15)范金民:《政繁赋重,划界分疆:清代雍正年间江苏升州析县之考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积欠清查亦同时展开。雍正三年至六年(1725—1728年)为地方自查阶段,七年至九年(1729—1731年)为钦差与地方要员专查阶段。(16)范金民:《清代雍正时期江苏赋税钱粮积欠之清查》,《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在此期间,地方官吏严追酷比,江南士族备受冲击。
华希闵曾在《自述略》中回忆道,雍正七年清查民荒,无锡县令江日容示谕里民:“数十年来沾恩蠲减者,皆冒滥,非真荒,吐出所蠲者免其罪,迟则详宪究惩,罪不赦。”地方人士闻之惊骇,“自首者数十百人,输银者三日内数至一千九百余两”。华希闵最初尚强作镇定,但眼见风声日紧、输银者日众,其心理防线也日渐崩溃。关键时刻,江苏巡抚尹继善下檄,命各属县不得以此滋事。锡金二邑“欢声如雷”,华家亦“尤如震风凌雨之得大厦”(17)华希闵:《自述略》,《无锡文库》第3辑第54册,第505页。。
钱粮清查对无锡人文环境与城乡关系的影响很快显现出来。邑人黄卬即称雍正时“迫于追呼”,城居地主纷纷出售田产,田价大贱。(18)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无锡文库》第2辑第1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0页。又言雍正间“邑旧族皆破坏,子弟多无力读书。而为商贾及力农有骤富者,又不知读书。此人文所以日衰也”(19)黄卬:《锡金识小录》卷4,《无锡文库》第2辑第19册,第54页。。在此背景下,地方士绅对于重振人文,确有现实紧迫感。(20)事实上,雍正八年会试,锡金二邑中试七人,战绩颇佳。六年后的乾隆丙辰科不仅再创“一榜九进士”的辉煌,秦蕙田还成为探花。筑坝前后,无锡确实迎来一个科举高潮。高鑅泉辑:《锡金科第考》,《无锡文库》第2辑第3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页。
然而,对乡民而言,风水改造与科举功名虚无缥缈,农田水利才关乎生存需求,这在民间水文化上也有所体现。无锡有两座水仙庙,其中之一位于太保墩,原为“湖溪渔人祀水神”之所。(21)窦镇:《锡金续识小录》卷2,《无锡文库》第2辑第19册,第230页。“湖溪渔人”主要指无锡县西南濒临太湖的富安、开原、扬名、开化、新安五乡渔民。清代以前,水仙的身份并不明确。鼎革后,里人以故令刘五纬为水仙,“于是撤其庙而新之,名以察院,冠服悉如明制,一时巫祝奔走若狂,不可复禁”(22)康熙《无锡县志》卷8,《无锡文库》第1辑第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114页。。
刘五纬为四川万县人,明天启元年(1621年)任无锡县令。(23)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一)》卷18,《无锡文库》第1辑第5册,第466页。其被奉为水仙,当缘于天启二年(1622年)芙蓉圩区的排涝工程。芙蓉圩位于无锡县西北,面积极大、地势极低,“若水逾二尺则各岸平沉,汪洋一片矣”(24)黄卬:《锡金识小录》卷2,《无锡文库》第2辑第19册,第27-28页。。天启二年大水,无锡西北“天授、青城、万安三乡圩田千顷,遇涝皆成巨浸”,知县刘五纬“躬率圩民并工挑筑,工成仍为沃壤”(25)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一)》卷18,《无锡文库》第1辑第5册,第466页。。刘五纬于清初被奉为水仙,反映出水利对乡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性。
显应桥下筑坝后,经梁溪上下之水皆绕墩东而行,由西水关入城之水量更为充沛。但对西乡民众而言,墩西水道阻塞,太湖来水多被挡在坝南;而坝北水流趋缓,不仅汇入支河水量减少,且河道更易淤垫,一遇旱魃受害不小。正如雍正年间一首竹枝词中所写:“西水关西显应桥,流通水旱救田苗。只因风水关科第,水阻桥门浪不漂。”(26)杜汉阶:《梁溪竹枝词》,《无锡文库》第2辑第30册,第627页。可以说,在雍正年间显应桥的“风水改造”中,官绅忽视了西乡民众的水利需求。作为弱势群体,后者无力反抗,但其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在19世纪初爆发。
二、争端:石坝废存
19世纪初,江南地区水旱灾害频发。自然灾害不仅引发社会动荡,也令显应桥石坝存废问题变得更为敏感。“显应义举”的领头人支凤正是在此时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乡民利益的代言人。
支凤,字浩明,庶民地主出身,“世居锡邑开原乡,半耕半读,安居乐业”(27)王福成:《浩明公传》,《锡山支氏宗谱》卷2,上海图书馆藏1927年木活字本。。支家的发迹史极其艰辛,据支凤自述,其高高祖至曾祖“代传贫乏”“佣工苦度”。祖父惟良公为曾祖母遗腹所生,成年后“耕田车戽,一日两粥一饭而不继,忍饥忍冻,克俭克勤”。惟良公30岁后才娶妻,育有二子,长即支凤父瑞祥公。如前所述,雍正时江苏汇追积欠,大户纷纷卖田,支凤祖父由佃农变为自耕农恰在此时。
支凤13岁失怙,依祖父过活。祖父临终前训诫支凤道:“吾志得有今日者,勤忍而已,吾恨未读书诗,往往绝劝之田,书载听赎,因而受累者有之。嗣后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28)《支浩明分家书》,无锡博物院藏。这大约是支凤决意捐监,使家族走上“半耕半读”之路的重要原因。支凤执掌门户后,家业愈发兴旺。因有监生身份,支凤还被推为约正,即官方认可的“老人”。正如宝卷故事中所称,“倘有乡民不公不法,即委支浩明笞治”(29)《显应桥卷》,光绪三年抄本,郑州大学图书馆藏,第7页a-b。。作为沟通官民的中介,支凤深度参与到浚河、赈灾等乡村事务中。
在嘉庆二十四年“显应义举”之前,支凤曾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九年(1814年)与城绅发生过两次冲突,起因皆为抗旱。多年后,支凤在分家书中详细追忆了第一次与无锡士绅发生冲突的情形:
嘉庆十二年旱,倡开王泗浜及钱桥河至双河,为西乡咽喉水道,吾竭力捐浚。偏荒富安一隅,吾即衔捐求县暨府,蒙蒋宪批:该约正支浩明首先捐资,足见情切桑梓,谊敦任恤。仰无锡县会同金匮县速查地方情形,务劝绅富量力捐资,挨查极、次贫民,按口给钱,作速筹议,通禀核夺,等因。再蒙府宪通饬八邑一体办理。蒙县宪韩令(30)即无锡县令韩履宠,嘉庆十二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在任。帖邀绅士至明伦堂议赈,绅云:五六不成灾,毋听匪议,或者要赈,止能买米煮赈。吾云:若议煮赈,老弱残废不能赴厂就食,仍多饿死,触忤众绅,拳掌斥逐。再蒙县谕,一面听绅煮赈,一面举董设法劝捐,按口给钱寝事。(31)《支浩明分家书》,无锡博物院藏。
可见嘉庆十二年的冲突尚未涉及显应桥开坝问题,城乡之间的分歧主要在灾情认定与赈灾方式上。支凤认为旱情严重,应“按口给钱”;士绅却称“五六不成灾”,至多“买米煮赈”,双方间的认知差异难以调和。最终在府县官员主持下,城乡间勉强进行了合作。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嘉庆十九年。这一年的江南大旱为多年罕见之“奇灾”。包世臣曾言:“国家休养生息百七十余年,东南之民老死不见兵革……至于大旱,四十余年之中,惟乾隆五十年、嘉庆十九年两见而已。”(32)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9正集9,《续修四库全书》第150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地方官为动员绅富参与私赈,大量聘任绅董,“其名遂见于官文书及上诏旨,且畴其劳,赏爵级有差”(33)梅曾亮:《柏枧山房全集》文集卷12,《续修四库全书》第15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5页。。在灾情与奖励的双重刺激下,各地赈灾皆较为踊跃。锡金二县亦于城中设立赈局,由绅士经理。无锡县所发之《邀图董赴局发捐簿票》中写道:“仰缙绅、吏即赍本县名帖,飞赴各乡,按帖投送,邀集各董事赴局议办赈务并发捐簿,毋得刻延。”(34)韩履宠:《锡山荒政存稿》,《无锡文库》第2辑第5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489页。可见士绅竟然与胥吏一同下乡投帖,其辛苦可知。
在官绅看来,此次赈灾可谓功德圆满。金匮县令齐彦槐在《观赈》诗中写道:“官赈才终私赈继,东家出米西家粟。赈钱中间又赈粥,行不乱群道路肃。”(35)齐彦槐:《观赈》,道光《无锡金匮续志》,道光二十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第24页a。凌鸣喈记无锡“邑绅富民力捐,得银十一万九千余两,较乾隆五十年大旱蠲赈之数且十倍之”(36)凌鸣喈:《序》,韩履宠:《锡山荒政存稿》,《无锡文库》第2辑第50册,第485页。。钱泳称“无锡计捐十三万余缗,金匮计捐十二万四千余缗”(37)钱泳:《履园丛话》,第115页。。地方志中更言“是岁捐数,锡金甲江左”(38)道光《无锡金匮续志》,第25页a。。
然而对乡民而言,赈济只能解一时之困,戽水救苗才是长策。为此约正支凤又“捐求仍将王泗河及钱桥至双河疏浚”,却遭钱桥生监与士绅阻挠。眼见开原、富安两乡农民“日夜勤戽,河水渐涸”,支凤又向知县呈请,准将太保墩之显应桥坝开通,“引湖水直达运河,分灌支港,戽救田畴”(39)《支浩明分家书》,无锡博物院藏。。知县韩履宠准其所请。于是显应桥石坝在筑成80余年之后,第一次为引水灌田而扒开。而嘉庆十九年恰逢甲戌会试之年,已经出钱出力、辛苦办赈的城绅对此不满,亦在意料之中。
旱情缓解后,石坝的善后问题提上议程。西乡民众希望自此废除石坝,并趁天旱水浅之际深浚河道。事实上,因此次旱灾导致运河淤浅,地方大员确有“导湖济运”之议,“又蒙勘明显应桥及西吊桥为通湖尾闾,一并入册估挑,引湖水入运,以利漕艘”。然而无锡县令韩履宠却不愿兴此大工,遂以“车戽将已停止,运河之水势必充盈,回空重运不无搁浅”为辞,详请免挑。(40)《支浩明分家书》,无锡博物院藏。
见此情形,支凤等复请改坝为闸,以利启闭。经江苏巡抚张师诚批复,勘准设闸。正在动工之时,锡金两邑绅士却以“显应桥开通有关城河水利”为由呈请堵塞,“复以改毁堤防等事上控”。压力之下,张师诚接受了士绅恢复石坝的请求,但向乡民许诺遇旱开通。他在批文中极力调和道:“显应桥改设闸座,固于农民田畴有益,而绅士以城河干涸为虑,既可随时开通,不若仍循其旧。嗣后逢旱许农民赴县呈请开通,以资车戽,俟河水充盈,即行堵塞。”(41)《显应桥奉宪遇旱开通碑》,《锡山支氏宗谱》卷2,第11页a、12页a。
见巡抚出尔反尔,乡民们在无奈之下,依然做了最后努力。支凤等再向江苏布政使杨頀递呈,称遇旱呈请开坝必要辗转批查,耽误时日,而“三时一过禾苗苦槁”(42)“三时”即插秧时间。江南各地对于“三时”的理解略有不同,无锡风俗以夏至后一日至六日为头时,又后五日为二时,又后三日为三时。钱基博:《方志汇编》,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放水亦无益。为此请求增加条款:“一遇旱涝,官为虔祷时即刷摹,呈请开通桥门济灌”,并勒石示谕。不久杨頀迁任、张师诚革职,继任巡抚胡克家、布政使陈桂生接手这桩公案。胡克家认可了乡民的请求,将呈请开坝时间写入规约。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六月,无锡县立“显应桥奉宪遇旱开通碑”,正式颁布显应桥坝开塞规则:“凡交芒种以后雨泽衍期,地方官设坛期请,准即赴县具呈开通。俟续得透雨,河水足资车戽,仍照旧闭塞。各乡农民不得擅自私开,如应开时,绅士人等亦不得藉词阻遏,各宜凛遵毋违。”(43)《显应桥奉宪遇旱开通碑》,《锡山支氏宗谱》卷2,第12页a-b、第12页a-13页b。
至此,因嘉庆十九年显应桥开坝而导致的城乡纠纷暂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士绅要求恢复石坝的理由是“有关城河水利”“以城河干涸为虑”,与雍正八年筑坝时的说法截然不同。而事实上开坝后的嘉庆十九、二十二年会试,锡金二邑连脱两榜,百年罕见。(44)高鑅泉辑:《锡金科第考》卷2,《无锡文库》第2辑第30册,第128-129页。士绅们却为何转变话题,不再强调风水与科举了呢?
因缺少史料,无锡士绅的真实想法不得而知。但从道光年间薛湘对“显应石桥宜堵”的议论中,或可发现一些线索:
湖水自西定桥直趋吊桥,波流甚属惴悍,覆舟陨命者每岁叠见。所以昔人于太保墩截断显应桥,令之分入城中。一以通城中水道,一以杀全湖水势,真两便之利也。嘉庆十九、廿四两年雨泽稀少,赦犯支浩明纠众妄开,断绝城中水道,大为城池之患。脱有不测,火灾及之,岂不可虞?而绅士之与争者,乡人辄以科名形势薄之。夫科名小数也,城池大患也,且堪舆家言何足凭信?惟城中炊汲大可虑耳。(45)薛湘:《锡金水利条议》,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二)》卷38,《无锡文库》第1辑第5册,第330页。
薛湘称昔人截断显应桥仅为“通城中水道”“杀全湖水势”,显然是不实之词;而说显应桥开通将“断绝城中水道”亦属夸张。薛湘即薛福成父,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与李鸿章同榜;此后由西漳寺头迁入城内,开启了学前街薛家的发迹史。对薛家而言,科名绝非“小数”。这段话中唯一“真实”的,或许就是“绅士之与争者,乡人辄以科名形势薄之”,可见民间舆论确实给士绅造成了压力。在嘉庆年间关于石坝存废的城乡论战中,无锡士绅们避谈科举风水,当与此有关。
概言之,与雍正初年相比,19世纪初的绅民关系与城乡关系已悄然发生转变。尽管士绅阶层仍具有相当的支配力,但也开始顾忌民间舆论。他们要保“科名”,却不再敢以“科名”为筑坝的正当理由。面对城乡矛盾不断升级,地方官也开始走调和路线:既满足城绅堵塞桥洞的要求,又接受乡民遇旱请开的提议;既不容乡民擅自私开,又禁止士绅借词阻遏。然而无原则的折衷无法令任何一方满意。何谓“雨泽衍期”?何谓“河水足资车戽”?何谓“应开之时”?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城乡间无法达成一致。难以调和的城乡矛盾最终导致嘉庆二十四年的暴力冲突。
三、高潮:“显应义举”
与嘉庆十九年相比,二十四年的灾情并不算严重。在毗邻无锡西境的阳湖县,地方人士称嘉庆十二年、十九年为“大旱”,二十一年(1816年)、二十三年(1818年)、二十四年“连年小旱”(46)庄宝煊:《阳湖高邮今年水灾说》,《警谦书屋遗稿·文存》,常州图书馆藏,1941年,第20页a-b。。但无锡人窦镇记载,嘉庆二十四年“麦收歉,夏秋大旱,山禾尽槁”(47)窦镇:《锡金续识小录》,《无锡文库》第2辑第19册,第224页。,这样的损失对农家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
关于开显应桥坝之事,支凤本人在分家书中追忆道:“二十四年又旱,公尔忘私,奉碑开桥。岂料巨绅挟恨,栽风种电,耸朦前抚宪陈(48)即江苏巡抚陈桂生。听情,令拿搜罗招告。”江苏布政使杨懋恬、按察使麟祥亲自过问。入狱一年间,支凤经历了多次刑讯,“叩胫骨碎,血泪染衣”。次年嘉庆帝驾崩,道光帝即位后大赦天下,支凤才被释放。(49)《支浩明分家书》,无锡博物院藏。
支凤所言“奉碑开桥”中的“碑”,当指嘉庆二十二年所立“显应桥奉宪遇旱开通碑”。如前所述,碑文中规定遇旱开通前乡民须“赴县具呈”,不得私开。但从支凤称“奉碑开桥”而非“奉宪开桥”来看,此次行动确实属于“私开”,或者曾经“具呈”但未获批准。至于被逮经过,支凤仅称“巨绅挟恨,栽风种电”,亦未详言。因史料所限,对于开坝的具体过程与细节实难探究。
开坝事件在无锡引起巨大轰动。自道光朝开始,钱桥监生支凤为引水救荒而开坝入狱的事迹便开始通过香诰与宝卷流传。香诰为拜香时使用的集体读唱文本,广泛流行于苏常一带。在无锡,香诰甚至成为一种童蒙教材。“孩子一到六七岁,便要练习抄香诰。进学堂的白天上学、做功课,晚上抄香诰。穷人家孩子上不起学,抄香诰便成为识字、习字的一种途径。”(50)朱海容、钱舜娟:《江苏无锡拜香会活动》,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第五集)——稻作文化与民间信仰调查》,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80、182页。宝卷则是职业说唱者使用的脚本。民间做会时多穿插宝卷演唱,称为宣卷,“是融合了民间信仰、教化、娱乐为一体的民俗文化活动”(51)车锡伦:《什么是宝卷——中国宝卷的历史发展和在“非遗”中的定位》,《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
与香诰相比,显应桥宝卷存世较多,抄录时间从清道光朝直至民国,情节内容互有差异,反映出不同说唱者对脚本的再加工。显应桥故事虽本于真人真事,但宝卷并非纪实文学,文本内容更多反映着创作者的主观认知及其对听众心理的迎合。因此,宝卷的价值并不在于呈现“客观的真实”,而在于投射“主观的真实”。(52)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曾指出:“经历和神话具有不容历史学家忽视的重要性和情感引力——我们也许该称之为一种主观的真实。”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士绅为何阻止乡民开坝?支凤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国法与神佛又是如何惩恶扬善的?宝卷中一一给出了答案。对创作者而言,情节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引发共情。就此而言,宝卷不仅是宗教说唱文本,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更是对地方记忆的制造与重构。“草根”阶层的文化策略与动员能力在此得到充分展现。
宝卷故事中,城乡争水首先被上升到“义利之辨”,乡民因之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支凤放水救苗,原是上保国课、下救万民的义举,而士绅们却只关心功名利禄,不仁不义。正所谓“显应桥下来筑断,只为无锡大乡绅。要按城中风水好,要出八轿大乡绅”(53)《显应桥卷》,第4页。。而府县官害怕得罪乡绅,不敢为民做主。如故事中的无锡知县韩履宠暗忖:“献映(引者注:即显应)桥古时水通北栅而来,只为无锡乡绅要做风水,故此将桥作坝。倘我出示开桥,我这个小小官儿不能留牢。”(54)《开桥宝卷》,道光二十五年抄本,郑州大学图书馆藏,第3-4页。常州知府卞斌也对支凤道:“你为天时大荒,要开显应桥,可以水通三路,可好救十七保半田禾也,是一桩公事。无奈此桥当初嵇璜老大人做好风水,为此作断,如今不能开通。”(55)《乡民卷》,1924年抄本,郑州大学图书馆藏,第10页。然而支凤不屈不挠,最终将开桥状子投到苏州城中的巡抚衙门。苏抚陈桂生为其义举感动,决定“准了他的状子,出了告示,准期七月二十四日开通桥,救熟稻苗。也保君皇国库,也救百姓丰熟,岂不两全其美矣”(56)《显应桥卷》,第12页。。
然而陈桂生准状纯属虚构,否则支凤自述中不会不提。官员的内心独白与对话也明显出于演义。从这些情节设计中,可以看到弱势群体的“特权想象”,以及他们试图描绘的“官绅民关系”图式:民众奉公守法,大宪也明辨是非,惟有士绅蠹国殃民、自私卑劣,是导致地方社会失序的根源。
宝卷故事中,支凤与无锡士绅的决裂有两种版本。在一种版本中,支凤从巡抚衙门拿到开桥告示后赶回无锡,乡民里老个个欢喜,但支凤认为开桥之事仍须与众绅商议:
支凤开口说事情,要帖传单四处闻。
众今要办红全帖,差人去请各乡绅。
(第一个请)无锡县里俞大人,(第二个)新庙前格许布政。
(第三个)河上秦家鸦片鬼,(第四个)邹四哭鬼半死人。
(五个)嵇五少爷阴司鬼,(六个)少宰地里姓孙人。
父子两人王翰林,大刑背后姓侯人。
南门脚下郑小大,降桥脚下姓顾人。
然而“满城乡绅多发贴,并无一个到来临”。一怒之下,支凤便在城中贴了告示,拂袖而去。至七月二十四日当天,支凤等带领乡民来至西门外显应桥下,开坝放水。(57)《乡民卷》,第12a-b页。
在第二种版本中,众绅受邀后来到县衙,支凤道:“各位大人在上,监生支浩明蒙两县父台、本府公祖卞大人、江苏抚台陈大人出告示,准期七月念四日开通显应桥,水通大塘河,以救养民稻苗成熟,回此与大人商议。”但乡绅邹炳泰提出:“再定三日开了罢,准期七月念七日。”支凤争辩道:“田中稻苗苦焦,再歇三日岂非旱死无数,开桥无用了。”一旁薛银大闻言生怒,“支凤连叫两三声。乡绅说话不肯听,一定念四开桥门。念七良时并吉日,不坏风水半毫分”。支凤也“掇起心头火一盆,拜别乡绅回家转”。至七月二十四日,支凤等不仅率领乡民砸开石坝,还将士绅们请来的拳师打得落荒而逃。(58)《显应桥卷》,第12-13页。
陈桂生准状既为虚构,县衙商议也不可能发生,然而宝卷中提到的俞、许、秦、邹、嵇、孙、王、侯、郑、顾等姓却是人尽皆知的无锡城中望族。其中秦氏在明代即出过“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秦金这样的大乡宦。“河上秦家”在清代依旧簪缨相望,师古河秦氏宗祠门首的“辰未联科双鼎甲,高元接武十词林”对联、祠内“一代词宗”匾额,都在讲述家族的科举成就。(59)秦铭光:《锡山风土竹枝词》,浦学坤、赵永良主编:《无锡掌故大观(附录)》,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725页。显应桥冲突发生时,秦氏族长为秦瀛,乃嘉庆《无锡金匮县志》总纂。
嵇氏的辉煌时代则由嵇曾筠、嵇璜父子缔造。嵇曾筠为康熙四十五年(1705年)进士,三朝为官,以治河著称;雍正九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1733年)拜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元年(1736年)加太子太傅,卒赠少保,谥“文敏”。三子嵇璜于雍正八年登进士,年仅二十。嵇璜为官近70年,亦善治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上书房总师傅;卒赠太子太师,谥“文恭”,“帝命皇八子奠酒,遣官护丧归里,海内荣之”(60)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14,《续修四库全书》第5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16页。。嵇氏宗祠在西水关内进贤桥之东,有雍正帝与乾隆帝御赐之“忠节留芳”与“人伦坊表”额。(61)嵇雨霖:《嵇氏宗谱》卷1,光绪三十三年修,上海图书馆藏,第1b、2a、7b页。
除秦氏、嵇氏外,宝卷故事中还提到嘉庆六年(1801年)状元顾皋、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俞肯堂,其余孙、王、侯、邹等家或出过状元,或曾有高官,都是世人眼中的“八轿大乡绅”。然而这些人物真的参与过开桥冲突吗?不仅史料中无法查证,宝卷故事里的说法也漏洞百出。宝卷作者无视事实的“自由创作”,充分反映在邹炳泰与薛银大两个关键人物身上。
宝卷故事中定要推迟开坝的邹炳泰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历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兵、工、吏部尚书。嘉庆十八年(1813年)邪教林清滋事,邹炳泰以失察降职,致仕回籍。(62)《清史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76-2477页。邹炳泰的身份确实称得上“巨绅”,但他居乡时间不长,也非把持地方之辈。方志中赞其“力厉清节,人莫敢干以私,囊橐萧然,澹若苦寒”(63)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二)》卷20,《无锡文库》第1辑第5册,第11页。。宝卷故事中关于邹炳泰的信息多属不实。如称薛银大为邹炳泰女婿,其实邹炳泰只有一女,适同里嵇文昕。又指邹炳泰为苏抚陈桂生座师,然而陈桂生乃优贡出身,并未参加过乡会试。另有版本说邹炳泰曾做过两江总督,更属无稽。在所有宝卷中,邹炳泰都在支凤出狱后畏罪自尽。而事实上,支凤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底被释时,邹炳泰病逝已近一年。(64)王引之:《协办大学士邹公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第14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00页。
薛银大这一人物,在不同宝卷版本中又写作“薛闰大”“薛壬大”,是构陷、迫害支凤的罪魁祸首。该人物的原型更为神秘。民国时期,无锡地方文人依然称“反对开坝最力的,为薛闰大,薛为南乡人,武进士,曾任知府,迁居城中(有疑为既系学前薛者,实非)”(65)张瑞初:《西神遗事》,南京图书馆藏2010年尤永基复印本,第145页。。然而有清一代,无锡武进士只得七人,其中并无薛姓。考虑方言发音,薛银大或为薛凝度。但薛凝度并非武进士,而是嘉庆六年进士(66)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二)》卷20,《无锡文库》第1辑第5册,第13-14页。,十九至二十五年间一直在漳州府任职,不可能介入开坝冲突。(67)《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福建》,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556页。至于怀疑这一人物出自“学前薛”,即薛湘、薛福成家族,亦无根据。
由此可见,开桥事件中的冲突双方在事后既未各自剖白,也未相互沟通,真相早已成谜。于是在敌对情绪与想象的推动下,城乡矛盾不断激化。对宝卷创作者与听众而言,立场取代了真相,“城里巨绅”的负面形象逐渐定格,他们到底做过什么不再重要。(68)直至近年才有地方文史专家指出,邹炳泰“身后被牵入显应桥风波,备受污蔑诬指。其实他与显应桥是丝毫无关的,必须为他恢复名誉”。无锡市滨湖区政协学习文史和社会法制委员会编:《滨湖诗存》,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6年,第275页。
宝卷故事中最为巧妙的写作策略,是七月二十四日开坝这一情节设计:苏抚陈桂生准期七月二十四日开坝,无锡乡绅却说推迟三天“不坏风水”,支凤拒不妥协,双方因此决裂。显应义举真的发生在七月二十四日吗?这个日子究竟有何寓意?这还须从宝卷的文本属性中寻找答案。
宝卷的创作与民间信仰活动相关,演出也多在赛会期间。在无锡,七月二十五日为张巡诞日,例于惠山张中丞庙举办大型赛会。张巡信仰在无锡历史悠久,明代载入祀典后更受到广泛崇奉。(69)王健:《神灵入祀与地方社会:明代无锡张巡信仰考略》,《史林》2013年第4期。钱基博在《无锡风俗志》中记载:“县人事睢阳尤虔……里中户悬灯,灯书‘收灾降福’字,竟一月,名曰‘大老爷灯’。”钱基博:《方志汇编》,傅宏星主编:《钱基博集》,第149页。张巡诞日是一年中最为重大的赛会之一,四乡民众往往提前一天赶至惠山,因此发展出二十四日晚的“坐夜”。巫仁恕曾指出,明清之际的庙会节庆“有类似欧洲狂欢节庆的颠覆及暴力的因子,甚至在庙会节庆中还酝酿了群众集体抗拒官方权威的作用”(70)巫仁恕:《节庆、信仰与抗争——明清城隍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行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34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第195页。。七月二十四日的惠山坐夜正是狂欢前的暖场,也与乡民开坝的亢奋场景契合。正如《显应桥卷》中所写:
且说乡下种田人,也有锄头掮一把,也有铁爬手中存。也有乌尖并铁鎝,还有石匠几十名。支凤王金前豆(头)走,镗锣敲得振田遥。十七图半乡下人无其数,尽到西门城外太保墩便了。开显应桥大胜会,人人个个尽知闻。一郡乡下人,大阿姆、二婶婶,东村西巷去搭人。真高衅(兴)人来搭子能几哼,田岸上排排一丈郡。面饼当点心,余裙袋里安不尽。挨挤到西门太保墩,开显应桥闹盈应。夜豆(头)到为(惠)山去,一夜看戏真快活。无穷拜神明把香焚,收灾降福大天尊。(71)《显应桥卷》,第14-15页。
“开显应桥大胜会”是否真的发生在七月二十四日,我们依然不得而知。但将这一时间融入开桥故事的用意并不难理解:在惠山坐夜的宣卷中,讲述一段发生在“历史今天”的乡民敌巨绅往事,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听众情绪。在对支凤的钦赞唏嘘、对乡绅的戏谑怒骂中,听众们获得了满足、强化了认同,并不断制造、延续着“乡民中心”的历史叙事,无以自辩的士绅精英反而成为失语一方。
事实上,从嘉庆二十四年开桥冲突的后续来看,城里士绅对地方事务的主导性也已大不如前。此前开坝、复坝,中间仅隔三年。而二十四年开坝后,桥洞却长期未塞。薛湘在《锡金水利条议》中提议“显应石桥宜堵”,已是近20年后之事。可见地方官员对桥洞当留当塞也犹豫不决。但最终石坝还是恢复了。
显应桥坝最后一次开通发生在20世纪初。1919年,江苏水利协会向省长呈请于各县农会下设立水利研究会,规划全县水利事务。研究会成员由市、乡及各法团推选,并公举主任一人。(72)《江苏各县水利研究会简章》,《江苏水利协会杂志》1921年第10期。无锡水利研究会第一届主任为胡雨人,天授乡堰桥村人。就任后,胡雨人起草《无锡全县救治旱潦之计划书》,其中议及拓宽西门桥、开通显应桥石坝并疏通水道,以救西北乡农民水旱之荒。(73)邹建章、胡雨人:《郡国利病:无锡全县救治旱潦之计划书》,《江苏水利协会杂志》1923年第15期。水利会中陈作霖、陶达三、邹家麟、钱孙卿等人对西门桥改造方案本无异议,后因薛南溟提出“此项水利与无锡市境内无关系”,10位城绅又一致反对。出身西北乡的胡雨人慨叹:“今何不幸,真见城绅全体一致,决陷乡人于死地而不恤也。”(74)胡雨人:《胡雨人先生对于水利之意见书》,《无锡年报》1925年第1期。最终双方妥协,西门桥拓宽工程照旧进行,但桥宽缩减1/3,显应桥坝同时打开。
胡雨人在无锡水利研究会中的境遇,与嘉道年间的钱桥监生支凤颇有几分相似,可见城乡冲突与权力格局的延续性。但时势变迁也是显而易见的。显应桥开通后,无锡第一区公所助理秦铭光作竹枝词赞道:“水利重开待百年,村儿攘臂识机先。朝山香卷今犹在,撤坝应教起九泉。”并在词后附注:“西门外显应桥,自昔惑于形家言,筑坝遏水。清嘉庆间,开原乡人支浩明以开坝成狱,几不测。先司寇小岘公实右之,狱得解。香会中有开显应香卷,宣颂其事。十二年癸亥,水利研究会议决开坝,桥遂通。浩明以小字阿凤著称。”(75)秦铭光:《锡山风土竹枝词》,浦学坤、赵永良主编:《无锡掌故大观(附录)》,第732-733页。
秦铭光所说的“先司寇小岘公”即秦瀛。在所有的宝卷故事中,秦家都是无锡城四大乡绅之一,虽不像邹炳泰、薛银大那样被骂作“坏官”,但终属抵制开坝的“巨绅”一派。秦瀛解救支凤之说实令人费解。但在“显应义举”发生百年之后,作为“八轿大乡绅”后代的秦铭光对支凤大加颂扬,并借机重塑秦家的历史形象,这也反映出城绅与时俱进的生存策略。
结 语
清代无锡县城西门外显应桥下石坝三筑三毁,见证了近200年的水利纠纷与社会变迁,也折射出江南城乡关系与地方秩序的重要特征。
自明中叶开始的士绅城居化趋势在清代得以延续,政治与文化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正如叶舟所指出的:“城居家族或者乡间家族中的城居房支不仅垄断了本分支的成功者,还垄断了整个区域的精英分子。”(76)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史林》2010年第3期。而像薛湘这样来自乡镇的科举成功者,也会在短时间内移居城市。与社会流动日益同步的城乡流动,不断分化着宗族组织与地方士绅群体,这绝非科举制废除后才出现的现象。至晚清,“城绅”一词已从“乡绅”概念中析出,频繁出现于各类文本中。
从任何一方面说,城市士绅都是特权阶层与社会精英,在政治经济层面具有“压倒性优势”(77)陈岭:《清末至民国江南水利转型与政治因应——以常熟白茆河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但这种“优势”的历时性波动亦值得关注。明中叶以降的历次赋役改革不断压缩着身份性地主利用特权避税的操作空间,清代的钱粮清查更对这一阶层造成沉重打击。如文中所述,雍正年间江南钱粮清查导致无锡城乡间大规模土地转手,地方人士明显觉察到“昔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今则乡多于城而散也”。至乾隆时又遇米价大涨,“一石价抵昔三石”,乡民“力田之勤则前此所未逮。遇旱涝,前多畏难中辍,今则竭力营救,且有因凶岁免租而起家者”(78)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无锡文库》第2辑第19册,第20、15页。。支凤祖父正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由佃户变为自耕农。到了支凤这一代,支家已有田地300亩。笔者认为,正是这一经济基础给了支凤对抗城绅的底气,这也反映出乡村在型塑城乡关系中的能动性。
因士绅城居化而导致的城乡心理隔膜则可追溯至明代中后期。滨岛敦俊指出:“对居住在城市,完全放弃农业经营的乡绅地主,期待要自然地怀有与庶民的共同感,对庶民的责任感,绝对是不可能的。”(79)滨岛敦俊:《明代中后期江南士大夫的乡居和城居——从“民望”到“乡绅”》,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江南与中外交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然而彼时乡民对官绅尚心存畏惧,他们的诉求往往要借助“经世济民型”的士大夫予以表达,这也奠定了后者作为地域社会“支配阶级”的道德基础。(80)森正夫:《民众叛乱、社会秩序与地域社会观点——兼论日本近四十年的明清史研究》,《“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第31-32页。这一情形在清中叶后逐渐改变,乡民不再“望官衙如在天上”,“混沌凿而机智开”(81)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无锡文库》第2辑第19册,第20页。在显应桥冲突中,乡民不仅直接向各级官员递呈,甚至能够掌控舆论。我们看不到“传统时代基于文化、社会身份之等差而形成的乡民对于士绅阶层的社群敬畏”(82)王先明:《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城市也并非“被尊敬的士大夫世界”(83)滨岛敦俊:《明代中后期江南士大夫的乡居和城居——从“民望”到“乡绅”》,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江南与中外交流》,第28页。。士绅对乡民的每一次胜利,都在瓦解其作为文化与道德权威的基础,建立在“乡绅支配”上的地方秩序格局也逐渐变形。
显应桥冲突本质上是城乡间的资源争夺,就此而言任何一方胜出都不能解决问题,只会激化矛盾。水利问题只能依靠水利治理解决,然而地方官却不愿积极投入水利事务。(84)罗晓翔、张景瑞:《治水之后:清代太仓水利实践中的利益纠纷与官方能动性》,《史林》2020年第5期。面对城乡冲突,他们选择了简单的调和政策,结果却导致矛盾升级。清代江南因士绅支配力下降、社会隔阂感加深以及官员能动性缺失而造成的城乡社会矛盾,一直延续至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