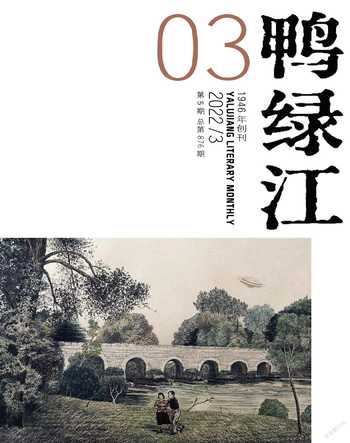神算(外一篇)
孙春平
其实,一走进墓园,靳勇就注意到那个人了。年近古稀,清瘦细高,可靳勇故意不搭话。烧过香,拜过墓,那人终于绷不住,凑上说:“老朽有一言,可为先生化险为夷。”
靳勇往前走:“天下高人,我见得海了去了。你还是快去挣你的活命钱吧。”
那人却紧傍身后,操着一口浓重的川地普通话:“先生印堂发暗,近日虽无大碍,却有一笔不小的钱财损失。老朽说得不准,先生拔步走人。老朽真若道破天机,先生且回故里,或半年,或一载,突然想起武侯墓前的干瘦老汉,您再专程赶来行赏,或八千,或一万,老朽绝无隆恩太重之愧。”
靳勇立了脚步,笑道:“你可就有点吹牛皮不上税的意思啦。你既有如此神通,何苦老天巴地跑到这儿来陪人说小话,太不值啦。”
没想老者正色道:“先生此言可是大谬。以老朽俗眼判断,先生眼下身家至少也是数以亿计,又为何不避劳顿,从东北奔到西南来?老朽敢站在武侯墓前说话,往高尚了说,是替诸葛先生广行善事,扬个美名;往平庸了说,不过图个自得其乐。好比河边垂钓者,常钓了鱼悉数送人的,他欲何求?一乐而已。再比如明朝有个皇上,丢下朝政不管,却非要躲在后宫做木匠活儿,他又为个啥子?天性使然,乐在刨锯,老天爷一时疏忽,错将他投了帝王家,没法子哟。”
老者这般高论,靳勇听来有趣,便在竹林藤椅上落座:“那你给我算一算,只当我在这儿歇脚了。”
老者问:“先生是东北人?”
靳勇笑:“就是聋子,也听得出我满口的苞米 子味儿。”
“先生到成都来,是为了一笔买卖。”
“眼下满世界跑的,除了被通缉的逃犯,还有几个不是为了挣钱做买卖的?你就说说我为啥要赔损钱财吧。”
“这个……却请先生说出一个字。”
“你到底是相面,还是拆字啊?”
“观面相,看手相,演周易,推八卦,拆字析梦,老朽不拘一格,最新说法,边缘科学。”
“好好好,算你有本事。那你就给我拆个成都的‘成’字。”
老者用扇柄在地上一笔一画写过,左看右看,才问:“可是加个提土,就是城市的‘城’?”
靳勇说:“我说的是成都的‘成’,没说城市的‘城’。”
老者说:“可此‘城’与彼‘成’仅存一‘土’之别。拆字无定法,全在一念之灵通。先生且耐心听我讲讲由此二字中透露出的信息。”
“随你讲,我听着就是。”
“先生眼下最大的心愿和计划可是想进城图发展?”
靳勇说:“庄稼人不愁吃穿之后,多是起房造楼,继而就是进城享福。老生常谈,不足新奇。”
“先生进城,最先图的却不是起屋造楼,而是一块地。”
靳勇心头不由一惊。此番来成都,他确是为了一块地。在东北老家时,他得一密报,说一直跟他暗中较劲的另一位农民企业家想扩大经营规模,拟把挨着厂子的一块长窄条子地买下扩建厂房。靳勇得了消息,便四处疏通,把那块地先买到了手。以他的算计,想求他让出这块地,对不起,用票子说话吧。让靳勇吃惊的是,眼下还属暗中谋划的算计怎么就让这个老头子说破了呢?可他掩饰着,问:“你怎么知道?”
“这‘城’字边有一‘土’,指的就是这块地。可先生本没想起屋造楼,完全是为地而地,想靠这块地另做打算呢。”
“啥打算?”
“这个……不便明言。商战斗智,老朽只恐误了先生大事。”
“那我这块地能够到手吗?”
“想不想留在手中,只在先生的一念之间。先生印堂发暗,便是坏在这块地上。”
“那老人家能不能再说说,一块地又跟印堂有什么关系呢?”傲慢的靳勇已在称老者为老人家了。
老者双目微合,沉吟有顷,才说:“这块地若是方正之地,会主先生大富大贵。比如‘封’字,二‘土’中便有一土为规则之地,可封侯也可拜相。遗憾的是,先生名下的这块地却应在提土上,‘城’字边的这个‘土’可是斜了身子的。如果老朽意念所得不错,你买的那块地歪歪扭扭,不呈正方形,可对?”
靳勇只觉脑门子冒起汗来,连连说:“老人家接着说。”
“先生可属大龙?窄促狭长之地,龙身只好随弯就弯,难得伸腰腾挪。若属小龙,倒还有几分扑腾。”
靳勇鸡啄米般点头:“那是那是,老人家务必帮我看看,是不是还有破解的办法?”
老者又作沉吟状:“已有些迟了。我死马且当活马医,送上一字,但愿助你逆天吧。”老者又在地上写下“抛”字,“何谓抛?须用九分力气,尽力掷出之谓也。九者,极数,所以先生要处理这块地,必须尽快、尽力,即使眼前有些亏损,也万万不要犹豫。”
靳勇站起身,深深一躬,又从怀里摸出一沓票子,数也不数,放到老者手上,就疾步而去了。
殊不知靳勇这边刚刚离开,老者正捻点票子,竹丛后面突然又闪出一个戴墨镜的汉子,笑道:“先生果然好手段,恭喜发财了。”
老者怔了一怔,却急背转了身子:“不是说好另找地方吗?”
汉子说:“不是不放心嘛。现在大功告成,我说话算数,这就兑现。”
老者抓钱在手,却急慌慌缩下身子,低声说:“快走,有话也不能在这儿说。别忘了眼下满世界都布天网,验脸书。刚才那位真要一时醒过神来,只要发现咱俩在一起,那就万事皆休,用你们东北人的话说,那就彻底完犊子啦!”
汉子发发呆,转身就跑,哪里还在意游人的惊诧,真的只恨爹娘没给他多生两条腿啦!
师惑
三十多年前,我在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同时兼着初三六班的班主任。学校好几位女老师休产假,我只好滥竽充数了。
充数的结果自然成绩平平。到了期末,其他班级都有奖状抱回,独剩我班墙壁上空白得干净。我脸面上过不去,便放出话,谁要是能为班级争得荣誉,我就让他当班干部。我的话里已有了悬赏招标的意思,但如风过耳,无人响应。
寒假前,学校给学生下达了积肥指标,每人五十斤。“积肥”这个词放在当下,许多年轻人已很难理解了,可当年,学校在郊区开出一片农场,组织学生学农种庄稼,把积肥任务落实到学生头上很正常。指标下达后的一天,有学生对我说:“老师,我能给咱班争取个积肥冠军。”
我好不容易才想起他叫邵杰。我问:“你准备怎样夺冠军?”
邵杰说:“我在班里啥也不是,说话谁听?”
这便是在伸手要官了。我想了一下,说:“那你就代理班长吧,正好班长寒假时去奶奶家过年。”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但初涉“班政”的邵杰放假后却和文艺委员紧密协作起来,他们组织同学在教室里排练对口词、小合唱,把本应冷清的假日教室搞得热热闹闹。那些日子,我心里嘀咕,怕不会是邵杰看文艺委员漂亮就有意和人家套近乎吧?
一练练到傍年根儿,邵杰才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全班同学都要穿戴上过年的衣裳,去部队联欢。
那天,同学们排列整齐,直向位于北郊的部队营房开去。我当然也得去,班主任嘛。演出之后,邵杰又提出帮解放军叔叔打扫卫生,目标是营房西北角的猪舍。首长见孩子们如此积极,且带来了工具,感动得不住嘴地夸奖。
猪舍足有几十间,大猪小猪百余头。到了这个份儿上,再愚钝的同学也猜知了八九,这叫曲线积肥呀!大家立刻鸟儿一般飞散而去。那一刻,我不时偷瞄邵杰,揣摩着他下一步的部署。
粪肥堆在了一起,挺大的一堆。邵杰跟首长请求:“叔叔,快过年了,这东西堆在这儿不好看,我们运走好不好?”
“这……好吧。”首长小有犹豫,还是答应了,又嘟哝说:“其实部队有园田,粪肥也不扔。”
邵杰装作没听到,立即安排同学去了营房北边的村子,借来了不少篮筐和扁担,还有两辆手推车。
我悄声问邵杰:“你怎么知道这儿有猪舍?”
邵杰一笑,“我舅家就在这村子。”
那一天,邵杰的巧出奇兵,不知激活了我的哪根神经,队伍快进校门时,我叫了停,说:“哪位同学家院子大,咱们先把粪肥送到他家存起来,大年初一再往学校送!”我又叮嘱学习委员,“你抓紧写篇文章,打在过革命化春节主题上,报社电台都给寄过去。”
经此一役,我们班一下变成了黑马,开学后,我们班不仅得了积肥奖,还有假期活动奖,我还被评为模范班主任。
开学后,那届学生就进入了中考冲刺阶段。发榜时,我特意关注到邵杰考上了师范专科学校,虽非重点高中,但也不错,师专毕业生可获国家分配,旱涝保收啦。
几年前的一天夜里,我接到一个电话,开口喊我老师,说要来拜访我。我问他是谁,他说:“我是邵杰,我当过代理班长,还带同学们去部队营房搞活动,想起了吧?”
远去的记忆蓦地在脑海中浮现。邵杰很快来了,身后跟着的秘书放下礼品盒就退去了。哦,三十余年未见,当年活蹦乱跳的小鹿已变成了驯练有素的高头骏马。落座,叙谈。我问:“你来得突然,不会是有什么事吧?”邵杰答:“那我就直奔主题。我现在的职务是市政府副秘书长,过两天有领导要出国考察,总要备些礼品,不可过于张扬,也不可显得小气,我就想到了老师的画作。我此程来,就是专程求画,也不白拿,三千元一幅,我要十幅,不难为恩师吧?”
三千,十幅就是三万!这些年,我虽痴迷于此,偶有出售,却多是两千一幅。
我故作迟疑,说:“只是时间太紧啊。”
邵杰说:“我一直在关注老师的创作,知道老师高仿某画家山水人物,已接近乱真。因为时间紧,这次您可只仿同一幅,先仿三幅就可。落款署名用印,您都仿就是。”
我脸上灼烧起来,原来这个他也知道。两年前,几位画友酒后小聚,我乘兴仿某人画了一幅,画友说仿得好,若能把落款用印也仿上,几可乱真了。唉,都是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呀。
我说:“这不好吧?”
邵杰说:“有什么不好。我听说,眼下国内,仿某人的不在少数,听说连他本人都在批量地生产画作。再说,此画带出国外,送画不过是一种礼仪,何谈鉴别真伪。”
那晚,邵杰打开礼品袋,盛情难却,我喝得有点多,加上夫人去了女儿家,没人监管,就更放得开,话也多起来,江河横肆,全无顾忌。邵杰也喝不少,说:“眼下从政,实际跟老师从教从艺一样,要说难,真难;要说容易,也简单。你只须记住四个字—— hū、hú、hǔ、hù,全了。”
我一时懵懂,追问:“哪四个字?你细讲讲。”
邵杰却猝然酒醒,摆手笑道:“玩笑,玩笑话,不说了。”
两天后,我如期交画接款,但邵杰说的那 hū、hú、hǔ、hù 四字,却好似魔界咒语,在我耳畔久久盘旋。我翻字典,敲电脑,终不知他指的是哪四字。便又想,我和邵杰相识几十年,到底谁是师,谁是生,真的整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