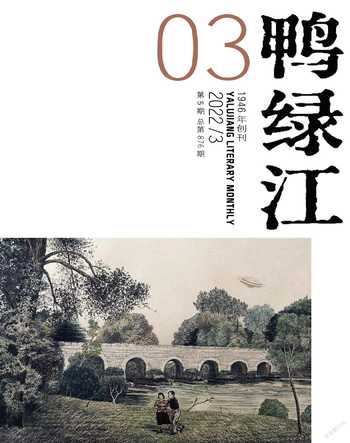午后沙尘暴
苒小雨
手机放在梳妆台上,周晓涵提前戴上蓝牙耳机,等着它响。
都已经收拾好了,只剩下口红还没确定。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琢磨用哪个色。平时不怎么化妆,但今天非同寻常,她认为必须隆重。
梳妆台下面左边的抽屉里有各色口红组成的方队,颇为壮观,多数是妈妈给她的。妈妈的口红换得频繁,每次都要给周晓涵带几支,不过都被她闲置了。
“天气预报今天有沙尘暴,你还是别出门了。”铃声终于响了,宋伟却这样说。
周晓涵一时没反应过来。在手机响起的瞬间,她果断拿起一支唇精华,它无色无味,涂抹后,可以在嘴唇温度的作用下变成淡红色,这是一种最自然的颜色。这也是最节约时间的一种方式。
“沙尘暴?”她站起身,把厚重的布帘全部拉开,打开门,走上露台。这个小区的房子全是三层高。她站在露台上,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郁郁葱葱的景观花园,与她所在的高度遥遥相对的是冉冉升起的朝阳。这样的天气,不可能有沙尘暴。
“宋伟,你是不是有其他事?可我们说好了的。”周晓涵说。
“我没有,但是……”
“但是什么?你后悔了?”她为他们即将去完成的壮举激动了一夜,此刻,他居然支支吾吾起来。
“没后悔,只是觉得你妈说得对,我给不了你好的生活。”
周晓涵听到咔嗒一声轻响,那是火机的声音,仿佛看到电话那头的宋伟点着一支烟,左手插在灰色工装的裤兜里,看着远处的彩虹桥。他身后是长长一排老旧的平房,墙上开着一个又一个门洞,距离一致,大小相同,连涂着白漆的卷闸门都是一模一样。
上周,周晓涵跟妈妈撒了谎,说去北京参加同学聚会,其实她哪儿都没去,在宋伟那里窝了三天。她每天早上都听到卷闸门“哗啦哗啦”升上去的声音,那个声音此起彼伏,要持续很久,像晨光里的交响曲。第一天,她就那么跟他说了。
“这里环境太差了。”他回答,抽出一支烟,又放了回去。
她愣了一下,“挺好的。”
“你真觉得挺好吗?可我觉得非常不好。”他起身出去了。
他们住在工作间后面的小屋,一张床,一个简易衣架,简陋但整洁。宋伟的家在不远处的老街上,早、中、晚他都会回去一趟,他说他妈坐在轮椅上,简单的家务能做,但也有做不了的。他回去的时候,她会守在工作间。
“去吃早点吧。”她跟了出来。
“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跟你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宋伟带她去了北头老张家的早点摊。
一条加了酵母粉膨胀起来的面团,被揉捏拉拽,下进油锅,滚烫的油花滋滋冒着,没一会儿,张婶就捞了一筐子油条。热气腾腾的葱花饼端出来,还有豆腐脑、胡辣汤、小米粥……
宋伟和周晓涵占了一张矮桌。
老张南邻鲜果店的店主和他老婆占了另一张矮桌。他一边吃油条,一边对老张表示了不满。店主认为他那边每天过早蔫巴的鲜果,与老张这边飘过去的油烟脱不了干系。老张说扯淡,你们两口子晚上少折腾几次,水果就不蔫巴了。鲜果店前面卖水果,后面用布帘隔出一张床的空间,那便是夫妻俩的卧室。再往南是烧鸡店、火烧店、童装店、女装店、打印铺,接下来就是宋伟的修车行。修车行南临一个培训班,教学兼卖架子鼓。那个梳着马尾的高瘦青年,下午两三点钟才会骑辆共享单车过来开门,一直到深夜,再关门离开。再往南几门之隔还有个书法培训班,教书法的胖子每天下午都会端个水杯,来宋伟这边坐会儿。胖子会写毛笔字,还会画水墨荷花,爱临王雪涛的荷,荷叶荷花都画出来了,就鸟画不成。这成了他的心病。
那天胖子进来,看到周晓涵,“弟妹吧?一定是弟妹。”
“快了,快了。”宋伟给胖子让座。
周晓涵瞪了宋伟一眼,“什么快了,现在就是。”
胖子大笑着,意味深长地拍了拍宋伟的肩膀,“弟妹好,弟妹好!”
这次胖子是来道别的。
“过两天我就走了。”
“走?你要去哪儿?”宋伟问。
“招不来学生,这破地方,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我看你这儿也没生意,进出的都是老街坊邻居,整条街上就没几辆车。”胖子说,“你也找找其他门路吧,你有文化,别在这儿耽搁。”
宋伟猛吸了几口烟,掐灭后,端起壶给胖子的水杯添水。
“邪了门了,不就是只鸟吗?”胖子突然盯着门外,老房子墙头错综复杂的电线上有几只麻雀,远处是风永远也吹不散的雾霾,“算了,没鸟就没鸟吧,老子不鸟它了,走之前,我写幅字,再画幅荷,挂你这屋。”
那天胖子离开后,宋伟从后面搂住周晓涵说:“刚他在没法说,下午得到消息,我考试通过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就把这儿转让出去,去从事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的事,都听你的。”
“为什么他在没法说?多好的事。”周晓涵说。
“都不容易。”
“还有,考试不通过,你就不听我的了?”
“不能让你受委屈。”
“你可是名校毕业的高才生,这对你来说算什么?无论做什么,你都是你。”周晓涵说。
“行,我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都听你的。”
可是今天,他这是什么意思?
“别提我妈,就说你自己吧,你为什么突然变卦?”周晓涵吸了吸鼻子,从露台上转身回房间,她身上是一条白色长袖裙子。她不大喜欢让这种衣服束缚自己,但今天真的非同寻常。房间另一端有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人也穿着白裙子,站在一望无际的绿草地上,头戴花环,瀑布一样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际,微微扬起头。
“我们说好了的,但是今天有沙尘暴,这总归不太吉利。”他说。
“你别找借口好吗?你抬头看看,天晴得不能再晴了。”周晓涵说。她听到一辆车开进了他的工作间,油门轰隆隆的,应该是一辆越野车。
“我先挂了,有人来了,一会儿再打给你。”宋伟说。
“喂……”
月亮从天上投下一个鲜冷色的圆,笼罩着她,圆的直径多大不好说,这是她不太擅长的数学问题。她注意到的是每跑一步都差点踩在圆周上,却总踩不住,很累,但她必须追上去。
那只手来自右侧的黑夜,带走了挎在她右肩上的白色坤包。里面有这个月刚发的工资、一串钥匙、一把檀木梳子、一面小镜子,还有什么?感觉很要紧的东西,却想不起来。月亮把所有的光都压在她身上,越来越沉,她用尽了浑身力气,却感觉离目标越来越远,像在一块海绵上原地踏步……她最后抬头看了看,头顶的光冷而刺眼,她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李亚子醒来,先看到一片朦胧的粉,是她熟悉的床单。目光慢慢走远,接着是她熟悉的原木色床头柜,那上面有每天喊她起床的闹钟,黑白相间的小熊猫头造型。然后,她惊得差点喊出来——周钧坐在那里,他的左手撑在左膝盖上,侧过头看着她。
“你怎么在这里?”
“你昨晚喝多了,那些王八蛋。”周钧收回目光,前后左右活动了一下脖子。熨烫笔挺的白色衬衣加深色裤子,他仿佛永远都是这身装束,像刚从会议室出来,腰里挂着霸气的汉字传呼机,上面有个小红灯一闪一闪的,看上去里面装了不少大事。
“可是,你怎么在这里?”
这可是李亚子的闺房。她的身体裹在被子下面,在向她传递着信息,她已经明白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周钧看着她,此时,他的那张脸被疲倦坠着,整个往下垂,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了不少。
“昨天下午,阿姨打电话,说她出差,嘱咐我晚上带你吃个饭,怕你一个人又不吃了,总这样对身体不好。我下班过来,你不在,打你单位电话,才知道你们去喝酒了,亏得我及时赶到,不然你就出事了,那些王八蛋,你们经常这样吗?”周钧摸了一把兜里的烟,忍住了,拿起床头柜上的可乐,拧开喝了几口。
她好好出她的差吧,又操的什么心。
李亚子很窝火。坐对面的如果是另一个人,事情就简单多了。可一切在两个月前的那个傍晚都结束了——他们面对面站在黄河边,她看着他,他看了她一眼,抬头看天,又看树,接着看河,河面被风吹皱了。
“你真的不跟我走吗?”他问。
“可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她说。
“三年了,你一直都不太懂我。”他说。
“她懂你吗?”她问。
“跟她没关系,她也去,但跟她没关系,至少现在跟她没关系。”他说。
“但将来或许会有?”她看着他。
他扯了一片树叶衔在嘴里,“我们明天就出发,打算沿着黄河,一路走到青藏高原去,一起去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朦胧诗代表人物。今晚在这里举行欢送会,欢迎你参加,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晚不算李亚子,有三十八个人,他们热血沸腾地围着篝火喝酒、跳舞、唱歌、朗诵诗。那个和他一起去的女诗人长发披肩,鼓鼓囊囊的胸裹在一件卡其色大衣里。后来一颗扣子掉了,女诗人低头看了一眼,解开了大衣上所有的扣子,露出里面一件有着几何图案黑白相间的紧身裙。裙子比大衣短,跳过一截肉色丝袜,她脚上穿着一双大红色长靴子,一直到膝盖下面,像从篝火里摘两朵火焰踩在了脚下,所以穿着丝袜的那截腿看起来也很暖和。她在他热切的目光里跳啊、唱啊、朗诵啊,总是很激动的样子,一激动就和他拥抱,抱在一起不是笑就是哭。有时候两个人抱,有时候很多人一起抱,大家都激动得不成样子。
李亚子坐在那里,看着那激动的三十八个人,想到母亲,想到忍无可忍却必须去忍的工作,最后默默低下了头。一双又一双脚从她面前跳过去,跑过去,再跳过去,再跑过去……地上一片狼藉,空酒瓶越来越多。篝火都累得奄奄一息,有点撑不下去的意思。
一轮红日终于从黄河对岸徐徐升起。太阳不动声色地看了看大地,看了看黄河,看了看那群诗人,又看了看篝火,篝火就彻底灭了。那群人被震慑到了,像篝火一样安静下来,回望着太阳。最后,他们发出了一声欢呼,然后迎着朝阳,踩着黄河岸边的冰碴子,“咔!咔!咔!”越走越远。
李亚子独自在晨光里蹬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
进门的时候,母亲站在椅子上挂门帘。入户门是竹帘,透风又挡蚊子。室内门是布帘,美术老师喜欢买块白棉布,自己设计,画一条河,两岸是茂密的花草,河蜿蜒曲折,偏左下宽,越往右上越窄,一条河生动地流向远方。从李亚子记事起,每年一出正月,母亲就开始郑重其事地准备这件事。
李亚子八岁那年,外婆为此对母亲摔了杯子。母亲为那个杯子哭过,据说那是从她插队的村子带回来的,送她杯子的人去了更远的地方。从八岁时,李亚子开始猜测,或许她的父亲在远方的某个城市,北京、上海、巴黎、华盛顿……她仰起头,认真地看墙上的地图,左边是中国地图,右边是世界地图,她看完左边看右边。但外婆说她父亲死了。
李亚子从地图上收回目光,看着外婆,外婆弯着腰扫地,一个深色的、薄薄的、有弧度的、缓缓移动的身影。如果父亲不在地图上标注的某个地方,那她更愿意相信,父亲是被那幅画带走的。在母亲放衣服的樟木箱子的最底层,藏着一幅画。画面上奇怪的线条和色块构成了一个仿佛在极速奔跑的世界,那个世界的中心是深黑色的。李亚子第一次打开那幅画时,感觉自己差点被吸进去。母亲为此打了她,然后折起画,郑重地锁进箱子。后来她总是回忆起那个画面,每次都感到头晕目眩。
母亲正挂第一个卧室的布帘,看到她进来,吓了一跳。“这么早,你从哪儿回来的?”她说,“过来搭把手。”
李亚子像没听到,进自己房间,脱了鞋和外套,钻进被窝。
电话挂了,周晓涵把手机扔在床上。门被推开,一个中年女人进来,穿着浅灰色的长袖衫和修身的白色长裙。周晓涵憋着一脸的委屈,倔强地说:“妈妈,下次可以先敲门吗?”
“可以。”妈妈看着她,语气温和,“你这是要出去?”
周晓涵没有回答,扫了一眼挂在衣帽架上的黑色双肩包。妈妈的目光也触到了那个包,皱了皱眉。周晓涵知道,妈妈看到这些,一定再次对她失望了。妈妈大概在想:看看,稍不留神,她又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
“看样子你是要出去,跟那个修车的?”
“您能不这样吗?什么叫修车的?如果您肯去了解他,我相信您不会再这样说。”
“我没那个兴趣。”妈妈说。
周晓涵看了一眼窗外,没再说话,关于这件事,该说的她都说了,没用。太阳又升高了一点儿,阳光透过玻璃,斜铺在欧式梳妆台上,她的左手搭在梳妆台的边沿,无名指上有一枚银戒指。那是宋伟亲手做的。
当时,她看着他变魔术似的取出一堆工具,模具、刮刀、揉泥板、砂纸……最后是一片泥巴。
“你要干吗?”
“给你做戒指,纯手工版的。”他神秘地笑道。
“就用这块泥巴?”
“嗯。”这是他收到好消息的第二天,前一天晚上,他答应了她的提议。
“感觉好麻烦。”她看到他开始用刮刀快速搅拌起那块泥巴。
“不麻烦。”他搅拌了半天,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小长条,压扁,绕在一个陶瓷模具上,一点点刮着、抹着,那么细心认真,一丝不苟。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不用,你看着就好。”
“一会儿来车了怎么办?”
“今天停业。”
“这泥巴从哪儿来的?”
“让一个开银饰店的哥们儿帮忙找的。”
“那你选个现成的多省心。”
“那不行,必须是宋伟独创,全世界限量版,你一个我一个。”
“一模一样?”
“一大一小。”
第三天下午,她从他那里回来之前,他郑重地把戒指戴在她的手上,那上面有一颗饱满的心,心的中间有一个“伟”。他伸出左手,无名指上是一枚同款的,心的中间有一个“涵”。
此时,她的那只手在阳光里显得很苍白。
“你就死了那份心吧,他不会来的。”妈妈说。
“为什么?”周晓涵回头看着妈妈问。
“你们两个不合适,别跟我提爱情,那样的人,他的爱情不可靠。”
果然又是这种腔调。周晓涵不再看她,轻声说:“那是我的事,我觉得挺适合。”
门铃声传来,她们都看门的方向。
“李主席,找您的。”小苏站在一楼客厅里喊,穿着干净的围裙,戴着着粉色橡胶手套。一个除了吃饭睡觉,时刻处于工作状态的聪明勤快的家政服务员,她在家也一口一个李主席。妈妈出去,周晓涵关上门,反锁。抓起手机拨打宋伟的号码,没人接。她把手机又扔回床上,盯着衣帽架上黑色的背包。房间很大,对面墙上的油画看起来很遥远,那是妈妈的作品,妈妈画的周晓涵。它的市场价已飙升到六位数。妈妈自然是出手不凡,在她眼里,作品只有好的和不好的,不好的她直接毁掉,好的她也不会轻易出售。
我可不是她的作品,我想去哪儿,想和谁在一起,可由不得她来管。周晓涵越想越恼火。
防盗门关上的声音传来,有人把什么东西放下后离开了。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回来,她房间的门把手被扭动,却没有扭开。门外没了动静。妈妈不会让自己在任何人面前失态的,哪怕是小苏,但她能想象到妈妈此时气得身子发抖的样子。她没理会,走过去盯着那幅油画,感觉无法忍受那个戴在发间的花环,画中人微微扬起头的样子也怪诞滑稽,两颊红得有些过分,口红的颜色更是令人无法忍受。她从储藏间找出一套绘画工具,拿着一把裁纸刀站在油画前,和油画里的自己对视着,接着她就动手了。
等李亚子从房间出来,天边只剩下一道越来越暗淡的晚霞。屋里两个卧室加上厨房,三个门上,三条河流向了远方。母亲从一个门帘后面端出了晚饭。
“你舅舅说好几次了,给你介绍个对象,啥时候去见见?”母亲做的炖土豆,给李亚子夹块土豆。
“不去。”李亚子低头扒饭。
“别置气,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
“那您呢?您当年置的什么气?让我连个爹都没有。”李亚子抬头,用酸疼沉重的目光看着母亲。
母亲愣了一下,“你这孩子。”她又夹自己碗里一块土豆,低头吃饭。
第二天中午,舅舅带着周钧登门拜访。母亲做了红烧肉、小鸡炖蘑菇,都是她的拿手硬菜。周钧直夸阿姨手艺好,也没客气,多添了一碗饭。李亚子始终没说话,埋头吃饭。趁周钧去厨房添饭,舅舅凑李亚子耳边说:“别犯傻,人家爸可是局长。”李亚子没理舅舅。没过两日,周钧自己来了,这次他带来了牛肉,新鲜的香蕉、葡萄和苹果,还有一盒带着冰碴儿的海鱼,说他就馋阿姨做的菜。“那就常来。”母亲乐呵呵说。李亚子转身进了厨房,站了一会儿,打开暖壶的盖子,提起炉子上的水壶往暖壶里灌水。
接下来的两个月,周钧每周都会来李亚子家两回。
床头柜上的电话响起。李亚子看了看周钧。他也看了看她,迟疑了一下,拿起听筒递给她,她伸出一只手接了。
“你今天不来上班了?”她对桌的同事。
李亚子看了看小熊猫头,十点一刻。她居然睡到现在。
“昨晚秃头去了医院,左腿胫骨骨裂,你可能有麻烦了。”同事又说。
“什么?”李亚子问。
“你还不知道?昨晚你男朋友实在太解气了。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谁都没注意,秃头还在灌你酒,你已经站不住了,他还灌,一桌子人,谁也不敢说话,只能闷着头自顾吃喝。你男朋友可没含糊,一下就把秃头撂倒了。那家伙骂骂咧咧扶着椅子站起来,抄起一个空酒瓶,可酒瓶子还没举起来,人却窝了回去,坐在一把椅子上,低头打起了呼噜,睡着得也太快了。喂,你男朋友干吗的?派头不小啊,都没听你提过,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哦。”
李亚子看了一眼周钧,脑子里顿时生出雾,越努力回忆雾越浓,昨晚的一切在她脑子里一片混沌,只有那个梦无比清晰。
“不说了,我收拾一下马上到。”李亚子匆匆挂了电话。
“今天天气不好,可能有沙尘暴,别出去了,我都帮你安排好了。”周钧说。
“哦。”李亚子看着周均,“你出去吧。”
周钧没出去,站起来去拿衣帽架上她的睡裙,放她枕头边,转身拿起可乐又喝了几口。李亚子拿过睡裙,在被子里迅速套在身上,这才坐起来,用手理了理头发。
周钧的左侧有一扇窗户,从老旧的木窗棂的格子里看出去,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陈旧但整洁,两米多高的青砖院墙上爬满了风藤。院子大门是木头的,两扇门一扇开着,一扇关着,关着的那扇门比门框小了一截。这个城市总是频发沙尘暴,她一直认定,木门上少了的那一截是被风带走的。
“我知道那家伙住院了,你不用担心,我会处理的。告诉我,你们是不是经常这样?”周钧又摸了一把兜里的烟,再一次忍住了。
“也不算经常。”
李亚子穿上拖鞋,从柜子里拿了衣服去了母亲的房间。一个月总有那么几次,领导命她和几个年轻的女同事参与饭局,陪领导的领导或者客户喝酒。李亚子没什么酒量,每次都不知不觉地醉得很难堪。
李亚子在母亲房间换好衣服,去了趟卫生间,洗了把脸。洗脸的时候,她终于还是没忍住,水一沾上脸,眼泪就出来了。她弯着腰,低着头,泪水和自来水一起往水池里流。流了一会儿,继续洗脸。洗完站起来,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两眼灌满了自来水,她拿毛巾胡乱擦了一把,出来,看到周钧跟过来等在门口。
“你说不算经常,那就不是第一次了,我看你还是离开那个地方吧。”周钧说。突然看到李亚子红肿的眼睛,愣了一下,接着又说:“昨晚怪我,没控制好自己,你别担心,只要你同意,我们马上结婚。”
李亚子没说话。外面起风了,院门口那扇开着的木门左右晃着,令人担忧,风会不会再带走它的另一部分。
“让我来想想。”周钧再次摸了摸兜里的烟,看了一眼李亚子,还是忍住了,“你是学美术的,去书画院怎么样?”
“书画院?”这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做专业画家,听说在那里还有机会出去深造。
“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来安排。”周钧往前探了探身子,突然握紧了李亚子的双手。她被吓一跳,诧异地看着那双手,它们让她感到无比沮丧。
有什么东西敲打在窗玻璃上,啪啪作响,外面的风越来越大。
手机响起,周晓涵扔下裁纸刀跑去接了,气喘吁吁地问:“你什么情况?”
“刚才来了一辆,刚走。”宋伟说。
“今天生意不错。”
“是啊,终于来车了。”
“是不是我妈做了什么?”周晓涵又问。
“你妈妈,她倒没做什么,她也是为了你好吧。”
“为我好?算了吧,她让我怎么样,我就得怎么样。再也不想听她的了。”
“你也别总跟她对着干,她说你最近很叛逆,这让她很难过,我能看出来,她只是想保护你。”
“保护?我看是控制吧!现在只要她看着我,我就会感觉在她的目光里连气都透不过来,甚至我会想到,从我一出生直到现在,就没痛快透过气。真受够了。”
“别这样想,晓涵,她真的只是为你好,即便对我,她也没有恶意。”
“那既然这样,她能同意我们在一起?”
“只有这个,她坚决不同意。”宋伟说。
“看看,她还是这样,不过无所谓,这次我不会听她的。我们私奔吧,离开这个城市。”
“我们能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周晓涵听宋伟说过,那间修车行是他父亲留下的,他父亲去世后,他父亲的徒弟继续维持着。宋伟大学毕业后,本来在上海工作,但他母亲的膝盖坏掉了,他不得不回来。他回来后,他父亲的徒弟就回老家开了自己的修车行。每天早上,他都需要把他母亲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她坚持坐在轮椅上做家务,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她不让雇保姆,说如果什么都不能做,还整天让人当废物伺候着,那还不如让她死了算了。中午她会在轮椅上睡一小会儿,下午接着忙碌。晚上临睡前,宋伟会先搬把椅子放在淋浴下,再把母亲从轮椅上抱进浴室,让她坐在椅子上。她会要求关上门,自己在里面摸索半天,等喊他进去时,她已经洗好,穿戴整齐。他再把她抱回床上。
“带上阿姨一起,我们去上海吧。”周晓涵又说。
“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我真的做不到和你远走高飞。我很清楚,在上海,我根本无法给母亲提供安稳的生活,我更不能拖累你。”宋伟说。
“那我们怎么办?”周晓涵问,她听到又一辆车开进了他的工作间,她觉得他又要挂电话。
“又来人了。”他果然挂了电话。
这次她把手机向油画扔去,手机弹回来,掉在地板上。他就是在找借口,一定是妈妈做了什么。妈妈做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居然退缩了。他们的感情如此不堪一击吗?究竟为什么?得去找他,问个清楚。
巨大的油画和她身上的白裙子都已面目全非。
她找出破洞牛仔裤和白色衬衣换上,把衬衣的前襟压在腰里,然后跑进卫生间重新洗漱,扎了马尾辫,素面朝天,背着那个黑色双肩包跑去开门——妈妈堵在她面前。
“怎么,你还是要出去?”
“对。”她说。
“我知道拦不住你,但是,我劝你,还是别去了。”妈妈说。
“为什么?”
“今天早上,我跟他通了电话,和他谈过了,我跟他说了两点。第一,你们不适合,他给不了你好的生活,你跟着他只会受委屈。第二,你应该知道,他刚刚通过了公务员考试,我只是告诉他,如果他放弃和你在一起,我可以保证他得到想要的岗位。他犹豫了一下,最后说他需要考虑考虑。”妈妈苦笑道。
周晓涵看着妈妈,脸色苍白,双肩包突然滑下来,挂在她的胳膊上,她说:“他并没有答应。”
“可他犹豫了,可以轻易犹豫的爱情,你觉得还可靠吗?”妈妈说。
过了半天,周晓涵才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不出去了。只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真的那么怀疑一切的话,您应该考验的是您的男人,是您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我的,您以为您是谁?真的可以给我一个童话般的生活吗?”
双肩包终于落在地上,那里面装着户口本。周晓涵和宋伟说好了的,她偷出家里的户口本,今天一早他们就去登记结婚,中午庆祝两个人的婚礼。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一切并没有逃过妈妈的眼睛。
周晓涵木然转过身,关上了门。
李亚子和周钧的婚宴盛大而隆重。她走在周钧身旁,看着他和对面走过来的每一个人问好、寒暄,她的脸上始终挂着一层笑意,跟着他的节奏不停地点头。其间,她看到秃头满脸堆着笑容走过来,毕恭毕敬地和周钧说着什么。李亚子看了一眼窗外。
好像起风了,风越来越大,接着便是黄沙滚滚。李亚子的手放在了腹部,她真想离开这里,她想应该去南方。她不希望她的孩子将来和她一样,每年都要经历几次可怕的沙尘暴。突然,滚滚的风沙里出现一个影子,那一袭白衣的影子越来越小……
你怎么啦?李亚子回头,周钧走了过来。不知何时,她已经离开了她的位置,站在了窗前。
周钧中午很少回来,李亚子独自坐在饭桌前,坐了半天,没吃几口,最后让小苏把饭桌收拾了。她靠在沙发上打算小憩片刻,但睡不着。她一会儿拿起手机看看,没过一会儿又拿起手机看看。窗外起风了,她站起来去关上窗户。她不可能看到,在离她很远的地方,地平线上突然出现大片的灰黄,翻滚着迫近,也就是一会儿工夫,天地间已混沌一片,整个城市仿佛都在狂风中颤抖。
她打开灯,看了一眼黑乎乎的窗外,又是这种鬼天气。
她坐回沙发上继续看手机,朋友圈也被沙尘暴席卷。她抬头看了一眼三楼,突然想起好久没有看到女儿的动态了。她找到她的头像,点开,惊讶地看到一条横线。她苦笑着把手机扔回沙发上,再次去看三楼,隐约听到手机的铃声。铃声持续不断。
她上楼推开了女儿的房门,一阵狂风席卷而来,门被风掀到墙上,发出巨大的碰撞声。她顶着风摸着墙壁上的开关,就在那一瞬间,所有的灯突然灭了,一切陷入黑暗中。没有手机的铃声。
但她刚刚分明听到了铃声,一遍又一遍地拨打,那应该是宋伟打来的。她到最后也不确定,那家伙会不会因为她的一句承诺放弃她的女儿。虽然她很希望他那样做。
“晓涵……周晓涵……”李亚子一边喊一边在黑暗里摸爬,没有回音。风沙让她站不起来,也睁不开眼睛,她顺着一面墙慢慢摸索,摸到衣柜,又摸到了床,床上没人。她继续在地毯上摸索,“晓涵,你在哪儿?”没有回音。应该是通往露台的门出了问题,风沙从那里狂泻而来,她想到应该退回去,找一个避风的地方等着。沙尘暴他们每年都要经历,彼此相熟,没什么可怕的。但是……“晓涵,周晓涵!”李亚子突然失控,声嘶力竭地喊道,她仿佛听见女儿在说:“您应该考验的,是您的男人,您自己的感情,而不是我的,您以为真的可以给我一个童话般的生活吗?”
一阵剧痛袭来,就像当年躺在产床上,疼到眩晕的感觉。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她无力地坐在风沙里,风把一切不可理喻的东西吹打在她身上。她感觉身体在一寸一寸冰凉、麻木。
不知道过了多久,风渐渐小了,周围开始亮起来。小苏跑过来扶起她,她们找遍了整个三楼,找不到周晓涵。最后给周钧打电话,报警,调监控,一处一处排查,终是无果。
晚上,周钧和李亚子疲惫地坐在一楼客厅的沙发上。
小苏上楼去打扫,先找到周晓涵的手机。接着是那条白裙子,再接着,小苏惊叫起来:“李主席,李主席……”
客厅里的李亚子和周钧对视一眼,慌慌张张跑上楼,看到小苏呆立在那幅巨大的油画前。油画里,一身白裙子的画中人身后,草地上突兀地出现一条河,偏左下宽,越往右上越窄,蜿蜒曲折,一直流到画框外。扎着马尾、穿着白衬衣和破洞牛仔裤、背着黑色双肩包的另一个画中人站在河对岸,安静地看着他们。
李亚子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她看到油画里草地的尽头,奇怪的线条和色块正在构成一个仿佛在急速奔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