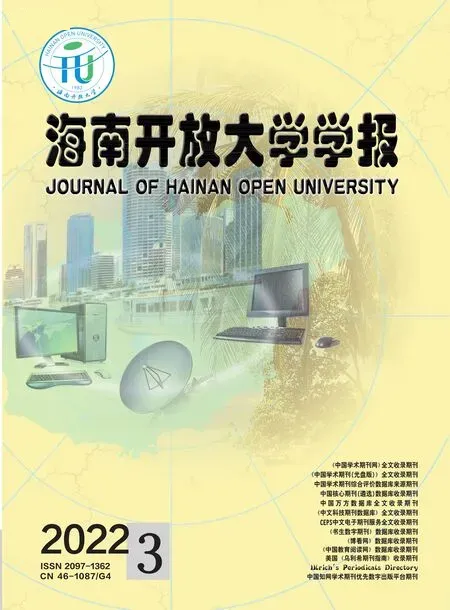中国古代刑法中正当防卫因素的流变与镜鉴
赵浩,程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法谚有云:“正当防卫无历史”,其旨在表明正当防卫权和生命健康权一样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无须经由任何组织的确认或授予。但近代社会中,以权利实现、保全为目的而行使武力的权利原则上由国家独占,正当防卫在何种情形下、多大程度上得到承认,实际上取决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贯彻武力独占[1]。正当防卫在国家权力更迭与人权观念演变的夹缝中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正当防卫制度源自大陆法系国家,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确立的正当防卫制度多借鉴了西方的刑法理论。但其实,我国刑法史中也可以找到正当防卫因素的源流,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中国古代虽无正当防卫之名,而有正当防卫之实[2]11。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考究中国古代刑法的变迁史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其一,助益于因地制宜地实现正当防卫制度的本土化塑形,克服舶来理论“水土不服”的弊病;其二,虽然传统小农经济社会所形成的“差序格局”受到信息时代的冲击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但是今日吾国与吾民仍然深受地缘和亲缘的影响;其三,“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德主刑辅、礼法并施的古代刑法精神对今时今日的大国法治仍有积极效用。中国刑法史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晶,也是推进法治建设的资源宝库。因而,有必要探究中国古代刑法中正当防卫因素的变迁,秉持去伪存真、古为今用的理念,遵循取精去糟、批判继承的径路,从而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正当化根据的祛魅:从私刑复仇到紧急处置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私力救济的历史便从未间断,但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在国家产生之前,私力救济是人们解决民间纠纷矛盾的唯一途径。但是,自国家产生以后,随着公权力的强化和政治制度的演进,国家长期以来倾向于对私力救济投射一种敌对性的目光,公权力越强大,往往越趋向于节制私人自助行动[3]。沿着时间脉络来看,正当防卫源生于人类谋求生存的防卫本能,并伴随着我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不断发展,以隋唐时期为分界点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早期
复仇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的氏族社会。当时的复仇主要是指血亲复仇及同态复仇,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以氏族部落为依存,依靠氏族的群体力量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在个人生命受到侵害时,同氏族的其他成员便具有了复仇的“权利”和“义务”。原始社会尚未建立起法秩序,这种复仇理念也仅能反映人类原初、粗浅的自卫意识。在氏族社会后期,文明和理性的演进完成了质的跨越,同态复仇的形态逐渐转变为了报应的形式[4]。刑事古典学派倡导的刑罚报应主义就有复仇观念的影子,“被害报应”的原型就是氏族间的复仇。当然,这种报应观念对现代社会而言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对加害人科处刑罚并不会为被害人带来利益,两者并不是等价交换的对象;另一方面,其所提倡的结果责任也偏离了现代责任主义的要求[5]。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原始社会在此过程中演变为奴隶社会,公权力的机器得以成型并开始运转。国家刑罚权就是公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此同时,社会的基本单元不再是纯粹的氏族集群,而是转变成了以地域标准以及家庭关系联结的社会组织结构,原初的复仇观念被消解大半。奴隶主贵族阶级一跃成为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法秩序之外的私刑并没有得到彻底封禁。而且,商、周时期保留了原始习俗的残余,兼有明显的宗法色彩,宗族的习惯法与国家的刑法在奴隶社会统治制中相须而行,并辔齐驱。此外,奴隶制时期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集权制国家,各地区各自为政的环境使得法制建设停滞在初级水平,私刑复仇在这一时期成为补充公权力的权宜之计。蔡枢衡就曾指出:利用被害人家属的力量来帮助镇压杀人现象,藉以维护统治秩序,本质上是统治者权力不够强大的一种表现[6]164。《周礼》对“公许复仇”制度作了细致的规定,到专门主管的官吏处办理手续,完成登记并获得批准之后,报复仇人就不再构成犯罪①《周礼·秋官·司寇》:“凡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辠。”。复仇在奴隶社会时期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和许可。除此之外,复仇的另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杀人者死”这一约定俗成的铁律②《荀子·正论》:“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这种观点一直以来都代表着最朴素的自然正义,被历代君臣民众奉为圭臬。但是,《周礼》记载的“杀人而义”不死③《周礼·地官·调人》:“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勿令仇,仇之则死。”,就可谓该原则的例外,陈兴良认为,这其实就是现代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同时也是古代刑法伦理化的重要标志[2]6。
战国时期,报仇的风气可谓盛行④比如,孟子有云:“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复仇之所以在奴隶社会被允许,是因为公权力的体制机制仍然羸弱残缺,法律制度及配套措施并不健全,私刑复仇远不能称之为正当防卫制度。但是,不可否认,复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正当防卫的部分功能,而且它们的正当性都根源自人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意识。春秋战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事断于法”逐渐取代了“设法以待刑,临时而议罪”,这从根本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随着法家学说的兴起,法律制度的设计与构想在各个诸侯国得到尝试和实践。比如,李悝编纂的《法经》就是法制建设承前启后的集大成之作。到了秦朝,“严刑峻法”已被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推向极致,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之后的阶段,封建帝国缔造了发达的法制和机构,生杀予夺之权自此就逐渐被国家收回,私人便不再有擅自杀人的权利。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春秋决狱”使儒家经典法律化,儒家学说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法律制度实现了伦理性的改造,私刑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据考证,至少在西汉末年就已经有禁止复仇的法令。自东汉以后,私自复仇的行为基本都被明令禁止,生杀大权尽听命于君主与政府,私人恩怨瓜葛必须寻求公共机关定夺[7]。部分朝代对复仇稍有宽容,但是禁止是总趋势。凶犯纵使犯应死之罪,亦须告官治罪,不得擅杀。私刑复仇,在权力集中、法制迈进的阶段,便沦为了与官方秩序相对抗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被政府所遏制也是必然的趋势。究其本质,复仇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是公权力的孱弱,随着法制的进步注定为历史所淘汰。私力复仇断然不同于规范的正当防卫,仅能视为正当防卫观念的萌芽。尽管这一时期的具有正当防卫因素的法律实质上可以视为正当防卫条款,但在立法例上,其碎片化地散落在各种法律文本之中,缺乏一般性规定和体系性设置,而且,相关规定的数量整体上仍然有限。正当防卫的制度根基和规范依据在这一阶段一直困顿于蒙昧之中。
(二)封建社会中后期
封建社会中后期一般指从隋唐伊始直至清朝灭亡。唐、宋以后的法律一贯地禁止复仇(元朝有例外)。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私刑复仇已经在周密的法律规范中几无立锥之地。复仇面临礼与律之博弈,人情与法律的冲突,尽管历朝历代都在打压复仇这一问题上做着不懈地努力,但史实证明,复仇主义深入人心、牢不可破,仍有不少悲壮之士铤而走险,慷慨赴义。以至于在部分时期,私刑复仇呈现出死灰复燃之势。但是,这与前述复仇之形态和规制状况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刑法史上正当防卫制度发展的拐点出现在唐朝。唐朝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峰,唐律是封建法典的典范,在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唐律之中制定了关于正当防卫较为完备的规范,使中国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初具雏形。比如,《唐律·贼盗》:“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答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的规定,被公认为是中国封建法律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的典范。首先,《唐律疏议》中对家者作出了具体的解释,即家宅院之内,保护民众私宅的所有权,反映了封建私有制的特征①《唐律疏议》规定:“谓夜无事故,辄入人家,笞四十。家者,谓当家宅院之内。登於入时,被主人格杀之者,勿论。”。其次,唐律将正当防卫的起因限定为不法侵害现实发生,民众在急迫情况下难以寻求官府的保护和援助,而且反击刻不容缓,可以通过私力救济对紧急状况进行处置。再次,唐律将正当防卫限于当时及时的反击,这也反映出法律对紧急处置的特别准许。虽然唐律中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与今日之正当防卫制度不可比拟,但是在当时封建社会的背景下,立法技术和水准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唐律在我国封建律法发展史中起到代承先启后的作用,提供了封建体制下正当防卫规定的范式和模型,直到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部法典都与唐律陈陈相因。封建社会的正当防卫制度的成形肇始于唐朝,自此之后的封建法律体系都与唐律具有十分清晰的沿革关系和内在联系,没有突破唐律所构建的制度框架,在“西学东渐”之前,也鲜有超越唐律创新。比如,唐、明、清之法律都要求为自己防卫时以请求官府救助为原则[8]361,仅允许个人在少数的例外场合中实施的防卫行为。再如,清朝法律也同样规定正当防卫的成立前提须具备“系猝遇强暴、情势危急、仓卒捍拒”②《大清律例·刑律·斗殴》卷二十八。的情势。又如,宋元明清关于正当防卫的立法体例,基本沿袭唐制,都是分散于各具体的罪责条文中[9]。
封建伦理观是中国古代刑法设置正当防卫条款的指导思想之一。唐律之后的历代法律,几乎都有为父母防卫的规定③《唐律·斗讼》:“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明、清律承上述规定,又补充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这些规定与现今之“为他人防卫”具有相似性,但是其出发点并非基于社会整体利益或所谓的团结义务理论,而是根据封建纲常伦理,将为父母防卫的正当性单独予以强调。这也鲜明地体现出,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伦理性。在当今高度文明的法治社会中,刑法保护的客体不再是伦理道德,而是法益。刑法只能保护具体的法益,不允许保护政治、道德信仰、宗教教义、意识形态或纯粹的感情[10]。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避免正当防卫的判断陷入误区。比如,通奸在古代属于道德禁忌,将奸夫淫妇当场杀死甚至能够被法律所允许。但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违反道德戒律的通奸行为,还是刑法明文规定的聚众淫乱等风化犯罪都没有损害任何人的法益④持结果无价值论的学者大多对刑法中聚众淫乱罪的立法根据持怀疑态度。,不具有刑罚可罚性,杀死通奸者或聚众淫乱者的行为难以被正当化。在某些场合,道德情感的评价会左右人们对正当防卫事实的认定和评价,人们习惯于同情道德纯洁者而主张严惩道德瑕疵者。但是,违反道德规范并不意味着丧失值得被法律保护的资格,刑事司法务必贯彻理性的审查,维持演绎的严谨,坚守公正的底线,不得将不合理的非难强加于无辜者。例如,甲在公共场合伪装成残疾人四处乞讨,乙将其揭穿并暴打甲,甲适时予以反击,虽然甲是因为个人不道德的行径而招致武力攻击,但不能直接否定其反击行为的防卫性,仍然要考虑构成正当防卫的可能,司法人员必须摒除先入为主的道德评价。
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私刑复仇在强大公权力的挤压下已然穷途末路。法制的健全使得复仇再无生存空间,也推动正当防卫走出了蒙昧的迷雾。封建制度允许民众在法定的紧急状态下享有私力处置的权限,不代表国家对个人权利的认可和照顾,而只是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秩序的工具,最终目的则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封建统治。换言之,无论是法律还是伦理,都是服务封建统治的手段,都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被法律所许可的正当防卫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受到伦理的限制。阶级性是封建时期正当防卫规定的本质属性。德国主流观点以及我国部分学者认为,现代正当防卫制度的正当化根据是个人保护原则与法保护原则。一方面,面对侵害展开自卫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这点即使在私刑复仇时代也并不否认。因此,现代法律制度绝不能建立在压抑人性的基础之上,而应充分考虑不可抗力或紧急事态对行为人产生的负面干扰。比如,受辱妇女反杀行为的司法定性近年极具争议。2017年,被告人王某不堪长期家暴,某日被丈夫邱某殴打后惶恐不安,趁其熟睡之际将他杀死,法院认为王某有杀人故意,不构成防卫过当,但其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情节较轻,依法可以从轻处罚①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17鲁0481刑初307号刑事判决书。。妇女在婚姻家庭中屡次遭受暴力侵害,被迫反抗也是人之常情,在实行防卫的场合,可以运用期待可能性的原理阻却犯罪的成立或减免处罚[11]。另一方面,正当防卫制度是国家诞生之后的作品,法秩序的形成是正当防卫制度存在的前提。之所允许个人采取必要保护手段反击不法侵害,是因为国家机关无法及时到场,个人防卫受到法定秩序的约束[12]。简而言之,法秩序的实存是正当防卫的基础,正当防卫制度也发挥着维护法秩序的功能。
三、正当防卫机能的异化:从排除犯罪到阻却刑罚
正当防卫的机能,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可以转化为,正当防卫在体系定位上是犯罪排除事由还是刑罚阻却事由。
(一)“无辠”或“无罪”
关于“无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周礼》规定,杀死城乡里的盗者和贼人,不构成犯罪②《周礼·秋官·朝士》:“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辠。”。蔡枢衡认为,《周礼》这一规定实际是具体而微的正当防卫。所谓杀之无辠,按照《义疏原案》的解释,就是不得以“擅杀”对其定罪,或者免除其“擅杀”之罪责,这种对正当防卫的法律评价,十分接近现代刑法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的观念[2]7。
何为“无辠”?蔡枢衡指出,要想区分“罪”与“非罪”,就需要明确“辠”的概念。“罪”在秦朝之前为“辠”字③《说文解字》:“辠,犯法也。”。他总结到,辠是人类社会的现象,包括造意、作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是违反统治者的禁制和利益的行为。辠,即罪,是人类违禁的行为。除违禁之外,还有违反统治者使命和违反容许的现象[6]165-169。从周代直到清末,罪名和违法的范围大体是相同的。由此可知,无罪,就意味着行为是被法律所容许的。这一解读与现代的形式违法论、违法一元论颇为相近,表明了中国古代刑法在违法性判断上的基本立场和依循。《汉律》规定,无正当理由进入他人的室、宅、庐、舍、车、船等居所的,侵犯了人身自由,将侵入者打死也是无罪的①《汉律》:“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蔡枢衡认为,这也是后世所谓正当防卫[6]166。可见,正当防卫发挥着排除犯罪的功能。
北齐有规定承袭了周代的遗规:侵入别人家里盗窃、杀人的,或者在村落和城镇里团伙作案的,将其杀死不是犯罪。告官备案后复仇的,不坐②《隋书·刑法志》:“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仇者,告于法而自杀之,不坐。”。不坐就是不击,亦即不处罚。这一规定有两处值得思考。其一,该规定反映了朴素的罪刑均衡理念,同样是盗与贼,“攻乡邑”相较于“入人家”则附加了一个“群”字,要求其集体作案才能与侵入住宅盗窃、杀人相当。现代刑法也将罪刑均衡作为基本原则,正如高铭暄、马克昌所指出的,“罪刑相适应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奴隶社会的等量报复。”[13]当某一行为不值得刑罚处罚时,就不得予以犯罪化,刑法只能将严重侵害法益或侵害重大法益的行为设置为犯罪。其二,前一情形“杀之无罪”,而后一情形“不坐”,表明了两者在法律评价上并不相同,因此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有所差异。可见,古代的法律规定在当时就有意区分不构成犯罪与不受处罚两种情况。但是,正当防卫行为的性质是无罪的,还是其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是不值得被科处刑罚,在学术史上曾出现分歧。这一争论于今日而言也并非毫无价值。如所周知,我国理论界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与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分庭抗礼,前者批判后者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四要件留有在犯罪成立之后再讨论犯罪排除事由之弊端,不仅导致认定的整体性和裁量的恣意,而且割裂了违法性的判断。根据阶层犯罪论体系的逻辑推演,正当防卫行为虽然该当于构成要件,但是不具有违法性,因而不构成犯罪。因为正当防卫行为本质上是合法行为、正当行为,所以不能对正当防卫行为进行正当防卫。但四要件犯罪论体系的思路是在判断了客观危害与主观责任之后再回过来判断客观危害(犯罪排除事由),容易导致将正当防卫认定为犯罪,因而备受诟病。
当然,对古代刑法的语境而言,传统刑律不同于现行刑法理论中的罪、刑分明,二者常常混用,而且更侧重刑罚适用的结果[14],而比起定罪来说,古代统治者与民众更加关心刑罚处罚的后果。无罪虽然不能仅仅理解为现代刑法学中的不构成犯罪,但是也同样不能与“不坐”等概念完全等同,即使其区别是微小的,但是法律规定在不同场合中使用不同的用语,也就不能无视其差异。
(二)“勿论”和“不坐”
“勿论”与“不坐”相较于“无罪”更加强调不处罚这一后果。尤其是唐律及之后,诸多规定表明正当防卫发挥着刑罚阻却事由的功能。《唐律》中规定,晚上无正当理由侵入别人家宅的行为是违法的,笞四十。户主当时将侵入者杀害的,勿论③《唐律·贼盗》:“诸夜无故入人家,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这一规定显然是对《汉律》的简化和继承。论意即照明文处罚,不论就是不罚。明、清律除了将“笞四十”改为“杖八十”外,其他的与唐律相同[8]362。蔡枢衡指出,主人面对闯入自家住宅的侵入者,当即杀之,本来就是无罪的正当防卫,而将这一行为规定为不处罚,未免自相矛盾[6]167。在我国古代刑法中常出现“勿论”的表达④《唐律·斗讼》中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元代有关于误想防卫的规定,“夤夜潜入人家,被殴伤而死,勿论。”明、清律中“本夫于奸所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勿论。”“祖父母、父母为人杀,子孙即时杀死杀人者,勿论。”。从上述解读来看,这些规定所明确的正当防卫之法律后果也是不处罚杀人者。
此外,唐朝有如下规定,他人饲养的动物损害财物的,当时将动物绞杀,减免处罚,因动物伤人而将其杀死的,不处罚也不赔偿①《唐律·厩库》:“诸官私畜产毁食官私之物,登时杀伤者,各减故杀伤三等,偿所减价,畜主备所毁。其畜产欲觝啮人而杀伤者,不坐不偿。”。偿是赔偿损失,属于民事责任,不坐就是不处罚的意思。明代、清代的法律中也有大体相同的规定[8]363。这类规定牵涉到紧急避险与狭义的对物防卫之间的区分问题。古代刑法将该行为的法律后果规定为不处罚,而不是无罪,“足见对于问题性质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的。”[6]167那么,对于有主动物(官私畜产),在主人没有唆使、动物自发侵袭(毁食官私之物或觝啮人)时,能否进行正当防卫?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仍争议甚巨。高绍先认为这种对动物侵害所进行的反击也属于正当防卫[15]。陈兴良在解读古代刑法规定时将其等同于紧急避险[2]93-94。主张人的违法性论者,一般认为不法侵害必须具有行为性,否定对物防卫的成立[16]。这也是目前德国的通说[17]。但是,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比正当防卫更为严格,对人的侵害可以成立为条件缓和的正当防卫,但是对于动物的侵害只能成立为更为严苛的紧急避险,这难以让人接受。如果基于物的违法性的立场则认为,动物侵害也明显地侵害或者威胁到了法益,从客观违法性论的立场来看,对没有责任能力的行为可以实施正当防卫,而对主人不能管理动物的侵害不能实施正当防卫,这明显不均衡,对动物侵害也应当能够实施正当防卫[18]。倘若认为正当防卫的对象并没有把动物排除在外,那么就应当认为可以对动物进行正当防卫。这也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所探讨的内容之一。
清末颁布的《大清新刑律》规定了法令行为、业务行为、符合公序良俗的行为、正当防卫行为、紧急避险行为等都“不为罪”②《大清新刑律》规定:“依法令或正当业务之行为,或不悖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习惯之行为”,“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避不能抗拒之危难、强制,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都“不为罪”,建立了违法阻却事由的概念和理论,其批判和吸收了“无罪”“不坐”“勿论”等规定。蔡枢衡认为,“不为罪”这一表述并不准确,“这三个条文的内容,都是由于实质不违法,所以不成立犯罪,理应称为无罪。而实际称为不为罪,未免美中不足。”而在第二次修正之后,将“不为罪”改为“不罚”,相当于肯定这类行为也是违法行为,“致使本来以实质不违法为特点的阻却违法事由丧失了本来的性质,实属大谬。”[6]1681935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也没有把阻却违法行为的“不罚”改为“无罪”,没有准确地把握正当防卫行为的性质,也存在缺憾。
时至今日,正当防卫能够排除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行为的违法性,已经几无争议。违法性判断的问题上也发展出社会相当性、法益阙如、法益衡量等各种学说。回望中国刑法史中正当防卫机能的变迁历程,从“无罪”异化为“勿论”“不罚”于今时观之可谓历史的倒退。这也使人警醒,在人权保障观念蓬勃兴起的当下,要注意妥当认定权利行为与违法犯罪,正当防卫行为实质上是合法行为,其利益在法律地位上优越于不法侵害人,不能仅因其存在瑕疵或不当就作为犯罪处理[19],即使定罪免罚或者适用减免条款也有违刑法的正义理念,不仅要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要坚守刑事司法的正当性。
四、正当防卫行为的构造:成立的具体条件
如所周知,结果无价值论在主观的正当化要素上一般采取防卫意思不要说,并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主张正当防卫行为须具备起因、时间、对象、限度四个成立条件。防卫对象问题已经在前文中有所论及,本文在此主要分析中国古代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中所包含的防卫起因、防卫时间、防卫限度三方面要素。
(一)防卫起因
在当前的刑法规范中,正当防卫的起因必须是针对不法侵害,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不法侵害都可以行使正当防卫权,还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盗与贼是古代官方认定的“不法侵害”,①《周礼》:“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李悝在《法经》指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盗是指古代社会中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而贼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
古代社会的法律带有鲜明的伦理印记,对防卫起因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一点。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的统治秩序,周朝奴隶主贵族特别重视不孝不友罪②《尚书·康诰》:“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周礼·地官·调人》:“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勿令仇,仇之则死。”。概言之,杀死不孝不友者,也是正义之举,不能对其复仇。《左传》中有记载:郑国游某强奸他人之妻,其夫对游某实行正当防卫,杀死游某以使其妻免遭强奸。裁断者认为游某咎由自取,被杀是正当的③《左传》:“郑游贩夺人之妻,其夫攻杀之,而以其妻行。子产复之,令游氏弗怨。”。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强奸妇女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危害性。因反击强奸而将侵害者杀死的行为,就是正当的。强奸有夫之妇之所以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伦理秩序和男性地位,但是也足以反映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传统的行为无价值论就曾主张,刑法保护的对象是社会伦理秩序,社会伦理秩序可以作为违法性的判断根据[20]。不过,这种学说如今已经式微。
古代刑法重视对住宅等私人领域的保护,在封建社会里,家不仅是私有财产的基础,而且是封建伦理道德关系的体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很多朝代法律都严厉打击侵犯他人住宅的行为,并允许对这种侵害实施正当防卫。比如,汉朝时期就已经允许对侵入居所的行为予以正当反击④《汉律》:“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这表明,在封建私有制时期,无正当理由侵犯他人的居所,已经触犯法律,可以对其正当防卫。唐朝对夜犯他人住宅的情形规定得更加细致⑤《唐律·贼盗》:“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答四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所谓夜,按照《唐六典》所记的《刻漏法》,“昼漏尽为夜,夜漏尽为昼。”之所以在该规定中,强调“夜”是因为“夜无故入人家内”的行为违反了唐朝的夜禁制度[21]。《大清律例》承继了前朝的法律,并对此作出了较为周详的规定⑥《大清律例·刑律·贼盗》:“凡夜无故人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其已就拘执而擅杀伤者,减斗杀伤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根据沈之奇的解释,在这一情形下已经完全具备成立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私自进入住宅的行为是夜晚,且无正当缘由,因此,主人在疑虑和担心的状态中,推测侵入者非奸即盗,在情急的状况下,防御侵害而将其杀死,理应被宽宥[22]。不难看出,这一解释已经与现行刑法中规定的非法侵入住宅罪所保护的住宅安宁权相近,将入户盗窃行为作为犯罪,对入户抢劫加重处罚,其合理性的根据古已有之。
古代刑法也有为他人防卫之规定,当他人正受到侵害时,亦允许对不法侵害人实行正当防卫。我国秦律把为他人防卫所遭受的不法侵害规定为法律义务,追究不救助罪的刑事责任。秦简记载,邻居在家中呼喊救命之时,如果周围的人不帮助就要治罪,而负有特殊职责的里典、伍老则不论在家与否,都要论罪⑦《法律答问》:“贼从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唐律》中规定①《唐律·捕亡》:“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窃盗者,各减二等。”,有人遭受抢劫、杀人,他的邻居听闻却不帮助的,都要受到处罚。邻里得知被害人正在面临暴力犯罪,至少要报官,否则就可能涉嫌犯罪[23]。《宋刑统》也承袭了这一规定②《宋刑统》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救者,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者论。”。自此以后,元、明、清的刑律族法均有此类规定③如《大清律例·刑律·贼盗》卷二十四:“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应当效仿德国在刑法中增设见死不救罪的声音。古代刑法把为他人防卫强制化的做法极大压缩了公民的自由空间,其目的是通过利用私力互助的方式来弥补公权力在维稳过程中的不足,进而巩固统治,公民防卫行为只是辅助公权力目的实现的工具。但是,现代刑法已经完全不同于极具干涉性的古代刑法,而应当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人权。通过法律纠偏来强化治理效果,并不是说就只有用刑法来惩治见死不救、见死不救这一条路[24],该行为未必达到足量的违法性,借由道德谴责或行政处罚的路径也能够对这类行为妥当规制。
(二)防卫时间
只有当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且尚未结束时才能进行正当防卫,否则属于防卫不适时。古代刑法中也有关于正当防卫时间条件的表述,即要求“事在顷刻,势出仓促”。在各类正当防卫的规定中,常见以“登时”“其时”“见”“即时”等用语来限制防卫时间。例如,《汉津》规定“立子奸母,见,乃得杀之。”
唐律中对于防卫时间的规定十分明确。《唐律》中规定“诸夜无故入人家者……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所谓“登时”就是指:“于入时”,就是“当时”的意思。明、清律中都有对防卫时间的规定④如“本夫于奸所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勿论。”“祖父母、父母为人杀,子孙即时杀死杀人者,勿论。”。值得关注的是事后防卫的问题。在侵害者已经被制服,不法侵害随之停止之后,如果户主依然将其杀伤,则以斗杀伤论处,造成死亡结果的“加役流”⑤《唐律疏议》记载:“‘已就拘执’,谓夜入人家,已被擒获,拘留执缚,无能相拒,本罪虽重,不合杀伤。主人若有杀伤,各依斗法科罪,至死者加役流。”。这其实就是唐律对事后防卫的规定,亦即,事后加害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而是犯罪行为。唐律还特别对“绝时而杀”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即“忿竞之后,各已分散,声不相接”,在双方已结束斗殴的情况下,如果一方“去而又来杀伤”则要“从故杀伤法”,“加斗殴伤罪一等”从严处罚[25]。可见,唐律对防卫时间的规定已然相当精细。清条例为了防止防卫手段被滥用,特别规定:若贼已被殴跌倒地,及已就拘获辄复叠殴致毙的,或事后将其殴打致死的,以擅杀人罪论;窃贼旷野白日偷窃无人看守器物,将其殴打致死的,不问是否当时,以擅杀人罪论。但是如果贼犯持杖拒捕,当时将他杀死的,依律勿论。
关于防卫时间的判断标准可以从古代刑法中获得有益借鉴。目前,我国不少学者主张,应当承认量的防卫过当的概念,从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2款减免处罚的规定引至事后防卫或其他防卫不适时的场合。根据防卫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综合判断,在防卫限度允许的范围内,如果不法侵害尚未结束或者仍存在较大威胁,那么就不宜认定为事后防卫。如果侵害人行为从轻微违法升级为严重暴力,比如盗窃后持杖反击,那么防卫时间则需要重新计算。此外,还需要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等导致期待可能性降低的事由,这些因素必然干扰防卫人对不法侵害持续与否的判断和应急反应。总之,不宜将时间条件限制得过于严苛。
(三)防卫限度
古代刑法规定的防卫限度因应了具体情境中的防卫前提条件,并没有提出如同“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统一限度标准,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中予以具体分析。比如,对杀死夜无故入室者与斗殴致死者的处罚就截然不同。这种重视个案分析的认定思路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避免“一刀切”地将案情僵硬代入“条件公式”验证和推演①2020年颁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要求,应当立足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境,综合考虑案件发生的整体经过,结合一般人在类似情境下的可能反应,依法准确把握防卫限度等条件。。《唐律》规定,斗殴无防卫,即使对方以兵刃逼己,因而用兵刃抵抗对方而将其伤杀的,也要依“斗伤杀法”论处②《唐律·斗讼》:“诸斗两相殴伤者,各随轻重,两论如律;后下手理直者,减等。至死者不减。”。古代社会认为,斗殴行为损害劳动者身体,妨害生产工作,扰乱社会秩序,因而被古代政权严令禁止。根据上述规定,对相互斗殴者的处理,要根据其行为方式及结果来进行轻重上的判断,被轻微殴打的然后将其反杀,显然超过了必要限度,不可能成立正当防卫。而且,相互斗殴者,即使是后下手理直的,也只能减轻处罚,不能对其免除处罚,这也体现出唐律对斗殴中免责的要求非常严苛③《指导意见》指出,要准确界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综合考量起因、双方过错、暴力相当性等客观情节。。
值得关注的是特殊情形下的正当防卫,以典型的暴力犯罪强奸罪为例。古代刑法已经出现了类似于今天,防卫强奸无过当的处断结论④《唐律疏议》中有如下记载:问曰:“外人来奸,主人旧已知委,夜入而杀,亦得勿论以否?”。答曰“律开听杀之文,本防侵犯之辈。设令旧知奸秽,终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难辨,纵令知犯,亦为罪人。若其杀即加罪,便恐长其侵暴,登时许杀,理用无疑。况文称‘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即明知是侵犯而杀,自然依律勿论。”。奸非,包括强奸和通奸,在古代一直属于重罪,因此对奸非的防卫也相当特殊,不仅包括对正在实施的强奸行为的防卫,对还未实施的强奸以及通奸也可以进行防卫,而且可以致行奸之行为人于死地而不负刑事责任[9]141。但是,古代刑法之所以如此重视奸非犯罪,其立场并不是保护妇女人身权益,而是纲常伦理秩序,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鲜明地反映了这种伦理至上的封建观念。总体来看,在古代,女性的权利没有得到全面保障,尤其是在缺失法律庇护的角落,妇女权利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事例屡见不鲜。如道光年间,林某强奸儿媳,儿媳林谢氏因反抗而将其割伤,林某因伤致死,道光帝最终判处林谢氏斩监候。现代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主义,摆脱了古代刑法的身份性和恣意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20条第3款允许对正在实施强奸的不法侵害人采取防卫行为,即使造成其伤亡的也不负刑事责任。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之下,防卫人具有更大出罪空间。根据法益保护的要求,该规定并不是所谓的特殊情形下的无限防卫权,即使面临强奸等行为,也不意味着防卫行为无必要限度之要求,仍然受法益衡量原则的调整[26]。相较于古代法律,现代刑法无疑更重视对人权的保障和对平等的维护,即使是不法侵害者,也不能超过必要的防卫限度损害其利益。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该规定仅是对防卫限度的提示性规定,而不是对防卫对象的一般性规定[27]。不能基于此就将作为防卫对象的不法侵害的范围限缩为强奸罪等几种罪名,对于非法侵人住宅、盗窃等罪都也能实施正当防卫。换而言之,即使造成非法侵入住宅者、盗窃者伤亡的,也可能构成正当防卫。
五、结语
从私刑复仇到紧急处置,中国古代法律的沿革生动地体现了防卫观念的流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政治制度的进步,私人暴力与公共权力在社会统治中的分量此消彼长。国家愈强大,对私力救济的控制便愈发严格。私力救济所充当的角色也在此过程中,从补充公权力缺漏的积极力量,转变为只能有限得以允许的不稳定因素。在公民个人权利意识觉醒之前,正当防卫只是维护国家统治的工具。这也启示我们务必转变正当防卫制度的基本观念,不能局限于对社会稳定的片面追求,也要强调对人权的保护,否则就会导致个体权益沦为牺牲品。
不仅如此,在稳定大于一切的今天,采取平和手段定纷止争固然值得提倡,但是,仍不能阻绝个人凭借私力追求基本正义的合法途径。过度限缩公民反击不法侵害的权限,则必然会不当地压缩公民的权力空间,不利于人权的保障,尤其是在国家难以及时保全个人利益的紧急情况之下,容易导致个人合法权益蒙受不必要的损害,也不利于对法秩序的捍卫。对于既成事实而言,所有的事后惩戒措施都于事无补,只有实现正当防卫理念和规范的“松绑”,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制度效益。总之,现代正当防卫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不能全盘否定或彻底丢弃古代刑法,而须汲取其中有益成分古为今用,以古人实践之得失,指引与警示今日之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