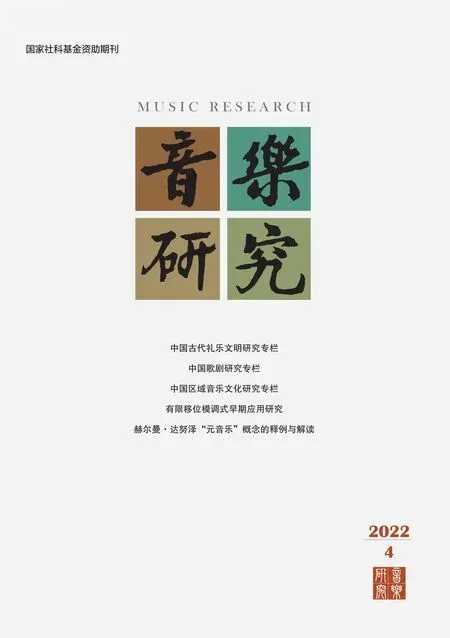区域音乐史编纂的方法与方向
文◎赵仲明
自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中国台湾音乐学家许常惠《台中县音乐发展史》《台湾音乐史初稿》问世,区域音乐史研究便持续升温。与整体史相比,区域史的研究注重特定空间的“小传统”“小历史”,不仅将区域史置于整体史的视野和框架内进行审视,同时更加重视对地方文献史料的搜集和利用。通过对趋异性与趋同性,区域史与整体史的理性观照,呈现出了区域音乐史的“活化”研究。然而,区域音乐史研究者的史学观念、方法论取向,以及历史书写中的问题意识、叙事方法等,仍然有待学界深入探讨。
一、区域音乐史编纂的文献史料
现有多部区域音乐史编纂的文献史料,大部分来自官方修编的地方志书,如各时期的省、州、府、县志和学校的音乐教材,以及近现代官方报刊的相关报道等。梁启超言“最古之史,实为方志”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356 页。。但“志”与“史”有所不同:“志者,一方之史;史者,天下之志”,“志有褒无贬,史有褒有贬”。②在中国史学史上,明清诸多史家均对“志”和“史”的关系有过诠释。明人李东阳主张“志,史类也”,“大则史,小则志,兼行而互证也”;清人杨佐国认为“志为史之余”;王棻认为“志为史之支流”;金鈜则认为“志者,一方之史;史者,天下之志”;吴美秀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史志所记必有善而有恶,志之所记有美而无刺,有善而无恶”“志有褒无贬,修志难于修史”。所谓“褒贬”,正是历史与历史学的重要区别——“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③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 页。
严格地说,将方志记载、学校音乐教材、报刊报道的相关音乐事象进行罗列,尚不能称其为音乐史或音乐史学。区域史既不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更不是相对于国家史而存在的一种地方性历史研究模式。虽然当地人做当地史,“弘扬心态”(陈春声语④陈春声《从地方史到区域史——关于潮学研究课题与方法的思考》,载《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文集》(2004 年8 月,山西太原),第110—126 页。)在所难免,区域史(或地方史)做得越细,越容易发掘出鲜为人知的史事;但是,如果缺乏史学理论和史学评判,便不能正确观照和处理国家典章制度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不能有效甄别和剔除方志记载中较为夸张或不实的描述,以致所谓的“地方特点”便有可能在史学研究中沦为自说自话的“假问题”。
将区域史视为地方志,并用修编地方志的方法进行区域史研究也并非良策。许常惠《台中县音乐发展史》《台湾音乐史初稿》等专著,在中国音乐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其著“志”的成分明显多于“史”的书写。何昌林当年曾经指出,其一部分属于“志”与“史”的历史书写问题,另一部分则属于国家典章制度与地方性知识的关系问题。⑤何昌林《许常惠的〈台湾音乐史初稿〉》,《音乐研究》1994 年第2 期。
事实上,区域音乐史编纂的文献史料,除各级政府编修的志书和官方公开发布的报刊报道之外,散见于民间的各类文人著述(包括回忆录、口述史),以及既不属于传统意义和官方认可的“高文化”的大众音乐事象,也是极为鲜活和珍贵的文献史料。以云南近现代史上志书无载、但在云南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实践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些音乐人物为例,他们的音乐活动更需要音乐史学家钩沉发微,探赜索隐。以“国立艺专”为例,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2014 年9 月11 日公布、晋宁区人民政府所立“中国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旧址纪念碑记”记载:
国立艺专在抗日烽火中辗转流离,一九三九年,陆续抵达昆明,迁原呈贡县(现晋宁县)安江村,借地藏寺、玉皇阁为校址,教学不辍。课余深入民间,宣传抗战,播送美育种子;并由学生刘鸿逵等人举办安江民众夜校,免费教育当地失学儿童。居民称之为“国立艺术大学”,传颂该校给安江四乡带来了“灵气”。⑥1939 年“国立艺专”抵达昆明,借昆华中学、昆华小学校舍,因陋就简,招生上课。因空袭日繁,1939 年夏,迁至晋宁县安江村(现为昆明市晋宁区)。
又如,作家老舍1941 年在散文《滇行短记》中对古琴演奏家查阜西的记录:
在龙泉村,听到了古琴。……绿荫下,一案数椅,彭先生⑦此处的“彭先生”,疑为古琴家彭祉卿(1891—1944)。弹琴,查先生吹箫;然后,查先生独奏大琴。……查阜西先生精于古乐。虽然他与我是新识,却一见如故,他的音乐好,为人也好。他有时候也作点诗——即使不作诗,我也要称他为诗人呵!与他同院住的是陈梦家先生夫妇,梦家现在正研究甲骨文。他的夫人,会几种外国语言,也长于音乐,正和查先生学习古琴。⑧老舍著,傅光明选编《老舍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年版,第85 页。另,关于查阜西在昆明的音乐事迹,又见严晓星《在昆明追寻查阜西先生的遗迹》,参见网站:http://m.thepaper.cn/rss_newsDetail_15869569?(2021 年12 月18 日)。
再比如,钢琴家傅聪常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忘不了许多甘苦与共的友人,忘不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皆因1948—1951 年他随其父傅雷在昆明生活期间与当地众多音乐爱好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音乐才华和参与的音乐活动,同样也给昆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傅雷先生到昆明后,从朋友处得知我的同学童永和家有钢琴,便带着傅聪拜望了她父母,希望能让傅聪到她家练琴……1949 年至1950 年间,昆明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常在锡安圣堂和万钟教堂举行音乐会,傅聪总是既独奏又伴奏。1949 年底昆明解放后,成立了昆明市委文工团。这伙音乐朋友又筹建了红旗管弦乐队,由叶俊松先生任指挥,曾祥华任首席小提琴⑨叶俊松、曾祥华后分别担任云南艺术学院的钢琴教授和小提琴教授。,演出颇为频繁。这些活动,傅聪也都积极参与。⑩姚曼华《少年傅聪在云南》,《钢琴艺术》2004 年第1 期,第23—25 页。
切莫说仅凭这些史料(甚至是较为感性的只言片语)并不能成为理性的音乐史。然而,历史学著述无一不是历史学家根据点点滴滴史料的理性和逻辑判断构建而成的。严肃的史学研究和历史编纂,也正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史料基础之上(甚至是在史料的字里行间),深入地对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展开研究,并在长时段的多种史料相互印证、相互比较中梳理出来。如果说,云南近现代的音乐历史(从总体上看),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民族民间音乐与专业音乐教育的交响画卷;那么,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里,云南最早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昆明担任“两级师范学校音乐教员兼省垣各学校音乐史地教习”并在云南最早推广学堂乐歌的李燮羲⑪根据《新纂云南通志续编(稿本)·李燮羲传》及《大理县志》所载:李燮羲,字开一,号剑虹,云南太和(大理)人,生于1875 年(清光绪元年乙亥)。1904 年(甲辰)东渡日本,在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音乐。1907 年(丁未)加入同盟会。1908 年因回国奔父丧,在昆明任两级师范学校音乐教员兼省垣各学校音乐史地教习,1926 年病逝于大理,享年51 岁。著有音乐文论、歌曲、教材,创办过音乐期刊。1929 年,革命军事新闻社出版了李燮义创作的歌曲集《雪耻唱歌集》,由于佑任题词。,以及受国立艺专“灵气”影响,1938 年考入昆华艺术师范学校,1941 年又考入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并走上专业音乐道路的哈尼族音乐学家杨放教授,他们是对云南民族民间音乐搜集整理、音乐创作、音乐教育等方面产生过影响的云南本土音乐学家,便是值得梳理和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
同样的,大师云集西南联大八年(1938—1946)期间,内地对云南的音乐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比如,马思聪对云南的小提琴普及和演奏教学;李凌、赵沨所发起的云南的新音乐运动和群众歌咏活动;傅聪对云南的钢琴普及和演奏教学。甚至近40 年来云南的琴学研究,以及由云南已故琴家金治中(1948—2007)创办的滇晖琴社和泓州古琴院等,也与吴钊有诸多联系。⑫金治中生前与吴钊来往甚密。从70 年代末起,吴钊每去昆明或金治中每到北京,二人必相约晤面切磋琴学技艺。由此可见,区域音乐史编纂,本质上即是在反向思维与相向思维的辩证统一中,将区域史置于整体史的考察中“以小见大”并与整体史相互呼应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二、区域音乐史编纂的方法论
阶级、战争、政权更迭,以及民族认同等,均是历史编纂和史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但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则属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范畴。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学界的认识已发生较大改变。江应樑指出:“我们着眼于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不为历史上的暂时分裂现象所左右”⑬江应樑主编《中国民族史》(中),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第7 页。。对音乐史的认知也是如此,唐德宗贞元十六年轰动朝野、影响巨大的云南《南诏奉圣乐》进献长安一事,便是较为典型的一例。⑭白居易曾在《蛮子期——刺将骄而相备位也》有所言及(《全唐诗》卷426,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4697 页);元稹也在《蛮子期》中有诗记述该事(《全唐诗》卷453,第4626—4632 页)。虽然这部规模宏大的乐舞作品究竟出自谁人之手,《旧唐书》和《新唐书》各执一词;⑮《旧唐书·音乐志》载:“贞元十六年正月,南诏异牟寻作《奉圣乐舞》,因韦皋以进。十八年正月,骠国王来献本国乐”(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1053 页);《新唐书·礼乐志》载:“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480 页)。南诏的统一和兴盛,以及南诏与唐王朝、与吐蕃的交往史上都曾分分合合,争战不断;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唐王朝和南诏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研究。仅从文献对《南诏奉圣乐》所用乐器、乐调、结构、舞蹈语汇,以及演员服装的描述上看,唐王朝与南诏长期交融,并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诸多事例便一目了然。比如,其兼具雅乐大曲和俗乐大曲的唐代宴飨礼乐的结构体制和乐舞形态;对龟兹部、胡部乐器的大量使用,以及唐代盛行的字舞形式——“舞‘南’字,歌《圣主无为化》;舞‘诏’字,歌《南诏朝天乐》;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圣’字,歌《雨露覃无外》;舞‘乐’字,歌《辟土丁零塞》”。但“舞人服南诏衣,绛裙襦、黑头囊、金佉苴、画皮鞾、首饰袜额、冠金宝花鬉、襦上复加画半臂”,“歌《天南滇越俗》四章”……以表达南诏对唐王朝“誓为汉臣,永不离贰”⑯此语出自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南诏王异牟寻与唐使在大理苍山中和峰南麓神祠举行“苍山会盟”时的誓词。之心。
事实上,“南诏”本身就是一个崛起于云南,由“魁雄六诏”(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组成的多民族共同体。⑰《旧唐书·南蛮传》:“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新唐书·南蛮传》:“夷语王为诏……蒙舍诏在诸南部,故称南诏。”鼎盛时期,南诏的疆域几乎覆盖云南全境,东南到达安南(今之越南),西北连接吐蕃(今之西藏),南面和女王国(今之泰国北部南奔)接界,西南和骠国(今之缅甸中南部曼德勒)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之贵州、四川长江南岸)。如果再往前追溯,先秦时期的百越、氐羌、百濮三大族群及其相互间的交往、交融,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南诏的音乐文化产生影响,或者说南诏的音乐文化与百越、氐羌、百濮三大族群是否有着某些联系?
考古学界把夏商周合称为青铜时代。然而,“云南青铜时代文化分布在全省70多个市县,共约200 多个地点,出土青铜器总数在万件以上”⑱云南省博物馆《十年来云南文物考古新发现及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第6 页。,甚至在目前铜鼓研究的八个分类里,云南铜鼓就占六个类型。从公元前12 世纪开始,由洱海地区发源,到公元前3—1 世纪在滇池地区达到鼎盛阶段,公元1 世纪衰败并进入铁器时代。整个青铜时代绵延千余年,成为灿烂的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人们不禁要问,古代云南何以产生如此辉煌璀璨的青铜文化?对此,考古学界得出的结论是:云南自古至今都是我国铜、锡、铅矿的主要产区,黄河中下游自古至今反而没有锡矿。因此,不仅石寨山铜鼓、贮贝器和广南鼓等云南古代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本省,⑲李晓岑等《云南早期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证》,《考古》1992 年第5 期。而且中原高度发达的殷商青铜文化,也注入了云南的“血脉”(矿料)——考古学家对商代妇好墓出土的91 件青铜器进行铅同位素比值测定,其中73%的青铜是铜锡二元合金,即锡青铜,27%是铜锡铅三元合金。测定结果表明:妇好墓中的大部分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省永善县金沙厂。事实上,云南富含铜、锡、铅、银、锌矿藏的地区并不只永善一地。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楚雄万家坝,以及牟定、祥云、昌宁等地出土大量青铜乐器(铜鼓、钟、羊角钮钟、编钟、铃、锣、钹等)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在对云南青铜器乃至在音乐史的研究中,有的学者仅仅关注云南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却忽视了汉文化深入古滇国以前,百濮、百越、氐羌三大族群已经在文化艺术上产生了交融。近年来,艺术人类学打破学科壁垒,走向学科交叉,同时秉承文化整体观,坚持世界意识的研究,对于区域音乐史的编纂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艺术学界在讨论中华艺术的民族性时,已经整体上超越了以单一民族为中心的艺术史观;艺术学理论及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门类艺术研究领域,均已经建立各民族艺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中华艺术多元一体格局观念,并从各自的学科视角阐发对民族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理认同。
汉族艺术与少数民族艺术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同化与被同化的关系,而是彼此欣赏、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关系。⑳李世武《多民族艺术“三维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4 期,第157、161 页。
显而易见,文化融合理论之所以能取代文化同化理论,皆因文化同化理论不能准确地揭示不同文化群体相互接触后双方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发生转变的过程。而对转变过程的研究,恰恰是历史科学的重要范畴。只不过,我们需要与之相适应且合乎研究实际的理论。在史学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突破,都以理论和理论创新为前提。“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㉑㉑ 于沛《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3 期,第5 页。㉒〔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 页。㉓ 参见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6 年第3 期。“历史学本质(性质)上是一种研究,是一种探讨,是要把一类事物弄明白。”㉒㉑ 于沛《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3 期,第5 页。㉒〔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 页。㉓ 参见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6 年第3 期。音乐史的研究与编纂也概莫能外。
三、区域音乐史的史学叙事
有人说history 的构词法是his 和story的合成,倘若果真如此,那么story 讲什么和怎么讲便是不能回避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问题。西方史学界(包括音乐史学界)对“史学叙事”的关注和研究无须赘言。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美国史学家怀特把盖伊“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琐碎的,而没有叙事的历史分析则是欠缺的”改写成了“历史叙事无分析则空,历史分析无叙事则盲”等均是例证。㉓㉑ 于沛《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史学理论研究》2000 年第3 期,第5 页。㉒〔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0 页。㉓ 参见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6 年第3 期。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海内外拥有大量读者,皆因他既秉承了“大历史观”的治史传统,同时还潜心研究史学叙事的结构与方法,以致笔下“无关紧要的”且“平平淡淡的一年”㉔㉔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2 页。㉕ 杨燕迪《音乐史写作:历史与艺术的调解——对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的深度书评》,《音乐艺术》2007 年第1 期。㉖ 黄宗权《“穿透”古典音乐风格迷雾的智慧之光——评〈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音乐研究》2017 年第1 期,第97 页。,也如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汉学家史景迁和卫思韩合著的《从明到清:17世纪的征服、区域与延续》(From Ming to Qing:Conquest,Region,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明确指出跨越明清两朝的长期连续性是客观存在,从而揭示了中国古代史以往按皇帝和朝代进行历史编纂最常见的“不唐不宋”“不明不清”“不清不明”的弊端。
无独有偶,欧美音乐史学界类似的优秀著作也有不少,仅以近40 年的代表作为例,德国音乐学家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1928—1989)的《音乐史学原理》(Foundations of Music History)和同样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的美国音乐学家罗森(Charles Rosen,1927—2012)的《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The Classical Style:Haydn, Mozart, Beethoven), 便 是值得中国音乐史学界思考和研究的杰作。杨燕迪曾针对达尔豪斯《十九世纪音乐》指出:“依照一般的看法,音乐的历史,无非就是音乐发展历程的记录与解说,人物、作品的编年整理,风格、流派的脉络爬梳,外加时代精神、思想氛围以及社会建制等方面的编织架构”,但“写作艺术史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企图,写成历史的只是艺术中那些根本不是艺术的方面”。㉕㉔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2 页。㉕ 杨燕迪《音乐史写作:历史与艺术的调解——对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的深度书评》,《音乐艺术》2007 年第1 期。㉖ 黄宗权《“穿透”古典音乐风格迷雾的智慧之光——评〈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音乐研究》2017 年第1 期,第97 页。他对达尔豪斯提出的“结构性的音乐历史”高度评价,赞誉有加。关于罗森的《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黄宗权也在书评里称:“首先,罗森以考察语言的视角来看待风格……其次,罗森另外一个看待风格的视角,显示了他‘形式论者’的立场。在进一步讨论风格问题之前,罗森就先行反对了常见的、把音乐的表现特征和风格建立关联的看法。那些认为古典主义风格是优雅的、浪漫主义风格是热情或忧郁的等等,在罗森看来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他坚定地认为风格和音乐的表现特征无关。”㉖㉔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14 年版,第2 页。㉕ 杨燕迪《音乐史写作:历史与艺术的调解——对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的深度书评》,《音乐艺术》2007 年第1 期。㉖ 黄宗权《“穿透”古典音乐风格迷雾的智慧之光——评〈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音乐研究》2017 年第1 期,第97 页。
然而,迄今所见的部分区域音乐史、专题史、少数民族音乐通史的编纂和史学叙事,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就编纂方法而言,被动关联型、史料汇编型、条目注释型的著作仍较常见。被动关联型,即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地方政府的响应,进行区域社会(或族群社会)音乐事象的碎片化被动关联,用后者为前者做注疏。史料汇编型,即区域史料(或地方史料)细碎化堆积,缺失区域史与整体史的内在关联。条目注释型,即将区域社会(或族群社会)的音乐事象进行辞书式条目罗列并逐一加以注释。其结果,区域音乐史的研究主体——鲜活、丰富,但源流、形态、文化及社会功能错综复杂的地方民间音乐,变得味同嚼蜡,平淡无奇。
比如云南,从最早的“西南夷”“爨蛮”,到唐代以后的“南蛮”,云南一直是“蛮夷”聚居的主要区域。明代后期,随着外来汉人的大量迁入,并与“西南夷”在数百年的不断交流,最终才融合为“云南人”,以及由古滇青铜文化、南诏文化、贝叶文化、东巴文化等共同构建的云南文化。云南文化的多样性存在,既是对华夏民族的认同,也是云南各民族的相互认同。而这种彼此欣赏、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双向认同,正是云南音乐史研究和编纂的重要基础。此外,距今170 万年的元谋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沧源崖画;战国至秦汉时期形形色色的青铜乐器,以及遍布云南城乡村镇林林总总的儒、释、道、伊斯兰和本地信仰的寺观庙宇;横断山脉纵谷深处、湄公河上游崇山峻岭中大大小小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等丰富的考古发现和文化遗存,也为研究云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音乐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但另一方面,云南既有得天独厚的物产,也有云南人自给自足的狭隘。20 世纪50—60 年代早期,随着中央人民政府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以云南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电影陆续上映,一大批以云南少数民族民歌为素材创作改编的电影歌曲迅即在全国传唱。但当时的云南,在很大程度上还仅只是一个供内地作曲家“淘金”的音乐素材基地,真正出自云南本土作曲家并能够在全国产生影响的音乐作品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直至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云南本土作曲家、表演艺术家和在“五大集成”搜集、整理、编纂中历练出来的本土音乐学家才崭露头角,脱颖而出。但与此同时,英国民族音乐学家李海伦(Helen Rees)客居云南多年,完成了她的《历史的回声——当代中国纳西音乐》(Echoes of History:Naxi Music in Modern China)博士论文;田丰无奈的爱恨情仇、《小河淌水》著作权对簿公堂、“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等“事件”,却不绝于耳并成为云南音乐史研究与编纂不能回避的话题。皆因“历史学所研究的,一是人性所扫描的轨迹,二是历史学本身……并不是有了活生生的历史,就会有活生生的历史学;而是只有有了活生生的历史学,然后才会有活生生的历史。”㉗㉗ 同注③,第10 页。㉘ 参见王尔敏《史学方法》,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135 页。㉙ 同注①,第107 页。正因如此,“活生生的历史”,既是治“史”和修“志”不能等同的关键所在,也是音乐史学“去伪存真,秉笔直书”的学术担当。然而,所有这些史事如何才能通过音乐史学家的史料拓展和史料裁断,㉘㉗ 同注③,第10 页。㉘ 参见王尔敏《史学方法》,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135 页。㉙ 同注①,第107 页。鞭辟入里,洞见古今,并呈现出严肃的历史编纂和新颖的史学叙事,仍然值得有志于区域音乐史研究的同仁共勉。恰如梁启超在其扛鼎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的那样——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然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是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较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惝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㉙㉗ 同注③,第10 页。㉘ 参见王尔敏《史学方法》,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135 页。㉙ 同注①,第107 页。
——评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