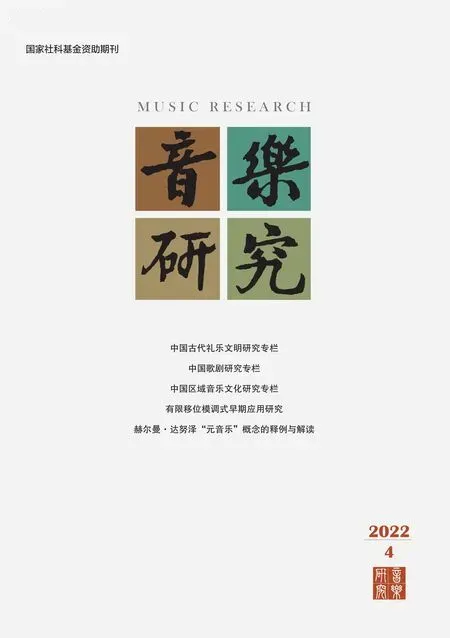论民族歌剧板腔体咏叹调创作的传承与发展
文◎居其宏
在民族歌剧音乐创作中,向我国传统板腔体戏曲学习,运用板腔体思维和结构创作主要人物的核心咏叹调,是从《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到《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剧目一以贯之的成功经验。近年来,特别是2017年文旅部设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以来,板腔体咏叹调创作便在业内同行中成为热门话题,引发颇多争议。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如何科学认识板腔体结构的戏剧性表现力?板腔体咏叹调是民族歌剧创作的必备项吗?如何在传承前辈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剧目不同情节、不同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和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在板腔体咏叹调创作中加以发展和创新?
本文将就上述诸问题阐发若干个人浅见,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一、传统戏曲与民族歌剧之“板腔体”释义
就我国传统戏曲音乐的戏剧性展开方式而言,有两大体系。其一,是曲牌联缀体,即以多个现成的曲牌作为基本的结构单位,将若干不同的曲牌联缀成套,构成一出戏或一折戏的音乐,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简称“曲牌体”,又称“联曲体”,代表性剧种为昆曲。其二,是本文要重点研究的“板腔体”,即通过不同速度的板式及其组合,构成大段成套唱腔,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又称“板式变化体”,代表性剧种为京剧和北方梆子。其实,在戏曲音乐中,“板腔体”有两层含义:一曰“板”,二曰“腔”。
(一)戏曲“板腔体”中的“板”
“板”,即板式。不同的板式有不同的速度,其中一些板式与西方音乐某些速度概念有共通之处:如一板三眼的慢板,可与西方音乐的拍相通;一板一眼的中板,可与西方音乐的拍相通;等等。但也有一些特殊板式在西方音乐中很难找到对应物。如有板无眼的垛板和无板无眼的散板:垛板虽可用拍标记,但在西方音乐中极少见到;散板并非任由演员随心所欲、自由处理,它的松紧、快慢、张弛等均有其内在节律所规定,演员的演唱要诀是“形散神不散”。
上述几个常规板式,都只涉及歌唱声部。此外,还有两种为我国戏曲音乐所独有、别具情感表现张力,又涉及歌唱和伴奏的板式——“摇板”和“清板”。“摇板”的特点是歌唱声部是散板,而伴奏声部却是有板无眼的垛板,系由两者纵向叠加而成;歌唱者既要深谙散板和垛板的各自演唱特点,更要将散板的自由节奏、换气、落拍,与垛板有规律的紧张节拍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唱出摇板的精气神来。“清板”常见于越剧音乐中,其特点是人物歌唱时乐队整体上停奏,只以轻击拍板(或称“手板”“响板”)与板鼓为歌唱声部伴奏,故称“滴笃板”;人物近乎清唱,为的是让观众能毫无干扰地听清人物的倾诉。
话说至此,就有必要厘清下列概念——我国板式联缀体戏曲中的“板”,既是速度概念,又是结构概念,是速度与结构融于一体的复合概念;所谓“板式变化体”,指的是由不同速度的板式为独立结构单元,并视剧情发展和人物情感抒发需要将这些结构单元组合起来,通过它们之间的有机连接与转换,共同构成一个层次丰富、对比鲜明、变化多端的完整大结构;因此,这个结构样式,正是西方曲式学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大体量、复合型曲式。
(二)戏曲“板腔体”中的“腔”
“腔”,即声腔,或腔调,或曲调,系旋律概念。板腔体戏曲中的声腔,与不同剧种的方言土语有极为紧密的联系,或者说,包括戏曲音乐和民歌、说唱、民间器乐在内的所有声腔或旋律,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当地方言土语之自然音律的艺术化提炼与升华。于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板腔体戏曲中的声腔,其地域和风格的规定性极强。板腔体戏曲中的声腔,以对称的上下句为基本单位,在此基础上,根据剧情和人物情感抒发需要,通过变形、拉宽、展衍、紧缩、简化、调式转换等灵活多变的发展手法,与若干个不同速度的板式有机组合,由此派生出大段成套唱腔,用以表达剧中人复杂的心理状态和情感诉求。
(三)民族歌剧板腔体咏叹调中的“板”与“腔”
民族歌剧板腔体咏叹调的板式,全面继承了板腔体戏曲的板式体系,并视剧情和人物在特定戏剧情境下的特定情感倾诉和心理抒发的需要,对散板、慢板、中板、快板、摇板、垛板等常规板式进行灵活组合,构成层次丰富的结构序列。
民族歌剧板腔体咏叹调的声腔,一般取自传统戏曲的旋律素材并做加工、提炼和专业化编创,将它转化为民族歌剧的唱腔和旋律。这种专业化创编赋予作曲家的使命是,一方面要保持住原有声腔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另一方面则要使旋律“既熟悉,又新鲜”。
当然,也有另一种发展与创新——由于民族歌剧板腔体咏叹调多用更具广泛群众基础的普通话演唱,故与传统戏曲声腔植根于特定地方语言不同,它的声腔或旋律素材具有更为多样的收纳性,既可在某一种地方剧种声腔基础上发展,又可吸纳多种地方剧种的声腔素材加以融合和创新,以在超越地方性的国家层面上彰显民族风格和中国神韵。
二、板腔体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中的奠基与完型
在我国歌剧音乐创作领域,首次提出向板腔体戏曲学习的作曲家是马可。其代表作《夫妻识字》和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的音乐创作,与陕北民歌和戏曲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马可从创作《白毛女》开始,一直到《小二黑结婚》,就已充分注意到我国民族歌剧的音乐创作仅仅向民歌学习已经远远不够了。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在新歌剧的创作中应该向民族音乐传统学习,但主要是吸收民歌,而不必或不一定去吸收戏曲音乐,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也能在我们的作品中渲染一些民族的色彩,虽然在某些场合中也相当地发挥了民歌抒情的特长,但从整个戏剧音乐的结构来说,从更深刻地表现人物性格与丰富的戏剧节奏等方面来说,民歌就显得贫弱无力了。①马可《在新歌剧探索的道路上——歌剧〈小二黑结婚〉的创作经验》,《人民音乐》1954 年第1 期。
为此他认为,一定要向戏曲音乐学习,特别是向板腔体戏曲学习,并指出:
至少它通过板眼的节奏变化而显示出来的表现戏剧进展或感情变化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在新歌剧的创作中采用的;戏曲唱腔中的许多拖腔、装饰音的进行、调式转换等方法,具有亲切的民族特色,也是在外国歌剧中少见的。如果我们的眼睛首先去看戏曲音乐的这些积极方面,就会觉得它是一种宝藏而不是负担。②马可《新歌剧也要百花齐放》,载《新歌剧问题讨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 年版,第187 页。
马可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创作实践中做了可贵的探索。在《白毛女》中,杨白劳唱段《老天杀人不眨眼》、喜儿唱段《我要活》,虽然还仅仅是板腔体的雏形,但已初见端倪。而喜儿流传至今、百唱不厌、百听不厌的板腔体咏叹调《恨似高山仇似海》,则是马可在20 世纪60 年代初修改定型的。
首演于1953 年初的《小二黑结婚》,对板腔体咏叹调的运用有着典范性表现。此剧的音乐创作,除了在民歌音调基础上新创优美动听的抒情短歌之外,继承和发展板腔体戏曲的音乐戏剧性思维,用板腔体结构创作主要人物核心咏叹调,成为最重大的创新点之一。其中,最突出、最成功的一例,是小芹的板腔体咏叹调《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通过散板—慢板—快板—散板之间的流畅连接和鲜明对比,形成篇幅长大、层次众多的大结构,来刻画人物心理状态的丰富层次及其复杂转换。
由此可见,民族歌剧音乐创作向戏曲学习,运用多个不同速度的板式及其自然转接,来抒发人物内心情感和复杂心理的重大发明,发端于《白毛女》,完型于《小二黑结婚》。
三、板腔体在既往民族歌剧中的传承与发展
民族歌剧板腔体咏叹调创作,从《白毛女》的雏形,到《小二黑结婚》的完型,在短短数年间即告完成,并显示出强大的戏剧性张力和惊人的艺术魅力,深受业内同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此后相继创演的《红霞》《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剧目,在一如既往地重视抒情短歌、谣唱曲、宣叙调、合唱创作的同时,更加重视传承和发展《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的成功经验,运用板式变化体结构创作主要人物的核心咏叹调。
(一)对板式变化体的传承
先看这一时期民族歌剧对板式变化体的传承。紧接在《小二黑结婚》之后,受其影响和启发,运用板式变化体结构创作主要人物核心咏叹调的,有下列几部重要的民族歌剧(按首演时序排列)。
其一,是中央实验歌剧院创制的新版《刘胡兰》(陈紫等作曲,首演于1954 年10月)中第一主人公胡兰子的著名咏叹调《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是由散板—慢板—中板—快板—散板共5 个段落构成的大段成套唱腔。
其二,是前线歌剧团创制的《红霞》(张锐作曲,首演于1957 年9 月)中第一主人公红霞的著名咏叹调《凤凰岭上祝红军》,通过散板—快板(分节歌)—垛板—散板结构,抒发了红霞将敌人带上凤凰岭时,完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一心祝愿红军把苦难的人民都解放的英雄情怀。
其三,是著名的民族歌剧经典《洪湖赤卫队》(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首演于1959 年秋),剧中共有三首板式变化体咏叹调,即韩英的咏叹调《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慢板—中板—稍快的中板—慢板—快板—散板)和《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慢板—中板—快板—散板—中板分节歌—散板),以及刘闯的咏叹调《大雁南飞》(散板—快板—散板)。
其四,是民族歌剧《红珊瑚》(王锡仁、胡士平作曲,首演于1960 年8 月)中第一主人公珊妹的板腔体咏叹调《海风阵阵愁煞人》,以及另一首核心唱段《渔家女要做好儿男》。
其五,是民族歌剧经典《江姐》(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首演于1964 年9 月),剧中第一主人公江姐有三首板腔体咏叹调,即《革命到底志如钢》(其板式结构更复杂,留待下文再谈),《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奉献》(慢板—中板—清板—摇板—垛板—快板—慢板—散板)和《五洲人民齐欢笑》(散板—慢板—快板—清板—散板—垛板—散板)。
其六,是民族歌剧经典《党的女儿》(王祖皆、张卓娅等作曲,首演于1991 年11月)。其中,田玉梅的两首咏叹调《血里火里又还魂》(散板—中板—快板—散板)和《万里春色满家园》(散板—中板—快板—散板)。
以上这些著名的咏叹调,都是作曲家继承传统戏曲板式变化体结构写成的,而这种独特的咏叹调结构,在西方歌剧或中国正歌剧的咏叹调创作中从未有过。其丰富的情感、复杂的层次和强大的戏剧表现力,丝毫不亚于运用西方既有曲式创作的任何一首咏叹调。
(二)对板式变化体的发展
再看这一时期民族歌剧对板式变化体的发展。首先,戏曲板式变化体唱段及此前《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的板腔体咏叹调,每个板式的基本声腔都是上下句;而从《红霞》的咏叹调《凤凰岭上祝红军》及《洪湖》中韩英《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开始,则将分节歌作为一个独立结构导入板式变化体,从而将传统板式的上下句扩充为起承转合结构,并通过分节歌的多段反复增加咏叹调的戏剧含量。此后,《党的女儿》中田玉梅咏叹调《万里春色满家园》,《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咏叹调《不能尽孝愧对娘》和杨母咏叹调《娘在那片云彩里》等,均在板式变化体结构中导入分节歌,且在艺术处理上更加自然和成熟。这就是对于板式变化体结构的发展和创新。
此前的民族歌剧在创作主人公核心咏叹调时,总是从戏曲音乐中学习、运用板腔体思维和板式变化体结构,以适应人物复杂情感和心理变换的表现需要。但无论是《小二黑结婚》的《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白毛女》增写的《恨似高山仇似海》,抑或是《红霞》中《凤凰岭上祝红军》,都有以下两个共同特点:其一,尽管板式组合顺序和相互转接关系各有不同,但都是以上下句为基本结构单元的纯粹板式变化体结构;其二,这些核心咏叹调都是抒情主人公一唱到底的独唱形式。
《江姐》的《革命到底志如钢》恰恰在这两点上突破了上述范式。其一,在这首咏叹调中,作曲家根据具体戏剧情境和人物情感抒发的表现需要,较完整地引进主题歌《红梅赞》,使之成为全曲结构既不可或缺也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从而极大地拓展了这首咏叹调的表现空间;而《红梅赞》恰恰是运用起承转合原则而不是上下句结构写成的。就这一点而论,江姐这首咏叹调与韩英咏叹调《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中引进分节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都是对于民族歌剧传统范式的突破。其二,从演唱形式和声部组合样态看,这首咏叹调的《红梅赞》部分是江姐内心意识的外化,由男高音以江姐丈夫彭松涛画外音的形式唱出,从而与抒情主人公的女高音音色构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作曲家还别具匠心地将川剧帮腔手法运用到咏叹调中,并将川剧传统帮腔的单声部形式改为更为专业化混声合唱,借此构成女声独唱咏叹调与混声合唱的重要对比。这两种演唱形式(男高音独唱与混声合唱)及其所营造的三种音色和声部组合样态的鲜明对比,成为全曲结构既不可或缺也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因此极大地丰富了咏叹调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当然同样也是对于民族歌剧传统范式的突破。
《革命到底志如钢》在上述两点上的突破,是我国民族歌剧音乐创作发展到20 世纪60 年代中前期的重要收获,为进一步向传统戏曲学习,丰富和深化板腔体咏叹调写作,拓展和增强其艺术表现力提供了新鲜经验。此后,在《党的女儿》第六场《柔弱一生壮烈死》和《危机就要到眼前》中,作曲家将这种传统手法用得灵活自如。
(三)对传统声腔素材的传承与发展
民族歌剧板腔体咏叹调的旋律素材,与我国各地的戏曲地方剧种、民歌、说唱有着极为直接的血缘关系,或者说,如今被业内同行和广大观众口口相传、百听不厌的那些板腔体咏叹调的优美旋律,不独是民族歌剧作曲家自觉传承我国民间音乐和传统声腔的产物,更是在学习民间传统的基础上,运用专业化作曲理论与技术,苦心孤诣地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艺术结晶。
(4)细嚼慢咽,口味清淡。因为工作或者学习的原因,为了赶时间,很多人吃饭都是狼吞虎咽。到了晚餐,时间充裕,不妨把速度慢下来,细嚼慢咽。这样不仅可以让食物更容易消化吸收,减轻肠胃的工作负担,而且更容易吃饱,减少食物的过量摄入。
我们看到,在民族歌剧板腔体咏叹调的声腔素材来源上,一般有如下几种思路。一是根据剧情、故事发生地,选择当地戏曲声腔为基本素材,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化的创编。如《白毛女》的咏叹调声腔,来源于眉户戏和陕北民歌音调。二是声腔选择的出发点并不是剧情和故事发生地,而是根据作曲家对声腔戏剧性表现力的认知和表现需要来决定。如《党的女儿》的故事,发生在江西中央苏区,但考虑到江西民歌缺乏戏剧性因素,故田玉梅板腔体咏叹调的声腔取自山西蒲剧。三是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剧种,而是广泛吸收本省多个地方剧种的声腔,在此基础上加以融合创新。如《洪湖赤卫队》,就汲取了楚剧、汉剧和湖北天(天门)沔(沔阳)地区的花鼓戏,以及天沔、潜江一带民间音乐的素材。四是声腔的跨省份融合,如《小二黑结婚》的声腔素材来源是“三梆一落”。“三梆”即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一落”即评剧,俗称“莲花落”。五是声腔素材的大跨度融合,如《江姐》不但采用故事发生地四川的民歌、清音、川剧高腔等民歌和戏曲声腔,还有杭州滩簧、苏州评弹、浙江婺剧等江浙一带戏曲和说唱音乐的音调,听来和谐统一且毫无违和感,可见作曲家对旋律进行糅合创新的功夫之深厚。
(四)《野火春风斗古城》板腔体咏叹调的两个突破
民族歌剧《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母咏叹调《娘在那片云彩里》,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采集、化用和旋律创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实例。
过去的民族歌剧核心咏叹调,其戏剧性对比,主要发生在不同板式和速度变化之间;也就是说,其音乐展开的戏剧性,主要是通过板式转换和速度对比实现的。在每一板式内部,其旋律形态及其运行状态,基本上都着眼于歌唱性和抒情性,旋律蜿蜒曲折,多以级进和四五度跳进为主,六度以上的大跳并不为多,八度大跳则比较罕见。而《娘在那片云彩里》则除了板式和速度变化之外,还充分运用乐句内部的音程大跳来形成强烈的戏剧性对比。这方面的例子在此曲中随处可见;此曲最后一个八度大跳,居然发生在清角音上,最后从清角音直接导向高八度的徴音,并以此作结,这样的花腔音调进行,如此高度声乐化和强烈戏剧性的唱段结尾,非但在此前的民族歌剧咏叹调中从未有过,且其独特性与它的音调原型已呈远距离相关,给人以不同凡响、新意充盈的听觉震撼。
综上所述,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历史,从继承发展的角度说,就是一部不断向传统戏曲学习、传承、创新的历史,其中诸多板腔体咏叹调一经演出便不胫而走、到处传唱,在数十年间已经成为脍炙人口、过耳不忘的美好听觉记忆。这就是民族歌剧板腔体咏叹调独有魅力的充分体现。
四、既往板腔体咏叹调创作的若干不足
既往的民族歌剧的板腔体咏叹调创作,曾产生过大批深切动人、至今仍在广为传唱的杰出板腔体咏叹调。但也不可否认,在马可提出民族歌剧应向板腔体戏曲学习的主张之后,也有少数作曲家及其板腔体咏叹调创作走过一些弯路,暴露出若干不足。
(一)“歌剧戏曲化”的理论与实践
“歌剧戏曲化”的主张是海政歌剧团在创作民族歌剧《红珊瑚》时提出来的,甚至在歌剧戏曲化的具体做法上还提出“宁可过头,不可不足”③胡士平《一次歌剧戏曲化的实践——歌剧〈红珊瑚〉创作回顾》,载《中国歌剧艺术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 年版,第282 页。的口号。必须指出,马可的“歌剧向戏曲学习”,与这里的“歌剧戏曲化”完全是两个概念,至于“宁可过头,不可不足”的做法,更是犯了“过犹不及”的大忌。虽然从《红珊瑚》的创演实践看,其整体还是成功的,但是也隐含着某些时代感不足、音乐和表演艺术语汇略显陈旧等问题。但在此后的民族歌剧创演中,某些剧目在追求“歌剧戏曲化”方面,的确出现戏曲化太过头、时代感严重不足的弊端,如在60 年代中期演出的《社长的女儿》——其唱腔与河南豫剧几乎没有差别。
(二)声腔“陈旧”问题
当然,民族歌剧对于戏曲音调和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运用和创编,如何突破观众对此长期形成的听觉记忆和感性经验,如何在保持民间素材如歌美质和风格统一性的基础上对之消化融合、赋予新意,令观众产生“既熟悉又陌生”“既传统又现代”“既好听又好记”的审美效应,确实是个难题。但在20 世纪的中国作曲家中,曾产生过马可、刘炽、李劫夫和于会泳等旋律大师,他们的共同经验便是对于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创造性化用。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我国民族歌剧在旋律铸造上的继承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作曲家对于民族民间音乐及其艺术精髓的深入了解和熟悉程度、高超的融汇化合功夫,以及旋律创新的深厚修养和出众才华。毫无疑问,这是长期积累、偶一得之的结果。
表面看来,声腔陈旧、新鲜感不足倾向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作曲家对民间音乐,特别是对戏曲音乐,学习有余而创新不足,继承有余而发展不足。其实,对所有民族歌剧的作曲家来说,无论是学习还是继承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遗产,掌握其规律、领悟其精髓,是毕生追求的目标,因此只能是永远在路上,而根本不存在什么“有余”问题。
真正成为问题的,笔者看有三:一是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和继承都不到位,远未达到精深的境界;二是对民族歌剧与传统戏曲的异与同认识模糊,从而容易将两者混为一谈;三是旋律创新的功夫不到家,故只能退而求其次,对音调原型照搬如仪或略做小幅变化。有如此三者,其音乐风格的整体不显陈旧才怪。
五、既不当守财奴,也不做败家子
当然,在当代民族歌剧音乐创作中,板腔体咏叹调是否系必备项?一旦运用了板腔体咏叹调,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复制和陈旧?在这些问题上,业内同行看法不一、争议很多,极为正常。对此,笔者的基本观点如下。
其一,从民族歌剧音乐创作的历史看,运用板腔体咏叹调来揭示主人公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和心理冲突,是民族歌剧音乐创作营造戏剧性、刻画人物音乐形象的重要法宝;从《白毛女》到《野火春风斗古城》,60 余年来,剧剧如此,无一例外。这里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这一点,有谁敢于否认吗?
其二,至于此后是否也必须“剧剧如此”?笔者以为倒也不必,不看剧目的实际情况,不做具体的艺术分析,就做如此僵硬的要求,这是典型的守财奴作风!正确的做法是,理应由作曲家视具体剧目的题材、情节和人物音乐形象塑造的需要而定。如《尘埃落定》写的是藏族题材,孟卫东就没有用板腔体咏叹调,同样非常成功;又如《沂蒙山》用了三首板腔体咏叹调,同样受到同行称赞、观众欢迎,有何不可?
其三,至于一旦运用板腔体,就必然导致复制和陈旧,只要听一听从《白毛女》到《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那些经典咏叹调,这个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即便近年来新创的某些板腔体咏叹调,偶有陈旧之感,那是作曲家在音调素材和旋律创作上未能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所致,与板腔体结构毫无关系。因为,按一般常识说,板腔体与西方曲式学中常见的三部曲式、变奏曲式、回旋曲式、奏鸣曲式等一样,都属曲式概念,与“陈旧”根本不沾边;按板式连缀体的特殊性说,板式不仅是曲式,而且与速度密切相关,因此是一个曲式兼速度的概念,同样与“陈旧”无关。
其四,板腔体咏叹调是民族歌剧向传统戏曲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又为人类歌剧音乐揭示抒情主人公情感世界和心理冲突的戏剧性思维,提供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复杂曲式结构。基于此,笔者坚持认为,运用板腔体思维和结构创作主要人物核心咏叹调,是中国民族歌剧对世界歌剧做出的杰出贡献。
关键的问题是,当代民族歌剧作曲家只要把握好声腔素材和旋律创新,就应放心大胆地使用;明明有条件使用而故意弃之不用,或以种种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把民族歌剧音乐创作最宝贵的经验束之高阁,那就离败家子作风不远矣!
既不当守财奴,也不做败家子,既要传承,更要发展,才有望将新时代民族歌剧及其咏叹调创作推向新境界。这就是笔者在板腔体咏叹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寒窑咏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