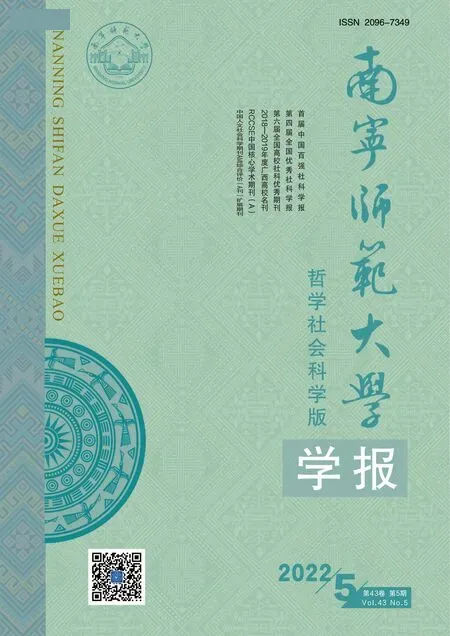“淡”范畴的哲学根基探析
周 斌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桂学研究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在萌芽之初就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浸染。对中国古代文论“淡”范畴的哲学根基进行挖掘,从中梳理出“淡”范畴最原始、最根本的哲学依据,有助于充分认识“淡”范畴的文化内涵和美学品格。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要数儒道佛三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它们三足鼎立、共同执掌,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淡”范畴以道家为根基,以儒佛为羽翼,是三教合流影响的产物,对“淡”范畴哲学根基的探析,自然离不开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深度挖掘。
一、道家哲学对“淡”范畴的滋养
道家哲学体系庞大、内涵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活水源头之一。“淡”是道家提出的,对“淡”最为推崇、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道家,道家哲学全面而深入地滋养了以“淡”为美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对“淡”范畴的哲学滋养贡献最大。
(一)老子的“淡”论
1.“淡”与“道”的品性:“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在老子看来,“淡”虽无味,但是因为具备了“道”的品性,所以成了一种超越世俗、超越有限而进入无限的“美味”“至味”。“道”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老子》一章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51作为永恒的道,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因此,老子将“淡”与“道”联系起来,《老子》三十五章指出:“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1]187大道淡而无味,虽然看不见,听不到,但是运用起来却无穷无尽。老子将“淡”视为“道”的品性,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淡”与“道”的本质联系。正是基于此,老子为“淡”确立了较高的哲学地位。老子认为“淡”并非追求感官快适,而是以求“道”为宗归,把“道”视为终极目标和本质内涵,“淡乎其无味”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深层、高级的美。
2.通“道”达“美”:“味无味”
“淡”,既然是无味,那又如何成为“至美”“至味”,乃至通“道”达“美”呢?老子的解释就是“味无味”。老子排斥感官认知,认为一味地追求声色之娱,会干扰人类的理性精神与道德情操,《老子》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100老子认为五色、五音、五味、畋猎、财货等都是声色之娱,是有害身心品德之物,因此,提倡人们不要沉湎于感官的享乐,而是追求有利于身心品德的东西。因此,《老子》六十三章提倡:“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1]282。“无味”即“淡”之至味,它胜过世俗之味,超越有限之味,是“道”的本味,是一种全味、至味。老子以“味”通“道”达“美”,认为只有保持着对“淡”之本味的体味,方能成就审美主体的虚静之心,得到至美体验,从而领悟“道”的境界。老子以“味无味”作为通“道”达“美”的审美体验方式,为后来的理论家继续描述“淡”的属性和本质,提供了理论参考。
3.治国理念:“恬淡为上”
老子在主张人要效法自然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恬淡为上”的治国理念,这对后世影响深远。《老子》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1]177老子在这里探讨了治国、用兵之道的最高境界为“恬淡为上”。“恬淡为上”虽在言兵,实际上道出了老子治国的核心理念。老子认为战争不符合“自然之道”,而效法自然之道是老子的社会之道、为政之道,追求天人、道我合一的“恬淡为上”就是老子治国理念的集中展现,是“效法自然”观的体现。“无为”是“恬淡为上”的核心思想。《老子》四十八章:“无为而无不为。”[1]233“道”在表面上虽看似无所作为,但实质上却无所不为,“无为”通过“无不为”,本质上成了一种至上、绝对、纯粹的“有为”,其具体表现包括“不言”“不争”“致虚守静”等方式。因而,“无为”是实施“无不为”的路径和方式,而“无不为”则是实现“无为之治”的目的和旨归。老子希望统治者效法自然生养万物之道,认为比较好的治国方式就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58,在“恬淡”的环境之下,君主悠闲无为,百姓自由发展,从而达到社会平和、民利百倍的至善至美之境界。可见,老子“恬淡为上”的治国理念既体现了对自然天道的推崇,也体现了对百姓的人文关怀。
4.“淡”的否定辩证法
老子哲学还有一个非常闪光的地方在于其充满哲学智慧的否定式辩证法。老子的否定辩证法是“淡”之否定辩证法的哲学起源,为我们认识“淡”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辩证思维方式,揭示了“淡”的辩证思维本质。《老子》一章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51既然“道”如此难以言说,不可辨认,所以,老子极少做肯定性的界定,而是频频使用否定性描述来说明。老子的否定辩证法主要体现在其道论的否定式思维方式中,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35(《老子》八十一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1]143(《老子》二十二章)老子善于从否定的、负的方面去描述和认识对象,而他通过不断的否定,就是为了达到肯定的目的,比如他不断地否定“道”的具体性、有限性,最终是为了达到肯定“道”的整体性、无限性和超越性的目的,这种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揭示对象的辩证本质,就是老子的否定辩证法。这种否定辩证法,后来被冯友兰援引使用,并被称为“负底方法”:“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2]冯友兰把真正形而上学的对象(共相、真际、理、气、道体、大全)说成是不可讲的,并运用他的“负底方法”对这些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事物、道理加以言说和把握,可谓是对老子否定辩证法的发展和运用。而对于“淡”来说,老子也运用了否定辩证法加以描述,《老子》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1]282把“恬淡”当作有滋味来品尝,既道出了“道”的修为和境界,也阐明了“淡”的辩证思维和辩证本质。
(二)庄子的“淡”论
相比老子而言,庄子更喜欢言“淡”,“淡”在《庄子》中多次出现,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淡”思想,提出了关于“淡”的本体论与美本源论。
1.“淡”的本体论:“恬淡”为万物之本
庄子关于“淡”的本体论主要体现在《外篇·天道第十三》和《外篇·刻意第十五》中,其主要思想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恬淡”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是生命底蕴的本原状态,是道德的极致和根本。“恬淡”与“虚静”“寂寞”“无为”皆是天地的根本和道德的至极,所以帝王圣人安心于这种境界。“恬淡”,即淡然、安静、无营求,不慕荣利,“恬淡”的实质特性指向自然的无意识性,庄子之道的精神也就是“恬淡”的精神。庄子发展了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1]187的主张,将“淡”视为“道”之品性,进而提出了恬淡为“万物之本”“道德之至”的观点。《外篇·天道第十三》:“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3]248“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3]249不但把“道”绝对化和本体化,而且也把作为“道”之属性的“恬淡”同样推至绝对化和本体化的地步。《外篇·刻意第十五》云:“虚无恬淡,乃合天德。”[3]293天德乃自然之德,恬淡因为切合物之自性,所以符合天德。圣人滥用心智、造作仁义而毁丧了本然之道,因此,他提出要“绝圣弃智”,摈仁除义,去除物累。人要戒除“二十四累”,必须要心境虚静而澄明,本着“虚以待物”的原则,做到“无为而无不为”,才能复其初心,返璞归真,以契合“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之自然本性。可见,庄子认为恢复道德的本质,返归自然的真性,关键是绝圣弃智、摈仁除义、弃物捐心,而最终落实到“恬淡无为”上。第二,“恬淡”为养生之道,是长寿的途径。庄子主张顺其自然,认为依照规律,就不会为外物所拘、所伤,就能潇洒随意地往返于大化之中,安适自得。因此,庄子倡导虚静恬淡的养生理念和无思无虑的人生态度。“恬淡”因“无为”而能实现养生、长寿的目的。庄子提出“恬淡”养生理念的目的是使人“复归于朴”,不至于为功名利禄所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和德性的完善,最终复归到人类婴儿时期一样自然、本真、淳朴的状态。庄子提出了实现“恬淡”养生的具体修炼方法,即“心斋”和“坐忘”,《内篇·人世间第四》:“虚者,心斋也。”[3]81《内篇·大宗师第六》:“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3]156一个人在心态上做到了恬淡、虚无,才能够成为“至人”“神人”“圣人”,也就是道德忘我无己,精神超脱物外,修养臻于完美的人。
2.美之本源:“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外篇·刻意第十五》:“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3]291庄子认为“淡”生众美,“淡”不仅是万物之根本,也是美之本源,庄子在这里提出他的“淡”美本源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体现了庄子主张回归自然无为本性与主张“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取向。在庄子看来,理想、完美的圣人之德,就是“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认为只有保持自然初心的纯朴,轻视功名利禄,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彻底忘却自我,才能成为“圣人”,达到理想的道德人格境界。第二,“淡然无极”是高层次之美,是“大美”,本质特征就是“朴素”。《外篇·知北游第二十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3]392庄子的“大美”是至美,它与天地、四时、万物的生态运行节律合拍,依顺自然万物之和,其气势和力量足以创造世间万物之美,只要达到“淡然无极”,世间一切的美好就会随之而来。《外篇·天道第十三》:“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3]250淡然无极作为一种大美,其本质特征就是“朴素”。“朴素”合乎自然之理,只有追求自然的“淡”美、朴素之美,才是高层次的美。第三,庄子的“淡然无极”是美的本源。“淡”作为美的本源,本身具有超越性和虚空性。《外篇·刻意第十五》:“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间,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3]291有无相生,虚实相济,正是因为“淡”的“无”与“空”,“众美”才能从之,因为“有”生于“无”,故“淡”能生众美。
庄子的“淡”美思想包含“朴素”“大美”“道”“自然”“无为”等内涵,意蕴丰富。“淡”,朴素自然、超然物外、虚实相生,超越了具体的形质和美相,成了一种极具张力、无限生长的美的本体和本源。
(三)葛洪的“淡”思想
葛洪的“淡”思想主要集中在《抱朴子》中,《抱朴子》集魏晋炼丹术之大成,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是战国以来神仙家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蕴含着丰富的“淡”思想。
第一,“宽泰自居,恬淡自守”的养生之道。葛洪提倡节欲淡泊的养生观,这与他的节欲主义哲学有关。与清谈家的适性主义相比,葛洪希望将情感欲望压缩到最低限度,以无欲为追求目标。与老庄提倡“淡”的目的在于“得道”不同,葛洪提倡节欲的目的在于修真。在葛洪看来,庄子也是未能免俗之人,他的“齐生死”,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仍然是贵生、乐生,与修真是背道而驰的。在修真的道路上,葛洪坚持个人内修与节欲的结合,故《抱朴子·内篇·道意卷九》有云:“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养其心以无欲,颐其神以粹素。”[4]383修真的道路上或许会遇到各种障碍,人能“淡默恬愉”在于其“养其心以无欲”。求仙问道之人本应该遣除喜怒好恶之情,无欲无求,如此方能保持心神的纯粹淡泊与性情的不染不杂,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无情无欲在修真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恬愉淡泊的生活正是修道的起点。《抱朴子·养生论》:“常以宽泰自居,恬淡自守。”[5]葛洪主张通过内省、内修以抵触外在名利欲望的诱惑,其实质就在于保持情志的安宁与精神的内守,进入一种心平气和、恬淡寡欲的自然境界,最终达到健康长寿、修真得道的养生效果。
第二,“味虚体淡”的理想人格。“味虚淡者”是葛洪提出的理想人格,居泠先生、怀冰先生、逸民先生、潜居先生、乐天先生、玄泊先生、伟人巨器、大贤先生等则是“味虚淡者”理想人格形象的代表。在《抱朴子·外篇·任命卷第十九》中,葛洪借居泠先生之口提出了他的理想人格:“味虚淡者,含天和而趋生。”[6]380除了居泠先生,《抱朴子》还对其他理想形象进行了描述和阐释。总结起来,这些理想人物共同的人格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重生的思想。由于意识到人生如同风驰电掣般短暂易逝,葛洪非常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在他塑造的理想人物身上充分体现了其“重生”思想,如《抱朴子·外篇·嘉遁卷第一》论怀冰先生:“且夫玄黄遐邈,而人生倏忽。以过隙之促,托罔极之间,迅乎犹奔星之暂见,飘乎似飞矢之电经。”[6]20但是葛洪也不是完全否定个体的社会价值,《抱朴子·外篇· 任命卷十九》云:“其静也,则为逸民之宗;其动也,则为元凯之表。”[6]383指出“逸民之宗”与“元凯之表”也可殊途同归。
其次,轻富贵的思想。葛洪认为,得道之人多轻功名,而俗人常被外物所累,他借笔下的理想人物对汲汲追求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抱朴子·外篇·逸民卷二》:“或有乘危冒险,投生忘死,弃遗体于万仞之下,邀荣华乎一朝之间,比夫轻四海、爱胫毛之士,何其缅然邪!”[6]69葛洪认为,对名利的苦心营求会使人失去原本自然的天性,导致人性扭曲,只有保持宁静的心境和恬淡朴素的生活,才能不为外物所累、所害,所以葛洪笔下的理想人物都过着清心寡欲、淡泊明志的生活。如《抱朴子·外篇·嘉遁卷一》描述怀冰先生:“薄周流之栖遑,悲吐握之良苦。让膏壤于陆海,爰躬耕乎斥卤。”[6]2追求现世功名,乃是弃本逐末,真正通达之人则是轻视功利、自然无为、淡泊明志。
最后,逍遥自在的精神。葛洪笔下的人物形象无不充满着逍遥自在的精神。如《抱朴子·外篇·刺骄卷二十七》论“伟人巨器”:“量逸韵远,高蹈独往,萧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间,神跻九玄之表。”[6]580再如《抱朴子·内篇·逸民卷二》评“逸民”:“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6]74这种逍遥自在的精神是一种不汲汲于外在功名利禄,无尤无怨的乐天任命和自得自足,是一种内在价值观,而这种精神的本质,或者说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体道合真”。只有胸怀高洁、慎重行事,思想与天地相连,才能保全本性,达到无限逍遥的境界。
道家追求清淡自然、寡欲无为,认为只有淡泊名利、无为不争,人才能远离祸患、全身招福。葛洪的“淡默恬愉”“恬愉淡泊”“居平味淡”“恬淡自守”反映了葛洪对恬淡生活的崇尚以及对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自然美的追求,这也正是道家“淡泊”精髓的体现。
二、儒家哲学对“淡”范畴的浸润
与道家的自然无为、消极出世思想相比,儒家则是积极入世的。儒家重视功名,主张积极进取,“修齐治平”,同时也强调对名、利、欲的节制,因而儒家思想也蕴含着“淡”思想,浸润着“淡”范畴的形成。具体而言,儒家积极倡导的“以理节欲”“贵和致中”“温柔敦厚”等思想浸润了“淡”思想,对“淡”范畴的内涵生成、审美特点、思维方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以理节欲与“淡”的理智性
儒家没有排斥和抵制“欲”,而是把对“欲”的追求视为人的本性表现,强调“以理节欲”,代表性思想主要有孔子的“克己复礼”“从心所欲,不逾矩”思想、孟子的“养心寡欲”思想和荀子的“以礼导欲”说。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强调对“利”“欲”的理性节制,浸润了“淡”的理智性,其提倡的以理节欲、重义轻利的积极进取的道德人格其实也蕴含着淡泊的因子。
《论语·里仁篇第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7]35孔子认为人追求富贵的方式要合乎“道”。《论语·述而篇第七》进一步论述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7]68可见,孔子充分肯定了人对富贵的追求,把它视为人性的一部分。对于人性的“食色”之欲,孔子并没有加以否定,他认为人们好色多于好德的现象是人性使然,是正常的。孔子支持用正确的方法和途径获得富贵名利。《论语· 述而篇第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69孔子反对为了富贵罔顾仁义的做法。孔子认为,只有追求符合“道”与“义”的“富贵”才具备正当性和合理性。《论语·颜渊篇第十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121符合礼的道德标准,则为“仁”,孔子用“礼”来克制欲望,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平衡理欲的矛盾。孔子“克己复礼”的节欲观,轻视物质欲望,注重道德礼义,强调以社会规范和他人正当利益来克制个人的欲望需求,并主张人们以正当的手段和途径满足自己的欲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孟子则在孔子“克己复礼”节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养心寡欲”论,《孟子·万章章句上》:“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8]206孟子认为,美好道德比物质享受更珍贵,好色、富贵都不能解忧,唯有施行孝顺父母等道行,才能获得持久的快乐。《孟子·告子章句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8]265生命和道义都是人之所欲,当二者不可得兼时,则要舍生取义。与孔子一样,相比富贵而言,孟子更重视仁义忠信等伦理道德。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养心寡欲”的主张,《孟子·尽心章句下》:“养心莫善于寡欲。”[8]339那些合乎道义、合乎天理的“欲”是“善”,而脱离“天理”“道义”的“利欲”“物欲”“私欲”都是“不善”的。可见,孟子对“欲”不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养心寡欲”的主张是赞成人们去追求那些合乎道义、合乎天理的“欲”,而克制那些脱离“天理”“道义”的“利欲”“物欲”和“私欲”。
荀子则在孔子“克己复礼”节欲观的基础上,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以礼养欲”的导欲论。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欲望,《荀子·礼论篇第十九》:“人生而有欲。”[9]227人饿了就需要食物,感到寒冷就需要取暖,劳累了就需要休息,喜爱利益而讨厌祸害,这都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性情。《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9]280所谓“性”是指人的自然生理欲望和物质生活欲求,人生而有性,有性就有情,有情亦有欲,人生而有欲,人性是“性”“情”“欲”三者的结合。对于“欲”的基本特性,荀子认为“欲不可去,也不可尽”,《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9]280欲望具有无法穷尽又无法去除的特点,人为满足欲求而采取不符合道德规范行为就是行“恶”,只有施行“礼义之道”才可以为“善”。《荀子·礼论篇第十九》:“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9]227荀子在这里提出了他的“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养欲导欲论,指出通过礼义来节制和疏导人们的欲望,才能平衡理欲之间的矛盾,达到个人和谐,天下安定的目的。欲所当欲,不欲所不当欲,对“欲”要有节制,对于有条件满足的欲望可以满足,而对于没有条件满足的欲望就通过“礼”加以节制,这就是荀子的养欲导欲论。
总而言之,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节欲观,提倡用“礼”来克制“欲”,从而平衡“理”“欲”的矛盾,规范人们的行为,孟子在孔子“克己复礼”节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养心寡欲”论,荀子则提出了“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的“以礼养欲”的导欲论。儒家不主张对人欲的否定和消除,而是倡导人们遵守伦理纲常或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来理性地克制自身的欲望和行为。儒家的“以理节欲”思想引导“淡”更趋向于理智性,对“淡泊”思想观念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二)贵和致中思想与“淡”的和谐圆通
“中”与“和”是儒家的重要哲学范畴,“贵和致中”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中庸之道的精髓。“淡”思想具有和谐圆通的一面,“淡和”的思维方式是指在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够采取不偏执、不过激的方法和手段,从而使得各种矛盾关系得到协调与平衡,实现和谐发展,其思想主要来源于儒家的“贵和致中”思想。
“和”的思想发端于《周易》,《周易·乾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10]6天地万物能够各得其性命之正源于天道的变化,只有万物协调、互相作用,才能保持冲和之气,有利于正道,达到“和”的最高境界。《周易》把阴阳和谐视为“和”最基本的含义,并进而扩展到了人与自然等诸多矛盾对立关系中,如《周易·乾卦》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0]24“大人”即合“中庸之道”的圣贤,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之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11]尧帝倡导部落邦国之间的和谐发展,协调理顺了各诸侯国的关系。《尚书·大禹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2]人心善恶难辨,道心微昧难明,因此要信守“中道”原则,不偏不倚地执着于“道心”,这是历代相传的道统秘诀。《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3]其把“和”视为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普遍规则。《国语·郑语》把“和”界定为“以他平他”:“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13]9可见,“和”承认客观事物的矛盾对立面,是协调事物矛盾关系的重要途径。孔子论“和”的独创之处在于将“和”与“合”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纳入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丰富和发展了“和”的内涵。孔子的“和”思想涉及国家治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在治国治民方面,孔子把“和无寡”视为与“均无贫”“安无倾”同样重要的三大治国理念之一。孔子认为政通人和的途径就是“宽以继猛,猛以继宽”[14],这是他关于治国治民方面的求“和”思想主张。而在人际关系上,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交往原则:“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7]140孔子之“和”,是有原则之“和”,这个原则就是《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164。孔子论“和”,除了要坚持原则,还提出要遵守礼仪的要求,指出:“礼之用,和为贵。”[7]7孔子揭示了“礼”与“和”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是“礼”的作用和功效之一就是促进“和”的实现;二是“和”必须以“礼”为准则,“和”的实现离不开“礼”;三是一味求“和”而缺乏“礼”的节制,是会出问题的。孔子毕生致力于“克复周礼”,希望借助周礼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制度,从而实现求同存异、互生共长、和谐融洽的理想状态。
“中”的思想在《周易》中也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卦辞、爻辞及对卦的排列中,意蕴丰富。在《周易》中,六爻从初爻到上爻的变化位置决定其吉凶,要把握事物变化过程,中爻最重要,五爻分处下卦与上卦的中位,一般得吉。如《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10]71《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3]73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15]“中”,即中正、适度。孔子发展了“中”的思想,赋予了“中”新的规范,即以“仁”为内在核心、视“礼”为外在形式,把“中”发展成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形成“中庸之道”。“中道”即中于道、合于道。《论语·子罕》:“我叩其两端而竭焉。”[7]88孔子认为凡两端都只是蕴含着一面的真理,不偏走两端,采取折中的态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过,就是做到“中”。《礼记·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夫礼所以制中也。”[16]可见,孔子“中”的标准是“礼”。“礼”使百姓从道德的层面认识到犯罪的可耻,从而教导百姓从被动守法转变为自觉守法。因此,就社会效果而言,“礼”比“法”要更胜一筹。《论语·八佾篇第三》:“人而不仁,如礼何?”[7]24“仁”是“礼”的基础,君子把“仁”视为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行“礼”之行为,最终才能实现“中”的境界。孟子在继承孔子“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变”的概念。《孟子·尽心章句上》:“执中无权,犹执一也。”[8]313孟子赞成“中道”的主张,他认为主张“中道”虽然不错,但是如果不知权变,执着于一点,而忽略了其他方面,最终会有害于“道”。荀子还提出了“中和”的概念,《荀子·王制》:“中和者,听之绳也。”[17]把“中和之道”运用于政治上,就是治民要宽猛适中、公平合理。荀子把“中和”上升为一种方法论,承认世界万物与个人思想的多样化与多元化,教导人学会包容正反两方面意见并加以融合。
总而言之,“中”与“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在承认和强调世界万事万物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采用或中庸或和谐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本质上都是追求协调一致,有机和谐地发展。“贵和致中”是儒家为了解决冲突,实现和谐而提出的重要哲学观念。“淡和”中追求和谐一致、和谐圆通思想的内蕴则主要来自儒家。儒家“贵和致中”思想以宽容并存,以和谐平衡为宗旨的互相批判和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对“淡”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导着“淡”走向和谐圆通的方向。
(三)温柔敦厚与“淡”的温厚含蓄
在“以理节欲”“贵和致中”的思想影响下,儒家追求“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和美学理想。“以理节欲”“贵和致中”“温柔敦厚”是互相渗透、互为表里的关系。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滋养了“淡”的思想理念与理想风格,“淡”追求温厚和平、含蓄从容的审美风格也是深受“温柔敦厚”思想的影响。
孔子是“温柔敦厚”诗教的积极倡导者,《礼记·经解》有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3]616“温柔敦厚”是指《诗经》产生的教育作用与效果,儒家学者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歌能教化出温柔敦厚的国民。一方面,《诗经》的部分作品虽然具有讽刺的功能,但是并不是尖锐地表达,而是通过温柔敦厚的方式,使国民伦理道德得到教化;另一方面,要求诗人要具有温柔敦厚的情感,并发而为诗,形成温柔敦厚的诗歌品格,进而教化民众,促进温柔敦厚性格的形成。孔子论《诗》有“思无邪”之说,《论语·为政篇第二》:“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7]11孔子认为诗歌的思想应该符合儒家的政治道德标准,只有纯正的诗歌才具有教化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和谐风气的形成。孔子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论语·八佾篇第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7]30孔子称赞《关雎》作为一首描绘男女爱情的诗篇,在表达乐哀的时候中节而有分寸,欢乐与哀怨皆不过分,达到了“发乎情、止乎礼”的适度标准,在诗歌中体现温柔敦厚的“中正”境界,也即是“淡”的境界,儒家对情感是持肯定态度的,却不支持情感的任意和尽情宣泄,而是主张用淡淡的方式来表达若隐若现的情思。这样的艺术才更加富有教化,使人沉浸其中,悠然神往,回味无穷。从这点上来说,“淡”作为温厚和平、含蓄从容的审美风格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滋养是分不开的。
温柔敦厚作为诗歌的一个创作原则,它既充分发挥了文学作品讽喻的功能,又不至于因为直接激烈而引起统治者的反感。这种折中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智慧,它既能让传统文人充分发挥其社会批判的功能而又不至于因为批判现实而惹祸上身,从而实现了文人和统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交流。这种温柔敦厚的“谏言”方式,作为一种折中的妥协,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滋养了委婉含蓄、反对直露的文艺审美标准,好评不绝于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反对的声音,如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指出:“《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18]王夫之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教对现实的批判如同“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有碍直言。王夫之主张真正的诗人应该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这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谈的;而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温柔敦厚”主张委婉含蓄的表达,不是对鸣不平的压制,而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与情感,在艺术上具有一唱三叹、余音缠绕、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黄宗羲《万贞一诗序》:“彼以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必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19]黄宗羲反对对“温柔敦厚”进行狭隘的阐释,他认为,“温柔敦厚”不是一味地有怀不吐,也不是只写喜乐而不写怒哀,对哀怨愤怒之情的注重和吐露抒情的表达,其实也并没有违背“温柔敦厚”主张的既不叫嚣乖张又不浅显直露的“和平”之旨,反而赋予了“温柔敦厚”更多的诠释空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使得“淡”的审美走向了委婉含蓄,蕴藉醇厚,言志而不直白,缘情而不放纵,怨刺而不失度的发展方向。
总而言之,儒家“以礼节欲”思想对于“淡”主体人格中的淡泊道德修养、理智的思辨思维和淡泊寡欲的人性修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儒家给我们提供了看待事物的另一种视角,它以“正”和“德”处世论文,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美德的同时,也蕴含着平正的审美和真挚的情感,具有“平淡”,即使“淡”平、使“淡”正,使“淡”有美德的作用。在艺术审美上,儒家主张的质朴平易、和谐中庸、委婉含蓄的审美原则也对“淡”的艺术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儒道两家思想的本质差异,他们对“淡”范畴的不同影响,使得“淡”美理想在具体的审美风格上出现了道家虚静式和儒家中和式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两者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淡”美的基本形态。
三、 佛家哲学对“淡”范畴的熏陶
“淡由玄而出,是由实通向虚,通向无的楔结点。只有淡泊,才能虚静、坐忘,也才能心不住念于物。因而,淡包含了由道家向禅家演变的全部内涵。”[20]说明“淡”与禅宗思想有深刻的关联。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追本溯源,佛家的核心思想如“中道”“悟空”“无我”等思想,也都与“淡”思想有着一定程度的默契,暗合了“淡”的理论内涵,熏陶着“淡”范畴的内涵生成与审美主体人格规范。
(一)中道思想对“淡”的熏陶
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它在印度生根发芽,最后在中国发扬光大。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文化在不断碰撞中融合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扎根于中国,最终成了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佛与儒道两家有着截然不同的本质差异,但是具体在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以及道德规范和人格修养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学者们也对它们的相似性进行了探讨,如《高僧传·康僧会传》:“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21]把佛教理论理解为与道家学说相一致。契嵩《镡津文集》卷三之《孝论·戒孝章》“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22],用佛家“五不戒”比附儒家的“五常”。宗炳《明佛论》“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23]指出儒道佛三家殊途同归,都在于“习善”。王嚞《重阳全真集》卷一《答战公问先释后道》“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24]4,认为释道是一家。王嚞《重阳全真集》卷一《孙公问三教》“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24]9,认为儒释道门道相通。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依附儒家和黄老道家来传播教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儒道合流,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淡”范畴的重要哲学根基之一。
佛家推崇的“淡泊”思想是“中道”思维的产物。“中道”,属于佛教术语,是释迦牟尼的核心教义之一,指脱离两个极端、不偏不倚的方法或观念。从字面上看,它虽与儒家的“中庸”有相似之处,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庸”在孔子看来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论语·雍也篇第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7]63这是从道德论而言,而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儒家的“中庸”指的是无过与不及,恰到好处。《论语·先进篇第十一》:“过犹不及。”[7]113孔子把中庸视为道的度量方法,认为只有中庸才能避免在体道、达道的行动上“过”或“不及”。关于如何实现“中庸”,孔子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和方法,即《论语·子罕篇第九》所谓“我扣其两端而竭焉”[7]88,孔子认为只有充分认清事物正反两极端的界限,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真正做到“执两用中”。《中阿含经》卷五十六有云:“五比丘,当知有二边行,诸为道者所不当学。一曰著欲乐,下贱业凡人所行;二曰自烦自苦,非贤圣法,无义相应。五比丘,舍此二边,有取中道,成眼成智,成就于定,而得自在,趣智趣觉,趣于涅槃。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是谓为八。”[25]佛家否定了各偏执的苦乐,主张在苦乐之间的“中道”思想。吴汝钧曾对“中道”解释道:“远离两个物事的对立状态。远离断常二见或有无二边,而臻于不偏不倚的中正之境。”[26]131丁福宝在《佛学大辞典》曾诠释“中观”:“三观之一,观中谛之理也。诸宗各以中观为观道之至极,法相宗以观遍计所执非有,依他圆成非空为中观,三论宗以观诸法不生不减,乃至不来不去为中观。”[26]把“中观”视为观道的至极之法,强调守“中”,把不来不去视为“中观”。佛教之“中道”是一种离开极端、偏执的二边而形成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把无我视为中,把无色无形、无明无知视为“中道”诸法的实观。佛法之“中庸”,并不仅仅是离开二端而取中央、中间、中庸的“中道”,而是远离二边的诸法真理,成为真理的代名词。不堕极端,不脱离二边,即为“中道”,佛教则把“中道”视为最高的真理、道理。佛教的“中道”思想成为佛教的重要教理,地位重要。在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容易在善恶、美丑、好坏、是非、空有、苦乐、去来、常断等两端打转,不得其法,陷入恶道,不能解脱,因此,佛教提出,众生要偏离两端的中道,认清万法的真理,以此作为实现涅槃解脱的第一步。佛教把“中道”视为佛性,企望通过“中道”思想来开发人类内在的智慧,以求脱离苦海,获得解脱。“中道”既是佛家的根本立场,也是其基本思维方式。由于具有了“中道”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佛家在认识上才不会发生偏执和障碍。
儒家中庸,是在面对两端的时候采取一种肯定性的辩证思维,阴阳两端,皆可为“中”,关键是用之宜,本质上是和谐与实用。而佛家的中道思想则是一种否定性的辩证思维,把无我视为中,把无色无形、无明无知视为中道诸法的实现,其本质上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佛教之淡泊,不是迷惘的沉静、无绪的安宁,而是智慧的觉解。”[27]129在佛家看来,“淡”不是偏执,更不是障碍,与中道思想一样,是一种觉解智慧。
(二)“空”思想对“淡”的熏陶
“佛教倡淡泊,淡到极致就是‘空’。”[27]134“空”,是佛家的核心范畴和根本思想,佛教以“缘起性空”为理论基本出发点,认为世界万事万物本质上都是空幻的,倡导在观照空理、证悟空性中实现涅槃。佛家的“空”思想具有“淡泊”因子,是范畴内涵生成的重要根源。
“空”观是佛教的核心思想,小乘的教义“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认为一切事物、一切行为都是空幻无常的、没有自性。大乘的祖师龙树也曾在《中论·观因缘品》中说道:“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28]124龙树认为假如从因到果、因、果都是实有,则其“生”的可能就是自因、他因、共因、无因四种可能,然而,却是不生不可得,不成立的。《中论》卷四:“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28]515缘、生皆无自性,皆起而无起,没有实体,自生自灭,“无生”才是因果的真实状态。万物皆无自性,世界虚幻,本质为空,这是空的真谛。因而,龙树在破完四生后,能够跳出对生死的恐惧与对涅槃的执着,皆因一切看“空”。佛教的“空”不是指世界的本源,也非指世界的本体是空的,而是指万事万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缘而变,因而不存在外在的主宰。也就是说“空”不是“有”,也不是“无”,是“中道”,“中道”是基于对“空”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出来的观点,是对“空”的内涵的深化。《心经》是佛学著名的经典,《心经》开篇第一句就阐释了其“空”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29]五蕴,旧译作五阴,是“我”的代名词,包括色、受、想、行、识,本质是“空”,观自在菩萨普度众生时首先就是要去除“五蕴”。此外,还有很多阐释“空”观的观点,《景德传灯录》卷第十五:“直道本来无一物,犹未消得他钵袋子。”[30]《波罗蜜经》:“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31]对“空”的阐释,虽然有诸多不同的见解,但是基本都遵循着“不知空本无空,唯一真法界耳”[32](希运《传心法要》)的原则,通过“有”来悟“空”。因此,佛教之“空”,并非绝对上的没有,而是实有之万事万物在本体上是空无虚幻的。《黄蘖断际禅师宛陵录》:“虚空本来无大无小,无漏无为,无迷无悟,了了见无一物。”[33]因而,佛家要求人们要破除执念,有觉悟,不要执着于追求名利、欲望、声色,而是要看到“空无”的本质,只有树立了“空”的观念,才能淡泊明志,实现超脱。一切看“空”,这正是佛家淡泊人生形成的重要基础。“淡”不是滞留于物,也并非无物。“淡”所呈现的虚无缥缈、若有若无的境界虽然不能等同,却是最接近“空”的,因此可以说,“淡”的远方,“淡”到极致就是“空”。
只有“悟空”,才能“淡泊”,佛家的“悟空”思想既看破了红尘,却又志存高远,其积极意义在于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让人们淡泊名利,把功名利禄看成空幻的过眼云烟,要求人们摆脱世俗的束缚,超越现实的种种纷扰斗争,不执着于生死、善恶、美丑、荣辱,从而实现对世俗的超越,最终获得精神的自由,因此,佛家的“空”观对淡泊主体的形成以及超越洒脱的“淡”美内涵的理论生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无我”思想对“淡”的熏陶
“淡”,由近及远,由实及虚,终极的目标是实现无我之化境,佛教的无我思想与“淡”追求的无我之境相契合。“禅宗要人们以平常心面对尘世,去掉种种偏执妄想,认清自我,恢复自我的‘清净本性’。物我两泯,方能妄执破除,这不正是清静淡泊的旨归吗?”[27]134“淡”在佛教禅宗的无我、物我两泯思想的熏陶下更加超脱自由,淡远空寂。
佛家中的“我”,并非一个人称代词,它是梵语的意译,原义为呼吸,后来引申为生命、自己、身体、自我、本质、灵魂、精神等含义,指一切事物不依因缘而存在的自性,它存在于一切事物的根源内,支配统一着个体。《大智度论》卷二十二云:“一切法无我,诸法内无主、无作者、无知、无见、无生者、无造业者,一切法皆属因缘;属因缘故不自在,不自在故无我,我相不可得故。”[34]“无我”作为三法印之一,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无我”就是无自性,包括“人无我”和“法无我”。佛家认为,人由五蕴组成,五蕴只是假借因缘形成的色身,本质是空。人有烦恼的存在,皆因执着于没有实有的“五蕴”,所以沉沦苦海,不能自拔,只有抛开执念,自净其心,才能走出困境,自我救赎。佛教把除自己外的一切事物或存在称为“法”,“法无我”又称法空,指现实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不断变迁,没有常恒存在的自体。“诸法无我”被称为“印中之印”,是佛教三法印的核心,成为贯穿佛教各家教派义理的根本思想。《中论·观法品》有云:“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28]348龙树通过批判“即蕴是我”与“离蕴非我”,来证明“我”本性“空”,自然推导出“无我”和“无我所”,要人们破除“我执”与“我所执”,阐释了人是如何悟得“诸法无我”的道理。“人”指主体,“法”指客体,“人无我”和“法无我”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对象不同。诸法性空,世人不明,看来皆实,故为“俗谛”,而圣贤之人能悟得诸法性空非“实”,故为“真谛”。只有认识到人和物“无我”,才能实现人真正的自我,即“真我”。“淡”追求的就是佛家所说的“无我”之境,在物我两泯的状态下,身与心的主客体矛盾消失了,主客体融合在一起便可以自由自在地表现各具形式的事物,“心”不再主导身体,那么这时,在境界上的表现便是“任其自然”了。
佛家认为“欲”就是“希求”,人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欲望,佛教对欲望不是持一味地否定的态度,而是提倡对欲望的正确引导,具体的方法如“中庸”“悟空”“无我”等。佛家对欲望的理性认识和对人生智慧的思考,正是淡泊的真意,虽然三家在对“淡”的人格理想与“淡”的审美风格方面的认识存在一致性,与儒道两家相比,佛家把“淡”的人格理想引向更加淡泊高远的方向,文艺审美更是趋于淡远空寂。
总而言之,相比儒、佛而言,道家是最为推崇“淡”的,道家的许多代表性人物都曾直接言及“淡”,道家哲学对“淡”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和建构,而儒、佛两家则更多的是在精神内涵上有着一定的契合和浸润,从这点上来说,道家对“淡”的影响是最直接也是最深刻的。正如陈廷焯所云“疏逸非难,冲淡为难”[35],正是在儒道佛三家哲学的多重影响下,“淡”才形成了复杂、深刻的内涵,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最难解的范畴之一,在被不断地诠释和运用中,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核心范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文艺精神面貌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