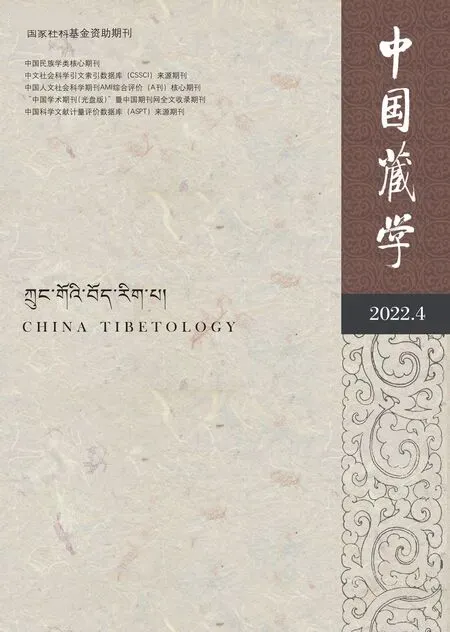19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职员的日常生活
——以戴新三 《拉萨日记》为中心①
王 川
1940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正式设立驻藏机构之始,亦是国民政府强化治藏主权的一大成功。近年来,驻藏办事处渐受学术界关注,已有一些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涉及该机构的历史作用、人事设置、具体事务等,尚未触及该机构职员的日常生活状况,以及这种生活状况对职员藏事心态、驻藏办事处藏事成效等产生的影响。①相关研究成果如陈立华:《简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历史作用》,《中国藏学》2009年第2期,第15—22页;王川等:《民国中期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及其影响 (1940—1944)》,《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78—85页;魏少辉:《20世纪40年代前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涉外藏务调查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83—89页;邹敏:《以教翼政: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传昭布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35—44页;以及中国台湾学者张瑞德:《钦差使命:沈宗濂在西藏 (1943—194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7期,第59—96页;黎裕权:《驻藏办事处的设置、功能与影响——兼论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1939—1949)》,台湾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资料匮乏,恐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本文将以新近发现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第二科科长戴新三 (1907—1997)于拉萨工作期间所写之 《拉萨日记》两册为中心,结合台北出版的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等文史资料,呈现驻藏办事处职员在拉萨的大致生活状况,包括收入、日常衣食住行和娱乐等,进而分析职员的藏事心境与演变及其对驻藏办事处藏事成效的影响。
一、驻藏办事处的职员与收入
根据国民政府 《修正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组织规程》(1940),驻藏办事处设处长、副处长各1人,简派;第一、第二科科长各1人,荐派;汉、藏文秘书各1人,荐派;设科员、办事员各4人,委派;设会计1人、医师1人,可聘雇员若干,成立卫队1支。另,办事处可派员分驻扎什伦布、昌都、江孜等重要地方。本文所讨论之驻藏办事处职员,为孔庆宗任处长时期,上述各职位的到职人员,计有:处长孔庆宗 (简任三级),秘书李国霖、华寄天 (荐任六级),科长马先根、戴新三 (荐任六级),科员刘桂楠 (委任二级)、吴三立 (委任三级)、苏大成 (委任四级),会计员张济安 (委任一级),翻译员意希博真 (委任八级),办事员高师原 (委任八级)、王德 (委任八级)、李耀南 (委任十级)、潘葛岚 (委任十四级),雇员张旺 (委任十四级)。副处长张威白,属于交通部人员,不在办事处支薪,故不列入讨论。另,王德为驻印办事员,不在拉萨生活,亦不列入讨论。
以上职员,除少数兼营商业者外②如处长孔庆宗,秘书华寄天,科员苏大成、刘桂楠等。,工资收入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根据国民政府关于文官官等官俸及福利的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收入由常规薪俸和各项补助构成,补助如生活补助、膳宿补助、医药补助等。职位较高者,则另有一笔特别办公费,驻藏办事处仅有处长、副处长享有特别办公费。根据1933年国民政府公布的 《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驻藏办事处各员每月薪俸收入最高者为处长孔庆宗,总计为1060元,其次是马先根、戴新三各370元,再次是李国霖、华寄天各360元,余下依次是张济安250元,刘桂楠230元,吴三立220元,苏大成190元,意希博真、高师原、王德160元,张旺125元,潘葛岚115元。③郭玉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四),台北:健琪印刷有限公司,2005年,第435—436页;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台北:祐恺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06年,第89页。数字可见,职员之间收入差距巨大,最高者孔庆宗的工资收入是第二高的马先根、戴新三的两倍多接近3倍,是最低者潘葛岚的9倍多。
以上是驻藏办事处职员的应得之工资收入,实际领得数并不如此。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规定所有公务员工资扣发两成,驻藏办事处职员工资也不例外,除 “每月基本生活实支五十元”④即生活补助费20元、膳食补助费30元。外,“余数按照国难期间紧缩办法,以八折发给”⑤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35页。。此外,薪俸还要扣除所得税。根据1940年5月孔庆宗致蒙藏委员会的电文记载,该处部分职员实支薪俸数额为:李国霖、华寄天各250元,刘桂楠154元,吴三立138元,苏大成122元,高师原82元,李耀南75元。①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41页。足见实领薪俸低于应领薪俸。
1941年开始,驻藏办事处虽正常开展年终考绩,根据蒙藏委员会复核之考成结果,不乏加薪晋级者。如1941年度考绩考成结果,苏大成、刘桂楠、高师原、张旺,分别获加薪40元、20元、10元、10元,华寄天 “依原拟加两级薪”。②郭玉琴:《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四),第429页。1942年度考绩考成结果,马先根、戴新三、吴三立、意希博真4人获得加薪, “依原拟加薪20元”,左仁极 “依原拟加薪40元”,潘葛岚 “依原拟加薪10元”。③同上,第435—436页。1943年度考绩考成结果,李国霖 “依原拟加薪40元”,马先根、戴新三、左仁极、刘桂楠、吴三立、意希博真等6人 “依原拟加薪20元”,张旺 “依原拟加薪10元”。④同上,第451—452页。但这些,均仅停留在数字上,驻藏办事处职员并未实际获得加薪。1944年筹备考绩事宜时,戴新三抱怨 “只考绩而不晋级”,李国霖则抱怨 “只晋级而不加薪”,称 “廿八年度及卅年度考绩结果,余已各晋级,孔处长已将会中电报交余阅过,但至今并未加薪”。⑤戴新三:《拉萨日记》(三),1944年4月13日,未刊稿,下同。
驻藏办事处各项费用均以法币计算,再由财政部结购英镑或者卢比转寄中华民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总领事馆再转寄驻藏办事处。为减少因汇率变化造成的经费损失,孔庆宗曾要去结购英镑转汇。⑥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266页。但据档案显示,仍然是以卢比结汇。发放薪俸时,驻藏办事处再根据多数职员的意见决定是以卢比还是藏银发放。如以卢比发放,则由各员再独自寻找商家兑换藏银,如以藏银发放,则由驻藏办事处统一兑换。这一兑换过程,尤其后期卢比跌价,同样数量的卢比能兑换的藏银数额不断减少,使办事处职员的薪俸也随之大幅缩水。
1944年3月,沈宗濂在向吴忠信呈报办事处预算分配表时,特别提到 “前印币 (卢比)一盾约合藏银九两,嗣降至五两,现在仅合二两余,是印币兑藏银之数大为减少”⑦同上,第339页。。根据戴新三在 《拉萨日记》中的记载,1942年11月时,卢比1盾可换得藏银6两5分,12月底时就降为4两,1943年7月降为3两,至1944年7月,降至1两8钱,11月时为2两。⑧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2年12月28日,1943年1月9日,7月24日;戴新三:《拉萨日记》(三),1944年7月30日,11月24日。
以戴新三的薪俸为例,1941年、1942年他每月薪俸为300元,兑换成卢比,再兑换成藏银,在1942年11月,约可得藏银1594两。1943年,戴新三每月的薪俸为国币320元,折合卢比约250盾,如以1943年7月卢比与藏银的汇率计算,约合藏银750两,比上一年少844两,减幅约为53%。戴新三在日记中记载,1943年7月,他的 “实际收入只合藏银七百余两”⑨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7月7日。;11月,他收到 “处中拨给七八两月薪俸,仅得藏银一千四百余两”⑩同上,1943年11月2日。。1944年,戴新三每月的薪俸为国币340元,折合卢比约266盾,如卢比兑藏银的汇率以2两计算,仅得藏银532两,相比1941年的1594两,少得1062两,减幅高达67%。
实际薪俸缩水,加薪不成,补助费的发放情形也不如人意。在1940年到职的11人中,孔庆宗、张威白、李国霖、华寄天4人没有领得生活补助费,其余7人 (刘桂楠、吴三立、苏大成、意希博真、高师原、李耀南、张旺),实际领取了生活补助费。①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89页。
1941年7月1日开始,国民政府实施 《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该 《办法》规定 “公务员实支薪给,无论多寡,一律每人每月拨给生活补助费六十元。公务员月薪实支在两百元以下者,一律另给特别生活补助费每人每月二十元”。②《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福建省政府公报》1941年第1143—1155期,第4070—4071页。按此,驻藏办事处职员的生活补助费当较前有所提高,但实际情形则是,至1942年9月,蒙藏委员会通知该处1941年7—12月追加经费案已经办理完结,且生活补助费已停发,“不在追加费内”。③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269页。处长孔庆宗对此感到非常疑惑,立即回电询问,“停发驻外人员生活费,自何月起,是否两种并停?仅限于不办追加,抑上年七月至本年九月牌汇经费内有无补助费?”并恳请蒙藏委员会体恤高原工作人员之艰辛,报请行政院,“照旧发给生活补助费”。④同上,第272页。孔又根据 《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平价食粮及代金的规定,在电文中提出,“弟处员眷米贴殆尽,向未报领,如生活补助费无法恢复,拟请依法报领米贴代金以资补救”。⑤同上,第272页。
1942年10月26日,蒙藏委员会回电,“生活补助费自卅一年 (1942)一月起,两种并停,米贴亦与补助费同性质,恐难办到”。⑥同上,第279页。11月14日,又通知驻藏办事处,自1942年起停发该处追加费⑦同上,第284页。。可见,办事处职员自1941年7月起,即无生活补助费。
1942年10月,国民政府以 《公务员战时生活补助办法》取代 《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对生活补助费、食米代金等公务员福利进行调整。后又经多次修正,“自1943年6月起,中央机关公务员战时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及薪俸加成数,分别增加;将生活补助费由原来的每半年更改一次,变更为每四个月更改一次,增加了一些福利待遇”。⑧房列曙:《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19页。这对驻藏办事处的影响在于恢复了生活补助费。1943年1月,财政部通知驻藏办事处,该处 “三十一年度 (1942年)一至十月份公务员生活补助费共11800.00元”已由中央银行汇拨,“即希洽办”。⑨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285页;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1月16日。此后至1944年4月,驻藏办事处发放了处内职员1943年10月—1944年2月之生活补助费。⑩戴新三:《拉萨日记》(三),1944年4月13日。1944年5月,蒙藏委员会又通知驻藏办事处,自3月起停发生活补助费。
以上所及,均属驻藏办事处职员实际收入之多寡问题,而他们除了要接受不断缩水的收入外,还必须面对另一个收入难题:经费拖欠,工资不能按时发放。1942年1月,孔庆宗即曾致电蒙藏委员会,述及 “经费不到,已逾半载”,以致 “员眷家属生活无法维持,本月开支分文无着”,希望会中尽速办理汇款。⑪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219页。在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收录的档案中,1942年一年,孔庆宗呈述处中职员生活困难的电文约十数条,如 “生活断绝,告贷无门”“职处经费早告枯竭,公私交困”“处费早□ (尽),上月挪借维持……员工生活无着,索薪甚急,多欲回渝”。①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235、240、248页。至1943年5月,办事处已有一年多未发过工资。戴新三在日记中记载, “公家积欠薪水年余,余在各商号赊货借款甚多”,此前,他还曾向处中借支藏银3000两。②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5月5日。该月办事处追加经费汇到,戴新三当即向孔庆宗表示,希望将其工资照数发给,暂不扣除借支,被孔庆宗拒绝,这让戴新三非常不愉快,致与孔庆宗发生争执。③同上。
工资被拖欠是常态,高原生活本就艰苦,加上拉萨物价不断上涨,卢比跌价,补助费又时有时无,致使驻藏办事处职员除少数兼营商业者外,生活日益艰难。
二、驻藏办事处职员的衣食住行
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是随着战事推进,波及大后方之西南地区时,受物资紧张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公教人员的收入逐渐难以应付日常生活开销。
驻藏办事处的职员中,处长孔庆宗本身工资较高,又兼营商业,同住拉萨者有其夫人及儿子孔繁旭,相对其他职员,生活较易。秘书华寄天,娶有一藏族妻子,兼营商业,收入较丰。科长戴新三、马先根,秘书李国霖,工资收入相对科员、办事员等,略高,但家庭负担也较重,尤其是戴新三。戴的家庭成员中,有一妻三子同住拉萨④分别是妻蒋淑华,及子戴京、戴乡和戴卫。其中,戴卫于1943年出生于拉萨。,其母亲及一子一女住于重庆,所有生活开销均由戴氏夫妇的收入提供⑤戴新三之妻蒋淑华,在拉萨小学任教员。。戴氏于1941年7月抵达拉萨,当年他每月收入约合藏银1800两,每月生活开销为:“伙食去银一千两,房租一百两,应酬费二百两,衣服每月平均二百两,吾母处每月生活费三百两”,即刚好收支相当。彼时戴新三,或许对藏事前途仍持乐观态度,对这样的生活状况,并无抱怨,只言:“虽无积蓄可言,当可勉强支持。”⑥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1月9日。李国霖有一妻一子两女,马先根有一妻两女,生活负担虽较戴新三轻,但受物价波动和货币汇率的影响,生活也不至于宽裕。其他职员如张济安、刘桂楠、吴三立、苏大成、高师原、潘葛岚、张旺等人,他们的工资收入在1942年时,折合藏银约在360—784两之间。该年,根据孔庆宗的汇报,在拉萨 “每人月需食费藏银300两”。⑦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272页。这些职员中,苏大成、刘桂楠未婚,当也不至于过分紧张。但像吴三立,在1942年虽每月可得藏银六七百两,但有一妻两女,共4人,生活就艰辛了。张旺、潘葛岚二人收入最低,在1941、1942年时,应领之工资收入分别为法币125、115元,⑧即在不扣除所得税和战时捐的前提下,个人所应领之全部薪俸和补助费。按当时的汇率,约合卢比98、90盾,兑换为藏银,约为637、585两,⑨法币对卢比,按1941年1元法币合0.7815盾卢比的汇率计算,卢比兑藏银,按1盾卢比合藏银6两5分计算。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129页;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2年12月8日。勉强可维持生活。
以上皆是基于收支数字对驻藏办事处职员的推算,他们的实际生活似乎并不那么糟糕。1943年年初,戴新三记因 “卢比骤跌,补助费早已取销 [消]”,他每月收入仅得藏银800两,“如仅以此数维持,此间伙食,亦尚差二百两”。①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1月9日。至该年下半年,戴氏每月收入约为藏银700两。1943年11月2日,戴氏领到该年7、8两月工资, “仅得藏银一千四百余两”。因工资拖欠,加上即将离藏的关系,戴领取当日即偕其妻淑华,约同吴三立 “往八角购回一批衣料,计花去藏银十三秤”,以备离藏后 “家庭中一两年之用”。②同上,1943年11月2日。所花费的13秤藏银,即650两,几乎是其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但戴氏并未言及此举会对他的家庭生活产生何种影响,许因他尚有一份军统兼职,以及其妻蒋淑华尚有收入,此前又曾向办事处借支了一些费用,并向汉商赊货借款,故生活仍能继续。戴曾记 “公家积欠薪水年余,余在各商号赊货借款甚多”。③同上,1943年5月5日。
1944年年初,因内返一事已定,吴三立送戴氏之妻蒋淑华 “哔吱衣料一件”④戴新三:《拉萨日记》(三),1944年2月20日。,亦未言及衣料之昂贵,或者购买困难。9月,戴新三在准备内返时,为筹备路费,决定将家中积存衣物售卖。9月5日,“谭兴沛、张知重、贾孟康⑤谭兴沛时为军统拉萨站站长,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交通部拉萨电台 (电报局)报务员、台长;张知重,曾任军统拉萨站副站长。贾孟康为藏族人,1942年代表刘文辉至拉萨布施。先后来寓购物,衣物当售去大半”。9月6日,“王信隆、颜俊、萧崇清⑥王信隆为时任拉萨小学校长,颜俊、萧崇清均为驻藏情报人员。先后来寓购物。午后,李茂郁、刘桂楠、邓明渊⑦李茂郁为沈宗濂工作团队之专员,邓明渊初为中央气象局拉萨测候站助理员,同时在拉萨小学任教;后军统驻拉萨情报组组长胡明春吸收其为试用情报员,成为军统在拉萨特务人员。偕来,李购黑盖皮袍一件”。9月10日,“颜俊夫妇及葛医生⑧即沈宗濂团队之医官葛成之。太太来寓购物”,“崔世达来寓,购去铁箱一口,床单一幅”。⑨戴新三:《拉萨日记》(三),1944年9月5日、6日、10日、28日。此处可见,戴新三出售家人旧衣,即可支付戴新三夫妇及3个儿子出藏路费,可见衣物不少,且也有皮袍之类价值较高者。
1943年,戴氏之子戴卫出生,戴记 “购得母鸡一只”,未及购物之困难及价格是否昂贵。但同一日日记中,他又记:“现因卢比又跌,每月开支至少需藏银一千五百两,而实际收入只合藏银七百余两,相差甚巨。”他断定,久居拉萨,生活必然受困,故 “已拟再度签请内调”。⑩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7月7日。
随着拉萨物价暴涨和卢比跌价,到了1944年,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戴新三记录,1944年8月,当时拉萨主要食品的价格为:“青稞每克13.5—15两。糌巴一袋系二克青稞制成,价40—45两。酥油一克,原28—30两,现50两。土面每袋二克半,现65—70月 (两)。麦、豌豆、蚕豆与青稞同价。”⑪戴新三:《拉萨日记》(三),单位与物价记录。此类农产品,即是拉萨的主要食物。就价格而言,相对较高。虽不知此时在拉萨,每人每月生活费需花费多少,但孔庆宗在1942年所说的300两藏银自然是不够的。戴新三、马先根等工资较高者,在1944年,月工资收入也仅得藏银500—700两,职位较低的办事员、雇员等,则不足300两藏银,其工资收入显然无法满足基本生活所需了。
不论住于处内,还是在外租房,住宿都算安稳。戴氏日记有两次记载职员住宿遭袭扰,均发生在1944年,一次是3月7日黎明,“忽有喇嘛一群行经办事处楼下,飞石将客堂玻璃窗击破三面”,将孔庆宗等惊醒。①戴新三:《拉萨日记》(三),1944年3月7日。一次是4月21日早晨,戴氏租住处,“窗外突有人掷石玻窗,幸未击中,但窗棂振动,訇然一声”,戴顿觉 “吒惊”,当即 “取自卫手枪开窗连发三响,以为恐吓”,枪响后,“有喇嘛一群惊逃而去”。②同上,1944年4月21日。
驻藏办事处职员出行,拉萨市内或市郊近距离出行,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远距离出行则由驻藏办事处商洽噶厦筹备乌拉。驻藏办事处共养马5匹,孔庆宗时期,办事处处长、秘书、科长等骨干人员,刚好5人,同时在职人员最多时为23人。5匹马,只能供处内职员平时零星使用,如遇数人集体出行办公 (如办理布施、参加宴请),则不敷使用。起初,处中职员公务出行,不论使用处中自有马匹,抑或借用马匹,均办事处筹备,到1943、1944年,不知何因,逐渐变为职员自行商借。好在这种借马的行为,并不需要支付费用,只是增加了出行的不便。
三、驻藏办事处职员的日常娱乐
拉萨娱乐与内地相比,相对单一,办事处职员和其他驻藏官员的主要娱乐方式就是玩牌、打麻将,午后的研习时间及周日,多以玩牌、打麻将消磨时光。其他娱乐活动主要有郊游、逛林卡、看藏戏、看电影等,但均不是经常性的。
参与玩牌、打麻将的有驻藏办事处职员及眷属,交通部拉萨电台、气象测候所、拉萨小学等各机构职员,以及中央驻藏情报人员、拉萨汉商及其眷属。玩牌、打麻将多为日常消遣,彼此邀约,以消磨时光;也有宴请后为活跃气氛而邀约。
如1942年11月14日,“福兴公司宴客当有剩菜,今日特约平商各号人员来寓聚餐。晚间余与王记白万金③白万金,在拉萨经商的北平商人。、曹自忠④曹自忠,在福兴公司工作,后因与老板不合,离藏回川。雀战通宵”。⑤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2年11月14日。1943年1月15日,汉僧大刚 “欲玩牌消遣”,戴新三 “因派人约华寄天、马太太至 (寓)。晚饭后始散”。⑥同上,1943年1月15日。1月19日,拉萨小学校长王信隆约戴新三 “至马先根寓,并约华寄天凑成牌局,至晚间十一时始归”。⑦同上,1943年1月19日。1月29日,华寄天约戴新三及军统驻拉萨情报组组长胡明春等 “围坐玩牌于晚间十一时始归”。⑧同上,1943年1月29日。3月6日,“午后,三立、颜俊、罗坚来寓玩牌”。⑨同上,1943年3月6日。三立即办事处吴三立。颜俊公开身份为交通部驻拉萨电台技工,真实身份是军令部二厅派驻拉萨的情报人员。罗坚,初为军统派驻拉萨的情报人员,后隶属于国防部保密局,曾任保密局拉萨支台台长,以拉萨小学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职为掩护。7月30日,“午后,大刚来寓约往电台,邀谭兴沛、李国霖玩牌,晚间回寓”。⑩同上,1943年7月30日。此次4人中,除谭兴沛外,均为办事处职员。
玩牌地点,除了上述提到交通部拉萨电台,华寄天、马先根、戴新三寓所外,便是汉商德茂永和裕盛永,如 “午后,偕淑华同往德茂永玩牌”①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10月18日。,“午后,偕淑华在电台玩牌,有马先根夫妇、张奇英太太、孟参喇嘛等”②同上,1943年10月24日。。其中,张奇英为在拉萨的北平商人。“午后,在德茂永玩牌”“饭后,余辞出,迳往德茂永玩牌” “午前,往访王信隆、魏小春及胡明春,旋偕王魏至裕盛永玩牌,至晚始归”“午后,在裕盛永玩牌”“午后,在裕盛永玩牌,有大刚、李国霖在座”。③同上,1943年4月2日,6月17日,2月21日,4月20日,7月11日。
自1942年年底 “藏警案”发生后,政治局势恶化,驻藏办事处与噶厦政府之间无法往返,陷入“僵局”,难以开展工作,加上拉萨生活困难,职员因此感到前途无望,无心工作。除申请内调,或请假返回内地外,驻藏办事处职员多以玩牌、打麻将排解工作和生活上的苦闷之情。戴氏在 《拉萨日记》中记录的玩牌、打麻将次数分别为:1942年11—12月,共5次;1943年1—12月,共96次;1944年1—10月,共95次。数据可见,随着年份的推移,玩牌、打麻将的次数也增多。尤其是在1943年年底—1944年年初,戴新三之子戴京、戴卫持续生病,戴卫几至丧命,马先根丧女,颜俊之长女和幼女先后因肺炎去世。此种噩耗频传,增加驻藏人员的不安心理。加上内调不成,或即使内调获准,也需等待新工作团队入藏完成工作交接,才能启程离藏,更增添了几分烦躁。故这一时期,处中职员玩牌、打麻将的次数及时间均较多。据戴新三记载,平均2—3天一次,有时接连数天,如1943年11月3—7日,1944年1月2—9日,2月23—27日。在此期间,也有通宵者,如1943年11月7日,1944年1月3日,且次日均为工作日。
玩牌、打麻将虽是娱乐,也具赌博性质。1943年3月13日,戴新三通宵玩牌,赢得藏银1500两。④同上,1943年3月13日。这个数字,与戴氏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收入相当,故戴氏在日记中表达出了几分欣喜。但一个月后的他被邀玩牌九,“输藏票一百张”,当即 “彻悟赌博可以倾家荡产之理”,告诫自己要 “戒之戒之”,以后 “除玩麻将消遣,切勿再染其他赌博之恶习!”⑤同上,1943年4月25日。马先根夫人也曾与藏中贵族玩牌至大输。⑥戴新三:《拉萨日记》(三),1944年1月4日。因处中职员玩牌、打麻将的次数增多,输赢又无法避免,致影响职员的正常工作和生活。1944年2月,处长孔庆宗特别向部分驻藏人员谈及:“近来拉萨麻将所犯输赢甚大,宜各劝告所属,勿常作此种游戏。”⑦同上,1944年2月2日。
除玩牌、麻将外,围棋是处中职员的另一项娱乐活动,但参与者不多。戴新三是擅长围棋的,另有孔庆宗及其子孔繁旭,以及后来入藏的陈锡璋。戴氏在日记中记载,与孔庆宗围棋消遣共9次,如 “孔邀余围棋”“余赴业仓领噶,孔处长已到,邀余围棋消遣”“午后一时半许,到达办事处,孔处长当约余围棋”。⑧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7月19日、20日,11月28日。
逛林卡是藏族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也是藏族人民喜爱的休闲活动。林卡,园林之意,戴新三在 《拉萨日记》中,多写为领噶。耍林卡,也称为耍林子、耍柳林子、耍领噶、逛林子、逛林卡等。每年夏季 (藏历五月十五日开始),藏族人民以家庭为单位,在拉萨近郊的柳林,贵族世家则在自家园林,搭建帐篷,进行野餐,开展各类游戏、歌舞等游乐,即为耍林卡。据戴氏记载,孔庆宗时期,驻藏办事处为增进交流,联络感情,即以办事处为单位组织耍林卡,邀请藏中贵族、汉商参加,共同游玩。办事处同仁也集体或个别参加汉商和少数藏中贵族的耍林卡,是为驻藏办事处每年的一大娱乐活动。
1943年7月17—19日 (藏历五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办事处在业仓林卡搭建帐篷,邀请中央驻藏人员一同耍林卡。①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7月15日。藏历五月十五日,为耍林卡之正日,除办事处全体同仁外,办事处还邀请了拉萨电台、气象测候所、拉萨小学等中央驻藏机构职员,以及中央政府派赴西藏的部分情报人员,如胡明春、蒋剑秋②蒋剑秋:军统驻拉萨站会计,1942年入藏。、汪 (藻)③汪藻:原名常希武,入藏前改名为汪藻,军统 (后为国防部保密局)驻拉萨情报人员,1942年下半年抵藏。参见常希武(汪藻):《国民党特工人员在西藏》,载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内部印刷,1984年。、李 (梦明)④李梦明:与汪藻一同入藏。汪藻等人入藏,系组成一个5人小组,分别是组长胡明春,副组长王钧,会计蒋剑秋,电台台长常希武 (汪藻)和报务员李梦明。、萧崇清⑤萧崇清:回族,军统 (后为国防部保密局)派赴拉萨的情报人员。1941年抵藏,1948年返回南京。、张知重等,共同耍林卡,以示团结。⑥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7月17日。除驻藏办事处组织的耍林卡外,处中职员也会参与其他驻藏机构及汉商组织的耍林卡。如该年7月,戴新三曾连请事假5日,以参加平商之耍林卡,之后又参加拉萨电台之耍林卡2日。⑦同上,1943年7月13日、18日、22日。1942年及以前,驻藏办事处与藏中贵族之间,当也会互相邀请,参与彼此之耍林卡。自1942年 “藏警案”发生,形成政治 “僵局”后,“藏中僧俗官员与中央官吏之公私宴会,均无形停顿”,⑧同上,1943年8月13日。故在戴氏日记中,不见此类记载。
1943年8月28日,谭兴沛、邓明渊等人组织过一次爬山活动,目标为拉萨近郊之磨山,参加者共有10人,多为驻藏情报人员,戴新三也应邀参加。同年9月,联欢社⑨联欢社:孔庆宗时期 “为联络藏胞感情,发起成立业余联欢社……内设体育、音乐、书报、演讲、棋奕等组”,场所、设备、经费等均由驻藏办事处资助。联欢社占地约100平米,拥有大礼堂、会议室、厨房、餐厅、阅览室、文娱用品保管室、宿舍、篮球场、排球场 (也做羽毛球场)、单杠和沙地等,不定期举办娱乐活动,也开办运动会,成为 “拉萨的汉族、各单位的公务人员和各商帮 (北京、四川、云南等)一部分人公共聚会的活动场所”。参见 《藏业余联欢社业已成立》,《申报》(上海版)1940年7月28日第23850号第3版。谭熹:《我在20世纪40年代进藏工作的经历》,载西藏自治区政协法制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发起过一次短足旅行,“以格仓佛之庙宇为目的地”,驻藏办事处有戴新三、马先根二人参加。⑩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9月12日。
除以上娱乐之外,游龙王潭、看电影、看藏戏等,也是当时拉萨的娱乐项目,戴氏 《拉萨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看电影一般是在宴请之时,如英驻拉萨使团宴请、美军官宴请。“英官鲁德诺⑪鲁德诺:也写作卢德罗、卢德洛 (F.Ludiow),1942年3月—1943年3月间为英国驻拉萨使团负责人。宴请办事处全体及尼泊尔正副头目……餐后演电影,计有 《地中海舰队》《北非战争》《陆空联合演习》《印度陆军生活》《英皇夫妇赴北美洲》等新闻短片。”⑫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2年11月18日。“美军官脱尔斯脱⑬脱尔斯脱:即伊利亚·托尔斯泰 (Ilia Toistoy),1942年6月,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派遣,经美国务院批准前往西藏。,定今日宴请办事处全体人员……餐后,即下楼看电影。”⑭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2年2月2日。英驻拉萨使团几乎每次宴请都放电影,其片子受喜爱度也较高,如 “赴英官邀宴……午餐后演映电影” “随孔处长及处中全体同事乘马往第及领噶①第及领噶:即英驻拉萨使团所在地。……餐后演电影”。②戴新三:《拉萨日记》(二),8月9日,10月14日。孔庆宗时期,驻藏办事处也放过几次 “科教片和动画片”,但受喜爱度大不如英国人播放的片子,加上 “购片、租片都有困难,旧片子放映几次后,大家就不再感兴趣了”。③常希武:《国民党在拉萨办学简介》,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内部印刷,第90页。戴氏在 《拉萨日记》中未提及驻藏办事处播放电影,许也有这类电影未引起他的兴趣或者关注的原因。
四、驻藏办事处职员生活与同时期重庆公务员的比较
1940—1944年期间,驻藏办事处职员的实际收入日益减少,以致生活困难,虽为事实,但如与同时期重庆公务员相比较,驻藏办事处职员的生活状况还不算糟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战争对驻藏办事处职员生活的直接影响相对重庆而言,要小得多;二是驻藏办事处职员实际生活的困难指数低于重庆公务员。
1938年2月—1944年12月,日军海陆空联合,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轰炸。在此期间,尤其是1939年5月、1940年夏、1941年春秋日军对重庆市区实施极为残暴的、无差别的、毁灭性的、连续性的轰炸,让重庆无数房屋损毁,街道化为废墟,数万市民无家可归。在重庆的各级公务员,与普通市民一样,深受轰炸之苦。
相较而言,拉萨算是战争期间的一片净土,驻藏办事处职员食宿安稳,不曾经历敌机轰炸之种种困难。
驻藏办事处职员工资收入的多寡,关乎的是其个人乃至其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就实际收入的购买力而言,抗战时期重庆公务员和驻藏办事处职员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就实际生活而言,驻藏办事处职员生活的困难指数是低于重庆的公务员的。
1940年以后,重庆一般公教人员的收入,已经不能支付他们的生活所需,以致 “叫苦之声弥闻,狼狈之态满露”。④《一年来重庆市公务员战时标准伙食费与本部职员伙食费比较表》 (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粮食部档案,83/1106。转引自郑会欣:《抗战时期后方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王子壮、陈克文日记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129—146页。郭川在其博士学位论文 《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中,总结抗战时期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状态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住不安居、行步维艰、生不能养、老不能孝、病不能医、死不能葬。⑤郭川:《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6—38页。
在重庆的高级公务员,简任一级的陈克文,以及同为简任一级、除薪俸外还享有一笔和薪俸相当之办公费的王子壮,抗战时期,他们的日记中,时常可见关于大米、布匹、衣服、水瓶等日常生活必须品之价格上涨的详情。陈克文在汉口时,因无夏季衣物试图购买,却因太贵 “不敢买”。⑥陈方正:《陈克文日记》(上),第216页。王子壮表示抗战爆发前,“对于日用必需品之价格,一向不知,无则往购,亦无注意价格之必要”,但抗战爆发后,“多少东西日用所需,而以其价高不能购取”,也就不得不关注其价格了。⑦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子壮日记》(第九册)手稿本,1944年5月18日,第199页。1940年11月,他想买一套中山装,见 “价涨达四五百元”,只有 “咋舌默退而已”。①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子壮日记》(第六册)手稿本,1940年11月16日,第321页。高级公务员的生活都如此,低级公务人员的生活就更加苦不堪言了。王子壮记:“低级公务员而有妻子,则倍感困苦,所入百余元,购米数斗即完全净尽,赤足草鞋褴褛之状,不堪寓目。”②同上。
受卢比跌价和拉萨物价上涨的影响,驻藏办事处职员的实际收入降低,生活日益困难,亦属实情。1943年7月,戴新三再次呈请内调,呈文曰:“窃去年十二月间,因卢比跌价,生活困难,当经历陈苦情,签请内调服务,旋以局势关系,未蒙层峰批准,勉力支持,转瞬又已半年。现卢比价格再跌,百物且倍涨,职每月实际所得,仅只藏银七百余两,而每月生活必须用费,至少非藏银一千五百两不可 (伙食及仆役工资一千两,房租一百一十两,衣服鞋袜两百两,灯油烟茶杂用九十两,应酬捐款一百两,重庆家庭用费尚未计算在内)。收支相差甚巨,虽千省百俭,亦无法继续支撑,惩前毖后,实深悚惧。”③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7月11日。
即便戴氏描述其在拉萨的生活已难以为继,但其日记中,不乏关于购物的记载,如 “至义生昌④义生昌:北平商人在拉萨的商号,商号地点紧邻 “文发隆”和 “兴记”。等处购物”“午前,偕淑华赴八角购布料”“偕淑华赴八角购物”“余至八角购物”⑤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2年11月8日,1943年4月14日、5月23日、7月9日。,“吴三立、刘桂楠偕来,旋偕往八角购物”“偕淑华至八角购物”⑥戴新三:《拉萨日记》(三),1944年3月31日,7月21日。。日记中,此类购物记载,共有24次,极少言及购物内容,更不曾言及物价或购买不易等问题。这与身在重庆不得不关注物价的高级公务员陈克文、王子壮等形成鲜明对比。
在戴氏日记中少有的几次涉及购物内容的记载,均为非生活必需品。如1943年8月16日,戴新三委托兴记总经理梁子质购买金手镯1支⑦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8月16日。;又花藏银150两购买小手枪1支⑧同上,1943年11月9日。,委托办事处医官魏小春 “代制公轮手枪皮套”⑨同上,1943年8月1日。。1944年,戴新三前往后藏扎什伦布寺布施,马先根委托他购买铜佛1尊⑩戴新三:《拉萨日记》(三),1944年5月29日。;而戴新三则向安钦活佛购买古铜佛2尊,“又古铜佛二尊,系余托罗觅来,拟以价购者”⑪同上,1944年5月14日。。这些物品,在当时亦算是奢侈品。在重庆的高级公务员甚至不敢买衣服,而身在拉萨的荐任六级公务员,尽管生活负担沉重,却对商品价格并无过分关注,且能购买奢侈商品,二者生活困难指数的对比自不必多言。
同为公务员,拉萨与重庆在实际生活上的这种差异,除去受战争的影响程度不同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外,就是人文环境了。在重庆,商人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他们利用战争,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大肆敛财,致出现士农工各阶层生活窘迫,商人照旧挥霍无度的奇怪社会现象,“盖今日惟囤积居奇之商人,豪奢逾常,而政府竟无法以控制之”。⑫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子壮日记》(第七册)手稿本,1942年9月8日,第506页。官商勾结,同流合污,在抗战时期虽有越演越烈之势,但毕竟这种行为有违国府政策,也并非所有公务人员都认同这种行为。部分奉公守法的清廉官员以及权势不够的低级公务员,与商人,基本是社会中相对独立的两个群体。
在拉萨则有所不同,因在拉萨经商的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英国及英印政府的西藏政策常对其经商活动产生直接影响),拉萨汉商注意建立和维系与中央驻藏官员之间的关系,以便在必要时获得帮助;驻藏官员则因货币兑换、拉萨物资相对稀少、购物不易等因素,需要商人的协助。再者,拉萨汉商、驻藏官员,均为在拉萨的内地人,这是基于历史和现实因素形成的群体身份认同。在上述背景下,向汉商借支,或在汉商处赊贷货物,成为驻藏办事处职员应对生活困难的主要方式。戴新三记载,1943年5月,他领得当年1—4月工资共藏银9000两,当即“持还各商号货账”,共花去6800两,且 “尚有铸记等二三家未还”。①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5月29日。足见,在工资被拖欠时,戴新三一家主要靠向各商号借支和赊货维持生活。不仅职员个人向汉商借支,驻藏办事处经费紧张时,也向汉商借支。如1943年传昭布施当日发生丢钱一事,办事处就向 “裕盛永、世顺和、兴纪、文发隆四家各借藏银一千两”,予以补救。②同上,1943年2月13日。
五、驻藏办事处职员生活困难的影响
西藏战略地位显著,自元朝时期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清政府又设置驻藏大臣,强化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和治理。进入民国,因之 “壬子事变”和西方侵略势力的挑唆、阻扰,中央政府任命的驻藏官员长期不能入藏,对藏固有主权遭遇挑战。驻藏官员的派遣与机构的设立,是中央政府行使对藏治权的保证,亦是拥有对藏主权的象征。故而,驻藏官员乃至普通职员,均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对藏治权,维系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强化主权拥有。
驻藏办事处职员的生活状况,直接影响其工作心态,进而影响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执行,干系国家主权。中央政府从政策上保证驻藏办事处职员的生活,应是当然之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确曾不断调整政策,冀图保障国家公务员的基本生活,然并未产生预期效果,不仅国家公务员的生活日益贫困,于驻藏办事处职员,反而因实际执行不一致的问题,产生反作用。
如1942年,蒙藏委员会通知驻藏办事处,取消生活补助费后,孔庆宗就呈述办事处职员因拉萨物价飞涨,本就生活困难,“取消生活补助费后,衣杂各费毫无,有眷之员,更难维持”,以致 “群情焦惶,供职不安”。③徐桂香:《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十三),第272页。1942年12月30日,戴新三、华寄天、吴三立3人以生活困难为由,签请内调:“窃查拉萨物价,向较内地昂贵数倍,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用品继续飞涨。自生活费停发后,单身职员生活已无办法,况职等均有家室之男。现印币又暴跌,受两次影响,月薪无异四折。本年度起已借债度日……我等虽向抱服务边疆志愿,但因生活环境均无办法,留此无益,不得不恳祈钧座,垂念苦情,俯允迅赐转电委座,准予内调服务。”④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2年12月30日。1943年,戴新三在家书中言:“重庆为首都所在,十数万公务员之生活,颇为最高当局所顾念,故能随时宣布种种救济办法。拉萨偏处边隅,又非中央力量所可控制之地,物价币价之涨跌,只有听其自然。政府救济,亦不能随时因应。瞻前顾后,愈觉困难重重,故已签请孔处长并迳电吴委员长,恳祈准予内调。”①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1月9日。
1944年5月,在发放了两年多的生活补助费后,蒙藏委员会又通知驻藏办事处取消生活补助费,正值驻藏办事处新旧职员更替之际,沈宗濂即将带领新的工作团队入藏,其办公经费是 “处中原有之经费多出六倍”,蒙藏委员会的停发通知,使 “处中同事均极愤慨,以为会中对人太不公道,重视新人,而忽视旧人”。②戴新三:《拉萨日记》(三),1944年5月29日。可见,断断续续的生活补助费,非但没有解决驻藏办事处职员面临的生活困难问题,反而因制度设计和经费划拨等问题,影响了职员的工作心态。
战争时期,公务员生活日益赤贫,然亦有不少官员罔顾国法,贪污受贿,官商勾结,大发国难财。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就利用职务之便,侵挪公款,经营商业。1943年年初,据吴三立推算,驻藏办事处经费 “当有三十余万两在孔处长手中,侵挪为经营商业之用”。③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2月10日。刘桂楠称,孔庆宗曾与他、苏大成3人合伙,“三次使用藏族劳动人民的乌拉差役做生意”。④检举孔庆宗的材料 (1966年1月20日),《有关孔庆宗的材料》,重庆市长寿区档案馆,3-1956-31-C-0024。他们在印度购买的货物,“可以在印度北部小城噶伦堡装箱时贴上办事处的封条,过境入藏,既免查,又免税,运到拉萨再特卖给康帮商行,真是一本万利”。⑤策仁旺杰·萧崇一:《抗日战争时期的西藏风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员会:《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87页。孔因此敛财不少,从1940年到1944年,“孔已腰缠黄金万两,变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富翁了”。⑥同上,第88页。相较而言,驻藏办事处诸如戴新三、吴三立、张济安等奉公守法者,则无力应对卢比跌价和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生活就日趋困难。
身为处长的孔庆宗,设法解决同仁的生活困难问题,乃至提供必要的帮助,当是应有之义。当戴新三等人初以拉萨生活困难为由申请内调时,他表示 “经济困难,彼可负责设法改善”,希望戴等“勿再坚请内调”。⑦戴新三:《拉萨日记》(二),1943年1月7日。孔确曾呈文蒙藏委员会说明处中职员生活困难情形,但并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当戴新三以 “前次处长留余,原谓对余环境及经济均将设法改善,使余满意”相追问时,孔答:“你们大家可联名电会要求。”⑧同上,1943年2月15日。戴新三因生活难以为继,向孔庆宗提出借支,又多被婉拒。如 “请孔处长借支藏银七百两,虽婉词恳求,亦终未获准,至今思之,犹有余痛”,“请孔处长借支,渠推传昭后设法”,戴新三夫人蒋淑华因此责怪他 “未以言词逼孔”。孔所谓的设法,最后不了了之,致戴认为孔庆宗对他 “仍无诚意”,对其 “经济困难并不设法”。⑨同上,1943年1月3日、2月15日、2月17日。
处长孔庆宗的作为,无疑影响处内职员的团结,加重他们对藏事工作和个人前途的担忧。戴、华、吴等称 “职等委曲求全,亦难取容”,⑩同上,1943年1月9日。科长马先根、科员苏大成,为孔庆宗亲信,得孔之照顾较多,也渐对孔 “深感失望”“不满现状” “急于求去”。⑪同上,1943年2月17日、7月7日。自1942年起,驻藏办事处先后有秘书华寄天、李国霖,科长马先根、戴新三等,科员吴三立、苏大成,会计员张济安等,呈请内调、请假或离职。虽然其中不免政治因素,但日常生活困难、处内人事复杂也是原因。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得以在拉萨建立起驻藏办事处,并派驻一支官员队伍,是民国治藏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驻藏人员因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加上政治环境恶化,而心生懈怠,对藏事前途和个人前途丧失信心,谋求内调,直接影响驻藏办事处的藏事成效和国民政府西藏政策的施行。
另值得一提的是,1940—1944年,驻藏办事处职员的生活虽日益苦难,借债度日,但相对同时期重庆公务员而言,他们的衣食住行均略胜一筹,唯因信息不对等,认为重庆情形更好,故而寻求内调,以摆脱困境。1944年下半年,新任处长沈宗濂率领他的工作团队入藏,原有职员分批离藏。沈宗濂抵藏不久,又因觉得前途无望,于1946年年初离藏,留下主任秘书陈锡璋代行处长职务。驻藏长官和职员缺乏扎根西藏、效力边疆、奉献国家的意志和吃苦耐劳、互相团结、顾全大局的精神,关心个人前途甚于藏事前途,轻则影响藏事成效,重则危害国家主权。
六、结 语
以上基于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第二科科长戴新三的 《拉萨日记》对驻藏办事处职员日常生活的探讨,虽不是全貌,但从中可见驻藏办事处职员生活贫困化对其工作心态的影响。国民政府虽尝试通过政策调适,维持公务员的基本生活,然并不能抵消货币汇率变化和通货膨胀对驻藏办事处职员实际收入造成的损失。加之政策执行的差异,对驻藏办事处职员的负面影响多于正面影响。民国中央政府之政策设计的不足、制度保障不到位,使驻藏办事处职员心生不满,乃至对个人政治前途感到悲观。
兼之抗日战争时期,一切为了前方,后方行政系统的混乱以及干部队伍建设的不足等,致干部素质参差不齐,贪污受贿、官商勾结、中饱私囊者有之,奉公守法、洁身自好者亦有之,前者聚敛财富,生活富足,后者则日益赤贫,生活难以为继。驻藏办事处的处长孔庆宗与科长戴新三、科员吴三立等,即属此类。此种情形,导致驻藏办事处职员内部分化,致一些人心生懈怠,影响了驻藏办事处的正常运作,也是国民政府治藏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之一。而驻藏办事处职员,又何尝不是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系统的缩影?国民政府时期,公务人员队伍的分化及其与政府离心离德,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亦是其政权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