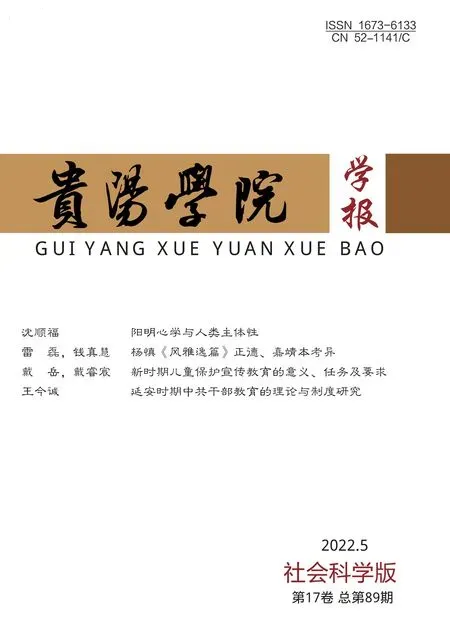萧光远与郑珍、莫友芝交往述论
刘海涛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萧光远,字吉堂,别号鹿山野人,遵义县北隅里人,晚清著名的易学家。萧光远生于清嘉庆九年甲子(1804 年),道光五年乙酉(1825 年)中举,道光七年丁亥(1827 年)春闱落第,归里坐馆授徒,后虽选教谕,不赴。先后主讲于湘川、育才、培英书院,“门人之众甲于西南”[1]212。萧光远勤于著述,著有《周易属辞》十二卷、《周易通例》五卷、《周易通说》二卷、《易字便蒙韵语》一卷、《毛诗异同》四卷、《禹贡拣注》二卷、《汉书彚钞》二卷、《鹿山杂著》二卷、《鹿山著杂续编》一卷、《鹿山诗钞》四卷等诸书。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萧光远卒于乡。
萧光远生前与郑珍、莫友芝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感情极为深厚。萧光远与郑珍、莫友芝的交往,始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 年)与莫友芝的订交,咸丰八年戊午(1858 年),莫友芝北上后,两人虽没有再见面,但仍保持着书信的往来。而就在同一年,萧光远与郑珍得以相见,开始了两人的交往,直至同治四年乙丑(1865 年)郑珍去世。在与郑珍、莫友芝的交往过程中,萧光远的学术研究以及诗文创作都获得长足的发展,其学术地位的确立也得益于郑珍、莫友芝的褒扬。本文依彼此订交时间的先后,对萧光远与郑、莫二人的交往作一全面的考察,借此以了解郑、莫对萧光远的影响,并以此管窥道咸同之际黔中学术的发展状况。
一、萧光远与莫友芝的交往
(一)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 年)的订交
萧光远与莫友芝的交往始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 年)。两人订交的情形,萧光远在《莫郘亭征君诔序》中有详细的描述:
君莫氏,讳友芝,字子偲,别号郘亭,独山州人。……予闻其率诸弟读书,能咬菜根,窃慕之。一日游白田,偕归,偶迟,城门闭,同坐门下,纵言及汉、宋两家之学,君笑谓:“自有此门,曾有人深夜讲学否?”劝著书,谓:“吾辈不偶于时,著述立言,庶几不朽。”时予方注《易》,就宿唐塾,出稿商量,此为订交之始,时道光己亥也。[1]217
萧光远与莫友芝城门下纵言汉、宋两家之学,正是回应当时的学术论争。黔中学术自明代中叶起渐兴,明代专讲阳明心学,至清代“讲明宋学以定斋为大宗”,遂从陆王一派转为尊崇程朱。而随着莫与俦来到遵义,黔中乾嘉汉学获得极大的发展。莫与俦是莫友芝的父亲,嘉庆四年(1799 年)成进士。嘉庆四年(1799 年)之科座主朱珪、刘权之、阮元,所拔取者张惠言、郝懿行、姚文田、王引之以及莫与俦所师事的纪昀、洪亮吉皆汉学之士,莫与俦因此“熟于国朝大师家法渊源”。后莫与俦自请改教授,自道光三年癸未(1823 年)在遵义府学教授生徒,时间长达十九年之久,影响巨大,“士人闻其至,争请受业,学舍如蜂房犹不足,僦居半城市。……其称江、阎、惠、陈、段、王父子,未尝隔三宿不言,听者如旱苗之得膏雨。其后门人郑珍及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为西南大师”[2]。莫与俦虽讲汉学,但不废程朱,表现出汉宋融合的特色,其曾对莫友芝言道:“学者立身行己,当法程朱,辅以新吾、苏门、潜菴、稼书之笃近。若言著述,我朝大师相承,超轶前代矣。”[3]769莫友芝秉持这种家学渊源,幼从父学,“周三岁,能识字,先君授之《毛诗》《尚书》《仪礼》《戴记》”,道光癸未又从莫与俦来到遵义,思想上也是汉宋兼融。萧光远则于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 年)执贽于岁贡生李森斋门下。李森斋“博涉百家,归于六经”,而尤邃于《易》,“究心濂洛诸书”“明邵朱之学”,显然也是提倡汉宋兼融。萧光远明经修行,学问根柢全在六经上,其教人也是必宗洛闽。正是对学术思想有相同的认识,所以萧光远、莫友芝两人相谈甚欢,这才会有“城门深夜讲学”之说。
萧光远说自己此时“方注《易》”,这也可视为萧光远易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萧光远在《周易属辞自序》中对此曾有说明:
自道光戊戌(1838 年),友唐君子固、子英伯仲召馆其家,答诸子问《易》,欲精捡众说,手辑一编,以便讲习。草稿过半,私怪彖、爻、翼何以一语而再见、数见、数十见,此中必有义例,乃屏弃旧说,专取经文观玩。初如面墙,积久似得端绪,因将同句、同字、同旁、同音及不同字分汇钞集。又以全《易》一千三百余字,据许叔重《说文》逐一比勘,渐次推出义例十数条。不揣愚蒙,僭编《易例》《易注》若干卷。[4]17
由此可见,萧光远研究《周易》,最初仍是遵循传统宋易义理阐释的路数,“精捡众说,手揖一编”,然而草稿过半,发现彖、爻、翼之字“再见、数见、数十见”,感觉此中必有义例,于是“悉屏旧说”而采用了汉易的路数,将许慎的《说文解字》运用到《易经》经文的观玩中来,从而编成《易例》《易注》若干卷。显然,萧光远的这种转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是为莫友芝所认可的。莫友芝“肆力于许、郑之学”,对许慎的《说文解字》有深入地研究,所以莫友芝也看出了《易注》存在的问题:“旧义新解,时或间杂,不若离之两美。”[4]17
(二)清道光二十一年庚子(1841 年)至咸丰三年癸丑(1853 年)的交往
萧光远与莫友芝订交后,莫友芝在协助郑珍完成《遵义府志》的编纂、校版增叶工作的同时,也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故,即莫友芝的父亲和其生母相继离世,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 年),莫友芝葬父于遵义县东青田山,并建青田山庐守墓。而青田山庐距郑珍望山堂三里,距沙滩黎氏旧庐六里,“三家者互为婚姻,又同志友善”,莫友芝与郑珍、黎兆勋等人以“诗古文辞交摩互砥,风气大开”(黎庶昌《从兄仲庸先生墓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 年),莫友芝守丧期满后,萧光远与莫友芝交往也日益密切。莫友芝的弟弟莫祥芝在《清授文林郎先兄郘亭先生行述》中曾言道:“甲辰除丧,以余事为诗篇,与郑学博及遵义黎伯容别驾兆勋相倡和,一时知名之士闻风向往,黔中言文雅,自此称盛。”[4]624莫祥芝所说的“知名之士”即包括萧光远。莫友芝此时期的诗歌中有多首写到了与萧光远的交往,如《八月十七日,子何、子觐草堂夜坐,萧吉堂光远乘月相过,时沉阴者三夕矣》。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 年)秋冬之季,莫友芝在遵义城西南碧云山麓下营建新居,而这与萧光远所在的“醉经山房”不远,萧光远在写到两人的交往时也曾说:“君旋卜居碧云峰下,望衡对宇,往来遂密”[1]217。咸丰元年辛亥(1851 年)七月初五日,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一千七百二十四年诞辰日,莫友芝招郑珍、萧光远等人于湘川讲舍共同祭祀,莫友芝著有《郑君生辰,敬赋二十四韵》诗。在诗前的小序中,莫友芝考证了郑玄的生日,并对郑玄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表达了黔中汉学学者对郑玄的崇敬之情:“今世文士于往贤生日,每举荐祀而歌咏焉,以志向往。高密郑君集汉儒大成,尤本朝儒者所宗法。不唯《诗》《礼》笔注抉发幽隐,补正旧疏,即他隊言断义,亦搜掇靡遗。郑学之盛,可谓千载一时。”[3]260非常遗憾的是,当时郑珍携郑知同赴贵阳应乡试,未能参加这次祭奠,也错过了与萧光远见面的机会。
萧光远与莫友芝交往的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并没有看到萧光远唱和的诗作,主要原因即在于萧光远把精力都用在《易经》的研究上。两人订交时,莫友芝即指出《易注》的问题,对此,萧光远则虚心接受,“乃略删节成稿,续改例增例,频增频改,最后得直卦例,遂逐爻变直为主,旧稿存者十不过二三”[4]17。经过十多个寒暑的“冥思默索,独往独来”,最终纂成《周易属辞》十二卷、《周易属辞通例》五卷、《属辞通说》二卷。而在这期间,莫友芝给予了萧光远莫大的帮助,萧光远在《周易属辞自序》中曾说:“朋友中莫君子偲点定商量,始终无间,偏旁、谐声补救尤多。”[4]17文字、音韵正是莫友芝的专长,也正是得益于莫友芝“始终无间”的指导与帮助,萧光远最终完成了书稿的写作。也正是因为共同经历了这一过程,莫友芝能深切地体会到萧光远易学研究的不易。咸丰三年癸丑(1853 年)秋九月,莫友芝为《周易属辞》作序时即写道:
当吉堂始治此经,亦仅集众家为解,既疑彖、爻、翼字句何以不厌相袭,即分条甄比、帖壁鳞鳞。然又计卦名八十字,不同字七十有二;彖不同卦名字,百六十有四;爻不同卦彖字,翼不同卦彖、爻字各五百有五十,亦昔人未言。遂屏去旧说,取全经千三百三十有六字,依《说文》求其故训,折其偏旁,其声纽,一切从本经比例索解,开卷茫无入处。日有乾爻五“龙”往来胸中,忽触“亢龙”字。以四“龙”爻变小过,见飞鸟象而得仰观例。睡中若有告经中字数非苟然者。亟起坐,取卦爻、天地、大衍、筮策诸数乘除,按之皆应。大雷雨集潦入室,不觉也。以渐得凡例若干条,旁推交通,妙义环起。乃著《属辞》十二卷,别为《通例》五卷、《通说》二卷先后之。……吉堂沉思独往,竭十六年,亡食亡寝,十易其稿以成此书,专精极矣![4]14
乾爻五“龙”往来胸中虽是奇异之说,但也可见萧光远冥思苦想的艰辛。
萧光远的《周易属辞》是“自创新例,非汉儒笃守之道”的“以一家之言成一家之学”(李蹇臣《周易属辞序》),但这种不同于传统的“一家之言”一直倍受质疑,《周易属辞》初稿完成时,萧光远的好友唐子英丁父忧自蜀回黔,“常执旧义相驳难”,萧光远则“揭其作注之义例”以说明。唐子英之所以如此,即是“知先生此书自成一家,固驳之,以求其当耳”(唐起尉《周易属辞书后》)。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 年),萧光远的故交唐炯回遵义省墓建祠时,取全稿观之,谓“说理根据象数,不汉不宋,是必传者谈次及《皇清经解》”,显然也是对《周易属辞》提出质疑。萧光远则“取《易》数种,略观条例,专取段氏《说文注》比勘二徐本,于稿中增引之”,由此可见萧光远的严谨,也可见其“用功甚苦而趣甚甘”[4]286。莫友芝对于萧光远的“一家之言”则认真加以分析,指出《周易属辞》是“据系辞所举二十二卦、十九爻,准天地数为《大有图》,以纲领全《易》;又于二十二卦中三陈之履九卦,就《序卦》《杂卦》次序,以通明夷之蕴,与大有相发明;又于十九爻中以,中孚七爻七乘之,应大衍用数,证‘大衍”章古本所以直接七爻”[4]14,而这也正是对易理的新发现:“尤大义卓卓,能阐不尽言、不尽意之秘”。与此同时,莫友芝也指出了《周易属辞》的不足之处:“唯其逐字求象及于助语,逐卦爻字求数,颇疑简易之道当不尔。”但瑕不掩瑜,“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古人言象数亦各就条例伸己说”,“易道广大,亦乌足为病乎!”因此,莫友芝认为“不袭前人”的萧光远可比肩易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友芝始见吉堂《大有图》,尝拟以陈希夷;见其别四圣取象,尝拟以胡双湖;见其比例经文字句,尝拟以焦里堂。然龙图缘三陈九卦自悟位数,论者以为《易》外别传,《卦象图》略为表识,未及推阐。吉堂因经求义,不袭前人,与里堂《通例》《章句》专比异同,以通古义者分道扬镳,庶几匹敌。”[4]14并称赞萧光远“其用心之苦,成功之难,殆过之而无不及也!”[4]14
莫友芝虽不以易学名家,且其在给乡人的信中也曾说 “友芝经学荒芜,于《大易》一经尤无解处,唯以少承先君之训,粗识径途”(《致徐祉堂元禧论〈易广传〉书》)[5]68,但莫友芝年幼时,莫与俦即每举惠氏《易》等众说精核绝者,为友芝指讲[3]769。所以莫友芝对《周易》也有很深的研究。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 年),在京应试的莫友芝于琉璃厂书肆见到乡先贤陈法所著《易笺》,“恭敬奉持”,并为之作序,将陈法的《易笺》与清平孙应鳌的《淮海易谈》、麻哈艾茂的《易注》合称为“黔中前辈说《易》三书”,由此也可见其对黔中易学的熟稔。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 年)春初,遵义县秀才徐元禧著《周易广传》向莫友芝请教,并请其作序①张剑撰《莫友芝年谱长编》记此事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 年)”,见第64 页。。徐元禧“绝服膺来瞿塘之《集注》”,故视其他易注皆不可取,如其《凡例》中指明其书名的含义,即以“孔子作传,解《易》者不必于传外,自汉迄明,注《易》者不一家,皆失之传外,此编准传解经,不敢放逸,故名《广传》”,文笔中充满了“高自标署、傲睨一切之气”,对此莫友芝则写下了万余字的长信与徐元禧商榷。与此同时,莫友芝见徐元禧(祉堂)《周易广传》中所引其兄徐元仁(厚山)《杂卦图解》一文有“可补前人所未及”者,遂给徐元仁的《杂卦图解》写了序文,并在序文中说道:“厚山闻见不多,所阐发已如此,亦可谓好学深思、错薪翘翘者。使得名师友广之群籍,以尽其量,其造就必大有足观。天不假年,才二十□以死,为可惜也。祉堂方壮盛力学,异日深诣,未易以量,故未应序其书,而序其兄遗书以归之。”[3]738非常遗憾的是,徐元禧并没有接受莫友芝的建议,并在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 年)将此书书名改为《周易理揆》而加以刊印。莫友芝得知此事后,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 年)在此信的底稿后写道:“道光癸丑秋,为徐祉堂勘其《易广传》,作此书告之,欲其研索去瑕,勿亟自见。越六年戊申,其书已刊成,意整理慎密矣。逮以本末,则但易其名曰《周易理揆》,于所条论间取窜其旧编,而所不从者又必为之辞,不曰‘断之以理’,则曰‘不必拘泥’,而《自序》且夸为邵、朱后不可无之书,《凡例》又谓‘某己得全易纲领,一切易说,亦无确论,裨点窜不觉,有观止之叹’。昔祉堂曾以《广传》谒贺中丞博青衿,向学若甚勇,既辱相往复,亦殷殷若不及者,岂意其犹自信如此哉?己酉仲秋,胡子何弟为检录此书稿,因论及之,余甚愧忠告之未尽也。”[5]71由此亦可见莫友芝严谨笃实的学风。
(三)咸丰四年甲寅(1854 年)至咸丰八年戊午(1858 年)的交往
随着《周易属辞》写作的完成,萧光远与莫友芝的交往也更加深入。咸丰四年甲寅(1854 年)之乱爆发,萧光远与莫友芝则在共同抗敌的战斗中,更加紧密地联系一起。同年八月,桐梓杨龙喜与舒裁缝于桐梓九坝起事,旋即攻占了遵义雷台山,遵义县北乡大溪里李七王、舒犬附之,威胁到了北隅里与大溪里之交的毛氏龛,此时在郡城授徒的萧光远闻警后毅然还乡,组建“和气团”,自任团长,立团规,壮士气,与起事者激战,后被起事者九路围攻,力竭难支,在付出惨痛代价后,“几死而幸不死”的萧光远退至郡城避难。此时,莫友芝已经由湘川讲舍进入县城,出谋划策,协助守御,并以举人的身份上书制军大人,其在《条陈剿遵事宜上罗制军状》中即对萧光远的壮举给予了高度肯定:“北乡自事起后,举人萧光远等始料理团事,于茅石坎以次联络,左而大力坝,右而宽长坝,板水,四渡跕,横亘百里,三贼巢声息皆为所断,又连杀贼百余人。贼乃以五道、七道并力于茅石坎。茅石坎破,而百里间皆无敢言团,他劲团亦闻风畏缩,阴助贼粮以救目前。然而,同仇之志,则未尝忘也。”[5]141并建议应效法萧光远等人励乡团以防胁窜:“今宜选晓事绅耆十数辈,私出与诸团长激厉大义,阴为整理。但俟雷台一破,乘民气踊跃时,奋臂而呼,团存者策以益紧,团坏者亦招而即复,使贼胁裹无从,逃窜无路,罔不授首矣。”[5]141遵义县城被围长达四月之久,莫友芝经历了这次战乱的全过程,留下了《围城九日》《遵乱纪事》《贼退口号》《和朱亮甫太守〈围城述愤〉》《蹇一士谔大令帅募卒剿桐梓杨逆余党,以十一月十日战没于其县西三十里之四冈,踰月归其柩于遵义,为赋挽诗四章》等近四十首纪事诗,其中对萧光远的“和气团”也多有褒扬,其在《遵乱纪事》中写道:“斗壁重冈茅石坎,阨贼捷途当颈颔。连村列格事垂成,七道妖烽夜争闪。村中志士萧冉徐,杀贼如麻胆气粗。援军不发半义鬼,失此岩险可嗟吁。”莫友芝并在诗后的小注中对此事件进行了说明:“茅石坎一带为自遵义走磨盘山九坝捷道,萧吉堂光远为团长,联络数十里扼其亢,已杀贼数百余人。十月十一日贼以七道进攻,团众不能御,吉堂子永京走军门乞援又不应。吉堂弟仪远死之,吉堂走免,其被擒者皆令拜贼旗免死,唯萧、冉、徐三姓不拜,皆被杀,萧氏男妇死至五十余人。”[3]294陈洐在《石遗室诗话》中说“子偲学人之诗,长于考证,……如《芦酒诗》后记一二千言,《遵乱纪事》廿馀首,《哭杜杏东》亦有记千百言附后,皆有注,可称诗史。”诚如陈衍所言,莫友芝的诗歌与小注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形提供了非常鲜活的材料,正可与萧光远所写的《北乡毛氏龛义民祠记》《书鹿山御贼》互看。
萧光远和莫友芝之所以有如此的义举,是与他们实用的思想相关。莫与俦曾言“读书当求实用,程子谓学须就事上学,朱子谓须就自己分上体验。盖凡人之所为,六经子史皆有一定之则以处之,苟徒从事章句,虽读书,仍与未学等也。”[3]767李森斋亦曾说:“读书专工词章,弋科名,学俗矣。必领取性命源头,一一归之日用,乃谓真贵,是幸耳,何与读书事哉?”[3]268“学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1]283正是在这种思想教育的熏陶下,萧光远和莫友芝才得以走出书斋,关注社会现实,承担社会责任。
咸丰四年甲寅之乱(1854 年)平息后,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定,萧光远与莫友芝也获得一段难得的安逸时光。甲寅之乱时,湘川书院、培英书院皆被毁,于是三书院合在一起,老友可以终日相聚,其乐融融。萧光远在《莫郘亭征君诔序》中描绘当时的情形即写道:“甲寅乱后,三书院聚云麓,同李仪轩三人未尝一日离。倡诗会,执骚坛牛耳,朋友之乐于斯为盛。”[1]217特别是咸丰六年丙辰(1856 年),莫友芝被聘为启秀书院山长后,两人交往日益频繁,是年四月初五日,众人聚饮影山草堂,约定每十日一聚,分韵赋诗,张剑在《莫友芝年谱长编》中谈论莫友芝这个时期的交往时曾言:“李蹇臣《守拙斋诗钞》中有《端午咏粉蒸肉》《甘薯歌》《萧吉堂光远同年夏日招集云麓精舍饮芦酒》《刺梨》《丙辰秋南城观稼次陶〈丙辰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韵》诸诗,与友芝此期诗歌题材多相类,可证他们交往紧密,唱和频繁。”[5]156其实,作为李蹇臣的挚友,萧光远也是这一时期各种聚会的主要参与者。萧光远保存下来的诗歌仅仅只有五十七首,而此一时期与莫友芝唱和的诗歌就达八首之多。也就是在与莫友芝等人的唱和中,萧光远诗歌的才华也渐渐得以展示。
(三)咸丰九年己未(1859 年)后的交往
咸丰十八年戊午(1858 年),莫友芝再次北上就知县选,兼试春官,从此两人再未相见。虽然萧光远、莫友芝相隔两地,但有书信来往。在同治四年(1865 年)正月廿九日乙丑(2 月24 日)的日记中,莫友芝写道:
又得黄子寿书、蹇征士书,……征士言其太翁仪轩尚健,所极念者郘亭、子尹、吉堂三人。吉堂言子尹有口病,甚殆。子寿犹谓有余之症不足虑。宁知二君寄书之月,子尹遂果不起耶?[6]131
在同治四年(1865 年)八月廿九日辛酉(10月18 日)的日记中,莫友芝写道:
萧吉堂光远在成都唐鄂生女儿碑寓授读,且有信至,言已刻诗一卷、说部一种,差可喜[6]159。
此时萧光远应唐炯之邀请来到成都,“言已刻诗一卷、说部一种”,“诗一卷”可能是指同治三年甲子(1864 年)刊刻的《鹿山诗钞》,“说部一种”或是萧光远所著《汉书彚钞》。《汉书彚钞》亦刻于同治三年甲子(1864 年),萧光远在此书《序》中言道:“平素喜读两《汉书》,苦性钝,不能强识。手钞二十余条,虽不免挂一漏万,窃谓汉代近古,其经术、吏治、忠孝、廉节,大端多有可观感者,差异于玩物丧志云尔。”[1]244萧光远喜读两《汉书》,亦是受当时乾嘉汉学思潮的影响,其曾在《钞〈汉书〉,有感故友罗东村兆仑、明经聚南应奎太学》一诗中写道 “平生不善读,见书心便憨。一经方释手,一史又沉酣。……窃自汉以下,群书未足贪。此物犹太羹,下酒味醰醰”,以表达对两《汉书》的痴迷。萧氏老屋在甲寅之乱中被焚毁,丁巳年(1857 年)重建,莫友芝为萧光远题写了匾额“鹿山堂”以赠,并令其子莫彝孙附书,索要萧光远近作。同治十年辛未(1871 年)九月十四日,莫友芝不幸病逝,后由莫祥芝与莫绳孙扶灵柩归黔,葬于遵义青田山间,萧光远亲自撰写诔文,对早逝的好友表达哀悼之情。
二、萧光远与郑珍的交往
咸丰八年戊午(1858 年)冬,郑珍应唐炯南溪之约,来到遵义县城与萧光远“聚谈数日”,由此拉开了萧、郑两人交往的序幕。在此之前,萧光远与郑珍早已相知,郑珍在《吉堂老兄示所作〈鹿山诗草〉,奉题道意》一诗中曾说“交米三十年,始知真可诧”,赵恺曾考定《吉堂老兄示所作〈鹿山诗草〉》一诗作于咸丰十一年(1861 年),据此推算,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 年)两人即已听闻过彼此的大名,所以萧光远说郑珍在修《遵义府志》时,两人即已神交,只是机缘未到未得聚首。此时正是郑珍学术生涯一个重要收获期,《仪礼私笺》《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图说》《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郑学录》等重要著述皆在这一时期完成。“聚谈数日”,谈论最多的应该是汉学、宋学与萧光远的《周易属辞》了,因为萧光远在《郑子尹征君诔序》中说:“至魁崖,寄予《周易属辞序》”。“至魁崖”是指咸丰十年庚申(1860 年)二月至是年秋,郑珍为躲避入境遵义的号军,北走桐梓暂居魁崖附近乡下之事。郑珍达到魁崖的时间即是庚申三月,稍作安顿,即将《周易属辞序》寄予萧光远。
对于萧光远这部“自成一家”的著作,郑珍最开始完全无法读懂,“今读其书,徒惊怖其都与昔者言《易》者异,所说盖十之八茫如也”[4]15。然而凭借深厚的小学基础,郑珍认为萧光远从“辞”来解《易》应该是可行的,因为孔子作《易传》时曾多次提及“辞”,如曰“圣人系辞焉而明吉凶”“圣人系辞焉以尽其言”“系辞焉所以告”,又曰“圣人之情见乎辞”“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又曰“其辞文”“其辞危”“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在郑珍看来,孔子如此繁复地提及“辞”,就是要昭示后人伏羲画六十四卦时并没有文字,而“学者欲憭其象,贯其数,会通其理,以成已而成物”,就必须“求之文王、周公所系彖、爻之‘辞’不能也”,而孔子所作的《传》,就是对文王、周公所系彖、爻之“辞”的解释。虽然由孔子之辞以求文、周之辞,进而探求伏羲六十四卦含义,这一路数是可行的,但在郑珍看来正确的理解“辞”也是不容易的,即使是宋代的吕祖谦、朱熹等人也存在误解:“孔子之辞所谓《十翼》者,自吕成公更次王弼本,朱子据之作《本义》,如其说于古似合,然张守节《史记正义》称‘《上彖》,卦下辞;《下彖》,爻卦下辞;《上象》,卦辞;《下象》,爻辞’,以之斠杨子《太玄》用方州部家拟卦,七百二十九赞拟爻为经,其八十一首拟彖者,与《攡》 《莹》《掜》《图》《告》《测》《文》 《数》 《冲》 《错》诸拟孔子《象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者并在经外,似杨子生西京,所见《易》即是张氏云者,比之吕、朱本为确。”[4]17郑珍自己思考了数十年,也无法理解张守节所说的“卦下辞”“爻卦下辞”究竟指代什么,所以郑珍不禁感慨道:“其为辞者且不能辨,何由知其所以为辞?”而萧光远的《周易属辞》即回答了这一问题,“执经、传所用凡一千三百三十六字析之,合之,䢒之,错之,纵横钩鈲,谓文王、周公、孔子用字各有定数,因推著其所以为辞者”,所以郑珍对萧光远的《周易属辞》高度的评价,称萧光远“于易家足名一氏也已”。正是郑珍、莫友芝等人的肯定与褒扬,萧光远易学成就才为人所认可,从而确立了萧光远在黔中易学研究史上大家的地位。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年)三月,郑珍避难来到遵义县城,任湘川书院讲席,这为两人的欢聚提供了条件。此时,萧光远与郑珍在诗文上的互动非常频繁。两人先后为黎庶焘的《慕耕草堂诗钞》、蹇谔的《秦晋游草》题诗、作序、写跋语,为张节妇题序、书表贞录。李蹇臣送郑珍九子木禾(包谷),郑珍、萧光远彼此唱和。李蹇臣将入蜀避乱,众人于董公寺饯行后,郑珍与萧光远步雪至寓所后吟诗抒怀。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 年)十月七日是萧光远生日,次日,萧光远宴请众友,郑珍作《萧吉堂二兄孟冬朔七为览揆之日,守程朱教谢客,其明日乃招余饮,礼也,然而其寿自在,书鄙句携往酢之》四绝句为贺,萧光远、李蹇臣即席赋和,朋友欢宴,其乐融融。郑珍主讲湘川书院这一段时间曾作有《借启秀书院居,新入举火,独夜诵少陵〈题衡山新学堂〉诗,感念湘川讲舍之废,因次其韵,呈蹇仪轩臣、萧吉堂光远两长兄》一诗,萧光远则在和诗之中将郑珍与自己比作唐代的杜甫与郑虔,由此也可见两人交情之深[1]241。同治三年甲子(1864 年)萧光远六十岁生日,而郑珍于此年九月十七日病逝,这让萧光远感伤不已,其在《岁在甲子,行年六十,不敢言寿,不足言诗,感述生平,自遣怀耳》一诗言道:“辛酉之冬文酒会,大醉狂歌怀郑李。即今二老亦暌违,空赋停云溯秋水。”[1]256
是年,萧光远将自己的《鹿山诗草》送与郑珍,郑珍读后,大为称赞,作《吉堂老兄示所作〈鹿山诗草〉》,奉题道意》一诗予以褒扬:
晨起读君诗,一二心已讶。再进眼忽开,益读益予吓。世久少此声,今乃遇之乍。不能尽阳元,信有如此射。君本学道人,苦志求羲画。思极神鬼通,孔子告深夜。我观《大有图》,不在九师亚。半世寒饿中,失小得者大。六经何铿铿,德容又酝藉。规行而矩步,使我爱而怕。每言及六诗,辄以不敏谢。由来研经徒,吟咏非所暇。我因信其然,岂谓特自下。此气韩之气,此话杜之话。君胡不早出,令我得避舍。交米三十年,始知真可诧。兹事诚小技,亦从学养化。世有昆岷源,江河自输泻。俗论故不尔,只解摘嫣姹。我生诚足笑,漫诩窥牗罅。桓死文未兴,宋襄亦聊霸。老矣悔少作,既出随人骂。然诗之佳恶,意殊不争价。百年有恒产,未死任犁䎬。如君诚余事,顾且甘出胯。大道夜行烛,还求肯余借。[1]237
郑珍是道咸年间宋诗派的代表人物,主张作诗先做人,强调以学问来涵养性情。其在论萧光远的诗歌时,首先即肯定萧光远在易学上的不朽成就,而正是得益于学问的涵养,才使萧光远德容酝藉、规行矩步,由此发而为诗,即是“韩之气”“杜之话”,由此郑珍也感悟出作诗的真谛,即诗从学养中来:“兹事诚小技,亦从学养化。世有昆岷源,江河自输泻。”萧光远的诗歌具有有浓厚的宋诗派的特征,其许多诗歌见解都与郑珍相同,如郑珍主张作诗先做人,萧光远则强调 “文章之与节义,相因者也”“忠孝节义,本也;文章,末也”(《秦晋游草序》),郑珍主张“率性真”,避免做“随俗士”,萧光远则给予“其人真,故发为诗,其事真,其景真,其情真,视俗派风月花藻迥然不侔”的冯子玉以高度的评价(《野人堂诗序》);郑珍主张“养气”,萧光远则强调“天地之所以生物,人类之所以相生、相养,祖宗之所以蕃育其子孙,子孙所以永保其族姓,皆此元气之周流而不息。故一身有一身之元气,一家有一家之元气,推之国、天下皆然”(《成山唐氏谱序》);郑珍指出“养气”全在力行,要躬行实践,萧光远则在甲寅、辛酉之乱中,建义团,作《招安语》,献《攻海龙囤议》,作《请川兵公状》,并“于乡人遭贼之惨、死事之烈,尤反覆言之”(《跋鹿山杂著续编》)。诚然,萧光远在诗歌上所取得成就离不开与莫友芝的唱和。莫友芝具有和郑珍相同的诗歌主张,主张性情与学问的融通,提倡诗以学问为根柢,等等。正是在与郑珍、莫友芝的唱和中,诗歌成为萧光远直抒胸臆、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文学样式。
同治元年壬戌(1862 年)正月,郑珍的望山堂被贼焚毁,花费四十余年心血收藏的五万多卷图书也化为灰烬。郑珍在给萧光远的书信中流露出内心的悲痛:“藏书未出者约计八九百部,其半有钱,南北可买,其半非我郘亭弟之善搜,不能得;至有三四十种,则海内无他本,不图一旦至是!”[1]218同治二年癸亥(1863 年)冬,郑珍再次回到遵义上馆,借居在萧光远家,此时郑珍的口腔开始溃烂。“腊尽将归,强留之,除夕谈达旦。甲子(同治三年1864 年)元日告归,谓‘身健游蜀’。”[1]218同治三年甲子(1864 年)大年初二,郑珍回到沙滩祭祖。此前朝廷下旨,任命郑珍、莫友芝等人为江苏知县,郑珍在给萧光远的书信中云“当出”,在萧光远看来,郑珍是希望借游蜀“得其资斧,下江南与子偲相聚也”。五月以后,萧光远再次致书郑珍,但没有收到回信,“时道梗,讹传已归道山”。八月八日,萧光远收到了郑珍的回信,云:“口病直害到今,医者谓服参当效。”在信中询问北乡之事,并悉数东砦百物昂贵。二十二日,又收到郑珍来信:“服参有效,可缓行二百步。”得知郑珍病情有所好转,萧光远也非常高兴,回信道:“如死而复生矣。”谁曾想,郑珍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于九月十七日病逝,当萧光远得知消息时,“怅然久之”。虽然萧光远和郑珍交往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却是陪着郑珍走完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最亲近的挚友,感情极为深厚,萧光远在“尤恨交君之迟”的痛苦中给好友写下了诔文。
三、结语
萧光远与郑珍、莫友芝三人年纪相仿,又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三人皆得益於乾嘉汉学的沾溉,各逞所长,分别成为礼学、金石目录学、易学方面的名家。三人的经术、人品皆卓卓有可观者,故常被后人并论。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 年)萧光远七十寿辰时,赵怡在《萧吉堂光远先生七十生日赋诗遣怀,遂用其韵寿之》中审视黔北学术发展的历程后,即将萧光远、郑珍、莫友芝合称为“三老”,这也是对萧光远的高度肯定:
吾邦文学途,道真开荒。洪惟北学归,傑立变夷僚。源衍及皇朝,宏畅大斯造。北山卓圣域,酉阳抉儒皂。当时遐裔里,已动中州瞭。勃兴得郑莫,骧驾益夐邈。巢经祖高密,精贯人天杪。津涯淼瀛海,光焰烛昏晓。郘亭事简册,钻研头不掉。博雅雄南中,文字觑天巧。而公与之值,名业自持挢。群经有家法,纷纶大椿抱。羲文理元赜,识恶醯鸡小。艰辛半生力,厥绩视薅蓼。风雨几韦绝,鬼神会冥杳。奇哉大有图,独立九师表。馀溢为诗文,唾咳尽瑶草。其于两叟间,绣躬各斧藻。尔汝复忘形,平生交有道。合绘三老图,矜式良不少。[1]218
赵怡高度评价了尹珍的开辟洪蒙以及李先立、陈怀仁的境界大开,而认为黔中学术的蓬勃兴起实得力于郑珍、莫友芝两人高远超卓,“勃兴得郑莫,骧驾益夐邈”。此时的郑珍、莫友芝在全国已经享有盛名,而身处偏僻西南、声名不彰的萧光远实则是与郑、莫两人旗鼓相当的,“而公与之值,名业自持挢”。赵怡高度评价了萧光远的易学成就,“羲文理元赜,识恶醯鸡小”“ 奇哉大有图,独立九师表”,并称赞萧光远虽不致力于诗文,但所作诗文皆是难得的珍品,“唾咳尽瑶草”。萧光远置身于郑珍、莫友芝之间,则是三人互相增辉。赵怡希望能有人“合绘三老图”,以成为后世尊敬效法的楷模。赵怡是郑珍的外孙,此年距莫友芝离世只有两年的时间,所以赵怡的看法代表了时人的观念。而在萧光远去世时,贵阳名宿司炳奎作挽联,“求实际以读书,与子尹子偲鼎足并称乡蓍旧;悟天道而讲《易》,溯康成康节抗心克绍古经师”,亦是将萧光远与郑、莫两人并论。诚如上文所言,萧光远的易学是乾嘉汉学思想影响下的成果,代表着贵州易学发展的另一座高峰,足以令后人仰止。而萧光远学术、诗歌的成就,离不开郑珍、莫友芝的指导与帮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众人共同铸就了晚清贵州易学的又一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