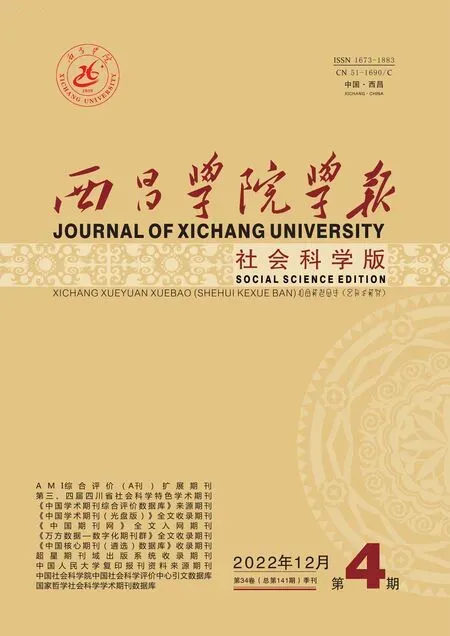数字媒体时代的国外游戏文化研究述评
彭帆影,彭体春
(重庆科技学院宣传部,重庆 401331)
目前全球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但游戏产业却逆势向上。据 Ampere Analysis[1]统计,从 2019 年到2021年,全球游戏市场的规模增加了26%,支出增加了390亿美元。而根据Newzoo[2]的产业预测报告,预计在2022年度游戏税收额度全球排名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将再次高居榜首,中国的游戏玩家人数将超过7.4亿人。中国高速发展的游戏产业及与之紧密关联的文化现象,理应成为国内文化研究的热点。但与国外将游戏研究(Game Studies)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相比,国内的游戏文化研究成果总体上还比较有限,对国外游戏研究的引介也还有很大空间。
一、游戏文化研究的总体脉络
最早的游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从古埃及贵族阶层的赛内特棋,到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竞技体育游戏、古罗马士兵行军途中的雇佣兵游戏,再到现代国际象棋的前身——古印度的查图兰加棋,以及传说起源于尧舜时代的中国围棋、博戏中的双陆等,游戏几乎与人类文明一样源远流长[3]。游戏蕴涵的文化意义,从古至今均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古埃及僧侣认为,棋类游戏为人们提供了窥探来世的机会,预言亡灵往生可能会遭遇的阻碍,警示不敬之人会面对悲惨命运。将棋子从棋盘上移走的规则教导人们死后如何逃出地狱、获得重生。在他们看来,游戏的仪式性内蕴着宗教的寓言[4]。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5]认为,只有神才具有最高的严肃性,人类作为神的造物和玩物,应该遵从本心去做高尚的游戏。无论是揭示游戏的宗教仪式隐喻,还是将游戏作为神的理式的反映,研究者均将游戏视为人与未知世界的联结。
近现代以来的研究者则将游戏作为人的本质,并将其扩展到了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1795年,席勒提出著名的论断: “人只有在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的时候才游戏,当他游戏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完全的人。”[6]后现代思想的先驱或代表人物承续席勒的观点,将席勒关于游戏的概念发展为后现代思潮的重要基础[7]。维特根斯坦[8]将游戏看作一些无法精确定义或缩小范围的事物的范例,并由此建立他的语言哲学,索绪尔发现了国际象棋对语言学的启发作用。胡伊青加[9]则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活形态主要通过游戏发展,人的本质是 “游戏人” (homo ludens)。
1958年,美国核物理学家威廉姆·希金伯泰制作出第一个交互式模拟电脑游戏 “双人网球” (Tennis for Two),开启了可视化电子游戏的先河。随后,电子游戏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兴起。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例如互联网、智能电脑、智能手机等数字化技术和设备的发明和普及,为游戏的大规模流行提供了优越的技术环境。各类网络游戏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推广,并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游戏研究的主题、范畴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学界对网络游戏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
国内学界关于网络游戏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以下五类:一是研究网络游戏与认知心理的关系。对网络游戏的研究成为教育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研究的案例,例如关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现象的研究[10]。二是研究网络游戏内容。主要通过内容分析,解读游戏的主题和角色形象等,网络游戏研究成为传统文化等其他领域研究的案例,例如研究国产游戏中的传统文化[11]、角色扮演类游戏中的女性角色形象[12]等。三是研究网络游戏产业。网络游戏研究成为媒介经营管理等领域的研究案例,例如研究网络游戏的营销传播[13]、网络游戏的虚拟消费[14]、网络游戏的广告传播[15]、网络游戏的直播产业[16]等。四是研究网络游戏玩家。分析网络游戏玩家的人际交往[17]、社会化行为[18]和身份认同[19][20]等。五是研究网络游戏衍生出的游戏化现象。此类研究引入国外游戏化(gamification)理论,重新审视当下的传播环境,进行了理论辨析和案例研究[21]-[23]。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运用符号学理论探讨网络游戏审美和融媒体环境的关系[24],此处不一一列举。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未将网络游戏研究作为专门的研究领域,通常是其他领域相关研究的例证。而国外学界则已经发展出专门的游戏研究理论,出现了众多专门性较强的游戏学家(game scholars)。游戏研究成为跨计算机科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跨话语、综合性研究领域,研究理论渐成体系,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形成了若干研究范式。
二、国外网络游戏文化的研究范式
国外游戏研究领域中,侧重从文化视域进行研究的范式主要有三类:一是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游戏叙事,关注游戏的媒介或商品性质、游戏的机制设置、游戏主题设定等内容,探析游戏和社会现实的关系,认为游戏是社会现实的折射;二是以理论辨析和案例分析为主,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游戏化,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应用游戏模式和机制的游戏化手段(gamification),以及更宏观的社会文化中内蕴游戏玩乐性质的游戏化逻辑(ludification);三是通过实地调查、访谈等方式关注游戏玩家及其玩乐行为,分析他们如何解读游戏的意义和如何通过游戏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
(一)游戏折射社会现实
游戏虽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虚拟空间,但仍遵循着基于规则的秩序,隐喻着现实世界。贾斯伯·尤尔在游戏研究专著《半真实:真实规则与虚拟世界之间的视频游戏》中分析了网络游戏的六个特征并进行总结: “游戏是一个基于规则的系统,有着多变的和可量化的结果(outcomes),不同的结果被赋予不同的价值,玩家付出努力来影响结果,并且对结果产生情感上的依恋,同时,这些活动导致的(现实生活)后果(consequences)是可以协商的。”[8]他认为网络游戏由真实的规则和虚构的世界组成,而游戏规则和游戏虚构之间的互动是网络游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种互动存在于游戏本身的设计、玩家感知和玩游戏的方式和人们讨论游戏的方式,在这些互动中,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盖洛威进一步认为,网络游戏 “与信息时代的政治现实直接同步”[25],是 “我们当代生活的寓言”[26],是人们通过机器玩耍、参与社会化训练的活动,也是创造新的游戏产品和促使游戏产业诞生的认知劳动。游戏中的设定、主题和人们的行为是现实的隐喻,投射着社会的现实存在。
许多学者关注网络游戏在数字媒体时代所发生的媒介变革,认为网络游戏及与之直接关联的媒介变革对于刺激社会活力具有积极的作用。托夫勒[27]认为,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流水线和大众传媒鼓励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和阶级划分,大众媒体传播着由某种中央系统制作的图像和信息,向人们注入所谓的大众思想(mass mind),进而塑造工业生产体系所需要的标准化行为。大众媒体由此延续社会压迫和同质化,使社会呈现出普遍的去人格化特点。但是,网络游戏的个性化则突破了以往媒介环境相对严格和固化的社会等级。数字媒体时代的人们不再屈从于机械化的节奏和例行公事,网络游戏充分体现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传播媒介的解放性特征。数字媒体技术构建了计算机化的社会新秩序,提供了处理信息的多样化工具,赋予了用户和消费者新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例如,微软、索尼和任天堂等有线革命(wired revolutionaries)中的数字化先锋企业,就宣称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公司提供的技术提高效率、解放尊严、实现 “自由” 。游戏中存在的连通性和互动性,还可以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游戏里,通过游戏建立虚拟社区,利用多媒体创造自己的文化,使网络游戏成为实现合作梦想的空间和硅谷式乌托邦[28]。大前研一[29]认为,网络游戏至少从两个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现实处境。一是基于网络游戏的连通性和互动性,人们通过游戏参与人际日常交流和感知全球经济变化,减弱了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二是人们通过游戏角色扮演重新审视世界的基本规则,通过操纵游戏图像掌控自己在游戏中的处境,减轻了日本传统社会中被动服从权威的文化压力。媒介变革使网络游戏与人们现实处境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由此不难理解,在全球化、跨国化的经济逻辑和文化逻辑下,网络游戏受到了普遍欢迎,成为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游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如克莱恩、戴尔-威瑟福德和德普特[30]等就认为,网络游戏是后福特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商品。他们反对关于信息技术的夸张的乐观主义,认为这只不过是技术决定论的新瓶装旧酒。他们认为,互动性的网络游戏空间的确能体现出年轻娱乐受众的活力,游戏制作者也的确比以往更积极地认可和回应玩家对意义协商的参与,但是,无论数字精英(digerati)如何包装,游戏也只是更灵活的生产模式中满足更个性化需求的一种理想化商品。游戏玩家的角色从技术的使用者转向消费者,他们在游戏中体现出的民主潜力不过是数字资本主义和游戏制作者们的合谋结果。尽管如此,研究者公认的是,游戏是一个自愿的、可控的、具有解放意义的空间,游戏的意义由游戏制作者和玩家在协商中共同构建。
(二)现实生活游戏化(gamification vs ludification)
如前所述,网络游戏满足人们理想化的现实期待。玩家可以自愿选择玩或者不玩一个游戏,自主决定如何玩这个游戏,并且在大多数游戏中,游戏规则和可能产生的结果都是相对明确的,玩家因此获得具有确定性的安全感,缓解现实中的系统性压力。 “对很多玩家来说,网络游戏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之外所做的事情,意味着脱离日常生活,意味着安全感和超脱世俗。”[31]早期的媒介研究者放大了游戏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对游戏的娱乐性、玩乐性带有较强的偏见: “自从法兰克福学派时代以来,关于愉悦和快乐的议题一直是媒介政治经济学家的眼中钉肉中刺。”[30]“对网络游戏的研究探讨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都成了一种‘另类阅读’”[3]。事实上,对大多数玩家来说,参与网络游戏的重要目的就是享乐(enjoyment)。无论是在虚拟的网络游戏世界,还是在真实的现实世界,更自由、更轻松地享受快乐是共同人性,因此,游戏并不总是保持着与现实世界的距离。国外的一些游戏学家认为,现实生活中充满游戏化手段,甚至现实世界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本质就是游戏化。
现实生活游戏化的国外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类,分别为gamification研究和ludification研究。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前者有所涉及,对后者则鲜少涉及。这两个英文词汇虽然都可以翻译为 “游戏化” ,但根据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两者的指向有明显的差异。Gamification体现为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网络游戏的设计机制、利用游戏手段将系统性的任务游戏化,表面上纾解了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压力,其实质是实现功利性极强的任务目标,被一些学者批评为实质上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压迫隐藏起来。Gamification因此可以界定为是游戏化手段,或工具式的游戏化。ludification的词根ludic来自拉丁语ludus,有游戏的含义,也有玩笑、戏谑、玩耍等含义,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中,这个词通常与 “文化” 相连,体现为现实文化生活诸领域回归游戏的玩乐、戏耍本质,有时甚至带有反讽的文化逻辑,反映出现实世界文化机理的游戏化,不指向某种功利性的具体目标。Ludification因此可以界定为游戏化逻辑或文化上的游戏化。
具体而言,工具式的游戏化(gamification)充分运用游戏进度的节奏把控、即时满足的奖惩机制和可量化的排位机制等网络游戏设计者用以增强玩家黏性的游戏手段,例如类似游戏血条的工作进度图、用于表现工作阶段性荣誉的动画勋章、学习成绩或工作业绩的动态排行榜、工作学习运动的积分兑奖活动等,激励人们在游戏式的环境中努力达成工作、学习、运动目标。德特丁[32]等人指出,在这种游戏化中,网络游戏中的机制和模式被应用到工作、学习、运动等日常生活场景中,表面上消解了 “严肃、无聊、艰苦” 的活动给人们带来的压力,但同时也消解了游戏的自愿原则和娱乐性质,即时的满足不再成为一种享受。雷[33]的研究成果则表明,工具式的游戏化是带有扮演性质的 “玩乐劳动” (play labor),他将其称为 “playbor” 。在这种劳动里,游戏失去了其本真(innocence),变成 “资本主义醒着的每一刻都在为之努力的殖民的一部分” 。雷的研究已经将工具式的游戏化与意识形态联系。富克斯[34]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工具式的游戏化就是21世纪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嵌入了一种无意识的动力程序(unconscious motivational processes)。在这种程序中,相较于被理性说服或强迫支配,人们更愿意在游戏化的无意识中 “快乐” 地劳动,经济、教育、文化和政治许多事务因此运行得更加顺畅。
文化的游戏化(ludification of culture)理论最早由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媒介理论研究的主席教授乔斯特·雷森斯[35]于2006年提出。他认为,网络游戏在全球的流行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表明 “玩乐” (playfulness)逐渐成为文化的关键属性。网络游戏的玩乐性质不仅表现在游戏领域,还体现在 “那些曾经被认为与游戏相反的领域”[7]。追求 “玩乐” 的游戏进入了传统意义上被认为较为严肃的教育、政治、军事等领域。例如,2010年荷兰新闻媒体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位政客被描绘成一个滑稽的木偶师,他的政治舞台被简化为游乐场。此后,这类将严肃的政治主题进行诙谐和玩乐化表达的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战争领域中,无人机的大量使用,使战斗行为变得如同操纵游戏机一般具有玩乐性。诸如此类,在戏谑、玩乐的游戏化方式中,现实生活中曾视为严肃、庄重的文化现象和主题被消解,游戏的本真在现实世界的文化逻辑中回归。与工具式的游戏化不同,在文化的游戏化中,工作与游戏的区别是模糊的。迪佩尔和菲泽克[36]引入物理学中的干扰模型阐释文化游戏化理论。在干扰模型中,工作和游戏既可以被分开理解,也可以产生叠加和交互。如果人们的工作不是功利性的现实目标,而是来于对玩乐的需要,那么就可以在游戏式的工作中获得乐趣,获得乐趣的游戏行为本身就成为工作。正如游戏开发工程师,既通过游戏开展工作,也在工作中享受游戏的乐趣。文化的游戏化,使工作或劳动出现了新的更有创造性和玩乐性的形式。
(三)游戏玩家的身份认同
如前所述,网络游戏既是虚拟空间,也与现实世界紧密关联。网络游戏的参与者如何在这种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模糊边界中认知自己的相对存在、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是国内学界关于游戏的文化研究中的重点,也是国外学界极为关注的研究命题。
游戏玩家的身份构成丰富、复杂,他们在游戏中沉浸式的丰富体验也提供了关于游戏与身份关系的第一手参考数据,但早期针对游戏玩家的身份认同研究中,游戏玩家的身份依然被少部分人代表,以至于成为刻板印象。例如,对于网络游戏文化的研究较少关注游戏玩家的第一人称视角[8],玩家对游戏的主观认知和解读没有被充分、全面地关照,其根源在于网络游戏文化的话语权被垄断。
“网络游戏的设计建立在极度重视奖励能力和努力的基础上。优异的价值(merit)是游戏内部代码的关键,并且有效地成为一种核心意识形态,决定了游戏的制作和玩法。……网络游戏为玩家提供了一种愿景,即如果你足够努力、足够优秀,你就能走上一条通往权力、财富和无限资源的直接道路。”[37]但是,这种乐观的愿景只针对玩家中的一部分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外。
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International Game Developers Association)于2015年发布的开发者满意度调查报告[38]显示,游戏开发者中有75%为男性,76%为白人。这份报告指出,游戏产业人员的典型肖像是一个32岁左右、拥有大学学历、住在北美、没有孩子的白人男性。由此可见,网络游戏文化话语权主要来自年轻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人群、白人、男性群体。游戏学家肖[39]指出,关于玩家身份的刻板印象将部分玩家排除在游戏话语之外,例如女性玩家、中老年玩家、非异性恋玩家、非西方玩家和非 “铁杆” 玩家(hardcore gamers)但也玩游戏的人。
在关于游戏玩家身份认同的研究中,性别研究又是国外学界关注的重点。2014年,在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名为 “玩家门(#GamerGate)” 的事件,随后在全球引起媒体和传媒学界的广泛关注。在 “玩家门” 事件中,几位女性游戏开发者、政治家、媒体评论人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和骚扰。由于这些暴力和骚扰主要基于性和性别问题,学者因此将这一事件概括为: “女性在游戏界对传统男权至上问题的发声与男性对之的捍卫。”[40]游戏玩家的性别身份问题更加直接地暴露在游戏研究者面前。类似问题在网络游戏领域大量存在,对其进行关注并深入讨论,在国外游戏学界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揭示了如下两方面的文化现象。
一方面,网络游戏世界的话语权由男性玩家主导,网络游戏成为了男性主导(male-dominated)或男性友好型(male-friendly)空间[41]。网络游戏被认为是科技类产业及相关文化的典型范例,而科技类产业和文化中存在一些典型的文化刻板印象,包括但不仅限于,认为男性拥有更高水平的技术技能和智力潜力,甚至 “技术” 这个概念也被想象为具有男性气质(masculinity)。随着数字技术成为强有力的塑造社会形态的影响因子之一,现实世界关于技术的性别话语权力结构,也从线下世界转移到了包括网络游戏在内的线上世界。传统的霸权式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含义随之发生变化,纳入了新的要素,以适应在这个新领域发展所必需的特征。马萨纳里[42]就将 “极客文化” (geek culture)与 “男性气质” (masculinity)这两个概念融合,创造了 “极客男性气质” (geek masculinity)这一新概念。她认为,包括网络游戏玩家在内的极客通常被认为具有专家式技能(expertise)、职业化的知识储备、聪慧的个人气质和智力潜能等特征,但这些特征在极客文化中被特别赋予男性,成为了 “极客男性气质” 。尽管 “极客男性气质” 可能与传统男性气质有细微差异,比如认为极客不擅长或者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在网络游戏等互联网空间,由于 “极客男性气质” 的普遍存在及其在科技相关的文化圈层中的影响力,男性玩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网络游戏等互联网领域的话语掌权者,网络游戏因之成为男性占据优势的空间。
另一方面,女性玩家在网络游戏中产生了更大的孤独感和更强烈的焦虑感。麦克林恩和格里菲斯[41]采取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很多女性玩家参加网络游戏时的积极贡献往往被忽视和不信任,她们为此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又反过来强化了女性玩家在游戏社区或社群中的被孤立状况。比如,她们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在个人资料中设置性别为男、使用男性形象的游戏化身、男性更常用的游戏昵称、使用变声器隐藏自己的女性嗓音等。或者,她们选择独自玩游戏。 “女性玩家几乎已经接受了她们应该单独玩游戏的想法,并且似乎产生了一个共识,即女性应该放弃与其他人一起玩游戏并在游戏中获得社会支持。” 更有甚者,当女性玩家感到无力应对游戏带来的负面情绪时,她们可能放弃继续玩游戏,以减轻心理负担。这种放弃式的抵抗又反过来使女性玩家在网络游戏社群的话语中进一步失声。与之相反,马蒂[43]等人通过案例式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一部分男性玩家会策略性地假扮女性,以寻求其他玩家的支持和帮助,进一步固化了网络游戏文化中关于女性玩家的消极形象和弱势角色。这些男性玩家在游戏中的策略,无关乎他们对自己性别身份的认知,性别身份成为了一种功利性手段。
三、结语
网络游戏是一种相对新生和活力愈显的媒介形态,也是文化研究中一个具体面向的载体。网络游戏文化是当前数字化环境中技术与人的新型关系的表征,是介于社会现实和虚构幻想之间的话语空间。探究网络游戏文化并构建相关的理论体系,有助于人们理解日常生活中随处暗示着、但又巧妙地隐藏起来的文化隐喻,这些隐喻提醒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无意识的常识性经验,并在这种审视中重新定位自身的相对存在。网络游戏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但它并不像镜子那样忠实被动地反射所有现实细节,而是经过有意识地重塑的微缩景观;也并不像镜子有坚硬的玻璃表面,严格地区分真实与虚构的边界,而是动态地、交互性地与现实彼此影响。国内学界对网络游戏文化的研究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案例,引入了多样的研究话语。国外学界的游戏研究起步更早,形成了不断继承、发展、批评、创新、丰富的理论体系。利用国外游戏研究的丰硕成果,化用国外游戏文化研究的相关范式,充分运用国内网络游戏领域的丰富案例,深入讨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游戏文化相关问题,产生与中国正走上世界网络游戏产业浪尖这一地位相匹配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网络游戏文化研究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