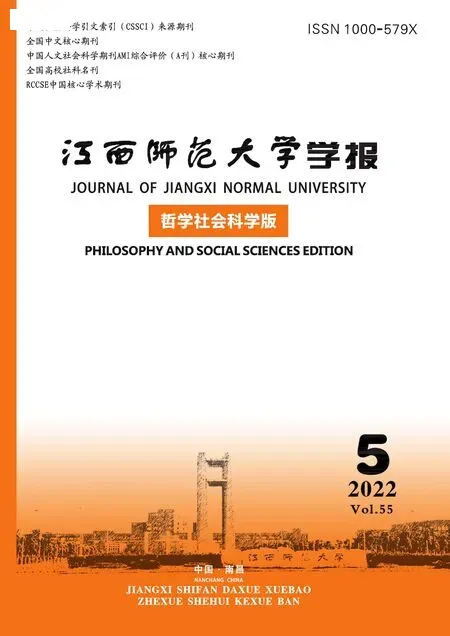从大观园到卞府花园
——论《镜花缘》雅集叙述的焦点转移
陈 庆
(1.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2.韩国首尔大学 人文学研究院,韩国 首尔 08826)
清代嘉庆年间,李汝珍作《镜花缘》,刻意凸显了这部小说与《红楼梦》的承续关系。《红楼梦》有“说来虽近荒唐”“大荒山无稽崖”“倩谁记去作奇传”[1](p1-2)等表述,《镜花缘》则有“茫茫大荒,事涉荒唐,唐时遇唐,流布遐荒”[2](p353)的说法;《红楼梦》说“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1](p235),《镜花缘》则说“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2](p307),《红楼梦》是一部“使闺阁昭传”[1](p1)的书,开卷第一回即是“作者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1](p1)《镜花缘》也把“使闺阁昭传”放在首位,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此书所载,虽闺阁琐事,儿女闲情,然如大家所谓四行者,历历有人:不惟金玉其质,亦且冰雪为心……岂可因事涉杳渺,人有妍媸,一并使之泯灭?”[2](p1)李汝珍的这些话,显然是从《红楼梦》的议论变通发挥而成。
《镜花缘》与《红楼梦》,确实具有明显的可比性,一粟《红楼梦书录》将《镜花缘》列为《红楼梦》“仿作”[3](p145),并非没有理由。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却更需予以关注。本文的宗旨所在,是经由与《红楼梦》的对比,透视《镜花缘》雅集叙述的焦点转移,并就这一写法的成因及其小说史意义略加申说。
一、从悲剧到轻喜剧
《红楼梦》的雅集,始终在大观园中:贾元春晋封贵妃,促成了大观园的产生;而宝黛钗等住进大观园中,则使雅集有了可能。第三十七回,探春说到结社的想法:“历来古人,处名攻利夺之场,犹置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每成千古之佳谈。……风庭月榭,惜未宴集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孰谓雄才莲社,独许须眉;不教雅会东山,让余脂粉耶?”[1](p444)大观园作为这些“能诗会赋的姐妹们”[1](p265)的雅集场所,无疑是般配的。
《镜花缘》的雅集则在卞府花园。“这卞滨……幼饱读诗书,由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世代书香,家资巨富,本地人都称他‘卞万顷’。”[2](p462)卞滨共有七个女儿,依次是宝云、彩云、锦云、紫云、香云、素云、绿云。“卞滨有两个妹子:一个嫁与原任御史台大夫孟谋为妻,一个嫁的就是礼部侍郎孟谟。那孟谋是孟谟的胞兄,早经亡故,存下四个女儿:长名孟兰芝、次孟华芝、三孟芳芝、四孟芸芝。孟谟也有四个女儿,就从孟芸芝排行:五叫孟琼芝,六孟瑶芝、七孟紫芝、八孟玉芝。”[2](p466)卞滨身为礼部尚书,又是首科女试的主考,他的七个女儿,加上她妹妹的八个女儿,一共十五人,在《镜花缘》的百位才女中,占了七分之一强,以卞府花园作为雅集之地,也挺合适。
大观园和卞府花园,一个是黛玉、宝钗、湘云等人的雅集场所,一个是百位才女的雅集场所,在两者似乎大体相近的背后,其实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差异:大观园承载的是一部悲剧,而卞府花园承载的则是一部轻喜剧。
《红楼梦》结构安排的一个特点是,可以根据大观园的兴衰存亡把小说划分为若干单元。开头五回是第一单元,相当于话本小说的楔子,其功能是对全书的内容、人物作含蓄的提示。第六回至第十六回为第二单元,为大观园的出现做了充分铺垫:贾母和元春是大观园的庇护人;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是大观园的主角;凤姐是大观园和贾府之间的纽带;宁荣二府是大观园的依托;这些内容都在第二单元做了交代。第十七回至第二十二回为第三单元,大观园落成,一个理想的雅集场所终于亮相。第二十三回至第三十六回为第四单元,宝玉、黛玉、宝钗等住进大观园中,宝、黛的亲密交往开始具有爱情的意味。黛玉急于证实她在宝玉心中的“唯一性”,用尽了方法试探,经常用“金玉”说事,而宝玉无论怎样剖白他的心事,都没法让黛玉放心。两人之间因此经常吵嘴,甚至弄得贾府上下都知道了。从第三十七回开始,海棠诗社成立,大观园进入极盛:宝玉和园内众姊妹们整日以吟诗作画、宴饮嬉戏为娱,过着一种超然于世俗的生活;贾母两宴大观园,与众人一起听戏、行酒令,热烈而欢愉的氛围弥漫四周;凤姐也专司逗趣之职,“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之类的狠辣算计似乎不复存在。黛玉和宝钗、湘云之间的争风吃醋,也从此告一段落。第五十五回,探春理家,打破了大观园原有的世外桃源的气氛,就连小姐们随意赏花、摘花之乐也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大观园单独开伙之后,不仅带来了世俗的烟火之气,也同时带来了各种家长里短的纷争。而“投鼠忌器宝玉瞒赃”,更是印证了世俗对大观园的挤压。第六十八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标志着大观园的色调已与外面的世界很少差别。此前的凤姐,也经常施展手腕和权术,但从未以大观园作为舞台,当大观园成了王熙凤“借剑杀人”的平台,雅集也就退居幕后了:“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虽努力挽回大观园雅集的颓势,但已无济于事。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王夫人开始了对大观园的强力挤压,她亲自到怡红院布置裁员事宜,第一个被裁的是晴雯,第二个被裁的叫惠香,又名四儿,接下来被裁的是芳官等家班演员,大观园从此充满了肃杀之气。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湘云和黛玉虽努力鼓舞豪兴,吟出的却是“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这样“颓败凄楚”的诗句[1](p996-997)。百无聊赖的宝玉,也终于生了大病。第九十五回,宝玉被迁出了大观园。贾母之所以做出这一决断,是因为院子里空旷少人,给人阴森之感。曾经洋溢着青春气息和欢悦情调的大观园,人越来越少了。当“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在潇湘馆中冷冷清清地离开人世,身边只有李纨、王奶妈、紫鹃等四五个人。大观园已是一派死寂。第一百一回,“大观园月夜警幽魂”,此时的大观园中,虽然还有探春、惜春等住在里面,但那种阴森气氛,已足以令人望而却步。至探春出嫁之日,气氛更加阴郁可怖。在这样的氛围中,一连串发生“锦衣军查抄宁国府”“王熙凤致祸抱羞惭”之类的变故,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第一百十二回,“活冤孽妙姑遭大劫”,当栊翠庵中强徒横行,妙玉“终陷淖泥”[1](p58),大观园和大观园的女儿们,风流云散,《红楼梦》也该落幕了。
《红楼梦》以大观园的兴衰存亡结构全书,或者说,大观园的兴衰存亡构成了《红楼梦》的主干情节。它不只是与一两个人物的悲剧相关,而是与一群女儿、一个家族的悲剧密切相关。
李汝珍写卞府花园,也试图唤起读者对《红楼梦》的联想,在写到百花仙子的雅集时,不时提到“盛筵必散”一类的话题,或与“泣红亭”呼应,点出百花仙子中有几位以悲剧收场。如第六十八回,亭亭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相聚既久,情投意合,岂不知远别为悲?况闺臣妹妹情深义重,尤令人片刻难忘,何忍一旦舍之而去?然天下未有不散的筵席,且喜尚有十日之限,仍可畅聚痛谈。若今日先已如此,以后十日,岂不都成苦境?据我愚见:我们此后既相聚无几,更宜趁时分外欢聚为是。”[2](p502-503)又如第八十一回,孟兰芝、谭蕙芳等所打的谜语,其谜底是“无根水”“尽其道而死者”等,师兰言听了,不禁摇头。盖师兰言精于风鉴,“看玉英、红英、蕙芳、琼芳、书香、秀英六位姐姐面上,都是带著不得善终之像。——那玉英姐姐即使逃得过,也不免一生独守空房。不意这些‘黄泉’‘无根’‘生死’字面,恰恰都出在他们妯娌、姊妹、姑嫂六人之口,岂不可怪!”[2](p601)诸如此类的例证表明,李汝珍是留意到了《红楼梦》雅集叙述之特点的,也努力唤起读者的联想,但他的用意,主要是借读者对《红楼梦》的记忆来维系他们对《镜花缘》的关注,并非要赋予卞府花园承载悲剧的功能。
作为百花仙子雅集场所的卞府花园,在《镜花缘》中并没有经历如大观园一般的兴亡历程。它一直处于同样的状态。在雅集结束、百位才女分别之际,卞府花园也一如既往:“蒋、董、掌、吕四家小姐彼此知会,都禀知父亲,就借卞府邀请众才女聚了一日。闺臣、若花同史幽探诸人也借凝翠馆还席。接著大家又替若花、兰音、红红、亭亭分着饯行。一连聚了几天。那‘长安送别图’诗词竟有数千首,恰恰抄成四本,极尽一时之盛。登时四处轰传,连太后、公主也都赋诗颁赐。”[2](p708)虽说是“盛筵必散”[7](p146),却散得如此风光,如此热烈,欢欣远过于悲切。或者说,大观园终归于荒芜,而卞府花园则始终完好。
在卞府雅集的过程中,有一个潜在的主角,那就是“笑话”。紫芝自然是笑话高手,几乎随时可以说出有趣的笑话来。其他会说笑话的才女,还有不少,如钱玉英,在第八十三回讲了一个讽刺人爱奉承的笑话;如张凤雏,在第八十四回讲了一个调侃人爱自夸其能的笑话;如蒋星辉,在第八十五回讲了一个以常识嘲笑禅宗的笑话;如印巧文,在第八十五回把“我不说,就是说”嫁接在禅宗话头“我不立起,就是立起”之上,众人“不觉大笑”[2](p631-632);如邵红英,在第八十五回讲了一个嘲笑人喜欢攀附的笑话;如掌红珠,在第九十三回讲了一个嘲笑人贪欲无艺而又求长生之术的笑话;如祝题花,在第九十三回讲了一个阴间不收醉鬼的笑话。《红楼梦》中也有一个笑话高手,即王熙凤。写这样一个人物,自有活跃小说气氛的功能,但主要是为了写凤姐的八面玲珑,并与她后来的不再会说笑话相对照,以烘托出贾府由盛而衰的巨大反差。《镜花缘》穿插大量笑话,则旨在引读者发笑,增加可读性。李汝珍颇为自得地说到他的朋友读《镜花缘》的情形:“其友方抱幽忧之疾,读之而解颐、而喷饭,宿疾顿愈。”[2](p760)李汝珍这部小说的魅力,他自己认为,主要在于它的轻喜剧风格,在于它以轻喜剧风格传达了广博的学识才艺。
李汝珍在全书结尾这样讲述他的创作心境:“恰喜欣逢圣世,喜戴尧天,官无催科之扰,家无徭役之劳,玉烛长调,金瓯永奠;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心有余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余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而仅得其事之半。”[2](p760)李汝珍的心境当然不如他说的那样愉悦畅适,但确实不同于曹雪芹立意写一部旷世悲剧,他虽崇拜《红楼梦》,却绝不会写出卞府花园的毁灭;尽管有几个才女惨遭厄运,也不影响总体的情绪基调。他甚至还欣喜地预告:“过了几时,太后病愈,又下一道懿旨,通行天下:来岁仍开女试,并命前科众才女重赴红文宴,预宴者另赐殊恩。此旨一下,早又轰动多少才女,这且按下慢慢交代。”[2](p759)未来绝不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1](p64),而是春暖花开,景色妍和。
二、从雅集主角到游艺道具
《红楼梦》中的雅集,人数最多的一次在第四十九、五十回,参与者在宝钗、黛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和宝玉之外,又新增了宝琴、李绮、李纹、邢岫烟和香菱,如果算上写了“一夜北风紧”[1](p617)的王熙凤,也只有十四人。除了宝琴、李绮、李纹外,每个人都自具面目,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在《红楼梦》雅集中毫无疑问处于主角位置。或者说,雅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表现的平台。
《镜花缘》中的雅集,参与者是百花仙子化身的百位才女,规模比《红楼梦》大多了。李汝珍颇以此自豪,第七十一回借阴若花之口说:“异性姐妹相聚百人之多,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佳话。”[2](p524)阴若花的话,自然是确凿无疑的。所以,蒋春辉同紫芝开玩笑说:“如何没凭据!我们本朝那部《西游记》可是有的?《西游记》上女儿国可是有的?你到女儿国酒楼戏馆去看,只怕异姓姐妹聚在一处的,还成千论万哩。”[2](p524)《西游记》写的虽是“唐僧”的故事,却不是“本朝”(唐朝)的作品,李汝珍故意错乱时代,开个玩笑,无非是为了加深读者的印象:《镜花缘》中才女雅集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红楼梦》。
雅集的规模如此之大,绝大多数才女只能作为龙套人物出现。李汝珍为此设计了紫芝与董青钿赌东道的关目,以便所有龙套人物都有过场机会。第七十三回,董青钿与紫芝打赌,让紫芝“到各处挨著看看众姐妹共分几处,某处几人,共若干人,除了琴棋书画,其余如说的丝毫不错,那才算得好记性,我情愿将手上这副翡翠镯送你;你若说错,就把翡翠壶儿送我”[2](p538)。第七十五回就此做了一番演示。宝云问紫芝:“妹妹可晓得众位姐姐共分几处?”紫芝答道:“姐姐:你等妹子先把这几处念给你听,就明白了:马吊那边是兰言、兰英、兰芳、兰音、玉蟾、玉英、玉芝七位姐姐;双陆那边是琼英、琼芝、红蕖、红萸、红英、红珠六位姐姐;花湖那边是锦枫、锦春、锦心、锦云、萃芳、琼芳六位姐姐;十湖那边是丽蓉、丽楼、丽春、丽辉四位姐姐;象棋那边是小春、小莺、乘珠、祥蓂、月辉、珠钿六位姐姐;投壶那边是婉如、婉春、瑞春、瑞蓂、兰芬、兰荪、紫樱、紫云八位姐姐;秋千那边是凤翾、蘅香、艳春、翠钿、素辉、彩云六位姐姐;品箫那边是亚兰、融春、花钿、芳芝、绿云五位姐姐,共四十八位。还有几处,等妹子看过,再来告诉你,大约青钿妹妹那副镯子是我的了。”[2](p552)第七十七回又有一番类似的演示。第八十八回至九十回,女魁星化身道姑,现身雅集现场,作了一首长诗,以“仿佛诸位才女光景”[2](p660),作用之一也是让百位才女依次亮相。无论是紫芝与董青钿之赌东道,还是女魁星之作长诗,都是写龙套人物的方式。
在整个雅集过程中,李汝珍也用心写了几个人物:例如紫芝、董青钿和花再芳,但她们仍然只是游艺道具。为了充分发挥其道具功能,她们无一例外地被写成了丑角。
紫芝在《镜花缘》下半部的重要性,与上半部的林之洋相当。她的主要职能是插科打诨,特点是说话有趣、长于调侃。第七十回,说起即将开始的雅集,紫芝道:“据我看来:我们大家倒要留神好好顽,将来这些事,只怕还要传哩。若在书上传哩,随他诌去,我还不怕;我只怕传到戏上,把我派作三花脸,变了小丑儿,那才讨人嫌哩。”[2](p516)“三花脸”又叫小花脸,是戏曲中的丑角,正是李汝珍给紫芝的定位。第九十回,女魁星化身道姑,作了一首檃栝百位才女前因后果的长诗,其中有两联是写紫芝的。一联是“嘲说工蟾吊,诙谐任蝶欺”,闺臣一听就知道是说紫芝:“他是座中趣人,与众不同,所以‘郢鼻’之外,又有这个考语。”[2](p674)一联是“白圭原乏玷,碧珷忽呈疵”,紫芝一听就知道是说自己:“这两句我最明白,大约上句说的是诸位姐姐美玉无瑕,下句是我丑态百出了。”花再芳补了一句:“座中就只你爱骂人。”闵兰荪再补一句:“而且你又满嘴乱说。”毕全贞又补了一句:“这句说的不是你是谁!真有自知之明!”[2](p675)如此一再渲染,可以算得浓墨重彩了。
在插科打诨之外,紫芝还有一些民间艺术家通常具备的技能,如讲笑话、说书等。在《镜花缘》中,紫芝说笑话的情节比比皆是,第七十三回,取笑打蟾吊的;第七十四回,取笑下象棋和画画的;第七十五回,取笑打秋千的;第七十八回,取笑贪得无厌、豁拳和故意找茬的人;第八十六回,取笑不会说笑话的人;第八十七回,取笑口吃的人;第九十三回,调侃题花爱听笑话。紫芝说书见于第八十三回。燕紫琼请紫芝替她说个笑话,紫芝也乐意,但绿云说:“紫芝妹妹向来说的大书最好,并且还有宝儿教的小曲儿,紫琼姊姊既饮两杯,何不点他这个?”紫芝公然不惧,说:“如果普席肯饮双杯,我就说段大书。”于是说了一段“子路从而后”至“见其二子焉”,众人纷纷叫好[2](p615)。从绿云的推介和紫芝的自评,可以看出,紫芝擅长多种技艺,足以在雅集时八面受敌。
花再芳同紫芝一样,也经常同人斗嘴。不过,紫芝的斗嘴属于调侃戏谑,花再芳的斗嘴则是“气性不好”[2](p553)。第八十四回,花再芳这样宣示她的人生哲学:“他口口声声只是劝人做好事;要知世间好事甚多,谁有那些闲情逸志去做。——不独没工夫去做,并且也做不了许多。与其有始无终,不能时行方便,倒不如我一善不行的爽快。遇著钱上的方便,我给他一毛不拔,借此也省许多花消;遇著口上的方便,我给他如聋似哑,借此也省许多唇舌。我主意拿的老老的,你纵有通天本领,也无奈我何。行为一定如此,这是牢不可破的。”[2](p628)听上去俨然一介利己主义哲学的代言人。第九十回,小春问女魁星化身的道姑:“世上每有许多好人倒不得善终,那些坏人倒好好结果,这是何意?”道姑答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岂在于此。若只图保全首领,往往遗臭万年。……只要主意拿得稳,生死看得明,那遗臭万年,流芳百世,登时就有分别了。总之: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当其时,与其忍耻贪生,遗臭万年;何如含笑就死,流芳百世。”[2](p678)众才女对这些话都表示认同,唯独花再芳当场提出异议:“妹子情愿无福,宁可多活几时,那怕遗臭万年都使得;若教我自己朝死路走,就是流芳百世,我也不愿。”[2](p680)这些笔墨,都是为了以调侃方式写出一个为一己私欲所囿的人。
董青钿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她和紫芝赌东,出场的频率较高。如第七十六回,紫芝慌忙跑开,来到百药圃,只见史幽探、周庆覃、国瑞徵、孟兰芝远远走来。兰芝问:“妹妹到那里去?”紫芝答道:“我同青钿妹妹赌东,要到各处查查人数。”[2](p561)第七十七回,青钿问:“宝云姐姐唤我有何话说?”紫芝道:“宝云姐姐请你非为别事,要告诉妹妹这个东道你可输了。题花姐姐把烟壶、镯子都给我罢!”青钿道:“姐姐且慢给他。我听他说过前后五十人,至当中五十人还未听见哩。”[2](p564-565)第九十三回,青钿道:“好容易我才捉住一位!请教宝云姐姐:‘夫妇’同‘石首’既不同韵,又不同母,失了承上之令,岂不要罚么?”紫芝道:“我同妹妹格外赌个东道:如宝云姊姊被罚,我也吃一杯;倘你说错,也照此例。你可敢赌?”青钿道:“我就同你赌!”[2](p705-706)一个经常同人扯皮打赌的人,当然也是丑角。
作为道具人物,紫芝、花再芳和董青钿的意义在于,为学识和才艺的展示创造了幽默风趣的氛围。《镜花缘》第二十三回,李汝珍这样介绍《镜花缘》的内容:“上面载著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喷饭。”[2](p163-164)第七十二回具体写了弹琴、下围棋、写扇子、画扇子,即所谓琴棋书画;第七十三回又细致交代,“分了马吊一桌、双陆一桌、象棋一桌、花湖一桌、十湖一桌。余者或投壶、斗草、抛球、秋千之类,……或吟诗、猜谜、垂钓、清谈”[2](p538)。诸如此类的游艺,才是实际上的雅集主角。有了喜剧性道具人物的参与,可以避免把《镜花缘》写成枯燥的知识读本。
《镜花缘》第八十二回至第八十七回,第九十一回至第九十三回,一共九回,全是写行酒令。《红楼梦》中也行过酒令,目的是写人,讲求的是雅俗共赏。《镜花缘》看重的是行令的难度,否则见不出学问。其要求有二:1.用“牙签四五十枝,每枝写上天文、地理、鸟兽、虫鱼、果木、花卉之类,旁边俱注两个小字,或双声,或叠韵。假如掣得天文双声,就在天文内说一双声;如系天文叠韵,就在天文内说一叠韵。说过之后,也照昨日再说一句经史子集之类,即用本字飞觞:或飞上一字,或飞下一字”[2](p606)。2.“凡上家用过之书,一概不准再用,误用的罚两杯另飞。”[2](p610)也就是说,一百位才女,至少要用到一百种书。之所以把难度设得如此之大,是为了显示“才女”之“才”,即紫芝所说:“你们三位可晓得这个才女的‘才’字怎讲?若一百人连百部书也凑不起来,那还称得甚么才女!”[2](p610)李汝珍对他所写的那些双声叠韵的酒令,极为自负,他借春辉之口说:“今日我们所行之令,并非我要自负,实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竟可算得千古独步。”总而言之:“别的酒令,无论前人后人,高过我们的不计其数;若讲双声叠韵之令,妹子斗胆,却有一句比语:石首 《任中丞集》 千载美谈,斯为称首。‘斯为’叠韵,敬宝云姊姊一杯。”[2](p704-705)玉芝因而提议:“妹子明日就将此令按著次序写一小本,买些梨枣好板,雇几个刻工把他刻了,流传于世,岂不好么?”[2](p706)这一句话提示读者,李汝珍写《镜花缘》,用意之一是让这些才艺包括双声叠韵的酒令流传于世。有时为了显示腹笥之博,才女们还会随机展开学术讨论。比如,第八十六回,因兰言提到“《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两句话”,青钿质疑说:“我记得‘……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两句倒像出在刘向《说苑》,怎么说是韩婴《诗外传》呢?”春辉答道:“你把这两部书仔细对去,只怕有几十处都是雷同哩。”[2](p636-637)这是说刘向名下的《说苑》和韩婴名下的《韩诗外传》,有几十处内容相近。李汝珍心目所注,乃是学问、才艺,才女们只是为了展示这些学问、才艺而设计的道具。
三、《镜花缘》雅集叙述的焦点转移:成因与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镜花缘》的雅集叙述,与《红楼梦》相比,焦点显然不同:曹雪芹旨在以悲剧情调传达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感悟,李汝珍则侧重于以轻喜剧风格来书写他的才情、学识和雅趣。《镜花缘》雅集叙述的焦点转移,既反映了乾嘉时代推重学问和才艺的风气,又代表了小说创作中一种新的取向。
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无论是文学,还是才艺,或是学问,都不应该是纯粹技术性的,所谓“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4](p4),所体现的就是这种理念。有些专注于技巧或技术性的文人,例如南朝的梁简文帝、南宋的吴文英,常因此受到批评。韩愈等人抨击六朝骈文,一个理由也是骈文只讲技巧和词藻,而不关心可以改善社会的“道”。再往前推,《韩非子》中那个著名的寓言“棘刺母猴”,也包含了对技艺或技术性的鄙视,甚至不惜把专注于技艺的人视为骗子。
但在乾嘉时代,这个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有所动摇。袁枚提倡“以文为戏”,“艺之精”被认为有其不必依附于社会功用的独立价值。他说:“文之佳恶,实不系乎有用与无用也。”[5](p1550)其《再答陶观察书》这样说明他辞去官职而一心从事于诗文写作的缘由:“尝谓功业报国,文章亦报国……所谓以文章报国者,非必如《贞符》《典引》刻意颂谀而已,但使有鸿丽辨达之作,踔绝古今,使人称某朝文有某氏,则亦未必非邦家之光!”[5](p1484)逞才斗技的次韵叠韵诗就是在这种风气中兴盛起来的。“次韵叠韵之诗,一盛于元、白,再盛于皮、陆,三盛于苏、黄,四盛于乾、嘉间。王兰泉、吴白华、王凤喈、曹来殷、吴企晋诸人,大抵承平无事,居台省清班,日以文酒过从,相聚不过此数人,出游不过此数处,或即景,或咏物,或展观书画,考订金石版本,摩挲古器物,于是争奇斗巧,竟委穷源,而次韵叠韵之作夥矣。”[6](p219)这种次韵叠韵诗,当然说不上社会功用,然而自有其美感和情趣。这一时期盛行的乾嘉朴学,所体现的也是对学问本身的超功利的看重:一代学者精思于文字训诂之间,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古人,他们的目的,并不像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等人那样,志在以实学裨补治化。他们在意的是学问本身的精深与否。“对文字一道,古来文人从审美的角度予以开发,形成了文学的传统;然而文字技艺,钻研未尽,清人于此发皇之,遂致穷奢极侈、尽态极妍,也是不可否认的。”[7](p415)一个人,可以只是学问家,可以只是诗人,而不必道济天下。他们当然也关心世道人心,但是学问和才艺的价值,不需要靠社会功用来证明。
一种想法,一旦成为许多人的想法,尤其是成为主流群体的想法,就有了巨大的影响力。李汝珍就是在这种风气中成长起来的,博学多才,音韵学造诣尤深,所刊行的著作,除了《镜花缘》,还有《李氏音鉴》《受子谱》(1)参见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79年,第513—560页。。《李氏音鉴》共五卷,又《字母五声图》一卷,是一部代表其音韵学成就的书。他是北方人,在南方生活了很长时间,对音韵的南北分合异同,体察入微,又能不囿于习见,所论极为切实。《镜花缘》第三十一回写的那张字母,就是《李氏音鉴》的提纲。《受子谱》一共搜集了二百多种围棋谱,可见李汝珍在围棋方面的精熟程度。“《镜花缘》里论卜(六十五回又七十五回),谈弈(七十三回),论琴(同),论马吊(同),论双陆(七十四回),论射(七十九回),论筹算(同),以及种种灯谜,和那些双声叠韵的酒令,都只是这位多才多艺的名士的随笔游戏。我们现在读这些东西,往往嫌他‘掉书袋’。但我们应该记得这部书是清朝中叶的出产品;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地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8](p529-530)胡适说乾嘉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这话当然是对的,但对乾嘉学术超功利的一面说得还不透彻,对李汝珍本人的理念说得也不透彻。在《镜花缘》第二十四回,李汝珍借淑士国老者之口谈了他改革科举制度的设想:“考试之例,各有不同: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只要精通其一,皆可取得一顶头巾、一领青衫。——若要上进,却非能文不可;至于蓝衫,亦非能文不可得。”[2](p169)言下之意是,考试的目的,不只是选拔做官的人,还要选拔不同知识门类的专业人才,同时也是为了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所以,要提高社会地位,非读书不可;即使是一介平民,也要读书。李汝珍把学问、才艺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连在一起,说明学问、才艺成了衡量人物高下的一个尺度,它本身就有价值,而不是因为其社会功用而有价值。
关于《镜花缘》一书注重学问和才艺的特征,论者多有评述,却不期而然地忽略了与之如影随形的诙谐幽默。如杨懋建《梦华琐簿》说:“嘉庆间新出《镜花缘》一书,《韵鹤轩笔谈》亟称之,推许过当。余独窃不谓然。作者自命为博物君子,不惜獭祭填写,是何不径作类书而必为小说耶?即如放榜谒师之日,百人群饮,行令纠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毕其一日之事。阅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犹津津有味,何其不惮烦也?”[9](p215)钱静方《小说丛考·镜花缘考》说:“此书为北平李松石著。亦系庐陵复辟事,首卷即从敬业起兵叙入,……以下海洋游览,女界论文,则皆作书者借以炫博之辞,无一非空中楼阁矣。”[9](p216)杨懋建和钱静方都忽略了一点,《镜花缘》叙写学问和才艺,努力写得诙谐有趣,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惟经作者匠心,剪裁运用,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10](p204-205)用趣味来统摄学问和才艺,体现了道具人物的价值,也体现了李汝珍所特有的艺术感觉。
从《红楼梦》到《镜花缘》,由雅集叙事的焦点转移所体现的新的创作路向,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普遍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所列“文章经济之作”有夏敬渠《野叟曝言》,“才藻之作”有屠绅《蟫史》、陈球《燕山外史》,“博物多识之作”有李汝珍《镜花缘》,这些小说都产生于乾隆、嘉庆年间[10](目录,p6)。这是一个把学问和才艺趣味化的时代,有人用诗来写,例如翁方钢;有人用小说来写,例如李汝珍,足见一时盛况。只是,以往的研究,对于知识阶层的这种趣味以及这种表达趣味的方式,习惯用挑剔的口气加以谈论,因而鄙薄者多。其实,正如乾嘉朴学有其重要的学术史意义,《镜花缘》所代表的这种趣味以及这种表达趣味的方式,也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和小说史意义。
通常做比较研究的人,习惯于从比较的对象中寻找其相同之处,而本文则致力于寻找《镜花缘》的雅集叙述不同于《红楼梦》之处,这一做法与艺术的特性是吻合的。卡西尔曾说:“在感官知觉中,我们总是满足于认识我们周围事物的一些共同不变的特征。审美经验则是无可比拟地丰富。它孕育着在普通感觉经验中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无限的可能性。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这些可能性成了现实性:它们被显露出来并且有了明确的形态。展示事物各个方面的这种不可穷尽性就是艺术的最大特权之一和最强的魅力之一。”[11](p184)李汝珍以不同于《红楼梦》的雅集书写体现了一种新的艺术风范,作为研究者,当然也不应辜负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