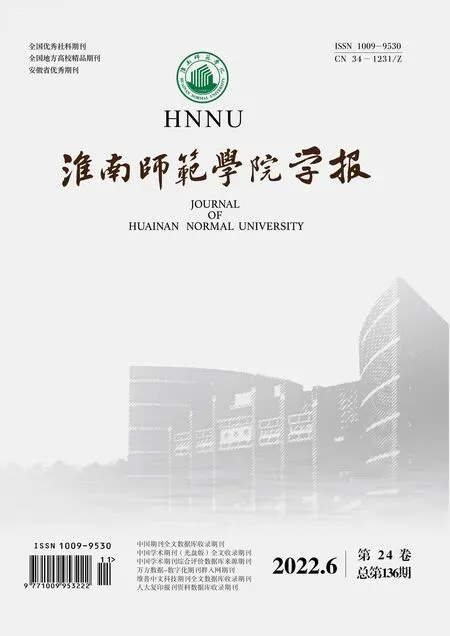新文科建设的理念重构与进路选择
徐兆武
(巢湖学院 文学传媒学院,安徽 合肥 238024)
一、文科的衰落与新文科命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科技革命和数字时代的来临,传统文科的衰落已成为全球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一个理论和现实问题, “文科的衰落” 已成为全世界学者的共识:1828年,黑格尔在一次美学演讲中提出了 “艺术终结” 问题[1](P15),如果黑格尔所说的终结论尚且隐含着新的 “出场” 和 “开始” 的意味,或寄寓某种期待的话,那么1984年阿瑟·丹托从艺术史的角度提出的 “艺术终结论”[2](P262),则预示着现代性的终结带来的艺术终结。1989年,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 》一文,明确提出 “历史终结论”[2](P263),2001 年希利斯·米勒在 《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开篇借用德里达《明信片》中关于文学终结的判定: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3]。 “文学终结论” 的话题遂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世界学者对这一问的关注角度和看法虽各不相同,但都意识到文科教育已深陷危机当中。以文学为例,传统文学的地位日益边缘化,文学的观念发生的深刻变化,文学阅读的衰落,文学共同体逐渐消散,传统文学的媒介正被电子化、数字化取代等等。
为应对文科教育面临的挑战,2017年10月,美国希拉姆学院率先尝试 “新文科” 教育的改革, “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4]但何谓 “新文科” ,其概念和内涵并未进行理论的界定或诠释。
2018年8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文件提出了 “四新” 发展( 即 “新工科” “新医科” “新农科” 和 “新文科” )[5], “新文科” 概念正式提出。 2019 年 4 月 29日,教育部、科技部等13部委正式启动 “六卓越一拔尖” 计划2.0,要求全面推进 “四新” 建设,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5]。随后 “新文科” 引起广泛关注;同年6月20日,时任高教司司长吴岩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的讲话中强调, “我们必须改变教育的形态,必须改变教育的结构,必须改变教育的理念,必须改变教育的标准,必须改变教育的技术,必须改变教育的方法,必须改变教育的评价,必须改变教育的体系。从形式到内容都要来一场革命,从物理变化必须到化学变化。 ”[5]并针对 “新文科” 专门指出: “我们一定要让新文科这个翅膀硬起来,中国高等教育飞得才能平衡、飞得高。”[5]2020 年 11 月 3 日,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在山东威海召开 “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 并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从实践操作层面对新文科建设工作作了宏观部署[6]。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在清华大学师生代表时进一步强调: “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7]由此可见,新文科的建设已经上升到回应社会关切、破解文科发展问题和实施高教战略的高度。
那么,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新文科?如何建设新文科?近年来,学界从新文科的背景、内涵外延、文科专业建设的具体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其中不乏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如樊丽明从 “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化发展、历史新节点与文科新使命、进入新时代与文科中国化、全球新格局和文科国际化” 四个角度分析了新文科建设的内涵”[8];杨灿明从 “时间、空间、世界观和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四个角度探讨了新文科之 “新”[8];刘小兵提出: “建设新文科,一定注意不能遮蔽,要更加凸显文科的本质,即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发展,关注人的全面发展。”[8]富有创建性的观点还有:方延明运用场域理论,从范式建构角度提出要建设 “全文科” 的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关联学科” “三元结构” ,并 “以文、史、哲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引领方向,把数学、外语、数字人文和融媒体技术作为方法论和工具,形成一个要素齐全、缺一不可的内核。”[9]刘振天认为,新文科建设要充分回应 “家-国” 和 “体-用” 两大重要命题,回答好新时代 “家-国” 与 “体-用” “中-西” 与 “古-今” “科-玄” 与 “雅-俗” 等重要命题[10]。
新文科建设问题的讨论,虽然不乏有创建性的理论思考,但也存在一些亟需深入讨论的问题,如:当下的新文科研究存在学科属性判定不明确、理念判断缺乏认识论基础、内涵外延阐述不深入、建设路径泛化等问题。新文科核心理念是什么,跨学科建设是否就能带来融合,新文科建设真正有效的路径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推进新文科建设工作必须厘清的问题,这既是一种理念重构,也关涉到方法论选择。鉴于此,本文拟从人文学科属性判定、理念重构、进路选择几个方面提出个人思考。
二、人文学科性质及其学科归属的重新判定
新文科建设的首要前提,是要厘清人文学科的性质和文科内部之间学科的属性问题,需要从国家层面重新界定文科属性和学科归属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3745-2009)学科分类与代码》将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和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大门类,共设5个门类、62个一级学科或学科群、676个二级学科或学科群、2 382个三级学科[11]。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目录(2022年)》统计,文科类一级学科共有52个,其中哲学2个,经济学8个,法学13个,文学6个,历史学 4 个,管理学 12 个,艺术学 7 个[12]。 1997 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学科、专业依然是目前各学位授予单位招生和人才培养的依据,根据这个目录统计,文科六大门类下的学科、专业多达106个,其中文、史、哲三大门类下的学科、专业共有45个,经、管、法三大学科门类下的学科、专业共有61个[13]。我国现行学科设置的首要基本条件是 “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学科内涵与其他一级学科之间有比较清晰的界限”[12]。可见,学科专业划分的核心理据是 “知识的体系” ,遵循的是科学逻辑。这种以科学统摄人文学科类属的做法与技术理性的越位有关。近代以降,西方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加剧了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越位,催生了以技术切割其他人文学科的现象,企图按照 “知识体系” 的构架,来囊括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从而导致20世纪科技和人文的对立,这种对立又强化了思维模式上的二元对立。
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智能制造和电讯产业的飞速发展,将人类带入了电子时代和数字时代,人文学科也步入了 “数字人文” 时代。在人文学科本已陷入深重危机的时代,简单化的将人文视为科学的一部分,加速了人文学科的危机,忽视了人文学科的最重要的内在属性:人文性。人文学科关涉的是人类生命的意义、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其思维方式不是逻辑推理演绎的方式。
对人文学科的归属进行重新界定,也尤为必要。破除科学主义的宰制,消解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模式,考虑人文学科的内在属性,将人文学科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剥离出来,将现有的五大门类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人文设定为人文学科。建立 “人文学” 的学科概念的同时,还要破除按照知识体系的标准对学科进行界定的做法。或者依据场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采用多维视域的划分,将现有的五大门类重新划定为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四大门类。
三、新文科理念重构的认识论基础
正视中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差异,重新审视当下失语症的原因,将人文学科从科学的宰制中解放出来,并从观念上打破人文作为科学的判定。这是构建新文科建设理念的认识论基础。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逐步奠定了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辨传统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其内在的理路是 “求真” ,这种 “求真” 传统演绎为对自然之理和社会法则的不断探求,从而最终形成 “概念—范畴—理念” 的强大知识体系。中国主流思想是 “向善” ,这种 “向善” 的追求,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思想上重宗法伦理、重道轻器的特点,文化的呈现方式上强调生命体验和道德实践。这种 “求真” 和 “向善” 的差异,直接带来思维上的差异: “求真” 导致倾向于探求 “是” “之所以是” ,从而形成线性思维,文化上带有明显的思辨色彩和高度综合概括的特点; “向善” 更倾向于圆融化转,出入有度,从而形成复返式思维,文化上带有中庸逍遥和不求甚解的特点。这种思维差异决定影响着两种文化的发展走向。
受制于 “求真” “求善” 的传统,中西方在知识的分类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中国古代对知识的分类是以 “人” 为尺度的,这个 “人” 指的是社会的、抽象的人,而非个体的、自然的人,更多指向社会性、道德情感、社会关系等范畴。即实际是按照事物与人的关系作为分类的根据,带有很强的功能性和伦理性特点。因此,中国古代文化重人文而轻科学,始终将科学视为 “用” 的范畴,不会上升到 “体” 的高度。如《论语》涉及自然方面的内容多达54条,但都是 “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14](P2)而西方对知识的划分是以自然为基点的,即根据事物本质及其关联逻辑作为分类的依据,所谓 “以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 ,推动西方科学的发展。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越位已是不争的事实。自尼采喊出 “上帝死了” 之后,福柯进一步指出了 “人之死” ,这里的 “人之死” 又直接指向了 “人文科学” 的 “人” 之死和欲望主体应该死。在他诸多颠覆性的著述中,无论是从内容上对权力与知识生成与变化的考察,有关知识的 “考古学” 和 “谱系学” 的生成和建构,还是从方法上对尼采谱系学的吸纳,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扬弃,都是指向对主体性的解构,其思路仍然是实证的、科学主义的老路。这种理路并没有背离西方文化思维的传统,而是更强化了科学主义之维中的技术理性思维。福柯的颠覆性理论在当代西方的巨大影响,加速了对 “文学之死” 的认同。
另外, “失语症” ,其实还有一个文科教育本身的问题,就是过于精细的学科专业划分,导致文科素养的严重缺失。懂外语的,可能文科素养不好;文科素养好的,可能又面临着外语的障碍。这影响言说自己和诠释中国故事的能力。
四、新文科建设理念重构的价值预设
建设什么样的新文科,关键在于树立什么样的理念。首先要破除将人文学科视为人文科学的判断。人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其重要的传承方式是涵咏化感,是哲学的、审美的、情感的、价值的、超越的,其指向是人化的,即文以化人。而科学探求的是自然或社会事物(事理)之间的本质或内在关联性,倾心于系统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其指向是物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学科并不是科学,应该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 “学科” 的最初含义。
在西方, “学科” (discipline)的含义,兼有古希腊文的 “教” 和拉丁文的 “学” 的意思,类似中国古代的 “学问” 。《学记》载: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15](P21)这说明了学和教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方法论意义。 “在中国古代做学问的天地中,学与觉通,学与问通。学问与思想息息相通。内在的省悟与外向的求索合而为一,一向是中国人治学的基本方法,由此构成了中国古代人独特的治学逻辑。” “其实中国先秦诸子在学问观上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了一套融通体悟式的逻辑方法。”[16]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人文学科,人文学科的内在属性就不会被误判。
但有所不同的是,在古拉丁文中, “discipline” 一词兼有知识体系和权力之意。《牛津英语词典》中, “discipline” 的释义有 “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 等[17](P384-385)。由此看出,学科其实包含有在一定场域(学术领域)内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以及按照这种知识体系而进行的规训行为,从而这种知识体系又在有形无形中产生了某种权力。可能正由于此,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学科也在加速度地细分而日益精专化,现代大学制度与学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双向同构。学科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历史概念,是指知识与权力的生产与变化,所谓学术共同体的产生,可能也隐含了某种学术权力的意味。伯顿·克拉克感慨: “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 “主宰学者工作生活的力量是学科而不是所在院校”[18](P33-35)。正是这种知识生产的组织模式和体制化运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文学科建设。
建设新文科,应能回应后现代语境下 “人” 的根本性问题,立足于现实反思,回归具有时代新质的人文教育,并回应社会关切。这要求在理念设定上应注重价值向度的选择。新文科建设的理念应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为核心,从马克主义的人学思想的社会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三个向度重构;在建设理路上,应该注重新思维、新方法的融合,将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和生命情怀融汇文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五、超学科:新文科建设的进路选择
(一)明晰跨界融合的限度
跨学科研究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其实就是文学、哲学和诗学的比较研究。《论语》中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更是强调文学、道德伦理和音乐三位一体,旨在以礼乐并论调和伦理秩序,以至于大同世界。 “六经皆史” ,说的是将文学、艺术、伦理、哲学与历史统摄;《文心雕龙》是融文学、政治、文化、哲学为一炉;《庄子》既是文学文本,也是哲学文本。纵观中西传统,文史哲融通,其实并不是单纯地学科组合与交叉,更深层次上是观念、思维、范式的融合。
目前文学的跨界研究主要表现为跨学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两个方面。跨学科主要涉及文学与哲学,文学与艺术(音乐、绘画、戏剧与影视等),文学与社会科学(社会学、统计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文学与生态学,文学与人类学等的关系;跨文化研究主要涉及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媒介,文学与人文(哲学、历史、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文学与科技(当下凸显为信息科学),文学与生态环境等的关联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文科建设需要充分考虑 “数字人文” 带来的新变,将信息技术融入文科建设,在原有文科基础上,整合新资源、搭建新载体、创新新模式、开拓新路径。
(二)超学科:新文科建设进路的应然选择
跨界融合,被视为新文科建设的必要进路,但跨界是否就能融合;跨界融合有没有向度和限度;上述各学科之间能否跨越重组为新的学科领域,量化的累加能否带来全新的具有质性特征的新文科;这种理论的预设,能否带来实践性的价值效用,化解这些困惑,需要突破跨学科的认识层面,用 “超学科” 理念引领新文科建设。
20世纪70年代,超学科概念已经出现。超学科并不是对学科的消解,完全超越于学科之外,也不是指向单纯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而是强调学科与学科之间、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甚至涉及文化场域的跨越。因此,超学科实际上代表着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下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研究范式和方法论。 “超学科性的核心思想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与各行从业者共同工作去解决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19]。因此,新文科建设既要考虑人文学科作为学科已然现实形态,也要考虑其超学科性。
文科的学科根本属性是其 “质的规定性” ,涉及价值、审美和人文等属性,它们不是单向度的和单质的,文科教育也不能局限于其中某一单一的维度。实际上,文科教育离不开思想道德、社会伦理、生命和价值教育的有机融合,只有融合适恰有度,才可能真正既提升审美素养和人文品质,又能获得文史哲综合素质的融汇性提升。开展新文科建设就是要在打通学科壁垒的基础上,实现学科与学科、学科与非学科,甚至教育和文化场域的互融互通。这需要通过超学科思维来提升思维能力、判断力、思想力,砥砺品格,铸造人格。
陈平原指出: “教育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制度建设,还是一个专门学科、一种思想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套文本系统”[20]。撇开制度层面不谈,文学教育的重点应立足于社会实践、专门学科、思想方式、文本系统四个方面,而社会实践和思想方式应是当下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的因素。文学教育作为一种 “思想方式” ,既是一种范式,又是一种方法,它有待于训练熏陶。文学教育当然离不开文学 “经典化” 的涵咏浸润,也离不开跨学科和跨界的互渗融汇。1928年8月,杨振声担任 “国立清华大学” (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决议改组 “清华学校” 为 “国立清华大学” )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第二天,他就和朱自清商订 “中文系的草创计划” ,明确提出 “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和中外文学的融会。”[21](P396)1931 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概况》一文中,也明确说到杨振声主持中文系时,提出的新目标就是 “创造这个时代的新文学。 ”[22](P146)为此,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课程除纯文学外,还涉及哲学、历史、音韵、考古学等。这与当时中央大学等高校的中国文学系只开设国学课程相比,无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重大创举。正是这种垮学科和跨界的课程设置,树立了当时文科教育的标杆,一直影响到后来的西南联大。可以说,这就是当时的新文科。
(三)场域:新文科建设的路径拓展
文科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知识文化的再生产活动。 “在文学生产和流播的过程中大学体制——包括课堂讲授以及朋友、师生、同事之间的互相提携,构成了另一个重要的‘文学场’”[12]。文科教育既要考虑到 “知识技能—过程方法” 二维目标,还应关注 “情感态度价值观” 的三维目标,所以,要注重文化、教育场域在文科教育过程中的浸润作用。这就需要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重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关注社会实践在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价体系以及整个培养过程中的作用。以 “场域理论” 的核心理念重构 “第二课堂” ,并与第一课堂有效融合,应成为文科教育之实践教育的重要改革核心工作。同时,在人才培养的系列体系中,考虑跨界融合的聚合作用,打破学科边界;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要打破物理属性的教育场馆的边界,不能简单化地将教育的场域视为一个固定物理空间,或者简单化切割为某几个领域。挖掘教育场域内有生气、有内驱力和潜在力一切因素,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是推进文科实践教育的重要路径。当前,部分高校所推行的 “书院制” 改革就是很好的探索。
总之,新文科建设要深刻认识文科教育的内在本质,充分发挥以文化人,培根铸魂的功能,厘清跨界的向度和限度;遵循文科教育规律,坚持守正创新,融汇人文教育与价值教育,真正发挥文化传承和价值引领的作用。这不仅关系到文科学科建设的实效,更关涉到文科教育功能的发挥。只有这样,才能正真实现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作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