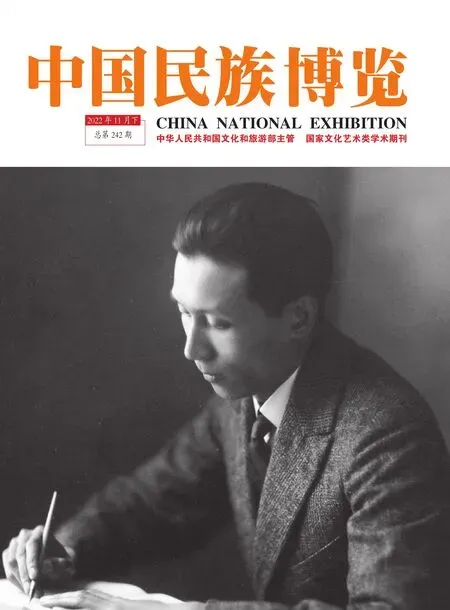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与审美特色解析
李嘉欣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引言
中国传统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由历史特定创作主体创造,因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社会状态、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逐步发展变迁,最终呈现出某种特有的规律形态特点。
近年来,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与审美特色等内容的研究,已属国内相关音乐理论群体的重点研究范畴。据悉,中国传统音乐各类专著皆重视概念观点的解构,且相关知识性论文亦多以单视角观照,侧重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内部某种单一性质特点,如仅针对“同均三宫”理论进行研究或唯美学核心理念“中和之美”之思想进行论证,然以实例为据,全面系统化解析中国传统音乐形态与审美方面的文章甚少。故而,部分受众群体只知其一或只知其然,而非知其所以然,仅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便无法全面体悟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与审美特色的内在精髓,更无法辩证分析传统音乐事象中表现出的音乐形态与审美的准确性。文章将通过实例分析,系统化论证中国传统音乐历时性发展所承续的文化特征恒定现象,一以贯之,更为深刻地体悟中国传统音乐所独具风格的表现形态与风雅高尚的审美品格。
一、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解析
(一)三律并用律制
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之一三律并用律制,即三分损益律、纯律、十二平均律三种律制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共同被使用。三分损益律最早见于《管子·地员篇》,其主要推算方式是将乐器弦长平分三段,舍去三分之一长度视为三分损一,增加三分之一视为三分益一,故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即形成宫、商、角、徵、羽中国传统五声音阶,另三分损益律并非仅生五正音,以此推算下去,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三分损益律亦可求得十二律。纯律起源于欧洲,是以琴的泛音列中第二分音与三分音之间的纯五度,第四分音与五分音间的大三度为基础,形成的一种律制。十二平均律最早开始被使用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其理论的出现是在1584 年朱载堉所作的《律学新说》中,将一个八度平均分为十二个相邻音律间完全相等的半音律制关系即十二平均律。此三律在中国古代并用现象繁多,中国民间“点笙”校音将互为四度或五度的两管同吹,判断其音高和谐进行音准校对,故传统笙所用律制为三分损益律。琴的律制主要由徽位所决定,十三徽中三、六、八、十一徽从比值角度看,其分母均为五,视为纯律所独有,《碣石调幽兰》《广陵散》等琴曲所使用的泛皆是纯律使用的绝对例证。此外,琴取音具有两种律制,泛、按、散三种方式中,可使用三分损益律推算弦长比值确定徽分,然部分徽分的产生亦需靠纯律求得,散声音高调律可使用三分损益律制,但其律制仅可决定散音律高,不可决定琴律的整体律制性质,因此琴律律制主要以纯律为主,但琴律以综合角度看,三分损益律与纯律皆被运用其中,属复合律制乐器。十二平均律理论在有品乐器中使用较丰富,琵琶、阮咸、月琴等皆使用十二律制,传统社会中以“柱”(品)来确定此类乐器音高,每一柱可确定几条弦上的音高,因柱为直状,不为曲状,在同柱异弦中无法产生纯律中的大小两个全音,故而只能使大全音缩小,小全音扩大,柱位要求两个半音构成一个全音,此方法只适用十二律制,故有品乐器皆以十二平均律制为基准。综上,三种律制中相关乐器进行器乐合奏的形式,应是三律并用之现象,杨荫浏先生在其文章《三律考》中提到:南朝宋、齐时清商乐的平、清、瑟三调中,都是琴、笙与琵琶并用;隋、唐九、十部乐的清乐中,亦是琴、笙与琵琶并用演奏;宋人临五代周文矩的《宫中图》中有琴阮合奏的部分。隋唐时期,隋高祖杨坚对宫廷礼乐制度进行实施,其中宫廷音乐表演有宫悬、登歌、殿庭、鼓吹、房中乐、内廷六部,据《隋书》记载:“高祖既受命,定令,宫悬四面各二虡,通十二镈钟,为二十虡。虡各一人。建鼓四人,柷敔各一人。歌、琴、瑟、萧、筑、筝、掐筝、卧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编磬下。笙、竽、长笛、横笛、箫、筚篥、篪、埙,四面各八人,在编钟下,舞各八佾。宫悬簨虡,金五博山,饰以旒苏树羽。其乐器应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庙加五色漆画。天神悬内加雷鼓,地祇加灵鼓,宗庙加路鼓……。”此为隋唐时期宫廷音乐使用三律并用之例证。另外唐墓壁画中李寿墓乐舞图像石椁内线刻乐舞图像共三幅,石椁北壁线刻坐式奏乐图像 、石椁东壁线刻立奏乐伎图像、墓室北壁乐舞图像,三幅壁画中女伎所持乐器皆有琵琶、五弦、笙、竖箜篌等乐器。由此可见,三律并用制在中国传统音乐中使用较普遍。
(二)五声性旋法和三种音阶并存
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之二五声性旋法和三种音阶并存,中国传统音乐普遍使用无半音五声音阶调式,传统民歌的五声性旋法使用较为典型,江苏民歌《孟姜女》(小调·春调)属G 宫D 徵调式,旋律主要使用了G、A、B、D、E 五正声,另出现一次偏音升F;原载《小慧集》中的《鲜花调》以工尺谱记谱,属F 宫C 徵调式,旋律仅使用了以F 为宫音的五正声;另外,矮腔山歌中的《放马山歌》虽仅采用了四个音,但仍然可通过大三度判定其宫音,属D 宫B 羽调式,虽仅采用宫、商、角、羽四正声,但仍归五声性旋法的范畴。传统音乐中采用五声性旋法者居多,此三例仅代表中国传统音乐五声性旋法作品中的一角。以传统五声音阶为基础,加入两个偏音,因偏音的不同而形成三种传统七声音阶,这三种七声音阶具有不同名称说法,在此采用黄翔鹏说,正声音阶加入的二偏音为中、变;下徵音阶加入和、变二音;清商音阶加入和、闰,因此形成色彩效果不同的三种七声音阶。此三种音阶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并存且出现并用现象,黄翔鹏先生以“同均三宫”角度做了论述。姜白石所作《白石道人歌曲》以杨荫浏先生译谱为依据,其中《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惜红衣》三首作品,黄先生认为是“同均三宫”的例证,其三首皆属F 韵,F 韵中的三宫为F 宫、C 宫、G 宫,其中《杏花天影》以大三度定宫角之理论,因F 音处强拍强位,故此作品为F 宫,之后可得其五正声,另外作品中的偏音降B 全部还原,根据正声音阶四五级与七八级半音特点,得出作品《杏花天影》为F 韵F 宫正声音阶D 羽调式;《醉吟商小品》以F 韵为基础,根据大三度定宫角,小二度定正变的方式,认为G 音处强拍强位,降B 得到还原,与G 音形成大三度关系,故《醉吟商小品》属G 宫,偏音为C、F 二音,其中三四级与六七级音形成半音关系,得出《醉吟商小品》为F 韵G 宫清商音阶G 宫调式;《惜红衣》依照前例,C 音处强拍强位,另作品小序曾有说明:“丁未之夏,予游千岩,数往来红香中,自度此曲,以无射宫歌之。”根据参考文献所提供,当时“黄钟”音高应为D,基于此,无射音高应为C 音,再根据下徵音阶特点,《惜红衣》实为F 均C 宫下徵音阶C 宫调式。以此三首作品为例,所使用的三种音阶皆以F 为韵,分别以F、C、G 为宫,音阶内所构成的音完全相同,因此姜白石三首作品可证“同均三宫”之理论。另外内蒙古西路二人台牌子曲《出鼓子》在部分文献中被视为“同均三宫”理论在同首作品中完整运用的实例,此作品以三小段合一遍循环三次加以尾声结束,其三小段皆以降E 为均,一小段以F 为宫,应为降E 均F 宫清商音阶F 宫调式,二小段为降E 均降B 宫下徵音阶F 徵调式,三小段为降E 均降E 宫正声音阶降E 宫调式,其中第三小段将降A 还原,因此《出鼓子》主旋律中三小段皆以降E 为均,所用音阶内的音完全相同,此例被部分学者认定为同首作品中使用“同均三宫”理论的实证。
(三)节奏节拍的散整结合与慢、中、快的发展规律
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之三节奏节拍的散整结合与慢、中、快的发展规律,中国传统音乐中节拍可分均分律动与非均分律动两种,均分律动在传统音乐作品中表现为有规律的节拍运动方式,时值及强弱等形态分明,在戏曲基础板式结构中,一眼板、三眼板、无眼板皆属均分律动节拍,且欧洲音乐体系作品节拍规律亦以均分律动为主。非均分律动以节拍无规则弹性伸缩为特点,善于表达情感张力,以戏曲音乐中的散板与无板无眼两种板式结构最为典型。中国传统音乐节拍特点将均分律动与非均分律动结合使用的现象较普遍,以唢呐为主奏乐器,辅以笙、竹笛等乐器伴奏的民间吹打乐合奏曲《百鸟朝凤》,版本以河南版与山东版乐谱使用最为普遍,在此以山东版《百鸟朝凤》为例,全曲共分八段,其中莺歌燕舞与百鸟朝凤两乐段,采用唢呐仿不同鸟类鸣叫的非均分律动节拍与笙等伴奏乐器演奏的均分律动节拍两者相结合的节奏形式展现,另外并翅凌空乐段亦以此种散整节拍特点结尾,除山雀啼晓使用非均分律动节奏引入,其余四乐段基本采用均分律动节拍进行,这种特殊的节拍特征,致该作品形态表现力丰富,内容饱满,故传统器乐曲《百鸟朝凤》为中国传统音乐散整结合节拍特征的典型作品。除此之外,戏曲音乐中亦擅用散整结合节拍,如摇板,又可称紧打慢唱,即以散板唱腔结合胡琴或板鼓的流水板伴奏形成的特殊板式结构,传统京剧《龙凤阁》中《二进宫》选段徐延昭与杨波之间的唱词:“探罢皇陵到昭阳,宫门上锁是贼李良。铜锤付与大人掌,击开宫门见皇娘。”即是二簧摇板的运用,此例亦可论证传统音乐散整结合的节拍形态。因中国传统音乐中均分律动与非均分律动的结合使用,致其形成散、慢、中、快、散的节奏发展规律。由刘天华先生于1927 年创作的琵琶传统独奏作品《改进操》,引子部分为庄严的散板;第一乐段节奏发展规律由极慢板进行到行板再至中板;第二段以慢速引子承上启下后迅速进入快板段落,再接行板双弹三指轮技法进行演奏,二段结尾处以慢板速度的过渡句收束,尾声速度发展逐渐转慢,形成类似散板的节奏形式。《改进操》这首作品的基础结构以散、慢、中、快、散的传统发展规律为核心,反映了作者由清浅淡泊到不能自已的情绪变化,体现了对国乐改革发展的急切心情与美好愿望,并富有坚定信念。此外,陕西民歌《走西口》亦是散、慢、中、快、散的节奏发展规律,传统民歌作品中不乏此种结构形态特征的作品呈现。
(四)乐音的带腔性
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之四乐音的带腔性,传统音乐中带腔的音并非两音之间的关系,而是某些独立音自身产生的音过程的不稳定性效果,欧洲音乐体系中音与音相连以直线式发展形态为主,单音的音过程亦以直线式状态呈现,而中国传统音乐中讲求音乐流线式发展形态,单音过程发展亦以曲线规律进行。中国传统音乐中所述带腔的音并非与特定作品旋律离散,而属某特定音中的成分概念,某特定音在发展过程中,因音高、音色、力度等因素影响使作品神韵发生微妙变化,即带腔的音。带腔的音在中国传统音乐各分支中占主导地位,琴曲《秋江夜泊》减字谱中即有充分证明,该曲分四段接以尾声,带腔的音具体体现于作品技法的吟、猱、绰、注之中,“吟猱”技法为左手上下颤动特定音产生的音过程;“绰”技法指左手以特定音为基准上滑;“注”与之相反为下滑,该作品中特定音以左手颤动或上下滑音产生的其音过程即是带腔的音的体现,除《秋江夜泊》外,古琴大量作品中亦使用吟、猱、绰、注技法皆可论证乐音的带腔性特点。刘天华先生创作的琵琶传统作品《虚籁》在演奏技法上借鉴古琴技法,运用吟、揉、绰、注、推、拉等技法表现乐音带腔性的形态特征,除此之外,戏曲音乐中的啜腔、叠腔、擞腔等戏曲演唱口法亦属戏曲音乐带腔性的表现。
(五)音高定量与时值定性相结合的记谱法
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之五音高定量与时值定性相结合的记谱法,中国传统音乐中所使用的记谱法有四种,文字谱、指法谱、图文谱、实物谱,其中常用文字谱与指法谱记谱。以定量角度看在多数记谱法中对音高的标注详尽,贮香主人所辑《小慧集》工尺谱记谱以合、 四、一、上、尺、工等字表示具体音高,甚至在古琴文字谱与减字谱中通过“弦次”与“徽分”交汇点可记录出比半音关系更为精准的“微分音”关系,琴谱与唐琵琶谱中记录的指法与演奏方式还可体现部分音色、力度变化的音过程。虽如此,然少数记谱法中仍有定性原则存在,北京智化寺京音乐是现存以俗字谱与工尺谱混合使用的骨干谱式,因其仅记有骨干音,演奏时需进行音乐作品的重复作曲,故属少数记谱法中音高的定性原则。《千秋岁》的原谱只记有骨干音,演奏谱在骨干音框架基础上加花润饰,演奏时再进行实际分析演奏;《观灯赞》中使用的“阿口”技巧亦可显示出音高的定性,此所谓“骨谱肉腔,谱简声繁”。虽有少量乐谱显示音高的定性特点,然而这并不能决定中国传统音乐脱离了音高的定量原则范畴,中国传统音乐大量乐谱仍然主要以音高定量形态特征为主。在时值方面,中国传统音乐却表现出大量的定性原则,现存最早减字谱琴曲《古怨》(姜白石作)用不同减笔字结合成的复合文字表示指法、弦位、徽位,音高定量的同时,时值方面虽通过实际演奏手法及动作可判断出少量的节奏逻辑,但仅在局部体现,即使译谱亦无法得到完整呈现,实际演奏中需再度自行把握;姜白石词调歌曲17 首采用俗字谱记谱法,其节奏时值方面无法通过技法标记臆断部分时值,故相比琴曲谱更难体现时值的定量,其究竟一字一音或一字多音无从查证。部分古谱中虽有节奏标识,如唐琵琶谱中用“丁”表示延长、“大小字”表示附点节奏,但节拍时值的准确性依然不能达到完全的定量原则,依旧靠译谱或演奏者的定性揣摩进行再度创作。由此可见,中国传统音乐在记谱法中多以音高的定量与时值的定性相结合的形态特征为主。
(六)音乐发展形态的单音性
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之六音乐发展形态的单音性,以单旋律织体为主体结构。欧洲音乐旋律发展主要以纵向发展思维构成,音与音之间无论是纵向结合的和声形式,亦或横向组合的连接形式,都多数强调音与音间的功能性特征。中国传统音乐的音响表现形式则与欧洲思想理论相反,其主要以横向思维为主,旋律织体以横向发展居多。戏曲音乐、说唱音乐的唱腔与伴奏间、器乐组合形式间可能存在复合型旋律织体,但此种旋律亦以横向方式展开,造成纵向发展效果。民间歌曲劳动号子、山歌、小调以极简歌词构成单旋律横向发展形态,其中部分多声部民歌可能具有复音型特征,但旋律发展状态并没有发生质变,多声部民歌中《星星月亮永远在一起》《起伏懒大桡号子》以接应型的一领众和形式进行,其和部与领部头尾相接,部分音重叠,但其音响形式仍以横向发展为主;支声性织体形态的多声部民歌《唱相思》《萨拉耶》等虽大部分声部重叠产生纵向效果,然声部间源于同一旋律主题居多,亦算不得纵向思维发展;主调性织体中的复声旋律,其主要以长音持续与节奏型铺垫为主,真正使用不同材料构成复调型织体的民歌很少,由此,中国传统多声部民歌从宏观角度来看,音响表现形式应为单声性织体结构。音响形式的单一性并非效果的单一,京剧《霸王别姬》虽主要使用皮黄腔声腔系统,旋律织体单一,然通过板式、速度、行腔等因素,使作品人物刻画更加鲜明;《碣石调·幽兰》《潇湘水云》等琴曲使用特殊技法,将单声织体旋律加花润饰,音过程体现得别有韵味。
二、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特色解析
(一)空灵之美
音乐美学思想“空灵之美”为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特色之一,是道家主要倡导的哲学概念,中国传统音乐追求“以虚见实”“实中映虚”“虚实一体”的空灵意境。西方传统音乐注重表达“真实”的理念,无论是展现浪漫主义情感,亦或是各类抒情性作品的演奏,皆要求所表达的内容真切强烈,加之西方音乐错综复杂的和声织体关系,更加突出其音乐“实”的特性。中国传统音乐恰与之相反,其求虚见实、致和致虚、虚实交融之态于传统音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是写实作品,其核心内容也非“实象”。著名二胡曲《二泉映月》,其母题以描写水中映月的自然题材为表象,而核心反映作者悲惨凄凉一生的命运,以月冷泉清的“实”,凸显不幸境遇之“虚”,便是传统音乐“空灵之美”的审美体现。另琴曲《梅花三弄》,亦是以描写“梅花”的“实象”,颂扬“不畏严寒,高洁顽强”品格之“虚象”,以“实象”为基础,表现作品中特殊的气韵与意境,营造缥缈之感,呈现传统音乐音实意虚的“空灵之美”。
(二)自然之美
音乐美学思想“自然之美”为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特色之二,即一切源于天地万物之间,无刻意而为所形成的音声,其审美趋于自然,反对人为控制。中国传统音乐中许多器乐曲以自然为母题,《春江花月夜》《流水》《梅花三弄》等,其题材中有描写月的宁静、山水的浩渺、草木的气节,皆是表现“自然之美”之态。另外,中国传统乐器的材质亦是崇尚自然属性为主,其八音中除“金”之外,石、土、革、丝、木、匏、竹皆属自然材质。另外传统音乐中不乏拟声之乐,《平沙落雁》《百鸟朝凤》并非大自然中的真实鸟叫,而是借以自然之声入乐曲之中,似鸟叫而又非鸟叫,音乐与自然完美结合,此尽是“自然之美”的表现。
(三)中和之美
美学核心思想“中和之美”为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特色之三,《论语·八佾》有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传统音乐“中和之美”的思想基础源于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与先秦尚和思想相结合,古人信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从而使传统音乐受到“以和为美”的思想教化,形成“中和之美”的美学观念。“中和之美”在音乐中的体现讲求音乐的精神文明修养,喜怒哀乐非极致,和谐、稳定、敦厚、温和更与之相宜。中国传统音乐的题材中,以“景”为和的题材占据三分之二之多,琴曲《梅花三弄》《潇湘水云》《碣石调·幽兰》《流水》;琵琶曲《飞花点翠》《汉宫秋月》《春江花月夜》《月儿高》等皆以“景”为和。琴曲《碣石调·幽兰》借兰花品格表达对未来充满希望之情,作品不仅展现自然之美,更寄以精神境界的感悟,道与人相知融合,体现潇洒超脱的思想理念,为琴曲“中和之美”之展现。另以传统音乐结构角度看,其多以统一为基础,结构段落间不讲求材料的搭配连接,一切皆自然形成,段落之间流畅融合,便是以自然体现中和之美的表现。琴曲《流水》以多段连缀结构形态展开,以散慢中快散为基础的结构布局,利用特殊技法,再现山河不同情态,此曲各段非功能性连接,并以传统音乐的速度形式为基准,体现由浅及深的景象发展,皆借景抚琴,洋洋乎志在流水,琴曲与自然合一,《琴赋》所述:“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是为琴与琴曲之“中和之美”。
(四)写意
美学原则“写意”为中国传统音乐审美特色之最高境界,传统音乐追求“写意”之最高境界,以形写意,以意为先;不求形似,而求神似;不似而似,变实未变。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以“形”与“神”、“意”与“象”的对立统一辩证的哲学思想为主,《淮南子》对“形神”之记载:“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也”,“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易传》对“意象”之阐发:“立象以尽意”,中国传统音乐并非写实,其追求“非具象性”特征,托物咏情,而非将物象形态特征完全刻画,其追求内在精神神韵,超脱物象之实,任何音乐现象背后皆附以“意”的表达,追求超脱的“弦外之音”,为刻画更深的意境之美。传统音乐之作中《流水》并非真实的流水之声;《平沙落雁》亦非切实大雁鸣叫之态,这便是中国传统音乐之“写意”的美学思想;传统音乐记谱法中的定性定量原则,追求作品一曲多面,以定性原则给予演奏者自由展现,亦为“写意”美学之象;琵琶传统作品《春江花月夜》其中的标题与分段小标题以“诗意性”为准则,具有强烈“写意”效果,《二泉映月》亦可体现;音响特点中,《春江花月夜》首句散板便由琵琶模仿钟鼓声推进,并非物象的完全刻画,而以求神似追求形似之态,皆是得意之象之表现;托物咏情作品《梅花三弄》,通过梅花高洁,不屈傲骨之姿,歌颂坚毅忠贞之心,承载梅花之情,亦为“写意”之美学思想的“意象”范畴。《庄子》约:“言不尽意”,意已超象,追求以形写神,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即以“中和之美”为核心理念,并以“空灵之美”与“自然之美”相辅相成,其并非独立个体,传统音乐审美特色圆融相通,最终追求“形神”与“意象”对立统一的“写意”之最高境界。
三、结语
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与审美特色是研究传统音乐各项内容的根本与基础,理清传统音乐内部发展所承续的守恒定律,即可更为有效的判断其中部分音乐的根源属性。本文依照具体实例,解读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特征及审美特色等各类概念于音乐事象中的表达,从而折射出中国传统音乐强大的传承机制与不同于西方音乐的结构特点。其中,五声性旋法;散整结合的节奏节拍;散慢中快散的速度发展规律;音高定量与时值定性的记谱法原则;乐音带腔性等特征,相对而言在传统音乐事象中更具典型性,亦更能切实普遍的反映出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格特点。另外,中国传统音乐的三种审美特色在音乐事象中表现出水乳交融之态,一首作品既可体现自然之美之意境,又可承载空灵之美之缥缈,再赋予中和之美之理念,最终达到写意之最高境界,便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之无上追求。综上所述,中国传统音乐独具风格的表现形态与风雅高尚的审美品格在音乐事象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使用作品进行分析,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中国传统音乐事业发展方兴未艾,望此类文章作为传统音乐各类研究主题的基石,更好的推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