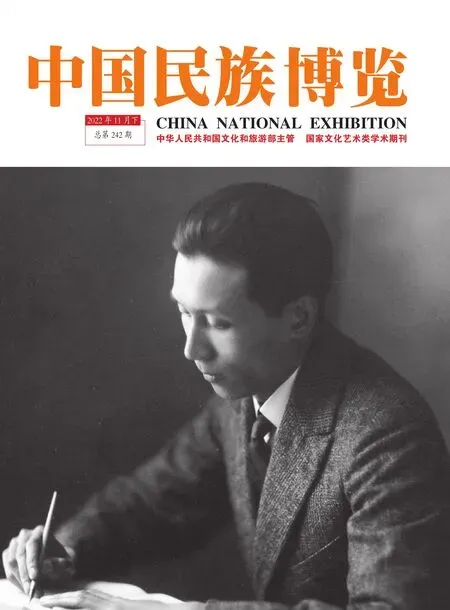唐代民间艺术管理史初探
王思允
(哈尔滨音乐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历史上经济和文化高度繁荣发展的朝代,其艺术活动也达到了上古以来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唐代统治者不仅扩大了皇家宫廷音乐管理机构的规模,增加了教坊,梨园等音乐管理机构,还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的管理制度。但宫廷艺术管理模式主要以为适应统治者,满足其自身审美娱乐的需求为主,由统治者的喜好决定艺术的发展,且只为皇权贵族和官僚阶级服务,虽然凭借统治者心情,会偶尔面向公众演出但次数极少,可以忽略不计,公共性不强。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宫廷音乐机构被破坏,乐籍制度变得松动,一些乐人受雇于民间可以从事营利性艺术活动,教坊曲通过宫廷乐人传向民间。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的碰撞使得民间艺术发展更加繁荣,同时唐代民间艺术活动的场所也为民间艺术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一、唐代民间艺术活动场所概述
(一)寺院
唐代佛教盛行,寺院林立,据不完全统计,唐代寺院多达千余座。佛教寺院为了宣扬佛家教义,吸引听众,将佛家故事编成百姓更易接受的通俗作品,而统治者为了达到稳定皇权、维护社会和谐的目的大力弘扬佛法。“俗讲”就是唐代佛教为了吸引听众宣扬教义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此类艺术作品在当时深受百姓的喜爱。当时民间的集体艺术活动和民间节日及寺院的宗教活动结合起来,使得寺院也成为了百姓欣赏艺术、参与艺术活动的一重要场所。唐高宗时代,长安的各大寺庙都会设立“戏场”,戏场里的艺术活动十分丰富,例如“俗讲”、杂技、乐舞和小戏。《资治通鉴》248卷记载,唐宣宗公主为了观看杂戏表演,偷偷躲到慈恩寺观看,被宣宗惩罚,可见唐代民间艺术活动的发展之繁荣,以及宫廷艺术无法继续满足皇室贵族的艺术文化需求。
在敦煌石窟里发现的无数乐谱、变文等均可以反映当时寺院艺术活动与社会活动结合的现象。
(二)坊市
坊市的出现不仅满足统治者实施商业管理的需要,也推动了唐代艺术的发展。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长期处于政治黑暗、藩镇割据的状态,但盛唐时期形成的经济繁荣在南方地区的延续,为中晚唐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局动荡,唐王朝已无力管理冗杂的宫廷艺术机构,以及无法承担繁多艺术机构高昂的供养经费,统治者开始大量削减其开支,宫廷艺人曾经“低地位高工薪”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低地位低工薪”,晚唐时期大量宫廷艺人被裁,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太常寺乐人由曾经的万余人削减至5000 人。大量宫廷艺人流落民间,不得不靠卖艺维持生计。同时,教坊艺人对外营业,承接“私活”。
唐敬宗宝历二年九月,京兆府刘栖楚奏:
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宾旅。伏以府司每年重阳上巳两度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需求雇教坊音声,以申宴饯。今请自于当巳钱中,每年方图三、二十千,以充前件乐人衣粮。伏请不令教坊收管,所冀公私永便。从之。[1]
这篇奏折较为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宫廷艺人受雇于州府,或大臣供其宴乐之需,这也反映了当时宫廷音乐由皇室专享向士大夫阶层享有转变。除教坊艺人受雇之外,太常寺乐师也有偿为民间演奏,顾况(约727—约820)有诗《李供奉弹箜篌歌》云: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调绦索金头。早晨有敕鸳鸯殿,夜静遂歌明月楼。……李供奉,仪容质,身材稍稍六尺一。在外不曾辄教人,内里声声不遣出。指剥葱,腕削玉,饶盐饶酱无味足。弄调人间不识名,弹尽天下崛奇曲。胡曲汉曲声皆好,弹着曲髓曲肝脑。……驰凤阙,拜鸾殿,天子一日一回见。王侯将相立马迎,巧声一日变一回变。实可重,不惜千金买一弄。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此州好手非一国,一国东西尽南北。除却天上化下来,若向人间实难得。[2]
可见中唐之后,宫廷艺人并非全职服务于朝廷,统治者对其管理相对放松,艺人们有一定的人生自由。以上两个案例均体现出,中唐之后,艺术逐渐商品化,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原本只供皇权享受的艺术娱乐活动逐渐走向社会,面向大众。
(三)妓馆与家院
安史之乱以后,以宫廷为中心的音乐交流方式被改变,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势力加强。酒楼妓馆也为唐代文人、达官子弟和各类商贾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妓馆的从业人员,也成为了社会艺术活动的主要人员。妓馆的艺术活动活跃之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一部分宫廷乐师迫于生计沦落妓馆,不仅成为妓馆的从业人员,也在妓馆中承担教习的职能,使妓馆艺术活动的水平整体上升,另一方面唐代妓馆的管理者为了自己的收益,往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对妓馆的从艺人员进行教习,在从艺人员学习的过程中管理者的要求往往是极其严格的。《北里志·海论三曲中事》载:
“初教之歌令而责之,其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3]
由此可见,妓馆管理者为了在艺人身上获得最大程度的回报,采取了严苛的手段。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文人士大夫的奢靡生活创造了条件,歌姬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专门满足社会各阶级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是顺应时代和社会需要产生的。他们为唐代文人艺术创作提供灵感,又在词曲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是唐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艺术群体。唐代文人艺术的迅速发展,也得益于“蓄伎”这一社会文化。除了上文中提到过的妓馆歌姬以外,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歌妓又分为家妓、官妓和私妓。
由于唐代的“蓄伎之风”盛行,权贵官宦、文人士子家中几乎都豢养了不同数量的歌伎,用以休闲娱乐,招待宾客。《新唐书·河间元王孝恭传》说:“(孝恭)性奢豪,后房歌舞伎百余。”[4]朝廷也有明文规定,允许官员按官位蓄养一定数量的歌伎。文人音乐“因不具像宫廷音乐那样承载着对国家政权的文化承诺,也不具有向民间音乐那样的群体情感个体化的文化向度,它最突出的特征是个体情感的个体体验,由此而显示出内涵的多样性和表现的细腻性。唐文人音乐的上述特点,给中国音乐文化在唐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和多元的价值,并且由于它对宫廷的渗透和对民间市井的影响,在音乐样态、音乐行为和音乐美学追求诸多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的音乐生活,同时也是唐代音乐文化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唐文人音乐对唐代音乐文化的贡献,应该得到重视”。[5]
二、唐代民间艺术活动管理机制概述
(一)寺院的艺术管理机制
唐代佛教寺院兴置受到更为严格的国家控制。依照朝廷之命,各州立寺院。首先寺庙艺术活动的开展与朝廷的宏观政策是分不开的,唐懿宗时,“(佛)降诞日,于宫中结彩为寺”,宫廷伶人“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宫廷对佛教的重视使得寺院的地位自然提高。唐代宗教音乐的从乐人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玄奘、不空、发朗等高僧为代表的主要传授者,二类是统治者将一些年老色衰的宫廷乐工下放到寺院,宫廷乐工也成为了寺院艺术活动的主要从业人员 。这种做法也使得宫廷音乐传播到民间,使得宫廷艺术活动与民间艺术活动有所互动,不仅减轻了朝廷的负担,还保证了寺院艺术活动的水准与质量,为佛寺成为市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场所奠定了基础。景明寺,八月节。“京师诸像(佛像),皆来此寺。”“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景兴尼寺。“有金像辇,去地三丈。”“飞天伎乐,望之云表。”“像出之日,常诏羽林(军)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由旨(皇帝命令)给(调拨)。”景乐尼寺。“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寥亮,谐妙入神。”“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这些史料记载的案例都可以证明寺庙艺术活动水平之高,当时艺术活动盛大的景象不禁引人遐想。唐高宗时期,“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入住慈恩寺”,其中众伎可能指的是寺庙里艺技精通的僧人,也称为艺僧,当时寺庙里有不少技艺精湛的艺僧,法云寺有西域乌苌国僧昙摩罗,他是表演幻术的高手,侧面说明了寺庙的僧人是寺庙艺术活动的主体。日本僧园仁(793—864)在《入唐求法·礼行记》中常常提到“开成六年(641)正月九日……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及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又敕开讲道教,……太和九年(835)以来废讲,今上新开,正月十五日起首至二月十五日罢。全昌二年(842)正月一日...诸寺开俗讲。五日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寺院开设俗讲,并面向公众开放,此时的寺院艺术活动已具有公共性。
(二)妓馆与家院的艺术管理机制
妓馆的管理者特点与唐代宫廷艺术机构管理者特点相同之处在于,其核心管理者并非从艺人员,或者艺术造诣并不高。所以在妓馆内部会设立“都知”“席纠”等职务,让其完成对新人的艺术培训任务和管理妓馆日常事务。岸边成雄在《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文中提到:“曲妓之头角者”赋予“都知”“席纠”名称,形同教坊乐官。[6]《北里志》记载唐代长安官妓的来源时说:“(北里)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为人所聘。一客云入京赴调选,及制至京,累月后仍逼令学歌,渐遣见宾客。[7]对于没有音乐基础的从乐人员,管理者强迫其学习音乐是一种极其常见的形式。唐代家庭乐伎的人员来源不同,导致了乐伎管理形式的不同。杜甫云:“南内开元曲,常时弟子传。法歌声变转,满座涕潺箔。”不难看出,当时家庭乐伎求教于教坊梨园技艺高超的音乐大师也是家庭乐伎学习音乐的主要途径之一。刘禹锡《伤秦姝行·序》曰:“河南房开士,前为虞部郎中,为余语曰:我得筝人于长安怀远里。其后开士为赤县,牧容州,求国工而悔之,艺工而夭。”一些家院中的管理者常常会为了使自家家伎技艺提高再请专业的老师为其进行再培训。管理者对于家院艺术活动人员的管理是相对自由的,与妓馆管理机制产生鲜明对比,但是两者之相同点在于管理者对于从艺人员专业技术的重视,这也侧面反映了唐代民间艺术活动的盛行与文化的繁荣发展。在宏观政策方面,中晚唐统治者对宴乐完全开放。贞元元年诏曰:“今兵革渐息,夏麦又登。朝官有假日游宴者,令京兆府不须闻奏。”[8]统治者对宴乐的开放使得朝廷官员可以有更多时间休闲享乐,艺术活动发展迅速。
三、结语
艺术管理作为一门在20 世纪60 年代才兴起的学科,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年轻的。但是自从人类有艺术活动以来,艺术管理活动就伴随产生了。公元前6 世纪的希腊,忒斯庇斯创建戏剧组织并开始使用演员,我国秦朝“乐府”这一礼乐管理机构的确立,都可以说明艺术管理具有的悠久历史。中国悠久的艺术管理史是为研究艺术管理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财富,所以研究艺术管理史、研究中国艺术管理史是十分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