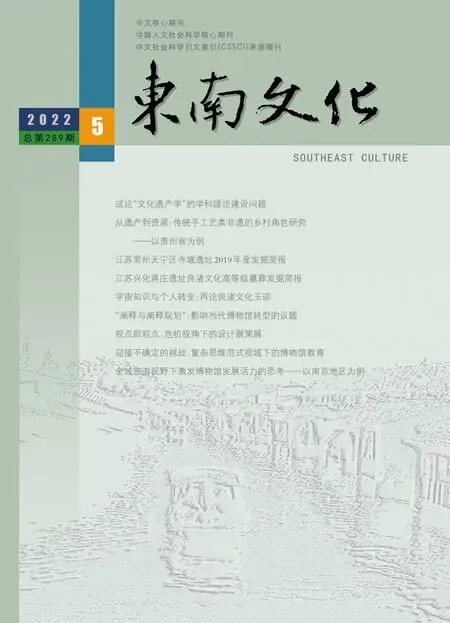危机下的转机: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恢复与重塑
冯 楠 周辰雨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而新冠疫情使得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大大受限。如何应对多重挑战,及时调整完善自身教育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积极探索新模式、新方案,是博物馆界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索博物馆教育职能恢复与重塑的方法:在理论层面,博物馆应明晰教育职能的定位,深化博物馆教育的理论研究,通过进一步整合教育资源,建立馆校双方教育人员知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在实践层面,博物馆应拓展教育空间,开启打破时空限制的展览与教育活动。此外,博物馆应将教育职能置于更为宽泛的视域下,拓展博物馆在承担社会公共责任方面的作用和价值,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重塑自我,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地博物馆根据相关疫情防控规定陆续闭馆,收入锐减,甚至陷入生存危机,许多博物馆采取减员降薪等措施“疫中求生”。2020年4月,全球有94.7%的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近半数博物馆的资金(包括公共资金与私人资金)收入减少,82.6%的博物馆表示不得不减少活动项目,还有12.8%的博物馆可能要永久关闭,展览和教育活动受到严重影响[1]。2020年以来,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对全球博物馆展开多次调查,如《调查:博物馆,博物馆工作人员和 COVID-19》(Museums,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COVID-19:Survey)关注新冠疫情对博物馆及从业人员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不少博物馆在政府赞助、私人捐赠和自身创收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教育、展览等公共项目上的预算也相应减少;同时还经历了自身的“大减员”,许多经验丰富的负责核心教育工作的员工可能永远无法回到这个领域[2]。美国博物馆联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AAM)发布的《关于美国博物馆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概况》(National Snapshot of COVID-19 Impact on United States Museums)就显示,有53%的博物馆表示已解雇或裁撤了部分员工,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从事博物馆教育工作和观众接待服务的人员。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的《COVID-19疫情下的全球博物馆》(Museum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COVID-19)表示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博物馆还会因疫情的反复导致开而复关[3]。随着疫情的不断反复,我国博物馆界根据疫情防控需要,适时采取临时闭馆、限制入馆观众人数、暂停人工讲解等措施。闭馆极大影响了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博物馆的展览数量、馆内开设的公众教育项目数量都在锐减。
一、砥砺前行: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恢复与发展
疫情初期,全球博物馆不得不闭馆以应对疫情的冲击;进入疫情平稳期后,博物馆逐渐恢复开馆。很多国家政府和社会展开了对博物馆行业的救助。如2020年英国政府拨出15.7亿英镑的款项,帮助博物馆和艺术文化机构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造成的影响[4];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ET)得到2500万美元的馈赠款项用于填补其财政缺口[5];俄罗斯的1000多家博物馆中有90%依靠企业赞助得以维持运营[6];美国国会(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于2020年3月通过“薪资保护计划”(Payroll Protection Program,PPP)拨付超过7998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缓解裁员危机、稳定就业[7]。但这些举措仅能够帮助博物馆暂度危机。
全世界博物馆教育人员对疫情的冲击迅速作出积极的回应,深入探索“互联网+博物馆教育”新模式。2020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博物馆部门影响的后续调查》(Follow-up Survey: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Museum Sector)显示,有43.5%的博物馆都表示正在或以后会逐渐开发线上学习项目[8]。如英国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开放线上藏品资源以供观众下载、学习和研究,包括“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等镇馆之宝在内的近450万件藏品可在线上浏览,近190万件藏品的图像和资料可免费下载使用[9];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在官网提供了藏品展示、线上课程以及针对不同年龄段受众的艺术教育项目[10]。我国博物馆界更是迅速开发了丰富的线上资源,据国家文物局统计,2020年春节期间全国博物馆共上线2000余项展览,推出“云展览”的博物馆达1300余家,总浏览量超过50亿次[11]。上海市发布的《2020年上海地区博物馆运营报告》也显示:2020年,全上海市博物馆共策划各类社会教育活动5307场[12],其中“春风千里:江南文化艺术展”等线上直播及其教育活动广受好评。
然而,这些措施是在疫情暴发之初为应对闭馆而作出的反应,仅作为博物馆教育工作恢复阶段的应急措施,而非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长久状态。博物馆是对实体艺术、多元文化和自然生态的实景展示与体验的场所,当传统观众突然改变习惯、转而感受线上参观体验时,博物馆目前提供的线上展览和教育活动其实远远满足不了公众的期待[13]。如何更积极地应对观众需求,继续与新冠疫情抗争,并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社会危机做准备,是博物馆发挥其教育职能的重要思考方向。
二、恢复与重塑:博物馆发挥教育职能的深入探索
这场全球疫情对大众的生活、工作带来了颠覆性改变,大众的心理需求随之发生很多变化。美国对疫情影响下的博物馆现状进行的一项观众研究显示[14],疫情使得观众需要相关文化机构在情感、社交等方面提供服务,并且这种需求进一步演化为希望文化机构能够帮助他们从疫情中分散压力、逃离危机。《博物馆学的历史:博物馆学理论核心作者》(A History of Museology:Key Authors of Museological Theory)一书指出,当代博物馆需要为满足科学、教育等方面的社会需求而贡献力量[15]。从当前社会需求来看,观众在希望博物馆继续发挥其教育功能的同时,也希望博物馆能够更深入地参与到社会中,积极探索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博物馆需要致力于成为公众信赖的机构和社会教育资源,以公众的利益和关切点为立足点,以提高社会福祉为出发点,重新思考博物馆教育的使命和愿景,积极采取行动以应对变化。
(一)教育定位反思:深化博物馆教育的理论研究
博物馆教育活动实践的发展需要有坚实的体系架构和基础理论研究作为支撑和引导[16]。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有所提升,越来越多组织机构加入文化行业。目前在文化竞争中,博物馆文化的个性特征越来越模糊,特殊价值也越来越淡漠[17],这使得博物馆所承担的教育职责更难被社会认知,其价值也很难实现。目前,学界在认识到博物馆教育功能重要性的基础上,在博物馆教育理论方面做了多种探究。如近些年发展正盛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体验学习(experiential learning)、教育生态理论(ecological theory)、情境式学习(situational learning)等诸多理论[18],以及通过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设计型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评估型研究(evaluative research)、案例研究(case study research)等诸多研究[19]。全球疫情使博物馆教育实践产生诸多变化,随着很多线上应急措施的实施,博物馆教育工作者也开始对危机时期的教育实践进行反思,包括疫情带来的新挑战以及一些长久存在但被疫情暴露的问题,比如关于不同观众群体的博物馆线上教育活动的可及性,这种审视带来的关注在疫情趋缓的情况下依然会影响博物馆教育人员的选择,促使博物馆探索如何提供更恰当的教育内容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在这样特殊的学习环境背景下,博物馆更需要考虑这些教育理论在新形势下使用的适切性和在博物馆场景中运用的局限性,需要坚实的理论去明晰博物馆教育在教育系统和博物馆内部的地位,进一步探讨博物馆教育的原则、伦理等,以更好推动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恢复与发展。
(二)教育资源整合:构建馆校合作的创新机制
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体系中的非正式教育场所,虽然在教育方式、学习内容等方面与学校教育有较大差异,但从育人功能的角度看,校外活动与课堂教学同样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20]。西方馆校合作诞生于19世纪晚期[21],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丰富,活动形式涵盖了研学旅行(field trip)、虚拟研学旅行(virtual field trip)、配套学习单(worksheet,pre-visit,visit,postvisit)、博物馆资源外借服务(loan service)和博物馆资源包(resource packs)等多个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疫情以来,学校和博物馆均采用了线上教育方式,公众也需要馆校合作带给儿童更多教育资源[22]。馆校合作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更需要馆校合作双方对这项工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目前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联合发布的《关于利用文化和旅游资源、文物资源提升青少年精神素养的通知》提及的“文教合作”,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双减政策”,都将开启关于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合作模式的新一轮探索。馆校合作要建立双方教育人员知识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机制,这可以从源头解决博物馆教育功能发挥的最主要“危机”。尽管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教育者为文化机构的使命和目标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的工作往往得不到认可,其表现和能力也被视为理所当然,这一问题在疫情期间更为突显。如果一线博物馆教育者的工作状态和前景得不到保障,博物馆无法实现由专业的教育人员提供教育活动,博物馆教育功能会大打折扣。馆校合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可以让博物馆教育的能力和价值得到社会认可,进而能从经济层面和知识层面保护博物馆教育从业者,让他们专注于改善其专业服务质量。博物馆教育者和学校教师之间通过对话与反思,可以共同搭建更广阔的社交网络,为博物馆教育发展建立新型的、更广泛的、更具有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共同体。
在实践中,很多国家的教育部门已经将博物馆纳入中小学教师培训计划,要求他们熟悉并善于利用馆方资源辅助教学[23]。例如美国博物馆界就在中小学教师培训方面不遗余力,所公布的科学教育标准为教师的职业发展项目增添了新动力[24];日本的学艺员制度(がくげいいん)是日本博物馆从业人员尤其是核心专业人士必须遵循的职业资格规则,对规范从业者的职业资格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5]。基于受众和需求的多样性,博物馆还可为教师提供多样化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的支持[26],如美国波士顿科学博物馆(Museum of Science,Boston)的一项屡获殊荣的课程——基础工程学(Engineering is Elementary,EiE),每年约有30万名学生参与课程,并已在美国及20多个国家/地区使用,教师的职业发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也被纳入馆校合作的范围内,项目资助来自美国21个州的80名小学教师,为他们颁发工程基础(EiE®)计划奖学金[27]。同时,针对博物馆教育人员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标准等问题,很多研究者和管理者呼吁加强对教育工作的专业认证,以促进博物馆教育人员形成专业认同感、承诺感、效能感和对工作的掌控感。
(三)教育空间拓展:打破时空的博物馆展览与教育活动
随着世界各国继续与新冠疫情抗争,包括博物馆在内的许多艺术与文化机构都在努力应对疫情带来的需求变化,寻找在人口密度高、空间封闭的公共场所减少病毒传播的方法。世界各地许多博物馆已经采用在线购票或通过自助终端购票的方法,并调整其物理空间,制订新的安全措施,甚至保留当前的疫情防控协议如定时票务和访客人数限制。在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甚至可能会完全取消排队购票。由于保持社交距离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举措,博物馆的前台工作人员以及教育工作者、讲解员都经历了大规模裁员,未来博物馆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和拓展教育活动空间,包括举办线上展览、缩小参与团体的规模、制作更多关于博物馆藏品信息的视频和音频、在户外场所开展工作坊或研讨会等。
一方面,线上展览的内容更加贴近观众的现实关注,不再是对原有展览的简单数字化。一些博物馆已经不再单纯地投放数字资源,而是基于观众需求开发相应的教育资源,回应观众期望。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在馆内原有展览“疫情暴发:流行病在互连世界上蔓延”(Outbreak:Epidemics in a Connected World)的基础上,新增了关于新冠疫情的内容,并配套举办虚拟展览和普及病毒疫苗知识的线上讲座[28]。随着疫情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很多博物馆也在探索恢复不局限于博物馆物理空间的线下教育活动的可能。荷兰阿姆斯特丹市博物馆(Amsterdam Museum)举办的“城市的记忆”(Collecting the City)展览,就将线下展览与观众参与融合在一起,展览由观众、艺术家和策展人共同策划,展览内容是动态的,每六个月更换展示内容[29]。美国圣地亚哥儿童发现博物馆(San Diego Children’s Discovery Museum)就推出一类新型展览方式,根据美国新制定的、采用统一的方式、跨学科和年级为所有学生提供符合国际基准的科学教育标准——“下一代科学标准”(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以观众所在地为基点,设置一种能够让学生和家长都加入进来的便携式、移动式科学实验展览[30]。在馆校合作方面,英国伦敦犹太博物馆(Jewish Museum London)依托博物馆实体资源并结合学校需要,开发出适合教师、学生使用的学习资源——“虚拟课堂”项目(Virtual Classrooms)。该项目将馆内现有的针对种族主义、种族宽容、大屠杀等主题的学校课程快速转化为线上内容,既便于老师使用,又便于学生学习。该项目取得了很大成功,有近5000名学生完成了课程,并在全英范围内发展了新的观众群体[31]。2020年加拿大多伦多市在一个372平方米的仓库举办了开车观赏梵高的展览(Gogh by Car),观众开车进入基于梵高画作《星夜》(The Starry Night)和《向日葵》(Sunflower)而打造的完全沉浸式投影空间里,在车内观展,这一模式给残障人士、担心病毒传染隐患的观众提供了相对安全的观展体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万人参观了此展览,展览所在的仓库也成为一个独特的活动空间,最近还举办了社会远程健身课程[32]。这次展览开启了对于未来博物馆新模式的尝试,即与其让观众穿过博物馆的物理建筑空间,不如创建“免下车博物馆”,在博物馆所在城市加入一些开车或步行时可以观赏的艺术品,如美国洛杉矶的艺术家们发起了一项“行驶过程中的艺术品”(Drive by Art)的博物馆新展览倡导[33]。
另一方面,以学习为中心的元宇宙(Metaverse)与博物馆相融合,如世界更美好博物馆(Better World Museum)使用的场景赋能,是对后疫情时期博物馆教育形态的重塑和构建[34]。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在亚洲最大元宇宙平台ZEPETO推出的“ZEPETO 治愈山岳”展,展示了该馆的镇馆之宝——两尊半跏思惟像并立相处元宇宙虚拟融合世界[35]。这一方面符合博物馆资源数字化倾向;另一方面元宇宙构建的学习场域具有强情境性、高协同性、便捷性的特点,使得博物馆内的学习从“场景之外”走向“场景之内”。元宇宙赋予博物馆观众切换学习场景的自主权,实现大规模协同学习,观众处于全场景化知识情境之中,具身体验完整的知识学习过程,获得心流体验(flow experience),为其自主发展、智识变化提供更高维度的交互契机。
(四)教育场域深度重塑:社会参与性转变
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但并不是博物馆的全部,单纯地强调教育的本身要义不足以支撑博物馆的使命。疫情的冲击给了我们重新思考的机会,更多人意识到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应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视域下展开谈论[36]。博物馆属于社会教育范畴,其定义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概念认为由博物馆产生的、具备教育意义和功能的一切事物皆可被视作博物馆教育[37]。著名博物馆学家约翰·科顿·达纳(John Cotton Dana)认为,博物馆应该努力追求为普通公众提供直接而有用的服务[38]。近年来,博物馆经历了“参与性转变”(participatory turn),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或美术馆开发项目吸引观众主动参与到博物馆中[39],包括各个层面的社会参与,突破不同机构、不同知识体系和技术层面的界限和鸿沟,从提供咨询服务、藏品外展到共同策展,确保所有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享有”我们所有人的文化遗产。
若想加强博物馆自身以及全社会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视,博物馆应发挥其在文化传播、跨文化对话、学习、讨论与培训以及教育(正式、非正式、终身学习)、社会凝聚力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即拥有社会各个方面所需要的学习内容。博物馆教育拥有独特的优势,但与系统的教育机构相比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广义的教育存在于社会各种生产和生活活动之中,一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和改变人们思想意识的过程,都可归于广义的教育[40]。博物馆重视教育,但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行为的实施层面。一个“有用”的博物馆应是能对社区需求作出反应的博物馆,博物馆应该积极地介入社区生活,致力于公共服务和教育任务[41],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正如美国博物馆联盟“博物馆教育实践优秀奖”(Excellence in the Practice of Museum Education)的获得者玛丽·艾伦·蒙利(Mary Ellen Munley)和美国观众研究协会(Visitor Studies Association,VSA)的经理兰迪·罗伯特(Randy Roberts)所说,博物馆教育者不仅应该将建立博物馆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作为教育的核心,还应该提升博物馆在社会变革中的公共服务,开发与维持社区组织、学校、文化机构、大学、博物馆与大众之间的关系[42]。社区理念对探讨博物馆教育的价值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3]。它能拓宽博物馆教育功能实施的场域,从吸引居民参与博物馆的活动延伸到促进居民个体知识的生成和治理理念的提升[44],从而拓展博物馆在承担社会公共责任方面的作用和价值。
目前,社会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是当代博物馆工作中一个非常具有国际意义的领域[45]。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保护与促进博物馆和收藏及其多样性、社会角色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Museums and Collection,Their Diversity and Their Role in Society),强调了博物馆应承担的社会角色,提出博物馆与所处地区经济发展的议题,特别是博物馆如何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些议题对各国博物馆助力社会治理政策架构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46]。美国博物馆联盟未来博物馆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Future of Museums,CFM)的报告《博物馆和社会 2034:未来发展趋势》(Museums&Society 2034:Trends and Potential Futures)也提出了博物馆助力社会治理的实践方式:博物馆依托其藏品、项目和社区拓展活动,将成为重塑公民参与模式的领导者[47]。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都开始就近为社区提供服务,在辅助社区学校教育和社区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观念上的改变对推动博物馆教育的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层面,美国博物馆联盟发布的《关于美国博物馆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概况》显示,很多博物馆已经在社区参与方面作出努力。博物馆除了为周围社区的公众提供线上资源、学校教育资源、远程学习空间、室外展览空间等基本服务外,还在社会关怀和治理方面做出了更多创新性尝试,如创建移动空间方便社区走访,并提供无线网络、社区活动和信息;与当地服务机构合作,组织艺术捐赠活动并为社区提供食物保障;为社区内有需要的群体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向艺术家提供经费和基金的资助;经营公共农贸市场方便公众生活[48]。事实证明,博物馆的社会价值是广泛的,能够为社区公众提供服务,在促进公众知识、技能、身体健康、形成和改变思想意识以及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与诸多国家在博物馆事业方面存在共性,博物馆事业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新经验都值得我们关注,若加以本土化调适,可促进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博物馆在经济困难中改变工作重点,为获得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资助,十分注重向社会提供丰富的服务项目[49]。这使得美国的一些博物馆更加关注与社会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实现教育目标。在疫情期间,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到意大利都灵城外的里沃利城堡(Castello di Rivoli)[50],许多博物馆已经把展厅变成临时疫苗接种点。英国伍尔弗汉普顿艺术博物馆(Wolverhampton Art Gallery)在面对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时就积极与公众讨论这些问题,通过一系列教育活动让当地的社区群体参与进来,鼓励启发他们去回顾历史并审视当下,从而促进伍尔弗汉普顿城市的改变与发展[51]。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Chicago,MCA)的“艺术和公民参与馆校合作项目”(School Partnership for Art and Civic Engagement,SPACE)成功地将本馆的学习体系突破博物馆的围墙,由学生调查当地社会问题,找到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最感兴趣的事件,并经过社会调查,让社区成员以对话的方式参与创造社区的变化[52]。2014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发起了“古根社会实践”(Guggenheim Social Practice),是探索艺术家、博物馆、社区三方合作,创新公众参与艺术教育活动的新方式。曾供职于美国史密森尼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现任玛丽·艾伦·蒙利评估机构(MEM&Associates)的负责人玛丽·艾伦·蒙利全程对其评估并得出实证性结论:“古根社会实践”能有效地推进前沿的艺术、社会和教育事业,扩大并加深博物馆与其所服务社区的联系;优化现有机构之间的合作,使观众和文化机构形成新的伙伴关系;能重新审视博物馆传统的、基于社会教育工作的吸引公众的方法,审视因艺术家主导的公共参与项目而改变的博物馆内部机构[53]。
新冠疫情给全球博物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新的形势促使博物馆在发挥教育职能时不断拓展自我,在博物馆教育资源与社会需要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制定适应社会发展的策略[54]。理论研究的深化、教育资源的整合、教育空间的拓展以及社会参与的尝试,这些内容都为博物馆教育功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但事实上,社会现实情况以及不同博物馆面临的各种窘境等对博物馆教育功能在实际中的应用与发展有着不同影响,诸多有关博物馆教育功能的理念共识和实践策划仍需结合现实情况来应用。博物馆教育功能具有广阔的需求土壤,它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自我反思,并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不断调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