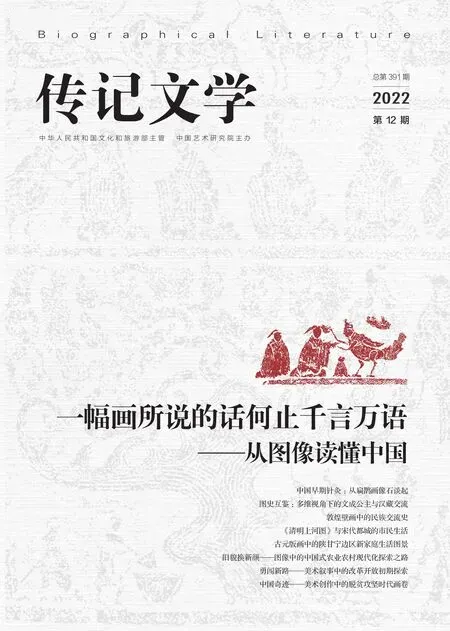2021 年中美传记电影比较研究
储双月
传记电影往往带有历史的印记,散发着时代的气息,蕴含着人文精神、价值取向,能够满足观众求真的诉求,而且其中贯穿着的精神力量对观众具有重要的激励或警示作用。
2021 年是中美传记电影大放异彩的一年,许多在此年上映的传记影片得到了重要电影奖项的垂青。中国传记电影《守岛人》获得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革命者》获得第34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第11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28 届大学生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影片;《柳青》获得第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传媒关注编剧奖;中国香港传记电影《梅艳芳》获得第40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员、最佳服装造型设计、最佳音响效果、最佳视觉效果奖。而美国传记电影《国王理查德》获得第94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第79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电影类剧情类最佳男主角奖、第75 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主角奖;《塔米·菲的眼睛》获得第94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和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里卡多一家》获得第79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电影类剧情类最佳女主角奖;《倒数时刻》获得第79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电影类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奖。
2021 年的中国传记电影有剧情传记电影《守岛人》《柳青》《我的父亲焦裕禄》《梅艳芳》,以及历史传记电影《革命者》,虽然在数量上较少,但与往年相比,已是传记电影生产的丰收年。而美国传记电影,亚类型更为丰富,除了《塔米·菲的眼睛》《里卡多一家》属于剧情传记电影之外,还有体育传记电影《国王理查德》《新王加冕》《美国草根:库尔特·华纳的故事》,音乐传记电影《倒数时刻》《尊重》,历史传记电影《美国叛徒:轴心莎莉的审判》《哈里·哈弗特》,犯罪传记电影《兰斯基》《无主之人》等。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以真人真事为根基来真实记录和深刻反思特定人物生平历史的传记电影进行比较研究,实属必要。
树立英雄模范的纪念碑与描绘普通人的肖像画
2021 年的中国传记电影以纪念性传记电影为主,传主的道德品行或个人成就都明显高于普通人,归入品德高尚者、事业有成者之列,值得后人纪念和瞻仰。除《梅艳芳》外,《革命者》《我的父亲焦裕禄》《柳青》《守岛人》中的传主都是正统的英雄模范。四部影片主要关注于刻画传主高大、光辉的人物形象,凸显人物的高尚品德与事迹行为,强调善行是内在的、永恒不变的。创作者聚焦于传主所崇尚的理想主义信念,从道德伦理角度审视人本身,是这四部中国传记电影的共同创作趋向。
《革命者》《我的父亲焦裕禄》《柳青》《守岛人》相比较以往的中国传记电影,除了突出其中的道德含义与教化作用之外,更突出了传主的坚定、忠诚、执着和朴实等鲜明品格,拉近了传主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我的父亲焦裕禄》以女儿的视角深情回忆了一名共产党员干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塑造了焦裕禄为官至臻、为夫至诚、为子至孝、为父至亲的光辉形象。影片回顾并赞颂了焦裕禄“洛矿建初功”“兰考战三害”“博山生死别”三个时期的高尚事迹,“伟其事”、“详其迹”,“试图为死者树立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借死者的伟大来鼓起生者的勇气”[1]。影片不仅注重传主的个人成就或公众生活,还较为注重家庭生活中传主与亲人相处的点滴琐事,突出了传主具有的高于常人的自律和对家人严格要求的道德品质。与《我的父亲焦裕禄》一样,《革命者》《守岛人》《柳青》也借助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为观众提供可供效仿的范例,以实现对观众的鼓舞、指导和启发作用,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言行。尽管四部影片有意塑造英雄模范的纪念碑,但是英雄模范并未因此失去生活色彩,也没有变成神坛上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偶像。因为创作者尽力嫁接英雄情怀与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力图还原其为有呼吸、有温度的人,竭力让真实亲切的“平凡英雄”走入观众心灵。例如,《革命者》透过三一八惨案的再现,让我们聆听和目睹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内心的恐惧、挣扎与怒吼。作为塑造理想人格为宗旨的纪念性传记电影,虽然仍免不了受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传统观念的影响,却已经在有意识地探讨历史存在的丰富性。创作者为了表达得体的致敬,在记录传主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与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的同时,又努力还原传主为“我们”中的一员,达到“见事又见人”的效果,体现了传记材料的博实与人物个性的彰显。
中国香港电影《梅艳芳》则展现了梅艳芳成长为歌后与影后的心路历程和作为“香港的女儿”的传奇一生。《梅艳芳》以述人为主,以刻画、描摹和凸显传主的性格为重,向观众展示了创作者所熟悉的传主生平中的轶事,使传主的人物性格惟妙惟肖、真实可信。传主童年时期和姐姐一起登台演出、养家糊口的场景让人过目难忘。影片通过传主与姐姐约好一起看婚纱却没有按时赴约而且拒绝道歉等情节描述,没有避讳表达传主性格中存在的某些瑕疵;影片还勾勒出了传主心灵的伤疤:从小到大都没见过父亲,在心底里把形象设计师刘培基、华星唱片总经理苏孝良、电影制作人何冠昌当作父亲,等等。创作者擅长心理分析,并以此为工具阐释传主,试图探索和呈现传主的内心世界。
而2021 年的美国传记电影重在描绘人物的历史,致力于生动刻画传主丰满而真实的形象,突出传记电影是描绘普通人的肖像画,即有明有暗的立体肖像画,而不是历史“大事记”、索引或目录,也不是轮廓图。它们不再以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成就为主,而对人自身产生了浓厚且意味盎然的兴趣,因此将重点放在塑造可以决定其命运的人物性格上,对人物性格的重视高于历史事件。这一时期的美国传记电影更加注重通过轶事和细节刻画人物性格,人物形象聚焦于雄心勃勃的运动员、青年音乐剧作曲家、有着明显性格缺陷的娱乐圈知名人士、被美国政府以八项叛国罪名提起诉讼的播音员,乃至臭名昭著的罪犯和黑帮人物等。
正如英国18 世纪传记理论和实践先行者罗杰·诺斯所说:“传记应该是一幅画,如果它的特有质素被省略,那断然算不上好作品。瑕疵、伤疤和污点应该和它的美一样被描写出来,否则它只能算一幅填满了百合和玫瑰的轮廓图。”[2]美国传记电影大多专拣传主私生活中细致入微的“瑕疵、伤疤和污点”开刀,通过日常琐事和个性化的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从而实现传记电影的娱乐功用。例如,体育传记电影《国王理查德》中的传主不是世界网坛巨星威廉姆斯姐妹,而是美国黑人贫民窟出身却将两个女儿成功培养进入体育赛道金字塔顶的传奇父亲理查德·威廉姆斯。该片是美国黑人明星威尔·史密斯继《拳王阿里》(2001 年)、《当幸福来敲门》(2006年)、《震荡效应》(2015 年)之后主演的第四部传记电影。在这部影片里,威尔·史密斯很好地塑造了网球明星姐妹背后挑战既定规则、强势犀利、纵横随心的不完美的父亲形象:一位“充满争议、蛮横霸道、爱自吹自擂的滋事分子”(影片语),充分展现了这位任性父亲的矛盾和多面性,延伸出多层面、有深度、有意义的社会话题。理查德就像集权统治制度中的国王,用“自我中心主义”“狂妄偏执”“独断专行”等来形容没有任何网球背景、完全靠自学的理查德的为人处世都不为过。影片从具有代表性的生活细节着手,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这位带有普遍性的黑人贫民作为传主的独特性和客观性。而音乐传记电影《尊重》则将主视点放在自强自立的黑人女性身上,提出“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社会性别”问题,以期改变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底层黑人女性的成见和歧视。对传主青年时期的自身堕落,如过度饮酒以及与家人的摩擦、争执等也一并展现,没有隐瞒或避讳。影片并未因对“灵魂歌后”艾瑞莎·弗兰克林心怀崇敬之情而在人物塑造上失去想象力,而是通过扎根于人物真实的情感经历来再现她众多成名歌曲的形成过程,音乐歌曲很好地成为激励她人生奋进、拼搏的无形力量。影片强调了传主琐碎、私密的一面,通过情感历程突出人物个性,且赋予深度和多层次的刻画。这些更能真实地勾勒传主的人格特征,使得人物形象显得更加光鲜亮丽、饱满生动。
深化崇敬型认同与寻求体验型认同
2021 年的中国传记电影,主要着力于叙述传主为国家与集体事业奋斗、奉献和付出的事迹,用以强化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和凝聚力。《革命者》《我的父亲焦裕禄》《柳青》《守岛人》强调了传主对事业专注、投入的伟大精神和无私品德,有益于观众理解传主道德完善的内在逻辑。影片通过文化身份的建构,把个人身份渗透到民族身份当中,使传主逐步地变成民族寓言里的父型人物。在德智双全的父型人物的形成过程中,民族身份的建构是至为关键的,占主导性的情感是崇敬型认同。四部影片均为观众树立了崇高可敬的英雄模范形象,用以升起一股对英雄模范的崇拜。这些英雄模范的典型事件让传主形成了壁立千仞的权威人格,在情感和认知上具有排他性。需要指出的是,这四部影片除了采取自下而上的仰视视角之外,还引入了平视视角,即除了强调传主的伟大之外,还不同程度地突出了传主的平凡,写出了平凡里所具有的难以磨灭的价值,以接地气。正是由于两种视角的组合,使得影片突破了崇敬型认同的最大局限,即创作者对权威人格的依附所造成的视域遮蔽。虽然崇敬型认同这种自下而上的探视方式和认知方式让观众看到了巨峰叹为观止的一面,却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视域受阻”,但平视视角摆脱了一般崇敬型认同的窠臼,有效弥补了与传主的人格契合。
在观看《革命者》《我的父亲焦裕禄》《柳青》《守岛人》的过程中,观众的灵魂能够得到洗礼,精神能够得到提扬,从而能够引发反躬自省、激发爱国行动。就观众与创作者的关系而言,《我的父亲焦裕禄》因双重叙事视角的使用显得较为亲切。影片中,传主的女儿在叙事中需要同时充当叙事者和传记电影中的人物。“这就强调了叙述者具备叙述的权威性:与传主关系亲切,是传主生平的见证人,是历史事件的目击者。”[3]叙事者在叙述与传主之间的亲切关系时,采用了传主女儿的叙事视角和理解能力,这时观众通过传主女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人物形象和事件是有限的,理解能力也是相对较低的;而在叙述传主其他生平事件时则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这样叙事者不仅能够知晓一切,而且能够对过去的所有事件清晰、正确地洞察。这样就能够产生两大好处:一是作为影片人物的传主女儿成为传记电影中所叙述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她刻画的传主就是经过自己的观察加工之后的人物形象。这就使影片不仅能够为加工手法找出依据,而且使传主形象更为可信;二是极大地增强了传记电影的生动性。这种手法将观众拉入叙事世界,并使观众透过传主女儿的眼睛身临其境地体验经过戏剧化渲染的事件,这便使观众的观看过程如同观看纪录片一般,大大提高了作品的逼真感。而《革命者》《柳青》《守岛人》中的创作者则不是置身其内,而是置身于传主的精神世界之外进行观察。影片表面上以传主的视点展示传主与他人的关系、传主与时代的关系,事实上是通过他人的眼光反观传主自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特别是对传主一生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之关系,把人当作一个整体,而没有使传主成为一座“孤岛”。在由别人来证实的事实的“诱导暗示”下,创作者把握传主的性格和精神气质,从而产生一种崇敬型认同。
而2021 年的美国传记电影都在讲述传主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以传主的人生经历、拼搏精神,给当下人的立身处世提供某种借鉴。大多数影片占主导性的情感是体验型认同,创作者似乎在亲自感受着传主的生活,探索着不同的人生。在体验型认同中,创作者不会过分关注自身的主观倾诉,而是试图进入传主的心灵空间。创作者与传主达到身体、思想、感情上的相融,从而达到一种精神、个性的契合,仿佛进入了无“隔”的化境。“融而不隔”,趋向一种整体性,即创作者与传主之间“隐含着一种交流的相互性、合作的平等感”[4]。创作者的视野甚至进入了传主个人的隐私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展现传主私下里亲密的一面,努力展现传主作为“人”的各个方面。
就观众与创作者的关系而言,这一时期美国传记电影的创作者大多力求在影片文本中与观众之间建立平等、亲密的关系,让观众自行判断影片中所述事件,并接近传主赤裸裸不加修饰的灵魂。例如,《美国草根:库尔特·华纳的故事》围绕华纳对爱情的真诚和执着、对梦想的追逐和坚韧,展示了他在遭遇挫折、低谷、阻力和打击过程中的笃定和坚持不懈,即使坐了四年冷板凳仍然没有放弃梦想并且坚定必胜的信念,让人感受到他作为平凡人在不屈不挠中所练出的强大心脏和壮阔胸怀。华纳对待顺境和逆境的态度以及其所持有的爱情观和人生观是个人奋斗成功的普遍案例,易于与观众个体的生存体验融为一体。而《倒数时刻》并没有过多阐述拉森在首演前死亡的戏剧性命运,把他当神一样来崇拜,而是把他当成普通人中的一员,描摹了他三十而立之时却一事无成,带着恐慌、急躁与困惑伫立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孤独身影。影片背后折射着当代年轻人身陷现实与理想夹缝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使观众对于生存感悟具有强烈的代入感。如果说《美国草根:库尔特·华纳的故事》和《倒数时刻》通过传主的励志故事展现了传主乐观、积极、进取的个人品质,那么《美国叛徒:轴心莎莉的审判》则把轴心莎莉不可告人的一面予以曝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使人看清真伪。创作者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倾向性平衡,既重视个体生命的复杂性,又防止类化造成的“扁平性格”。也就是说,创作者没有把轴心莎莉当作“类”来处理,而是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刻画。观众看到的是轴心莎莉变幻如虹的个性展示,是一种生存极限不断受到挑战之下反抗品质愈演愈烈的程度递进。轴心莎莉在纳粹德国官方广播电台“柏林之音”为纳粹宣传,瓦解美国军队士气,是因为受到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胁迫,身陷战争无法选择对错,迫于生存需要才沦为被操控的傀儡。创作者清晰的创作意图了然可见:试图通过冷静的历史分析,勾勒出轴心莎莉作为一个普通正常人的一面——对生命和爱情的强烈渴望,而不是用脸谱化方式去塑造一个遗臭万年的人民公敌和一个助纣为虐、恶贯满盈的女性形象。影片没有把轴心莎莉描绘成一副没有血肉的骨架,而是具有传记电影应有的剖析深度,达到了艺术的完整性。电影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同类,观众在看传主的生平故事就是某种程度的自我释放、自我排解。在另一个人的踪迹中,观众的内心产生一种共鸣,会反观思考自我。在同样的时代中,在同样的处境里,观众会联想到自己是否也可能出现同样的困惑,犯下同样的错误,走向同样的道路。这就是体验型认同带来的必然结果。
秉持求善的标准与坚持述奇的原则
2021 年中国传记电影《革命者》《我的父亲焦裕禄》《柳青》《守岛人》的创作者强调通过描写传主生平中具体的事迹而不是通过抽象的讲道来弘扬善德。创作者的目光主要聚焦于人物行为,抓住经脉,围绕个人的历史事件与成就展开叙述。同时,《革命者》《我的父亲焦裕禄》《柳青》《守岛人》里的传主都是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行事,他们本人的利益和国家、集体的利益是一致的,即是以善的标准来行事。四部影片强化和突出了传主舍己为民的牺牲品格,艺术地揭示美德之美,秉持求善的标准来深化影片的主旨。
《革命者》《我的父亲焦裕禄》《柳青》《守岛人》注意表现的是传主心灵中不变的特征、永恒的品质。提炼心像是这四部影片的立传点。“在人的整个一生中,行为变化莫测,境遇时好时坏。心像就要在这些不定的因素中提炼出本质的东西、不变的东西、极富特征的东西。”[5]虽然《守岛人》叙说了王继才起初并不愿意守岛,但此后其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自愿和主动守岛的,因此忠诚守岛仍然属于王继才心灵里的不变本质。在《革命者》中,李大钊从1912 年回国到1927 年牺牲都是坚定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的革命先驱,为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民幸福发出时代强音。影片基本上遵从通过围绕人物心像叙述其成就和公众生活的历史叙述传统。在《我的父亲焦裕禄》中,公共事务和家庭生活的作用最为关键。影片详尽地罗列出传主的公共事务,以强调传主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格。因为是传主女儿的叙述视角,影片还把一部分心思放在家庭生活上,去展现日常生活中传主是如何身体力行地教诲儿女的,竭力表现传主世俗的伟大。影片《柳青》在塑造传主心像上,既纵向贯穿了历史发展的线索,同时也进行了横向的交流互动,传主的性格从一而终,始终是深沉地热爱人民和土地的作家。总之,无论是李大钊、焦裕禄、柳青还是王继才,创作者都注重表现他们与人为善的本质和善行。传主本人的特质为传记电影平添了生命的光辉。四部影片均写出了传主心灵中“本质的东西”,写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亦即围绕心像写出那些富有精神意味的行为、言辞和事迹,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叙述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而2021 年的美国传记电影的目光不局限于杰出个人,也不局限于人物光辉的一面。它们展现了美国的众生百态,只要人物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就可以成为传主。既可以叙述善行也可以叙述恶行,创作者尽量保持客观中立的叙述。它们普遍注重述奇且实录,如实展现传主的原貌、全貌,以栩栩如生的描述见长。真实性、准确性、传奇性是美国传记电影创作追求的目标,其中传奇性独具一格。
例如,《里卡多一家》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明星伉俪露西尔·鲍尔和戴斯·阿纳兹在排演经典情景喜剧《我爱露西》第二季的五天轶事为主线,讲述了鲍尔遭遇突然怀孕、政治身份质疑、丈夫出轨等人生阶段中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鲍尔身上接二连三的恶意诽谤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缩影,影片以真实而辛辣的笔触展示了在麦卡锡主义冲击下演员的生存状态,嘲讽了麦卡锡主义的荒诞可笑。同样是讲述电视明星伉俪故事的《塔米·菲的眼睛》,不再像《里卡多一家》一样采取特写式聚焦和横截面叙事,而是讲述了塔米·菲和吉姆·贝克这对夫妇作为电视福音布道家大喜大悲的人生。影片再现了夫妻二人艰苦创业的经历,又披露了他们一步步跌落神坛的过程,两人虔诚激情的福音布道和奢靡纵欲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强烈反差。两部影片都抵近真实,带领观众看到两对明星夫妻婚姻破裂乃至事业陨落的真相,不避私生活,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观众追求传奇性的情感需求。而《兰斯基》以迈入古稀之年且隐居在迈阿密海滩的美国籍波兰裔犹太人梅耶·兰斯基找作家述说自传为主线,回顾了他在20 世纪上半叶的血腥发家史。兰斯基杀人如麻,在美国是爱国者也是逃犯。影片没有美化他的罪恶、洗白他的污点,而是诚实以待,展示了这位黑帮大佬的经商逻辑和生存哲学,并穿插了罪与罚的因果报应。兰斯基是一个正直与邪恶并举、瑕疵与能力皆不寻常的人。整部传记电影条理清晰,逻辑分明,人物展现极具穿透力和新奇感,把一位个性复杂、野心勃勃而又有情有义的兰斯基描绘得光彩夺目、立体生动。影片把传主的生平和许多琐事也处理得极富戏剧性,这种富于历史整合能力的叙事技巧使得影片的叙事紧凑生动、跌宕起伏,既把兰斯基的性格描绘得活灵活现,并且准确地把握和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对于想了解20 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和黑手党首领生活的观众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兰斯基人性的真实和复杂,包括灰色地带,在影片中都被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真实毫无遮掩,即使是最隐秘之处也呈现出来。创作者竭尽全力实现真实性和全面性,而且力图展开微小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传主不同于他人的个体差异性。
2021 年美国传记电影大多以奇制胜,以奇闻轶事娱乐观众,娱乐性强、可观赏性强是其突出特点。一方面,为了践行传记电影的娱乐目的,创作者善于抓住传主与众不同的个性和最典型的特征,包括邪恶的特征,充分体现对人物个性的重视;另一方面,在传记电影中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立传,实现了人物高度的全面性,忠实地呈现传主的缺点、弱点和错误,善于从私密生活中挖掘丰富的细节,将人生的琐碎细节和人物的千奇百怪刻画得淋漓尽致,从小处发掘人物的过人之处或揭示人物的离经叛道,令人耳目一新。
结语
2021 年的中国传记电影和美国传记电影,都不再只是突出传主的行为及外在的个性表征,而是努力探索传主生活和思想深处之路径,更加趋向于对传主个人意识的探究,坦露的形式也转向传主的自我与内心。影片不仅是对传主一生重大事务的记录,同时也是对其私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具有特性的细节的描述。中国传记电影则更加注重于个人与时代发展的融合,弘扬社会道德的正向能量。此外,传记电影创作不仅需要注重传主的个性和多样性,而且还要寓教于乐,运用各种手法将传记的娱乐性与道德教化目的融为一体,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清晰、有力地表达观点,以娱乐性为契机实现极好的道德教化效果。
注释:
[1][4][5]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122 页,第130 页,第214 页。
[2][3]唐岫敏等:《英国传记发展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年版,第126 页,第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