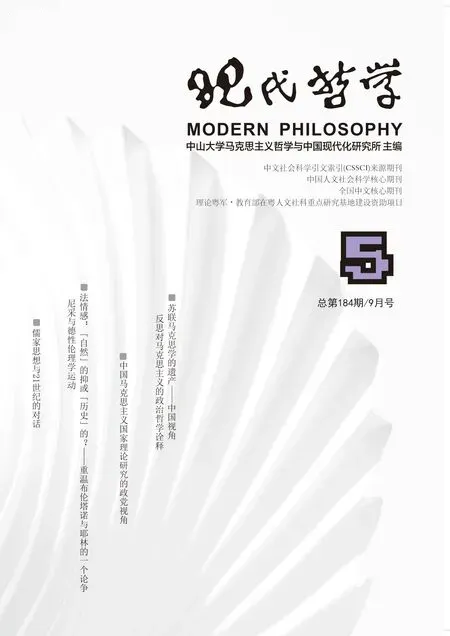关于现象学美学史分期的初步设想
——从马里翁-亨利的还原观出发
方向红 黄子明
一场延续一个多世纪的现象学运动已蔚然大观,一部现象学运动史也早已问世,可与现象学运动几乎同期展开的现象学美学运动却至今缺少一部严格的现象学美学史,究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也许还是在于现象学美学史的分期问题。我们知道,凡是历史都涉及到分期问题,而分期的依据是相关的理论设定或学术范式,现象学美学史当然也不例外。由于缺乏一种俯视现象学美学史的目光,目前已出版的各类现象学美学史的文章或著作鲜有对这个问题作过全面的反思。
说到现象学美学史,当首推塞普(Hans Rainer Sepp)和任沛德(Lester Embree)合编的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现象学美学手册》(1)H. R. Sepp & L. Embree (eds.),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Dordrecht/Heidelberg/London/New York: Springer, 2010.,但即使在两人合作撰写的导言中,现象学美学史也没有任何分期,他们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并结合地域对现象学美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逐一作了介绍。国内有一本作为专名出现的《现象学美学史》(2)郭勇健:《现象学美学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在“绪论”中作者对历史分期有着明确的意识,但在具体分期时,还是用几个先后出现的概念来框架现象学美学的发展史(3)同上,第8页。,而对这些概念背后的学理支持、不同发展阶段的现象学美学与相应时期的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其自身内部的问题以及各阶段之间的转化逻辑避而不谈,似乎现象学美学的发展是突然之间从一种研究模式进入到另一种研究模式。对现象学美学分期真正具有方法论自觉的作品应该是苏宏斌的《现象学美学导论》,作者明确强调探讨现象学美学问题之哲学前提的重要性并将其归之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4)苏宏斌:《现象学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页。。这种做法给出了现象学美学所依据的学术范式,满足了我们的严格性要求,但由于作者以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的《审美经验现象学》为自己著作的“基本框架”(5)苏宏斌:《现象学美学导论》,第7页。,所以在杜夫海纳这本书之外或之后的现象学美学思想便不再进入该书的视域,这使得作者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反思。其他涉及现象学美学史的文献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在谈到现象学美学的发展史时只是给出了“意义”及其理解的一条单一的线索(6)[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9-99页。,斯坦福哲学百科谈到了一些重要的现象学美学家,但却没有出现“现象学美学”这个词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本文的做法是,站在现象学和现象学美学的最新发展点上,依据现象学运动史的分期、现象学与美学的内在关联并结合美学自身的特点对现象学美学进行分期。这个做法的理由是,美学本身的每一次流变都依赖于哲学理论的转变,现象学美学更是如此,现象学美学学派的每一场内部争论以及学派之间的每一次思想冲突和理论演进都与同时期现象学理论的争论和转向密不可分。正如哲学是美学的上位学科一样,现象学也是现象学美学的上位学科。因此,对现象学美学史的分期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学美学发展史的内部,而必须从现象学运动史的高度把握这个问题。
当然,对现象学运动史的理解有很多种,对它的分期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们这里遵从的是法国“新现象学”家马里翁(Jean-Luc Marion)和亨利(Michel Henry)从现象学还原角度对现象学运动史的理解。
一、现象学还原与现象学运动的转向
马里翁认为,迄今为止,在现象学运动史上一共存在过三种类型的还原。对于这三种还原,他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描述。关于第一种还原,他说:
第一种还原是超越论的还原(这个还原是“笛卡尔的”,“康德的”还是“现象学的”,在这里并不重要),它等同于对象的构造。(1)对它的展开是为了意向的自我(Je)或构造性的自我。(2)它把被构造的对象给予自我。(3)对这些对象的把握是在区域存在论中进行的,而区域存在论通过形式存在论完全符合于对象性的视域。(4)这样,它便从被给予性中排除了所有无法被回溯到对象性之上的东西,就是说,排除了所有存在方式(意识的存在方式,用具的存在方式以及世界的存在方式等)在原则上的差异。(7)[法]马里翁:《还原与给予——胡塞尔、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48页。以下简称为《还原与给予》。
这段话的关键词是自我、意向、通过区域存在论而出现的对象以及通过形式存在论而出现的对象性(8)在胡塞尔那里,对象(Gegenstand)和对象性(Gegenständlichkeit)是不同的,前者位于特定的区域之中,例如钢笔位于学习用品这个区域中,而后者是某种类似于对象一样的东西,例如一个句子“这支钢笔是借来的”,其意义本身就是一个类似于对象的东西,它的组成成分中包含了形式化的要素如“这、是”等等。,马里翁在这里不无道理地把它们统统称为对象性,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自我和对象也都是意识对象,都是意向性意义上的对象性。
这就是第一种还原,在马里翁看来,它的缺陷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那些无法还原到对象性之上的东西就不再进入胡塞尔意识哲学的眼帘了;另一方面,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存在方式,例如意识的存在方式、用具的存在方式、世界的存在方式等等,都被敉平了,相互之间不再有根本性的区别。显然,这些缺陷不是两个缺陷,而是同一个缺陷的两个方面。
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海德格尔发动了第二次还原,马里翁将其称为生存论还原:
第二种还原表现为生存论上的还原,它的方式是通过生存性的存在者而推动这个还原……(1)它还原到此在,对它的理解所依据的是它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已经着眼于存在者之整体而被扩展至在世中,并且通过操心而被一直回溯到它的超越性。(2)它给出了(或声称给出了)不同的存在方式,因而也给出了存在论差异本身,简言之,给出了“存在的现象”;(3)它依据时间的境域,因而它尤其依据作为原初的和终极的现象的存在本身。(4)于是,它排除了那些不必存在的东西,特别是排除了“存在的现象”的先决条件(无聊,要求,等等)。(9)[法]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348-349页。
这段话的关键词有此在、存在者之整体、在世、存在论差异、存在的现象等等,在马里翁看来,经过了生存论还原,我们发现对象性的先决条件在于生存论,正是由于此在在世中的各种生存活动才产生出意识的各种对象性。由此,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现了:生存论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或者如马里翁所说,“‘存在的现象’的先决条件”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胡塞尔的“被给予”概念是一个不自觉的回应,而海德格尔所谈到的“存在的呼声”或“吁求”以及作为情绪出现的“深度无聊”已经透露出并指引着可能的回答,马里翁正是沿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无意和有意之间开辟的道路继续深化现象学还原的,他把还原推进到第三阶段:
恰当地说,第三种还原——我们全部事业的目的仅仅在于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认识到这一点——不存在,因为严格地实行着还原的呼声不再来自存在的境域(也不来自对象性的视域),而是来自纯粹形式的呼声。(1)它还原到被吁请者,其方式是把任何自我(Je),甚至任何此在回溯到单纯的听者的形象,而呼声——由于它的不确定性,它仍然是绝对的——恰恰先于这种形象并创设了这种形象。(2)它给出了赠礼本身:这是一个让人走向呼声之要求的赠礼,或者是让人避开呼声之要求的赠礼。(3)它所依据的仅仅是绝对无条件的呼声和绝对无约束的回应的视域。(4)这个要求在前提和规定上的原初缺席使它有可能发出召唤,而且这种召唤没有任何限制,——它既不局限于客观化之物的上面,也不局限于非客观化之物的上面;既不局限于不必存在的东西上面,也不局限于必须存在的东西上面。最后的还原还原到被吁请者,因而给出了所有能召唤的和能被召唤的东西。(10)同上,第349页。黑体为原作者所加。
这一段的关键词有呼声、召唤、吁请者、赠礼等,在马里翁看来,呼声、召唤和赠礼都是“绝对无条件的”和“绝对无约束的”,它们位于自我和存在之先并使之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它们越出了意识哲学和存在论。正是在这里,现象学需要实行第三次还原,也正是由于生存论还原受到还原,所以马里翁说“第三种还原……不存在”。由这种“不存在的”还原所给出的绝对意义上的吁请者就是马里翁所谓的“神”。
如果回顾现象学还原的三次历程,我们就会发现,随着还原的彻底性的增加,被给予的实事也越来越多。马里翁把这种情况总结为“有多少还原,就有多少被给予”(11)同上,第348页。,亨利对这种情况更加准确的表述是“还原越多,给予越多”(12)[法]亨利:《现象学的四条原理》,王炳文译,《哲学译丛》1993年第1期,第25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还原可以无限进行下去。在马里翁眼里,第三次还原是最后的还原,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实事本身的自身给予的程度了。
现在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现象学运动的历史分期问题了。从第三次还原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现象学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意识现象学阶段、存在现象学阶段以及“新现象学”阶段。意识现象学以意识为最高概念,以意向性统摄自我、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三个方面的研究。这三个方面可以接续几乎所有哲学领域的研究:从认识论到价值论,从符号学到判断理论,从经验主体到先验自我,从本我论到交互主体性,从伦理到审美,无一不在意识现象学的辐射范围之内。胡塞尔显然是这一现象学的代表,其他如舍勒(Max Scheler)、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慕尼黑小组、哥廷根小组等也都属于这一阶段;存在现象学以存在为最高概念,通过对此在在世中的生存论分析将意识现象学的总体思路安置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并对意识现象学的几乎所有的概念进行了颠覆并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这一现象学的代表当首推海德格尔,但胡塞尔中晚期的发生现象学也具有典型的生存论特色,属于这一阶段的现象学家还包括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萨特、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等人。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萨特和梅洛-庞蒂虽然也笼罩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思想的巨大阴影之下,但他们从法国思想传统出发对已有的现象学概念,如海德格尔的“情绪”(萨特)、胡塞尔的“身体”(萨特、梅洛-庞蒂)等,所作的新的描述和分析,其丰富性和深度远远超出了经典现象学家的讨论域,对于现象学运动乃至现象学美学运动的转向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新现象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在德法同时诞生,虽然对他们的命名相差了30年(13)施密茨在1980年就出版了以“新现象学”命名的专著,而整整新一代法国现象学家直到2011年才由冈代克(H.-D.Gondek)和腾格尔义(L.Tengelyi)给出了相同的名称。(See Hermann Schmitz, Neue Phänomenologie, Bonn: Bouvier, 1980; H.-D. Gondek & L. Tengelyi, Neue Phänomenologie in Frankreich,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1.)。“新现象学”的共同特点是对生存论还原进行还原,以便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超出存在论的领域。法国“新现象学”的思路在前述的马里翁的还原理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在德国,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的表述似乎更加直截了当:“摆脱并超越先验现象学思想是困难的,而且会遭到形形色色的敌视,而摆脱并超越存在论现象学就更为困难且会遭到更多的敌视。然而现象学思想迫使自身趋向于此。”(14)[德]罗姆巴赫:《现象学之道》,王俊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2期,第13页。法国“新现象学”的主要人物有马里翁、晚期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晚期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亨利、里希尔(Marc Richir)等人,他们无视意识现象学的规定和存在现象学的要求去重新思考意识、自我、主体、存在、此在和在世等主题,完成了现象学运动的神学转向;德国“新现象学”的旗手是施密茨(Hermann Schmitz)和罗姆巴赫,后者通过自己的“结构现象学”和“密释学”取消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位置,把人降为自然之“大结构”的一部分,而前者则更进一步,他批判地继承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创造性地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情绪”理论以及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身体”学说引向一种新的、基于自然之上的“气氛”。两人合力完成了现象学运动的生态转向。
有了现象学还原理论以及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对现象学运动历史分期的理解,我们现在便可以尝试对现象学美学史进行分期了。
二、关于现象学美学史分期的初步设想
我们将现象学美学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1)德国现象学美学,这一阶段可进一步细分为哥廷根-慕尼黑阶段、弗莱堡—康斯坦茨阶段;(2)法国现象学美学;(3)德法“新现象学”美学。下面将具体介绍各个阶段的思想特征、主要人物和核心概念(15)下文对现象学美学个别人物的谱系学关联及其评价参照了《现象学美学手册》。。
(一)德国现象学美学阶段
这一时期的现象学美学围绕着意识现象学和存在现象学展开美学思考。现象学作为20世纪初的新思潮登上历史舞台,其基本思想方法和立场初步形成,现象学美学随之初具雏形。这个阶段奠定了后来现象学美学的基本方法和主要议题的基调,后来的现象学美学无论是拓展还是批判,都与这一时期的现象学美学的工作密切相关。依据现象学自身的逻辑发展,这一时期的美学又可以分为哥廷根-慕尼黑阶段和弗莱堡-康斯坦茨阶段,分别基于现象学的两大传统,即胡塞尔开创的“意识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开创的“生存论现象学”。
第一,哥廷根-慕尼黑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可以概括为意识现象学美学。现象学兴起于哥廷根小组,而现象学美学却初成于慕尼黑小组。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慕尼黑利普斯(Theodor Lipps)的学生圈子里首先赢得了一批支持者,他们对美学和艺术问题感兴趣,在慕尼黑形成了现象学美学。道伯特(Johannes Daubert)是两个小组之间的重要联系人,他关注对人的感觉感受的考察。哥廷根小组的代表人物有沙普(Wilhelm Schapp),他侧重感知现象学研究,他的“故事哲学”展开对叙事结构的现象学研究。由于有着现象学和移情心理学的双重理论来源,这一时期的现象学美学也伴随着一些内部争论,如康拉德(Theodor Conrad)坚持在美学中将现象学方法独立于心理学解释,而费舍尔(Aloys Fischer)则主张通过现象学与心理学方法的结合来分析审美享受。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现象学美学的共同点在于从意识尤其是从意识的意向性结构来谈审美,关注的重点在于感受、享受、价值等问题。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为盖格尔(Moritz Geiger),他从现象学角度对心理学美学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将基于心理事件的事实论美学提升为基于审美享受的价值论美学,赋予审美价值以现象学的客观性,形成了现象学的心理学美学。
第二,弗莱堡-康斯坦茨阶段。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可以概括为存在现象学美学及其与意识现象学美学的调和。如果说上一阶段对应着胡塞尔早期思想即本质现象学,那么这一阶段则对应胡塞尔晚期思想(发生现象学、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生活世界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早期基础存在论时期的思想。在这一阶段,美的显现不再以单纯意识哲学的方式来考察,而是置于“此在”的“在世之在”的生存论基地上来探讨。这一时期的美学除了继承上一阶段的基于审美体验的美学价值论,还发展了具有艺术存在论意味的艺术哲学。这一组人物有一部分来自哥廷根和慕尼黑小组,他们尝试将现象学两大传统加以综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舍勒将艺术表现性还原到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而哈特曼则强调艺术作品的完成还在于它的被接受和被解释的过程中,这些视角都是基于意识现象学重塑艺术存在论;与此相反,考夫曼(Fritz Kaufmann)尝试以生存论改造早期的移情理论,这是基于存在论重塑审美意识理论。另外,这一时期还包括现象学美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波兰籍哲学家英加登(Roman Ingarden)(尽管他的主要成就并不都是在德国时期完成的),他将审美对象归结于“纯粹意向对象”,对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加以详细的层次分析,旨在对每一种审美范畴的价值给予定位,建立现象学的艺术存在论。胡塞尔的另一位学生芬克(Eugen Fink)的“游戏理论”作为艺术表现论结合了两大传统,“游戏”作为一种“符号”既在世界之中(现象学存在论),又朝向世界(意识现象学),他尝试在综合的基础上超越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继承了他的老师哈特曼的思路,将艺术作品如何通过解释得以实现的理论充分发展起来,创建了奠基于现象学土壤中的哲学解释学,由此诞生了解释学美学,其解释学美学的最新发展表现为在康斯坦茨形成的接受美学学派。这一学派以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伊泽尔(Wolfgang Iser)为代表,这种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胡塞尔交互主体性思想在美学领域的回应,它强调读者对于文本之完成的重要意义。其中伊泽尔的接受美学吸收了英加登关于文学作品的美学思想,认为是文本与读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意义,强调作品完成的动态过程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
(二)法国现象学美学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身体现象学美学。在西方美学传统中,身体维度是长期缺位的,法国现象学美学将德国现象学中已经出现的身体理论作为核心要素纳入艺术和美学理论。这一阶段的现象学美学主要是对弗莱堡-康斯坦茨阶段的存在论美学议题的回应、批判和改造。萨特和梅洛-庞蒂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萨特不仅在意识现象学美学的意义上处理了感觉与想象、呈现与再现等传统范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存在现象学美学的意义上将身体引入现象学和现象学美学,对身体的自为性、为他性、散朴性及其在情绪、自欺、爱和性等方面的表现提出了自己见解;梅洛-庞蒂更是实现现象学美学的身体转向的关键人物,他的知觉现象学通过对知觉的超越性和直接性显现结构的描述来说明知觉活动对于揭示人的“在世之在”的基础性意义,而知觉恰恰是表明人与世界之统一关联的最原始而直接的身体性活动。在《眼与心》中,梅洛-庞蒂通过还原消解了对视觉感知的笛卡尔式的理解模式,艺术是通过身体与现实的“原始而生动”的接触方式而显现的。在这里,真实与想象、可见与不可见、主动与被动等范畴在新的知觉理论中得到重新思考。审美知觉的超越性最终通过身体与世界、身体与作品之间的“可逆性”概念得以完成,这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在存在论及审美现象学中的拓展。“可逆性”意味着从意识分析向存在论过渡的一条完成路径,它表明世界和艺术家是同一个力量的两个方面,艺术作品在其创作和表达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夫海纳,作为德法现象学美学的集大成者,他在自己的美学体系中对意识现象学美学和存在现象学美学进行沟通、诠释和整合。他的著作《审美经验现象学》被视为“现象学运动中美学方面不仅篇幅最大而且很可能是内容最广泛的著作”(16)[美]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92页。,该著作既有古典美学的精致架构,又有现象学的先锋思想,其论题范围和思想综合性达到当时最高水平。杜夫海纳的美学思想表现出对德法现象学传统的诸多渊源的合流:他将“审美经验”从“审美知觉”和“审美对象”两方面加以分析,其结构是复刻胡塞尔的超越论意识现象学将“纯粹意识”分为“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两方面;审美对象被归结为“知觉对象”而不是想象对象,这是深刻理解了胡塞尔的超越论还原得出的结果,同时对知觉的审美直接性的强调与梅洛-庞蒂的知觉理论有深刻关联;对“审美经验”的先天性的分析则是综合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对于审美普遍性的传统问题给予现象学角度的回应;而他对“纯粹美学”理想的批判性探讨则是站在现象学的开放性立场上对传统存在论美学建构理想的回应。他的《诗境》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艺术存在论的最终基础,其中蕴含着“新现象学”的萌芽思想。
(三)德法“新现象学”美学
如果说德法现象学美学是一段过去了的、可以初步加以定论的思想历程,那么德法“新现象学”美学则是正在进行中的、活生生的当下的历史,其中一些核心人物尚健在,他们的思想还在不断酝酿、完善和建构中。尽管如此,但这一阶段现象学美学的总体特征还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美学家们试图完成对此前现象学工作的反思、综合、批判与超越。这种超越,与德法“新现象学”的超越相呼应,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转向——生态转向和神学转向。
第一,德国新现象学美学。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现象学美学的生态转向。这一转向的主要推动者是罗姆巴赫和施密茨,从罗姆巴赫的“大结构”可以直接走向生态现象学并进而走向现象学生态美学,而施密茨的“气氛”本身就是一种“气氛美学”。当然,这种气氛美学与现象学生态美学在理论背景和实践旨趣上并无二致,甚至在波默(Gernot Böhme)那里,前者只是后者在理论探索上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第二,法国新现象学美学。这一阶段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现象学美学的神学转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推马里翁、亨利、里希尔、后期德里达和利科(Paul Ricoeur)。无论是马里翁关于“不可见者”与“可见者的交错”,亨利关于康定斯基绘画中存在的“内在的悸动”和内在的启示,或者是德里达在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中发现的“幽灵”,抑或是利科在《活的隐喻》中所谓的在诗歌中“创造与启示的耦合”,都无一例外地朝向那经验不仅无法驱除反而将其凸显出来的绝对超越者。
这是我们对现象学美学历史分期的初步尝试。可以看出,这种尝试与现象学运动本身的历史分期既高度重合,但也有不完全对应的地方,这该如何解释呢?
三、几点补充说明
现象学美学是现象学的下位学科,它作为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与现象学运动是同时发生、同步展开的,因此它的分期与现象学运动的分期高度重合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这里的重合表现在三个方面:地域重合、人物重合和主题重合。一般来说,现象学在某地发生的突破会立即引发现象学美学在同一地方的形成或转向。无论是在哥廷根-慕尼黑这个地域,还是在弗莱堡-康斯坦茨这两个地域,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我们看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同理,一些现象学家在完成现象学基本框架和核心概念的突破之后会亲自将自己的创新应用到现象学美学的讨论之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典型者如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德里达、利科、马里翁、亨利等等;同样,有很多重要的主题或概念在现象学和现象学美学那里是通用的,如感知、图像、体验、对象、价值、解释、接受、主体、生存、世界、情绪、可见、不可见等等。这些现象都会让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现象学美学与现象学在分期上必然是完全重合的。
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现象学和它的子学科的展开状况,我们会发现它们也有不少不完全对应的地方。在地域上,有一些现象学美学家,他们不在德国或法国,也不用德语或法语写作,例如,俄罗斯的施佩特(G. Shpet)、日本的西田几多郎(K. Nishida)、西班牙的加塞特(J. O. y Gasset)、意大利的班菲(A. Banfi)等,按理说,他们似乎无法归入我们的分期系统里去。不过,如果根据现象学美学每个发展阶段的思想特征再结合他们各自的理论框架和关键概念,他们的美学思想应当属于意识现象学美学或者存在现象学美学。在编撰现象学美学史时,在这两个阶段之下增加一些补充说明,这样便可以消除地域不对应的情况。
在人物上也有一些不对应的地方,这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有的现象学家前后期思想不一致,例如,胡塞尔的早期思想属于哥廷根-慕尼黑阶段,中后期思想总体上属于弗莱堡-康斯坦茨阶段;海德格尔中期思想属于弗莱堡-康斯坦茨阶段,而他的后期思想则达到了德法“新现象学”阶段;达到这一阶段的现象学家还有晚期德里达、后期利科、中后期列维纳斯等等,而这些人的早期还停留在法国现象学阶段;另一方面,有的人在现象学界和现象学美学界的地位差别很大,例如,盖格尔和杜夫海纳同为现象学美学界的巨擘,但他们在现象学运动中的地位并不高。对于这两点,我们也可以很容易消除其中的不对应状况。对于前者,我们只要不固执于同一个现象学家的所谓的思想整体,而是将他们的不同思想时期置于现象学美学史的不同阶段,就可以实现这种对应;而对于后者,我们不必拘泥于他们在现象学领域中究竟完成哪些创新或突破,而是要着眼于他们接受了哪个阶段的现象学思想范式以及如何将这个范式成功地与美学问题嫁接在一起。这样,不对应的状况自然也就消失了。
尽管现象学与现象学美学共享某些概念,但还是有大量的概念彼此并不对应,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这里只想强调的是,现象学运动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最高概念,其他概念围绕最高概念铺开,它们一起形成现象学的某种理论构架,而相应阶段的现象学美学并不会以现象学的最高概念为自己的思考目标,它只是在这种理论构架下作关于美的显现问题的探讨。因此,就像意识现象学美学不会也不能以意识为自己的最高概念一样,存在现象学美学也不以存在作为自己的思考目标,同理,现象学运动的身体转向也好,神学转向或生态转向也罢,在现象学美学上都被转换为对美及其显现方式的新的理解。
现象学运动史和现象学美学发展史在分期上是高度重合的,坚持这一点,现象学美学的不同阶段内部的谱系关联及其外部的起承转合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放弃这一点,则不仅会让现象学美学史的分期失去理论依据,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对现象学美学流派的理解和评价,例如,国内有些学者在进行现象学生态美学或气氛美学研究时对海德格尔的早期、中期和后期思想不作区分,直接拿来当作自己的论证资源,这在学理上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从马里翁或罗姆巴赫的还原理论可以看得很清楚,海德格尔的早期和中期都隶属于生存论现象学美学阶段,只有晚期的思想才从根本上超越了存在,达到了德法“新现象学”的高度,而西方的现象学生态美学或气氛美学的学理基础则是已经完成第三次还原的德法“新现象学”。没有分期的依据,缺乏学理的支撑,我们如何能真正理解现象学生态美学和气氛美学?又如何对它们作出恰当的批评和评价?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现象学还原视域下的现象学运动史分期及其对于现象学美学史分期的指导意义,坚持现象学运动史分期的优先性及其与现象学美学史分期的高度重合性。
——专栏导语
——《17—19世纪法国美学主潮》评介
——《巴蜀美学史稿》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