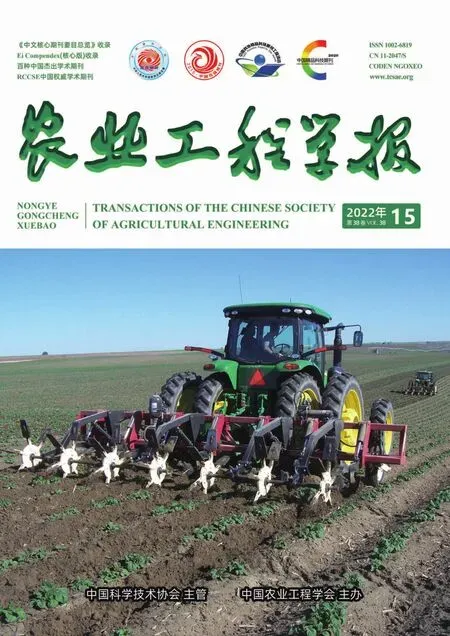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特征与中国特色乡村发展路径探索
洪仁彪,张忠明,李树君
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特征与中国特色乡村发展路径探索
洪仁彪,张忠明,李树君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与农村规划研究所,北京 10012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该研究提炼了西方发达国家乡村发展实践中功能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村落转型和政策演进等方面的共性特征,总结了中国乡村具有担负粮食安全任务、并联式现代化环境、家户小农主体、流动性多元化社会、聚落空间变革、发展基础薄弱等方面的特性。在此基础上,探索提出了树立城乡等值理念、重视粮食生产与农业现代化、培育壮大乡村二三产业、以精明收缩指导空间优化、巩固乡土文化和创新机制政策等中国特色乡村发展路径建议,为中国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为政策制定提供策略参考。
乡村振兴;发达国家;乡村转型;中国;乡村发展路径;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引 言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如何看待乡村,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乡村发展规律,对于谋划乡村振兴路径和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从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提取规律特征,可以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参考。
国内外对于乡村发展已进行了诸多研究。乡村内涵特征是研究乡村发展规律的起手,尼克等[1]综合了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和规划学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后指出,乡村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人口低密度”区域,具有特殊的空间结构,以及独特的经济体系、文化形态、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胡晓亮等[2]辨析了国内外学者对乡村概念的理解,认为乡村概念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内涵。部分学者比较了西方各国乡村发展历程,提炼出乡村演进规律,汤爽爽[3]指出乡村发展经历了单一功能到功能分化,再到多功能协调的演进;姚龙等[4]认为乡村发展是乡村由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进步、转化的过程,是特定乡村地域系统内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和谐进步、环境不断改善、文化持续传承的良性演进。还有的学者研究了乡村演化机制,叶超等[5]提出城乡关系变化与乡村演变高度相关,陈诚[6]认为政策是乡村演变的重要推手,张俊杰等[7-9]发现各国都把规划作为重要政策工具,规划在乡村演变中起着重要作用。姚龙等[4,6,10-12]通过案例分析,指出各国乡村发展路径是自身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邹一南等[13-14]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认为历史悠久、党的领导、人多地少、“并联式”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特征,要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各种研究从不同角度梳理了各国乡村发展脉络,揭示了各国乡村的变迁特点和政策走向,但对各国乡村演进的共性特征研究仍然存在系统性不足、规律性模糊等问题。同时,对中国乡村的发展特点和乡村建设的时代特征分析依然有待深化。鉴于此,本文选择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典型发达国家,通过对比分析各国乡村发展的历程和转型机制,找出其中的共性特质,总结乡村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剖析中国乡村振兴的国情农情乡情,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路径,为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为政策制定提供策略参考。
1 西方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特征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实现了乡村繁荣。尽管各国历史条件与发展环境不同,发展进程与变迁路径相异,但在乡村功能、经济体系、聚落空间、社会结构,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的演进特征。
1.1 乡村功能转型特征
发达国家的乡村功能转型总体上经历了从“农业生产功能为主的生产主义”阶段到“生态与休闲消费功能快速提升的后生产主义”阶段,再到“多功能协调发展的城乡等值化”阶段的演化。二战结束后,提高粮食自给率成为各国的迫切需要,乡村功能定位在进行农业生产,提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社会对健康营养食品、精神文化的需求快速增长,对环境保护日益重视,提供优质农产品、观光休闲产品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了乡村发展的重点内容,随之,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迅速发展,乡村空间从生产基地逐渐商品化为消费区域。20世纪90年代后,为进一步推进区域协调和城乡互补,发达国家陆续将乡村置于与城市等值的地位,乡村的生态保育、文化传承、社会稳定等多元价值得到了深度挖掘,乡村不仅成为多元产业的承载地和城乡居民共同的居住休憩场所,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
在各国乡村功能价值演化路径中,可以看到3个共同特点:1)粮食生产具有国家安全层面的战略地位[1]。只有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乡村的经济发展、生活居住、生态维护、田园景观和历史文化等多种功能才会得到有效发挥。2)乡村功能演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乡村从弱功能低水平到强功能高水平的螺旋式升级是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在城镇化水平达到60%以上时,对乡村的生态、居住、旅游、文化等多功能需求将快速增长。3)国家政策对乡村向多功能转变具有关键引导作用。经济政策引导人口和资本流动方向,调整着乡村经济结构;空间规划决定了土地的用途,调整着乡村的人地、产地关系;生态文化政策等直接决定着乡村功能的结构模式,调整着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利用方式。进入21世纪,保持乡村多功能性已经成为乡村发展政策的重要内容。
1.2 乡村经济转型特征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将农业作为乡村的基本产业和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采取各种措施相继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但由于农业与二三产业生产率差距日益增大,在GDP中占比不断降低,农业吸纳就业、带动增收和支撑乡村发展的作用逐渐减弱,乡村出现衰退。为此,各国采取推动工业下乡、发展乡村旅游业、培育房产业和服务业等措施,吸引城市人口、资本到乡村居住、投资,重塑了乡村经济。英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大力扶持乡村企业发展,支持乡村小微经营和农业多样化经营,开展乡村文化和传统文物保护开发活动,振兴乡村旅游业[15]。到2004年,英格兰的乡村产业中,农业占10%左右,制造业和建筑业占20%,第三产业占70%左右,其中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16]。法国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工业去中心化”政策,引导城市产业向乡村分散,到20世纪90年代,中小企业成为乡村经济的新支柱。乡村新村民的迁入带动了乡村旅游和地产服务业的蓬勃兴起,在欧洲,服务业已经成为乡村地区主导产业,2010年服务业提供了65%的地区生产总值和59%的就业岗位[17]。在美国,177家世界500强企业主要分布在小城镇,旅游休闲产业发展较好的农业县,人口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
各国乡村经济转型过程具有3个共同特征:1)从农业经济为主转向非农经济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增收地位与就业地位下降,生态和景观作用提升。非农产业成为乡村的经济支柱,发展乡村旅游、工业、房产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成为维持乡村活力的重要举措。2)经营主体从农民为主转向小企业为主。小企业在乡村布局,建设投资少、运营成本低,加上政府的政策支持,乡村成为了小型企业的摇篮,个体经济集聚成为了乡村经济的重要特征[1]。3)经济政策从农业补贴转向乡村空间管理。政策从关注农业生产效率转为关注商品化的乡村空间,调整土地利用功能、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网络、营造乡村美好景观成为提升乡村经济水平的重要措施。
1.3 乡村社会转型特征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和博格“推-拉理论”认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必然带来人口的流动[19]。乡村人口的变化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组成,社会运行和治理方式也随之改变。城市迁居群体陆续进入乡村,带来了资本和技术,活跃了乡村经济,但对乡村发展模式、文化体系和社会关系带来冲击,引发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20]。例如,德国乡村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空间分散化、居住层次分异化、地方文化多元化趋势[21],乡村原有的社会理念和生活方式逐渐边缘化,部分以原住农民为主的社区在新的乡村结构中成为“胶囊型社区”。
各国的乡村社会转型呈现5个共同特征:1)社会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原有的乡村居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离开了乡村,而逆城市化促进非农产业从业者、房地产投资者、旅游者、养老人员来到乡村,乡村从原来单一农户群体转变为非农户为主的多元群体。2)社会结构从紧密转向松散。居住群体的重组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乡村原有的血缘、地缘关系降低,以利益为纽带的业缘关系增强,内聚力减弱,市场力提高,村庄从“共同体”紧密结构过渡到“社会性”松散结构。3)社会联系从封闭走向开放。新移民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和交流方式,叠加交通设施和信息网络的改进,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更加开放、多元,人口、资本、技术、信息在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乡村系统从稳定性转向流动性。4)社会价值观由同质转向异质。教育的进步、人际的交流促进了乡村居民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变化,村民更加崇尚理性的社会关系,个性化、自由化成为新的人生取向。5)社会管理从内部自治走向多元共治。在传统社区,村民自己制定规则,决定乡村发展方向和建设方案。随着政府政策作用的增强,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以及村民多元化引起的冲突增加,现代社区的发展和建设越来越受法律、政府、企业的约束和引导。
1.4 乡村村落转型特征
村落是人们在乡村生产、生活和进行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22]。乡村功能、经济、社会的转型对乡村提出了新的空间需求和村落布局逻辑。在城市化过程中,法国的大村落规模逐渐增大,而偏远地区小村落走向消亡,乡村类型分化成城市型乡村、薄弱乡村和新兴乡村等类型[20]。日本、韩国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房屋空置、公共基础设施运营困难、社区功能衰退等问题,后期通过村庄布局更新,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以及公共服务设施“中心+圈层”配置,提高了乡村的活力[23]。德国通过“土地整理与村庄更新”运动,乡村的土地利用、聚落结构、聚落形态、建筑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24],重新焕发了乡村活力。
村落变化主要有5个方面的特征:1)村落总体规模缩减[23]。1990-2018年间,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6个国家总人口增长了17.40%;而乡村人口却由1.50亿减至1.20亿,下降了20%,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4.54%下降到16.77%。尽管后工业化时期,各国制定了诸多政策应对乡村收缩,促进了乡村人口回流,但乡村规模总体上仍呈收缩态势。2)村落布局集聚化。随着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水平的进步、经济境况的改善,特别是建设需求的变化,建房选址导向由便于农业生产逐步转向便于就业和生活,村落向交通干道沿线、公共服务中心集聚。3)村落类型分异化。在地域条件、区位交通、技术经济和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村落逐步分化,除农业资源丰富而二三产业发展条件不足的乡村保持农业主体功能外,城市周边的乡村演化成工业型村落,具有观光资源的乡村发展成旅游主导型村落。4)村落等级化。村落类型的分化带来村落规模和村落地位的差异,具有产业、教育、医疗等资源的村落升级成为具有辐射作用的中心村或集镇,与其他村落一起形成“集镇—中心村—一般村”规模等级结构。5)村落内部空间多元化。在乡村功能的迭代演进过程中,生活设施、文化娱乐、人文交流等生活空间需求日益增多,工业、旅游、商服等方面的生产空间规模大量提升,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景观等方面的生态空间成为建设重点,村落空间由农业生产与村民居住主体功能空间向生活、生态、生产多元复合空间转变。
1.5 乡村政策演进特征
19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顺序发展的“串联式”现代化过程,城乡关系从同一到对立,又走向融合。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对乡村的认识不断提高,乡村政策的理念导向、施政对象、动力设计、途径谋划等随之变化。1)在政策理念上,从乡村服务于城市转向城乡等值化。城市化前期,乡村政策以促进乡村向城市提供农产品和劳动力为导向。城市化后期,以城乡协同发展为导向,城市反哺乡村,提供城乡均等化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16]。2)在政策内容上,从单一部门政策转向综合性乡村区域政策。二战后,政府根据农业和村庄建设需要分别出台相应的政策。随着对乡村多功能的日益重视,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以法律为保障、国土空间规划为引导约束、乡村整体繁荣为目标的区域发展政策。德国的“整体性乡村更新计划”、法国的“乡村整治规划”和《乡村复兴区政策》,日本的《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都以区域整体作为对象。3)在政策着力点上,从外源性助推演进到内生性激励。二战后,各国普遍通过政策撬动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本建设乡村。这种外部力量的介入方式为乡村带来了资金、技术以及现代管理观念等,但也忽视了乡村居民自主性和地方经济文化特殊性,致使乡村发展深陷主体迷失与作用异化困境[25]。为此,各国相继转向内生式发展模式,通过发掘乡村当地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等内部潜力,合理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技术、智力资源提升内生发展能力[25]。日本在“一村一品”运动中,聚焦各村技术、产业、文化、市场等方面的地方独特性,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定居吸引力。韩国的“新活力”事业通过挖掘当地的特色与资源,改善发展“软环境”,推动区域发展[23]。德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把内生型发展优先作为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2002年又将内生型发展作为“德国的未来前景”[26]。4)在实施路径上,从自上而下转向多元主体上下协同。把国家的引领作用与民众的自发创造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是西方国家乡村发展的重要经验。20世纪80年代,英国乡村发展战略的制订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注重地方的需求,强调社区的建设。韩国的新村运动也由前期的“官主导、民参与”,改为后期的“民主导、官支援”[27]。
2 中国乡村发展特征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14多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历史底蕴、资源禀赋、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乡村基础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2.1 立足国内确保粮食安全是基本国策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粮食需求量大,解决14多亿人的吃饭问题历来是国家的头等大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粮食需求仍将呈刚性增长,预计到2030年前后,谷物需求将达到峰值的7.1亿t,即每年需增产100多亿斤[28]。这么大的需求量在国际市场既买不到也买不来[29]。据测算,中国粮食在可获得性、质量安全的指标评分仅为67分和73分[30]。近几年,受新冠疫情、俄乌局势等影响,粮食出口禁令频发,国际粮价飙升,全球粮食供应链极不稳定,中国利用国际市场的空间更加收窄。正是基于国家战略和国际市场的考虑,党中央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但由于资源硬约束[30]、粮食作物面临非粮产业竞争挤压等原因,国内粮食产能扩大的难度也在增加。紧张的粮食供求关系决定了保障粮食有效供给是中国乡村建设首要而长期的任务。
2.2 “并联式”现代化是乡村发展的时代特征
发达国家的乡村现代化是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且城市化率为工业化指数两倍左右之后发生的。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吸收了大量的乡村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现代化。之后,逆城市化又推动了工业的再布局和人口的“回流、归乡”,促进了乡村的复兴。发达国家走的是工业化、城市化、乡村现代化顺次推进的“串联式”现代化之路。中国作为“追赶型”国家,走的是“并联式”发展道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推进,前一阶段的任务没有完成,后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开始,时间压缩、目标多重、任务叠加。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中期,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89%,仅为工业化率的1.7倍。在这个阶段推进乡村振兴,仍然面临许多困境。首先,城市的虹吸作用仍在持续,资源要素总体上仍从乡村流向城市,在乡村发展二三产业推力不够,这也是部分县域开发区发展无力的部分原因所在。其次,乡村青壮年劳力持续外流,乡村劳力素质下降,空心化村庄逐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运行成本上升,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和服务均等化难度加大,严重影响了乡村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同时,国家财政收入有限,无法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对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进行高额补贴,乡村发展外源支撑乏力;此外,城市居民收入不高,到乡村消费能力弱小,加上乡村要素市场瓶颈难以破解,乡村从生产基地转变为消费区域的动力不足。在“并联式”现代化的宏观环境下,如何既充分利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成果,又克服其负面影响,增强乡村发展的动力,是乡村发展的核心问题。
2.3 家户小农是乡村发展的主体力量
中国是家户制国家[31],家户小农众多并将长期存在是中国乡村发展需要面对的基本现实,也是中国特色乡村发展道路最大的特色。2020年,全国农村有农户2.73亿户,其中经营耕地10亩(约0.67 hm2)以下农户占73.3%[32];即使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全国仍将有4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家户小农既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也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细胞,对乡村发展发挥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从对社会的贡献角度看,家户小农是乡村社会稳定和文化传承的基石。家户制强调人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其坚韧不拔、诚信友善、守望相助、家国一体的传统美德[33],成为乡村善治的精神支柱。而兼具生产与生活双重功能的特性赋予了家户小农发展的“韧性”,具有环境的适应性、面对外部就业压力时回乡的灵活性,这种韧性铸就了社会稳定的根基[31],成为社会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同时,家户小农还是农耕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承载着乡村记忆,维护着乡村生态[33]。然而,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角度看,小农经济存在先天不足。户均规模小、土地碎片化、劳动力老龄化,不利于农业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发展,市场竞争力不强。因此,在农业资源有限、“四化同步”难以充分解决乡村劳动力就业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家户小农赋能育力,克服其短板弱项,有效发挥其对乡村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价值和功能,是推进乡村建设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2.4 流动性多元化是乡村社会的发展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乡村保持着群体的单一性、经济的相对封闭性和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改革开放以后,刚性的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松动,乡村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村民个体开始从家庭、宗族、集体等组织结构中脱嵌出来,形成流动着的、多元化的乡村社会。随之,农民分化愈来愈明显,村民由原来单一的农业劳动者群体,转变为包括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多元主体的集合。富豪型、富裕型、小康型、温饱型、贫困型等不同层次收入的家庭类型显现,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拉大[34]。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层使得社会关系多元化,单纯的乡亲关系转变为乡亲、雇佣、管理、商务等多重关系,农民由“集体人”变成“社会人”,乡村社会由“熟人社会”变成“半熟人社会”,维系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人情关系逐渐由业缘关系取代,差序格局、伦理本位转变为利益格局、市场本位,身份认同走向契约认同。多元化的社会又催生了多元的思想文化,农民不仅追求更好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传统乡村文化失去了传承的土壤,部分文化出现了异化。乡村社会流动性、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给乡村善治增加了难度,提出了挑战[35-36]。
2.5 聚落空间优化是乡村空间治理的重点难点
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发展驱动中国乡村空间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在村庄总体布局方面,村落整体数量趋减与发展类型更加多样并存。从1990年到2018年,行政村从100.01万个减少到54.2万个,自然村从377.3万个减少到245.2万个[37],相当于每天消亡130多个。由于区域禀赋、经济发展和政策导向的差异,村庄从“同质同构”走向“异质异构”。工业型村庄、旅游型村庄、电商型村庄不断涌现,这类村庄经济实力强,成为人口持续增长的实心村,而经济薄弱的村庄成为了空心村。2016年空心化率不低于5%的空心村占比为57.50%,人口实心村仅为12.15%[38]。村庄的分化加速了村庄布局的重构,村庄聚落从均态分布,分化为“单核集聚”“多核结构”“单中心体系”“多中心网络”等多种布局类型。在村庄内部空间方面,村庄用地粗放扩张与新的功能空间短缺并存。从1990年到2016年,全国乡村人口从8.41亿人下降到5.73亿人,降低了31.87%,村庄现状用地面积却从1 140.1万hm2增加到了1 392.2万hm2,增加了22.11%[37],部分地区农村宅基地闲置、房屋废弃现象严重。同时,非农产业、公共服务、休闲娱乐和生态等新的功能需求越来越大,乡村空间正在由简单的居住、耕作组合走向居住、农业、工业、商业、旅游等多元化组合,村庄内部均衡分散化的“小聚居”体系开始瓦解[39],但与新功能相适应的空间结构仍未形成。作为经济、文化、生活、生态功能的载体和各种群体权益的载体,空间结构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色和质量,如何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作用,协调各方利益,优化空间布局,满足发展需要,是乡村空间治理的难点重点。
2.6 “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乡村发展的现实基础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其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目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明显,2020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1,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始终保持在3倍以上[40];城乡在教育培训、养老服务、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41]。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群体差异较大,202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为最低省的3.22倍,高收入群体户平均收入是低收入群体户的8.23倍[42]。县域经济薄弱、乡村产业单一、就地就业岗位短缺、生产要素沉积、乡村空心化等问题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改变。发展基础薄弱、体制机制不完善仍将是乡村发展面临的困境,推进共同富裕任务艰巨。
3 中国特色乡村发展路径探索
中国乡村振兴需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但又不能照抄照搬,必须立足国情农情乡情,走中国特色的乡村发展之路。
3.1 城乡等值化是乡村发展的前提
城乡关系及演变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标志,以城乡等值化提升乡村功能、协调城乡关系,是发达国家的重要经验。中国已经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要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等值化并不是要求城乡同质,而在于推进城乡具有同等的产业、社会、政策地位和生产、生活品质。从这个意义上,城乡等值化不是农村城市化,也不是对城市的线性追赶,而是通过充分发挥农产品保障、环境协调、社会稳定、家园价值和经济腹地等功能[43],实现乡村系统功能重组和综合价值提升,形成城乡各美其美、功能互补、空间联动、文明共享、设施均等、共生共荣的融合状态。
3.2 粮食生产与发展现代农业是乡村建设的首要任务
在人口众多、自然资源有限、工业化起步晚、城镇化相对滞后的中国,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国家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既不能照搬欧洲把农业置于旅游休闲、乡村房地产和生态环保之后的做法,又不能仿照美国大规模、机械化经营模式,也无法采取日韩依靠高补贴、高价格维持小农户高收入的策略,必须探索适合自身环境条件的发展路径。首先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贯彻大食物观,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通过保总量、保多样、保积极性,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其次是走适度规模农业现代化之路,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和农户特征,完善多种组织形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44],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通过内涵式发展方式,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增强质量效益竞争力。
3.3 二三产业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在乡村区域,单靠农业内部生产力的提高,难以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45]。基于中国现阶段农业现代化挤出大量劳动力,但又难以被城市大幅度吸收的情况,迫切需要加速乡村产业结构转型,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和乡村稳定发展。首先是壮大农业产业链,做优做强农产品加工业、物流仓储业、乡村旅游、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业效益。其次是推动非农二三产业下乡,发展生活服务、互联网创业、健康养老、文化创意、培训研学等适宜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再次是培育县域经济发展增长极,把小城镇、县级产业园区作为城镇和乡村的重要联系节点,承接大中城市产业转移,发展新型社区,推动职住平衡。同时,积极激活乡村要素,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加快改革创新,盘活农村土地,充分释放农村土地资产功能[46]。
3.4 精明收缩是乡村空间的优化策略
乡村土地整治是发达国家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针对中国村落总体衰减、村庄空心化、建设用地粗放经营等状况,乡村空间建设拟采取“精明收缩”策略,达到“总体减量、存量升级”。首先是推动村庄“精明布局”,开展乡村布局规划和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根据村庄发展基础和前景,确定村庄发展类型、发展规模和结构,促进村落的有序更新,引导形成“集镇-中心村-一般村”村庄布局。其次是推动村庄资源“精明利用”。通过村庄搬迁撤并、村内闲置土地复垦整治、居住空间置换调整等措施,将沉淀的闲置资源利用起来,用于新产业新业态新功能发展。再次是推动村庄空间“精明调整”。根据乡村发展需求,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产业空间从农业空间向多产业空间拓展,生活空间从“原住民”空间向“多元化村民”生活空间发展,生态空间向生态与景观空间复合。在空间优化的过程中,切实保护体现历史文化的宗庙、祠堂文化和生活价值空间,以及体现村民生产生活的田园、村庄肌理和聚落空间,保持乡村的“乡村性”。
3.5 乡土文化是乡村发展的社会基础
地方历史文化基因具有乡村的纵深感与独特性,是乡村的魅力所在。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乡村振兴,首先要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农耕文化,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次是筑牢农村思想道德阵地,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采取符合乡村特点的方式、方法、载体,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农村生产生活之中。同时还需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构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增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推进“三治”建设,促进乡村善治[47]。
3.6 机制政策创新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
长期以来的二元结构阻碍了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有效配置,迫切需要创新体制机制,为乡村发展提供制度支撑。首先是构建乡村区域发展政策体系,出台有关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综合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在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治理的现代化方面全方位发力,提高政策的综合性、协同性和落地性。其次是创新内生动力激活机制,破除机制障碍,引导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科技等先进要素更多地向乡村流动,实现乡村资源的效益转化。同时,需要建立健全城乡等值导向的体制机制,推动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总结提炼发达国家乡村转型发展的共同特征,立足中国乡村发展的特质,探索提出了中国特色乡村发展路径建议:
1)乡村转型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战略影响着乡村的地位和功能的发挥。当前,中国已经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进程,“三农”工作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认清乡村地位,乡村又如何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和要求,需要进一步研究。
2)发达国家的乡村现代化是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实现的,乡村转型具有坚实的外部支撑和充分的发展需求。在中国“并联式”现代化大环境下,乡村如何应对城市的虹吸效应,如何激发内生动力,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3)发达国家乡村在功能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村落转型和政策演进中呈现出诸多规律性特征,但具体做法各有不同。本文提出了中国乡村发展的总体特点和总体路径,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差异明显,还需针对不同区域乡村特点开展针对性研究,提出针对性路径措施。
4)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中,政策对乡村转型发展具有关键引导作用,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政策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如何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构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乡村发展需求相匹配的综合性乡村政策体系,仍需进一步探讨。
致谢: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辉研究员对本文的选题、思路和观点给予了全方位的建设性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1] 尼克·盖伦特,梅丽·云蒂,苏·基德,等,闫琳译. 乡村规划导论[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 胡晓亮,李红波,张小林,等. 乡村概念再认知[J]. 地理学报,2020,75(2):398-405.
Hu Xiaoliang, Li Hongbo, Zhang Xiaolin, et al. On the re-cognition of rural definition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75(2):398-40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 汤爽爽. 法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政策与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2012,33(6):104-109
[4] 姚龙,刘玉亭. 乡村发展类型与模式研究评述[J]. 南方建筑,2014(2):44-50
Yao Long, Liu Yuting. A review on the type and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J]. South Architecture,2014(2):44-50.(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5] 叶超,曹志冬. 城乡关系的自然顺序及其演变:亚当·斯密的城乡关系理论解析[J]. 经济地理,2008,28(1):79-95.
Ye Chao, Cao Zhidong. A review concerning Adam Smith's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J]. Economic Geography,2008,28(1):79-9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6] 陈诚.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乡村政策演变与乡村地方重组及其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J]. 地理科学,2020,40(4):563-571.
Chen Cheng.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state rural policy evolution, rural locality reconstitution and its uncertainty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4):563-57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7] 张俊杰, 欧阳世殊. 整合性乡村更新实践及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J]. 热带地理,2016,36(6):985-994.
Zhang Junjie,Ouyang Shishu.Integrated village renewal practic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the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Weyarn, Germany[J].Tropical Geography,2016,36(6): 985-994.(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8] 系长浩司[日],宋贝君译. 日本农村规划的历史、方法、制度、课题及展望:居民参与、景观、生态村[J].小城镇建设,2018(4):10-13.
Koji Itonaga, Translated by Song Beijun. History, methods, institutions,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of rural planning in japan: Public participation, landscape and eco-village[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18(4):10-1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9] 张立. 乡村活化:东亚乡村规划与建设的经验引荐[J]. 国际城市规划,2016,31(6):1-7.
Zhang Li.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roductions for rur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2016,31(6):1-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0] 刘志荣. 德国乡村发展的做法及启示:赴德乡村建设规划标准体系培训情况报告[J]. 农村工作通讯,2019(6):61-64.
[11] 乔婷. 发达国家和地区乡村振兴经验及借鉴[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6(6):89-97.
Qiao Ting. The experiences for refer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on[J].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Social Sciences),2020,46(6):89-9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2] 芦千文,姜长云. 乡村振兴的他山之石:美国农村政策的演变历程和趋势[J]. 农村经济,2018(9):1-8.
[13] 邹一南.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时空特征与实践逻辑[J].理论视野,2022(3):43-49.
[14] 刘守英.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J]. 经济学动态,2021(7):12-21.
Liu Shouying. The unique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1(7):12-2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5] 龙晓柏,龚建文. 英美乡村演变特征、政策及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J]. 江西社会科学,2018,38(4):216-224.
[16] 德意英农村发展考察组. 德意英三国农村发展考察及其启示[J]. 中国发展观察,2007(7):55-57.
[17] 赵文宁. 1950-2010:战后欧洲乡村发展理论与规划策略回顾[J]. 小城镇建设,2019,37(3):5-17.
Zhao Wenning. 1950-2010: The overview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strategy in post-war Europe[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19,37(3): 5-17.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8] 朱寅健. 乡村旅游:美国经验与中国借鉴[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9(2):66-73.
Zhu Yinjian. Rural Tourism: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ference for China[J].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2020,39(2): 66-7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19] 李家伟,刘贵山. 当代西方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理论、模式和假说述评[J]. 新学术,2007(5):83-86.
[20] 范冬阳,刘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乡村复兴与重构[J]. 国际城市规划,2019,34(3):87-95.
Fan Dongyang, Liu Jian. Rural renaissance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in France after World War II[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9, 34(3): 87-9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1] 黄璜,杨贵庆,菲利普·米塞尔维茨,等. “后乡村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当代德国乡村规划探索及对中国的启示[J]. 城市规划,2017,41(11):111-119.
Huang Huang, Yang Guiqing, Misselwitz Philipp, et al. Post-rural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China learn from new planning approaches in contemporary Germany[J].City Planning Review,2017,41(11):111-11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2] 周国华,戴柳燕,贺艳华,等. 论乡村多功能演化与乡村聚落转型[J]. 农业工程学报,2020,36(19):242-251.
Zhou Guohua, Dai Liuyan, He Yanhua, et al. Rural multifunctional evolution and rural settlement transformation[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0, 36(19): 242-251.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3] 张立,李雯骐,白郁欣. 应对收缩的日韩乡村社会政策与经验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22,37(3):1-9.
Zhang Li, Li Wenqi, Bai Yuxi. Rural social policies and experienc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response to rural shrinkage[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2, 37(3):1-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4] 孟广文,Hans Gebhardt. 二战以来联邦德国乡村地区的发展与演变[J]. 地理学报,2011,66(12):1644-1656.
Meng Guangwen, Hans Gebhardt. Rur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since the 1950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2011,66(12):1644-165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5] 张文明,章志敏. 资源·参与·认同: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2018(11):75-85.
Zhang Wenming, Zhang Zhimin. Resources, participation and identity: Logic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path selec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8(11): 75-85.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6] 钱玲燕,干靓,张立,等. 德国乡村的功能重构与内生型发展[J]. 国际城市规划,2020,35(5):6-13.
Qian Lingyan, Gan Liang, Zhang Li, et al. The func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Germany[J],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0, 35(5):6-13.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7] 赵民[韩],李仁熙. 韩国、日本乡村发展考察:城乡关系、困境和政策应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小城镇建设,2018(4):62-69.
Zhao Min, Lee Inhee. Evolving urban-rural development, dilemmas and policy Agendas: Lessons from Korea and Japan[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18(4):62-6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28] 杜鹰. 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下)[J]. 农村工作通讯,2020(22):17-21.
[29] 杜鹰. 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上)[J]. 农村工作通讯,2020(21):35-38.
[30] 马建堂. 迈向2035年的中国乡村[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1.
[31] 陈军亚. 家户小农:韧性国家的历史社会根基[J]. 学海,2021(1):14-20.
[32]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 2020年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
[33] 徐勇. 以农民特性为视角的田野政治学[EB/OL]. (2021-02-27)[2022-01-10],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5317.htm.
[34] 刘奇. 转型期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与结构的变化特征[J]. 中国发展观察,2007(2):23-25.
[35] 张天佐.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及发展[J]. 农村经营管理,2021(7):14-16.
[36] 姜德波,彭程.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落现象:成因及治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视角的分析[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15(1):16-24.
Jiang Debo,Peng Cheng. The phenomenon of rural declin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auses and governance—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J]. Journal of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2018,15(1):16-2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7] 中国统计局. 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20[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38] 李玉红,王皓. 中国人口空心村与实心村空间分布[J]. 中国农村经济,2020(4):124-144.
Li Yuhong, Wang Hao.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flow at the village level in China: Evidence from village samples in the third national agricultural census[J].Chinese Rural Economy,2020(4):124-14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39] 杨洁莹,张京祥,张逸群. 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治理重构:对婺源县Y村的实证观察[J]. 人文地理,2020,35(3):86-92.
Yang Jieying, Zhang Jingxiang, Zhang Yiqun. Rural space production and governance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market capital: a case study of Y village yin Wuyuan[J].Human Geography, 2020, 35(3): 86-9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0] 张琛,马彪,彭超. 工农劳动生产率趋同: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J]. 农村金融研究,2022(1):28-34.
Zhang Chen, Ma Biao, Peng Chao. Convergence of labor productivity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 important path for common prosperity of rural areas and farmers[J]. Rural Finance Research, 2022(1): 28-34.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1] 彭超,刘合光. “十四五”时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形势、问题与对策[J]. 改革,2020(2):20-29.
Peng Chao, Liu Hegua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moder niza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The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J].Reform, 2020(2):20-2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2] 马建堂. 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J]. 中国发展观察,2021(21):5-6.
[43] 申明锐,沈建法,张京祥,等. 比较视野下中国乡村认知的再辨析:当代价值与乡村复兴[J]. 人文地理,2015,30(6):53-59.
Shen Mingrui, Shen Jianfa, Zhang Jingxiang, et al. Re-understanding rural China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perception, value and renaissance of the countryside[J]. Human Geography, 2015, 30(6): 53-5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4] 魏后凯,苑鹏,芦千文.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研究的历史演变与理论创新[J]. 改革,2020(10):5-18.
Wei Houkai,Yuan Peng,Lu Qianwen.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China[J]. Reform, 2020(10):5-18.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5] 黄季焜. 乡村振兴:农村转型、结构转型和政府职能[J].农业经济问题,2020(1):4-16.
Hung Jiku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ransformation,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government’s function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0(1): 4-1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46] 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业务创新部课题组. 发达国家推动乡村发展的经验借鉴[J]. 宏观经济管理,2018(9):69-77.
[47]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乡村规划理论与实践探索[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21.
Explor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ider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Hong Renbiao, Zhang Zhongming, Li Shujun
(,,100125,)
Experience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can greatly contribute to following the law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path of r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rural areas.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was also summarized to extract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Literature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ere made in this c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develop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presented some common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functional value, economic system, settlement space, social structure,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Specifically, the functional value of the rural was generally included in three stages: from the stage of the "productivism dominated by agricultural functions" to the "post productivism with the rapidly improved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and finally to the stage of "urban and rural equivalence wit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functions". There were some changes in the rural economic system. Specifically, the industry was dominated by the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rather than agriculture. The business entities were small business owners, rather than farmers. The economic policies were focused on rural space management rather than agricultural subsidies. There was also a different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past. Social subjects were changed from the single to the collective. The social structure was changed from tightness to looseness. The social connections were changed from the closed to the open. The social values were changed from homogeneity to heterogeneity. Social management was changed from internal autonomy to external governance. Correspondingly, the overall scale of villages was reduced in terms of village changes, indicating the clustering of village layout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village types, the hierarchies of village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village spaces. More importantly, the rural policies were also keeping pace with the change of rural functions: the policy concept was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stead of the countryside serving the city; the policy content was focu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regional policies rather than single sectoral policies; the driving force wa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just exogenous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was the multi-subject synergy rather than top-dow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ural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nfers that the individual farmers were the main bod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In addition, there we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uch as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ingle rural industry, the weak county economy, shortage of local jobs, deposited production factors, and hollow villages.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food can be the primary and long-term task of rural construction, due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more people and less land. Meanwhile, there is the accelerated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ettlem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environment of “new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orryingly, there are still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to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for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omparison was made between the rur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1) The concept of urban-rural equivalence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for the rural multi-function. 2) Food security should be ensured on the road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n a moderate scale. 3) The rural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should be introduced, the small towns and industrial parks should be developed as the growth poles. 4) The rural space should be optimized with the shrewd shrinkage theo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use of land resources. 5) The local agricultural culture should be consolidated to protect, inherit, develop and utilize. 6) The mechanism and policy should be innovated to activate the rural endogenous power using a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system.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ed countries; rural transformation; China; path of r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10.11975/j.issn.1002-6819.2022.15.039
F323.211
A
1002-6819(2022)-15-0359-08
洪仁彪,张忠明,李树君. 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特征与中国特色乡村发展路径探索[J]. 农业工程学报,2022,38(15):359-366.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22.15.039 http://www.tcsae.org
Hong Renbiao, Zhang Zhongming, Li Shujun. Explor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ider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22, 38(15): 359-366.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doi:10.11975/j.issn.1002-6819.2022.15.039 http://www.tcsae.org
2022-07-06
2022-07-30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自主研发课题(CXTD-2021-01)
洪仁彪,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农村发展与规划、规划编制、农业建设项目前期等。Email:1350120177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