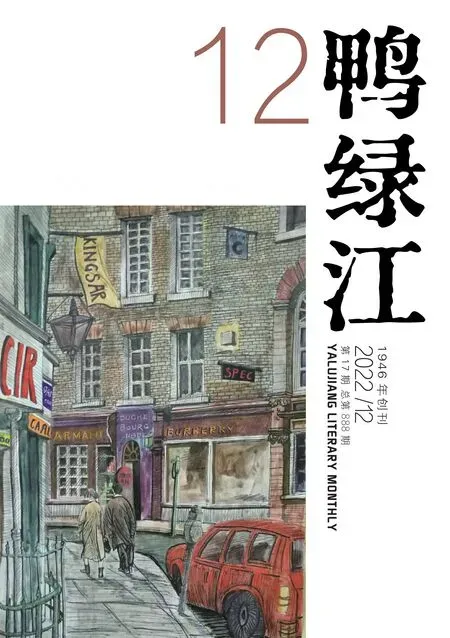纸姻缘(短篇小说)
董玉明
那是一个寒风萧瑟、满目疮痍的秋天,那是一个飞鸿鸣叫、昼短夜长的秋天,那个秋天属于在静寂与期待中默默观望的姐姐。
姐姐的床榻紧靠窗子,老旧的窗子沾着灰迹,半遮半掩的窗帘仿佛永远悬垂在那里。窗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街,几株斑驳的老榆树在街两旁兀自站立。人们在窗外闲谈说笑,在小街两旁走动停留,在霜寒露冷、落叶纷飞的叹息中遥想着即将到来的冬天。
姐姐靠着被子,苍白娇小的脸颊盛着秋日最后一抹光亮,她努力地向外张望。其实那时她已经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十多年的疾病在她体内蔓延,视网膜和眼底病变已经让她没有了一丝光感。我和母亲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默然地看着静寂中的姐姐。我忽然想起,姐夫好像快两个月没来家里了。
姐夫是一家集体企业的倒班工人,他性情随和、不善言辞,又粗又重的眉毛下是一双忧郁而清澈的眼睛。六年前,姐姐经人介绍与他相识,姐夫敦厚内向的性格和清贫破落的家境掀起了姐姐内心的波澜。
姐姐当时在一家大医院做外科护士,她生得聪慧,率真懂事,还是全系统的劳动模范。姐夫的双亲都已年过七旬,姐姐走进姐夫的内心世界,自然承担起伺候照顾二位老人的义务。
姐夫的家是一处平房,狭窄潮湿的几间砖瓦木板房里住着老少六口人。老爷子瘫痪在床,整日整夜地大睁着双眼,目光呆滞地望着剥蚀的墙板。老太太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皱纹堆累的脸深埋在厚重的烟雾中,偶尔把落寞的目光从烟雾里转出来,投向老爷子,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充斥咳嗽和呻吟声。姐夫的二哥二嫂和他们的孩子挤在另一间黑乎乎的屋子里,争吵哭闹声清晰可闻。姐夫在漆黑的过道里搭了一张板床,他在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暗淡的视线里闪动着几丝幽怨。姐姐下班以后,就会坐上公共汽车,大老远地去看望姐夫和两位老人。她的体贴和细心、温柔和开朗,使姐夫的家里充满了生活原有的情调。那些日子里,不经意的笑容常常在姐夫和他家人的脸上绽露。
姐夫偶尔也会骑上自行车,大老远地来我家。母亲就会亲自掌勺,做几道拿手的菜。父亲也会拿出珍藏的西凤酒,招呼大哥二哥和姐夫一起喝上一杯。四个人都没什么酒量,脸色一个比一个红,姐姐贴着姐夫的耳朵说话,像是叮嘱他少喝一点儿,姐夫连连点头,脸上却洋溢着沉醉般的幸福。
那一年冬天,老爷子过世了。第二年秋天,姐姐和姐夫正式登记结了婚。他们的新居就是当初老爷子老太太住的小板房。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摆放着几样木制家具,床罩、被罩、窗帘、门帘都是姐姐一针一线精心刺绣的,朴素中平添了一丝温馨。屋里最大的变化就是拆掉了原来老爷子睡过的土炕,支起了一张钢管的双人床。老太太搬到亲属家里暂住,两个人寒酸却温暖的新婚生活就这样开始了。那一年我15 岁,想想看,那真是一个让人感动的秋天啊!
寒来暑往,光阴荏苒,当我和母亲默然无语地陪着姐姐注视窗外的秋天时,姐姐与姐夫的感情生活已经走过了六年。六年里,老太太患肺心病过世了,姐夫的单位也解体了。六年里,我的父亲过世了,大哥被单位派到北方驻扎,二哥也辞职去了外地寻求发展。六年里,姐姐因病放弃了工作,母亲也从单位退了休。六年里,我已从学校毕了业,参加了工作,还交了女朋友,堂而皇之地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我不是个敏感细心的人,对姐姐和姐夫的婚姻生活可以说是茫然无知。
姐姐的病情几度加重,她白天在单位护理救助别的病人,晚上把针管药水带回家,自己给自己打点滴,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着。后来,她不怎么回姐夫那里了,婆家离医院太远,各方面的条件实在太差,万一病情发作,姐夫不在身边,恐怕就来不及了。疾病把姐姐折磨得不成样子,她浓密的头发日渐稀疏,她红润的脸颊日异苍白,她晶莹如水的眼眸越来越暗淡。她常常叨念着姐夫的名字,叨念着那个简陋寒酸的小家。姐夫隔三岔五地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看着姐姐憔悴不堪的模样,他的话就更少了。他一个人搬到外面去住,二哥二嫂索性占据了他们的房间。姐夫想与人合伙儿做点儿小生意,结果不是被人算计了吃亏上当,就是跟自己怄气一条道儿跑到黑,即使稍有盈余,也要交给二嫂贴补家用,更别说还要承担姐姐这边巨额的医药费了。姐姐几次提出离婚,姐夫只是沉默不语。姐姐不停地去医院住院,姐夫夜以继日地护理她。周围人的闲言碎语像角落里的苔藓随处滋生,姐夫英俊的面孔那段日子忽然衰老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的焦虑让我十分鄙夷。我最讨厌男人悲伤流泪的样子,对眼前这个男人充满了蔑视。姐夫来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直到有一天,姐姐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了。直到有一天,两个穿制服的陌生人送来了一纸离婚协议。
姐姐想见到姐夫,但是她没有如愿,所有的好心人这时都站了出来,仿佛他们是拯救苦难的上帝,随时准备把姐夫拯救出苦海。姐姐仍在叨念着姐夫的名字,她像所有女人那样,默默地洗衣、做饭、拖地、织毛衣,她像所有女人那样听歌、流泪、自言自语,她像所有女人那样期待着奇迹的降临,祈祷着幸福的回归。当她再次见到姐夫时,却是在法庭上。那天我没有去,我想象不出姐姐用残存的视力摸索着在判决书上签下名字的情景,我也不知道姐夫那天眼里是否噙着酸楚自责的泪花,那应该是个仓促而漫长的过程,仓促得只需在那张薄纸上写下几个字,或者按上一个指印,却漫长得要你用一生去破译领悟这现世的姻缘。
姐夫再次见到姐姐的时候,姐姐已经病入膏肓,在弥留之际。姐夫的出现让姐姐颇感欣慰,她久已不见的笑容重新绽放在脸上。她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询问姐夫的身体、工作、家庭和情感,虽然时隔一年,姐夫的生活状况仍没有转变。那些关心过他的人好像失去了耐心,那些指点迷津的人仿佛迷失了方向。春天来临的时候,33 岁的姐姐病逝了。送葬的时候,已经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姐夫,臂上缠着黑纱,手中捧着姐姐的遗像,走在家人亲属的最前面。
也许我是全家最有权利记恨姐夫的人。虽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原本来自尘土,最终也要回归尘土,但人心的冷漠,爱情的崩溃,乃至希望的破灭,无异于让人在清醒存活之时深刻地感受到死亡。想一想姐姐在病逝前遭受过的病痛折磨,那肌体上的疼痛,那黑暗中的孤独,那情感上的空寂,也许生命的终结对这个蒙受苦难的女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当姐姐摸着我的耳朵轻轻说:“小弟,别怪你姐夫,是我对不起他。”我忽然明白了,这世间原本有两种婚姻:一种是纸做的,人人看得见,它常常用在各种社会交往中,容易得到,也极易丢失;一种是用心做的,只要你常常用心血去浇灌,用泪水去呵护,那你就永远不会失去它。你睡着了,它会把你疼醒;你死去了,它会把你复活;你陨灭了,它会让你永生!
姐姐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好像在不断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真爱,虽然我仍是独身一人,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求。姐姐和姐夫彩色的婚纱照就放在我的书柜里,我隐约从别人那里打听到姐夫的消息。他似乎仍在与别人做生意,但是没有成功。他似乎新交了女友,但是也没有结婚。他似乎经常一个人去喝酒,听说几年前在吃饭时与人发生口角,用酒瓶给人脸划伤了,造成了轻伤害。他似乎进了劳教所,出来后又转而去了南方,大概已组成了新家庭吧。
在这个落叶满天的季节,回忆这些陈年往事,也许只是为了祭奠一下音容依稀的姐姐。各式各样的爱情故事还在人间上演,我伫立窗前,努力向外张望,冰凉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轻轻滑落。我痛恨自己这样,我痛恨所有的男人这样,但我控制不住。幸而我所爱的人只在梦中出现,她还不会增添我对现世的困惑。我该用我的语言我的诗篇告慰姐姐呢,还是用我未泯的理想和信念去装点自己的行程?我看见最大的一枚叶子缓缓地从天空坠落,悄无声息。我止住空想,深情地向它瞩望,那是姐姐不死的灵魂,她正倾听我的内心,用斑斓绚烂轻轻回答着我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