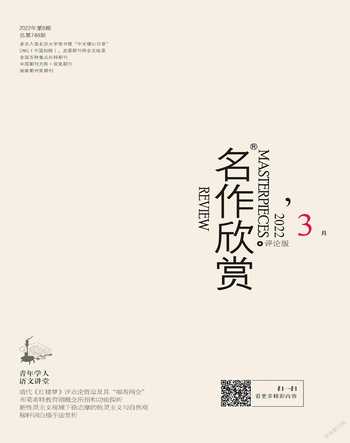承认黑暗,向光向善
苏家璇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两个插曲的内容,指出作品塑造的世界中存在自我身份认同危机和真实与虚构间界限不清的问题。同时,本文结合后人类主义的观点,认为这两个插曲指向了人性中矛盾的方面,提出珍惜并不吝啬于颂扬人的光明,了解并不怕承认人的幽暗,或许是我们避免最终走向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社会的出路之一。
关键词:《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菲利普·K·迪克 人性
菲利普·K·迪克是美国科幻小说家,一生共出版四十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二十一篇短篇小说。迪克的作品集中探讨“个体身份建构”与“何为真实”的问题,充满了对人性的思考与追求。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创作于1967年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是最负盛名的一部。
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人类为躲避核战带来的辐射而移民火星,只有极少数人留在了地球。火星上每个人类都自动拥有一个仿生人。然而,一些不想再被奴役的仿生人会杀掉主人逃到地球。政府为了不引起恐慌和推进移民顺利进行,在地球警局安排了一批专门追捕仿生人的赏金猎人。故事便围绕赏金猎人里克·德卡德如何在一天内追捕仿生人而展开。在追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插曲,这两个插曲的意义,可以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思路。
一、一场追捕——难以处理的自我认同危机
在德卡德的追捕过程中,他的人类身份在仿生人鲁芭的质疑下受到挑战。鲁芭针对德卡德提出的仿生人不在乎其他仿生人死活的说法,表示猎杀仿生人的德卡德正是一个仿生人。但这站不住脚,因为作品中辨别仿生人的方式是“移情测试”:仿生人难以理解人类对他人和动物产生的移情,只能进行伪装,但机器和技术可以甄别。于是,鲁芭询问德卡德是否做过移情测试,德卡德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可鲁芭提出,或许那是植入的假记忆。德卡德反驳说他的上司也知道测试结果,鲁芭又说:“或许曾经有个跟你一样的真人,后来某个时候你杀了他,取而代之,而你的上司并不知情。”
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插曲,它提出一种可能性,即被默认是人类的德卡德其实是一个仿生人。作品中,伪装成警察的仿生人加兰德将德卡德带到了另一个执法部,这里的布局、办案流程与他熟知的警察机构几乎没有差别。但这个执法部其实是仿生人伪造的,里面的视频电话线路通不出去,他们运营着一个内部完全静止守恒的单位。同时,加兰德还在德卡德与另一名赏金猎人菲尔·雷施之间埋下了怀疑的种子,让二人通过测试才确认了彼此的人类身份。
虽然最后德卡德的身份没有发生反转,但鲁芭的两个“或许”不止让故事更有波澜,而且指向了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人是什么?科学将人类这一物种命名为智人(Homo sapiens)。在哲学领域,苏格拉底认为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康德说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做出这些结论时人类身体与机器之间的界限还比较清晰。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这一界限逐渐被模糊。例如,英国女孩蒂莉幼时失去了部分小臂,在仿生手臂的帮助下,她可以通过肌肉来控制仿生手指的伸缩,并成了一名美妆博主。就算她安装了仿生义肢,也不会有人以此为由认为她不再是人。但书中对于人的定义却有所不同,如果一个人的遗传基因被辐射污染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不能再算作是人类。这个论断隐含的内容是,基因被污染前,或者将时间轴拉向更早,在出生之时,他还是一个人。因此,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单就出生时的状态而言,暂且不论日后身体和基因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人的一个特点是由胚胎发育而成,并经历了生育这一过程。而仿生人(androids)是一种人型自动机器,它拥有表面上的“血肉之躯”,假设砍掉仿生人的一只胳膊,露出的不是电子元件或精密电路,而是“血肉”和“骨头”。但是,仿生人其实是由生物材料制成的,对它来说并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发育与出生。这就是传统的人与仿生人在身体构造上的不同。
就作品而言,起初,外表可以区分人和仿生人,但当仿生人不断更新升级,甚至拥有更完美的身体时,从生物学角度出发,依靠外表和身体来定义人就不再是可能。那么记忆可以吗?美国心理学家罗芙托斯指出:“随着时间逝去,在适当的驱动下,或在引进干扰或冲突的情境片段时,记忆的线索会改变,而且我们一般而言是意识不到这改变的。于是我们便开始真正相信自己对于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忆。”这说明人的记忆是可篡改的、不可靠的;而记忆植入在作品中已是现实,被植入记忆的仿生人毫不怀疑自己的记忆,也从不质疑自己的身份。作品中的仿生人蕾切尔就是如此。因此记忆也可以是虚假的、被捏造的,也不能定义人。那么外部的确认与他人的认同是依据么?也不是,就像那个封闭的执法部一样,即使得到了他人的承认,仍不能说明“我”正是他人眼中的“我”。
德卡德对仿生人逐渐改变的态度也体现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起初,他猎杀仿生人时毫不愧疚,在他看来仿生人只是冷血的杀手,但他逐渐对女性仿生人产生了移情,在情感上更偏向鲁芭而不是冷血的雷施,并且想要辞职;在德卡德与蕾切尔发生关系后,他对蕾切尔说:“法律上,你没有生命。但其实你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你不是由半导体线路搭起来的,跟那些假动物不一样。你是一个有机的实体。”这意味著他对女性仿生人的移情已经完成。虽然最后德卡德完成了猎杀任务,但他也陷入了困境,他认为关于他的一切都变得不自然了。他变成了一个非自然的自己,赏金猎人是他的职业,可现在他却因移情对象的扩大化而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质疑,进而动摇了已经建构的自我身份。最后他变成了默瑟本人,因为于默瑟而言没有什么是陌生的,默瑟接受一切。也就是说,德卡德完成了自身身份的重建,并扩大了生命认同的边界。此刻的他认为电子宠物也拥有微弱的生命。
德卡德人类身份受到的质疑、他自己对于“生命”边界的扩大,都体现出在仿生人存在的世界里,自我认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我们可以在德卡德身份认同的动摇与重建的过程中,看到迪克对于个体身份建构的思考。
二、一个骗局——被打破的真实和虚构的界限
在高科技低生活的世界,唯一将人类互联成为人类精神支柱的就是默瑟主义和共鸣箱(empathy box)。共鸣箱只提供一个场景:荒芜的山坡、干瘦的野草、灰暗的天空和独自攀登的老人威尔伯·默瑟。通过双手握住共鸣箱的手柄,人可以完全沉浸于虚拟的场景中,并成为正在攀登的默瑟,和默瑟达成肉体、意识与精神的合一,这在书中被称为“默瑟融合”。融合后不止能具有身体感觉,还可以感知到同一时刻所有握住手柄的人的思绪。然后所有人,或者说所有人复合成的默瑟会开始攀登。
在攀登过程中,会有敌人投来石块造成疼痛和伤害,但由于能得知所有人都遭受了同样的折磨,孤独的假象会被众人的嘈杂打破。意识到并非只有自己在受苦,攀登者才能继续攀登。到达山顶后,他将沉入坟墓世界,等这里的生灵由断骨会合成新生命后,他才能和生灵一起上升,重新开始西西弗斯式的攀登。
默瑟主义就得名于攀登者默瑟,它是基于人类的泛同情心而建立的一种宗教,并通过共鸣箱体现和被感知,不断循环的攀登就是默瑟主义的主旨,“是你身体的延伸,是你接触其他人类的途径,是你摆脱孤独的方式”。进一步说,默瑟主义通过攀登这个过程,让人们产生融合感,强调大家的情感体验,通过感同身受来加强共鸣。它的实质是人类群体的同理心,是人从自身之外得到的情绪安抚的抽象集合体。这种同理心也被扩大化,使人也能对动物移情。
然而,仿生人却揭露了默瑟主义是个骗局:默瑟是演员扮演的、天空是画上去的、山坡是在影棚搭建的、石头是胶皮塑料的、默瑟根本不痛苦。这是书中另一个重要的插曲。日益荒芜空虚的世界导致人类在生活中情感缺失,需要情绪调节器来调节情感,所以共鸣箱和默瑟主义便成为人类的精神寄托。仿生人本以为,骗局被揭露之后,当人类意识到将他们合为一体的默瑟并不存在时,会造成信仰崩塌的恐慌,可事实上什么都没有改变。智力低下的特障人伊西多尔仍然能够握住共鸣箱的手柄见到默瑟。
默瑟说,伊西多尔看不到这一切,是因为他离得太近、太过投入了;而仿生人离得太远、太过理性了,他们虽然能看出这一切都是假的,却不理解为什么没有变化,这正是感性打败了理性的证明。同样的,曾有人在融合中因剧烈的折磨死去,但不曾有人放弃融合。即使知道存在着死亡的风险,为了体验融合和寻找共鸣,人们还是会选择承受痛苦。
默瑟主义的确是个骗局。吉尔·加尔文在《进人后人类集体》中指出,默瑟主义和共鸣箱是在日益恶化的环境中为保证人民安分守己、便于驾驭而被制造出的工具,它通过伪造的场景和宗教的形式来维护稳定。它是一种悖论:握住手柄时人既是孤独的又是有人陪伴的;这里的场景是虚假的,但体验又是真正有意义的以及真实发生过的。在这种悖论中,情感的真实超越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真实,感性的作用被无限放大,理性反而被忽略了。
事实上,当作品中的人的本质特征从理性转向感性时,就已经暗示了人们并不需要默瑟真实存在。事物本身的真假失去了意义,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愿意相信。人们选择相信同生为人的相似性和悲悯心,选择移情来感同身受,选择共情来抵抗孤独,那默瑟主义就不会改变。这种把孤岛连成大陆的过程,就是在荒芜世界里人们找到的精神支撑。
三、两个插曲的意义
自《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之后,后世的赛博朋克作品在人机关系之间做出了更大胆的假设和描绘,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在1984年完成的小说《神经漫游者》。在这部作品中,人类已经可以实现人体克隆、身体与基因改造、芯片植入,还能将意识连接到电脑上,让意识脱离肉体在网络中漫游。人与机器的关系就从“人支配机器”变成了“人机共存”,产生了超越人类原有身体机能的“后人类”。后人类的主题是人类与智能机器的结合,这与控制论(cybernetics)密切相关。
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中看到控制论中对反身性(reflexivity)的注重。凯瑟琳·海勒认为,反身性就是一种运动,经由这种运动,曾经被用来生成某个系统的东西,从一个变换的角度,被变成它所激发的那个系统的一部分。即根源最终被证明成为结果,或是成为结果的一部分。她以博尔赫斯的《环形废墟》为例,魔法师通过做梦创造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最终证明了魔法师也是他人梦境中的“另一个少年”。这也体现出反身性趋于无限倒退的特点:少年被魔法师梦到,魔法师又被他人梦到,就这样不断地后退。同时,反身性意味着原先被认为源于一系列条件的某种属性,实际上被用来生成条件。结果也可以成为原因,并且永远找不到真正的根源。
反身性在作品中的表现是德卡德成为默瑟。默瑟先于德卡德存在,并通过默瑟主义塑造了原本的德卡德,而德卡德不依靠共鸣箱就变成了默瑟,他只能等待分开。依靠那只他眼里的“真”蛤蟆,德卡德脱离了默瑟,打断了无限倒退的过程,电子宠物微弱的生命将他从融合中拽了出来。结尾,他回家后不需要情绪调节器便陷人沉睡,得到了机器才能提供的安宁。
海勒对这种转变与结局做出结论:当人类对创造物——不管是生物的还是机械的——表现出容忍和关爱,与它们共享这个星球的时候,就会处于自己最佳的状态。这体现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观点:除了探讨人机关系外,受解构主义与其他后现代理论的启发,后人类主义推翻人文主义将人作为万物尺度的“人类中心论”,不再将人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消解了人与其他物种及自然本身的二元对立。
由此再看作品中的两个插曲:自我认同的危机因仿生人而产生,默瑟主义的骗局因仿生人而被揭露。前者让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后者让人对自己的信仰甚至周遭世界产生怀疑,两者呈现出递进关系,容易导致虚无主义。
然而,仿生人并没有对人类生存和延续造成伤害:移情成了人的本质特征,所以德卡德最终确认了自己的人类身份,并扩大了生命认同的边界,默瑟主义也没有消失。作品之外,这两个插曲可以理解为人性中矛盾部分的斗争,人性是拥有无数可能性的灰色地带,仿生人过于理性、缺失移情能力,象征着人性中的冷漠与歧视;共鸣箱和默瑟主义的背后是人类没有摒弃的同理心与怜悯心,象征着人性深处的向光本能。卢梭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他认为怜悯心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美德,通过它,人可以克制只为保存自己的自爱心,进而有助于所有人类的互相保存。怜悯心早于理性存在,是天生的,因而可以称其为一种本能。当冷漠与歧视发起冲击时,作品抓住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用情感共鸣和移情来抵御,在与他人的联结中寻找情感慰藉,并以此作为自己人类身份的证明。虽然作品中的移情测试不曾出错,但我们不禁思考,如果有一天科技可以让仿生人也能移情,那我们该如何分辨仿生人?
作品中仿生人与人类如何相处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个体身份建构与何为真实的问题也存在于当今社会中。尽管现在的世界还没有发展到微尘满天、情感缺失的程度,但未来的走向是未知的,倘若无法移情的仿生人就是人类的归宿呢?既然自爱心只为保存自己,而怜悯心能使人类互相保存,那么珍惜并不吝啬于颂扬人的光明,了解并不怕承认人的幽暗,就像海勒说的,容忍、关爱和共享,或许是我们避免最终走向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社会的出路之一。
参考文献:
[1]菲利普·K·迪克.仿生人會梦见电子羊吗?[M].许东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2]伊丽莎白·罗芙托斯,凯萨琳·柯茜.辩方证人:一个心理学家的法庭故事[M].浩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3]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M].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纪晓桐.菲利普·迪克科幻小说中的后人类身份问题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20.
[6]冉聃.赛博与后人类主义[D].南京大学,2013.
[7]王启名.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身份重构[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19.
[8]王宁.“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走向后人文主义[J]. 文艺理论研究,2013,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