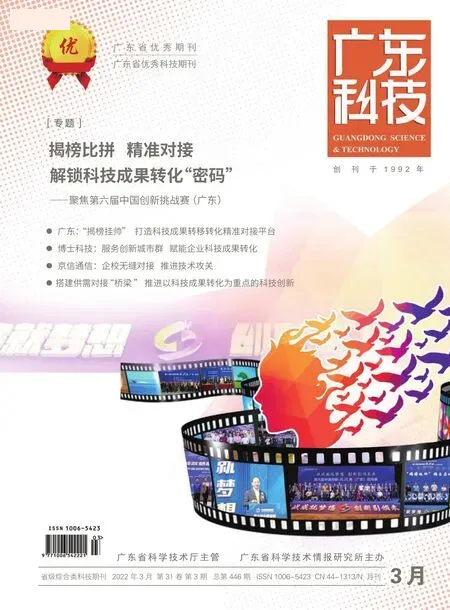大数据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模式与对策研究*
文/吴亚榕 梁健铭 唐家豪
0 引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城市和乡村建设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城乡差距仍然存在,且有拉大的趋势,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短板问题日益凸显。自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我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如在人均收入上,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9年达到了16020.7元,人均消费支出达到了13327.7元。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加速演进,传统粗放、松散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快步转变为高品质、高效率、高集约、专业化的生产形式。这些变化要求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必须具备更高的素质、掌握更复杂的技能。一般我们把以农业生产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称为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领域中的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创新“三农”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和培养现代化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已经成为当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超过2000万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市场规模突破了千亿元。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出现“新型职业农民”一词,提出重点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培养;2017年,原农业部出台《“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助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2021年,广东省政府出台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培养“精勤农民”,全力打造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出,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推动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也是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的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在各个行业当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范永艳从课程设计和教师队伍的建设探讨了大数据时代下电子商务教育模式的转变策略;胡霞提出了数据化教育管理和个性化人才培养等将是大数据背景下高等教育创新的必然趋势和路径归属。这些都说明了,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普及为传统教育培训模式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引领了新的方向。
从当前已有的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方面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已经开展了大量详实的研究如蔡云凤等总结了北美、西欧、东亚三种较典型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模式,并提出了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的优化措施;吕莉敏针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主要供给侧的农村职业教育存在培育目标不明、资源分散、保障不力、内容不实、形式不活等问题,提出了明确培育对象、改革内容与方法、创新培育模式等建议。不少学者也开始研究大数据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如胡寒松等认为大数据技术在新兴职业农民培养中的应用可以实现培训资源的共享,改善不同地区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象;柴沙沙认为大数据将有助于更新培训新职业农民的方法。
基于以上研究的梳理,本文将以广东省培育新型农民教育模式为例,在充分分析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大数据技术在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中的优势,进一步创新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模式,为大数据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提出发展建议和对策。
1 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现状及存在问题
1.1 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现状
近年来,广东省大力推行“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建设。截至2019年,广东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了7175.89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8818元,农产品产量、进出口贸易总额等指标都在持续增长,共建立了184个省、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拥有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1009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1778家、示范家庭农场180家。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迅速、农业农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从培训开展条件来看,农业高等院校的建设一直是“三农”领域中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农村面临空心化、人才紧缺的大环境下,农业高等院校毕业生成为了新型职业农民的主力军。近十年来,广东高度重视高等农业教育,农业高等院校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稳定上升,其中,2019年农业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数提升幅度最大,达到了24.6%(见表1)。

表1 广东省农业高等院校招生和毕业生数量
从培训开展情况来看,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平台和主体规模较大,具备较强的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供给能力。2018年,广东省公布了265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对相关从业人员开展培训活动,至今累计培训新型职业农民600余万人次,有力促进了农民技能水平的提升。在农村科普活动主体建设方面,自2016年起,广东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数量和会员数量、农村科普示范基地数量等指标都有持续下降的趋势。截至2019年,广东省共有农村专业技术协会799个,较上年减少17.03%,会员人数为71875人,较上年减少33.75%,建立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共554个,较上年减少13.98%,三项指标均有明显的下降(见表2)。在农业高等教育、农民培训等投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农村科普活动开展的条件情况却没有变好,说明农村高素质人才外流的现象比较严重,这对于今后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形成了一定阻碍。

表2 广东省农村科普活动主体建设情况
1.2 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存在问题
一是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实际参与率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高速发展对新型职业农民的高需求。一方面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农业技术也在不断革新,在政策引导下,政府、社会机构、企业等多方主体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另一方面,农民虽然意识到学习新技术能够带来更多致富的机会,但由于农民本身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低,在考虑到成本效益、学习难度等多方面情况下,大部分农民实际参与技能教育培训的意愿较低。如耿丽敏等在河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参训意愿的调查中就指出,接近80%的农民具有参训的意愿,但仅有不到10%的农民实际参加过培训。因此,尽管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供给主体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如果不解决农民参与培训动力不足的问题,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就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二是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内容较为单一,缺乏针对性。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的课程体系设置通常遵循理论、管理、实操三个环节,以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例如,2018年,台山市农业农村局在佛山举办的2018年度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采用“集中授课+现场讲解+观摩实训”的方式进行;2019年江门市蓬江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主办的蓬江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训班,课程设置共分为高校教学、电商教学以及农业实训教学三个模块。从近年来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来看,举办形式基本都是以集中培训为主。然而,由于各个地区的参训人员实际的文化层次、经营种类、产业规模等有较大差异,对培训课程内容的接受能力也不一致,采用集中式的大班授课方式,缺乏对参训主体的针对性,培训效果较差。农民参与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也会影响其参与培训的积极性,造成培训资源的浪费。
2 大数据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模式选择
2.1 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模式
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模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以政府直接主导的培训模式,即由地方政府、教育、农业等相关部门对农民、农业从业人员等开展的技能培训等。广东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联合高等学校、科研支撑机构等资源,开展了大量的高层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充分发挥“头雁效应”。例如2021年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与华南农业大学联合,针对农机技术人员举办了农机使用专家培训班,充分发挥高层次新型职业农民的示范带动作用;惠州市农业农村局针对荔枝种植加工户、农机技术人员等举办了农机安全暨农机化人才培训班,促进农机化科技创新与推广;广州市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从业人员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培训,并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技能竞赛,既提升了培训参与者的技术水平,也促进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创新。另一种是由社会组织、团体、企业等社会力量主导的培训模式,如信宜市农机服务中心组织农技专家开展了十期农机技术培训,帮助当地农民学习和了解农机作业的新技术。
2.2 大数据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的机遇
2.2.1 大数据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形式的转变
当前,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实际参与率并不理想,很大一方面是由于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没有能够很好地响应农民、农业从业人员等受训主体的需求,培训的开展缺乏针对性。基于大数据相关技术在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中的应用,可以实现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从“端菜式”培训到“点菜式”培训的转变,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培训供给主体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快速准确地掌握农民的文化水平、生产状况、经济水平、产业布局等信息,通过准确的分析和预测,可以揭示出以往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过程中存在的不合理的地方,为下一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提供更准确的参考方案。
2.2.2 大数据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内容的转变
一是通过利用大数据手段,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大数据信息平台,一方面可以根据农民的文化水平、生产状况、经济水平、产业布局等信息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数据库,方便培训主体能够有针对性地选取培训对象,进而根据培训对象的信息设定培训内容,使培训的开展更具有针对性。另一方面,利用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大数据信息平台,可以实现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培训专家与培训对象进行在线授课和讲解,从而节省了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的时间、资金、场地成本。
二是通过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大数据平台资源库,更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管理。将不同区域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信息整合至大数据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对后续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工作和相关技能考核的实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三是利用大数据手段对培训对象进行长期的跟踪指导,能确保培训成效。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不是简单的一次讲座,而是需要定期进行跟踪反馈的长期性的工作。利用大数据手段,培训主体可以及时将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的开展情况录入数据库,建立新型职业农民个人培训档案,以便于对培训对象进行长期培训指导,从而增强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的有效性。
2.2.3 大数据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模式的转变
当前,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模式主要分为以政府牵头的培训模式和以社会组织、团体、企业等社会力量主导的培训模式两种,由于针对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信息缺乏统一的平台进行管理,相互之间不能够有效实现公共数据等资源的共享,各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屏障。因此,利用大数据的手段打造政府、社会团体和企业各个主体之间互通的信息共享平台,有利于将社会团体和企业等主体所掌握的地区农业发展现状、农民结构和特征、技术需求等具体信息与政府进行资源共享,形成以政府为主,社会团体、组织、企业等其他主体为辅的多方合作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
3 大数据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发展对策
3.1 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基础化建设,提高农民培训参与意愿
推进大数据技术在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中的应用,远程教育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是重要前提。一要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等移动设施的普及,努力扩大农村地区互联网的覆盖范围;二要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线上远程教育,鼓励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专家、讲师使用直播、录播等远程教育方式,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师资力量分配不均等问题;三要注重提高农民综合文化素质,大力宣传和鼓励更多人才反向就业,加强农业经营管理方法模式和农业技术推广,不断提升职业农民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能力。
3.2 加大投入力度,利用大数据手段优化调整培训内容
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依据不同区域的产业分布,依托大数据技术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平台和培训基地。进一步加强人才投入力度,积极组织专业技术人才组成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大数据研发团队,积极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不断降低大数据技术在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中的应用门槛。另一方面,大力支持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数据库,根据培训反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对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对象进行周期性的培训服务跟踪。
3.3 建立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数据管理体系
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主体在需求信息采集过程中,需要采集大量的新型职业农民的个人信息,这必将带来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数据管理体系来对数据使用进行规范,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培训对象的个人信息。
4 结语
本文基于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的条件、投入、开展情况等现状,深入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大数据技术在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中应用的优势,进一步探讨了大数据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发展的对策。研究表明,当前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开展条件和培训投入情况较好,但也存在培训实际参与率低、培训内容单一等问题。合理利用大数据技术将有利于转变和创新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的培训形式、培训内容和培训模式,提高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的效果。最后,本文从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基础化建设、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完备的数据管理体系等三方面提出大数据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技能教育培训发展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