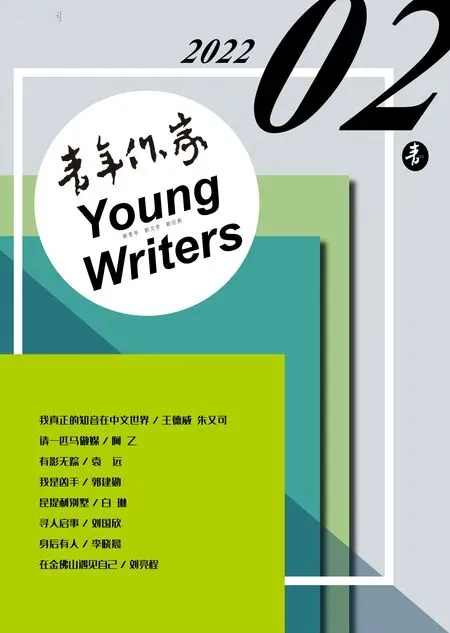树 洞
许桂林
大家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莫非,大家发现我爱上了那个瘦弱的男人?
他常常坐在小区斜对面的公园,或者发呆,或者读一本薄薄的诗集。一副瘦弱得能被风吹起的模样,大概是过去的三十年,他都吃不饱吧!像我们这样的富人小区,怎么会有被饿瘦的人呢?这是一个值得我思考的问题。我坐在自家落地窗前,看着树底下的他。我这么想着的时候,他刚好,推了推往下滑的黑色眼镜,仿佛在思考的人是他。
我得看看,这副眼镜背后的眼睛。
今晚没有月光,可惜了,要是有月光就好了,黑眼镜就会到树下读那本快要被他翻烂的诗集了。我喝着一杯红茶,透过窗户,看着他。
他就那样坐着,捧着那本诗集,并没有读,却流泪了。
我更好奇了,一个大男人,干嘛在树下哭啊?
单身多年的我,浑身上下都觉得忧伤,但是很快又被自己否定了。我拿出手机,把他哭的样子录了下来。晚上,躺着,反复看那个视频,总觉得这个男人像谁,又说不出来。
每天清早,我到对面公园跑步,都看到他坐在树下,手里还是拿着那本破旧的诗集。大概过了一个月吧,夕阳从橘红到橘黄,季节从夏天到秋天,他总那样看着斜阳,莫不是在吟诵声声慢?还是临江仙?
我天天跑步路过,他也不看我一眼。虽然我看了他那么多眼。然而,每次我将要跑回家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目送我。
出版社的工作,实在是繁忙,恰好我负责新一年的选题工作,我慢慢地忘记了他。面对众多的选题,我也十分纠结,看看这个选题不错,那个选题也不错,但是不自觉地,总会偏向诗歌或者诗论方向,在电脑前迟迟没有敲定方案,突然想起他手里常常拿一本诗集,想起这个人来。离开电脑,我走到窗前,不知道黑眼镜在不在树下?不在。他真的不在。“把工作放一放吧,过几天再思考。”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就喝起红酒来。
临近傍晚,我到小区的花园里散步,意外地发现他跟一个同样很瘦的女人在谈话,女人化了精致的妆,我看不出她的气色,黑色的长发比瀑布还要好看,只见瘦女人递给他一部手机,不是苹果手机,也不是华为手机,明显是老人机,叫不出名字。瀑布走了,我也转身要走。
他叫了我,说嗨。我说嗨,好久不见。
他也说好久不见。
“刚才那个长发美女是你朋友呀?”
“不是。”
“感觉像快递员,送了东西就走。”我笑了笑。
“那就是吧!”
“你常常都坐在这棵树下吗?”
“是呢!”
“拿的是谁的诗集呀?”
他沉默。
我再想说点什么,他转身要走了。初秋的风,吹着他单薄的身子,仿佛一根细小的排骨,在萧瑟中荡漾。我借着散步,不知不觉,跟在后面,想看看他住哪一栋——我们小区有一百栋房子。我悄悄尾随着他。
他七拐八拐,走到53栋门前,并没有进去。我感到奇怪,干嘛不回家呢?他只是路过。我却发现,53栋前面的那棵枫树有点熟悉。小区太大了,我都还没有离开过自己住的28栋,我怎么感觉自己见过这棵枫树呢?我再次问自己。
一抬头,他已经走远了,我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去,像电影中的间谍。
他最终停在100栋门前,输入密码,门,开了。我刚要走,他突然转身,两只深陷的眼睛看着我,灼灼直射,把我吓了一跳。
他轻声说:“跟了这么久,到家里坐一会儿吧!”诚恳得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我犹豫着,这孤男寡女的,怎么能共处一室呢!他伸过来一只瘦弱的左手,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单元门、电梯门、房门。
这是一套复式楼。如果用“富丽堂皇”来形容,可能就俗气了——豪华之中,满是文学气息。跟我家寸草未生的荒芜相比,我服气。
“你坐。”
他只说了两个字,很轻很轻。
“哦,坐哪儿?”我没有找到凳子、椅子、沙发,整个大厅只有书柜和床。
“坐床上。”
他说了三个字,很轻很轻。
看着整齐的床,再看看刚刚跑步结束,浑身上下都是汗水的自己,我不吭声。到别人家里,也不能坐床上啊!
他把手上的那本旧诗集放在床头,床头上放着几部老人手机。他领着我走上楼。楼梯是干净的,像是一直有人打扫,但没有看见家里有阿姨。
是间书房,房里竟然养了一棵枫树,有几片叶子正在变红,过几天,应该就全红了吧。
“你坐。”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只说两三个字?这没有地方坐啊?”同样是书柜和床,只是这个书柜比楼下那个书柜大很多,我表现出了无奈和不解。
“你以前都喜欢坐在地上。”他看了我一眼,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黑色封面的诗集。
“嗯?你以前认识我?”此时我已经盘着腿坐在地上,他家的卡其色地毯很柔软。
他从床上缓缓地起身。打开书柜。“啊!”我的尖叫声没有把他吓到。一个坐在树洞里、长得跟我一样的女人!
我定定神,细看,不是活人,是蜡像。
“这是什么?”我的声音在颤抖。
“是这本诗集的作者。”他递给我那本黑色封面的诗集。
我看了看,我不认识这个诗人,而且这本诗集没有书号。我把诗集递回去给他,脑海里闪过的不仅是问号,还有心慌。
“这个是你的双胞胎姐姐,她和你一样,喜欢坐在地上写诗。”他说得很轻很轻,“她喜欢枫叶,喜欢……”“你骗人!”我打断他,“我是个孤儿,没有兄弟姐妹!”
他伸出手来,不知道是不是想要抱住我,我本能地往后退,往后退。他逼近我,我一下子慌了神,倒在床上。他双手撑着床,直直地看着我,几乎是脸贴着脸,“你们长得太像了。”他轻轻地说。我挣扎着起身,被他一把搂在怀里。这是三十年来,第一次有个男人把我搂在怀里,我竟然放弃了挣扎,安静得像一只刚被收养的流浪猫。我歪着脑袋,用眼角偷偷地看他,那张瘦弱的脸上流着两行清晰的泪水。我伸出右手,擦干那些泪水。
我在他怀里,听他说关于我的、我却不知道的故事。关于那个双胞胎姐姐,我确实不知道。
我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小学六年级辍学,开始写诗,诗歌创作已经二十年,因为一直用笔名,所以诗集再畅销,除了圈内的人,身边的其他人,没人知道我是个诗人,我也不参加任何诗歌分享会。版税加上出版社的工资,足够我在上海这个大城市的中心,拥有一套临江的大房子。
在我们小区,怎么会有人知道我是个诗人呢?
这么思考着的时候,他温热的吻就落在我的额头上。这一切都来得太梦幻了。我拒绝了。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指说:“你和她一样,喜欢坐在地上写诗,从早晨到黄昏。”他望向日出的侧脸,没有弧度,却写满了怀念和忧伤,以至于我有一点相信,我可能真的有个姐姐。
“她死了。”他把脸转过来,“在那个遥远的黄昏。”
我松开他的手,冲下楼,到了大厅,发现出门也要输密码,身后传来他的声音:是你们的生日。我输入我的生日,门,果然开了。我回头,抬起眼皮,看着一脸淡定的他,他没有说什么,我也没有说什么。
带着许多疑问,我回到了28栋,说来也奇怪,大白天的,一路上也没有遇到小区里的人。拉上阳台的窗帘,躺在地毯上,我拿出手机,想要报警。
但是我报警说些什么呢?
他并没有非礼我,我也不想因此多一个已经死去的姐姐,孤儿院在二十年前就拆了,院长也去世了,在孤独这条道路上,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是的,我只要回归今天早上跑步之前的生活即可。
我脱光了衣服,到浴室泡澡。在镜子前,有一丝丝不舍得洗脸的念头,因为额头上还留着若隐若现的吻痕——那是我打娘胎出来的第一个吻,当然,除了院长妈妈的收留之吻。
洗澡之后,喝了一点牛奶,我开始新的一天写作。
睡了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临近傍晚。眼前不断地出现他的样子,他说的那句“在遥远的黄昏”,是一句多好的诗啊!我在心里反复地读着这句诗。不禁又想起了坐在树洞里的女人,那个蜡像做得太逼真了,我一度觉得是自己灵魂出窍。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内心不知道在挣扎些什么,我自己也搞不懂,吃了一片安眠药,我睡过去了。
第二天醒来,在窗前,我习惯性地看向小区对面的公园,树下,没有任何人。我想,应该是他还没有去吧!也许过一会儿就去了。我照例穿好运动服,去晨跑。
跑了一圈,第一次路过树下,他没有来。跑了第二圈,第二次路过树下,他还是没有来。半个小时,五公里结束后,他还是没有来。我心里竟然有一点想见到他。是一种单纯地想见一见的想,不说话,看见就好。然而,他始终没有出现。我回到家,洗澡,吃早餐,开始一天的写作。
写了一组诗,我停下打字的手,找了个借口——给窗前的绿萝浇水,顺便可以望向对面的公园,望向路过树下的行人。没有看见他。
又到了黄昏,我在键盘上敲下一行字:你此刻,在哪个遥远的黄昏?
我赶紧删掉,脸,一下子红了。
太阳,都想休息了,我也休息吧!关了电脑,换了套红色的丝绒睡衣,我就窝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了。像许多剧情一样,这时,门铃响起来了。
我惊喜地睁开眼睛,不顾身上穿着睡衣,就跑过去开门,很遗憾,不是他,而是一个推销诗集的胖胖的男人,场景仿佛几年前很火的小说《推销员》当中的情节。我随手从门边的鞋柜上拿出一百元。
“买一本!”我说。
“一百元五本。”他补充道。
“可是我只想买一本。”我已经开始不耐烦。
“五本都是不一样的呢!”他摊开手上的诗集。
“不要。”
“这些诗集好得像晚霞。”
我看了一眼窗外,是呢,晚霞好看得很。为了结束这无聊的对话,我同意了。
把门关上。我还睡眼蒙眬的,想着继续睡。随手把那五本诗集丢在沙发上。手机响了一下,看见是陌生人发来的信息:
翻开诗集,保持冷静。
好奇心驱使我翻开那些诗集。五本诗集无一例外都是黑色的封面,打开一看,全是我的作品,每一首诗都配了一幅插图,我有一点不冷静了,因为有一些是我写的,并没有发表,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快速地回复:你是谁?
短信很快回复:昨天吻你的人。
我套一件外套,便奔向100栋。在密码锁上,熟练地按下密码,我记得,他说密码是我的生日。
大厅里,他正安静地坐在卡其色的地毯上。那张瘦瘦的却十分好看的脸,准确地转过来,目光刚好落在我脸上,他微笑,示意我坐下来,我坐下来了,他示意我靠近一些,我没有执行。他把屁股挪了挪,靠近我。二十多年的写作,练就了我的冷静。
我在等他说话。
“这是你姐姐写的诗。”他轻轻地拿起桌上的一杯红酒,也递给我一杯,“是不是感觉写得跟你的一模一样?”
他喝了一小口红酒,我没有喝,我在等他说话。
“你确实是有一个双胞胎姐姐,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一样,就连诗歌创作都一致。”他又喝了一小口红酒,“她发现你居然还活着,她想去找你,可惜,她打听到,你对外都说自己是个孤儿,无兄弟姐妹,于是,她让我在这个小区买一套房,这样能常常看到你。”
我心里已经有许多问号。我还在听。
“第一次在晨跑的人群中看到你,”他伸过手来,“我就很想牵你的手。”说着,他真的拉住我的左手,只拉住两根手指,见我没有拒绝,他慢慢地握住我的整个左手,很快,手中传过来温热,有一点像秋天的小太阳。
“你姐姐原来是上海市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他接着说,“在一个下班的深夜,遇到了一个传销团伙,专门骗年轻的女人,她想去报警,却在掏出手机的时候被一棍子打在头上。”他说着,示意我看了看蜡像的头部,果然有个小洞,“这是被打破了头。”
“来吧!”他在我耳旁说。他拉着我,进入书柜中的树洞。
树洞里有特别柔软的卡其色毛毯,有很好的空气循环系统,可是,我依然感受到急促的热的空气,在不断地拥挤着我,那大概就是荷尔蒙的气息。我慌乱地逃离了。他没有追出来。回到家,我努力让自己平静,我心里完全不在意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姐姐,我紧张的是,自己似乎闪电似的恋上他靠近的温热。
“叮。”手机短信响起来,是他,“明天早上,树下等你,一起跑步。”我鬼使神差地回复了一个字:好。
我似乎立即就后悔了,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也不了解他为何“虚构”了一个姐姐,我在好奇姐姐的同时,其实更多的是迷恋他不断靠近自己的气息。“怕什么,要玩游戏就玩一次,人生难得有刺激,来一回小荒唐。”我马上安慰自己。说着,打开电脑,继续进行新的一年选题工作,还是有一点心不在焉,也许心不在马更合适,我打趣自己的花痴。
清早的跑步,比任何一次都来得积极,以往是惯性,这次是“积极”。他早就在树下的十字路口等我了,眼里全是温暖,“嗨”,他一个字。“嗨。”我一个字。晨跑就开始了。
“你姐姐写的诗,真的很好,她一首都没有发表。”他说。我分明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温柔,是在回忆一个无限热爱的人的那种温柔,我有一点不高兴,我还没有搞清楚自己为什么不高兴,他接着说,“你姐姐很漂亮,也是你这样的短发,我最喜欢她的耳垂,软糯的感觉。”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我们跑四公里了吧?”嗯?我都不知道时间过得这么快,“哦,是的。”我说。
他不跑了,在树下等我,我继续跑完最后一公里,心里增加了一些什么,也许是嫉妒,可是我嫉妒什么呀?跟一个不确定的人,不存在,甚至说是“死人”计较?这么想着,最后一公里也跑完了,他拿着海口生榨椰子,冲着我轻轻地笑,这种感觉像极了恋爱中的小情侣,因为他的瘦弱和略带沧桑的眼神,我默默地给这种感觉加了一分。
各回各家。想着这几天放假了,不想加班工作,索性关了电脑,坐在阳台上发呆。窗外,下起了大雨,摸出手机,看看天气预报,说是要下雨一个星期呢!一个星期没法在室外跑步了,幸好家里有跑步机。
拿过一个酒杯,一下子,不知道喝哪一瓶。我想着,这个姐姐是个怎么样的人,孤儿院里的伙伴,还有联系的,只有杨树了。
我打了杨树的微信电话,说起孤儿院的往事,我有意无意地说起来,当时院长妈妈有没有收养其他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女孩,杨树说,“有啊,那个女孩,只来了一个星期,就被抱走了。”我的心一下子紧了紧,杨树接着说,“哎,都二十几年了,当时只有三岁吧,整个孤儿院只有两个小女孩,其他都是男孩子,所以,院长妈妈一直都对你们很好。哈哈,话说,你们俩长得还有一点像呢!都是短发,肉嘟嘟的,特别是眼睛和耳朵,长得像,脸形也像,可惜啊,被抱养了,不然呢,像你们俩这样漂亮的小孩,哈哈,长大了要迷死很多男人啊!”
杨树的笑声通过电波传过来,在我的耳膜、脑海快速地循环。
“哦,还有这事啊,三岁的时候,距离现在二十七年了,我真的记不得了。要是院长妈妈还活着,还可以问一问她。”我回应着。
看来黑眼镜说的是真的。那是怎么死的呢?不重要了。我既然没有参与过她的成长,也没有经历过她的死亡,我没有必要去了解了。我心里突然对黑眼镜更有好感了。
“叮。”手机短信响起来,是他,他在门口。我过去开门,他站在门口,瘦瘦直直的,像是被风吹来的一棵小树,他从兜里拿出一个本子,是空白的,我疑惑地看着他。“下雨了,”他把伞靠在门边,“想过来在你这里坐一会儿。”他很绅士,没有做出马上要进屋的样子,他微笑,我笑了,“进来吧!”顺手拿了一双我的棉拖鞋给他,鞋子有点小,他说,要不直接穿着袜子吧,我点点头。
他走进大厅之后,我才发现,他还拿了一支铅笔。我喊他一块儿坐在阳台的地毯上。他说,你的地毯和我家的一样呀,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是的,上个月在你家看到你的地毯很好看,我就买了同款,”我拿过两个酒杯,“喝点红酒吧!”他握着酒杯的样子,有一点迷人。
我倒好酒,发现他竟然在本子上写诗:你坐在阳台上/我坐在阳台上/我不关心窗边的蝴蝶/除了,你一点一点靠近的感觉。我的脸应该是红了吧,仿佛恋爱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他说:“你姐姐写诗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微笑,每次都只穿着睡衣在阳台上写诗,天气冷的时候,就把阳台的窗户关了,开着空调,哦,是她喜欢的26度。”我听着他软软的声音,心里升腾的竟是数不尽的嫉妒,这一回,我知道,这嫉妒是我想取代姐姐在他心里的位置。
“取代”这个词在胸腔中翻滚了许久,他还在说着,我似乎记不清他说了什么,只是很迷恋地看着,以至于不知道他何时已经坐在我的身后,轻轻地抱着我,是的,很轻,反而让我这个母胎单身的剩女感受到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为了缓和略带燥热的眼神,我们聊起了工作,谈起出版社的工作,我更多的是无聊,倒是很想听一听他的工作,他在上海一家大型培训机构,做公务员学员培训,据说,经过他培训的学员,大部分考上了公务员。我正要为他鼓掌,他轻轻地说,他也是孤儿,原来,我们俩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伸出手,握了握他的手。
晚上,他离开之后,我百度了那家培训机构,果然是有他这么一个人,我好像一瞬间放心了很多。
往后,只要他不上班的时间,他都来我家里写诗,我们也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阳台上的绿萝,陪伴我们经历了许多个黄昏。算起来,认识快半年了,除了简单的拥抱,他没有侵犯过我,而我却越来越陷入他的温柔之中,有时候甚至想放弃矜持,但他似乎没有想更进一步的意思,我仿佛掉入了情感的树洞之中。
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如果没有新的学员进来,培训机构很快撑不下去了,周围竞争的机构太多了。”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让我介绍一些学员过去,他知道我们出版社跟上海大学文学院有合作关系,培养写作人才,而文学院的学生当中,有不少想报考公务员的。我正在思考着,他伸过手来,很轻很轻地抱住我,很轻很轻地吻我的耳朵,他说过他喜欢姐姐的耳垂,我这是取代了姐姐在他心里的位置吗?哦,我瞬间没有了思考的能力,沉浸在一片虚无之中。在我想着还有点什么的时候,他却停止了,温柔地抱着我,听窗外的雨。帮我想了一系列的好办法,我也不忍心看着他们的培训机构倒闭,就默默地同意了。
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去了一百多个,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大学生想考公务员,也可能是文学院的老师想在我们出版社出书,动员了许多大学生,培训费也很快就全部交齐了。可能是因为人数多,他忙着,一个星期都没有来我家,我打他电话,他都说在忙着。
我开始有意识地问那些大学生,我隐隐约约想到了“传销”这个词。我在这些大学生当中找了几个机灵的,让他们留心观察起来。他们告诉了我一些情况。
连续两个星期了,他都在忙。每当坐在窗台上发呆,我就不停地在想念那些一起写诗的日子,想起他抱着我的样子。躺在床上,那种孤独感也反复袭来。
在一个深夜,他发来信息,只有三个字:我想你。我看着手机屏幕,心里激动得要哭,同时收到我安插的“眼线”来信息:这个培训机构是有问题的……我还没有读完信息,他的信息又来了,是四个字:我很想你。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家里,我立马就套上一件外套,跑去他家。我已经很熟练他家的开门密码,门开了,我跑进客厅,他坐在地毯上,准确地看着我的眼睛,一直往下,停留在胸前,我有一点羞涩,用手轻轻抓着睡衣的飘带,他直接就抱起我,往楼上走。
“眼线”的信息没能阻挡我浑身的热,在那个有着“姐姐”的树洞,我萌生了一种胜利的喜感,“我终于取代了姐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我确实是这么想的。第一次知道人间有如此的激情和浪漫,在一阵疼痛和微微的眩晕之中,我竟然睡着了。
我醒来,他不在身边。我走出树洞,走下楼,看到桌上的几个老人手机,心里痛了一下。回到家里,我拿起手机,又放下手机。
不得不说,如果我报警了,我将失去他,那一定是蚀骨的痛。可是,我明明知道了那是犯法,而且那是一百多个大学生啊!我打开跑步机,快速地跑起来,直到精疲力竭,累得只能靠在跑步机上,天也黑下来了。他发信息说回到家里了,我不知道中了什么邪,起身就跑去他家。我进了大厅,没有看到他,他发来信息,在树洞,我奔到楼上,毫无意外地,“姐姐”又一次扫描了整个做爱的过程。
我躺在他怀里,享受一个男人的温柔,他显然不知道我发现了什么,说:“现在这批大学生都培训得差不多了,看看文学院那边还有没有大学生要考公务员?上海其他大学的文学院你应该也认识吧?”我点点头。他不再说什么,轻轻地搂着我睡去。
- 青年作家的其它文章
- 我真正的知音在中文世界
——王德威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