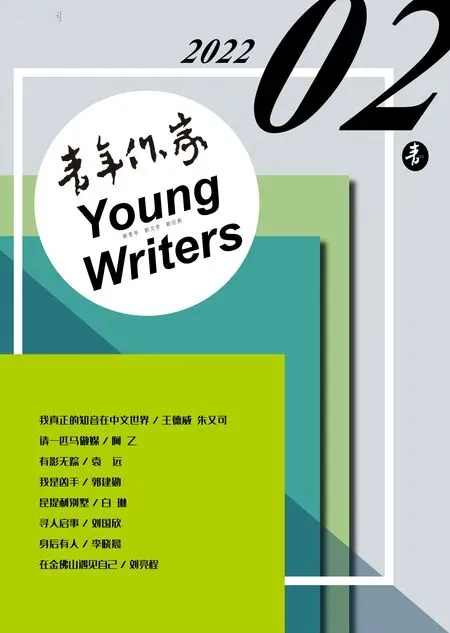我真正的知音在中文世界
——王德威访谈录
王德威/朱又可
“情”的论述,在中国有自己的体系和脉络
朱又可:谈谈你最近的研究和写作吧。
王德威:OK,我刚刚出了一部恐怕又要引起很大争议的书,哈佛版的《新编中国文学史》,这本书在2017年4月底出版。英文版有1060页,中文版大约一千五百多页。这个书原来编写的对象是英语世界的读者。但是,我觉得我真正的知音应该是在中文世界,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会引起什么反应。
朱又可:从什么时候开始编的?你是主编,你请了多少人参与呢?
王德威:从2013年开始的这项文学史工程,我邀请了143位作者。这部新编中国文学史是哈佛的大型文学史系列之一。1989年出了第一本《法国文学史》,在过去的28年里面,又出了《德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一共有161篇文字,按照编年的体系,以散点辐射的方式,并未刻意强调那些伟大的事件。这本书打散了所谓大叙事的做法,它不是从头写到尾、一以贯之、巨细靡遗的一本书。和哈佛其他国家文学史的体例一样,每篇短文2500字,选取一个历史上的时间点,某年某月某日,有新闻报道一样的标题。之所以有严格的字数限制,是希望在统一的体例之下,找出某种秩序,来形塑一种特殊的写作风格。面对西方英语世界的读者,可读性是非常重要的。
朱又可:你都邀请了哪些方面的作者?
王德威:除了做文学研究的学者,有很多作家应邀加入文学史的写作。王安忆写她的母亲茹志鹃,作家女儿写作家母亲;哈金用小说体写鲁迅写作《狂人日记》的1918年4月26日那个夜晚;余华写他在华东师大的翻墙故事;莫言写今天写和读长篇小说的意义,等等。
朱又可:你向一百多位作者提出什么写作要求?
王德威:你一开始问我最近做什么,对于作者,我现在延续这样类似的一个理念,我就更展开了,就在不同的论述上,问了一些我们大概都觉得无从问起或者是习以为常的话题。什么是文心?这是一个好像不能问的了,文心不是文心雕龙吗?或者心是什么东西,文学跟心?鲁迅说要因人心者《摩罗诗力说》,或者鲁迅在《墓碣文》说一个自抉其心的死尸,自抉那个心是什么东西?所以,这类问题,像什么是史?什么是诗史?好像是很古典的,我们现代文学应该把它区隔开来的话题,我认为它是在很多脉络里,渗入我们的文学意识以及文学写作上。到了今天,我觉得很多东西非常有趣,很可以介绍给下一辈的学生或者同事。尤其我对话的对象,当然在西方的学院里——比方说比较文学系,我自己在比较文学系有另外一个兼任的职位——我怎么去跟我的同事谈这些话题?所以这是我的做法。
另外,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就是这几年我也在推动所谓的华语语系研究。过去,华语语系就是所谓的海外文学。现在从中国以内的立场来说,是世界华文文学。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些不同的命名和它的语境之上或是之外,再找出一个对话的平台。当然,我们文学的能量在于修辞,在于发明新的文学观念,所以用华语语系的观念重新作为进入大陆和海外的,不论是文学的交流或是交锋的一个场域。
朱又可:为什么会做新编中国文学史这件事?
王德威:因为我觉得这个事件有很深的意义。我自己在做的,应该算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所谓的现代中国文论理论架构的重新思考。我想你都不会意外,就是我们整个学科领域基本的架构,是来自于经过日本所传来的西方文学的定义,还有美学的原则以及论述的方法学,过了一百年,我们接受的这些冲击、灵感,整个形塑了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什么是文学的观念。当然,我自己也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我的所学甚至我教学的方式,也都在这个系统里。但是,在过去的10年到15年里,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虽然已经深深地浸润在西方的范式之下,同时有了足够的信心,对中国文学有了一个更全面的理解。应该是时候重新思考从晚清到现当代不同时期的不同知识分子、文化人,以至于作家自己,关于什么是中国文学,甚至最简单的,什么是文学的这些观念。这是我现在正在开始做的,而且已经做了一些了,比如前年我出了《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
如果这个观点是习以为常的一个反应,就是一个很软性的、很小资的、很个人的文学姿态,或者是一个文学写作的风格,那么抒情这个观念,也的确是来自于西方的浪漫主义转接到现代主义的一个言说过程。但是,我想任何有一点点中国传统文学理念或训练的,无论是学者或学生,立刻理解到抒情这个观点,在中国其实是源远流长的。第一个把抒情公之于文学表达上的,是屈原,“发愤以抒情”。所以,抒情,还有它的关键词“情”的观念,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其实被狭义地定义为很简单的伤春悲秋或者是无病呻吟。事实上抒情或“情”的论述,在中国有自己的体系和脉络,从情感、情境到情实,不一而足。因此,就这个观念,我把它重新发掘出来,同时也观察到现在中国文学以及文化界,从晚清以来对抒情的观点,不论是鲁迅或是朱光潜,不论是李泽厚或者是王元化,都有很多不同的抒发。所以,我把这样的一个脉络理出来,在我的书里,着重在1949年前后所谓的史诗时代里面,有那么一群自谓用抒情来面对历史风暴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怎么来面对所谓史诗的挑战,这是我的前一个著作的大致说法。为哈佛新编文学史,则延续了这一对文学和文论重新思考的脉络。
朱又可:你的文学现代史的起讫年代是怎样的?
王德威:这个编年史的时间进程开始于1635年的明朝,结束点是未来式的2066年。英文的Modern是有一个很宽广的定义,我采取了一个宽松的定义。在时间的论述上,现代的观点和中国以内对于文学的近现当代的分期法颇不一样。
中国现代文学从1635年开始
朱又可:你为什么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是从明代开始的?
王德威:这只是假设的一个可能性。现代文学,我们当然可以很轻易地给出几个制式的时间定义,比方说是1898年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本馆付印说部缘起》,也可以定在1902年梁启超提倡新小说,也可以是1902年慈禧太后下诏成立所谓的文学科,或者是1904年北京京师大学堂第一次的文学史教材编写。我觉得这些都是言之成理的文学起源点,就是文学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起源点,更不用说是五四运动那一天了。所以,我们把文学的脉络推到1635年,其实是一个问号,就是有各种可能的开端,也有很多结束的方法。所以这篇文章的时间点不是只有一个日期,它其实是有三个日期,1635年、1932年、1934年。在不同的时间点,大家投射他们对文学的看法。
从1635年到1800年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只有少数的几篇文章而已,并没有刻意夸张所谓线性的逻辑脉络。真正文字越来越频繁的时间点,应该是在19世纪初期的1807年,当莫理逊到广州住了一阵后被赶走,因为不能让外国人住进来,他最后到了澳门,跑到马六甲。这是传教士所发动的一个所谓翻译的文学现代性的开始。与此同时,也并不能排除中国的文人,在那个时候,哪怕是晚清的第一代维新之士,像龚自珍这样的,他对于文学可以做什么,也有些想法。所以,我不会很刻意地标明哪一个点是“开始”的点,但是从文章的安排上,读者可以感觉出来,问题越来越具象化,越来越引起大众自觉地注意,应该是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就是1820年、1830年之后。
朱又可:你说第一个现代作家是明代的杨廷筠。
王德威:在时间上,我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第一篇文章是从1635年开始,当晚明的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文人杨廷筠,接受了西方像艾儒略等传教士对于文学的看法,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学做了新的定义,从这儿开始。但是,同样这篇文章里面我也邀请了台湾一位学者,提出了1932年、1934年周作人和嵇文甫分别从左派和右派的立场、人文主义和革命主义的立场,将中国文学、思想的“现代性”上溯到晚明的这样一个事实。杨廷筠其实是一个文人,是一个读书人。他在他的一个文集里面开始思辨什么是文学,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话题。因为文学其实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在中国,文学这个词一直上溯到汉代以前。但杨廷筠在这个时候受了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的影响,他认为文学里面有审美的层面,应该怎么样,所以他就有一个论述。这篇文章的写作者认为,这是近现代文学各种开端里面一个比较早的开端。他的这个说法不见得是唯一或绝对的,也有同事不认为如此,他们觉得这个太早了,我们真正想到文学应该还是19世纪,我们现在定义的文学也是19世纪才开始的。所以,我觉得在文字的修辞上,我作为编者,就特别要谨慎,避免这些作者以为自己好像发现一个东西,太想成一家之言,把话讲得太确定了。这个大概和我们想象的文学史的开放性是不符合的。因此,在文字上我做了很多功夫来修订这种话语上的表达方式。
朱又可;杨廷筠是1627年去世的,为什么说第一篇是从1635年开始的?
王德威:应该说是杨身后,1635年出版的集子里,出现他对文学的新定义。为慎重起见,我将问题转给原来文章作者李奭学博士,请他再确认。李奭学的回答是:杨廷筠原有《代疑篇》一书,刊刻于1621年。他又写了续书《代疑续篇》,但不知完成于何时,而人已在1627年去世。1635年,福建人——应为天主教徒张赓——可能在福州刻之。《代疑续篇》里把1623年艾儒略在《西学凡》《职方外纪》中用以中译耶稣会《研究纲领》(Radio studiorum)里的“文艺之学”(littera/litera/philologia)一词改为“文学”。“文艺之学”中的“文艺”二字,我有限的知识里,至少欧阳修的《新唐书》里已用来指清人所谓“集部”(文集、诗集等),故杨廷筠一把“文艺之学”改为“文学”,就等于在历史上掀起了一个名词大变革(而且沿用至今),因为民国以前,“文学”多指“儒家经籍”或“教育”等概念,和今天我们以为的诗、文等“文学”的内涵不一样。艾儒略的概念由欧而来,故而今人使用“文学”,也是“西化”的结果,亦由欧洲而来。鲁迅及王国维等认为是日本译词舶来,不对。日本译词亦由天主教耶稣会传给基督教的传教士,再由他们东传到日本去使然。鲁、王失察矣。
朱又可:你收入的关于明代的另一篇作品是什么?
王德威:另外一篇是一个普林斯顿大学荷兰来的教授写的,他讲了在明清之际,崇祯亡国的事情怎么经过当时的外交和商旅途径,传播到欧洲去,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里面,成为欧洲戏剧的题材,就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变动。
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另外隐含的论证,也同时是中国的世界文学或世界的中国文学。中国怎么进入这个世界的体系,这个是我隐含的一个论证,所以,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是这个文学史的主轴之一。文学翻译,或是文化传译、传播旅行、文学跟世界的关系等等,我觉得必须提供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学。
朱又可:那么,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世界性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这个世界性,不管是世界进入中国,还是中国走向世界,那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王德威:对。这是我的论述之一,我在导论里面提了几点时间的复杂性、空间时空的这种大裂变、旅行传译、文化传播、巡回等等问题。读者一定会觉得不满意或不过瘾,但我希望这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创意,或批判性的回应。读者可以就这已经有的日期触类旁通,想象更多增补文学史的可能,而不是这个书不能给我哪几个条文,让我考试可以早点过关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
晚清的科幻小说是多么精彩
朱又可:你在《剑桥中国文学史》里专门写了晚清的部分。在你主编的哈佛文学史里,关于晚清有多少分量?
王德威:晚清的部分,有相当分量。二三十篇逃不了。这个晚清是一个长的晚清,而且包罗的范围相当广,包括传教士文学的系统,也包括由龚自珍所代表的公羊派的士大夫的转向,梁启超、康有为、严复这个系统,当然也有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兴起。除此之外,包括女性文学的兴起,文化生产包括报纸,还有第一本中国的文学杂志,就是《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邦庆的《太仙漫稿》等等。晚清的厚度越来越加重了,从1807年马礼逊到广州,再到《镜花缘》的写成等事件,时间的间隔还比较大,人物、文本之间的关联似乎没有那么密切,可是到了1880年、1890年就越来越复杂。因而,我当然认为晚清是一个有意义的重要时代。到了我们正统的所谓五四之后,文学现象就非常多元了,像是对于鸳鸯蝴蝶派重新的关注,古体风格写作的诗文等,都有一席之地。
所以,“现代”其实是非常繁复的、有厚度的一个文学现代性,我们现在的文学史一看就知道,每一个文学史一定是有几个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大家按顺序排列,然后有革命论述、启蒙论述,大概就是这样。我想这个论述无可厚非,值得尊重,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我就觉得不够满足,我所阅读、所惊艳的这样一个文学史,这么丰富,为什么不用一个好的机会介绍给西方读者呢?
朱又可:记得你在其他的文章中谈道,中国的现代性,一方面是外来的,另一方面是内部自生的。
王德威:是的,这是那本《被压抑的现代性》。过去所谓冲击跟反应的模式,我想大家基本上已经有很大的质疑,不需要再辩论,中国不是一个被动的老大帝国,只是因为西方的强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勉强作出反应,而且反应得很不好。我所要强调的是,在东西方的文化跟政治板块碰撞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机里面,它当然有时机的因缘际会:就在这个时间它发生了,但这样一个现代性当然牵涉到中国的本土知识分子,还有民间面对各种不同文化的撞击——外来的、内里的,高雅的、卑俗的,翻译的,还有传统的,各种资源的撞击——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有的失败了,如果给它二十年自由发展的机会,说不定它会成功,但这些都已经是历史的后见之明。
但是,我们不得不从一个文学史的角度上去思考,有哪些资源、传统、线索、计划,可能在有意无意的情况之下,被压缩了、被扭曲了、被误导到不同的方向了。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历史学家也会想的话题,可是历史是讲究实证的,它要证据。文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文学提供的是想象力,它从虚构里面去遐想、去假想中国的过去,也从过去想中国的未来。
我举一个例子,晚清的科幻小说是多么的精彩!1902年到1910年的这些年,《新中国未来记》《新纪元》《新石头记》想象中国的飞天入地,变成大帝国、乌托邦等等,这是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谁能够在那个时代想象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会有刘慈欣跟韩松这些人出现,这不是一个历史不可思议的吊诡吗?其实那个10年的小说很精彩,可是时过境迁,并没有发展的机会。可是到了这个10年,刘慈欣、韩松等现在全中国、全世界所受到的关注,不正印证了我原来所谓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论述吗?所以,看刘慈欣的现象,不得不回想到梁启超在1902年写的乌托邦小说,或者是吴趼人在1908年改写《红楼梦》的科幻传奇等等。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能量,还是在幻想、在虚构的角度上,但为中国的过去跟未来擘画出很多不同方方面面。这是历史学家、政论学家所做不到的。
朱又可:那么,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的一百年年,从科幻小说看有什么发展变化?
王德威:发展变化太大了。1910年之后小说变成写实现实主义,这是统率整个中国文学的主流。每个人都认为写实现实主义是最进步、最科学、最启蒙、最革命、最“真真实实”的东西,就叫写实现实主义,我们到今天还是讲这个。为什么中国一般的阅读大众,却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在这么强力的一个写实现实主义号召之下,居然这样为刘慈欣的世界所着迷呢?
所以,文学想象的层面底部,那不可思议的变化性,这是我们得珍惜的。主流论述的力量也许十分强大,可是我们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叫做“文学”:当历史论述哲学的思维或政治意识形态的教条塑造了一个理所当然,不能撼动的“现实”,你摸不准的小说家就冒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始料未及的东西。这些虚构的东西很多时候是被压抑掉了。但是,你不能够阻止后之来者去回看原来各种各样虚构的轨迹所做出的联想,有的时候是有意的联想,有的时候是无意的联想,有的时候是不由自主地就出现了。
余华的《兄弟》太像晚清的谴责小说了
朱又可:你说晚清那么丰富的一个东西,各种各样的文学,小说也是各种各样的,后来它就窄化了。
王德威:我认为五四导向写实现实主义,这在当时大家认为是最主流的、最科学的,文学就应该这样,那也很对。“文学反映人生”,五四文学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但是,我一直觉得,即使在五四的正统文学里,很多晚清所留下来的线索是在的,五四文学也不是只有一种。老舍写的作品,跟巴金写的就不一样了,鲁迅写的跟茅盾写的就不一样,萧红跟叶绍钧(叶圣陶)写的东西就不一样,这些很丰富的东西,何必非要把它挤成一个教条式的公式呢?
在晚清,我所处理的四大小说文类里面,其实每一个文类都有一个特定的论述的关键词,这些观点其实是进入五四话语领域里面的,它只是用写实现实主义这样一个东西表达出来。比方说,我认为侠义公案小说——当然《七侠五义》到今天还受欢迎的——代表了一代人正义的向往以及自欺。另外,应该是狎邪小说,就是五四的这些青楼女子等等,那是一个大传统,它其实探讨了什么是欲望、身体的解放和管理等问题。科幻小说它真正指向我们的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所埋藏的“真理”以及“知”的问题。我觉得科幻小说表面上写的是光怪陆离的东西,但是对知识型的打破,是非常大的助力。最后一个,应该是写实现实主义和谴责小说,就是黑幕小说,我认为黑幕小说所投射的价值辩证充满张力。黑幕小说所暴露的各种各样的是非曲直黑白的伦理、政治、欲望交换性的巡回脉络,指向的却是什么是价值问题。
其实,我有四个蛮大的关键词,而这个关键词在五四以后的写实现实主义小说里面,不断地繁衍、不断地衍生,什么是价值、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知、什么是欲望等。何况到了21世纪的中国新小说。我看余华的《兄弟》,会立刻反应说这太像是晚清的谴责小说了。我看贾平凹的《废都》,这不是一个讲狎邪、讲欲望散乱的故事吗?刘慈欣以《三体》证明科幻对于什么是知、什么是真知真理的问题整个典范的转换。正义,我不用多说了,我想整个的正义论述在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年,有太多的小说不断地说明,余华的《第七天》、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都是好的例子。莫言的《生死疲劳》不是讲轮回的故事而已,也是讲了一个什么是正义的故事。我刻意用小说这个领域来说明,小说——或是文学——对我们的社会是有意义的,是重要的,对中国的人文环境尤其重要。当大历史不能告诉我们历史真相的时候,当各种其他的论述,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论述显现它的局限或僵局的时候,我觉得一代又一代作家不断在经过小说来突破、来突围。
朱又可:就是一开始丰富,后来狭窄,之后再丰富……
王德威:我觉得,即使在狭窄的那些年代里面,窄就窄了,它有好的作品出现,但是我认为晚清所代表的那样一种多元的、奔放的想象力,有的是正面,有的是负面,的确它在经过一个世纪之后,在我们这个时代又释放出来。
这样一个经历,现在不见得是纸上的传媒所传达的而已,我们只要到网上的文学去看一看,我想任何人都会很惊讶,那样奔放的、恣肆的想象力,我觉得20世纪有一辈的作家是想象不到的。网络文学那种活力,正面的、反面的、混乱的、好的、坏的,竟和晚清相似。晚清出现报纸、杂志、印刷。我觉得过了一个世纪,新的时代在网络上的实践,那种想象力的狂放,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是我们并不低估网络相生相克的力量。所以这个问题是在进行中的。
中国的文和西方的文不同
朱又可:你说,中国的文和西方的文是不同的?
王德威:有同,也有不同。我举一个例子,像《美国文学史》,两位编者说为什么要做美国文学史,他们的理念是“美国就是文学”,这是很妙的。这个“文学”的意思,是无中生有的、虚构的或创造的意思,这跟西方从柏拉图以来对于所谓的诗是什么——诗是一个创作,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造的观点——是相契合的,也符合了美国开国的一个精神,充满了想象力、创造力,从没有到建立新国家的一个理念、一个表现,这是美国文学。
但是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我不能依样画葫芦,我不能说中国文学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这和我们中国传统对“文”“学”的看法也不太一样。最后,我甚至觉得什么是文的观念,已经和西方的文学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需要来解释什么是中国定义里的文的观念,什么是文学的观念。我了解到从《文心雕龙》以来,中国人对文的观念的包容跟开阔性,居然超过西方非常多,甚至有意无意地和当代西方的很多文论、西方的文学论述相对应,是可以对话的。我做的中国文学史,即使在理论架构上,我相信也有相当中国的成分了,不再只是西方的后现代结构这些时髦的话语之下的一个产物。它让我们了解到中国传统的文的观念,其实是可以投射到现当代我们对于文学史的一个重新的思考和回顾上。
“文”这个字一开始我们知道是“错画”——就是一个标志,线条的交错、装饰。文学也曾是一个官位的名称。“文”作为一个审美的作为或者审美的呈现,是六朝的事情,都已经是第三、第四世纪以后了。“文”也是文明的意思,是一个文化教养的事情——斯文。“文”也是一个不断长成的人跟宇宙互动的现象,天文、地文、人文。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我今天在介绍一个文学史,当然要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和西方以模拟和再现的观点所产生的文学观念就不一样了。中文的天人、人跟心跟物情景交融等等,是很中国的这一套。我的辩论是,即使到了21世纪,这一类观点依然流传在我们对于“文”的使用上,何况文学跟政治的观点。为什么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是奉了文学跟文化之名而兴起的,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文”和“政”之间的复杂性其来有之,任何做古典文学的同事都可以告诉我们。
朱又可:能举例说说吗?
王德威:比方说,我们说“礼”“乐”“诗”之间的关系,一个政通人和的时代称为礼乐之治,而礼、乐在儒家政治正统思想里,最完美的表现就是诗。诗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一个诗人有了灵感,就写下一点儿个人的心情或者风景,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传统的文人就“住”在诗里,他就生存在诗里,而这个诗必须是在一个从个人到家国到天下的理念脉络里面不断涌现的文字和作为。所以,对文的观点,即使到了后来,不论是五四还是延安讲话,对文学那样的重视,它不是简单的宣传、口号文学而已,它有很多言不尽意的中国传统对文的一种信仰,一种想当然的思维逻辑在里面。
所以为什么是重写文学史,而不是重写文化史,政治、经济、森林、农业史不可以吗?重写文学史在1980年代末的冲击力非常非常大。这里面复杂的文学跟政治的关系,是隐含在那里的。
朱又可:那么像汉语的新诗,就是现代中文诗歌呢?
王德威:汉语的新诗基本上是另外一个文类了,跟中国古典诗歌所代表的那样一以贯之的,从文学到修养到家国的,所谓大的一个逻辑式的推演是不太一样的。汉语新诗的出现几乎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新的文类出现。这个新的文类到今天的辩证性仍然是存在的。与此同时,我们过去的文学史基本上就觉得新诗出现了就取代旧诗,很简单,文学革命。但是,这两年现代的“古典诗歌”研究已经起来。现在中国的政治诗人,有谁比毛泽东更受到大家瞩目?他也作诗,而且是古体诗词,他也是文学界的一分子。我们有一篇文章,就是讲毛泽东的旧诗词。写作者是我的同事田晓菲教授,她非常妙地把《红旗歌谣》和毛诗在同一年出现的两个极端放在一起,一个是帝王式的,大家敲锣打鼓的所谓18首诗、19首诗的出现;另外一个是民歌采风,但同时也有政治的脉络在里面,重新把所谓的民歌运动又召唤出来。我们对诗的定义是真的蛮谨慎的,新诗跟旧诗完全是两个路线,是两个东西,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当代已经70年,现代只有30年
朱又可:你曾强调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而不是五四……
王德威:还是《被压抑的现代性》那本书。我曾经做了这样一个观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对我来讲,中国文学史的脉络是这样的复杂,我们从哪一个点开始,你都可以看出不同的历史脉络,也能作出一个不同的文学研究心得,横看成岭侧成峰。我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讲过,“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对我来讲,这是方法学上的一个训练,没有五四那一代的文人,包括胡适、鲁迅在内,重新看待晚清众声喧哗的时代,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晚清研究的这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在时间上的一个策略翻转,其实让我们对于文学史的丰富以及厚度,有了更多的体会。从这个复杂的脉络角度,我不觉得中国的文学现代性只有五四才能够定于一尊,或者是只有在五四才达到高潮。晚清在那个时代所代表的种种面对西方和中国以内的各种冲击、各种各样求新求变的冲动、实验、失败、成功等等,它所汇集出来的一种力量导向了五四后来的另外一波高潮。所以,我把晚清当做是一个被压抑的现代性,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复杂的晚清70年,在日后的文学史、文化史,并没有得到很完整的观察或重视。
在最近这些年,近代、现代、当代开始合流,有很多的各种复杂的脉络,大家开始重新放在一块谈。但我想即使今天在中国大学的教学过程里面,这个分割还是很明显。近代是从哪里到哪里,现代从哪里到哪里,当代从哪里到哪里。当然,最反讽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当代已经越来越长,从1949年到现在,这个当代已经快70年了。现代的部分特别短,是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这都变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讽刺。当代,是当下此刻的意思,当代本身已经物化成一个历史必然;而现代,就是西方约定俗成的时间进程观念,被挤压成一个很短的时间;近代则变成一个腐烂而颓废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一个形容词来标志。在国外的文学史论述,这种规范和禁忌——恐惧——似乎不多见。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天
朱又可:这个每篇2500字的文学史个案,怎么写?
王德威:我举几个例子,也许你就明白了。比方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这不是太约定俗成的一个话题,2500字能写出什么来?天安门广场上北京大学学生示威等等。但是,我邀请的这位英国学者,他写到1919年5月4日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天,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天安门没有示威什么的,而是对当时的一些重要文人,很多事情是后见之明。那天早上,鲁迅到书店去领取日本寄来的书等等,那天又有其他的文人做了这个事、那个事,而五四之所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历史事件,是要经过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酝酿、传播,媒体的推波助澜,还有整个中国一种所谓的感觉结构,民心士气的一种倾向,所汇集出来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文章的标题就是对五四运动的意义的一个质疑。这个文章提出来最早直接描写五四运动的作品,并不来自我们今天约定俗成的五四文学正统,而来自鸳鸯蝴蝶派那些作家。鸳鸯蝴蝶派是最敏锐的,最立即反应对五四运动意义给予支持。
这里面有很多文章,从各种小的历史脉络里面,重新去介入这个大历史千丝万缕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也不知道这个做法对中国国内文学历史的大传统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但是我们想做到的是,至少让英语世界的读者,第一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在一个很短的文字里知道五四是什么,五四可能代表的意义有多少不同的方面。但也不见得是要做翻案文章,我觉得那也太简单了。五四没有什么好否定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的事件,从文学立场上我们怎么来看待才是我关心的。因此,许多文章是从一个事件开始,或是一本作品开始,或是一个器物开始,之后扩散出去,由点到线到面,产生很多不同的对文学和历史的比较广义的看法。
朱又可:你邀请作家来写文学史,有什么特别之处?
王德威:我邀请了王安忆,但是我没有让她写她自己,我请王安忆写了她的母亲茹志鹃。茹志鹃应该算是第二代中国革命女作家了。在1950年代她的母亲写作的时候,所面临的方方面面各种灵感的冲击,可能跟不可能的写作风格。同时,王安忆也借这个机会,表达了一个作为作家的女儿,对一个作为作家的母亲的一种亲切的想象的对话。另外,我请了余华,讨论在1985年他怎么读西方的各种文学翻译作品的一个经验。我们都知道余华受到西方的很多影响,但余华就写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个人怎么翻墙的故事。这个翻墙是语带双关的,在故事里面,他真的就在华东师大每天翻过墙到那些书店去买卡夫卡、川端康成、海明威等人的作品。还有,莫言写他认为为什么到21世纪还应该读小说的意义。我请了不少作家,台湾的作家我请了朱天心,香港的作家我请了董启章。
比较正规的题目,我请了陈思和来回想在1988年怎么和王晓明策略了重写文学史的运动。我又请了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张英进教授,描写1949年王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是怎么写他的文学史的。我请了李欧梵谈夏志清如何写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如何和马克思主义汉学家普实克打笔仗。
我也请了汪晖写一篇关于墓碑的随想。他自己在德国做研究的时候,在一个墓园里面看到了各种墓碑,引起他对个人所来之路的回想,对西方的这些哲学家的贡献,或是他们所遭遇各种冲击的回应。这篇文章结束在鲁迅的《墓碣文》。
我想象的文学史,真的就是“文学”史。过去我们的文学史,是没有“文学味道”的历史。它没有文学性,文学史跟经济史、社会史、地理史放在一起,只是文学有那些事儿把它做成资料而已。
我告诉作者,这些是文学史,我们都是创作者,我们真是在思考文学的力量、感动人的力量,所以不要顾忌形式,自己来发挥。因此,有的人还写了小说。我请了哈金,他是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华人英语作者。他写的是一个重要篇目,写鲁迅怎么写《狂人日记》,他写鲁迅在1918年4月26日的晚上,怎样踌躇自己的未来,那晚上就想到写出小说,就是《狂人日记》。哈金有很多史实线索,把整个经历用一个小说家之笔重新变成小说、变成文学。这是自己也有很多感时忧国之痛的哈金,来遥想鲁迅在1918年怎样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当时中国的状况。
演讲的声音是不是文学?
朱又可:你把文学的观念确实拓宽了,收入了碑文,此外还有什么?
王德威:其实对于什么是文学的观点,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反省跟思考。我们现在讲文学就是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四大文类。但是在1902年,当文学变成一个学科之前,中国的文和学,还有文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很不一样的观念。我回顾中国一个大的文学文化史的语境,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有力的批评观点,重新把文学放在更广义的历史脉络上,来回应当代西方对文学的定义,一下子就豁然开朗:原来中国文学是这样有意思。
“演讲”是一个很新的观念,孙中山在1924年唯一留下来的留声机或者唱片的一段演讲的声音,和毛泽东在1949年天安门上开国时候的演讲,这是不是文学的一种呢?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朱又可:谈的是声音,就是说不是演讲稿,而是演讲本身?
王德威:这些历史人物的演讲经过留声机的传播之后,变成大家可以听到、感受到,然后体会、反应的一种陈述过程。这是不是文学呢?这是文学生产的物质性(也包括身体性)的一面。这篇文字我请的是北大的陈平原写的。相对于此,关于声音的,有一章是讲邓丽君的,邓丽君是1995年过世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在中国的文学上代表什么意义?从声音、从邓丽君唱歌的歌词,还有她感动的整个华语社群所造成的所谓邓丽君的神话,老邓跟小邓的问题,一直到这两年新的3D、立体的幻象式,邓丽君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演唱会用3D激光的方式把邓丽君的影像投射出来。这是我们对于“声”和“色”、“文”和“影”的观念的一个互动。所以,文学不必是四大文类。到了这个世纪,可以发挥成新的传统,如电影算不算文学就是一个问题?《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不少关于电影的文章。我们刻意打破这个领域,也是要推翻过去或当代定义或范式,重新思考文学在21世纪作为活泼的、有能量的,而且仍然是我们大家互相传动的一个文化表征,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像年轻的网络文学,我有一章讲韩寒的问题。还有几章是关于网络诗歌、电脑的游戏等,这就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文学。当我们思考电脑游戏所产生的一种叙事的力量,文学的元素似乎又挑战我们的认知。所以,文学史顾及方方面面,但我们的挑战是怎么样让它不要变得太散,因为太多太散乱,也不能够成为一个论述,怎样在收跟放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挑战。
朱又可:韩寒是谁写的?
王德威:是一个德国学者写的。他从1999年《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从韩寒的17岁,一个纯粹的文青,一直到韩寒怎样变成文化界里一个偶像式的人物。那是另外一种包装出来的文学现象。所以,每一篇文字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刺激我们去思考文学的体制、什么是文学、文学能做什么等等这些问题。
国际性也包括了社会主义的文学
朱又可:在你的现代文学史中,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内地你涉及哪几个作家?
王德威:1949年对中国文学的意义当然有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像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也有专文讨论。长征,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进入的方式就不再是因袭现有论述的表面文章。我特别请了一位资深人类学/历史学家,她在前几年访问了硕果仅存的几位长征时期的女战士。这些女性在长征路上所经历的艰辛,还有她们个人作为女性长征者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等,是过去男性中心论述,不论是军人或是非军人,比较少碰触想象的。所以,他一下子就把长征的革命感召与现实挑战等很多的面相打开了,长征是一个真正有血有泪的故事,不必是神话性的事实了。延安“讲话”,我请到了钱理群教授,我很光荣。
涉及的作家还有路翎、胡风、浩然,还有《青春之歌》的杨沫等等,诗人也有几位。文学在我广义的定义里面,当然包括了其他艺术形式,包括田汉的《关汉卿》,当时应该是在首都剧场,这个剧场本身配合戏剧制作的,所产生的反响非常轰动。还有《茶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等。《东方红》这个歌是怎么起来的,从陕北开始,在1960年代初期怎么酝酿变成一个大型歌舞剧,最后变成电影版,还有一度禁演的命运等。当然也有《红灯记》始末,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是,1954年出来的黄梅调《天仙配》,当时最卖座的电影。所以,我们想象的文学,应该是蛮复杂的一个现象。还有,比如就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中国跟阿尔巴尼亚做了一个热闹得不得了的民族表演活动,这里面也有当时中国政府希望跟在中苏边界的少数民族像东干族的文学互动的一些尝试。所以,我们的文学史不是刻意在批判什么,所谓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它有它自己那一套,不容忽视。因为我们今天在西方,都已经习惯西方这一套的国际性,忘掉了社会主义。
朱又可:社会主义有它的世界性和它的国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