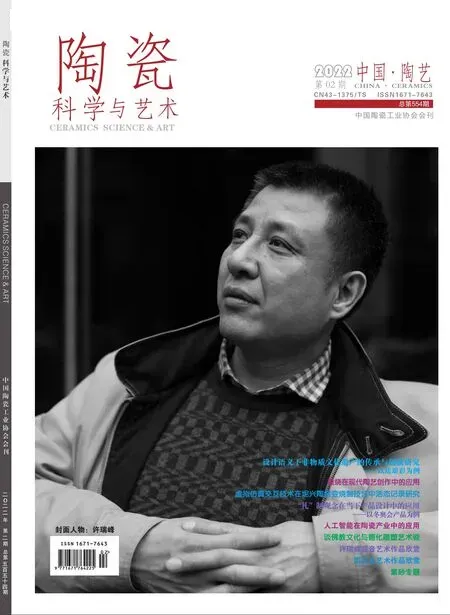论紫砂陶刻的文化传承
——紫砂掇只壶《百子图》之创作感悟
唐 田

紫砂陶刻艺术需要将紫砂泥与书画艺术相结合,在传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简单来说就是将中国的文学、绘画、篆刻、书法等等的艺术形式及艺术内容通过精妙的陶刻刀功,融会贯通地呈现在紫砂器之上,其模式基本与古时的陶器刻文一脉相承,紫砂艺术的包容性和中国文化的传承性都在其中得以体现。在此就以这把紫砂掇只壶《百子图》之创作来谈一谈紫砂陶刻的文化传承。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众多的文化印记沉淀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让中国文化牢牢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巅。无论在哪一个社会,孩子都是未来的希望,中国社会整体对于教育的投入有目共睹,每一对父母都期望自己的孩子喜乐安康能够生活得更好,《百子图》正体现了这种普遍的精神面貌。《百子图》又叫做“百子迎福图”或“百子嬉戏图”“百子嬉春图”,在我们的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百子图》中的“百”并非是单纯地指数字一百,而是阐释出大或无穷、圆满之意,是一种将祝福的愿望发挥到极致的描述。久而久之,当这种祈福被普遍接受的时候,书画创作中将一百个孩子完整地描述出来的作品也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紫砂掇只壶《百子图》便是以此为题,在眼前这把掇只壶的壶面上,用刻刀完整地刻画了一幅《百子图》,用细腻的刀法表现出十分精巧的画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传统紫砂壶形中掇只壶本就是非常完备的造型,通常一把比例得宜的掇只造型会无限趋近于完美,这样的紫砂壶上通常是不需要进行任何装饰的,所以在一把掇只壶上进行陶刻创作,可以说是在破坏这种“完美”。所以眼前这把掇只《百子图》首先需要改造这种“完美”的印象。在这把壶的壶上,以阳刻的形式用篆书来点明作品的创作主题,简单而直观地转换了整体的艺术性质,其后掇只的造型不需要作出任何变化,即可以用刻刀在壶面上刻画出完整的《百子百福图》,一百个孩子一百种幸福,纯以线条来进行塑造,人物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都继承自传统绘画艺术,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简化,阴刻的线条将画面塑造得既独立又完整,孩子们之间既可以一人成画,也可以组合在一起相互呼应,并且每个孩子的动作、眼神皆不相同,同时这些孩子又具有近乎统一的穿着气质和快乐蓬勃的精神面貌,刻画既能够感受到人物间各自的不同,同时又传递出一致的令人高兴的气息。
《百子图》充分借鉴了传统绘画中的图像表现,差别在于平面的绘画如何合理地转换到茶壶的壶面之上,由于掇只壶的壶面腹鼓块阔,在壶肩与壶底之间存在一片最佳的展示空间,在这个区间内进行刻画,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画面的表现力。事实上在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一个创作题材需要作出本质上的转变,并且在转变之后还能够保持一定的延续性,这便是陶刻创造的难点之一。在这把壶上,先不说构图,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刻画比例的拿捏,每个人物的大小本身需要维持一致,从而获得画面整体的协调,但壶面不同于平面绘画,无论是横纵、空间都极为有限,而《百子图》的刻画又对整体的连贯性要求极高,这就需要在壶面上疏密相宜,画面平滑有序,不会出现此处密而彼处疏的情况,孩童嬉戏的间隔就成为了把握整体性的关键,通过协调不同的人物组合,使整个画面连贯起来,加上掇只壶本身圆的通转如意,一连串的画面刻画将与茶壶本身契合得更为圆满。
结语:自明清以来,陶刻一度成为了紫砂陶艺创作中彰显品味与雅趣的必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紫砂艺术本身正朝着一条更为大众朴实的道路前进着,陶刻的创作主题也逐渐变得更加的亲切和熟悉,褪除掉高深的文化外衣,紫砂陶刻的文化传承显然是一种适合普罗大众的艺术创作,在陶刻中引入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熟悉而亲切的题材,让陶刻艺术更接地气,能够让更多的人喜爱紫砂,也就能更好地传承我们古老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