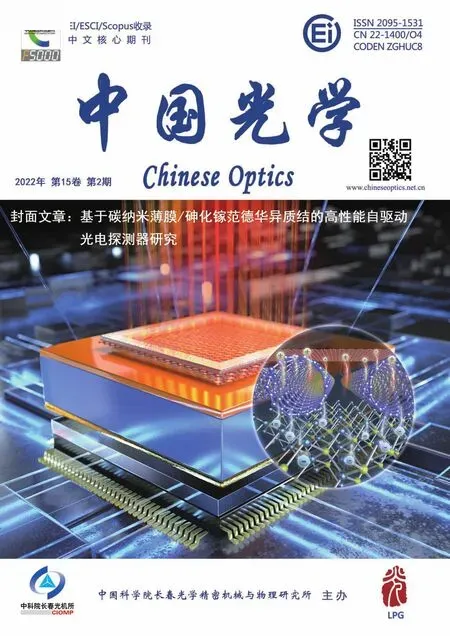姚骏恩院士
人物小传

姚骏恩,1932年4月生于上海市。应用物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1952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后为大连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1952—1964年在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后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工作。1964—200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学仪器研制中心(后为北京中科科仪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3年起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是我国电子显微镜研制和生产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设计并主持完成我国第一台大型透射电子显微镜、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等,促进了国内电子显微镜制造、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率先在我国主持研制完成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光子扫描隧道显微镜等十余种纳米检测仪器和器件,对有关理论和应用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 成长经历
1 历经战乱,曲折求学
1932年4月9日,我出生在一个邮局职员家庭。父亲姚国勲安分守己,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从小教导我们三个子女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他常讲:“每人头上都有一爿天,不要嫉妒别人;要自己努力,不投机取巧;要尊重长辈,助人为乐”。我的母亲唐玉瑛生于1899年,为人正直善良,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她一生跨越三个世纪,享年105岁。一直用端庄贤良深深地影响着我。正是父母的教导、良好的家风激励着我在战乱中不断成长。
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我家从上海闸北宝山路开始逃难,一路上历尽苦难和屈辱,最后终于在“法租界”暂时安顿了下来,是年4月9日,我就在那里出生。1936年秋,在我4岁的这年,我来到上海培成小学开始接受教育。1937年8月13日清晨,日舰用重炮轰击上海闸北,日本海军陆战队越过淞沪路冲入宝山路,我军予以自卫反击,“八·一三”淞沪会战由此开始。我家不得不再次迁到“法租界”,之后我转读了巽明小学。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有点小“聪明”,很是贪玩,不好好读书,常在弄堂里踢小皮球,结果小学三年级时留了一级。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是日,路上行人稀少,形势分外紧张,日军占领了上海法租界。一天上午,我正在家中,突然听到一声巨响,浓烟四处弥漫,断壁残垣上燃烧着火焰,同时周围哭喊声、惨叫声连成一片。我和哥哥急忙跑出去,才知道是日本两架军用飞机在演习时相撞,坠落在离我家仅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几十间房屋瞬间倒塌,我家弄堂对面的房子后半部都被烧为了灰烬。
抗战开始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从漕河泾区吴家巷搬迁至“法租界”的菜市路,改名为私立沪新中学。1943年,我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此。
1946年初,我就读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迁回郊区的吴家巷原址,我第一次离家住校,开始独立生活。是夏,我初中毕业,心想考取自己学校的高中部不会有问题,结果掉以轻心,最终名落孙山。我就先到了上海市复兴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复兴中学的前身是始建于1886年的“麦瑟尼克”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重建,定名为“上海市复兴中学”。 校名“复兴”,含“复兮旦兮,兴我中华”之意。复兴中学的师资和校舍都很出色,离家又近,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不过由于父亲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海中学的前身),哥哥也是该校的学生,我一直希望继续在这个享誉全国的上海中学学习。于是,半年后我又再次报考,结果还是没有成功。我并不甘心,1947年暑期第三次报考,还记得当时的作文题目是“你为什么要考上海中学”,我有感而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终于如愿以偿地再次进入了上海中学。我插班到理科高中二年级,由于我是班上年龄较小的,同宿舍的同学叫我“姚弟弟”。我所在的丁班,虽然考试成绩不如其他几班,但我们不死读书,都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很喜欢运动,如短跑、跳高、垫上运动、足球、垒球、乒乓球等,记得当时我们在课间的时候,曾把老师的讲台临时拉上球网,直接就打起了乒乓球。至今我还保留了那时的一些旧照片,这些记忆也是我一生中宝贵的财富。
2 求学大连,幸遇名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正值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是年,全国高校分区联合招生。我是在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环境下长大,日本飞机经常在大中城市狂轰滥炸,而我们毫无还手之力,在“航空救国”的思想下,我选择了大连大学的电机系,一方面是共产党使我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而大连大学是共产党在解放区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哥哥也很鼓励我去;另一方面是因为该校有一批名师,都是在解放军渡长江前后辗转进入解放区的。此外,我担心父亲失业,家庭经济收入没有保障,无力为我交学费,而大连大学学生享受“供给制”待遇,不仅免交学杂费还提供生活费用,而且在上海首先发榜。父母虽然希望我留在上海,但最终也相信我的选择。于是,我和上海中学的几十名同学一起,乘坐学校包租的火车专列去了大连。
那时,直达东北的火车还未开通,路过南京时,还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到达天津后等待了十多天,考虑到坐船去大连不稳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继续乘火车。在东北广袤的大地上,只有我们这辆“专列”,边修路、边行车。晚间,我们就睡在车厢顶部的行李架和座位下面的地板上。走走停停,从天津到大连竟行驶了好多天。1949年9月底,我终于到达了大连,就读于大连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0月1日,我们这批大学生列队在大连火车站广场上,聆听了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备受鼓舞。
是年年底,为了解我们这批首届学生的业务水平,学校组织了物理学摸底考试。有些考题我在上海中学时学过,所以答题比较顺利。当时我感到监考老师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交卷时老师签名,我一看像是“美術”两字,后来才知道这是老师“王大珩”三个字的连写。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恩师王大珩先生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大连大学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校开办之初,就大力建设实验室。在刚解放的大连,什么科学器材都很难买到。物理系主任王大珩先生亲自带领教师和实验人员,从仓库和旧货市场上淘来旧秒表、天平、望远镜、电位差计和光学玻璃等,自己动手制造仪器。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可同时容纳130名学生做实验的普通物理实验室。
王大珩先生指导学生做实验,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审查实验报告也非常仔细。在给“不对”两字时,故意不说明原因,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有的同学嫌仪器设备简陋,做实验不顺手、太费事,王大珩先生的回答是:“告诉你们一个真理,所有精密的东西都是用不精密的设备造出来的,你们要学会用低级的仪器做出好的实验结果。”他说自己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时,有位老师经常讲,不能给学生好的东西用, 就是要逼着学生学会自己动手。后来王大珩先生告诉我:“1950年在为你们准备钟摆物理实验时,那根挂钟摆的吊线经常断,实验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很着急。后来才发现,是穿过吊线的那个小孔边上有毛刺,把吊线割断了。刮去了毛刺,问题就解决了。” 王大珩先生就是这样以身作则地教会了我们实验要认真负责、重视细节。后来,我们这些学生能独立思考并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与王大珩先生当时的细心培养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1950年秋,王大珩先生动员学生读应用物理。他说:“物理可以说是一切工业技术的基础,再冠以‘应用’两字,对新中国的建设更有现实意义。‘物理人’比单纯学工科的考虑问题更深入些,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知道该去找什么人。”就这样,我们二十个同学成为了应用物理系的第一批学生,我从此开始进入了应用物理学科。大学一年级时,包括体育在内,我各门成绩都是5分,在全校名列前茅,因此我担任了班长,后来当选为校学生会数理分会主席。当时,我的体育老师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教授,他特别擅长短跑,动作步频快、步幅大、向前性好,悉心传授我们的短跑技术和经验,使我们受益匪浅。
3 投身科研,艰难缔造
根据国家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需要,1952年全国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都提前一年毕业。当时王大珩先生已受命在长春市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后改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从各地招收了二十名大学应届毕业生,我是其中之一。当时的长春满目疮痍,还没有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我从设计大礼堂的座椅、采购器材和实验设备开始,日夜兼程、东奔西走,全身心的投入到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的建设工作中。
1953年,我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研制精密电阻箱。研究期间我发现电阻的阻值竟不是书本上所写的固定值,而是天天在变,而且引起变化的原因有很多,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了事物的复杂性。第二年,我又开始研制测量微弱电流的检流计,仅读数不回零的问题就经过数十次试验才得以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书本上没有的,必须自己找出关键所在,“尽信书不如无书”,正是这样的经历培养了我独立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后来看来,这些极为普通的常规仪器,当时却还要在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研制,可见建国初期的科技水平是何等落后。
二 投身电子显微镜事业
1 参与研制我国首台电子显微镜
显微镜是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有力工具。光学显微镜的出现,使人们发现了被称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的生物细胞,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一个极大的飞跃。诞生于1932年的电子显微镜和1982的扫描隧道显微镜,分别作为显微镜发展史上继光学显微镜之后的第二和第三个里程碑,促进了纳米科技的诞生和持续发展。
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把一台该国蔡司公司生产的、代表当时世界水平的电子显微镜(简称电镜),送给毛主席作为六十寿辰的大礼。1956年,我国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时,由王大珩先生领导的仪器规划小组提出要研制电子显微镜。而当时的苏联顾问认为这个项目难度太大,在此期间中国做不出来,不要列入规划,中国如要用,可以向苏联买。但王大珩先生并未因此停止研制电子显微镜的步伐。我当时是仪器规划小组的工作人员和俄文翻译,在此期间,光机所拟送我去苏联国家计量院学习,但因体检发现视觉红绿色弱,不合格而作罢。
第二年,长春光机所又选派我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蔡司公司学习红外光谱仪器制造技术,在中国科学院沈阳干部学院学习了将近一年的德语。年底,一切去德的手续都已办妥,行李也送上了火车,准备第二天出发。可是,当晚接到中国科学院的紧急通知,“暂不去德”。我们以为又发生了类似的“匈牙利事件”。后来才明白,是德国方面要分别“安排”。不久,到大学进修的去了德国,而蔡司公司则不接受我们去学习他们的关键技术,德国之旅未能成行。
1958年,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思想指引下,所长王大珩先生大胆提出在长春光机所研制电镜,并邀请了一位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博士作为负责人,以中国科学院武汉一个研究所刚从日本订购的中型电镜作为参考样机开始研制工作。研制电镜需要解决真空问题,当时光机所只有一台前苏联生产的氦质谱真空检漏仪,在此期间,我翻译了俄文说明书。通过夜以继日的刻苦攻关以及高效的协调配合后,只经过短短的72天,在1958年8月即成功制造了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加速电压50 kV,分辨本领达10 nm。这台电子显微镜作为光机所研制成功的“八大件”(指八项先进的高端光学仪器)之一,于当年国庆节前夕在北京中关村展出。毛主席参观了这个展览会,当工作人员介绍到电子显微镜时,他高兴地说“我们也能做这个东西(电子显微镜)了”,对这些科研成果倍加赞赏。
后来我独自一人去武汉归还之前借来的日本电镜,由于是被拆成零部件后再重新装起来的,问题不少,就连机械泵也发生了故障。当时,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敢把它拆开,清洗精密的旋转刮板后再装起来。我打开不容许用户触动的50 kV高压油箱进行检查维修,并过滤高压变压器油。经反复调试,这台电镜的分辨本领终于恢复到其出厂指标2.5 nm。
此后,该中型电子显微镜向南京教学仪器厂(后改名为江南光学仪器厂)等推广生产。他们在光机所图纸的基础上不断改进,于1961年实现了小批量生产,至1994年共生产了两百多台。
2 共同自主研发电子显微镜
在成功制造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后,有人说,你们能做电子显微镜,很好!但这是仿制的,自己设计行吗?我们了解自主研发面临的巨大挑战,但更加深知这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1958年9月,长春光机所决定自行设计研制100 kV大型电子显微镜并成立了电子显微镜研究小组,由我任组长和课题负责人,电子所的一位专家为技术负责人。
由于我在研制检流计时熟悉了磁路设计,加上具备相关的光学知识和英、德、俄文的基础,参考了国外有关经典文献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西门子公司的Elmiskop型电子显微镜产品样本,很快就完成了电子显微镜总体设计和电子光学系统、电磁透镜的设计,并提出了对加速电压及纹波、透镜电源和真空系统等的要求。经过全体人员十个月不分日夜的辛勤劳动、协同合作,终于在1959年9月末,我们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电子显微镜(XD-100型),分辨本领优于2.5 nm、加速电压100 kV、放大倍数达10万倍以上。
为参加国庆十周年全国工业交通展览会,我们特别包租了一节火车车皮,我和负责机械设计的同志就坐在电子显微镜的包装箱上,星夜奔赴北京。在北京展览馆安装好后,却发现冷却水漏进了物镜线包造成漏电,导致电子显微镜无法工作。当时已是放假前夕,我抱着十几公斤重的物镜找到兄弟单位,用真空烘箱烘干,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抽真空,终于及时解决了问题。10月1日,这台10万倍电子显微镜作为一项重大科技成果,在北京展览馆按时展出,并且摆在了中央大厅的显要位置。观众十分好奇地排起长队等待着用电子显微镜来观看蚊子翅膀上的“汗毛”,这个场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当天,天安门前举行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这台XD-100大型电子显微镜的巨大模型排在中国科学院游行队伍最前面,接受了检阅。
这台电子显微镜被列为我国仪器仪表行业从仿制到自行设计研制的一个里程碑标志,被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之一,并收入了记载古今中外自然科学大事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
长春光机所发扬当时提倡的“全国一盘棋”和“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1958年和1960年先后将仿制的中型电镜和自行设计制造的XD-100大型电子显微镜的全部设计资料和机械图纸无偿地交给南京教学仪器厂和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后改名为上海电子光学技术研究所)。我也多次到上海、南京毫无保留地向他们介绍电镜设计及调试技术。就这样,我国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电子显微镜制造领域。
1960年9月,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电子显微技术交流会,我作了题为“ XD-100大型电子显微镜研制”的学术报告。会议期间我被确诊得了肺结核,11月回到上海家里,肺部已有严重的“空洞”,在接受近一年住院治疗后,才得以再次回到长春工作。
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在XD-100型基础上制成了DXA2-8型电镜,分辨本领达2.0 nm。当时,为了庆贺全国八个具有代表性的新产品问世,邮电部特别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8张),其中一张就是DXA2-8型电子显微镜。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以电子显微镜为主题的邮票。1965年7月,研制成功DXA3-8型一级电子显微镜,分辨本领提高到0.7 nm,通过了国家鉴定。1968年定型了DXA4-10(0.7 nm,100 kV),到1977年共生产了72台。中国科学院新疆化学研究所购置了第一台DXA4-10商用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并利用这台仪器发现了四百多种动植物病毒,不但为我国动植物病毒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这也印证,我国自主研发电子显微镜的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
3 调入北京继续从事电子显微镜研发
1964年4月,根据中国科学院集中力量的决定,将长春光机所电子显微镜研究室包括我在内的13人调并到北京的科学仪器厂(后为北京中科科仪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全厂召开联欢会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
之后,我出任了电子显微镜研究实验室副主任,负责研制DX-2型100 kV透射电子显微镜,主要负责总体设计和电子光学系统计算。在此期间,我重点解决了电子显微镜的“心脏”——物镜极靴的研制和高稳定度100 kV高压电源的问题。
1965年底,中国科学院组织成果鉴定,结论为:“根据在鉴定过程中所拍摄的铂铱粒子照片,测得最小可分辨距离为0.4 nm和0.5 nm 的五对点子。按国外常见的表示方法,DX-2电镜的分辨本领可达0.4 nm。按国内采用从严的分辨本领鉴定方法 (以第五对最近点中心间的距离计算),评定该电镜的分辨本领为0.5 nm ,电子光学放大可达25万倍以上。由此可以认为DX-2电镜在分辨本领和放大倍数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原结论中以埃为单位,1 nm = 10埃)。1966年1月,DX-2型电镜作为重点展品参加了北京全国仪器仪表新产品展览会。 此后,我参与了6台DX-2型电子显微镜的小批量生产。
我指导并参与研制完成了我国第一台扫描电镜(DX-3型),负责人是我的第一位研究生。这台扫描电镜性能达到了1973年我国进口的日本扫描电子显微镜的水平,并且实现了批量化生产。同年,科学仪器厂扫描电子显微镜组获得了国务院总理亲笔题词的荣誉证书,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
我还负责研制X射线波谱仪,并将其和同轴光学显微镜一起配装在扫描电镜上,发展成DX-3A型分析扫描电镜。该型扫描电镜先后生产了近百台,并向国内几家单位推广生产。
1982年出现了扫描隧道显微镜(缩写STM),横向分辨本领达0.1~0.2 nm,纵向分辨本领高达0.01 nm,这是其它显微镜难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STM克服了电镜试样必须处于真空环境的限制,可在大气、真空、甚至液体环境中观察物体在自然状态下的表面结构和实际状态。1986年的诺贝尔奖物理奖即授予了扫描隧道显微镜的两位发明人和50年前(1932年)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创制者。
后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北京电子显微镜(开放)实验室,依托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学仪器厂,我被任命为副主任。我认识到STM大有发展前途,自己又有研制电子显微镜的经验,于是提出自行研制STM,得到了实验室主任的大力支持,由我兼任STM研制小组组长并且赴美调研,不久我确定了设计方案,经过半年多的刻苦攻关得以研制成功。
北京电镜室工作者用自制的STM首次获得了石墨表面原子图像,横向和纵向分辨本领分别达到了0.1 nm和0.01 nm,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8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上的报眼以“我国制成新型扫描隧道显微镜”为题,对此进行了专题报导。该型电镜后续实现了小批量生产。
第二年,在英国召开的第三届STM会议上首次报导了我国研制成功的STM,并选入了会议论文集。我们还在国际上首次用实验验证了一个重要论断,即STM图像不只是试样的像,还与探针有关。
之后,在1989年又诞生了光子扫描隧道显微镜(PSTM),分辨本领突破了传统光学显微镜光束半波长的衍射限制,引起世人瞩目。1991年我又提出研制PSTM,在与大连理工大学物理系的合作下,于1993年6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光子扫描隧道显微镜,图像横向分辨本领优于10 nm,纵向分辨本领为1 nm,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应用研究,不断推动我国的电镜事业跟上世界发展的脚步。
我从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学仪器研制中心退休后,也未停止科学研究的脚步,继续从事发展原子力显微镜的工作。我之前与一位专家合作共同发展了一种国际上分辨率最高的MoS2固体径迹探测器,研制生产了我国第一代激光检测原子力显微镜。
2001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后,老师王大珩先生告诫我“要更加谦虚谨慎,发挥作用”。还有位院士朋友对我说:“当选院士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继续工作”。这些我都铭记在心。2003年我受聘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机会。1949年上大学我报考的就是航空工程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转为应用物理专业,在应用物理领域一干就是半个世纪,这一次可谓实现了我54年前报考大学时为祖国航空事业服务的愿望。对此,我十分珍惜,兢兢业业,只争朝夕,把这份工作当作自己再一次“创业”的机遇,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
我积极开拓学科方向、组建科研团队、引进优秀人才、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先后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筹)首席科学家和理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主持组建 “北航微纳测控研究中心”,筹建“微纳测控与低维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任筹备主任和名誉主任。负责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学技术部等多项专项课题。开展了近场光学显微学、离子束纳米级加工、原子力显微视频成像、高次谐波及多频激励成像、频率调制原子力显微术以及智能化便携式原子力显微镜等研发工作。
我曾在《科学仪器》杂志上发表我国第一篇系统论述电镜设计制造的文章“XD-100型电子显微镜”;撰写了数十篇科普与综述文章,以推动显微镜领域科学传播;多次组织国际和全国学术会议并编辑出版论文集;组办学习班,编写教材,在全国普及电子显微学知识等等。始终致力于促进国内电子显微镜的研制生产和应用。
1980年中国电子显微镜学会成立,我是主要创办人之一;1982年《电子显微学报》创刊,我作为副主编、主编主持日常工作。
三 漫漫电镜路,汲汲求索心
我们实现了多种电子显微镜的国产化,多项产品的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这些国产电子显微镜为促进我国的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发展作出了贡献,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但是改革开放后各种电镜大量进口,促进了外国公司的发展,而国产电子显微镜因使用性能等不如进口产品而竞争力有限,只剩下一个研制单位——北京中科科仪股份有限公司还在艰苦奋斗,小批量生产中档扫描电镜。但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建成创新型国家,我国必须掌握高端显微装备的核心技术,必须自主发展新的纳米测量方法和纳米加工技术。
50余年来,我有幸负责自行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透射电子显微镜;指导、参加研制完成我国第一台扫描电镜,并在国内推广电子显微镜的设计制造技术;率先在我国主持研制完成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光子扫描隧道显微镜等十多种纳米检测仪器和器件,对有关理论和应用研究作出了一些贡献,为发展我国纳米科技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起了先导作用。我对于发展电镜事业心坚如磐,走过的这条路踏实而又厚重,不断的为我国高端电镜的自主可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世纪初,由于种种原因,国产电镜和扫描探针显微镜的质与量还远远不能满足全国的广泛需求。为此,我与王大珩先生等在2003年1月,向国家呈交了“建立我国自己的纳米测量仪器和纳米加工装备制造业”的“工程院院士建议”,2006年初又提出了“振兴我国的电子显微镜制造事业”的建议:
(1)发展具有自己特色、先进的多功能亚埃(<0.1 nm)分辨率、亚eV级像差校正电子显微镜,实现我国在纳米尺度表征与度量的髙端突破;
(2)整合国内现有基础,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电子显微镜规模产业;
(3)创建电子显微镜研发团队,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显微镜研发平台和基地。
国家科技部考虑了这个建议,并将“场发射枪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研制”列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重大课题,推动了电镜产业的加速发展。
其实不仅是国产电镜和扫描探针显微镜,整个中国科学仪器制造行业都面临极大的挑战。国外厂商对中国的策略往往是,你不能制造的精密仪器,他要高价,甚至不卖给你;当你有能力制造时,他以低价销售给你,打垮你,让你难以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自立自强。电子显微镜,从1958年开始我国就做出来了,但稳定性、可靠性不如国外产品。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日之功。生产高质量仪器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条完整的科学仪器产业链。从材料的选择、加工工艺,到整机的装配调试,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注意,每一个细节都需要精益求精,这需要一整套技术标准,才能实现高指标、高可靠性。我们需要一个打基础的过程,一个积累的过程,而这样积累的过程是难以一蹴而就的。只有选择性地把某些仪器做到满足国内需求以减少对国外的依赖,在打好基础的情况下逐步发展我们的技术特色,利用我国己领先的新原理、新材料等来制造新仪器,争取一部分先超越。这样,中国的科学仪器制造事业才能逐渐强大起来。
现在国内已研制生产了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质量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原位观察测试研究的开发与应用研究等。时至今日,我仍在为发展我国的超显微镜制造事业继续努力,展望未来,我必将为这项事业奋斗终生。
回首过去的人生轨迹,有成长的曲折,成功的喜悦,也有未竟的遗憾。从失望到期望、从惴惴不安到信心满怀。我相信,只有经历磨难,生命方有厚度!